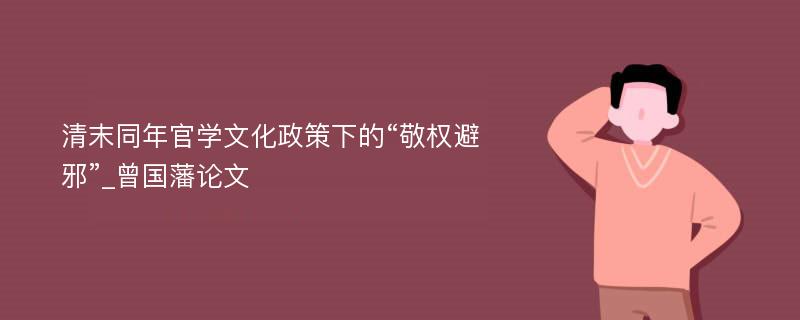
晚清咸同年间官学文化方针下的“崇正辟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年间论文,方针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K252
这里所谓“官学”,是指旧时官方以政治权力来指定和维护的所谓“正学”,与之相悖者则视为“异端邪说”。“官学”的典型特征是学政联体,学为政用。本文拟对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的官学文化方针,以及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崇正辟邪”的一些具体措施,试作论述。
一、“崇儒重道”、昌明“正学”的方针
“宋学”与“汉学”并为官学的局面,在清前期即已形成,进入晚清时期以后在一定时间里仍得以沿袭,但随着具体条件的变化,统治者在宋、汉两学并用方面也自然要有所调适。概言之,突出表现在进一步调和宋、汉两学,淡化其门户分野,将其统归于“儒宗”兼容并包,既张扬“崇正”,又强调“求实”,以图更能结合实际,为维护其政治统治服务。同治元年(1862年)的一则上谕于此体现得颇为典型:
我朝崇儒重道,正学昌明。士子循诵习传,咸知宗尚程、朱,以阐圣教,惟沿习既久,或徒骛道学之虚名,而于天理民彝之实际,未能研求,势且误入歧途,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各直省学政等躬司牖迪,凡校阅试艺,固宜恪遵功令,悉以程、朱讲义为宗,尤应将性理诸书随时阐扬,使躬列胶庠者咸知探濂洛关闽之渊源,以格致诚正为本务,身体力行,务求实践,不徒以空语灵明流为伪学。至郑、孔诸儒,学尚考据,为历代典章文物所宗,理不偏废,惟不得矜口耳之记诵,荒心身之践履。尤在职司教士者,区别后先,薰陶乐育,士习既端,民风斯厚,海宇承平,奇袤不作,于以观政教之成焉。(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引文中的“濂洛关闽”,是分别指濂溪周敦颐,洛阳程颢、程颐,关中张载,闽中朱熹,为宋代理学主要学派的代表人物。)
很显然,它既以“宗尚程、朱”为重(所谓“重道”,“道”,即指道学,也就是理学),又肯定对汉学的“理不偏废”,虽说对两者的地位仍有分重轻主次的隐意,但无疑都纳入所当崇之“儒宗”、所要昌明的“正学”之列,特别是都强调要取其能端士习、息奇袤的实用,防止误入空虚的歧途。这可以视为当时清廷的一种基本文化方针。至于宋、汉两学的功用和关系,不妨借看《清史稿·儒林传》编者的这样一段评论:
综而论之,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踵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学人求道太高,卑视章句,譬犹天际之翔,出于丰屋之上,高则高矣,户奥之间,未实窥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是故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经义确然,虽不逾闲,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注:《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43册第13100页。)这恐怕也很符合当年清朝统治者的认识。清统治者首重宋学,正是因为它以阐扬封建纲常名教为核心,而又不弃汉学,则基于汉学在其名物训诂当中,恰恰又是以探索礼制为要务的,两者可以有机结合,相得益彰。若是离开名物训诂,就失去了“登堂入室”悟道的门径,不能窥得其实际。而“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则会陷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的迷误境地,根本不知有堂室可入。这两种蒙蔽都要不得。如此看两者之间的关系,似可以说是以宋学为体,汉学为用,体用结合,并行不悖。这可视为晚清统治者兼容宋汉两学文化方针的学理基础。其时重臣、名臣曾国藩的有关思想认识的发展成型,可以为此作一个极好的注释。
曾国藩本来是“一宗宋儒”的,但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危机,他从“卫道”而“求治”的现实需要出发,很自然地成为宋、汉兼容的倡导者。他有一段总结性的话语:
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于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赅,源流毕具,虽极军旅、战争、食货杂凌,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注:曾国藩:《复夏弢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在曾国藩看来,“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是把礼视为治国平天下的不二法门,称道“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第2次印刷本,第256页。)正是从推本礼教这一点上,曾国藩认定“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注:曾国藩:《复夏弢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
曾国藩辈既是当时清廷文化方针的自觉贯彻者,又是其文化方针形成的积极促进者,也是其文化方针学术理论基础的奠定者。而清廷这种以融通宋汉为学理基础、以崇儒重道昌明“正学”为主旨的文化方针,向社会贯彻的实践自然是多方面的、多途径的,但归结起来无非是“崇正”与“辟邪”的结合,是正面宣传教育与对反面经验汲取的结合。
二、正面宣传教育的措施
从其正面宣传教育看,起码采取了下述一些措施:
一是整饬文教机构,以求培本端风。
翰林院具有国家文化机关的职能,是高级文士的荟萃之所,对于国家文化方针的贯彻,文化风习的培养,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清廷时有整饬之令。譬如针对翰林院庶吉士专以诗赋“为揣摩进身之阶,敝精劳神,无裨实用”的积习,同治元年十二月间发布的上谕说:“翰林院为储材之地,膺斯选者必须经术淹通,于古圣贤性理精义讲明而切究之,确有心得,将来扬历中外,本其平日所身体而力行者,发为经济,著为事功,方能名实相副……自应将庶常馆课程及散馆旧章量为变通,以求实济。着自明年癸亥科起,新进士引见分别录用后,教习庶吉士务当课以实学,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学等书,随时赴馆与庶吉士次第讲求,辨别义利,期于精研力践……俾士习蒸蒸日上,贤才辈出,共济时艰,有厚望焉。”(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显然,是强调以教习内容的“正”与“实”为指归,戒除虚饰之习,以符所谓“国家芸馆培英,造就人才”之本意。
更常见的是对学校系统和教职官员的整饬。譬如就在上述布谕对翰林院整饬的同时,清廷也对从国子监到各级学校发出整饬谕令。对于国子监,主要是针对其近来“专以文艺课士,该祭酒等既以是为取去,而士子复以是为工拙”的弊端,强调说,“太学为自古培植人才之地,我朝振兴庠序,加意教育”,而国子监作为“四方观瞻”之所,有关人等应“躬行实践,讲明正学,以为表率”,令其“嗣后于课诗文外,兼课论策,以经史性理诸书命题,用觇实学”(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对各级学校的整饬立意亦在于,“自来储才养士,必视学校盛衰”,必须“庠序修明,敦崇实学”。对于学校中出现的与此相悖的种种弊情,清廷认为主要责任是在教职官员失职,并不按朝廷旨意认真训课,自身不正,要求“各省学政务当整躬率属,督饬各教官读书立品,毋为士子所轻,平时训导诸生总以躬行实践为归,勿崇尚浮华,勿虚应故事”(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尽管越到后来学校的趋新变化越加显著,但统治者始终力图坚持不违“圣教礼法”的前提性原则,各类学校中都把教习经书作为必修课程,并强调课时保证,严格限制。
二是奖励“正学”成果,刊印颁行钦定书籍。
对于学人士子刻苦淬沥、钻研“正学”所获著述成果,可由礼部交由南书房审阅,乃至选择进呈皇帝,经审读合意者,给予奖赏。像这方面事例屡有不鲜。仅咸丰、同治帝《圣训》中就记载有多则,如:咸丰元年(1851年)十二月,有上谕奖称江苏举人、安徽黟县训导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一书,“引证尚为赅洽,颇于小学有裨”,对作者赏加国子监博士;福建举人林昌彝撰就《三礼通释》进呈,经南书房校阅后因有“较多脱误”发还, 作者详加校改后再次进呈, 于咸丰三年(1853年)九月被上谕奖以“留心经训,征引详明”,给予作者以教授归部选用的奖赏;同治元年四月,谕奖广东举人、拣选知县桂文灿所呈《经学丛书》四函,“各种考注笺注均尚详明,《群经补正》一编于近儒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诸经说多所纠正,荟萃众家,确有依据,具见潜心研究之国功”,并特别训示:“惟古人通经致用,总以躬行实践为归,经师、人师合为一致,方能羽翼圣经,无惭名教……读书明理必须体用兼备,不徒以记诵训诂见长也。桂文灿既能潜心训诂,不蹈虚靡之习,务当益加刻励,身体力行,勉为有体有用之学,以备国家任使。”曾任内阁中书的张应昌所撰《春秋属辞辨例编》八十卷,经南书房审读认为“原本宋儒,兼及众说,间附按语, 亦颇详审”, 同治九年(1870年)十月有上谕表扬作者“耆年好学,甚属可嘉。”(注:上举数例见《大清十朝圣训·文宗显皇帝》,卷十四,《文教》;《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
鉴于经过太平天国、捻军事变,有关省区各府州县中“旧藏书籍大半散佚,经史板片亦皆毁失无存”的状况,同治六年(1867年)五月间清廷谕令各直省督抚转饬所属,“将旧存学中书籍广为补购”,特别要将“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先行敬慎重刊,颁发各学,并准书市刷印”,旨在“以广流传,俾各省士子得所研求,同敦实学”(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就特别注重的所谓“列圣御纂钦定经史各书”而言,据统计仅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清内务府所刊定的钦定诸书,经部类有27种,953卷;史部类有79种,5738 卷;子部类32种,12479卷;集部类19种,3410卷,共计157种,22580 卷。(注:据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5页。 )昭梿在《啸亭杂录·续录》中这样述说清帝亲自审定节目的事情:“列圣万几之暇,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世之巨观也。”(注:据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5页。)清帝之所以如此, 就是为了只让符合圣学圣道的“纯正”之书占领文教阵地。这从乾隆帝直接干预、控制下编纂四库全书的辑录原则也可进而得以印证,即所谓“离经畔道、颠倒是非者,掊击必严;怀诈挟私、荧惑视听者,屏斥必力”(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晚清皇帝自然也不会放弃这种原则,此番布置购补、刷印书籍的情事,即不失为一个例证。
三是宣讲圣训儒经,普及圣道教化。
本来自清前期就有定期宣讲《圣谕广训》的制度,但“奉行日久,大半有名无实,讲如不讲”(注:《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本,第1册,总350页。)。针对这种情况,晚清统治者屡欲扭转,切实施行。咸丰初年,两江总督陆建瀛进呈新刊刻的《御纂性理精义》和《圣谕广训直解》,并附所定选讲章程,其中拟议“责成教官慎选朴实生员,每月赴乡宣讲”(注:《大清十朝圣训·文宗显皇帝》,卷十四《文教》。),为清廷所嘉纳。同治二年(1863年)国子监司业马寿金奏言“宣讲圣训尤为化导之本,请饬令学臣实力奉行”,上谕肯定了其意见,令“各省学臣督饬教官实力宣讲圣谕,考其勤惰,分别劝惩”,说是如此“庶几经明行修,邪慝不作”(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
四是崇祀“圣哲贤儒”,维护“正学”偶像。
孔子及其他名儒为中国封建统治者所神化利用来作为“正学”的偶像,为时久矣,及至晚清时代,当政者不但没有放弃这一手段,而且进一步强化利用,把它起码在形式上推向极致。这由对孔子的祭祀可以醒目地显示出来。孔子祭典有两次升格变化。一次是在明代嘉靖年间,由群祀升为中祀。再一次就是在晚清光绪末年,由中祀升为大祀,与祭天等最崇之祀并列起来,这中间有一个逐步加尊的发展过程。清朝顺治初年,对孔子定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承旧例以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祀(习称“四配”)庙堂。两庑祀十哲,即闵子骞、冉伯牛、冉雍、宰予、子贡、冉有、子路、子游、子夏、子张。康熙五十一年和乾隆三年,先后分别将朱熹、有若(字子有)升哲享祀,从祀的“先贤”、“先儒”两类,顺治初年分别为69人和28人,以后时有增删调改。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清廷采纳礼部大臣建议,明确如下原则:“从祀盛典,以阐圣学、传道统为断。余各视其所行,分入忠义、名宦、乡贤。至名臣硕辅,已配飨帝王庙者,毋再滋议。”(注:《清史稿》,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0册第2537页。)同治二年,更订增祀位次,各按时代为序排列。至圣先师孔子以及“十二哲”外,在两庑从祀的排位,列东庑者为从公羊高到陆陇其共31人,列西庑者为从谷梁赤到汤斌共30人。并将此绘制图例颁布各省。以后仍陆续有增列从祀者。与此同时,“至圣先师”故里山东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经不断扩建,规模也越来越宏大,典制也越来越严整。
晚清这时对圣哲贤儒之辈祀典的愈发重视,决不单单是一个礼仪形式问题,更主要在于,统治者面临“异端”百出,“圣学”陵夷的危机形势,力图靠对若辈的进一步神化和张扬,强化其“正学”权威,以利维护旧的文化形态和进行思想控制。对孔子辈的崇祀与对儒学典籍刊印推广是相辅相成的。当然,孔子作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化大师,留给后世十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有许多弥足珍贵的精华内容。对其人其学,应该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来认识和对待,而晚清统治者对孔子、孔学的利用,自然谈不上如此。
三、有的放矢地辟“邪”、伐异
道末咸初酝酿和爆发,历时十余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不但对清王朝的政治统治给予沉重打击,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使清朝统治阶级惊呼不迭的一场空前“奇变”。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起义利用了拜上帝教。该教并不等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而是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由具有特定主观条件的洪秀全,利用他可能利用的基督教的一些素材,结合中国传统宗教和文化成分,而创立的一个教种。对其宗教本身的真实面目,清朝统治者并没有能认识得十分详确,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无意歪曲了的。然而,对于太平天国于清朝统治者所认定和极力维护的“正学”,对传统纲常名教的正面冲击,他们是异常敏感和重视的。特别是太平天国的前半期,这方面的声威与其势如破竹的武装斗争相配合,也确实显示出颇为强大的冲击力。
太平军由起义地北进以及定都天京后西征、北伐的进军当中,所到之处不但大量地捣毁从民间所立乃至为官方致祭对象的庙宇、偶像,而且凡“学官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注:张德坚:《贼情汇纂》,卷十二,《杂载》。)。在其都城天京,把孔庙尽行折毁,甚至把孔子牌位劈碎抛于马粪堆里,地主文人因有“大成牌位不完全,委地搀将马粪捐”(注:《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第6册,第389页。)的感叹。清朝的原江宁学宫被改作“宰夫衙”, 文圣之殿堂变为“椎牛屠狗”的场所。对于清朝以及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的儒家经籍,则斥之为“妖书”,在“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之列,甚至曾在辖区大规模地进行搜禁“妖书”的活动,出现所谓“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注: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妖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神州国光社1954年第3版,第4册,第735页。)的局面。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文化态度,其中包含了对传统文化无分析鉴别地一概否定的简单和偏激。不过,这种情况没有也不可能保持太久,很快就有一个宣布“孔孟非妖书”的根本转变。尽管如此,太平天国起义本身就足以让清朝统治阶级深切地感觉到“名教之奇变”的忧惧和仇恨。湘军首领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有这么一番典型的话: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注:《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第2次印刷本,第232页。)
这中间固然有为动员封建士子起而投身镇压太平天国的策略宣传成分,把太平天国利用拜上帝教指认为所谓“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亦不准确,但无论如何,鉴于太平天国当时对若辈心目中正统文化的破坏,惊呼此乃“名教之奇变”,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种观感,而且可以说也是代表清朝统治阶级发出的卫道社会动员。当时,在这个方面清朝君臣上下呼应配合,形成一种浓烈的政治文化氛围。清廷屡屡发布有关谕令,下面举同治二年(1863年)岁末的一谕为例。当时正当太平天国被镇压灭亡的前夕,形势对清朝方面已十分有利,清廷布谕说:
方今大江南北渐就肃清,一切抚绥安辑叠经降旨,责成地方官吏妥为办理,教养兼施,使百姓革面洗心,不致再为教匪邪说所煽惑。(注:《大清十朝圣训·穆宗毅皇帝》,卷十三,《文教》。)显然,是把辟“邪”作为抚绥安辑的要事。
对所谓“教匪邪说”者的指称,其范围应该说是颇为宽泛的,不消说太平天国自在其列,同时,也包括中国土生土长的各种秘密会社、教派,如不乏被利用来组织反清起事的像白莲教、八卦教、天地会、小刀会等。即使对于在当时中国不断加强势力的真正的“洋教”,清方也是存防邪之心、辟邪之意的,只不过不好公然宣明罢了,情况比较特殊。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把“传教”作为侵华手段之一,通过一系列有关不平等条约,不断扩大攫取在华“传教”特权,特别是通过第二次鸦片战争胁迫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之后,中国从沿海到内地都被迫向外国传教士开放,但教方所受到的中国绅民的抵制也是强力的,双方冲突激烈,教案迭出,不但给西方列强方面以羁绊和打击,而且使清朝统治者陷于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不论从有悖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还是列强的借教干政来说,他们对“洋教”都是宁愿认其“邪”而不愿认其“正”的;另一方面,由于被迫在条约中承认了外国在华传教的“合法”性,并且在办理教案的实践中越来越体察到外国在华传教的不可抗拒性,又不得不遵约行事,对“洋教”不但不能公开倡言“辟邪”,而且还要加意保护,对反教臣民进行限制乃至镇压。如果说,他们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种折衷调和境界的话,那么“明保暗防”、“不禁之禁”之类的策略思想便应属之。
同治年间清朝统治集团在关于教案问题的大讨论中,上述策略思想表现得就颇典型。总理衙门在所颁发的供有关大员讨论的函件中就强调:“自议款以来,传教已奉明文,欲于此时禁止,势万难行”,虽然教方迭生事端,但亦惟有“平日联络绅民,阳为抚循而阴为化导,或启其误,或破其奸,是亦不禁之禁也”(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五,页十六。)。其时曾国藩持论:“周孔之道万古不磨”,“但使中国修政齐俗,礼教昌明”,夷教“虽百计开拓,亦终鲜尊信者”(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页三一四。)。李鸿章则提出“明为保护,密为防闲”的原则。按其意思,“明为保护”是鉴于外国在华传教“久立专条”,不得违约,只好采取暗中防范,而其要项之一便是要“崇礼明儒,以资劝化”(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四,页三一四。)。这是当时清朝统治集团中洋务派大员们的典型观点。至于顽固派官员们,因为他们比较坚决地持守着“夷夏之辨”,以“以夷变夏”为大防,更是明火执仗地反对洋教,高扬“崇正辟邪”的旗帜,甚至直接充当反洋教的倡率者。顽固派与洋务派在这方面的表现上似乎大相径庭,其实,从真切政治文化观念上寻根究底,两者间并没有根本性差异,心里坚持的还都是“官学”、“正学”的文化本位。
这个时候,外来文化事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并不仅限于洋教,更有从器物、技艺到政教层面的世俗性内容。正是由于对此的反应不同,遂有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分野,其间产生论争。像同治年间在同文馆问题上的论争即颇典型,此事为人所熟知,不复赘述。这个时期中体西用思想已在雏型初具阶段,并且在官方主持进行的洋务运动中开始得以实际贯彻。总之,当时官学文化所受到的冲击致变因素不仅来自中国内部,而且也来自外洋。不过,这个时期西学的冲击层面还相对表浅,冲击力度还不是特别巨大,而清朝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暂时挽救“内忧”危机,走向所谓“中兴”的过程中,维护其官学文化,从主观到客观都还具备一定的现实条件。而后,随着西学东渐势头的不断加强,同时传统官学文化自身的“异化”因素也在不断发生,到头来,它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对此,拟另文论述。
标签:曾国藩论文; 同治中兴论文; 我在大清当皇帝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晚清论文; 筹办夷务始末论文; 同治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国学论文; 孔子论文; 史记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