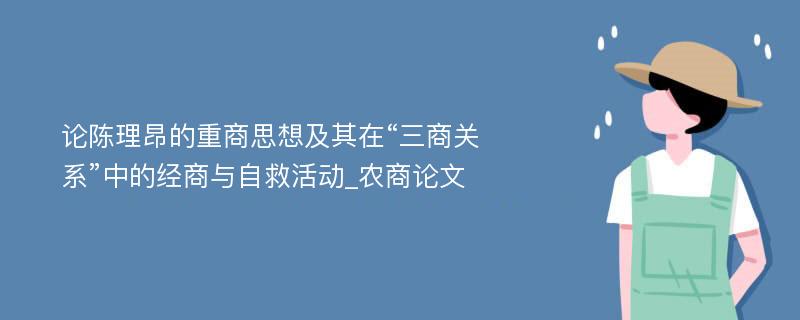
论陈亮“农商相籍”的重商思想及经商自救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陈亮论文,农商相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亮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史学理论家和军事谋略家。他矢志抗金,面对山河破碎、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加剧的严峻形势,五次向孝宗皇帝上书,呼吁南宋当局发奋图强,重振国势。他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主张。其中,在经济方面,他大力提倡发展商业,反对抑制经商,提出“农商相籍”论断,强调农业和商业并重发展,保护商人,肯定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疑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本文在阐述陈亮商业思想的同时,试图论证其通过经商实现自救并得以致富的人生实践,以期更真实地认识这位历史人物和他所处的时代,感受宋代未入仕文人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念和生存状态。
一、时代和环境培育了陈亮“农商相籍”思想
从唐太宗贞观到玄宗开元,将近百年的时间,是唐朝繁荣发展时期,属于江南东道的江浙地区,经济发展尤为迅速。五代十国时期虽然是兵燹战伐的动乱年代,但吴越统治者钱镠为了百姓安居乐业,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与当时的军阀推行兼并掠夺的黩武政策迥然不同,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实行“兴筑海塘,治理潮患”、“经营水利,发展农业”,“奖励蚕桑,振兴越瓷”、“海上贸易,沟通中外”一系列政策;在政治上推行“保境安居,不事兵革”、“礼贤下士,网罗人才”、“扩建杭城,富甲东南”①等基本国策,使吴越经济得到较大的发展。赵宋代周立国,结束了南方分裂割据局面,正如《东都事略》中所云:“天下于是定矣!”②由于社会环境的安定,赵宋统治者在稳定其统治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宋代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和海外贸易在唐、五代的基础上得到了空前大发展。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和全面繁荣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空前的,而“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岁糟都下米百五十万担,其它财富供馈不可悉数”,③“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④到了南宋“高宗南渡,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⑤宋代两浙路在唐、五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的发展、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兴盛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许多方面还居于世界前列。如都城临安既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商业、海外贸易异常发达,城中各种工商行会多达414个。⑥所交易商品不仅来自全国各地,而且世界上四十余个国家的“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⑦单是熟食品供应就不下于二百种。不仅城内如此,就是郊区镇市,其“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⑧而当时的浙东地区也是全国商业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先后涌现出明州、越州、温州、婺州、台州等商贸城市,这些地区的农村集市贸易也十分发达,如叶适的家乡温州永嘉县城“一片繁花(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⑨城内街道纵横,市肆林立,“其货纤靡,其人多贾”。⑩早在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其商税额就相当于当时全国的商税平均数的七倍,这是十分可观的。叶适在《送王宗卿》诗中说:“米多糠少贺丰登,莲吐双花麦五茎。”说明农业大丰收的景象。在《登北务后江亭赠郭希吕》中说:“何必随逐栏头奴,日招税钱三万亿。”(11)此处的“栏头”指外出市场上收税的税吏,每天能收到税金三万亿,“三万亿”未必是实数,但足见永嘉商业发达之盛况。陈亮的故乡婺州所属各县手工业也极为发达,商品交换十分频繁,史称金华县城“民以织作为生,号称衣被天下,故尤富”。(12)婺州属下的浦阳县(今浦江县)“俗善织,凡补吏者,指此邑为膏润。其空囊而来盈装而归者,前后或相继。”(13)陈亮家乡婺州永康县的打铁业,相传早在唐代,在该县方岩镇已有打制菜刀、剪刀、锄头和铁耙,生产兴隆,“百工之乡”正在形孕之中,今天有誉满全球的永康国际五金城,其渊源可追溯到唐宋。
司马迁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4)说明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财富。“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百工、商贾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5)“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16)从事工商业活动是达到富有的最有效途径。宋代两浙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货币经济的冲击波,社会各阶级和阶层产生了对财富占有的强烈欲望,刮起了一股疯狂追求财富的浪潮,许多商人经商致富,追求财富的观念体现于生活的各个细节,有的甚至近于畸形。有一位叫刘钱的商人“唤筭子作长生铁”,“彼日日烧香祷祝天地三光,要钱生儿,绢生孙,金银千万亿化身”。(17)人们追逐财富,“居物逐利多蓄缗钱,至三五十万以上,少者不减三五万”。(18)正如古人云:“钱之所以为之钱,人所共爱,势所必争。”(19)陈与义在《书怀示友》诗中亦云:“有钱可使鬼,无钱鬼抑揄。”(20)当时不仅上自官僚贵族、地主豪绅、富商巨贾,下至平民百姓、太学生等世俗之人对金钱占有都具有强烈的欲望,就连出家的和尚、尼姑以及道士也都视钱如命,说什么“钱如蜜,一点也甜”。当时的浙东地区自然也卷入了这股商业竞争,追求金钱财富的浪潮中,甚至一些著名学者也积极参与经商营利活动,如金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唐仲友,虽然身为台州知府,但仍在台州、金华一带开设店铺,经营织造、印染作坊和采帛铺、鱼鲞铺、刻书铺等行业,取得丰厚的商业利润。在陈亮众多的亲朋好友中,有不少是经商致富的,如永康人孙天诚、陈良能、胡航;义乌人喻夏卿、何大猷、何恢;东阳人何坚才、郭彦明、郭德麟;浦江人方允修、方超等都是腰缠万贯“积累至巨万”的富商大贾。陈亮的岳父大人何茂宏还是义乌的首富。
显而易见,陈亮、唐仲友、叶适等浙东学派的著名学者的重商思想,正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地区特殊的时代和特定的地域土壤环境中诞生、养育和滋润而成的。他们对传统的“重义轻利”、“厚本抑末”、“重农抑商”等观念提出大胆的批评和挑战,明确提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陈亮一再强调“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22)叶适指出:士农工商“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23)要求南宋朝廷重视商业,肯定商人的社会作用,保障商人的合法权益。
二、陈亮“农商相籍”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里,重农思想一直是经济思想的主流,厚本抑末是历代统治者一脉相承的基本国策,这是农业社会的自然现象和有一定合理因素的治国方略。历史发展到了宋代时,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人们的头脑里也渐渐萌发了改变以往把商业视为“末业”的观点,商业逐渐成为社会的“本业”之一,有人已经认识到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24)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果仍然固守“厚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显然是有悖于时代潮流的。南宋事功学派的旗手陈亮则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其事功思想的主导下,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制学、经济学、军事学、史学、教育学、文学、宗教学、社会学等广泛领域的主张。在经济方面,他大力提倡重视农业的同时,关注商业,要求积极发展商品经济。他认为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商业的重要性并不比农业低,相反,在某种情况下,商业的繁荣与发展决定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发展商业可以增加百姓的财富,从而增加国家的财力。
就农业与商业在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地位而言,陈亮认为并无轻重高低之分,他说:“官民一家也,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卷一二《四弊》,第140页)这里的“民”指的应该是中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及佃农和商人。就农商之间的关系,陈亮认为两者是互惠互利、互为促进、互为基础的,“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卷一二《四弊》,第140页)。只有真正做到农商“有无相通”、“求以相补”,经济才能发展,才能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商业的发展对稳定百姓的生活和国家的统治秩序都是大有裨益的。它可以在丰年避免谷贱伤农,在灾荒年月帮助农民渡过难关,若一味抑商,只能使“贫民日以困,货财日以削,卒有水旱,已无足依”(卷一三《问汉豪民商贾之积蓄》,第153页),一旦遇到战事,则很容易导致民愈贫、国愈弱的困难局面,所以商业对于富民强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陈亮就如何发展商业提出了不少有益于社会的主张。
首先,他认为必须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传统的轻商观念支配下,历代统治者多把商人视为不务正业的贱民、游民。因此商人地位低下,他们常常受到许多不公正的待遇。所以,他认为要推动商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商人的社会作用,对统治者来说首先必须正确树立“经商之人亦是才”的思想。成功的商人,其才能决不会逊色于科举之士,而相对于那些汲汲于一日课试之文,“夫以终岁之学,而为一日之计”、“以考求治乱……猎取一二华言巧语,缀缉(辑)成文而为欺罔有司”(卷一四《问学校之法》,第157页)的迂儒而言,他们对社会和国家的贡献更大,理应取得应有的合理社会地位。陈亮对于那些品行端正且有才能的富商巨贾是相当尊重和推崇的,他在给吕祖谦的信中声称自己曾有过从事商业的念头,“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卷二七《与吕伯恭正字·又书一》,第321页),只好作罢。
其次,国家应该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发展商业的政策、措施。政府对商业是扶持还是压制,很大程度体现在税收政策上,政府是否实行宽商政策,直接关系到商业的发展和繁荣。据《都城纪胜》记载,南宋时都城临安“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25)没有或不得加入行会的城市商人,深受“官司上下须索”,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京师置杂买务,买内所需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经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千万者,或云其直,寻给干当……京师甚苦之”。(26)天子脚下的都城商人受勒索的情况尚且如此,至于其属下的州县更是目无法规,自行其是,商人之苦尤甚。“舟船经过,必留旬月,多喝税钱”,(27)使得“巨商大贾,以收敛藏蓄不行。步担力运者,则迂枉小路以避郡县”。(28)陈亮强烈反对向工商业者征收重税和种种敲诈、勒索的做法,认为繁重的赋税剥削和强行科索是导致大批工商业者破产的直接原因,从而造成商业萧条,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当今“民生嗷嗷,而富人无五年之积,大商无巨万之藏,此岂一日之故哉!”(卷一四《问古今财用出入之变》,第161页)这种局面的形成乃是长期以来施行苛商政策的必然结果。“今之为官者,往往或以贿闻,居则争利于平民,而郡县不能禁也;出入则争利商贾,而关、津不能谁何也”(卷一三《问贪吏》,第153页)。“乡必有坊,民与民为市,犹不胜其苦也。而户部赡军、激赏之库棋布于郡县……漕司有库,州有库,经总制司有库,官吏旁午,名曰‘趁办’,而去来无常人,收支无定籍,所得盖不足以偿其费,而民之破家械系者相属也”(卷一四《问榷酤之利病》,第163页)。他认为,朝廷对社会商业活动进行管理并征收合理的赋税以充国用,是无可非议的,但这必须以推动商业的正常发展和促进社会的繁荣为前提。如果朝廷能做到“于保民之间而获其利”,“则必有道也”;反之,若“上下交征微利,则何以保斯民而乐其生哉?”(卷一四《问榷酤之利病》,第163页)
另外,他肯定经营商业的合法性,提倡保护商人的利益。陈亮认为,政府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保护商人,承认商人正当经营的合法性,并保护财产不受侵犯。他对“困商贾之说”提出严厉的批评,“阡陌既开,而豪民武断乡曲,以财力相君,富商大贾操其奇赢,动辄巨万,甚者以货自厕于士大夫之后。此言治者之通患,而抑兼并、困商贾之说,举世言之而莫得其要也”(卷一三《问汉豪民商贾之积蓄》,第153页)。他认为经商是一种正当的谋生手段和职业,与利用各种不正当手段发财致富有本质的区别,不可混为一谈。他还对王安石变法中某些具体做法,如重农抑商、抑制富商大贾的轻商观念、无视商人利益等,进行无情的批判,云:“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括郡县之利尽入于朝廷,别行封椿以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输之法,惟恐商贾之不折也……不知立国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谋国也。”(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6页)“困商贾”不但无助于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使大批商人破产,增加社会失业人员,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从而达不到强国目标的实现。反之,肯定经商的合法性,能保护商人的利益,调动其经商的积极性,使“富商大贾出其所有,亦足以应朝廷仓卒之须”(卷一三《问汉豪民商贾之积蓄》,第153页),这对国家、商人和百姓都是有利的。陈亮主张发挥“强宗豪族”、“富商大贾”在赈灾、维持地方秩序等方面的作用,这一卓见切中了宋朝基层管理的要害,是一项降低治国成本的有力措施。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陈亮并不仅仅只是当时商人阶层的代言人,他虽然积极倡导重商,但并不是因此而走向轻农重商的极端,只是为了纠正历史上诸如商鞅轻贱商贾之令,秦汉强迁商贾之举,西汉、南北朝污辱商人之法,西汉、唐朝掠夺商贾之蛮等等轻商、贱商、掠商的极端偏见,(29)才比较多地强调商业的重要性。事实上,综观陈亮相关的系列论述,他所反对的是斥商为末的贱商观念,对于以农为本的思想,则持完全赞同的态度。他说“农者衣食之源也”,农人“俯首于田亩,雨耕暑耘,终岁勤勤,而一饱之不继也”、“今兼并为农患”(卷一四《问兵农分合》,第164页)。他坚决反对对农民敲骨吸髓般的盘剥,对农业肆无忌惮的摧残,因为从根本上讲,只有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商藉农而立”才能出现商业的持久繁荣,并进而发挥其积极作用,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陈亮列举强秦速亡的例子和汉文帝吸取秦亡的教训,通过采取休养生息、保护农民的政策,使西汉初年一度萧条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西汉王朝也由此走向富强,(30)通过这正反史例说明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的重要性。陈亮在主张重商的同时,把重农劝农列为君主治国之道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治具之綦大者,不过数端而已:制度也,时令也,养老而乞言也,崇儒而重道也,厚本而劝农也”(卷一八《汉论·明帝》,第202页)。说明重农重商,“农商并重”是陈亮一贯的主张。
三、陈亮对“为富不仁”说的批驳,对经商致富精英、楷模的赞扬
马克思认为,商人对于以前由于世袭而停滞不变的社会来说,是一个革命要素。但是,由于世俗传统思想对商人持有偏见,自古以来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有损于商人人格的言论,诸如“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无商不奸”、“慈不主兵,义不主财”、“商人重利轻别离”等,把商人视为奸诈之徒、洪水猛兽,长期加以抑制。即使像孟子这样的“亚圣”大儒也不免发出“为富不仁”等论说。
对此,陈亮从理论上进行批驳。他认为,财富和仁义并不是对立的,“仁者天下之公理,而财者天下之大命”(卷一四《问古今财用出入之变》,第160页)。他强调人为地将义与利、仁与富割裂和对立起来乃是主观之迂见。陈亮还从人欲的角度论述了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必然性。他认为“人生何为,为其有欲,欲也必争”(卷三六《刘和卿墓志铭》,第488页),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欲望,“耳之于声也,目之于色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出于性,则人之同欲也”(卷四《问答下》,第42页)。陈亮强调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并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他认为对于求富欲望而言,对于那些有能力、擅长经营的人来讲,具有现实性,是合情合理的,而对于那些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之辈,那些混混耗耗的闲散懒汉之流是空想。他认为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应该是平均的,提出“高卑小大,则各有分也;可否难易,则各有力也”(卷四《问答下》,第42页)的观点,人的求富欲望有大有小,他们才能有高有低,人为地、强制地抑巨富、求平均只能使平庸者无自知之明而萌生非分之想,走上犯罪的道路,使社会不得安宁;有才者却无故受制约而无法一展宏图。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他还把“大商巨富无巨万之藏”列为“国势日以困竭”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反对平均主义,鼓励合法的经商致富和“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陈亮主张君子之财应取之有道,明确反对为求富而不择手段去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那才是“为富不仁”的表现。
陈亮不仅从理论上对“为富不仁”说进行批驳,而且还通过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和事进行批驳辨正,树立正面典型,作为人们尤其是青年人学习的榜样。现仅举三例为证:
例一:陈亮的朋友义乌人喻夏卿“中年与其侄分田,不过分到百三十亩”,由于他善于营生,勤劳致富、经商致富,到91岁去世时是一位“卒亦几至于千亩”的大富翁。虽然喻氏很富有,但他“友爱子侄,而计较秋毫之心不萌动矣”,“慈恤里闾,而豪夺力取之事不行焉”。因此,陈亮认为像喻夏卿这样在亲族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对他的话“人人常信之”,能“孝友慈爱”,对“亲戚故旧之急难,族人子弟之美事”都能热心帮助而毫无私心的人,怎么能说“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呢?所以,陈亮大声呐喊:“‘为仁不富’之论,盖至夏卿而废矣。”为此,他特以喻夏卿为正面典型来教育年轻一代“孰昭斯铭,以淑我后生”(卷三六《喻夏卿墓志铭》,第482-483页),为年轻一代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例二:陈亮的朋友永康人孙天诚也是既富且仁的榜样。孙氏经商致富绝不是“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而是通过实践经商致富的经典名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而富甲一方。孙天诚经营土地是“勤取啬出,以尽有其土。大较二十年间,富比他人”。他不仅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大商人,而且在家乡大施仁政,行善事,同情扶助贫困失学青年,重视教书育人,且富有成效。同村的徐子才、胡行仲都是贫苦出身的青年学子,而“行仲之贫特甚”,孙天诚不仅没有歧视他们,而且“皆妻以女左右之”,并在他的支持、鼓励下,徐子才、胡行仲双双“联登进士第”,成为有用之才,于是“乡里莫不讙(欢)言”(卷三五《孙天诚墓志铭》,第469页),传为美谈。
例三:陈亮的朋友婺州属县东阳人郭德麟,其父郭彦明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富商巨贾,居然“徒手能致家资巨万,服役至数千人,又能使其姓名闻十数郡,此其智勇必有过人者”。对郭彦明的大智大勇大富本应大书特书、大力表彰的,但由于受世俗贱商思想的影响,加之当时“国家以科举造士,束天下豪杰于规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笔为文,则可曲折以求自达”的社会风气,郭彦明“虽智过万夫”,由于“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没有文凭、学历,因此又“为乡闾所仇疾”。更为可悲的是郭彦明的儿子郭德麟是非不分、黑白颠倒,非但不以其父为荣,反而以父为耻,“固常常惴惴焉以前事为未满也”。鉴此,对这种侮商、贱商、仇商的悲剧,陈亮以满腔的不平,以壮士扼腕的怒吼,写下《东阳郭德麟哀辞》以昭告天下,抒发“解德麟之惴惴而宁其死”(卷三四《东阳郭德麟哀辞》,第457页)的悲愤。
上述三例充分说明世俗对商人抱着歧视和偏见,把经商致富的富商、能人、奇才诬说成“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此类论调在陈亮看来实在是荒谬至极,需要大张挞伐的。
陈亮并不否认存在一些不法商人投机钻营、追求名利,为逐利而完全违背仁、义、礼、智、信道德准则的现象。他清楚地看到商业经营活动中存在许多不正当手段,希望缓解激烈的商业竞争给社会带来的种种不和谐因素。为此,陈亮大力表彰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经商致富成就出众,且又富有人文精神的商界精英、楷模。他对春秋战国时计然重视商业,并提出“平籴论”大为称赞,对白圭最早提出经商应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典名言大力表彰,对越国政治家、思想家范蠡的弃政从商和救济百姓的行为推崇备至。
四、陈亮的经商自救活动
关于陈亮是否曾经从事经商活动,未见有史籍明确记载,但从他本人的文章及与友人的来往信函中可以寻得其经商的证据,从其生活境遇的前后贫富对比也可以推知其经商致富的必然性。
陈亮致友人石天民云:“亮为士、为农、为商,皆踏地未稳,天之困人,宁有穷已乎!”(卷二九《与石天民》,第396页)可以说,陈亮较明白地表示了自己为商的身份。另外,“亮昔尝与伯恭言:‘亮口诵墨翟之言,身从杨朱之道,外有子贡之形,内居原宪之实’”(卷二八《又甲辰秋书》,第339页)。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善于经商的,如果陈亮没有从事经商活动,他不会无故自比子贡。陈亮交游甚广,上自丞相叶衡、王淮、周必大,朝廷大臣章德茂,下至地方官员,如唐仲友、孙伯虎、韩元吉、吴运成等等,另外不论在商业发达的永嘉地区还是在家乡婺州属下的永康、义乌、东阳等地多有经商的朋友,陈亮通过取得他们的帮助,在浙东一带做些生意拥有十分便利的条件。与友人的交往过程中,陈亮借友人的关系并求得帮助从事一些经商活动也属正常现象。他曾致信丞相叶衡:
忽去秋偶为有司所录,俾填成生员之数,未能高飞远举,聊复尔耳。岂敢不识造物之意,而较是非利害于荣辱之场,不自省悟?来秋决去此矣。重以三丧未葬,而无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阙然,每一念至,几不聊生。又羞涩不解对人说穷,愈觉费力;就使解说,其穷固也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辄拜之。相公旦暮归作霖雨,则穷鳞枯枿自应须有生意。西望门墙,跂立依依而已。(卷二九《与叶丞相(衡)又书》,第378页)
陈亮致书叶衡,一方面是谢其援救其父出狱之恩;另一方面述说自身之处境,生活之困窘,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殷切期望得到他帮助之意。另外,吕祖谦曾一度写信劝陈亮放弃经商:“闻便欲为陶朱公调度,此固足少舒逸气,但田间虽曰伸缩自如,然治生之意太必,则与俗交涉,败人意处亦多,久当自知之。恃契爱之厚,不敢不尽诚也。”(31)这是陈亮从事经商活动的又一旁证。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满怀济世抱负的陈亮不先选择通过应举之途改变境遇而是走经商致富之路呢?这与陈亮的家庭境遇密切相关。陈亮年轻时,家境贫寒,他在《祭妹文》中回顾了当时的窘况:“而吾母以盛年弃诸孤而去。未终丧而吾父以罥窐困于囚系,我王父王母忧思成疾,相次遂皆不起。三丧在殡,而我奔走,以救生者。我妻生长富室,罹此奇祸,其家竟取以归。吾弟亦挟其妻而苟活于道旁之小舍。”(卷三三《祭妹文》,第447页)“三丧在殡”,陈亮无力营葬;出自富室的妻子被接回娘家;陈亮弟弟一家寄宿于道旁小舍,内外交困、生活艰难之状跃然纸上。另外,陈亮曾在不同的文章中多次提及早年生活的困苦,如“于是时,余盖七年弗克葬其母矣,蚤(早)夜腐心疾首,不忍闻天下之有是事,惟恐其我告,而敢以问人乎!后二年,始克毕事,因顾谓其友:‘即填沟壑无憾矣’”(卷三三《孙夫人周氏墓志铭》,第489-490页);“晚以三丧不举,无颜对公……故三年丧毕而一吊之未成”(卷三○《祭周参政文》,第407页);“以亮之畸穷不肖,本应得罪于一世大贤君子,秘书独怜其穷,不忍弃绝之”(卷二八《丙午复朱元晦秘书书》,第353-354页);“其后公兄弟相继下世,亮亦坎壈穷困,至为囚于棘寺而未已”(卷三○《祭妻叔文》,第411页)。到陈亮父亲去世时,仍“葬不克自力,乃从人贷钱以葬”,“因得窃衣食以苟旦暮之活,至避宅以舍之……将以明日迁置道旁之居,徒令妻孥以供饮食”(卷三一《先考移灵文》,第414页)。陈亮在《复李唐钦》一文中提到:“亮拔身于患难之中,蚤(早)夜只为椀饭杜门计,虽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卷二七《复李唐钦》,第331页)从中可见,陈亮抱着“以贫为耻,以富为荣”的观念,以与人道穷为羞涩之事。为了解决具体的吃饭、穿衣、温饱等生计问题,陈亮从事经商活动改善生活困境,实现自救具有现实的迫切性、必然性。在仕途屡屡受挫,家境困顿、难以活命的情况下,的确也只有经商才是他的出路。
与早年生活困窘完全不同的是陈亮通过经商致富家道中兴后的情景。在陈亮给朱熹的信中,他详细描述了当时(淳熙十二年,1185)的家境、屋宇状况,阔绰排场、规模之盛,与原先的困苦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反差、鲜明的对比:
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数处小亭子……亮旧与秘书对坐处,横接一间,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对柏屋三间,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围以竹,杂以梅,前植两桧两柏,而临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抱膝之东侧,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颇大,名曰小憩。三面临池,两傍植以黄菊,后植木樨八株,四黄四丹,更植一大木樨于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为桥屋三间,两面皆着亮窗,名曰舫斋。过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间。又作箔水,正临大池,池可三十亩。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驿路。去驿路百步,有一古松,甚大而茂,当是七八十年之松。赤水堂正对之,名曰独松堂。堂后为宁廊一间,中有大李树,两旁为小廊,分趋舫斋。小廊之两旁即植桃。堂之两旁,为小斋以憩息,环植以竹。独松堂寻赤水木未足,度与舫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如偃月,西一头既作柏屋,东一头当作六柱榧亭一间,名曰临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梓亭于其上,名曰隐见。更去西十步,即作小书院十二间,前又临一池,以为秀才读书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两池之东有田二百亩,皆先祖先人之旧业,尝属他人矣,今尽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复何憾!田之上有小坡,为园二十亩,先作小亭临田,名曰观稼。他时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余未有力也。此小坡,亮所居屋正对之。屋之东北,又有园二十亩,种蔬植桃李而已。(卷二八《又乙巳春书之一》,第342-343页)
亭台楼阁,花草树木,一派“楼台侧畔杨花过,簾幕中间燕子飞”(卷二八《又乙巳春书之一》,第343页)的景象。在人地矛盾比较突出的两浙地区,陈亮拥有如此规模盛大、令人眼花缭乱的山庄别墅更说明其富有。此外,陈亮还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置有房屋和芦地,“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买得一两处芦地,变为江上之人矣”(卷二七《复吕子约》,第329页)。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家乡永康到千里迢迢之外的京口购置房产显然不可能。陈亮的财富之盛充分说明,光靠其著书立说、教书讲习是万万不可能做到的。周梦江先生在《试论陈亮永嘉之行及其目的》一文中指出:“单是信中所说田二百亩,按当地市价计算,一亩田值钱十贯,二百亩田就有二千贯钱,已是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中等地主了,靠教书的微薄收入似乎是不可能达到如此富裕程度的。”(32)更何况陈亮除拥有水田二百亩之外,还拥有如上所述的柏屋(抱斋)、桥屋(舫斋)、赤水堂、独松堂、小斋、书院、燕坐、居所等房屋30余间;种植蔬菜、桃李、柑桔的菜园、果园四十多亩;大、小池塘五六十亩(仅一大池就有三十亩);宁廊、小廊、小梓亭等各种亭子回廊数处,加上水田二百亩,其财产之巨,实实在在是一个大地主了。对于陈亮家道中兴的原因,漆侠先生认为以一个教书匠的微薄收入是不可能的,只有经商与放债才可能做到。(33)致富后的陈亮有如此规模之大的房产,琳琅满目的亭台楼阁,风景优美的园林池塘,数十种树木花草之清新幽香,难怪乎陈亮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的满足感:“如此老死,亦复何憾!”陈亮为摆脱生活困境,通过经商,赎回祖上田产,又不断扩大经营家产,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信中所说“今年不免聚二三十小秀才,以教书为行户”,则是陈亮视教育为神圣使命的职业嗜好,是他想把他的学生培养成“浩然之气”、“百炼之血气”,“当得世界轻重有无”(卷二八《又乙巳春书之一》,第347、346页)的雄伟豪杰之人的高度责任感使然,他将其育人观念付诸实施,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形成了独到、系统的教育思想,而绝非是为了区区微薄的一点束修以维持生计。
关于陈亮的系狱,也与他经商致富直接相关。《宋史》记载陈亮系狱有四次之多,而据邓广铭先生考证认为是两次:一次是淳熙十一年(1184),另一次是绍熙元年(1190)冬至绍熙三年春,(34)分别是在陈亮42岁和48岁。第一次狱事之后,陈亮在《谢郑侍郎启》中云:“身名俱沉,置而不论;衣食才足,示以无求。人真谓其有余,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仆射日生之利,子弟为岁晏之谋。”(卷二六《谢郑侍郎启》,第304页)说明42岁时的陈亮已经“衣食才足,示以无求”。陈亮因为富有而招来“乡闾仇疾”,被乡人诬告,才致两度遭受牢狱之灾。这使陈亮在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并造成病痛缠身,暮年的陈亮多次想以死了此一生,这在他的自述中多有提及:“侵寻暮景,行将抱之以死矣。”(卷二七《与章德茂侍郎·又书一》,第315页)“望见暮景,天已与夺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为快脆,其他尚复何说!”(卷二七《复楼大防郎中》,第325页)“望见暮景已自如此,不如早与一死为快脆也”(卷二七《复陆伯寿》,第326页)。晚年体弱多病,原本也是正常现象,但陈亮早年生活潦倒,食不果腹,这势必给身体埋下隐患,加之科场失利,且遭受诬告而入狱,人生境遇之坎坷带来的精神负担,无疑会伤及躯体。人生经历两次狱事,则是陈亮产生厌世情绪,想以死了却一生的直接原因,而入狱则是由于他从事经商致富“为乡闾所仇疾”,受人诬告造成的。因自救而经商,因经商而致富,因致富而招祸,经商的坎坷和现实处境,使他意识到致富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改变他的处境。得到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尊重,具备了一定的经济能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燃起陈亮重新应举的渴望。
陈亮经商的主要原因,是迫于生计,在“三丧不举”、“无寸土可耕”、“贫不能自食”的窘境下,通过经商实现自救,“拔身于患难之中”。陈亮选择经商自救,与他本身具有浓厚的重商思想倾向也是密不可分的,“立心之本在于功利”,陈亮认同于友人戴溪的观点:“财者人之命,而欲以空言劫取之,其道为甚左。”(卷二四《赠楼应元序》,第272页)陈亮经商,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亲友的影响,如前文所提及,陈亮的岳父及众多亲朋好友很多都是富商大贾,他们通过经商而富甲一方。陈亮在科举之途受挫及贫病交错无路可走的境况下势必要寻找出路,而在与亲友的交往中,耳濡目染他们的富足之态,这不但是促使陈亮重商思想形成的一个原因,而且也在无形中刺激其作出通过经商来改变生活境况的抉择。在两浙路商业繁荣的大环境中,在亲朋好友的影响下,陈亮形成了“农商相籍”、“农商并重”的思想,因迫于生计,走上经商致富之路,从而使其商业思想得以付诸实施,并在从事经商活动中重商思想得以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陈亮的经商实践和人生经历也成为他萌生并完善其系列商业思想的源泉,为重商而呼喊,为商人而鸣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切身的感受进而实现了理论的提升。
陈亮所处的时代,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士人的观念已经产生变化,传统的义利观念已经加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像陈亮这样未入仕的文人,迫于生计,选择以经商方式获取生活来源,以商养学,在宋代已是较普遍的现象。
五、余论
当然,确认陈亮曾从事过经商活动,并不否认他的文人学者身份,更谈不上弃文从商。陈亮自我宣称的职业是“以教书为行户”的乡村教师,他只不过是将经商作为谋生的副业而已。在陈亮的潜意识中,宋代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主流意识是刻骨铭心的,是至高无上的。他说:“至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仇疾,而每每有身挂宪网之忧。”(卷三四《东阳郭德麟哀辞》,第457页)信中所说,也正是陈亮自身处境、切身体会的真实写照。他论证商业的重要性,褒扬合法经营的商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切身利益的呐喊。尽管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经商营利成为社会上较普遍的风气,但是经商的合法性毕竟没有像科举入仕那样得到朝廷的鼓励,商人的社会地位、人格尊严及行业价值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肯定,使陈亮在经商的过程中难免产生一种无以言状的自卑感,而且这一自卑感贯穿在他的言谈举止中。例如上文所提及他在给吕祖谦的信中说道:“亮本欲从科举冒一官,既不可得,方欲放开营生,又恐他时收拾不上,”而且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陈亮的存世文章中并没有正面提及他是如何经商发家致富的。无论是出于为宋廷献计献策,为商人取得应有的社会地位辩护,还是为自身经商致富找到合法性的理论依据,陈亮萌发出如此丰富而具体的商业思想是在情理之中。也正是因为陈亮自身有经商的切身体会,使得其来自于实践的理论,言之有理、动之以情,显得丰富、系统而深刻。而在“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有女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成为宋代士人强烈的精神动力的情况下,读书应举成为社会之风气,升官发财成为士人追求的风尚。对于曾在科场上失意而又满腹经纶的“天下奇材”(35)陈亮来说,科举的成败始终是成就一世才名的心结。在他的骨子里,文人应举才是正途的观念是根深蒂固、难以动摇的。再说陈亮一生一再强调做人要做“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卷二八《又甲辰秋书》,第339页)的人,也就是说要做一个能改天换地,对社会有贡献的顶天立地的英雄。因此,作为“人中之龙,文中之虎”(附录:邹质士:《崇祯刻本龙川文集小引》,第566页)的陈亮,虽然在人生道路上惨遭种种磨难,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如木出于嵌岩嵚崎之间,奇蹇艰涩……陆沉残破,行不足以自见于乡闾”(卷二八《又甲辰秋书》,第338页)。当“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卷二八[附]朱熹:《寄陈同甫书·十五》,第375页)的陈亮试图“正大之体,挺特之气,竖起脊梁,当得轻重有无”(卷二八《又癸卯秋书》,第336页)之时,通过业余经商致富,解决了生计问题之后,尽管具有了浓厚“重商”思想和富足的物质生活,拥有令人钦羡的别墅山庄,但最终还是寄希望于通过科举及第,获得社会的真正认可,以实现他抗金统一“欲为社稷开数百年之基”(附录:于伦:《万历刻本龙川文集序一》,第562页)的伟大抱负。于是,陈亮在第二次系狱获释后,迫切希望回到“能把笔为文”的生活中,在他给朱熹的信中低调地提到:“后年随众赴一省试,或可侥倖一名目,遮蔽其身,而后徜徉于园亭之间以待尽矣;其他当一切付之能者。”(卷二八《又乙巳春书之一》,第342页)此后,陈亮参加了绍熙四年(1193)的科举考试,终于在51岁时中了状元,七月授佥书建康军判官厅公事,以实践他“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的宏愿。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考上状元八个月后的第二年,即绍熙五年(1194)三月,陈亮在走过人生的坎坷、崎岖之路,饱尝了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心力交瘁,终因“忧患困折,精泽内耗,形体外离”(附录:叶适:《陈同甫王道甫墓志铭》,第534页),未能实现他一生的宏伟抱负,离开了人世。对于他短暂的人生,时人和后人都倍感惋惜,如李幼武感叹地说:“以同父之才与志,天下之事孰不可为,所不能自为者,天靳之年。”(附录:李幼武:《陈亮言行录》,第545页)同样,明人方孝孺更是无奈地将陈亮的死归之于天意:“余所憾者,以同甫之才,而不得一展以死,又岂非天哉!”(附录:方孝孺:《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第560页)但是他留给后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功利主义思想及其富有开创性的商业思想却是光辉灿烂、永照后世的。至于陈亮为了生计进行业余经商致富的自救活动,不但使他走出了贫穷的困境,为他的学术研究和爱国活动提供了物质保障,而且充实、丰富、完善了他的“农商相籍”的理论体系,也给人们提供了富有传奇色彩的文人经商致富的一段佳话。
注释:
①倪士毅、方如金:《论钱镠》,《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第54-61页。
②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八《隐逸传一百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82册,第769页。
③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九《奏议六首·进单锷吴中水利书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7册,第838页。
④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七之四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4913页。
⑤脱脱等:《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4156页。
⑥参见西湖老人:《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条》,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第22页。
⑦耐得翁:《都城纪胜·井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页。
⑧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九《塌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0页。
⑨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一○《两浙东路·温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930册,第236页。
⑩程俱:《北山集》卷二二《外制·席益差知温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0册,第221页。
(11)叶适:《水心集》卷七《古诗·登北务后江亭赠郭希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64册,第152页。
(12)刘敞:《公是集》卷五一《先考益州府君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21页。
(13)强至:《祠部集》卷三三《送监征钱宗哲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7页。
(14)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458页。
(15)蔡襄:《端明集》卷三四《福州五戒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0册,第625页。
(16)《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第2470页。
(17)陶谷:《清异录》卷上《不动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47册,第847页。
(18)宋祁:《景文集》卷二八《奏疏·乞损豪强优力农札子》,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58页。
(19)余叟编:《宋人小说类编》卷二之一《诗词类·古人咏钱》,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
(20)吴之振编:《宋诗钞》卷四二《陈与义简斋诗钞·书怀示友十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61册,第822页。
(21)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史记·平准书》,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73页。
(22)陈亮:《陈亮集》卷一二《四弊》,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下引此书只在文中夹注卷数、卷名,第140页。
(23)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一九《史记·平准书》,第273页。
(24)陈耆卿:《赤城志》卷三七《风土门二·重本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86册,第932页。
(25)耐得翁:《都城纪胜·诸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90册,第3页。
(26)张镃:《仕学规范》卷一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75册,第102页。
(27)《宋会要辑稿》食货一八之一,第5094页。
(28)《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七之四三,第5090页。
(29)参见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52页。
(30)《陈亮集》卷二○《汉论·帝朝》:“秦始皇为己而忘民,厚己而刻民,重赋苛敛以肆其欲……糜丽之极,未有若此者;”“一旦民力竭,而秦也亡”;西汉文帝则“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籍田先农,明年以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
(31)吕祖谦:《东莱别集》卷一○《与陈同甫》,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0册,第284页。
(32)周梦江:《试论陈亮永嘉之行及其目的》,见陈永革主编:《陈亮研究——永康学派与浙江精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周梦江改变了以往所持“陈亮家道中兴有可能利用妻子嫁妆来赎回祖业”的观点,认为陈亮经商才是其家道中兴的原因,并考证了陈亮四次永嘉之行,其目的是在经商致富。
(33)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80页。
(34)参见邓广铭:《邓广铭治史丛稿·陈龙川狱事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63页。
(35)《宋史》卷四三六《陈亮传》,第129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