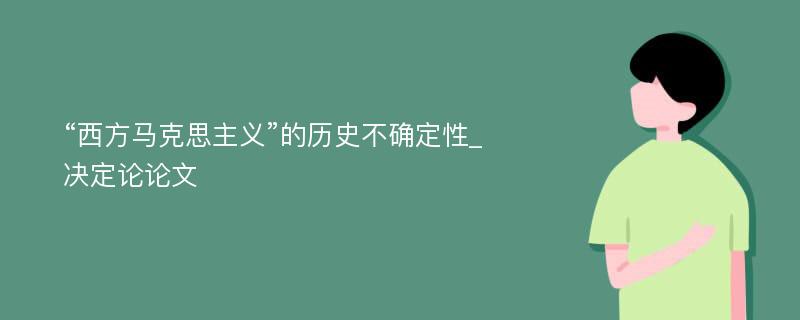
“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非决定论商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决定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人类历史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卷208页。)。唯物史观就是历史决定论。这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但却否认历史有自身的规律性,断言历史是非决定论的,其中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如此。
卢卡奇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的《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出版)一书,被公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书中用“总体性辩证法”取代历史唯物主义,说“总体性范畴的首要性是科学里的革命原则的承担者”,“在历史的说明中强调经济动机的首要性,这并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思想决定性差别,决定性差别乃是总体观点”(注: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所谓“经济动机的首要性”,就是指马克思恩格斯所一再强调的,人要生存,首先要生产劳动。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发展的动力,发展规律性之所在。卢卡奇的“总体性范畴”取代“经济动机的首要性”之后,又把“总体性范畴”界定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历史和思维的统一,认识和实践的统一,说“具体的总体性即是主体”。这样,他将客体溶于主体之中,重蹈了黑格尔纯逻辑的主客体关系辩证法的唯心主义覆辙。他也想凸现实践的历史作用,然而实践又被他泛化为包括人的精神、智力活动在内的一切活动,把恩格斯作为实践例证的实验和工业看作是“直观的”活动,置生产劳动于次要地位。卢卡奇的这些观点,使得主张卢卡奇“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也不得不说:“他对总体性观点的强调是离开历史决定论尤其是离开经济基础决定作用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他把总体性概念对庸俗经济决定论的否定,错误地扩大到对经济优先性、历史决定论的否定”。(注:陈振明:《青年卢卡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和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葛兰西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怨无悔地为意大利和国际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贡献一生。然而,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却步入否定历史决定论的歧路。他说:“问题不在于发展‘决定论’的形而上学的规律,并且不在于确定‘万能的’因果律”。(注:葛兰西:《狱中扎记》1971年伦敦版第94页。)他认为历史规律、历史法则等等概念是早期工人运动由于处于被压迫阶段处于防御地位、没有首创精神时候发展起来的一种“补偿性思想”,是一种原始的准宗教信仰,类同宗教宿命论,对力量弱小的工人阶级能起到一种自我安慰的作用,在他看来,从根本上说,历史规律的说法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历史论定论将成为障碍而需要抛弃。他称自己的哲学是“实践哲学”。历史进程是由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不是由历史法则预先注定的,而是由人的意志决定的。实际* ,他犯了以往许多哲学家犯的同样错误,把历史规律与人的意志和实践绝对对置起来。
法国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著称,强调要从日常生活大众文化批判做起,改变日常生活,从微观达到宏观的“总体革命”,建立他所憧憬的“总体社会主义”,以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的不可扼制的普遍异化的趋向,变革资本主义的“总体专政。”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虽有经济的,主要是政治的、文化的及至心理的,革命如果单纯是经济的和政治的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进行“总体性革命”才能奏效。因此,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是哲学过去的遗物,将消灭在只有自由创造才能创造未来的变革中。说“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所持的经验论的、实证主义的态度和技术至上的观点,只能使人类永远奴隶般地屈从于客观规律。他把恩格斯依照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规律而论证的共产主义关于国家消灭的理论,谈成是:傲慢的”恩格斯背叛了马克思,是“包含着空想主义思想和带有某种风险的设想”。(注:列菲伏尔:《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40页。)
萨特是个著名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他自称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不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却又把历史决定论和辩证唯物主义放在一起加以批判。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辩证法,历史决定论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他清洗了辩证法的客观内容,说辩证法是人的特性,表述人的实践创造。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研究历史客观过程的规律的,只研究人及其实践的,是“历史人学”。而人是绝自由的个体,不存在历史客观必然性的制约。凡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即历史决定论研究人的自由和人们解放的,萨特一概斥之为教条主义,是公式化和形式主义,是“懒惰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照搬,说由于这种懒惰的照搬使“真实的人只成了马克思主义神话中的符号”(注:参阅英国约翰·霍夫曼《实践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萨特对恩格斯如下论述表示不满,恩格斯谈社会,都“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506页。)萨特认为,恩格斯取消了特殊性,限制了辩证运动,窒息了思想。他把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说成是任意使一些因素服从另一些因素的“先验的抽象的计划”,把经济必然性说成是先验的“概念的深刻性”,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断定为先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大流派法兰克福学派,对历史唯物主义表现出特别的热情,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用人的自由创造的理论取代历史决定论。这一学派的主将和曾经被60年代西方造反的“新左派”青年学生奉为导师的马尔库塞,自称坚持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却认为在“本体论”规律和范畴一览表中根本不存在必然性。他极力推崇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思想,大谈资本主义现时代的人们异化,却剔除了异化的私有制的社会根源,成了纯粹精神领域中的异化。他和弗洛姆运用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的观点,分析个体的人心理的、非理性主义的生存状态,把这种生态状态糅合到各种社会矛盾中去,把抽象的人及人的本质的异化当作诠释历史变化的基本原则。他们用人本主义的有色眼睛,把资本主义存在的深刻危机谈成是一场“人的本质的大灾难”,高科技以及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严重压抑了人的本质,人处在“身心贫困的状态”,人成了“单向度的人”,既缺乏批判精神又没有超越现实的欲望。出路何在?他们的结论是,改变主体的个人内部心理结构,扬弃异化。他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生产方式内部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源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核心内容谈成是“外部原因论,是片面的和不正确的。马尔库塞说:“历史命令归根结底是由人所给予的”(注:马尔库塞:《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弗洛姆说:“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注: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他们去掉了经济因素的必然性,必将重蹈人的精神决定历史发展,否认历史存在客观规律的覆辙,历史决定论也就不复存在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人本主义派对唯物史观的修正和否定是多方面的,重点各异,但无不聚焦在唯物的历史决定论上。他们都以人的思想或者实践当作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否认经济因素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地位,进而否定历史存在客观规律性。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人本主义派的研究逐渐多起来,研究论文屡见报刊。这是和他们力图用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揭露批判他们所在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有关的。这有助于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再认识。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影响也多起来。这些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们的历史非决定论的观点,在我国学术界的影响不容忽视。最近出版的《西方社会哲学》的专著,引证了不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材料和论述。该书断言,“社会活动是人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是在意识和目的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不存在以必然性和因果性为基础的客观规律”,主体活动不可能存在着或体现着“不依主体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历史是个“非决定论系统”(注:王守昌:《西方社会哲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历史决定论“是完全错误的”(注:王守昌:《西方社会哲学》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常引证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尚留有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影响的思想,如《1844年经济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人的异化的思想,批判恩格斯关于历史决定论的论述。笔者也感到恩格斯有时候对社会实践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强调得不够,比如《费尔巴哈论》第四章主要论述唯物史观产生及主要内容时,却没有给社会实践以应有的地位。然而,马、恩两人在历史决定论上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那种认为马克思只强调历史发展中的人的活动而否定历史规律性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只要看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经典式概括就一目了解了。在这里,马克思不仅从社会结构视角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并揭示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还从历史发展的演变中阐明了社会经济因素推动着历史发展,从社会的静态和动态两个视角论证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这一论述具有严谨的逻辑震撼力,使读者不得不跟着马克思的思路走。这是每个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熟知的事实。马克思斩钉截铁地肯定了历史决定论。这一事实也无需多言。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作了这样的概括:“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及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多次阐述了关于社会发展遵循客观规律的历史决定论。他也因此招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非难。
恩格斯坚持历史客观规律,承认经济因素否定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无视或贬低人的活动的自主性、能动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有些人硬说恩格斯是只看到经济作用的机械“经济决定论”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曾对资产阶级学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歪曲或误解马克思的观点,说马克思是所谓“经济唯物主义”表示极度愤慨。他在给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成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7页。)恩格斯给约·布洛赫的信中,对人的意识与历史规律的关系作了精辟论述,指出历史规律是从许多单个人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各个人的意志……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4卷,第478-479页。)这就是著名的“平行四边形”即“合力论”原理。它昭示着历史规律不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的某种越世脱俗的尤物,而是人们活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之间本质的必须联系,是人类活动实践的内在逻辑,是通过实践而生成和表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被认识和利用。
“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陷入否定历史决定论的历史唯心主义泥坑呢?
我们认为大抵有以下原因:首先,他们没有挣脱带有形而上学色彩的近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规律观的窠臼。社会规律是人的活动规律受到人活动中的价值和意义因素的影响,变得异常复杂,历史事件不可重复,从宏观上看,主要不是表现为线性因果律。而是表现为统计规律即发展趋势。用刻板的重复性、预测性来量度历史规律,必须得出否定存在规律的结论。当然,自然规律与历史规律不是不可通约的。历史过程的重复性、预测性主要表现为引起事件的原因和结果之间、事件进程决定思想进程、物质关系决定思想意识诸方面的重复性。其次,没能辩证地唯物地理解人活动的自觉性和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应该说恩格斯的“合力论”可解内中疑团。“合力论揭示了历史不是外在于人自觉活动的独立存在,而是内在于、生成于、作用于、实现于人类活动之中的,其客观性是在个体人的自觉活动和各种力量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合力中作为趋势而得以存在、表现和实现的。再次,在思想方法上侧重共时性,忽视历史时性,习惯于就资本主义谈资本主义。他的视野较少地扩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之外。他们偶尔也谈社会主义,或者带乌托邦的空想,或者停留在僵化的有片面性并由他们的偏见扭曲了的苏联模式,很少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基于历史长河的高瞻远瞩谈论社会的未来。如若能忠实马克思主义奠基的思想方法,即从原始社会经过阶级社会三个阶段而到共产主义这样思考问题,历史规律的客观性、重复性以及预测性就比较容易地理解了。
“西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把历史客观规律与人的实践和意识绝对对立起来的思想方法,必然导致否认历史规律走向历史非决定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是自然过程和人的自觉活动过程的统一论,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把人的自觉性和创造性排除掉的倾向,问题在于合理地理解它。
标签:决定论论文; 恩格斯论文; 西方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