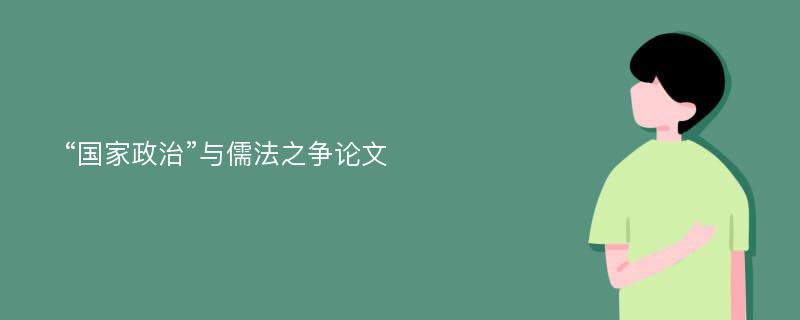
“国家政治”与儒法之争
任健峰, 袁 刚
(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1)
〔摘 要〕 法家对儒家的批判是在“国家政治”兴起这一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法家认为,国家政治是一种“陌生人”的政治,需要打破血缘、脱离伦理、去除人情,才能实现政治的统一、稳定、公平。儒家政治,根本上是一种源于伦理人情的政治,难以完成这一时代任务。所以,必须要将“政治”从儒家的“伦理道德”中分离出来,并建构一种超越伦理的政治道德。因此,法家主要从秩序构建、治国之道、为政之道三个层面,分别对儒家的“德性”“德治”“德政”进行批判、清理。法家的创变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也产生了相应的副作用,但其出路在于进行政治国家的改造,而不是重新将“政治”收入“伦理道德”之中。
〔关键词〕 儒法之争;政治与道德;国家政治;法家
萨拜因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中,将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分为城邦的学说、世界社会的学说、民族国家的学说三个阶段,与此相应的就是城邦政治、教会政治、国家政治。也就是说,“国家政治”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形态,是在分封政治崩溃时产生的,其早期的具体形态就是官僚帝国。虽然中西之间政治发展历程、内容有所差异,但都有从分封政治向国家政治的转变过程。而随着国家政治的兴起,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西方世界最早由马基雅维利、霍布斯等开始隆重地讨论这一问题。而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从尼采到韦伯、施米特等,道德与政治的冲突在对国家有着强烈渴望的德国人那里得到了最集中的显现。在中国,战国时代就开始的官僚帝国构建让这一问题较早地凸显出来,先秦的儒法之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政治的转变对政治思想提出了创变的要求,因此儒法之争实质上是关于政道的争论,而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又是争论的核心问题。此后,这种争论也屡次以不同形式贯穿在中国历次的政治改革、政治运动中。
4.参考文献采用顺序编码制,用阿拉伯数字加方括号在文后标注:引用文献的作者名、引用文题名、出版单位、出版日期和页码。
无论是理论的争论还是现实的实践都表明,虽然道德与政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但政治不可完全脱离于道德,也不可全然地服从于道德。〔1〕因此,我们可以尝试放弃道德与政治简单二分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可以从不同的领域、层面去思考道德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可以将道德分为伦理道德、政治道德等多种。各个领域的道德所遵从的原则是不一样的。至少从法家对儒家的批判,及其相应政治理论的建设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张。法家认为,国家政治的构建必须摒弃儒家的仁政,那就必然要将政治从“伦理道德”的收束中解放出来,而建立一种脱离于伦理的政治道德。从此,便产生了政治道德与伦理道德(公德与私德)的冲突,也自然就有了法家道德污名化的问题,以及法家非道德主义政治的判定。〔2〕然而,我们应当看到这种“非道德主义”实质上“非”的是“伦理道德”,而不是一切道德。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国家政治,而不是道德本身。因此,进行政治国家的改造,而不是重新将政治收入“伦理道德”,才是正确的出路。
一、儒家的“德性政治”
政治秩序本身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因而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政治秩序就有不同的方法,比如依靠习俗、伦理、权力等。在儒家看来,只有伦理关系是天然的内生关系,因而政治秩序的构建需要以伦理关系为基础。任何秩序的存在都是一个系统,都有应对“他者”的机制。伦理秩序通过将亲人伦理向外推及熟人,既而通过“化生为熟”的方式将陌生人纳入“亲—熟”的伦理体系中,扩充以血亲为中心的秩序格局。由此而来,政治秩序的构建就可以通过与“家”的同构或扩充而实现。家庭伦理就外推为政治规范,仁义孝悌转升为三纲五常,如《尚书·洪范》中“天子作民父母”,《大学》“乐只君子,民之父母”等。《论语·学而》中所言,“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作乱者,鲜矣”,及《论语·颜渊》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为明白地体现了这种伦理与政治的同构。
从图8(a)、图8(b)可以看出,带内误差补偿前,成像场景中强目标距离向旁瓣很高,远端旁瓣数值也较高,会遮盖周围弱目标,成像效果很差。经过带内幅度和相位误差补偿后,旁瓣数值降低十分明显,远端旁瓣对周围目标的影响非常小,成像质量得到明显改善。综合以上处理结果可知,子带内幅度和相位误差得到了有效的补偿。
在法家看来,无论是“仁爱”还是“兼爱”都是以伦理的方式应对政治问题,必须“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政治与伦理有着本质的差异,政治秩序的构建必须彻底抹除伦理道德的底色,从其国家起源论可以看出:
儒家方案使得政治秩序的构建与扩张很“自然”,但同时会面临一种应对陌生人所需要的“普遍性”“统一性”的压力。因此,由伦理而道德,再将道德深入人性,为政治秩序奠定更深刻、更普遍的基础,就成为儒家理论必然努力的方向。在孔子思想中,“仁”是对源于伦理的道德的总称。但是,孔子对弟子问“仁”的回答却各不一样,如“爱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恭宽信敏惠”,“克己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种“不稳定性”迫使孟子不得不将源于人伦的“仁”上升为人的普遍本性,而有恻隐、是非、辞让、羞恶等德性,这也是人的情性。正是这些性质支撑着“人”的存在,政治秩序也应该是这种情性的扩张和实践,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因此,儒家的伦理政治也就是基于伦理的“德性政治”。政治秩序就是一种“德性”的秩序,政治的目的就在于践行人伦道德,扩充、实现人的这种情性,使人成其为“人”。故孟子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以“德性”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德治”也就自然成为儒家的治国之道。国家治理的关键就在于以“德”来维持相应的秩序、分配政治资源,其核心就是“把政治收摄在道德教化中的‘政教合一’的模式”,“以道德教化为政治,化政治为道德”。〔3〕仁义道德就成为人才选拔与任用的依据,“君子”人格必然成为治国者应有的素养。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论语·子路》)国家应当以高尚的道德之“士”“君子”来组建官僚体系,以“正人先正己”“道之以德”的方式来管理民众,将政治参与变成人格修养、道德实践必不可少的环节。坚持“义先于利”的原则,用仁义道德调节利益矛盾、分配政治资源,以爱民之心发展生产、轻徭薄赋、富而教之。
虽然从分封制到官僚帝制公私之分的内容和形式有所差异,但都是国家治理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公私问题事关政治稳定、政治公平,因此“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商君书·修权》)。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法家认为“德治”作为治国的工具和方法,不仅无济于事,还会干扰政治的正常运行,儒家主张的“以德治国”被法家称为“以乱治国”。无论商鞅还是韩非都对儒家提倡的道德进行了猛烈的批判。比如,“国有《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商君书·农战》),“奚谓以其所以乱者治?夫举贤能,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商君书·农战》),“任贤,则臣将乘于贤劫其君”(《韩非子·二柄》),“行义示则主威分,仁慈听则法制毁”(《韩非子·八经》),等等。在国家治理中,儒家所主张的道德被视为“虱害”“奸私”“隙蠹”,原因就在于“德治”不利于维持政治稳定、查验政治真实、实现政治公平。
由“德治”上升为“德政”(仁政),就是儒家的为政之道。仁政就是行“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根本的逻辑就是“推”。由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便可“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之掌上”,“仁政”就成为最正当、有效的政道,是王天下之道,“为政以德,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孟子·离娄上》)。上古的尧、舜、禹等皆行仁政而王天下,“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政,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孟子·离娄上》)等。儒家进一步将仁政赋予历史理性,成为人之德性、政治理性与历史理性的统一。
如果说国家政治秩序的构建是要应对陌生人“争利”出现的混乱,那么国家的治理就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对“陌生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合理地分配。先秦时期,乃至中国整个传统政治中最核心的利益分配问题就是“公私之分”,也即儒家所关注的“名分”“义利”问题。先秦的“公私之分”并非现代政治中公共权力和个人权利的分野。公,最早是对人的尊称,如公刘、古公壇父等,后逐渐演变为对王侯、国君等的指称。私,同样指人,是指与公相对应的家臣、家奴、民人等。春秋时期,“‘公’是指大氏族所有者,‘私’是指小宗长所有者,‘公’是指国君以至国事,‘私’指大夫以至家事,所谓‘私肥于公’,是政在大夫或‘政将在家’的意思,私并不是私有土地的私,孔子‘张公室’,‘抑私室’,就是为国君争权”〔8〕。
二、法家的批判之一:德性与秩序构建
墨子最早对儒家提出全方位的批评,主要是“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弦歌鼓舞,习为声乐”,“厚葬久丧”,“以命为有”(《墨子·公孟》)。墨家认为,儒家的仁政不信鬼神、要求厚葬、重视礼乐、安生信命等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政治失败。仁政源于仁爱之道,因此墨家以“兼爱”相抗衡。事实上,正是“兼爱”之道击中了儒家思想的软肋,即无力应对“陌生人”的问题。
然而,在利益面前个人道德是经不起考量的,很容易会沦为利益的说客。任何利益集团也都可以利用相应的道德来掩盖背后的私利,以一副道德的面孔出现。如《韩非子·八说》所言:“为故人行私谓之不弃,以公财分施谓之仁人,轻禄重身谓之君子,枉法曲亲谓之有行,弃官宠交谓之有侠,离世遁上谓之高傲,交争逆令谓之刚材,行惠取众谓之得民。”同时,道德的评判往往需要言论的支持,政治主体就可以操控言论进行道德美化,所以“任德”必然导致“任言”,继而助长沽名钓誉、言论操控、朋党勾结。而在权力的压制下,道德很容易被其俘获,成为权力的婢女,出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仁义存焉”的道德异化。因此,在政治利益的驱动下道德会成为“藏私”“藏奸”的场所,形成道德、话语、权力的合谋,不利于统治者查验政治真实,损坏政治公义,增加治理成本。
其实,这也就是费孝通曾说的“同心圆问题”〔4〕,即儒家以人伦道德为基础来构建政治秩序,其秩序格局必然呈现一个水波状的同心圆形状。这个同心圆是一个差序格局,离中心越远则力量越小。如此,便难以形成统一的、稳定的、有力的规则,自然就难以应付“陌生人”问题,必然会出现秩序的碎片化与多中心的问题。“兼爱”就是为了消减这个“同心圆”的层序问题。墨子当然也看到“兼爱”之道的实现必须依靠政治的力量,要“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墨子·兼爱下》),因而墨家主张的“政治”有一种与伦理分离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其“兼爱”的追求又试图将政治拉回到伦理道德之中,这又造成了墨家理论内在的冲突。同时,“兼爱”虽然可以消减“仁爱”产生的差序格局问题,但却有消灭“圆心”的危险,因而被孟子称为“无父无君”之论。因此,虽然墨家看到了儒家理论的重大问题,但“兼爱”之道的问题似乎更为严重。所以,即使墨家多方批评儒家也没能颠覆儒家的理论,反而顺利地被儒家所吸收。
停站时间主要由列车与屏蔽门开关门时间、乘客上下车时间、司机确认信号时间构成。其中,列车与屏蔽门开关门时间由车辆与屏蔽门的具体性能确定,对于系统而言属于常量;乘客上下车时间由运营方根据各站的客流量进行设置,对于线路上的各站而言也属于常量;关于司机确认信号时间,随着近年来信号系统的不断完善提升,能够确保在不用司机确认信号的情况下、条件满足后也能安全地发车离站。
1)基于授课过程进行评价。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可在每次课后对课堂教学进行评价,授课教师在课后可以看到学生的评价结果,以判断学生对自己本次授课的满意程度,从而主动发现问题并加以总结改进。在一个学期内,经过一段时间的授课或者课程全部结束之后,教师已获得学生多次评价,从评价结果曲线可以判断学生对自己一段时间内授课内容的接受程度,也可以看出学生对授课内容中不太满意的章节,便于后续的复习总结中有所侧重。同时,学生在每次课后评价中也可以以文字形式更加具体直接地向教师反馈意见,便于教师在后续课程中改进。
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也,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当此时也,民务胜而力征。务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正,则莫得其性也。故贤者立中正,设无私,而民说仁。当此时也,亲亲废,上贤立矣。凡仁者以爱利为务,而贤者以相出为道。民众而无制,久而相出为道,则有乱。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财、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既立君,则上贤废而贵贵立矣。(《商君书·开塞》)
法家同样赞成伦理关系是人类最自然、最基础的关系,人类早期组织都以“亲亲”为基本准则。但是,“亲亲”也就自然有了“分别”,而“分别”也就必然会产生“争夺”。因此,要定分止争就不得不建立更具普遍性的“仁义中正”,“亲亲”扩张为“尚贤”。这也正是孟子要将人伦规范上升为普遍意义的人之德性的原因。但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分化,“仁义中正”难以应对“民众而无制”的问题,即无力在大规模的共同体中建立统一的、有力的规则,必然再次陷入混乱之中。此时,唯有建立国家政治,以“尊官”“贵贵”取代“尚贤”“亲亲”,方可止乱禁暴。也就是说,历史的发展要求人类必须构建超越仁义的政治国家方可继续存在,而要建立超越家族主义的国家政治体系,就必须否定伦理道德对政治秩序的支配。虽然,儒家主张的“德性政治”似乎能让政治充满着人性“情”“爱”的温暖,但人类却会囿于这种温暖而难以进一步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否定以伦理道德来构建政治规则,将政治与伦理道德分离,将所有人都当作“陌生人”来对待。“陌生人”之间是一种利益关系,而非伦理关系。同时,“陌生人”之间往往是一种疏离的、戒备的、冲突的关系。因而,“陌生人”之间的“利”往往是冲突性的、不两立的。因此,“利”必须作为构建政治秩序首要考虑的因素。虽然孟子同样看到了“上下交征利”的问题,但在儒家的逻辑中,“利”是一个被决定的问题,即“上下交征利”是不讲仁义道德的结果。在处理义利关系时,需要遵从“义先于利”,要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儒家始终将“利”包裹在“道德”之内,这实则忽视了“陌生人”的天然性存在。
为此,法家大肆渲染人性好利,以及各领域的“异利”“争利”。如,经济中农商本末之间,“粟生而金死,粟死而金生。金一两生于竟内,粟十二石死于竟外”(《商君书·去强》);家庭中父子夫妇之间,“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韩非子·备内》);政治中君臣上下之间,“君臣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亲也,而群臣之毁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贤圣之戮死哉”(《韩非子·奸劫弑臣》)。这种好利、争利、异利的逻辑被法家发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让人以为法家尽是些六亲不认、无父无母之人,令人不寒而栗。实际上,法家的这种冷酷并非是“事实”描述,而是“价值”主张。也就是说,国家政治秩序的构建应该要将每个人都当作“陌生人”来对待,不别亲疏贵贱,并且应当以“好利”的逻辑为基础。商君有言:“非疏父子而亲越人也,明于治乱之道也。”(《商君书·修权》)这并不是法家的阴暗狠毒,而是秩序构建的需要,只有将每个人都当作陌生人来对待,才能最大限度地建立起统一的、稳定的政治秩序。
采集节点的数据经GPRS网络传送到上位机后,经MatlAB7.0处理后,得到的土壤水分含量盐分补偿前后效如图6所示。未补偿时, 由于土壤盐分Ts的影响,EC-5高估实际水含量θ′,且偏差Es随Ss的增大而增大;θ′越大时,相同的Ss引起的误差较大,最大误差为0.098 4cm3·cm-3。经过补偿后,精度可达0.15%,θ′越大补偿精度越高(MSEmin=0.091 1),因此选择合适的LS-SVM训练参数,可以得到较高的训练精度。
因此,法家的这种无情和冷酷并不是一种道德上的恶,而是一种深刻的实践理性。〔5〕现实社会不能保证纯粹理性所设定的那种“普遍”,任何事都存在例外的可能,所以法家并没有将这种“好利”情性绝对化,而是看到人既可以超越名利,也可以舍生求利。所以,法家在政治秩序构建上所追求的这种“普遍”,并非是哲学意义上的“所有”“一切”,而是“多数”。因此,法家主张,“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韩非子·显学》)。所谓“适然”就是反常的、特殊的,“必然”乃是多数的、经常的。所以,韩非的“必然”与“适然”并不与哲学上的“必然”与“偶然”,而是“多数”与“少数”。韩非说:“未有天下而无以为天下……此殆物也,治国者不以殆物为要,而以常者”(《韩非子·忠孝》)。所谓“殆物”就是“犯刑趋利,忘身之死者”的盗跖,以及“未有天下而无以为天下者”的许由等。任何政治体系都不可能获得所有人的认同,说“不”是人的本性能力。因此,治国的主要对象是除此“殆物”之外的“多数”,而政治秩序的构建也当以“多数”为基础。因此,法家所主张的“必然”就是要不断地去寻求“多数”,扩大“多数”。而这,正是典型的政治思维,是政治行为特性和功能的体现——“争取多数”〔6〕。
先秦是一个由血缘社会向政治社会转型的时期,打破血缘来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的、集权的国家是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政治任务。〔7〕此时,君臣之间早已不是血缘同族,剧烈的社会动荡也让人际之间形同陌路。此时政治秩序的构建首要的就是将个体从原有的伦理关系中剥离出来,把每一个人都当作“陌生人”来看待。在这样的前提下,构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来解决“陌生人”之间“争利”的无序与混乱,尽可能多的将天下“异利”的“陌生人”维持在一个完整的政治共同体中。而政治国家首要的特性就是对强制性力量的需求和垄断,只有以此为后盾才足以应付这一问题。这就是法家所坚持的“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厚德之不足以止乱也”(《韩非子·显学》)的原因。
三、法家的批判之二:德治与公私之分
总之,虽然先秦儒家并没有西方“政治”的观念,但是从其思想中可以析出相应的政治思想。儒家认为,政治应当是一种“德性政治”,这种德性源于人的情性,也就是人伦情感,其核心就是“仁”。政治秩序的构建应当以这种德性为基础,这也就决定了儒家政治秩序与伦理秩序的同构性、一致性。与此相应的治国之道,就是通过扩充人的这种德性,来实现“义先于利”的政治分配方案,即“以德治国”。仁政即德政,是儒家的政道,体现了儒家政治的根本逻辑,及运作政治的根本方式——“推”,通过“正人正己”“推己及人”由家庭亲族而国家天下。由此,法家对儒家的批判也正是从这三个层面逐步展开。
由此可见,分封制时期的公私之分主要是指国君与诸侯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孔子“张公室”“抑私门”就是要解决诸侯博大而造成对君主和分封制度的威胁。战国时期分封体系的彻底崩塌,以君主为核心的官僚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官僚政治中,官僚受君主的任命而成为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是不能谋取个人私利的。因而由国王“分封”转向国君“任免”,必然使公私之间的对立更为激烈,理所当然地由春秋的“张公室抑私门”转变为战国的“立公去私”。“公”就成为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整体利益、天下利益,“私”则是与“公”相背离的个体私利。所以法家认为,“背公谓之私,自环者之为私”(《韩非子·五蠹》),“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污行从欲,安身利家,人臣之私心也”(《韩非子·饰邪》)。法家这种激烈的态度,正是官僚帝国构建中公私冲突的直接反映。
“任务驱动法”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上的教学方法,是基于探究性学习和协作学习的一种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以“任务”作为学生学习的主线,把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巧妙地设计在独立的任务中,使学生通过完成任务来学习知识和提高技能。实训以情景引入,将模块知识点融入案例,明确相应的操作要求和教学任务,给出具体的步骤引导学生边学边练,自主完成学生任务。
因此,小孩若有脾胃疾病如食欲不振、厌食、腹泻、便秘,肺系疾病如反复感冒、咳嗽,神经系统疾病如夜啼、睡眠不安、爱哭闹等,捏脊疗法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其中,因在治疗小儿食积、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方面疗效尤为突出,故捏脊法又有“捏积”之称。
首先,明分公私先要明辨公私,这是统治者进行利益分配的首要任务。现实政治中,利益主体间的关系异常复杂。统治者时刻都会受到各种利益主体的围攻、引诱、欺骗。在君主政体中,君主处深宫之内,远离事实现场,一切论断皆凭官僚陈说。加之世袭政体具有君主的不断平庸化的弊端,以君主一人之力更不能应付这样的困难。因而在国家治理中,就必须要有便捷、简省、有力的工具,才能保证统治者对政治事实作出明晰的判定,作出正确的裁定。换句话说,就是要利用相应的手段、工具、方法,让统治者能够明辨是非,明察秋毫,让君主变成“明君”。统治者在政治生活中保持“明”的状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才能防止被利益主体的蒙蔽、甚至威胁,才能维持政治稳定。
式(1)中,r(h)为半方差函数,h为分隔两样点的矢量,称为步长;N(h)为被向量h间隔的实验数据点对的数;Z(xi)和Z(xi+h)分别为区域化变量Z(x)在位置xi和xi+h处的数值。式(2)中,D为分维数值。样点方差在N-S(0°)方向变异最大而且有意义,因此选择此方向作为变异函数结构的分析。
更为严重的是,统治者一旦被蒙蔽,就容易被操控。在君主政体中,被操控的君主就会面临被弑杀的危险。君主被蒙蔽,是非曲直的判断就会被奸臣所掌控。久而久之,奸臣就会逐步成为位高权大的重臣。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人的功利特性会导致群臣趋炎附势、朋党横行。而一旦重臣党羽的势力不能得到及时的遏制,就会威胁到君主王位的稳定,严重者弑君篡国。而这,同样可以在道德的旗号下进行,并通过权力对历史的改写而成为道德的榜样。在此极端之处,伦理道德与政治生活的悖论便显现出来。以儒家所尊崇的尧、舜、禹、汤、武等为例,事实上,尧舜为人臣而臣其君,汤武为人臣而弑其主,而他们却又成为天下赞誉的圣贤。由此就有:汤武弑其主是道德的,汤武弑其主是不道德的;汤武不弑其主是道德的,汤武不弑其主是不道德的。作为政治行动者的法家,对这种“两可”“两不可”的悖论极其厌恶,这会在治国理政的行为中产生巨大的困扰,而尧舜汤武之道会成为臣下的“谋逆”之道,危及政治安全。
道德不可作为知人论事的工具和标准,也不可作为利益分配的基本规则,否则会损害政治公平。这就是“定分”的问题。《商君·定分》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卖者满市,而盗者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定分”就是确权分利,是决定治乱的关键。法家认为,“定分”必须要公平、公正,要达到“上下称平”。《商君书·去强》说:“国无怨民曰强国。”无怨民就是要公平、公正,政权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才能凝聚民众力量成为强国。《慎子·威德》有言:“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蚓蚁同矣,则失其所乘也。”龙蛇飞游,就在于云雾的支撑。政权同龙蛇一样,而云雾就是绝大多数民众。所以,只有建立公平公正的分配制度,才能将绝大多数力量吸纳到相应的政权中。而公平公正的分配规则必须要有明确、清晰的标准,不可模糊。因此,“论功行赏”应当是政治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由于道德的评判往往缺乏明确的标准,其规则会随着具体的情境改变而难以作为政治资源分配稳定的、统一的依据。
将道德与利益挂钩不仅会异化道德,更会侵蚀国家存在的根基。政治国家,是“一套以执行权威为首,并或多或少是由执行权威加以良好协调的行政、政策和军事组织”〔9〕。军队和财政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因而在传统农业国家中,政治资源的分配也就必须充分保障“农”与“兵”的政治公平。法家认为,“善为国者,其教民也,皆作壹而得官爵,是故不官无爵”(《商君书·壹言》)。“作壹”就是农战,以农战功绩来分配政治资源是最清晰、公平的规则。因此,以“道德”而得“官爵”实则是对此时作为国家根基的农战之士的不公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若“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商君书·农战》)。所以,如果有一人可以通过不公平的手段很容易就获取了政治利益,那么就会鼓励整个社会以不公平的手段谋利。事实上,正是有了这种公平的分配制度,才使得秦国的国家构建快速、有力。所以,“立公”就在于以公平、公正、明确、统一的制度将个体的正当利益和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这对大国的简省治理至关重要。因此,就工具和方法而言,立公去私不可以德治国,这也是法家批评儒家有“治人”而无“治法”的原因。
四、法家的批判之三:德政与王天下
既而,由仁心“外推”仁政而王天下的方案就必然成为政治空想。儒家认为,仁心无关私利,因此仁心可以成为政治所需要的“公心”。统治者的任务就是由仁心而行仁政,以仁政来扩充、实现个人善的潜能,最终成就个体的完满。与此相应,个体对统治者的服从也就是对仁心的服从,对自己的服从。而法家认为,在“以不忍人之心”和“不忍人之政”之间缺失了最重要的一环。仁心,是“存在”的问题,而仁政却是“实践”的问题。因此,儒家并没有真正给出由仁心“外推”仁政的真实条件。如果统治者看到民众“皆务为利”,却依旧要求“义先于利”,那么仁政若要避免失败,就必然要以极权主义的方式推行,而这就必然与仁政相违背。因此,统治者要将仁心上升为仁政,就必须首先论证仁政的合理性、有效性。而这,正是仁政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因为在法家看来,一个人不会因为另一个人的仁爱而产生政治服从:
孟子通过设置“乍见孺子将入于井”这一特定场景,“内推”了仁心的存在,且仁心与私交、名利皆无关系,成为人之为人的必备条件。单纯从对人的认知而言,“内推”本身并不成为问题,而一旦放置于实践领域中就需要用现实来考验了。虽然人人都会在“孺子将入于井”时产生“怵惕恻隐”之心,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人在政治领域中依旧能够保持这种善良。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设定其它特定的场景,同样以“内推”的方式,论证人还具有其它“心”的存在。人是社会的人,对人的考察必须立足于社会历史的“变”,这种“推”的方式实则忽略了人心的“变”,由此政道的选择也就丧失了社会历史基础。因此,法家认为体察人心不能以“推”的方式,而应该是“描述”,人更多的是由环境塑造、社会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要走出“特定场景”的限制,整体的、直接的、历史的去把握。
由此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受区域经济发展变动影响较小,土地综合承载力提升主要依靠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承载力的有效互动、协调发展。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提高很大程度上依靠土地潜在综合承载力的挖掘,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能力的增强能够助推区域经济第二、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总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与区域经济发展系统之间仍存在着互动不足、融合不够等问题,这就有必要对两者的协调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价。
通过诉诸于历史,法家发现人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基本趋势就是“古之民朴以厚,今之民巧以伪”(《商君书·开塞》)。法家同样认可上古是一个淳朴的时代,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人心越来越虚滑巧诈,而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名夺利,乃至“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刑赏》)。虽然法家持有与儒家不同的人性态度,但这并不表示法家对“仁心”的彻底否定。至于“仁心”是否存在并不重要,因为政治的首要目的是去恶而非扬善,更不能通过扬善来去恶。人心有千种,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有不同的面向,到底哪一面应当重视,不仅是价值判断的问题,更是实践选择的需要。国家政治的构建需要将所有人都当作“陌生人”来看待,因而必须注重人性更为直接、现实、冲突、甚至阴暗的一面。所以,通过“内推”而来的“仁心”为政道奠基是不“现实”的。
药品加成指医院在销售药物时,可以对其加价百分之十五后再进行销售,主要是因为我国当时处于建国初期,国家整体经济水平很差,而人民生病的问题又无法避免,国家财政不足以对其进行补贴,在多方因素的影响下,药品加成政策应运而生。但因药物高昂的售价,造成了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的情况,但是近些年,随着国家的飞速发展,整体经济水平不断上升,国家变得富裕起来,已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人们看病进行补贴,终于,卫生部宣布全面取消药品加成政策,医院减少的收入由国家进行补贴、设立药事服务费以及对部分手术费用进行调整,其中设立药事服务费的主要目的不是盈利,而是对医疗工作者的一种鼓励,至此,我国药品加成政策被全面废除。
如果说治道体现为工具和方法的选择,那么政道则是进行这样选择的深层依据。政道,就是运作政治的基本方式、理念,也是根本的政治逻辑。德政即仁政。仁政的运作方式和基本逻辑就是“推”,即每个人都可从人心中“内推”仁心的存在,统治者由仁心“外推”仁政于天下,收天下人心。仁心不分古今,先王行仁政而王天下,后王当“推崇”先王仁政。法家看来,这种“推”的逻辑并不适用于国家政治,仁政不能满足此时社会对政治的需求,政道的选用也应当立足于现实人性,并结合历史趋势与时势要求,而仁政不别古今、不顺大势,实则是一种“守株待兔”的表现。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五蠹》)
这种失败的情形不仅出现在父子之间,在陌生人之间更是屡见不鲜。当仁爱道德不足以对一个“不才之子”产生效用时,只有通过政治权力,甚至动用武力威慑,才能使其弃恶从善、“变节易行”。这正是仁政“推”的逻辑的失效之处,即“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商君书·画策》)。政治区别于伦理道德的地方就在于,政治是“支配”,而伦理道德是“自觉”。若以“自觉”的方式去实现“支配”,那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是尧舜,而若人人都是尧舜那就不需要政治了。这并不是说道德教化没有意义,而是在国家政治之中,必须通过强制性的支配关系才尽可能地将贤、不肖,君子、小人等各种人纳入到这个统一的政治系统中,让各种异利的政治主体服从于统一的政治秩序。当然,这种支配性关系可以通过强制、说服、魅力、交易等多种手段实现,并非一定是赤裸裸的武力。因此,在这样一个世俗的国家中,政治服从必然基于个人理性的算计。除了政治公平,强力就必不可少。法家正是看到国家政治对“强制”与“支配”的需要,必须要摒弃柔弱、无效的仁政。因此,现实要求的为政之道就并不是简单的顺人心而已,政治往往是要逆人心而为。法家甚至明确提出“政作民之所恶”(《商君书·弱民》),认为“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韩非子·显学》)。政治,必然要做一些民众所厌恶的事情,而这是国家存在所必须的,比如战争、徭役、赋税、刑罚等。所以,一味的“适民”、顺民心往往会让国家软弱无力、混乱无序。所以,历史中有行仁政而王天下者,如周文王等,也有行仁政而亡天下者,如徐偃王等。
儒家的政治遭遇也说明这点。孔子周游列国,却“累累若丧家之犬”,孟子遍说诸侯,无一人施行。商鞅见孝公说以帝王之道,皆罢而不用。而秦王见《说难》《孤愤》,急攻韩。儒法遭遇的差别,并非法家对统治者的逢迎所致,而是时势使然。法家并不否定上古时代的淳朴,也认同行仁义而王天下的政道。但是,这种美好和成功仅仅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也必然要求政道的变换。上古巢氏、燧人氏教人筑巢取火而王天下,中古天下大水而有鲧、禹之功,近古桀纣暴乱有汤、武征伐而王天下。商君总结为:“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智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夫民愚,不怀智而问,世智,无余力而服从。故以智王天下者摒刑,力征诸侯者退德。”(《商君书·开塞》)针对不同的社会现状应当实施不同的政道才可以王天下,对于朴素蒙昧的古人而言,依靠智慧就可以王天下,而对于巧诈虚伪的今人,必须具备强制性的力量才行。如若不知时势变异而将尧舜之道用于当世之民,则是迂腐的表现。因此,先王之政也并不值得后王效仿,当察世事之变,知必然之势,行必治之政。而今,“当大争之世,而循揖让之礼,非圣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车,圣人不行推政”(《韩非子·八说》)。因而,当今时代的王天下之道必须舍弃仁政,变换政道,当退德用力,行“力政”〔10〕。
五、结 语
萧公权曾说:“韩非论势乃是划政治于道德之外,建立近代意味的纯政治的政治哲学。”〔11〕这当然是与西方马基雅维利比较而得来的结论,法家也确实如此。但是,这仅仅看到了其中的一面。萧先生只是笼统地说“道德”,而没有说明是什么“道德”。从分析可见,国家政治的构建需要构建超越伦理的政治道德,因而法家所反对的乃是儒家基于伦理的道德。同样,马基雅维利所颠覆的并不是一切道德而是基督教的道德。与此相应,法家是要否定儒家的“德性政治”而建立国家政治,而马基雅维利则是要否定神权政治而建立国家政治。因此,我们应当看到,法家在将政治从儒家伦理道德中抽离出来的同时,必然会着手新政治道德的建设。在法家看来,政治道德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道德,是一种“去人情”的道德,因而别有根基。正是在这一点上,法家吸收了道家“不仁”“不义”的思想,主张一种超越人伦的,更高层面的政治道德。统治者时刻要将整体、公利放在首位,必须克服个体、局部的偏私、人情,以一种“不仁”“不义”“无情”的态度成就一种普遍的、超越伦理道德的“大仁”“大义”“大爱”。
然而,目前高职教育的现状并不乐观,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教师普遍缺乏企业(行业)工作经历,实践经验少,传统的偏重理论的“一言堂”教学模式大量出现在高职教学课堂,不足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完成培养高技能、高水平技术人才的任务;二是教师对高职教学的“必需、够用”原则作简单、片面的理解,过于注重学生的技能训练,忽视学生知识结构的构建,理论知识讲授过少,所培养的学生技能只针对某一特定工作岗位,技能单一,知识面狭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1]。
既而我们可以看到,法家所要求的政治道德,必然会与伦理道德产生冲突。韩非曾说:“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五蠹》)两者的冲突也在国家政治最激烈的时候显现得最为明显,当进行“大义灭亲”与“亲亲相隐”的抉择时,就会明显感到在“情”与“法”、“公”与“私”之间总是难以两全。这种冲突从表面上看是两种道德之间(公德与私德)不相容所造成的,但其根源却在国家政治本身。后世儒家不断以“秦政”为镜鉴,要求“攻守异道”“逆取顺守”,行宽缓、仁义之政来缓和两者的冲突,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走出这一困境。而“百代皆行秦政法”,也让这种冲突一直伴随着中国传统政治。因此,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道德之间的冲突,而在于政治。所以,真正的出路并不在于重新将政治收束于伦理道德之中,而是对政治国家本身进行改造。但是,一旦涉及到这一问题时,又如何避免“交争利”的状态呢?这是法家对“旧病”治疗后产生的“新病”。而这,却不是法家所需要应对的时代问题。
当然,以上的讨论是置于国家政治兴起这一进程中来思考的,而对于国家政治本身的考量却是悬置的。事实上,这在先秦诸子那里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是否需要构建一种国家政治,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政治(权力)本身就是一个被探讨的问题。至少在道家看来,政治本身就是恶的,是“落马首,穿牛鼻”的人生戕害。因此,政治在人类生活中应当越少越好,更遑论国家政治了。儒家则显得温和,主张人类只需要少量的政治,政治的运行也必须坚持伦理道德的原则,否则会给自身带来灾难。法家则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使得人类需要更多、更强的政治才可以走出当下的困境,国家政治是人类发展的“必需品”。在这一问题的观照下,儒法之争可能就是另一幅图景。
注释:
〔1〕〔德〕艾尔哈特·艾普勒:《重返政治》,孙善豪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11-128页。
〔2〕杨阳:《韩非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述论》,《政治学研究》2015年第2期。
〔3〕沈锦发:《先秦儒家“圣王原理探析”》,《南昌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
〔4〕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1-48页。
〔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97-99页。
〔6〕孙津:《超越民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7〕周谷城:《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34页。
〔8〕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9〕〔美〕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0页。
〔10〕任健峰:《何谓法家?——先秦法家的政治观探析》,《理论导刊》2018年第12期。
〔11〕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153页。
例如,在学习关注心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时,教师可以将心血管疾病的并发原因向学生进行说明,当然在生活中有很多的并发原因都是因为不当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造成的,所以教师有必要针对生物知识进行深入地讲解,进而引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养成正确健康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避免疾病的发生。
作者简介: 任健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2016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政治思想史;袁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7.005
〔责任编辑:汪家耀〕
标签:儒法之争论文; 政治与道德论文; 国家政治论文; 法家论文;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