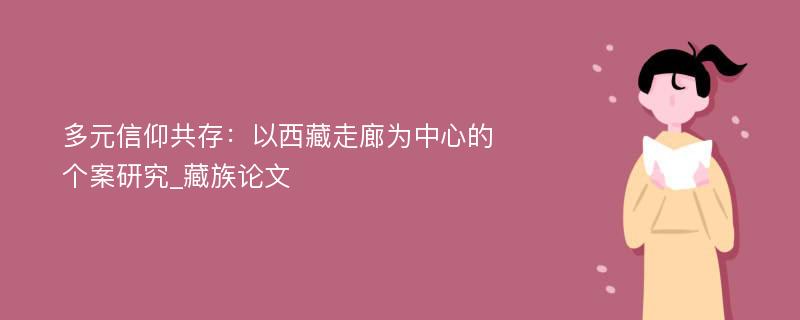
多种信仰共存:以藏彝走廊东缘多续藏族为中心的个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个案论文,走廊论文,多种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6)01~0020~07 毋庸讳言,古往今来人类群体间的矛盾或区域性战争大多是由宗教信仰冲突引发的,而以宗教信仰为旗号的血腥和暴力纷争也不在少数,十字军东征、中东冲突、原教旨主义运动等诸如此类的案例不胜枚举。特别是自美国“9.11”事件爆发以来,宗教日益成为恐怖主义的基础和动力[1],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分子经常在全球发起无预兆的恐怖袭击,极端信仰与暴力行为相结合不时刺激着各国政要和大众平民的神经。如何实现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当前乃至今后极具探讨和研究价值的学术选题。 引人思考的是,笔者近年在藏彝走廊特别是其东缘地区田野调查时发现了一种图景,它与世界各地常因宗教信仰冲突引发民族矛盾不同的是,该区域各种宗教信仰之间杂糅兼容、并行不悖,呈现出一种高度和谐包容的状态。藏区水电建设者们常能发现这样的现象,生活于同一条沟域的几个村寨分别信奉不同的藏传佛教派别,有时甚至连一家人信奉的教派都各不相同,造成寺庙搬迁和移民工作十分复杂棘手。在川西北壤塘、阿坝等地至今还传承着卫藏等地业已消失的觉囊派,其与格鲁、萨迦、宁玛、噶举以及本教各行其是。不仅如此,与这些制度化宗教同时存在的还有个体宗教职业者从事的民间宗教活动①。石硕教授曾对此进行过专题研究,指出:“他们的宗教活动与当地各教派寺院僧人进行的宗教活动往往并行不悖,但功能略有区别。”[2]宗教信仰是民族文化心理与情感的终极寄托,由信仰冲突引发的民族矛盾不仅难以消解,且通常会自动代际传递。藏彝走廊东缘作为多民族共居区,各种信仰却能在这里彼此并行不悖、相互共存,最可消解由民族交往、交流引发的冲突和矛盾,并可增强相互间的文化心理认同。鉴于不同宗教信仰和谐相处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拟在安宁河流域多续藏族信仰个案调查基础上,结合笔者对硗碛藏族的田野调查与前人相关研究,对藏彝走廊东缘地区的多种信仰共存状态进行深度揭示,同时尝试探讨导致此种状态出现的内在原因,以期引起学术界的进一步关注和研究②。另外,文中所举材料,除引用他人成果予以注明外,其余均来自笔者2008年7月至今对多续社区的调查和当地知识精英的个案访谈。 “多续”系藏族多续人的自称,又写作“多虚”、“多须”,他称有“西番”、“俄助”、“吉苏”等,主要活动于安宁河发源地及其上游地区,具体分布在四川凉山州冕宁县惠安乡的擦拉、九堡、湾子、大垭口等村;城厢镇的伍宿、和尚冲等村;哈哈乡的木拉乐、青山嘴、拉堡、那甲瓦等村;复兴镇的洪兴、高堡、新银、白土等村;林里乡的嘎撒、嘎马山、两河口、结果罗等村;后山乡的大热渣、小热渣、连二瓦等村;森荣乡的呷伍村;原来还有部分人居住在大桥镇和宁源乡,后来因大桥水库建设搬迁到西昌月华等地[3]。据孙宏开、龙西江等人调查,多续藏族的人口数量在3000左右[4~5]。2008年,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曾组织科研人员前往安宁河流域对多续藏族分布集中的点开展调查,统计冕宁多续藏族的人口数量约在2000人左右。笔者有幸参与2008年对多续藏族的调查,此后每年都前往多续分布比较集中的社区进行走访调研,由此对当地民众的信仰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和认识。 据前人相关调查及田野访谈材料,藏传佛教信仰在多续藏族中曾经非常兴盛。《冕宁县志》载:“冕宁藏族,信奉藏传佛教。……清代以前都信本波教(俗称黑教),故自称为‘本波家’。约明末清初,格鲁等教派(泛称却教)传入,僧侣日众,但民众一般都信本波教。”[6]承当地百姓告知,“十年动乱”前每家每户都保留有许多藏文经书,房子二楼放置经书的地方称为“经堂”,是请喇嘛诵经的地方。据称建国前在冕宁曹古有一印经院,至今许多藏族群众家中还保留有许多张印在牛皮纸上的藏文佛经,可间接印证此说。在迫夫村还出过一个活佛,因此建有一个喇嘛庙,此庙后搬至惠安擦拉。庙里供奉的神灵有释迦牟尼、弥勒佛、大鹏鸟、唐卡、“当家”③、“古吉贡布”④,经书有满满两大房间。清咸丰《冕宁县志》亦有关于多续先民“余多习喇嘛经,进藏为喇嘛”的记载。本地群众对藏传佛教十分尊崇,当多续与纳木依争吵时,认为该区域位次排序等级最高的是西藏来的喇嘛,多续次之,再次是纳木依。此外,在一些地方至今还保留着藏文石刻经文以及嘛呢堆、嘛呢旗等。 马文中先生是多续本地知识分子,他说:“冕宁这地方以前是我们藏族人聚居地,藏文石刻、喇嘛庙四处都有,因建过藏传佛教寺院或与之配套的转经房而得名的‘喇嘛房’、‘转经房’地名不少。”[7]马先生曾主持编修过《冕宁县志》,搜集过许多本地掌故、乡野传说,他曾对冕宁历史上的喇嘛寺作过专门统计,有结尾寺、莫觉寺、瑶寺寺、额基寺、大村寺、糯白瓦寺、咱耳山寺、勒垭寺、黄家坝寺、白沙寺、大盐井寺、曹古寺、热即瓦寺、元通寺、凹姑寺、庙高山寺、迫夫寺、三代寺、些基罗寺、嘎丝寺、热咱寺、和尚冲寺,以及其他多地虽知建有寺庙但莫能言其名的喇嘛寺[7]。这些寺庙所在地域与多续历史分布区域大体相重,可认为大多为多续先民崇信喇嘛教而兴建。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冕宁的藏传佛教发展可追溯到元明时期⑤,清代非常兴盛,清末民初由于多续人口下降以及彝人北上、西进等原因,许多寺庙坍塌、传承中断,“十年动乱”中,破四旧致许多庙宇被毁,现今多续关于历史上的冕宁藏传佛教寺院仅存于坊间旧谈或耆老回忆中。 不过,对于以上所言之“喇嘛寺”或“藏传佛教寺院”,切不能将其与通常意义上藏区所言的藏传佛教寺院等量齐观。多续人传统上将宗教分为“贵教”和“却教”两类,其中“贵教”指“本教”或“本波教”而言,“却教”泛指“本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甚至连在西藏及其他藏区“一家独大”的格鲁派也被归于“却教”一类。因此,以上“喇嘛寺”绝大多数是指本教寺院而言,仅“结尾寺”可明确知其属于黄教,其余寺院究竟属于何种教派限于资料尚不可知。综合藏传佛教发展历史⑥,《乙亥随录》中关于明初多续首领与高僧普济共往拉萨“朝法王”、“得经文”的记载,可视为多续先民早在明初即与本、格鲁以外的其他藏传佛教派别建立联系之事实⑦。由此言之,不排除以上所举寺庙中有属藏传佛教其他教派的可能。 与“喇嘛寺”这些制度化宗教并存的,还有本地民间个体宗教职业者主持的仪式与活动。这些个体宗教职业者称谓主要有“帕比”,俗称“大鼓和尚”。与之相对的是“萨巴”,或写作“沙巴”“什比”“什巴”,俗称“小鼓和尚”。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大鼓和尚”负责“做帛”,所用的鼓是吊起来打。而“小鼓和尚”负责送鬼,所用的鼓用手握住打。擦拉堡子的穆宗容的记忆中有两个和尚,一个是中村的嘉玛和尚,一个是伍其山。据传“大鼓和尚”法力高深⑧,但多续藏族“大鼓和尚”传承体系已趋中断。马文中先生将这些个体宗教职业者称为“祭司”,认为“沙巴”包括“大鼓和尚”、“小鼓和尚”两种,另外还有一种使用“大鼓”的祭司,称“赞克”,是“专事发度亡魂做道场的掌坛大法师”。此外,还有一种祭司称“那摩”,系无师自通、感应而会,拥有驱魔撵鬼的法术⑨。另据韩正康调查,民间个体宗教职业者还有“冈差”、“迷莫”等,但现今已莫晓其义、所事为何[8]。 本地民间信仰十分盛兴。当地群众称,开天辟地最大的神是“石巴觉”,或称“什巴觉”,传为开天辟地的始祖,也有群众称其为“家神”⑩。“觉”的载体是一块洁净的白石,通常供于神龛上,平时无论大小事或逢年节都要祭拜。据相关学者调查研究,“觉”崇拜存在于川西南地区的多个藏族支系,如里汝、尔苏、纳木依等[9~10]。多续每个家庭都有家神,一般供奉于堂屋正中上方,据称其可管理家中一切事宜。家神系建新房后,从本地河滩或高山上选一块洁净呈椭圆形的石头即可,不一定非得要白色,如灰色也可,逢年过节都要敬家神,祭品有刀头肉、猪头、猪尾、整鸡、面、斋饭、香、酒、烛等。以石为载体的信仰还有“赶山菩萨”,是对锅庄左方所供石头的称呼,过去打猎行前必须先杀鸡祭敬;锅庄上方供的石头也是“菩萨”,忌踩踏,每天用餐时都要放点菜肉在上面请“菩萨”先享用。在擦拉堡子村中心位置,俗称“打老牛”的地方摆放有三块大石,中间的石头最大,当地群众称“吉阿布”,左右两石是其助手,平时严禁人坐其上或用脚踩踏。此外,在每个多续“汝都”(11)的“拉咱”(12)山上,在“措巴作”仪式举行地(下详),每个有资格享受后裔祭拜的先祖亦依次摆放石头作为代表。这种古老而浓厚的石崇拜信仰,应与古蜀文化中大石崇拜以及川西高原的石棺葬文化、安宁河流域的大石墓文化存在某种内在联系。 多续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十分突出。每逢农历七月十五前夕,多续各“汝都”都要前往本“汝都”的“拉咱”山祭祀先祖。能进入“拉咱”山享受子孙祭祀的先祖,其身份条件必须同时符合年满60周岁以上、儿孙双全且正常离世等条件,并列石为志。这种祭祀先祖的仪式多续语称“措巴作”。祭祖的物品有羊心、羊肝、鸡心、鸡肝、鸡头,一般是先将活羊、活鸡杀死后用火烧后再行祭拜,同时斟酒、烧纸。毕后,所有参加仪式的人共享祭品。 在祖先崇拜基础上,多续人信仰体系中诞生了两位人格化的祖先神或英雄神:一是古吉贡布,一是“大佛爷”。当地群众认为,古吉贡布是哥哥,“大佛爷”是古吉贡布的妹妹,又称“董巴贡波”、“西番娘娘”。过去喇嘛寺中大多供有二人神像,特别是圆通寺供奉的“大佛爷”最负盛名。 多续人的自然崇拜也十分丰富。天神,多续语称“仲克”,每年正月初一要点天灯敬天神。点天灯要立一个三丈多长的白杉杆(平时人不能跨,不干净的东西不能堆),然后用竹篾编一个灯笼,置入灯具并注满清油,像升旗一样把它升起来。升灯之后要请天神,即像敬天一样,唯一的不同在于请神时要敲三下铜碗。灯升起来,等大家到齐了之后,开始绕着柱子按逆时针方向转三圈,之后集体唱歌、跳舞。 多续崇信的山神有“尼雀奥约姆”“沙雀央哇娜姆”、“喔得嘬嘬姆”和“喔嘬曲登嘎布”(13)等。本地民谚称“山神不开口,老虎不吃人”,因此,平时上山砍柴、挂纸都要敬山神。在“措巴作”仪式上也要敬山神,具体做法是在祭山神前的石台上放三杯酒、一小杯米饭,一坨刀头肉(不放熏烟的地方),用檀香木做成的木签作熏烟用。此外,凡丧葬动土、举行婚礼等重大场合也需要先祭拜山神。在惠安乡擦拉村至今还保留有全体村民祭拜山神的仪式,当地称“三月三”或“封山节”。具体日期可选择农历三月初三、十三或二十三,一般依据农时或老人推算来决定,由会首负责具体操办,并按年轮流由两家人担任会首一职。此外,每个汝都的“拉咱”山都被奉为神山,或称“菩萨山”,山上所有草木皆不可动。位于九龙、冕宁、石棉交接的“则尔山”,被视为多续、里汝、尔苏等藏族支系共同的神山,其意是“穿白裙的仙女”。 与山神崇拜相对应的是水神信仰,承宋达瓦告知,多续藏族共同信仰的水神有苏嗯嘎亚布(东南方水神)、苏甲森呐仁差、苏甲米谷嘎布、苏甲热达、苏莱嘛热达等。 树神崇拜,几乎各村都有。城厢镇和尚冲村水箐坝水源处有一棵很大的“蒙子树”,村中凡治头痛病者送油香都要送到这颗树所在的地方(14),其枝叶不得采摘或砍伐。擦拉堡子举行“封山节”、“还天愿”的地方也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平时村民或家中丢失财物,或遭遇不公猜忌,或彼此纠纷难解,都要去神树那里倾诉或卜算。 多续人还崇拜布谷鸟,亦即杜鹃。当地群众称:“布谷(杜鹃)不来,就不种荞子”,“会打架就不打舅舅,会打鸟就不打布谷鹊”。古蜀有杜鹃崇拜,传其为蜀王望帝的化身,有诗云“望帝春心托杜鹃”,多续藏族崇拜布谷鸟可能正是这种古老信仰的孑遗。 此外,在多续藏族中盛传关于“小神子”的传说。访谈中有不少村民告诉笔者曾亲眼见过“小神子”,或村中某某人见过“小神子”。传说“小神子”是未成年婴幼儿死后的化身,特别小气,听不得别人说他的坏话,而且还经常与所冲突之人作对(15)。 汉地信仰在多续藏族居住区也较普遍。城厢镇和尚冲村路口有一土地庙,庙里供的是“土地老爷”、“指方老爷”,分别画在两个木板上。当地群众认为其可挡病、挡灾、挡鬼。土地庙一般在农历七月初七日举行仪式,由村内汉藏群众共同出钱买肉、纸、香、烛等,敬的东西还包括一甄子饭(饭上插一把筷子)以及贡果。举行仪式时,要撒荞子、麦子、谷子、豆子、苞谷,总称“马草马料”,撒这些东西象征天老爷将五谷收走,就不会发生冰雹灾害,意在保佑庄稼有收成。一些多续人的大门口还立有“泰山石”,意在镇邪、避灾,此习俗与汉区相同。 本地还有一个川主庙,是汉族与藏族共同出资修建。庙中供奉的神像有川主和大佛爷等。在多续藏族聚居的大热渣也有一个类似的庙,里面供有财神、观音、地母、杨祖师等,这显然是受汉族民间信仰影响所致。伍宿王桂英家堂屋进门左边的墙上放置着4个木娃娃,当地人称“童儿”或“老根根”,其功能是保佑家里的孩子健康成长,据称此木娃娃系请汉族道士所做。 毕摩是彝族文化的集大成者,其地位类似于纳西族的“东巴”、羌族的“释比”。在当地藏族家庭为老人“做帛”,即通过该仪式让家中福寿双全的老人进入“拉咱”山成为祖先崇拜之对象时,主持仪式者正是彝族毕摩。可见,由于多续藏族“大鼓和尚”传承的消失,由彝族的毕摩填补了这一角色。这种情形同样见于与多续藏族有着密切亲缘关系的藏族里汝人之中。据伍呷在乃渠乡调查,1983年统计该地有里汝支藏族493人、彝族401人,汉族1147人,在这些藏族中间流行一句俗语:“人在世讲哪种语言,过世就请操该语言的和尚”,“如彝族去世,多去水打坝大队烂堡子村请吉都毕摩。汉族过世后,多请汉端公,83岁的少万红老先生。但无论是藏、汉、彝各族如果本族宗教职业者断定过世之人为鬼凶死的多请彝族的毕摩来接鬼。在各族村寨中如遇此事,都得去请远近闻名的82岁的吉都毕摩。”[11] 综合以上调查,可发现安宁河流域多续藏族信仰至少存有五种类型:一是积淀深厚的本地民间信仰,包括以石为载体的“觉”、家神、祖先与锅庄石崇拜,天神、山神、水神、树神、古吉贡布、“大佛爷”、“小神子”等;非制度化的民间宗教形式,主持仪式与活动的民间个体宗教职业者称谓有“帕比”、“萨巴”、“赞克”、“那摩”、“冈差”、“迷莫”等。二是制度化宗教信仰,即多续藏族所称的“贵教”(本波教)与“却教”,主要是制度化的本教以及藏传佛教格鲁派等教派。三是道家与汉地信仰。四是古蜀文明中的信仰孑遗,主要为杜鹃鸟和大石崇拜等。五是彝族毕摩文化信仰。 笔者曾对青衣江上游硗碛藏族乡的信仰进行过考察,发现其至少可分三种类型:一是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藏传佛教信仰;二是有浓厚本教色彩的民间信仰;三是道教及汉地其他信仰[12]。在木里藏族自治县,除藏传佛教、民间信仰外,还存在大量来自汉地、彝区、苗区、羌区、壮区等地的信仰,并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交相杂糅在一起。2015年11月19日,笔者在小金调研时,该县民宗局长告知汗牛乡某寺分别为两个教派僧人居住并共同活动。11月26日,笔者在青海果洛州久治县德龙寺(又名“德合龙寺”)调研时,该县民宗局长也指出多种教派与信仰并存是本地极富特色的人文景观,德龙寺也存在宁玛、觉囊两派在一寺共同活动的历史(16)。此外,还能在金川、甘洛、石棉、九龙等多地发现多种信仰共存的田野案例。可见,多种信仰共存是藏彝走廊特别是东缘地区一种普遍存在的人文景观。 与他处宗教信仰之间彼此冲突或相互纷争所不同的是,藏彝走廊东缘区域不仅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成为常态,且各种信仰彼此并不相互排斥、界线亦非泾渭分明。综合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并结合笔者在多续社区的调查材料看,安宁河流域作为历史上多续人活动区域,多种信仰共存至少可从以下三个显著迹象中得以揭示。 第一,历时性信仰共存于多续人文生态空间中。以本教为例,通过调查分析即可发现多续保留有本教在各历史时期的形态。首先,种种迹象表明多续人的本教存在多种来源。多续耆老称,过去本地喇嘛需赴德格地区学经、考试,表明本地“喇嘛寺”教法主要源自德格的本教寺庙,其中有部分僧人甚至还去过拉萨。九堡马氏家中藏有一珍贵白海螺,上刻文字符号19个,其就有“卍”字符,表明其为法器,而马氏传其先祖源自青海“鹰”部落。龙西江通过调查,称多续的本教“主要是从九龙县迁冕宁的尼汝人吴尼和黄姑部落带入多须人社会的”[5]。笔者曾调研过与多续存在亲缘关系的甘洛尔苏人(17),当地群众称其本教信仰来自西藏阿里。很明显,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本教不大可能同时传播到安宁河流域。 其次,多续历史上“喇嘛寺”众多,前已指出此“喇嘛寺”系指“本波教”或本教而言,当地又称其为“贵教”,是多续历史上最主要的信仰。这些本教寺院既然拥有自己的组织、经典、活动场所以及相对完整的教义,当指受佛教影响而制度化的本教,亦即本教发展阶段中的“局本”而言[13~14]。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认为“局本”分为早、中、晚三期,说明“局本”的发展经历过不同阶段[13]。冕宁历史上本教寺院众多,是“局本”的传播和发展区域之一,这些“喇嘛寺”有可能存在先后之分。 再者,与制度化本教相对应,多续本地民间还有许多个体宗教职业者。其区别是:一类能诵读藏文经书、超度亡灵,法力较高深,通过师徒相承或父子相传的方式传承(18);一类不会藏文、没有经书,口耳相传、父子相承,法力较前者低。两者的共同点是,均由男子担任且从事兴旺人家的法事,平时不脱离劳动生产,不隶属于任何寺院或教派。从事物发展由简单到复杂的规律看,后者存在的年代显然早于前者,或可认为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产生的。由其活动内容和形式看,其与“笃本”、“伽本”颇为相近(19),且早在喇嘛寺之先存在。故此二者有可能是本教的早期形态。由前者能“诵读藏文经书”看,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贵教”的影响。 第二,外来信仰不断与本地民间信仰进行有机结合、相互兼容。最典型的案例是“古吉贡布”和“大佛爷”,安宁河流域历史上许多“喇嘛寺”都供奉有二者神像,表明藏传佛教在向东缘地区传播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纳当地神灵并与民间信仰相互交融。其中,“古吉贡布”被演绎为西藏喇嘛的弟子。有趣的是,圆通寺主要为供奉“大佛爷”而建,本地民众又称其为“观音堂”,即将“董巴贡波”视为观世音。据称此寺规模甚大,喇嘛两三百名,清代冕宁最大的法会——“大佛会”即在该寺举办[7]。清咸丰《冕宁县志》记:“自二月朔日起,汉女番妇妆饰入城,献花进香,口宣佛号,手击钹鼓,俯伏蒲团,竞诵经卷。观者云集,市香烛者万计,还愿饰扮功曹鬼率者千计。至初八日大佛出,游巡四街,高桩遐举,旗帜横飞,盈溢闾巷,男女混杂”(20),法会之盛大可见一斑。此记载表明,“大佛爷”在清代冕宁藏传佛教神灵体系中地位甚高,并成为当地汉族的重要信仰之一。 此外,本地体现汉地信仰的庙宇中同样供奉有多续人信仰的神灵,成为汉藏民族共同的宗教场所,表明汉地信仰在向多续传播时同样需要与本地民间信仰有机结合、相互兼容。 第三,多种信仰之间各行其是、并行不悖。综合前述调查材料和相关研究成果,可发现多续藏族人文生态空间中既有制度化的宗教,也有许多民间宗教形式,与其并在的有本地民间信仰、道家及汉地信仰以及古蜀文明中的信仰孑遗,这些信仰之间虽彼此功能有所不同但并行不悖。耐人寻味的是,传统上多续藏族家庭为老人“做帛”的仪式由“大鼓和尚”主持,但在该传承体系中断后,司仪者换成彝族毕摩(21),存在以多续藏族传统“做帛”风俗为“体”、毕摩为“用”的文化现象。 由上言之,多种信仰之间不仅共存、并行不悖,甚至彼此交织杂糅、相互接纳兼容,导致几种信仰层次并非泾渭分明。通过对青衣江流域硗碛藏族乡的信仰考察与分析,笔者同样发现了该地各种信仰“相互间并不排斥,彼此存在一种并行不悖、相互兼容的关系”[12]。这表明,藏彝走廊东缘多种信仰共存且相互交织杂糅、相互接纳兼容并非个例。 那么,多种信仰并存这一现象为何在藏彝走廊东缘区域突出地体现出来呢?这是一个极富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话题,其内涵需更多田野个案调查和多学科研究方可揭示。不过,笔者认为思考这一学术话题不可回避以下两点因素。 一是藏彝走廊东缘历史上长期作为多民族迁徙互动的廊道存在。从现有文献记载看,历史上大的民族流动先后就有蜀人南迁、羌人南下、僚人北上、吐蕃东渐、蒙古南下、彝人北上,以及不同时期、不同强度的汉人西进等。伴随这些大的人群集团流动的同时,还有众多大小不一、文化各异的部族间的交流互动。频繁的民族迁徙与文化互动直接导致该区域人群来源的多元化。笔者在对多续族源调查时发现,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安宁河流域发现许多大石墓遗迹,此与至今仍保留于多续藏族中“拉咱山”举行的“措巴作”仪式存在联系,可认为多续人的主体是由安宁河流域本地人群发展演变而来;不少多续人保留有其先民“瞻堆起祖、呷尔落业”之后分房的记忆,说明其族源来自西边;部分称其先祖来自“邛州南桥十八洞”,表明与古蜀的南迁相关;也有人称其祖先最早生活在青海,之后不断南迁终至冕宁,惠安乡至今还有木雅沟的地名,这与吐蕃东向发展造成部分党项人活动至此不无关系。不同民族间频繁交流互动,直接导致民族与民族间的族界意识趋于淡化。大凉山彝族史诗《勒俄特依》记载,彝、汉、藏是一母所生的三兄弟;纳西族史诗《人类迁徙记》亦认为汉、纳西、藏是一母所生的三兄弟。类似传说存在于藏彝走廊的多个地区。这种共祖传说对民族民间交流交往中强化彼此心理认同、模糊民族边界提供了依据,其结果是大幅消解不同文化信仰间原本应有的对立与紧张。 文化随人群流动而传播发展,多元的族源导致不同时期的不同文化在特定人文生态空间中“碰撞”、“交汇”、“叠压”与“融合”,造成藏彝走廊的区域文化共性远大于某单一民族的文化共性。石硕教授研究发现:“在藏彝走廊区域,……局部区域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大于同一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似性。也就是说,不同民族或族群交错杂居在同一局部区域内,经过长期的接触和文化交融,两者之间的文化相似性将会明显的增强,以致于造成在一定条件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似性要大于同一民族的文化相似性。这是藏彝走廊中的一个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15]此论极富见地。相对于体质、语言而言,文化变迁发展较快,当族界意识在日常交流与生活中趋于淡化,地缘认同被植入根基性感情和文化心理中,多种信仰共存由此而得到人文生态“土壤”。 二是藏彝走廊东缘位于文化过渡带及其所具有的边缘性特征。以多续为例,其位于藏、汉和藏、彝的交接与过渡区域,同时又处于汉、藏、彝三种文明体系的边缘。一般说来,位于文化过渡带上的文化会呈现一种亦此亦彼的状态,不会出现某种文化“一家独大”的局面。这一点在生物学上也是如此。而边缘地带由于距文明中心较远,政治权力、主流文化对边缘区影响较弱,从而为主流文化之外的其他文化的保存和发展提供了庇佑之所。同时,主流文化要想在边缘区立足,其所凭依的不是中心区所具有的政治权力,而是降低“身价”与本地民间文化或信仰相调和,经过“本地化”或“再地化”历程。与之相对,藏彝走廊东缘诸族对于藏、汉两大文明实体通常都是两边交好、互不得罪,新旧《唐书》所载既世袭唐朝官职、又“阴附吐蕃”的“两面羌”即为明证。在此背景下,汉藏两种信仰都会在藏彝走廊东缘地区扎根立足、开花结果。因此,文化边缘地带或文化过渡带的人群文化具有显著的多样性与复合性特征,在此文化基础上极易导致人群信仰的多元化。 民族研究理论通常认为,民族与民族在交往过程中,相互之间的种种差异会被凸显出来,这种差别正是构成民族内部亲和力和民族意识的重要来源。费孝通先生指出:“一个民族的共同心理,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可以有深浅强弱的不同。为了要加强团结,一个民族总是要设法巩固其共同心理。……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情感,把它升华为代表这民族的标志。”[16]也就是说,世界上之所以民族众多并相互区分,根本在于情感上的心理认同和文化差异。但通过以上对藏彝走廊东缘地区多种信仰彼此共存、并行不悖的田野个案调查,笔者发现该区域作为一条多民族频繁互动的廊道,以及汉藏等文明体系的边缘区和文化过渡带,其文化具有显著的多样性和复合性特征,其区域文化共性要大于民族文化共性,甚至不同民族认为彼此系一母所生的兄弟,导致族界意识的模糊化。可见,藏彝走廊东缘区域民族与民族在交往过程中,凸显的并非民族差异而是文化共性,既有相关研究理论尚难以对此作出充分解释。笔者以为,对此种现象及其内在机制的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各民族和谐共处之道,对探索各种文明或信仰体系间如何做到并行而不冲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这些个体宗教职业者称谓各地有别,如巴塘、得荣称“本更”,道孚称“奥外”,丹巴、小金称“更(工)巴”,冕宁、九龙称“帕比”(“扒比”)、“木尼”、“阿什”,北川、平武称“北布”,石棉、甘洛称“沙巴”,鱼通藏区称“公嘛”等。 ②鉴于“宗教”系外来词汇,本文将更多采用“信仰”一词来统称与宗教及宗教相关的认知和活动。 ③系音译,具体所指百姓说不清楚。 ④系音译,指一位骑羊、身披铠甲、手执弓箭和木枪,据称是圆通寺“大佛爷”的哥哥。 ⑤清韩金甲《乙亥随录》记明初宁番卫(冕宁):“番居甚众,番人奉佛,苟敦睦,非佛无以动也。……愿以高僧普济随酋赴逻些,以朝法王。翌年归,得经文六十一卷”。由明朝初年“番人奉佛”以及有高僧前往拉萨等迹象判断,冕宁藏传佛教应早于明初。另据《圆通寺碑》记载,该寺建于明洪武年间,但民间相传其始建于元(马文中:《冕宁藏传佛教寺院觅踪》,载《凉山藏学研究》2004年第5期)。 ⑥“后弘期”本教已在卫藏等地式微,而黄教开始兴盛。 ⑦结合卫藏地区相关史实,当时最可能的应是藏传佛教噶举派。 ⑧穆宗容说:“大鼓和尚念经文,念得狠的话,猪、羊都自己去跪起。”多续民间有许多关于大鼓和尚施法的传说,如念经止雹、腾空飞行、施法灭蛇以及与其他个体宗教职业者斗法等。 ⑨参见马文中所撰:《川西南散居藏族》,打印稿,2015年,第109页。 ⑩也有人认为神龛或神柜正中供“什巴觉”,左右两边分别供祖先和家神。笔者认为,将其称为家神应是比较晚近的说法,可能是后人在崇信“什巴觉”、家神基础上的信仰简化,将神灵合并集于一身的结果。 (11)略相当于汉族的“宗族”,或历史上西南地区出现的“大姓”。 (12)指祖坟山。 (13)指西昌庐山上的白塔。 (14)送油香是在瓦片上加上火炭、猪油、荞面、柏香等烧着送到树神那里。 (15)多续青年马学伟告诉我们:“如果你这一家人和睦而你这家人有小神子的话,就会越来越发达,因为把别人家的东西搬过来。如果你这家人家庭内部不和睦,互相之间争吵,经常在那儿争吵呀,打、骂呀这种呢,小神子就不高兴,反而把你家东西搬出去,你家就越来越穷。” (16)见于德龙寺寺管会室内墙壁上《德合龙寺简介》。 (17)目前学术界大多将多续归于“尔苏”系统,多续语是尔苏语的方言之一。 (18)比如“大鼓和尚”,陈宗祥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调查冕宁多续时指出:“这类和尚懂藏文,会推算大卦和甲子,也懂天文、历法,并了解本部落的历史。他们会诵读很多经书,如万年历、医药经、山神经、水神经、祈祷富裕经等。他们拥有很多法器……。大鼓和尚常为人家作祭祀祖先、超度亡灵的道场,也给人家驱鬼医病,也会使用咒人的巫术。除有人邀请他们作法外,平时仍然从事农业劳动”。参见陈宗祥:《冕宁藏族苯教送魂九路初探》,载西南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史研究室编《民族文化史研究》(文集),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9)笃本“下方作镇压鬼怪,上方作供祀天神,中间作兴旺人家的法事”;伽本“精通各种超荐亡灵之术”,有“关于见地方面的言论”。参见土观·罗桑却季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20)笔者未能找到清咸丰县志原本,本段引文系转引自李绍明、刘俊波编《尔苏藏族研究》,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665页。 (21)笔者曾专门就此事求教于当地长者,他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过去大鼓和尚能把远近大小的神都请来,然后挨个送,少了一个都会对主人家不利;现在大鼓和尚没了,只有彝族毕摩能做到把神既请得来、又送得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