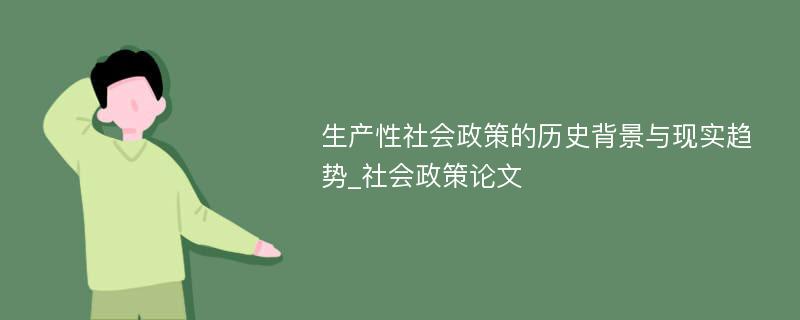
生产性社会政策的历史脉络与现实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脉络论文,走向论文,现实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359(2010)05-0052-06
社会政策的概念从1891年瓦格纳(Adolph Wagner)提出到现在,仍旧不是一个已经具有一致内涵的概念。作为历史产物的社会政策有必要回到历史中去厘清其起源、探究其背后的社会背景、梳理其内涵变化的过程及原因。由此,为把握其未来走向提供更可靠的依据,为学科建设积累资料。
本文以生产性社会政策(productive social policy)为分析讨论的对象,但讨论仅限在欧洲社会政策发展的经验上,一是由于生产性社会政策是源自欧洲特殊社会背景的,尽管即便在欧洲也未对它形成完整统一的认识;二是因为任何一种社会政策的理念都可能是路径依赖的,欧洲模式的有效性是很难移植到其他社会中的。但可以肯定,在发展中国家相似的问题也正亟待解决。
一、生产性社会政策的起源及内涵
社会政策起源于对社会问题的应对,“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历程来看,每当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新的变革时,尤其是在社会变迁时期,国家受到显著社会问题的困扰,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1]。梅志里(James Midgley)则将社会政策视为对社会问题控制的操作化。
社会政策的概念最早见于19世纪末期的德国关于社会问题的讨论中。当时的德国刚刚完成了国家统一,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劳资矛盾开始加剧,相应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尖锐。对于当时的德国政府来说,如何应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保障国家和社会体系的延续是一个重大问题,原来内涵比较宽泛的社会问题开始集中到国家生存层面的问题上来。在这一社会背景下,以瓦格纳为首的讲坛社会主义派(Kathedersozialismus)①创立了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这被视为社会政策的源头。对于瓦格纳等人而言,所谓社会问题是社会组织在经济自由竞争背景下的扭曲和工业资本主义对其社会责任的逃避。在这一框架内,社会和经济构成了一种深刻的对立的关系,“社会”成了经济的间接后果,社会危机成为了工业发展的对立面。可以说,早期的社会政策更多的是“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而不是公民福利的提升”[2]。
乔治·斯坦梅茨(George Steinmetz)指出,19世纪德国社会科学话语中“社会”(the social)这一概念的兴起是与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看来,所谓“社会”是一个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特定空间。市场是不受政治权力和“看不见的手”控制的充满内在危机和混乱的空间,其驱动因素是个体利益、经济理性以及破坏性竞争(destructive competition)。与之相反,社会是一个集体领域,是超越了个体的共享价值空间。在社会危机的背景下,正是“社会”这一概念使得以共同利益的名义进行干预成为可能,这些干预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失范——对社会结构的破坏、对政权的破坏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破坏。“干预逐步被视为对于社会问题的一种有效的解决手段,一种超越个人的控制。”[3]2
社会政策作为一种干预手段,嵌入到社会和经济的二元关系中。这一关系是构成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意识形态下社会政策多样性的基础。历史地看,这一关系很少是均衡的,蒂特姆斯(Richard M.Titmuss)将社会政策理解为经济的仕女,形象地表达了这一关系的一个侧面。早期社会政策被视为经济政策的一种,其理念基础是认为经济效率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社会组织来保障。
瓦格纳等人的主张催生了德国的社会改革,其直接表现就是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整个德国社会改革都是建立在预防性(prophylactic)理念基础之上的,强调对经济生产进行预先干预以应对社会成本的上升或大规模的经济效率降低问题。“作为一种预防性手段,社会政策是生产性的经济策略,而非慈善式的自助机制(philantropic selfhelp mechanism)。”[4]生产性社会政策由此开端。
这样看来,生产性社会政策或作为生产性因素的社会政策(social policy as a productive factor)并非某一特定社会政策的名称,它指的是某一类型的社会政策或者说是某一类型社会政策背后的支撑理念,是与将社会政策视为经济的负担或成本的观点相对立的。使用这一隐喻式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出社会政策作为资源的产出与生产活动的产出是可以比较的,社会政策本身是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或动力。在这一意义上,生产性社会政策承担了经济和社会之间桥梁的功能,用以表述社会层面上对于创造剩余价值或导致产出的社会资源组织的干预。社会政策生产性的另一方面的含义是认为社会政策是一种社会投资,一种有利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积累从而间接作用于经济效率的投资。
二、生产性社会政策的发展脉络
艾伦·沃克指出“早期社会政策进路称为‘社会行政’,它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将政府行动等同于‘社会’。第二,假定社会政策的目标是提高福利。第三,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5]17。在社会行政的框架下,政府要介入市场及社会之间,对“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构,在不同的目标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了不同的作用方式。在这一线索上,生产性社会政策的内涵发生了明显的演进,或是吸纳其他理念形成内涵扩张,或是面临被质疑、被拒斥的困境。
社会政策具有生产性或社会投资的理念均是根源于欧洲社会的独特传统,特别是与欧洲历史上的社会正义、社会团结等价值理念相联系的。可以说,将社会政策视为生产性因素是欧洲的特色。与此相对应,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政策多被视为对市场外溢效应的必要修正。总体上,生产性社会政策的发展并非直线式的,而是历经了数次反复。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石油危机的加剧和对欧洲社会经济生产力的关注,这一说法逐步淡出社会政策领域。而2000年欧盟《社会政策议程》的推出使得这一理念又重新得到政府及学界重视。总结欧洲社会政策百余年的历史经验,有三个重要的因素推动了它的演进过程。
第一是社会权利理念的兴起,在公民权利上升的社会背景下,社会政策的生产性获得了新的内涵。
19世纪末期社会政策中的生产性概念很少与个人安全或是社会团结的思想相关,更多的是一种道德理念,它只是一种针对社会下层人士的劳动力(manpower)政策,而社会权利理念的兴起则改变了这一状况。马歇尔(T.H.Marshall)认为契约权利(civil right)、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是从前至后演进发展的。社会权利视角下的社会政策,将其原有的问题取向(problem-oriented)进一步深化,即以“问题背后的问题”为目标,如贫困及其背后的社会排斥问题。社会权利理念的中心内容是将个体视为国家的生产性资源,“最终目的是要使公民可以从组织上融入社会”[6]。
社会政策是在回应保障个体安全和保证社会资源的分配以促进生产效率的二元挑战中建立起来的,这种二元性是公民权利和社会契约关系的反映。历史地来看,生产性社会政策通过主张社会权利对于经济效率的作用或多或少地试图合并以往的二元性观点,它把社会权利既视为个体安全也视为市场效率,以此来构建一个个个体参与和社会权利之间的生产性社会契约(productive social contract),或找到社会团结和个体安全之间的结合点。瑞典经济学家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也认为社会政策不是濒危植物的温室,而是通过提供最基本的安全以使个体在社会最大利益之下参与生产性活动。
第二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促使生产性社会政策内涵发生扩张。
随着20世纪3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起,社会政策成为质疑旧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在英国的费边主义(Fabianism)、瑞典的功能社会主义(functional socialism)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等思想中,社会政策的理念成为了提升经济效率的方法。生产性社会政策也在当时的劳工运动中找到了回应。
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在1932年指出:“现代社会政策是投资而非成本。社会政策的生产性来源于它的预防性功能,即防止社会经济体系中的问题发生。”[4]他批判斯德哥尔摩学派(Stockholm school)关于社会支出的论述,反对其将储蓄作为摆脱社会危机的方法。他认为,社会政策要解决的不仅仅是重新分配的问题,而是以国民收入增长为目标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因而,将社会政策视为一种生产性因素对于当代的社会民主主义具有战略性意义,它是推动彻底的社会改革的重要动力,它既是对福利国家扩大的重要辩护,同时也是对自由主义将社会政策视为成本和生产性资源的负担的反击。
生产性社会政策的理念顺应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发展,很多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不仅将其视为实现个体安全和再分配的方法,也将其视为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法。在这一框架下,社会在家庭方面的支出是一种对于累计总需求(aggregate demand)的投资,家庭政策成为对未来社会资本的一种投资,即通过对公共服务的广泛投入,使得妇女和儿童等群体也能与宏观的经济发展相平衡。同时,失业保险和福利津贴也成为缓解社会资本缺失的手段。生产性的社会政策这一理念一下子成了通过扩大福利国家来进行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工具,它使得原先对立的经济和社会的关系被正相关关系所替代,这样,团结和安全并不会有损于经济效率而成为其先决条件。于是,团结、公平、安全的概念和生产力与效率联合在一起。
第三是随着福利国家危机而来的对生产性社会政策的普遍质疑。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福利国家危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模式的终结。从经济层面来看,这一危机的导火索是石油危机,但从社会层面看,这一危机的实质是所谓“社会”产生的消极结果。“借用唐泽洛特(Jacques Donzelot)的社会自决(autonomization of the social)的概念来形容当时的情况是极为准确的,也就是当社会优于经济时,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的危机。”[4]社会和经济关系的逆转带来了对于个体生产性能力和公民权利之间联系的质疑。1968年爆发的对福利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次对以政府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质疑,也是一次对劳动力的社会组织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福利合同的质疑。同时,批判性的社会科学和新的社会运动对于战后公民权利有关的团结、平等和安全的概念也产生了质疑。这一系列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社会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被称为与战后精英式(technocratic)社会改革的断裂,也被视之为社会改革和经济效率之间连接的断裂,其直接后果是社会政策被与资本主义福利模式对于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失败联系了起来。
于是,社会政策的问题取向也发生了转移,社会问题由原来在工业资本主义和福利改革框架内解决的问题转移到了这些框架本身的问题。仍以贫困问题为例,现代的贫困是劳动力市场以外人群的贫困,它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正常结果;旧的视角下的贫困是对社会团结的破坏,而现代贫困则通过排斥不参与社会生产力活动的群体,形成了福利国家有组织劳动力和资本主义市场之间妥协而成的社会团结。历史上,贫困是导致社会动员(social mobilization)的原因,但现在对于少数人的排斥反而成了促成另一些人融合的动力,贫困成了一种惩罚。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社会排斥和融合造就了新的社会分化(social divide),福利国家似乎正在通过贫困文化和标签理论创造着贫困,而这与福利国家的根本目的是背道而驰的,排斥或边缘化的概念是和公民权利相对立的。
生产力发展的停滞和社会成本的上升构成了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在这一背景中社会政策被与成本一方联系起来。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洛夫·帕尔姆(Olof Palme)在对于社会政策的批评中指出:“社会政策并非投资而是资本主义对社会资源的破坏的代价,是评估国家发展中不能忽略的成本。”[4]这一批评的主旨不是质疑经济发展在社会方面的结果,而是将“社会”视为经济危机中的关键因素。
维瑟(Jelle Visser)指出:“福特主义福利国家(Fordist welfare state)以及凯恩斯经济政策终结的过程是和社会政策从经济政策中外化的过程并行的,社会政策不再是经济政策的附属物,开始与在分配和消费紧密联系起来。”[7]然而,积极地创造增长和竞争却导致了对于社会政策是否是一个生产性因素的质疑,这一质疑使得社会政策逐步成为需要通过经济中更具生产性的剩余供给而获得财政支持的成本。储蓄和削减成本作为社会干预的方法正是建立在对于社会政策是一种成本的认识上的。
从讲坛社会主义到社会投资,在不同的时期生产性社会政策体现着不同的内涵,既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效率的干预思想,也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思想。在国家社会政策操作层面上:“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开始在提升国家竞争力和欧洲一体化的名义下,对于各国原有分散的福利国家机构进行拆解,当时,社会政策被视为主要的经济发展的障碍。”[8]193在经历了大约10年的经济一体化和社会服务成本的消减之后,为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的风险和挑战,强调社会政策作为生产性投资的视角又开始回归。欧盟《社会政策议程》提出了社会欧洲(Social Europe)的建设目标,它强调社会政策与经济互动的历史福利国家模式,即社会福利的目标在经济政策中占据重要位置,并且认为社会政策具备了诸如生产力(productivist)的鲜明的经济特征。“生产性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欧洲各国共建社会欧洲的过程中,这一概念对于欧盟形成对于社会政策的共识尤为重要。”[9]
三、生产性社会政策的争议与现实走向
虽然最近20年以来,“生产性”、“投资”开始成为社会政策领域的一些重要话语,但仍不能乐观地认为社会政策已经掌握了对新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生产性的理念在历史上已经是一个国家通过干预促进经济效率增长的手段了。梅志里认为生产性的理念源起于新政和凯恩斯-贝弗利奇时代,蒂特姆斯则将生产性的理念追溯到20世纪初的英国扩张战争时代,那时士兵恶化的健康状况成为对英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
本文在生产性社会政策的演进脉络和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已经展示了对于其内涵的基本争议:即生产性对于社会政策而言是可能的吗?或者说,社会政策究竟是一种投资还是一种成本?仅就欧洲经验来看,这也反映了欧洲对于走向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还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争议以及从民族福利国家社会到社会欧洲的争议。社会政策由于其诞生就以国家财政作为主要的运作来源,将它视为一种成本的观点似乎更易为人所接受。但就其“生产性”而言,北欧模式似乎也提供了一个例证,即社会政策可以促进经济效率。
全球化为欧洲带来了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当欧洲正忙于应对老龄化、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崛起等问题的时候,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形成,如艾伦·沃克所言:“对社会政策的最大挑战并不是社会经济的或人口的挑战,而是政治上的挑战:一种与欧洲社会模式对立的经济意识形态的兴起。”[5]40在这一美国模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框架下,被称为“左派供给方议程的(a supply-side agenda for the left)社会投资理念”所强调的生产性社会政策将会接受更苛刻的质疑。
不仅如此,围绕社会政策生产性的多元概念也是带来争议的原因之一,例如发展型社会政策(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尽管本文的目的不是辨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但仍有必要明确他们在基本层面的一致和差异。张秀兰等认为,所谓发展型社会政策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称为积极的社会政策,有的称为社会投资”,“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就是因应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压力而提出的,它的基本特征是:使社会政策具有生产性”。[10]7-9在这一层面上,生产性社会政策与发展型社会政策内涵是重合的;发展型社会政策中强调的动态思维和注重中长期战略理念则非生产性社会政策关注的重点,后者强调的仍旧是在经济的框架内社会政策的结果或经济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多数学者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西方社会政策的发展正在经历一个从再分配范畴到经济生产范畴的转变,哈德森和科尔纳通过对OCED内23个国家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的比较研究后认为,可更具体的将这种转变称为“从保护性向生产性的转变”(from protective to productive)[11]。
然而,争议也将长久地持续下去。在艾伦·沃克看来,欧盟对于社会政策是一种生产性要素的强调,无非是对蒂特姆斯提出的社会政策的仕女模式的强化,社会政策的未来,显出了一种“愈来愈附属于经济的倾向”[5]41。
对于生产性社会政策争议的根源与对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争议,以及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宏观的国民经济产出和微观的个体及家庭之间的关系的争议,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对于上述关系的优先次序的判断是不同的。生产性社会政策理念是应对社会问题的一种主动的(proactive)而非被动的(reactive)反应。强调社会政策的生产性一面对于欧洲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的经济一体化和社会分裂之间的分裂症的应对,是重建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使社会政策成为欧盟各成员国应对大规模的社会排斥、长期失业和生育率下降的手段。
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即便形成广泛的共识,生产性社会政策能够承载如此多的理论期冀吗?根植于欧洲的社会政策的生产性理念正在以及还将如何影响欧洲的社会政策走向?
艾伦·沃克认为:“社会政策未来的发展轨迹,可能是国家的发展阶段与该国所经历的福利历程的函数。”[5]39生产性社会政策之所以重新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欧洲面临着全球化对于欧洲社会模式的冲击,迫切需要一种有力地回击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强势地位及其自由主义经济的影响,确立欧洲更大层面上的社会团结的工具。这使得欧洲社会政策的走向显现出一些明显的趋势:
一是更为明确的投资理念。新福利国家的设计师马歇尔在20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社会投资的概念。在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中,也区分了传统的福利国家和新型社会投资国家,吉登斯的机会平等的概念是和结果平等相对的,机会的平等是一种投资,而在传统福利体系中它是一种供给(或成本)。投资理念更多地关注的是工作而不是补贴救济,是责任而非权利。简而言之,投资国家就是工作福利国家。吉登斯这一理念也反映在作为欧洲现代化的路线图的《社会政策议程》中,通过建立一个积极的福利国家,投资于人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政策是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是知识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的生产性因素。
诚然,即使在《社会政策议程》也并没有把所有的社会开支和社会政策都视为对人力资源的投资或生产性因素。辨别哪些政策是投资,哪些政策是成本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政策目标的转向,即从补贴救济和消极福利转向就业能力(employ ability),从纠正失效转向推动市场更加有效。
二是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合理念。《社会政策议程》指出:欧盟社会投资的概念主要是对社会排斥的回应,同时建立经济活力和增长的基础,即所谓“生产性”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人物——被排斥的群体。社会排斥指的不光是物质的贫困,更是被拒于社会契约之外的状况,正因为如此,社会排斥也是对作为社会基础的社会契约的威胁。《社会政策议程》中强调的社会排斥,指的是在当今全球发展背景下被排斥者的技术缺失。所谓被排斥者指的是在知识社会劳动力市场中缺乏相应的素养的群体、缺少抗风险能力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例如移民、少数族裔、妇女、单亲母亲、残疾人,也就是哪些无雇用、无技术、无知识的群体。传统福利国家的体系中,这些群体并非生产性劳动力储备(productive labour reserve),他们缺乏能力不具备什么生产性;而在社会投资理念的框架中,认为可以使得这些被排斥的群体具备劳动力市场所要求的相应的能力,因而,社会投资成了促进社会融合的途径。
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认为:“从福特主义福利国家到熊彼得的工作福利国家,从再分配福利权利到工作福利是对社会政策生产力的重建(productivist re-ordering of social policy)。”[12]13他强调生产性参与是一种重要的权利,这与历史上的传统福利模式强调个人的生产性能力是不同的:社会政策反映了一种责任话语,生产性参与被视为公民权利的基础。生产性社会政策作为工作福利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最终制定具有生产性的社会政策总要落实在“工有其酬”(making work pay)上,使劳动力市场和福利救济相比起来对于个体而言更具吸引力,就需要有效地手段对个体进行刺激。在《社会政策议程》中,社会团结的概念就是机会的平等,即平等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
三是更明确的社会质量理念。艾伦·沃克指出:“质量”已被作为欧洲社会政策的核心主题。社会质量概念的提出旨在为欧洲社会模式的可能内涵提供一种愿景,并通过使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服从于社会质量这一目标,彻底改变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倡导,由社会质量的理念来统一社会政策的目标及手段或许将成为一种新的模式。
四、结语
历史视角下的生产性社会政策是一个在欧洲福利国家背景下不断变迁的产物。它说明社会和经济是相关联的领域,一方变化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要在另一方中体现出来,生产性社会政策作为一个结合点,是重构经济效率与社会发展之间联系的重要方法。欧盟在按照阿姆斯特丹条约(Amsterdam Treaty)和里斯本峰会、尼斯首脑会议的目标进行欧洲社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作为生产性因素的社会政策是经济有效增长的前提条件,也是欧洲在面对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竞争优势。
当今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在围绕劳动力作为生产的中心因素而重建,工作福利作为一种有前提条件的福利,逐步扩展到对劳动力市场以外的群体身上。生产性社会政策的作用在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个体的生产性参与和社会团结之间的社会契约,通过将社会政策视为一种对于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利的投资,促进生产性参与和社会融合。在这一意义上,它承担了经济和社会之间的桥梁的功能,用以表述社会层面上的对于创造剩余价值或导致产出的社会资源的干预。因而,欧洲社会政策被视为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呼应,创造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广泛的社会融合的案例。这对于诸如中国等新兴民族国家的启示作用尤显突出。
在生产性社会政策的框架中,很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但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为了创造经济效率有必要对经济实施控制,社会政策作为生产性因素或社会投资应有所作为。
注释:
①“讲坛社会主义”起源于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这并非一个确切的名称,而是指的以瓦格纳等人为首的活跃在德国大学社会科学讲坛的一批人,他们倡导社会改革但反对马克思主义。该派的基本原则是:经济、社会生活与国家密切相关,国家必须进行引导规范,反对利益霸权。其思想还影响了英国的费边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