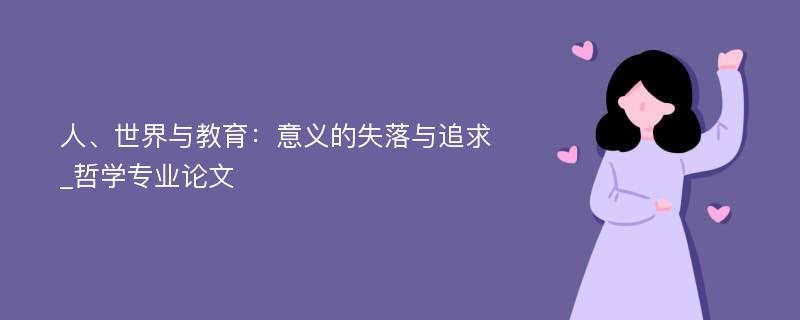
人、世界、教育:意义的失落与追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当代教育面临着意义的失落与重建。理论层面,应在深入反思教育存在之根本的基础上构建整合人文与功利的回归生活的教育理论体系;实践层面,应实现由主知教育向生活教育的提升,把智力的开发转换成意义的生发,在广泛的交往中把人引入世界。人、世界、教育构成一个真实的意义的世界。
一、人、世界、教育
(一)世界是什么
世界,world,意指the universe,everything(宇宙,万有,万物)[①]。世界是物质的,但世界不等于物质。世界不是物的集合。世界是“一切事物的总和”[②]。“物”拓展于空间,“事”延宕于时间,世界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事”是有“物”的“事”;“物”是有“事”的“物”;构成世界的“事”“物”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作为整体的世界不等于部分之和,即世界不能还原为一件件“物”,一个个“元素”。世界的每一物都是世界的产物,是“世界的物”。“世界的物”蕴含、传递、表达着“世界的事”、“世界的信息”。故每一物,连同它所覆载的“信息”,构成一个“小世界”。人通过与“小世界”交往去认识“大世界”。
世界总是有“事”的“世界”,“事”是“活”的、开放的,世界亦是“活”的“世界”。“活的世界”蕴含着诗意、美、意义,我们说,世界是诗意的、美的、意义的。世界的诗意、美、意义只向那些懂得这种“诗意”、“美”、“意义”的人呈现出来,它不会自在地呈现。世界呈现在理解并接受它的人的面前是“诗意的世界”、“美的世界”、“意义的世界”,而呈现在不理解也不去理解它的人的面前则只是“物的集合”。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世界“观”。
(二)人与世界
动物“有”花,“有”草,“有”山,“有”水,但动物“无”“世界”。人不仅有“有”花,“有”草,“有”山,“有”水,而且“有”“世界”。“只有人才‘有’一个‘世界’,动物混同于世界之中,所以‘有’是人与‘世界’的一个最有力的基础性的关系,……就象世界向我们提供五谷杂粮一样,‘世界’、‘物质的世界’,不仅是‘我(们)’的‘物质’的基础,同时也是‘我(们)’的‘精神’的基础”[③]。人不仅存在而且能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人的“意识”拓宽了存在的内涵并改变了混同于动物存在的本质。人在世界中存在,与世界交往,建立关系。从根本上说,人与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并不是“纯物质”的,因为人不是动物,纯粹地与世界发生占有自然物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不是“纯精神”的关系。人具体地实实在在地生活在世界中,人在世界中生长、交往、劳动、思想、创造、收获、奉献,人在世界中展开生活与人生。人“有”一个“世界”,但并不是“持有”、“占有”,而是“生活”“在世界中”。“世界”是人的“生活”的“家园”。
人在世界之中,“我已住下,我熟悉、我习惯、我照料”,“我居住于世界,我把世界作为如此这般熟悉之所而依寓之、逗留之”[④]。人并非纯粹地“占有”“世界”,人理解它、欣赏它、亲近它、称谓它、吟诵它,而非单纯的利用它、操纵它。世界原本是有声有色的活的“世界”,活的“世界”向人展示出它的“活”,人进入这个“世界”并领略其中的“意义”。人“享有”这个“活”的“世界”,领受、欣赏、看护、赞美这个“世界”。
“‘在世界中’来‘看’这个‘世界’,‘世界’就不是静观的‘对象’,而是‘交往’的一个‘环节’。”[⑤]人在世界中“烦忙”,力图去改造世界,使世界更好地“为人”。要使世界更好地“为人”,人亦必须更好地“为世界”。世界不仅是“为人”的,而且是“自为”的。世界只有是更好的“世界”,才可能是更好的“人的世界”。人改造世界的“改革”是有限度的,人只能依凭世界的“事”(规律)去改造世界。常言“征服世界”,“征服”的并不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只是世界中的“物”,而不是“物”中的事,不是规律,“世界”本身并不是一“征服”的“对象”。我们改造“世界”,建设“世界”,使“世界”更多地富于“诗意”、“美”、“意义”,使世界“世界化”。人更多地领承“世界”的“诗意”、“美”、“意义”,更好地“生活”“在世界中”。在此意义上,使世界“世界化”即使世界“人化”。
(三)人、世界与教育
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不断发生、发展变化的。人并非一生下来就“有”一个“世界”,就“在世界中”。人对世界的开放性,使人有可能去亲近“世界”,领略“世界”。“世界”启发人的感觉和思维,启发人的思想与精神、情感与智慧。人在“世界”中交往,被抟塑、被改造、被锻炼。“世界”是一本“大书”,“活”的“书”;“世界”是一大的“课堂”,“活”的“课堂”。“世界”培育了“我们”,“世界”使“我(们)”成为“人”。我们在创造“世界”之先,“世界”“创造”了我们,世界首先教会我们如何去“创造”。这个过程乃是教育的过程。
教育的过程即把个体带入“世界”“之中”,让“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人的生活的世界”。陌生于“世界”的个体受教育导引,逐渐地进入“世界”“之中”,让“世界”不断地成为“我”的“生活的世界”。“我”“在世界中”生活,“我”的“世界”的品质成为“我”的品质。在提高“世界”的品质的同时也提高了“人”的品质,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了“人”自身。
世界本是同一个世界,人却是不同的“人”,人的实际的“生活的世界”千姿百态、各不相同。我们都在世界之内去“看”这个“世界”,“听”这个“世界”,但许多时候许多人却“看”而“不见”,“听”而不“闻”。世界不会自明地彰显世界之为“世界”,只有那些能“看”“世界”、“理解”“世界”的人,才能“理解”“世界”的意义、发现“世界”的美、领略“世界”的诗意。教育启发人去“看”“世界”、“理解”“世界”、“发现”“世界”、“体验”“世界”,从而真正地进入“世界”,“在世界中”“生活”。
人在世界中,人在教育中,教育要引导人进入“世界”,让世界成为“人的世界”,人和世界都必须“在教育中”。人、世界、教育玉成人之为“人”。教育因为揭示“世界”的意义并启发人的意义而获得自身的意义,世界的意义、人的意义、教育的意义由此获得统一。
二、从和谐到征服与从人文到功利
文明伊始,人类尚把自身混同于世界之中,依赖自然而生存,世界赐与人们 以祸福,故初民对世界怀有一种内心的虔敬与畏惧,当然不敢扬言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古希腊前苏格拉底时期,希腊人已开始“把整个自然界看作人和神的伪装、面具或变形”,在他们看来,“人是事物的真理和核心”[⑥]。司芬克斯半人半兽的形象表明,人类已经意识到自己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已经从自然界、动物间抬起头。但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更多地看到的是人与世界的统一,如赫拉克利特所言,“世界是亘古岁月的美丽而天真的游戏”[⑦]。
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毫不留情地撕开了那“美丽而天真的游戏”。对于苏格拉底而言,作为思维者的人才是万物的尺度(笛卡尔),他提出“认识你自己”,他的思想、人格与行为成为追求知识与美德的楷模,也成为激励人们去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文化先驱。亚里士多德秉承这一精神而成为古希腊文明的集大成者,他把知识加以分类,并奠定了整个西方文化科学知识发展的基础,也由此而开始“世界”不仅作为研究的“客体”,而且被分割而列入不同的知识范畴视野之中。
分析的智慧带来了西方科学文化的繁荣。中世纪宗教的神秘色彩给自然或世界以某种“附魅”(enchanted),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把人稳定地移向宇宙的中心,把世界置于科学的关照之中,“知识就是力量”,人类不愿再顺从世界或自然的秩序,而力图征服世界,控制世界,世界不再是负载人生意义与伦理价值的“附魅”的宇宙体系。伴随16、17世纪的科技革命,世界逐渐成为物的集合的场所,一切自然物被统统“去魅”(disenchanted)[⑧]。自然界的事物不再与价值、意义相关,它是纯客观的、独立于人的、非生命的。自然被物化、数学化,世界展示为客观物的世界,世界的诗意开始隐退。
人类不断地改造世界,世界也在不断地“改造”着人类。人本是世界中的人,是“世界”的人,当人以功利化的心态去应对周遭的世界时,人自身亦被功利化。“我们同周围大多数人之间只能建立有限的相互介入关系……我们是以实用主义来确定我们同大多数人的关系。”[⑨]我们以实用主义来确定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同世界同样只能建立有限的相互介入关系。人的世界的简单化,意味着人自身的简单化。人类处于征服世界、改造世界以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来赢得“美好生活”的积极进取的热望之中,“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⑩],人因此而成为“单向度的人”。
与此同时,人的生活诗意与生活意义缩减。在认识世界、征服世界的进程中高扬的是人的工具理性,“我(们)”始终作为依凭理性来审慎世界的主体,世界始终处于“它之国度”,“我(们)”不可能把自我完全交付其中,沉浸“在世界中”,去体验这个“世界”,领略“世界”的诗意和意义,“我(们)”遂不能藉与世界的交往来启发个人的生活诗意与意义,意义的失落在所难免。“理论或理智的片面高扬意味着人失去了诗意的存在状态,人不再生活在感性的因而是诗性的自然中,而是在静寂、冷漠客观的环境中寻生计。”(11)不仅如此,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生态失衡、能源危机、战争威胁、核武器的恐惧等构成现代人真实面对的“文明危机”,更加重了现代人的意义危机。
教育是建构人与世界关系的中介。“经验与功用造就人‘与’之世界的基本关系。……随着‘它’之世界的扩展,人之经验能力与利用能力也持续增长。人越来越多地获致这样的能力:以‘学习知识’这一间接手段来取代直接经验,把对‘它’之世界的直接‘利用’简化为专业性‘利用’。人不得不一代代将此种能力传递下去。”(12)现代教育一开始就适应了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力量,人始终作为被武装的手段而投入于现代教育之中,功利性成为现代教育的首要特征。功能化的世界,功利化的人生与功利性的教育相统一。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13)这样,科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占居主导地位,人文教育退居教育的边缘,价值与意义不可避免地为功利所湮灭。现代教育给学生开设了各式各样的课程,但通过教育,学生获得的并不是世界整体的印象,而是支离破碎的知识的堆积。学生在其中感受到的更多的是知识的压力,没有通过知识而积极地启发世界的意义,也启发人生的意义。人在教育中感受不到意义的充盈与生活的完满,亦感受不到教育的意义。世界、人生、教育共同面临着意义的失落。
三、回归生活世界:意义的追寻
应该说,人类在近两个世纪内改造世界、征服世界的过程中获得的成功是无可比拟的。人类不仅实现了外在的生存条件的日新月异的改善,而且获得了科学技术本身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得以将征服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不断推向前进。但与此同时,人的内在生存境遇却并未同步上升。20世纪的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诸层面面临着经济与伦理、科学与人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传统与现代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分裂、失衡。“理性性价值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在当代主要已不再是肉体的,而是精神的,即人的意义世界的埋葬。”(14)深入反思人类的生存境遇,反思人与世界的关系,成为穿越世纪的主题。
随着人类的认识能力的提高。科学文化得到了发展,人凭藉科学去认识自然、改造世界,这本无可非议。但随着人们改造世界的成功,科学与理性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从而笼罩了人的整个视野,使人遗忘了就在他身边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明确提出,欧洲的科学已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并非具体科学本身的危机,而是因之而引起的文化危机,是人自身的危机。人们被实证科学的表面繁荣所迷惑,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理想化的科学世界遂偏离了关注人生问题的理性主义传统,把人的问题排斥在科学世界之外,科学同人的存在分离,科学失去了意义,人在对科学的迷信中亦失去了意义的世界。胡塞尔率先倡导向生活世界回归。在生活中,人和世界保持着统一性,这是一个有人参与其中的、保持着目的、意义和价值的世界。“现存生活世界的存在意义是主体的构造,是经验的、前科学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义和世界存有的认定是在这种生活中自我形成的”(15)。
维特根斯坦提出了“生活形式”,通过回归生活形式,把语言从抽象的逻辑王国拉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意义世界,试图为陷入危机之中的科学世界和人文世界提供一个内在于生活世界之中的意义世界。“他对生活形式的回归实际上就是在寻找被实证主义所遗忘的人的世界和生活的世界”,“寻找作为生活形式的语言是寻找一个安宁的家”(16)。
海德格尔把“此在”而非单纯把人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此在”就是“去存在”,就是“在世界中存在”。“在世界之中”就是同世界相亲熟,“熟悉之”,“依寓之”,“逗留之”。人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先于主体自我意识。人的存在过程在时间中展开,先于解释、反思、认知。人对自身存在的关心,意味着人关切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关切他与世界的各种联系。关切的对象,是包含着人类自身在内的整个的存在世界。这种关切表现在对存在的理解中,就是要求在人的存在与他所处的世界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这样,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命题被转换成“我在故我思”,“我”先在这个世界中存在,才能在这世界中“思”、“思”这个世界。不是“在”去回应“思”,而是“思”要回归“在”;不是人的生活向理性与知识回应,而是理性王国向生活世界回归。“生活”重新作为人与世界的根本的基础的关系在现代人的视域里凸现出来。人与世界的关系由征服而逐渐转换成平等与对话。“对话关系不仅消解并超越了抽象普遍性对人的统治,使普遍—特殊结构向整体—部分结构转变,而且还消解并扬弃了人的自我中心结构,使人的存在获得了开放性和创造性。”(17)人重新向世界开放,在“附魅”与“去魅”之间,利用、操纵与欣赏、理解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对世界保持适度的“温情与敬意”,以谋求平等与对话,在对话中参与世界意义的生成,并启发、创造人生的意义。
当工业、科学、技术推动着教育向前发展时,教育思想领域也始终没有放弃教育意义的追寻。从卢梭、裴斯泰洛其到福禄培尔,都坚决主张遵循自然的儿童教育,反对压抑儿童的天性,强调教育应发展人的天赋的内在力量,把教育的目光指向人自身。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人文科学”的复兴和大发展,教育领域中出现了“人文学科观点”的时代。在德国,以狄尔泰的生命哲学和精神科学方法论为基础,出现了“文化教育学”,反对实证主义、理智主义,坚持以完整的、生成中的人的生命为根据来考察教育现象,主张生命是完整的,教育应培养完整的人格。20世纪30年代的实验的、科学的教育,忽视甚至排挤人文学科和人文精神的教育,这一情况促成了1930年前后至二战前出现的永恒主义教育运动,明确提出自然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和科学的哲学及其在学校中的教育实践(占优势)是不合适的,学校需要有来源于除自然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学说以外的指导价值和标准。二战后,西方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再度消解了教育思想领域中的人文精神,直至五六十年代,当人们关注全球性的问题时,人文主义的教育学日渐上升到教育理论中的主导性地位。存在主义教育学强调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强调个人的“自我创造”、“自我设计”和“自然超越”,强烈反对“人格异化”。教育人类学依据哲学人类学和生命哲学的成果,探讨人的“完整的”存在。强调教育应遵循人的天性,关注人并增进人的完满的存在,这在理论上促使教育得以超越功利的趋向,捍卫了教育的意义。应该说,教育哲学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要求,即教育开始了在哲学的高度来反思教育的方方面面,追寻教育的意义,如奥地利马丁·布伯和美国尼勒用存在主义哲学观来说明和解释教育,认为教育的目的和价值在于使人深刻地理解人生,发展人的个性(18)。
但是,在实践领域,受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推动,教育自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以统一的教育技术、统一的课程、统一的教育程序,制造成统一的标准的教育成品,不关心世界与人的价值和意义,服膺于外在的目的,功利性淹没了教育的内在意义,也不去追思教育的内在意义。贯穿教育过程始终的是如何有效地致知,强调知识技能的学习掌握,并不关心知识技能对于人自身的意义,古典人文教化转换成知识技能训练,并且一直兴盛不衰,甚至还随着教育的技术化水平增强而更趋强化。众多教育改革改来改去大都跳不出主知主义的背景与框架,多具改良色彩。20世纪上半叶的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把社会生活移进课堂以取代传统的知识教育,可谓彻底的反正,但由于他没能很好的处理教育与知识这一现代教育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使其发动的进步教育运动难免不了了之。传统主知教育的根基尚十分牢固,人们开始思考“教育改革的限度”(挪威,波尔·达林)。
教育的意义究竟何在,教育何以捍卫自身的意义,教育何以应对人与世界的意义,这些都成为世纪之交的迫切问题。
四、当代教育的命题:意义的重建
教育置于人与世界之中。人类对世界的征服依赖教育来支撑,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改善同样也离不开教育的支撑。教育的发展植根于人类生存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与教育密切相关。当人类与世界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危机时,教育应当积极关怀人与世界关系的改善,关怀人与世界的命运。
长期以来,教育不能主动而有效地选择、消化并汲取社会对教育的影响,教育缺乏这种充分消化吸收的能力。教育目的在教育实践中是不言自明的,或者说不是一个教育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实现此目的。在教育范围内关注的是“怎么做”而缺乏对前提“为什么做”的充分反思。即使教育思想领域提出了合理的教育目的,也并没有内化而成为整个教育的“声音”,目的与内容、手段、方式、方法彼此脱节。教育科学名目繁多,但大多数只是从不同角度来解释传统的教育视域,并没有充分拓展教育的视野,把教育置于“世界”之中,立足于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探讨教育的根本问题,反思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其存在本身的根本意义,并由此而展开整个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所以,“繁荣”的背后难免“思想的贫困”。当前,教育的改革必须先从理论层面上,打破先见,突破“限度”,而向“世界”,实事求是,去建构富于时代特色和长远意义的教育理论体系。
教育是培养人的,人的根基在世界。没有“世界”的教育是“无根”的教育。人“在世界中”生活,这是教育的基本事实,是教育的起点,亦是教育的归宿。教育必然地在人与世界的生活关系中展开并经由教育进一步拓展人与世界的关系,把陌生于人的外在的世界转换成人的“生活的世界”,建构人与世界的活泼、丰富的富于意义的关系,改善人的生活品质,充实生活与人生。完满的世界、完满的生活与人生、完满的教育相统一,世界的意义、人的意义、教育的意义相统一。当代教育应以人的生活为根本立足点,以人与世界关系的改善为根本指向,建构整合人文与功利的向生活世界回归的教育理论体系。
从“学会学习”到“学会生存”、“学会关心”主题的转换,意味着当代教育开始了一种不自觉的转型。“在文明人那里,随着知识的不断增长和积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认识、知识成了第一性东西,欲求和意志则成了认识的仆从。仿佛人一诞生下来他的全部生命就是认识世界,对他来说似乎从来就没有一个生存问题……他们受的教育越多,他们的思想就越包裹在一层坚实的知识硬壳之中。……现代文明人对知识的崇拜更为严重,只有当他们的生存被撕开一个裂口,即面临巨大灾难时,他们的目光才会重新回到生存问题上来(19)。人们越来越多地经由知识的积累而获得了谋取生存的“力量”,人们的自立性越来越高,独立性越来越强,在人们心目中人越来越少地直接依赖于他人,依赖于外在世界,故人也越来越多在疏离他人与世界。人受功利性驱使不断地获取知识,向前探索创造,却遗忘了人的生存本身。教育引导人不断地求知、致知,掌握技能,以顺应于社会,却遗忘了教育自身究竟是什么,应该做什么。在此意义上,20世纪后期的教育命题“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就不仅仅是一句针砭时弊的口号,而是指涉人类生存命运的关切,它呼吁人关心自我生存本身,关心他人,关心生存于其中的世界,在此关心中实现人性的复归与完满,也实现教育向自身的回归。
在实践层面,要完成主知教育向回归生活教育(20)的转换与超越决非一夕之功,当前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轨可以说是一个全面的开端。
在人类大肆开发自然的同时,人自身也成了开发的对象——并非把“开发”作为完善自我的手段而更多地把“开发”本身作为了目的——人类藉不断科学化的教育象开发自然那样地开发人力资源(21)。故知识技能掌握与人力开发是当代教育的核心。当我们要转换主知型教育时,并不是排斥知识技能掌握与智力、体力、心力开发,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引导学生去理解世界,去“看”世界,去“体验”世界,理解人生,“体验”人生,理解人与世界的关联,在此“理解”中领悟世界的意义,践行教育的意义,启发人生的意义,从而把知识掌握、人力开发与对生活的理解密切结合,知识与人生经验融合,生活自然地整合教育的影响,教育及时而有效地充盈生活与人生。所以,在教育实践中,要把“理解”作为教育关注的核心,在“理解”中实现教育的“内化”、“潜移默化”、“人文教化”,把人力开发转换成意义的生发,把知识教育提升为生活的教育。
教育要切实地拓展并深化人对世界的理解,还必须关注交往实践,时刻把人引向与世界的交往,拓展交往的广度与深度,提高交往的品质,在交往中实践人与世界的关系,人经由交往不断地“在世界中”去生活,不断把陌生于人的世界转化成人的“生活的世界”,完善“生活世界”的品质。这样,交往就不仅是教育的一个环节,而是教育的整个环节,即教育就是为了人与世界去交往,去“打交道”。
人在教育中,即人在与世界的交往中,人在理解世界意义的“理解”中。人通过完整地理解世界意义、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启发人自身的意义,故人在教育中即人在意义中。由此,世界、人生、教育彼此关照,交相辉映,构成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意义的世界。
注释:
①《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
②《古今汉语实用词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⑤叶秀山:《美的哲学》,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页、第43页。
④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67页。
⑥⑦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1页、第72页。
⑧参考吴国盛:《追思自然》,《读书》,1997年1月。
⑨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震荡》,第104页。
⑩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中译者序,重庆出版社1983年。
(11)朱红文:《人文精神与人文科学》,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29页。
(12)马丁·布伯:《我和你》,三联书店,第56—57页。
(13)斯宾塞:《教育论》,人教社1962年,第43页。
(14)(17)何中华:《回到自身:世纪之交的哲学重建》,《学术月刊》,1995年10月。
(1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81页。
(16)尚志英:《寻找家园——多维视野中的维特根据坦语言哲学》,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98、204页。
(18)参见桑新民:《呼唤新世纪的教育哲学》,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5页。
(19)俞吾金:《问题域外的问题——现代西方哲学方法论探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16页。
(20)本文所言的生活教育不同于杜威的生活教育,亦不同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请参考拙作《试论教育与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1986年第4期。
(21)从当前名目众多的智能开发工程和儿童从小就要遭至的繁重“开发”教育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