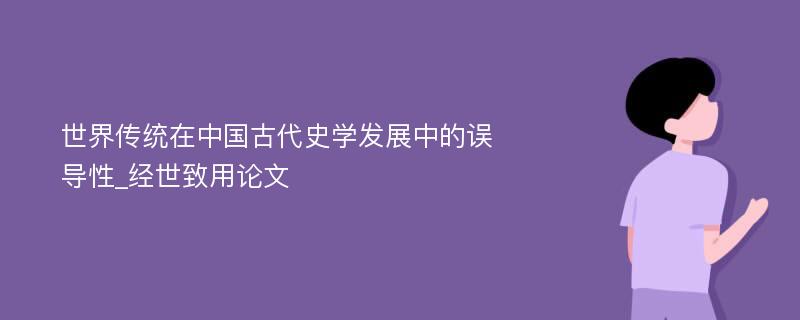
经世致用传统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误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史学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社会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们由务虚而趋务实。在这种全新的社会价值取向面前,史学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史学究竟有什么价值?在新形势下史学如何求得发展?史学发展趋势如何?当今史学研究存在什么缺失?怎样弥补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等等,问题接踵而至。为寻求在这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史学的新发展,史学研究者必须对上述问题予以研究和探索,像文学有文学评论一样,建立史学评论。对此,学界虽已有所涉猎,但还远远不够,犹应进一步深入的探究。为此,我刊从1996年首期开始,特设“史学价值与史学自身发展探索”专栏,在一定时期内对上述问题进行集中探讨。我们衷心希望本专栏能得到史学界同仁的深切关注,欢迎具有高质量的有关论文投往本专栏,我们既欢迎名家的大作,也欢迎中青年学者具有开拓创新性的篇什,鼓励争鸣。我们坚信,有学界同仁的热心关怀和大力支持,本专栏一定会达到预期目的,为史学跨世纪的发展尽绵薄之力。这是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应当为她矢志不渝地努力!(注:因版面有限,来稿一般应在8000字以下)
内容提要 历来对中国古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多持肯定态度,本文则着重论述了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消极影响。文章从中国古代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中挖掘了经世致用观念的思想文化根源,指出它虽是史家以史学为工具去介入干预现实,从而表现出中国学者所一向标榜的积极入世精神;但它实际是学者们自觉不自觉地误入专制政治的陷阱之中,使史学变成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致用工具,从而丧失了史学自身的独立学术品格。在近代以来兴起的科学民主的学术潮流中,经世致用传统固有的不足愈显不合时宜。摆脱致用功利意识,建立以求真为第一义的学术发展范式,乃是中国史学的现代化希望所系。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它强调的基本倾向是史学研究要具有为现实服务的实用功能。如史法经世乃其表现之一,它通过对所载史实以纲常名教的标准予以是非善恶的褒贬,从史学角度介入和影响现实。虽然由此表现出史家的积极用世态度,但却使史学染上强烈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历代统治者从史学汲取治术的做法,对之进一步在政治上给予肯定。如果从以求真为治学范式的理性原则视之,经世致用传统突出了实用主义的目的性,易于对学术发展产生功利性误导,主要是使史学的学术性减弱而引向政治化与实用化的趋向,最后导致无视史学自身价值的后果。所以在总结经世致用史学传统时,首先要注意它曾给史学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
一、孔子《春秋》与史法经世
唐李延寿在论及史学的功能时说:“斯盖哲王经国,通贤垂范,惩诫之方,率由兹义。”〔1〕此乃对史学经世致用功能的简明概述。 其形成主要与孔子修《春秋》有关。《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春秋》推崇备至,其要旨不外经世致用之义。其中说道:“《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此实是《春秋》为治民经世的典范。
较早肯定孔子修《春秋》之论见于《左传》,其成公十四年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此“圣人”即孔子。由此可见《春秋》中的记载方式寓有特定旨义,是即方法义例。《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孔子修《春秋》之因时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即谓孔子修《春秋》,是为宣传自己在现实中所无法实现的政治理想。为此他总结创造一套书法义例,并用以褒贬评议历史。后人认为孔子这样做,有似在行使一种权力,惩恶劝善,宏敷王道,为后世立法。为此汉人称孔子为素王,《春秋》为孔子素王之业,即认为孔子修《春秋》等于建立起自己的王业。《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则谓:“《春秋》作新王之事,变周之制,当正黑统。而殷周为王者之后,绌夏改号禹谓之帝,录其后以小国。”此说列孔子《春秋》于王道三统之中,俨然为黑统之王。其实在汉人这类夸大性说法中,无非表明这样一种意义,即孔子以《春秋》为经世致用的工具。在孔子之前的史官记事原有一套方法如所谓书法,并为孔子所知。《左传》宣公二年:“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汉书·艺文志》亦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史官有法。”孔子对此加以继承和创新,形成一套书法义例,并用于修《春秋》,以贯注自己的政治理想,施加影响于当世及后来。所以,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实由孔子《春秋》发其端。
刘知几曾把《春秋》在史学上的贡献归结为创通史例,《史通·序例》:“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昔孔子修经,始发凡起例;左氏立传,显其区域。科条一辨,彪炳可观。”按“史例”、“科条”主要指孔子修《春秋》所开始形成的书法义例等一套修史方法。它为后人修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规范法则,对史学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孔子修《春秋》的贡献不仅在于创通书法义例,还在于他表现出的政治理想与政治责任感。由于孔子借《春秋》表现出的政治追求对后世产生巨大感召力,因之经世致用精神在他之后深入人心。汉代桓谭在《新论·本造》中说:“余为《新论》,术辨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邪!”即自言其著述宗旨要参与当世政治,以效法《春秋》的经世致用精神。孔子之后,经一些史家的相继阐发,经世致用在史学上的影响日渐深广。司马迁继《春秋》之后在史学上卓有建树,但他思想的真正追求并非表现于为史学的献身精神上,而在于他要借《史记》争取政治上的一席发言权,要以自己的著述影响现实的那种强烈意识。这是他体悟孔子《春秋》精神的至深之处。司马迁之后,能在史著中表现出如此强烈感情的几成绝响。但有成就的史家,都把为政治提供借鉴做为修史宗旨。而能否如此也成为评价史著优劣的重要标准。汉代荀悦所著《汉纪》为世所推重,其序曰:“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故君子可观之矣。”即《汉纪》所载可为现实提供各种借鉴,尤其可为当政者提供有益训诫。东晋袁宏在所著《后汉纪序》中说:“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即提出著史的重要宗旨之一是宏扬名教。接着历举《左传》、《史记》、《汉书》、《汉纪》等,认为它们虽在“扶明义教,网罗治体”及“大得治功”方面有所成就,但在“述名教之本,帝王高义”方面犹有所未尽。因而为弥补诸史的这些缺憾,袁宏决意著史“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宏敷王道。”即他把著史的极致归结为笃名教、弘王道的现实目的上。总之,孔子以后历代史家多注重突显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致用功能,并把它标榜为史家职责予以鼓吹,似不如此则不足为史家。如《文心雕龙·史传》曰:“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元脱脱《进辽史表》曰:“史臣虽述前代之设施,大意有助人君之鉴戒。”〔2〕至章学诚则径直说出“史学所以经世”〔3〕的宗旨。 是皆从为现实服务的角度,论述史学功能与史家职责。经历代史家推阐,经世致用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传统。
发端于孔子的史学经世传统,其最终目的不在史学自身。实际上,它是以史学为工具发扬一种道德裁判权,用以维持社会的政治伦理秩序。因而其所刻意追求的不是史学的内在发展,而是全力贯注于其外在的社会效果,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得鱼忘筌,因而社会效果既达,则完全可以无视史学自身的存在及意义。因为任何以实用主义为指导的行为,在目的既达之后,手段或工具已一文不值,可以弃置不顾。因而它对学术自身的发展,对维护学术的独立价值,极为有害。这就是我们为维护史学自身的发展及其价值,反对经世致用史学传统的认识论根据。
二、古代史学与帝王治术
如果说以史法经世还只是学者们出于经世致用的目的,以史学为参与现实的工具,因而还多少保留些学术上的意义;那么,历代帝王卿相研究史学,则主要是出于政治上的目的,因而几乎完全等同史学于权谋治术,史学自身的学术意义已在若有若无之间。这是史学在经世致用观念引导下,史学被政治化和实用化的最大影响。
史学被等同于帝王治术之一,其来甚久。《汉书·艺文志》诸子类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按此谓道家乃人君南面之术,但其渊源则系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可证很早起,人们即已认识到史学与人君治术间的密切联系。这样,《春秋》一书在春秋时代已成为国君太子的必修科目之一〔4〕。 至战国时代,则出现卿相师傅们专门撰作史书给国君观览的现象。《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世,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此诸人皆以王傅、国相身分著书供人君观览,无疑是以史学为政治教本,使人君从中汲取权谋治术。这种以《春秋》一类史书为帝王政治教本的做法,后来竟成为一种传统。如汉初陆贾在高祖前论治天下之道,认为居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于是高祖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十二篇,名《新语》,每篇写竟,即进读于高祖之前〔5〕。 东汉末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为《汉纪》三十篇。”〔6〕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 本为进呈皇帝御览,《宋史·司马光传》:“光常患历代史学,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宋以后《资治通鉴》成为历朝帝王的必读教本。以上诸例,可见由臣下撰作史书供人君观览,已成为封建社会中的一种传统。这类史书已成为一种政治教本,专供人君揣摩权谋治术。由此导致从政治需要上评议史书性质的特殊现象。如西汉时东平思王入朝求《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对成帝说:“《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7〕是西汉视《史记》为政治权谋之书, 其传布关系汉室安危,因而朝廷秘不外传。历代统治者也多于政治倾轧中,视史书为汲取谋略、历练权术的教本。东汉和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8〕按此乃汉和帝为诛除外戚窦氏, 因而寻求权谋于前朝历史。《汉书·外戚传》记载了西汉皇帝与外戚的斗争;所谓“故事”据李贤注:“文帝诛薄昭,武帝诛窦婴故事。”这些都是当时和帝为诛除外戚窦氏所可取鉴者,大要不外取鉴其权谋术略。十六国时后赵石勒很喜欢史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9〕,以作为切摩治道,练达权术的一种“智谋库”。宋神宗对《资治通鉴》的认识,最能代表历代帝王对史书价值的理解,“神宗皇帝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曰《资治通鉴》。”〔10〕按“有资于治道”乃历代帝王寄意于史学的根本目的所在,从而反映出历代帝王寄意于史学功能的共同心理。
帝王卿相高居于庙堂之上,讲论史册,切摩治道,其风流于天下,必使各方面受到影响。一些起于草莽的英雄豪杰,在图举大事时也往往有意求助于史册。但由于他们限于自身的文化知识条件,只好在庙堂史册之外退而求其次。如明清时《三国演义》一类通俗历史读物,多满足此需要。黄人《小说小话》载:“张献忠、李自成及近世张格尔、洪秀全等初起,众皆鸟合,羌无纪律。其后攻城略地,伏险设防,渐有机智……闻皆以《三国演义》中战案为玉帐唯一之秘本。”〔11〕据说努尔哈赤当年只有些粗略的战略战术,应与他好读《三国演义》有关。及至后来皇太极有意敷设文教,最初还要通过《三国演义》去寻求“帝王治平之道”〔12〕。这恰恰反映出帝王卿相庙堂史学的政治功利观所投射的影响。
综之,由于历代帝王为获取权谋治术而研治史学,使史学自身的性质进一步政治化、实用化。由此又决定了史学存在的价值取向。即史学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它能满足统治者的现实需要,能为他们提供政治上的致用效果。此外,它自身几乎没有多少可以独立存在的价值。这是皇权实用主义罩在史学上的最大阴影,它使史学真正成为政治功利的附属品。史家们受此思想的左右控制,也从政治致用功能方面去定义史学的价值,从而为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推波助澜。此可举唐代两个大史家的观点为代表,首先是刘知几。他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要国有家者,其可以缺之哉。”〔13〕此论把史学推为国家统治者不可或缺的利用要道,其所具有的政治致用功能自不待言。其次杜佑曰:“每念懵学,莫探政经,略观历代众贤著论,多陈紊失之弊,或缺匡拯之方。”〔14〕即杜佑著《通典》,乃有意探求“政经”与“匡拯之方”,亦即其属意于治术理道。后杜佑觉《通典》繁重,曾将此书提要写成《理道要诀》10卷,此名直接标示出杜佑为研索治术理道的史学致用宗旨。刘知几与杜佑二人在史学上的贡献至巨,其思想影响颇大。他们这种史学政治致用论,颇可代表中国古代史家的一般观点,从而使经世致用的史学传统与官方的政治需要相一致。中国古代史家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统治者定调的史学政治致用论,其后面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
三、经世致用观念对史学发展的误导
经世致用实反映出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即注重功利实用的理念意识。此理念意识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以一切服务于现实社会人生的功利效果为极致。受此观念影响,士大夫知识阶层养成积极入世的人生信念,往往把政治上的功能效益做为检验学术文化价值的最高标准的。由此导致的社会文化后果,就是文化学术功能被政治功能所淡化甚而替代;士大夫知识阶层及其拥有的学术知识,只能附庸于政治,其价值也只能经过经世的实践和所达到的社会政治效果加以验证。这又导致士大夫知识阶层及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的丧失,在中国也从未发展起西方式的文化超越精神——对学术文化自身价值的追求和肯定。中国文化发展中的这些特点,在史学上得到充分反映。
有的学者提出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认为“历史意识的发达是中国实用理性的重要内容和特征。”〔15〕中国古代很早就注重对历史的借鉴,而取鉴历史是为了指导现实的功利目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就是在此文化条件中培养滋生而出。《易·大畜》象辞:“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书·说命》:“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这是古人为畜德、建事而注重对历史知识的学习。《易·系辞》:“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行大业至矣哉。”“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易》为儒家哲学之根本,而“致用”又是《易》所反复强调的利物精神。上述就是史学致用传统形成的文化思想基础。而首出以史学致用精神干予社会世道的典范,当推孔子《春秋》。所谓“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16〕这是孔子以《春秋》经世的典型致用范例。孔子之后,古代史家和史著无不以经世致用做为思想指导,由此形成史学经世的主流传统。究其原因,除孔子的影响外,主要还因秦汉以下历代统治者的政治诱导所致。
首先,朝廷通过控制修史权,倡导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史学致用意识。《汉书·艺文志》有“史官有法”之说,此有两层意思,一是由朝廷设官修史;二是史官修史遵循特定的史法,主要是史官褒善贬恶之法。这两点在《左传》中皆有其证。秦汉以下,历代始终设法把修史权控制于朝廷之手。汉代班固曾因人告发“私改作国史”而下狱〔17〕,隋文帝则下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18〕至唐代设立史馆,朝廷控制修史的制度措施极大地完善。由于古代的修史权始终由朝廷秉持,故史学的经世功能亦附著于统治权能之下为朝廷所倡导督行。
其次,科举考试使史学的致用意识深入于士大夫知识阶层。唐代科举考试已列史学为考试内容,如进士习业要求有“一史”,秀才科要求“学兼经史”,“兼通三史”。进士科考试有经史策论一项,其中史策“问成败得失”。此外专设置史科,其考试内容如:“自(南朝)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19〕据其所述,显然通过把史学列为考试内容的办法,达到把史学引向培养人仕者治术才干的目的。但史科旋即罢废,历代考试基本保留经史策论的内容。顾炎武注意到此问题,认识到应在科举考试中恢复加强史学的内容科目,以利于有实际治术才干的人才培养。如他曾列举宋太常博士仉思论关于科举考试中史学内容对人才培养之益:“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分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益国家。”显然已指出史学在培养人仕者治术才干方面的意义。因此顾炎武主张效法唐代科考设史学一科:“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20〕其目的亦要通过科举考试的倡导,利用史学培养通达政体,治术练达的实际人才。这样,由于科举考试制度,史学做为有益世道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性质,日渐从思想观念上深入于士大夫知识阶层。
与科举考试利用史学做为培养士人治术才干的倾向相关,唐代开始出现从两汉以来重视经学的风气转向重视史学的趋势。这从帝王的教育内容中亦可考见其大概。唐代帝王教育在儒家经典之外,开始增设史学的内容,即注意用历史知识培养人君的政治智慧及才干。宋司马光撰成《资治通鉴》,史学正式成为帝王资以究明治国之道的工具〔21〕。这样,史学经世的致用功能开始在政治上得到充分发挥的机会。本来在汉晋以来的帝王诏敕及臣僚奏疏中,往往引历史为论政的根据,自唐代起,此风愈甚。这样,史学由附庸于政治又进而与政治合为一体,并被帝王卿相们正式承认为有益治术之学。试观《贞观政要》,在唐太宗君臣的问对中,每征引历史为论政求治的根据。而自宋代起,《贞观政要》成为历朝帝王观摩学习的重要教本。但无论历代史家以史法经世,还是帝王卿相以史学为补益治术工具,都不过是史学经世的传统在学术领域及政治领域的表现。归根结底,他们并不把史学自身做为发展对象,而是以史学为工具去达到外在的社会政治目的,因而绝非为史学自身的内在发展。于是史学自身的独立学术品格被阉割。可以说,中国古代史学的存在与发展,几乎是以牺牲自身的独立学术价值而甘为政治的附庸为代价才换得的,因而本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所言“中国前者未尝有史”,绝非故做惊世之语。时至近代,学术发展要求摆脱政治而独立,从而表现出新的学术价值观念。在近代世界出现的科学民主潮流中,中国古代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已不再符合学术发展时宜了。
近代以来的中国学者,多已意识到学术应脱离政治而独立乃时代发展的潮流。如严复说:“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22〕显然严复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肯定学术脱离政治而独立乃是文明开化的一种表现。王国维则径直提出:“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23〕陈独秀也对“文以载道”一类经世观念表示反感,提出学者应知学术独立的神圣,他说:“学者自身不知学术独立之神圣。譬如文学自有其独立价值也,而文学家自身不承认之,必欲攀附《六经》,妄称‘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以自贬抑。”〔24〕近代的学者们认识到,只有学术独立,才能培养起纯学术的自由研究精神;而这是促使学术自身能获得长足发展的先决条件。英国科学史家丹皮尔曾提出“为求知而求知的纯粹科学观”,他说:“科学主要是追求纯粹知识的自由研究活动。如果实际的利益随之而来,那是副产品,纵然它们是由于政府资助而获得的发现。如果自由的、纯粹的科学遭到忽略,应用科学迟早也会枯萎而死的。”〔25〕就是说,学术研究是一种自由的“求真”活动,“用”是其次的。因而学术在摆脱政治的羁绊而独立之后,还要摆脱致用功利观念的影响。因为学术发展史已证明,致用功利观念是学术发展的大碍。所以,树立起纯粹知识的学术追求,亦即提倡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信念,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极为重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是西方科学产生的真正源头,科学的“用”是从“真”衍生出来的;这种“为真理而真理”的精神,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类知识共同立基的根本。这些正是中国所缺乏的〔26〕。
如果从学术文化传统中去追溯东西文化的差别,脱离致用功利观念而进行纯知识探求精神之有无,可以从根本上区别中西两种文化体系。与中国文化的实用理性特征不同,西方文化自其发端的古代希腊起,就已发展起一种纯知识追求的自由研究精神。如罗素曾指出:希腊人“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所做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索所束缚。”〔27〕罗素这里显然对希腊人在纯粹知识领域的创造上,在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的自由探索上,给予极高评价。古代希腊的城邦民主制提供了独立思考、自由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使人们能够从事纯粹知识的探求,并建立起西方自由的智性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则不然。在中国古代专制政体之下,始终不容许任何游离于政治控制之外的自由学术追求,一切学术文化的存在,要以是否有利于维护现实的政治伦理秩序为价值取向标准。于是政治的和致用功利的功能被加于学术文化的自身属性之上。这种长期受专制制度控制影响的文化传统,无视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反对自由思索的研究精神,设置种种戒律做为牢范限制文化发展的条规,并倡导学术文化为现实政治伦理秩序服务的致用信条。这就是中国的政治伦理型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它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负面效应不可低估。“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28〕固然焚书坑儒式的文化专制主义无法禁绝学术文化,但经世致用的思想诱导却达到控制学术文化发展的文化专制功效。总之,与近代以来科学民主的学术精神相比,经世致用传统由于缺乏独立自由的研究宗旨,适为史学发展之一弊。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已向世人昭示,中国亟需建立一种摆脱致用观念而以求真为第一义的学术发展范式。这是中国史学乃至中国学术全体的现代化希望所系。
注释:
〔1〕《北史·序传》。
〔2〕《辽史》附录。
〔3〕《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
〔4〕见《国语》之《晋语七》及《楚语下》。
〔5〕《史记·陆贾传》。
〔6〕《后汉书·荀悦传》。
〔7〕《汉书·东平思王宇传》。
〔8〕《后汉书·清河王传》。
〔9〕《晋书·石勒载记》。
〔10〕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
〔11〕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874页,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12〕参见商鸿逵先生《论清代的尊孔和崇奉喇嘛教》,载《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13〕《史通·史官建置》。
〔14〕《旧唐书·杜佑传》。
〔15〕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305页, 人民出版社1985年。
〔16〕《史记·太史公自序》。
〔17〕《后汉书·班固传》。
〔18〕《隋书·文帝纪》。
〔19〕《通典》卷十七《选举五》。
〔20〕《日知录》卷十六《史学》条。
〔21〕朱鸿《君储圣王,以道正俗——历代的君主教育》,载《中国文化新论·制度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22〕《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载《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
〔23〕《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遗书》第五卷《静庵文集》。
〔24〕《随感录·学术独立》,载《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5〕丹皮尔《科学史》中译本,第634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
〔26〕余英时《论文化超越》,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27〕《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上卷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
〔28〕郑樵《通志·校雠略》。
标签:经世致用论文; 儒家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孔子论文; 国学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汉纪论文; 春秋论文; 汉书·艺文志论文; 通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