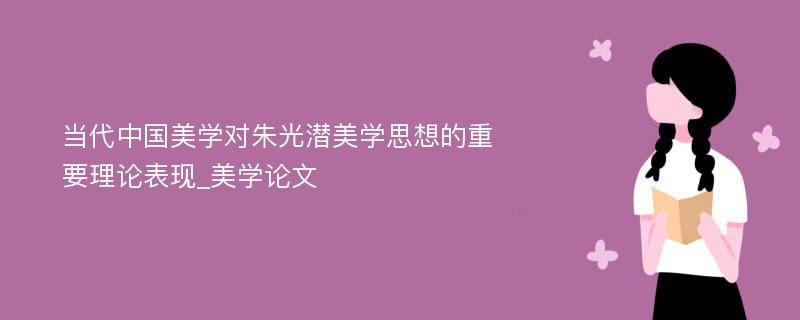
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理论表现——评朱光潜美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朱光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是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理论表现。因为在中国当代美学之中,朱光潜的美学思想极为丰富、深刻、全面,其影响也极为深远、广泛;在他的美学思想中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美学思想运行的脉胳和走向,能够深切地体验到中国当代美学运动的脉膊的跳动。
自五十年代迄于九十年代的今天,在这四十余年之中,中国当代美学,我以为集中地、反复地讨论了以下四个基本问题,这就是:一、美的本质;二、审美的内涵和规律;三、艺术的本质和内容;四、艺术思维的特点与规律。在这四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和广泛的展开。朱先生积极地参与了这些讨论,并在讨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当代美学的讨论中,可以这样说,常常是以朱先生的美学思想为中心的,讨论常常是围绕着他的论点进行的,在讨论中,他发挥着轴心的作用,而且常常又是在他的思想的启发、诱导下,讨论才得以深入地展开。所以,朱先生对于中国当代美学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朱先生的美学思想,称得上是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理论表现。以下我想从五个方面来具体地谈谈他的贡献。
一、启开了深入美的本质的大门
美学的根本问题是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也是美的本质问题。中国当代美学的探讨,首先就是围绕着美学的哲学基础、美的本质问题展开的。具体地说,中国当代美学发轫于五十年代初对于解放前一两本美学著作的批评,即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和蔡仪的《新美学》。即起始于对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为代表的美的“主观论”的批评,和蔡仪的《新美学》为代表的美的“客观论”的批评。1953年吕荧就著文批评蔡仪的美的“客观论”。他在《美学问题》一文中说:“《新美学》认为美是客观的,但是不从客观现实出发”,而是“主观地断定,‘美是物的属性’,是有人类以前的存在,‘典型就是美’”,《新美学》“从超社会超现实的观点来看美,把美看作超越人的生活和人的意识的客观存在”[①]。1956年,李泽厚也对蔡仪的观点提出批评。他在文章中说,蔡仪在《新美学》中,“把美或典型归结为一种不依存于人类社会物体的自然属性”,这是“形而上学旧唯物主义”[②]。接着在1957年,在《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一文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蔡仪的美学观点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了美的客观性的存在,但却否认了美的依存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质”[③]。对于朱光潜美学的批评,基本上是始于1956年他“引火烧身式”的自我批评。解放前,朱先生的美学思想是以克罗齐的“直觉说”为基础的,解放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学会并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阐释美学问题,在逐步清算自己在美学问题上的唯心主义观点的同时,建立起自己的新的美学体系。1956年他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就是他批判旧美学建立新美学的起点。在他对自己的旧美学作自我批评的同时,黄药眠发表了《论食利者的美学》,李泽厚发表了《论美感、美和艺术》,都对朱光潜的美学观点提出了批评。当时主要是批评他的直觉说,但也直接关系到他的美学的哲学基础。黄药眠批评了他的“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的观点,指出这一观点实际上“把物质的第一性取消了”。又指出他所谓的直觉所创造的“意象”,“完全是一个主观的存在”[④]。李泽厚在《论美感、美和艺术》中,更明确地指出,朱先生所说的美,“是个人主观作用或‘外射’‘传达’于客观的产物”,“所谓‘心物的关系’实际上就只是反映者与被反映者的关系”,而“承认或否认美的不依于人类主观意识条件的客观性是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分水岭”[⑤]。(重点号原有)五十年代的美学论争,基本问题是美学的哲学基础问题,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主观唯心主义或机械唯物主义?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是要回答:美是什么?美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或是主客观的统一?在当时,无论是批评者或是被批评者,无论其对美持什么样的解说,而从其所持立论的原则来看,基本上都是列宁的反映论。因此,我把这一段的美学,总括起来称之为“反映论”美学。如朱光潜在《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说:“唯心主义者把美看作主观的感觉,机械唯物主义者把美看作事物的属性,都是不解决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美学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指示了一些总的原则,首先是列宁的反映论……”[⑥]。蔡仪在吕荧批评他的美学观点以后,写了《论美学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一文,批评吕荧的美是“观念”说,指出他的观点,“不符合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映论的原则”[⑦]。李泽厚同样是运用反映论原理来解决美学问题。他说,“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不能正确解决美的客观存在性质问题”,而唯心主义者则把美当作只“是人类主观心灵的创造”,“只有辩证唯物主义能够真正正确解决美的客观存在这一根本问题”[⑧]。认为:美感的客观基础是“现实美”,“美感是美的反映美的模写”[⑨]。他说:“从美感开始,也就是从分析人类的美的认识的辩证法开始,就是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一哲学根本问题开始”[⑩]。
解放以后,朱先生的美学框架是以马列主义的“反映论”为基础的,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又逐步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特别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思想。这是朱先生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表现了当时国内美学理论的走向,与当时美学界对于美的本质的研究的深化相适应。
朱先生的美学的哲学基础是马列主义的“反映论”。他对于“反映论”的存在和意识的两个方面,在运用上,以“存在决定意识”为自己的理论前提,而把自己的理论建构放在“意识也可以影响存在”之上。所以,他十分强调意识对于存在的能动作用,美感对于美的辩证作用。他引证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话说:“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11)]。而且他还进一步提出区别“科学的反映”和“意识形态性的反映”(我称它为“美学反映”)。认为意识形态性的反映比科学的反映能动性更大。他说“认识‘花是美的’与认识‘花是红的’,这中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这就是认识“花是红的”,这是“科学反映”,“主观条件不起什么作用,或只是起很小的作用,它基本上是客观的”;而认识“花是美的”,这是“美学反映”,“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2)]。所以美感不仅能影响美,而且对于美还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美感是怎样影响决定美的呢?由此他提出了作为他的美学理论的基石的“物甲”“物乙”说。他说,必须对“物”与“物的形象”作出区别。“物甲”就是“物”,就是“自然物”,是“纯粹客观的”[(13)];“物乙”则是“物的形象”,是“物甲”“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14)]。所以作为“物”的“物甲”只是产生美的客观条件,或者说是创造美的素材。朱先生说:“物甲是感觉的根据,艺术的素材”[(15)]。要使“物甲”成为审美对象,成为美,还需经过人的意识的作用,使之成为“物的形象”——“物乙”。“物的形象”——“物乙”,才是美,才是美感对象。我认为朱先生的这个“物甲”“物乙”说,是他的全部美学理论的基石。他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结论,美是意识形态性的论断,以及艺术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的观点,等等,都是从这一“物甲”“物乙”说中引伸出来的。所以他在《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说:“我的基本论点在于区分自然形态的‘物’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物的形象’,也就是区分‘美的条件’和‘美’。这个基本论点的根据是‘文艺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上层建筑’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则”[(16)]。
朱先生的“物甲”“物乙”说,虽然存在着问题,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但也包含着他的深邃的美学智慧。所以说它包含着深邃的美学智慧,第一,因为正是它首先启开了深入美的本质的大门。因为“物甲”“物乙”说,既肯定了美的存在的物质基础、自然属性,又揭示了美的人性内涵。单纯的事物、纯粹的事物形式,或者是无形式的思想、情感,抽象的人性,都不可能有美,美是客观事物与人性相适应的性质,是人和自然的统一,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物甲”“物乙”说既反对了纯粹的“客观论”,又反对了抽象的“人性论”。它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了。而只有达到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才可能有美。朱先生给美下了这样的定义,他说:“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17)]。可见,这一定义只需我们给它稍加改造,就已经接近了美的本质的真理。所以说它启开了深入美的本质的大门。第二,因为“物甲”“物乙”说,它揭示了审美的实质。审美并非只是纯客观的反映,它总是融合着审美者的情感、思想活动。审美并非只是对审美对象的直觉的观照,而且也是对审美对象的体验。审美的过程,也是审美者的心理活动过程,审美者的心理处于异常活跃的状态,有对于审美对象的理解,有对于审美对象的想象。所以,审美实质上是一个意象孕育、意象创造的过程。朱先生所说的“物乙”,事实上并非“物的形象”,而恰恰正是这种“意象”。然而这“意象”的创造,却是审美的最高形态,也是审美的真正实质。第三,“物甲”“物乙”说,也揭示了艺术思维的根本,或者说关键。这个“关键”或“根本”就是“意匠经营”。我国古代伟大的文艺理论家刘勰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18)]。艺术创作总要先孕育意象,形成意象以后,才能进入具体创作。具体的创作过程,即是意象的物态化过程,或者说是对象化的过程。艺术创作的全过程,简要说来,就是直觉观照、孕育意象、形成意象,然后将意象物态化成为艺术形象的过程。孕育意象,就是艺术构思。所以刘勰说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所以意象的孕育、形成,这是艺术思维之根本。艺术构思,同时也是审美过程,亦即直觉观照、审美理解、审美体验、审美想象的过程。意象正是在观照,理解、体验、想象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朱先生说:“美感经验或艺术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包括整个阶段的创造或欣赏活动的‘意匠经营……’”[(19)]。“整个过程的美感活动都是客观事物和主观意识形态两方面所供给的素材而加以选择、安排、集中和融会”[(20)]而这种“选择、安排、集中和融会”也正是孕育、形成意象的过程,从而也是艺术思维之根本。第四,“物甲”“物乙”说,揭示了艺术的本质内容。艺术既要反映现实生活,所以需要以“物甲”为基础,又要融入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才能形成“物的形象”,也即艺术形象。所以,艺术应该是客观再现和主观表现的统一。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也就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而这个再现和表现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正是艺术的全部内容。最后第五,则揭示了艺术美的本质。在朱先生看来,“美是艺术的一种属性,而艺术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21)]。这样,凡是美就都是艺术美,只有艺术才有美。艺术既然是意识形态,那么作为艺术特性的美也“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22)]。他说:“自然美与艺术美确有不同,但是在本质上都是意识形态性的”[(23)],都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24)]。既然一切美都属于艺术的美,那么他所说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其实质即指艺术美。一切美的本质固然不都是意识形态性的主客观的统一,但艺术美的本质,确是意识形态性的主客观的统一。所以朱先生的主客观统一论,作为美的本质,固然是不全面的、不很正确的,但是作为艺术美的本质,却是正确的,也是科学的。
所以,朱先生的“物甲”“物乙”说是深刻而精微的。但是却也存在着深刻的逻辑的矛盾。“物甲”是物,是客观存在,这是无庸置疑的,问题出在“物乙”身上。“物乙”是“物的形象”,作为“物的形象”的“物乙”,朱先生也认为是物。“物甲”、“物乙”只是物的分类。但事实上,朱先生所说的“物乙”,却已不是客观的物,而是作为物的反映的人的主观意识,他所说的“物的形象”,也不是物的客观形象,而是经过主观意识加工创造的“意象”。所以,他混淆了物与意识之间的区别,物的客观形象与主观意象之间的区别。他把意识等同于物,把物等同于意识,把主观意象等同于客观形象,把客观形象等同于主观意象,模糊客观与主观的区别,把客观等同于主观,把主观等同于客观,从而引出了美是意识形态性的错误的结论。
不过朱先生的“物甲”“物乙”说是耐人深思的,只要我们分清主客观的界线,并稍加深入,则就能逼近揭示美的本质的真理。朱先生的用意是要区分“形”与“象”,事物的“形”并非就是审美对象,只有事物的形象才是真正的审美对象,这个意图是很好的,这个见解也是相当深刻而精微的,但是不幸的是朱先生把审美对象与审美意象给混淆了,于是最终未能揭示出美的全面本质。如果我们把朱先生的“物乙”加以分解,把“物的形象”分解为物的客观形象和物的主观形象两个部分,那么全部美学的关键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中国古藉《周易》就有“象”“器”之别。《系辞上》所谓“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形乃器物之形式,象乃生活真理之感性显现。如若我们从美学的角度来考察,那么作为器物之形式的“形”,它只是事物的物质存在的形式,它还不能算是审美对象;而作为生活真理之感性显现的“象”,则是审美对象。而这个审美对象则是客观的美的存在。譬如“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只这句诗,诗中的“草”还不是审美对象,诗只是描述了郊原上的青草长得很长、很茂盛,每年都经历着一次枯萎和繁荣,它只是写出了物的生存形式,而接下去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则才真正进入了诗境,有了诗意,使“一岁一枯荣”的“离离原上草”成了审美对象,因为它显示了生活的真理,有了哲理,成了生活真理的感性显现。这种感性显现无疑是客观存在,它不仅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的自然规律的反映,而且显示了人的现实生活的真理。这是自然规律和人的现实生活的统一。而美正是这种统一的表现。作为艺术的美,正是这种生活美的反映。必须把形与形象加以区别,又必须把形象与象加以区别。形象与形的不同,是形象包含了人性的内容,只有有了人性的内容,形象才成了审美对象。朱先生把形与形象加以区别,正是要指出美不是纯自然的属性,它有着人的、人性的内容。这就是朱先生指出这个区别的重大意义。同时又必须把形象与意象加以区别。形象是客观存在,意象则是主观的创造。“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为事物、现实生活的客观联系,它是客观的存在;但是它作为诗人白居易的独特的感受,它就是诗人创造的意象,并由这意象转化而成的艺术形象。“悲落叶於劲秋,喜柔条於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这是物与人性之间的心理的客观联系,作为显示这种客观联系的形象,当然是客观的。而作为这种客观联系的反映的“审美意象”、艺术形象,则是主观的。如梅花的美,正在于它的自然属性能够显现高洁的人性,而梅花这种能够显现高洁的人性的品格,是梅花的自然属性与人的高洁的人性的统一,是客观的社会存在。诗人对此进行欣赏,乃就形成梅花的审美意象,形之于笔端,乃就成了梅花的艺术形象。梅花的审美意象是梅花的客观形象的对象化、物态化。而梅花的客观形象的美,则又是梅花的自然属性与人的高洁人性的统一。这样,事物的“形”(自然属性)、事物的形象(自然属性与人性的客观的统一)、审美意象(对于客观形象的感受和反映)、艺术形象(意象的物态化),四者就达到了符合客观真理的逻辑的统一。从而朱先生的“物甲”“物乙”的理论,也就达到了揭示美的本质、美学规律的真理。
朱先生美学的哲学基础是“反映论”,他在文章中一直重申这个原则。在1961年《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一文中,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有一个总的出发点,那就是反映论:文艺是客观现实的反映”[(25)]。1963年2月28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美学史的对象、意义和研究方法》一文中又说:“把美学或美学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研究,我们就须经常把握住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亦即关于反映论的三个互相密切关联的大原则:一、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二、社会意识反转过来影响社会存在;三、各种社会意识形态互相影响。”“一切美学和美学史的重大问题都是隶属于这三大原则的”[(26)]。
但是朱先生的美学理论并没有囿于“反映论”,他在五十年代就注意到了实践观点,他在1957年《哲学研究》第四期上发表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就说,“把文艺看作一种生产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恰恰是这个重要原则遭到了企图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讨论美学的人们的忽视”[(27)]。他又进一步说:“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把文艺作为生产实践来看,美学就不能只是一种认识论了,就要包括艺术创造过程的研究了”[(28)]。他认为艺术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生产劳动”[(29)]。但是这时候,朱先生还未系统阐发美学的实践观点。1960年《新建设》第三期上,他发表了《美学研究些什么?怎样研究美学?》一文,他对美学的实践观点有了进一步的阐释,他引述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一名著句的话,即“用艺术方式掌握世界”。并作了具体阐发。他说:“概括地说,它包括三类因素:首先是创造性的劳动,例如手工艺的活动;其次是专门性的艺术,例如音乐、舞蹈、图画等等;第三是对现实生活(自然、社会生活)起审美活动。可以说,艺术掌握涉及人在生产斗争与阶级斗争中的一切活动,涉及与人有关的一切现实现象,决不仅限于艺术”[(30)]。这样,朱先生就把“用艺术方式掌握世界”推广到人类全部生活活动,换句话说,人类的全部生活活动都要用艺术方式去掌握。这样,根据朱先生的观点,人类的一切生活活动也都有了艺术的性质,从而也就都有了美的属性,因为美是艺术的特性。用艺术方式掌握世界也就是用美的方式掌握世界。不久,朱先生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一篇长文,题为《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副题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这篇文章以马克思的“用艺术方式掌握世界”这句话为纲,同时主要是结合运用了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一些论点,如劳动的两个尺度、美的规律、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的感觉力的社会历史的形成、人在自己所创造的对象世界里直观自身,以及异化劳动等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对于美学起了根本变革的作用”,论证了美“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即改变世界又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31)]。并在最后系统地概括说:“实践观点就是唯物辩证观点,它要求把艺术摆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轮廓里去看,要求把艺术看作人改造自然,也改造自己的这种生产实践活动中的一个必然的组成部分”[(32)]。(重点号原有)又说:“人类文化发展史,归根到底就是政治经济发展史,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交互作用和交互推进的历史。这部历史是从生产劳动开始的。……这生产劳动本身是社会实践,同时也是人对世界的艺术的或审美的掌握,因为生产劳动的产品‘对象化’了人的本质力量,‘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中观照自己,’因而感到喜悦。因此,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包括一系列的矛盾的辩证统一,首先是人与自然(即主体与客体或对象)的对立和统一,……第三是认识与实践的对立和统一,……”[(33)](重点号原有)虽然,朱先生的美学,即使是在八十年代也还是在“反映论”的框架之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已经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它已在向以实践观点为核心的美学进行转化。他的上述这些观点,都是极为深刻的,对中国当代美学无疑是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即使我们今天,从审美文化角度研究美学,也仍然是受到了朱先生的一些观点的启示。朱先生在上述论述中,早已明确指出,美学要“摆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轮廓里去看。”
但是随着朱先生的美学的实践观点的提出和深化,他的美学体系的矛盾也就日益突出。1961年《哲学研究》第二期,朱先生发表了《美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的实践观点进一步深化了。他说:“马克思不是把美的对象(自然或艺术)看成认识的对象,而是主要地把它看成实践的对象;审美活动本身不只是一种直观活动,而主要地是一种实践活动;生产劳动就是一种改变世界实现自我的艺术活动或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34)]。(重点号原有)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是不同于人对世界的实践的掌握的,因为前者偏重精神方式,后者则主要是物质改造。朱先生上述论点有把艺术活动与生产劳动等同或者混淆的倾向。这是朱先生美学思想的局限。这一局限的根源,是朱先生把美只看作是艺术的属性之故。而事实上朱先生也已看到,美并非只是艺术的属性,在前面我也已经提到,朱先生已经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一文中,指出了美“是人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既改变世界又从而改变自己的一种结果”[(35)]。既然美是人通过生产实践既改变客观世界又改变主观世界的一种结果,那么,美就不只是艺术的一种属性了。可见,朱先生已经对于自己原先的观点,已经有所突破。以后,他在1980年《美学》第二期上发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一文中又说:“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文艺创造都可以产生美感”[(36)]。既然物质生产也可以产生美感,那么美也就不是艺术所独有了。但是,朱先生仍要继续保持美是艺术的特性的观点,仍然要坚持美是意识形态性的观点,这样,就造成了朱先生观点的深刻矛盾。1980年,他在为《百科知识》写的《美学》条目中说:“马克思主义为美学带来了一个最根本的转变,就是从单纯的认识观点转变到实践观点。以往的美学大半从认识论出发,只满足于解释一些美学现象。马克思主义美学却首先从实践观点出发,证明了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显出基本一致性”[(37)]。朱先生既要坚持他的美是意识形态性说,又要引进实践观点,这就势必造成他的美学的危机,使他原有的体系处于瓦解状态。因为美要则只是艺术的属性,要则是根源于人类实践物质生产的创造,两者不可能既是又不是。朱先生的美学处于两难境地。要摆脱这种境地,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调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的一致性,混淆两者的区别,朱先生说:“审美活动本身不只是一种直观活动,而主要是一种实践活动;生产劳动就是一种改变世界实现自我的艺术活动或‘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38)]。当然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有着“美的规律”的共同性,物质生产也是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但是两者还是有着质的区别。这就是物质生产是人对自然的物质改造,是人的现实生活的基础,而艺术生产则是在物质生产基础上形成的,是意识形态的生产、是精神的生产。这里有着第一性、第二性的区别。物质与精神,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如果说,美是人类物质生产的结果,那么美是第一性的;如果说,美是艺术的属性,那么美是第二性的,这里不可能有调和的余地。朱先生揭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共同遵循的“美的规律”,这是他的贡献,而混淆两者的区别,则是他的局限。这是他既要引进实践观点又不能打破原有的美学体系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到了七、八十年代,国内出现了“本体论”美学、“主体论”美学以及所谓“生命美学”,这些美学思想,可以说是实践美学的引伸,因而亦可在朱先生的美学思想中找到端倪。所谓“本体论”美学,即是以人类实践为本体的美学。这种美学思想的根底,即是把美归结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朱先生的美是艺术的特性,艺术是生产劳动的观点,生产劳动也是艺术掌握世界的观点,以及审美主体的本质必须和客体相适应的观点,“审美的感官是和人手一样在生产劳动中发展起来的”[(39)]的观点,这些观点,无疑对实践为本体的美学发生了影响。
同时,朱先生的“对美学特别有意义的是人‘在自己所创造的世界里观照自己’”,“劳动创造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肯定,美感是认识到这一事实所感到的喜悦”[(40)]。“人这个主体须根据客观具体事物来作为创作和欣赏的对象,而这种对象也须体现人的本质和修养,主客两方缺一不可”[(41)]等观点,对“主体论”的美学也发生了影响。所谓“主体论的美学,即是把人的本质视为美的本质的美学。这种主体论美学,可以说是以实践为本体的美学的自然引伸,但是它重在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这亦和朱先生把美感视作意识形态性的反映有关。朱先生认为“意识形态都是伴着情绪色彩的思想体系,它决定着个人对事物的态度,形成他对于人生和艺术的理想”[(42)]。而意识形态需要放在人类整个历史背景上去考察。朱先生说:“意识形态不一定就只反映同一历史阶段的基础,因为上层建筑一般都落后于基础。这就是说,一定历史阶段的意识形态可能有新旧两种因素,新的反映当前基础,旧的反映前一个或几个历史阶段的残余影响”[(43)]。“每个历史阶段都吸收了消化了过去所有历史阶段的许多有用的东西。每个成年期都是由婴儿期、幼年期发展起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每个历史阶段的生命都融会了过去所有历史阶段的生命”[(44)]。以后国内出现的所谓从“主体心理结构”方面来探讨美学的理论,不过是朱先生上述思想的引伸。事实上朱先生在论证他的美是主客观统一的论点时,已经具体地阐明了人的审美心理结构。他说:“这‘人’不只是一种赤裸裸的只具有生物机能的有机体,他是一个社会的人,是社会历史的结晶,在他身上具有不同程度和性质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文化遗产的影响。在他的意识里,这影响的总和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世界观、人生观、阶级意识,以及对于政治、宗教、哲学、文艺等等观点。……在人对现实起反应(认识或实践)时,他所运用的不仅是有机体的生物机能,而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人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遗产”[(45)]。所以在具体谈到审美时,朱先生又说:“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人的意识形态,人凭这个意识形态去了解自然的意义,因此意识形态不同的人对同一自然会起不同的审美态度”[(46)]。可见,朱先生的意识形态总和的理论,具体地阐释了审美主体的“文化心理结构”,而这也正是“主体论”美学的重要依据。
至于所谓“生命美学”,本质上只是“主体论”美学的另一侧面。“主体论”美学强调人的审美文化心理结构,而“生命美学”则强调人的外在的生命活动。这是人的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朱先生说:“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便是人性”[(47)]。朱先生的美学,特别重视人的内涵,他特别反对“见物不见人”的美学,认为“见物不见人”的美学“是反马克思主义的”[(48)]。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一文中,通过对马克思的消除私有制和异化劳动的思想的阐发,指出审美的人必须“全面发展他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本质力量’”,以达到“整体的人”的人的本质的全面解放。所以朱先生还特别重视美的生理基础。他说:“适合生理要求的引起快感的东西对于美是起作用的,他们正属于我所说的‘美的条件’。唯物主义的美学决不能忽视美的生理基础”[(49)]。又说:“马克思论劳动,也说过美感就是人使各种本质力量能发挥作用的乐趣。人为什么爱追求刺激和消遣呢?都是要让生命力畅通无阻,要从不断活动中得到乐趣”[(50)]。显然,不仅是“主体论”美学,而且“生命美学”也都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如果说“主体论”美学更重视人的内在心理结构问题,那么“生命美学”则更重视人的外在方面、人的肉体方面。
二、指出了美学研究的中心是审美问题
美学的根本问题是美的问题,而美学的基本问题则是审美问题。中国当代美学从侧重对于美学的根本问题——美学的哲学基础,也即是由对美的探讨、对美的本质的揭示,逐步转向侧重于对美学的基本问题,也即审美以及美学体系、构架的研究。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表现了这种趋向。朱先生过去的美学,并不注重对于美的研究,他注重的是审美经验。他的解放以前的著作《文艺心理学》,着重的就是美感经验的分析,他在“作者自白”中说,“‘文艺心理学’是从心理学观点研究出来的‘美学’”[(51)]。他在《文艺心理学》开头第一章第一句话就说:“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至于一般人所喜欢问的‘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的问题还在其次”[(52)]。可见,他对审美经验的重视,远胜过于对美的重视。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解决了美感经验问题以后,才能解决美的问题。“因为事物能引起美感经验才能算是美”[(53)]。解放后,在五、六十年代,朱先生虽然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关于美学的哲学基础、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和争论,但是他依然认为审美经验是美学研究的中心对象。他说:“美感活动阶段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阶段,所以应该是美学研究的中心对象”[(54)]。他认为艺术活动和审美经验是一致的,所以他把它们“等同起来”[(55)]。他说:“美感活动是与欣赏或创作相终始的”[(56)],“它包括整个阶段的创造或欣赏活动的‘意匠经营’……”[(57)]。朱先生所以认为美学研究要以审美经验为中心,因为在他看来,研究审美经验就是研究艺术,因为整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就是审美的过程、美感的过程。同时,朱先生认为,“脱离美感而讲美也是讲不通的”[(58)],因为美是艺术的特性,而艺术创造却又离不开审美,作为艺术形象的“物乙”或“物的形象”的美,也不过是美感影响下的产物。审美包含着美的创造,因为整个审美、美感过程,也就是艺术的“意匠经营”,而艺术家或欣赏者的“意匠经营”,“他的意识形态总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59)],关系到审美者的文化心理结构。因此,对于审美经验的研究,构成了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而且它比对美的研究远要具体、复杂、丰富、重要得多。离开对于审美的研究,美学研究就会变得贫乏、枯燥。所以朱先生关于美学研究要以审美经验为中心的论点,必然地成了我国当代美学运动的深入发展的趋向。
三、阐释了艺术的基本内容: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中国当代美学,基本上是“反映论”美学,作为艺术的指导原则,它要求艺术必须反映社会生活。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也很强调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但是个人的思想、感情必须融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之中,必须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相统一;也强调理想,但不是作家、艺术家具有个人特色的理想,而是必须符合生活发展的必然的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理想。因此,在这样极其严格的划一的要求之下,作家、艺术家具有个性的思想、感情就很难得到表现,个人及其个性事实上被消融了,个人独创性从而也就被窒息了,于是艺术创作出现了类同化、概念化倾向。艺术创作中的单纯“英雄主义”就是这种倾向的反应。三中全会以后,这种状况有了改变,作家、艺术家在努力再现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能够自由地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艺术创作做到了再现社会生活与表现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之间的统一。艺术创作中这一倾向,可以说与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思想是合拍的。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基本构架。
众所周知,朱先生过去是个表现主义者,朱先生在检讨自己的文艺思想时曾说:“艺术对于我只是个人情感的表现”[(60)],后来,他在《表现主义与反映论的基本分歧》一文中又说:他也有一度“主张要把反映论和表现主义结合起来”,认为“反映论也必须容纳表现主义”。然而以后,他又觉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在这篇文章中把“反映论”“表现主义”作了严格的区别,通过两者对比,对“表现主义”作了批判。他一共讲了四大分歧,在谈到第二个分歧时说:“表现主义把个人主观情感看作艺术的源泉,反映论则把客观现实社会生活看作艺术的源泉。表现主义从个人主观情感出发……反映论则从社会客观现实出发,把艺术看作是认识世界从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一个项目,所以要求艺术家首先要投入现实社会生活,参加火热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从实践中认识现实社会生活。能动地把它忠实反映出来;在这反映过程中,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的思想和情感都起作用,并不像自然主义那样被动地‘摹仿自然’。……所以反映论的艺术观是实践与认识的结合,是客观主观的辩证的统一,也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61)]。(重点号原有)可见,虽然朱先生把自己的美学的艺术观纳入到“反映论”之中,虽然他决心要抛弃表现主义,但是,他并没有全盘否定作家、艺术家个人的思想、情感的作用,他仍然为“主观”的表现留有一席之地。在朱先生看来,在反映的基础上进行表现,这是符合艺术的客观规律的。所以他说:“单提表现主义,就会取消反映论,把艺术引回到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62)]。而艺术的客观规律,应是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之上的“客观与主观的辩证的统一”。
朱先生具体而深入地阐释了自己的论点,他说:“反映虽根据现实,但由于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社会意识形态,文艺修养和创作劳动等)发挥了作用,却对现实有所改变,而不是被动地抄袭;反映的结果是现实而又不是原封不动的现实”[(63)]。(重点号原有)所以艺术“不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是主观世界的反映”[(64)],“艺术形象反映了现实,也改变了现实;反映了物,也反映了作者自己”[(65)]。“从客观方面看,这是反映;从主观方面看,这是表现”[(66)]。“艺术并不要求艺术作品就是现实”[(67)],艺术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人根据客观现实进行‘改造制作工夫’所得的结果”[(68)]。所以艺术是主客观的统一,也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朱先生认为“‘物’只能有‘美的条件’,‘物的形象’(即艺术形象)才能有‘美’”[(69)]。而“物的形象”则是审美者或艺术创作者“意匠经营”的结果,是主观意识的“艺术加工”[(70)]。所以“物的形象”(即艺术形象)是主客观的统一,美也是主客观的统一。而主客观的统一,也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所以朱先生的“物甲”“物乙”的理论,同时也即朱先生的艺术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的理论基石。
四、提出了艺术创造既是反映又是生产的论点
艺术只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还是同时也是“物化”的劳动生产?只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同时又是一种特殊的生产形态?艺术的理论基础,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映论”,还是而且同时也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这是当前关于艺术本质问题争论中的一个比较热烈而突出的问题。艺术是反映,还是生产?看来这两者不能绝对化。艺术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艺术家的生产、创造。艺术家的生产、创造,要以“反映”为前提,而“反映”则又必须通过艺术家的生产、创造。没有艺术家的生产、创造,也不可能进行“反映”。“反映”的过程,即是艺术家的能动的创造过程。“反映”需要通过生产,“生产”就是进行反映。“反映”和“生产”是艺术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又是同一的过程。艺术创造是“反映”与“生产”的统一。“反映”与“生产”的统一,也就是再现与表现的统一。就“反映”来说,这是“再现”;就“生产”来说,还是表现。“反映”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为基础;“生产”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为基础。认识论和实践论的统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目前情况看来,持艺术是反映说的,一般都比较注重艺术的意识形态性,比较重视艺术创造的意识活动,而对于艺术的“物化”过程,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这一情况看来,持艺术是生产说的,可以说是对艺术是反映说的一个发展。从理论上来看,持生产说的,也并不否认要以反映论为前提,但是主张要突破它的局限。如何国瑞《文艺学方法论纲》中认为,“要科学地认识文艺,反映论还不是充分的理论基础。譬如,人类为什么要进行艺术生产?反映论就不能很好作出回答。只有马克思的生产论才是最正确最充分的理论基础。”“从生产论的‘人类为什么创造艺术’出发来建构体系”,“它可以更好地贴近艺术本体,把它放在人类三大生产动态系统中来考察它的动态的辩证的全过程。可以这样设想它的体系结构:本体论、主体论、客体论、载体论、播体论、受体论、管体论”[(72)]。当然美学、文艺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个问题还可继续深入探讨,但是生产论是对反映论在理论上的一个深入、丰富、发展,却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
朱先生的美学的艺术观,可以说是艺术生产论的发端,而且在朱先生的理论中,反映论和生产论这两种观点是统一的。朱先生早在1957年8月《哲学研究》第四期上发表的《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一文中就指出:“把文艺看作一种生产劳动,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一个重要原则”[(73)]。他说:“从生产劳动观点去看文艺和单从反映论去看文艺,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单从反映论去看文艺,文艺只是一种认识过程;而从生产劳动观点去看文艺,文艺同时又是一种实践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是要把这两个过程统一起来的”[(74)]。而且他还说,艺术形象“它不只是一种认识形式,而且还是劳动创造的产品”[(75)]。在他看来,艺术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生产劳动”[(76)]。他说:“艺术为一种意识形态和艺术为生产劳动”是“两条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基本原则”[(77)]。他在1958年1月《学术月刊》第一期上发表的《美必然是意识形态性的》一文中又进一步说:“艺术对自然事物,不但增加了一些东西,而且减少了一些东西,改变了一些东西,艺术根据自然事物所创造的东西是一种新的东西。……这种‘增加’、‘减少’和‘改变’就是一般所谓‘选择’、‘集中化’、‘典型化’,是创造过程,是生产劳动过程,是主观能动性与意识形态起作用的过程,也就是客观与主观矛盾统一的过程”[(78)]。(重点号原有)他在1960年4月在《新建设》第四期上发表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一文中,更系统、深入地论证了艺术是生产劳动的观点。并在文后归结性地指出:“单提‘艺术是现实的反映’而不提艺术是人对现实的一种掌握方式,侧重艺术的认识意义而忽视艺术的实践意义”[(79)]。(重点号原有)他在1980年1月为《百科知识》写的“美学”条文中又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为美学带来了一个最根本的转变,就是从单纯的认识观点转变到实践观点。以往的美学都大半从认识论出发,只满足于解释一些美学现象。马克思主义美学却首先从实践观点出发,证明了文艺活动是一种生产劳动,和物质生产劳动显出基本一致性”[(80)]。同年在《美学》第二期上发表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美学问题》一文中又进而指出:“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文艺创造,都可以产生美感,……。这是艺术起源于劳动的理论基础”[(81)]。从上述可以看出,朱先生是艺术生产这一理论的肇始者。
五、揭示了艺术思维的根本规律
艺术思维,是艺术创作的根本。在艺术思维的理论上,朱先生有如下贡献:
①指出“在艺术活动中形象思维是主要的”,不过也须“借助于抽象思维”;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只能互相起伏交错,不能同时进行”[(82)]。
②指出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两种思维方式: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打破了认为思维就是抽象思维的片面观点。他说:“形象思维不仅在历史发展上先于抽象思维,而且在实际运用上也远比抽象思维更广泛。”“文艺主要用形象思维,但形象思维并不是文艺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83)]。这是对思维学的一个重大发展和突破。
③朱先生也有关于形象思维也要抽象、也有逻辑的看法,指出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这两种思维都从感觉材料出发,都要经过抽象和提炼,都要飞跃到较高的理性阶段,所不同者逻辑思维的抽象要抛弃个别特殊事例而求抽象的共性,形象思维的抽象则要从杂乱的形象中提炼出本质的典型形象,这也就是和科学结论不同的另一种理性认识”[(84)]。揭示形象思维也要抽象、也有逻辑,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揭示了形象思维的抽象、逻辑的规律,形象思维才能作为人类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被肯定下来。
④指出了意识形态式的反映与一般感觉或科学式的反映的基本区别。指出这一区别对于美学和艺术尤其重要,因为它揭示出了审美和艺术创造的本质特征。这个基本区别就是:“一个受主观方面意识形态总和的影响,对所反映的事物有所改变甚至歪曲;一个不大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当然也只是相对的),而基本上是对于事物的正确的反映”[(85)]。他用“认识‘花是美的’与认识‘花是红的’”来说明两者的本质区别。他说:“科学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不起什么作用,或只是起很小的作用,它基本上是客观的”。“犹如红是花的一个属性”,“完全是客观的,与主观成分毫无关系”;而“美感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却起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举例来说,时代、民族、社会形态、阶级以及文化修养的差别不大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红的’的认识,却很能影响一个人对于‘花是美的’的认识。”[(86)]朱先生又进一步明确地说:“要科学地解释‘红’只消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加以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分析就行,要科学地解释‘美’,单把它当作一种自然属性似无济于事,它要涉及‘鉴赏的人’的人生观,阶级意识、生活经验、文化修养等主观因素……由于这个分别,我把‘红’看作反映一般自然现象的意识形态,‘美’则是社会意识形态,前者受主观的影响较小,后者受主观影响较大。”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复杂而曲折的”,是“折光的反映”,[(88)]它不是物的简单的“复写、映象、摹写、镜象”,而是能动的创造性的反映[(89)]。意识形态是由基础决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它“不一定只反映同一历史阶段的基础”,它既反映新的基础,但也“反映前一个或几个历史阶段的残余影响”,且“这一种意识形态”还“可以影响那一种意识形态”。[(90)]所以一个人的意识形态,他是受着“意识形态总和的影响”。这种意识形态的总和,表现为一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每个人的思维,总要受制于这种文化心理结构。而审美的反映、艺术的反映,就要受到这种心理结构的有形、无形的制约。就有形来说,就是自觉思维的意向;就无形来说,就是潜意识、无意识的作用。所以,朱先生对于意识形态式的反映与感觉、科学式的反映的区别,对于审美以及艺术创作的规律的本质特征的揭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⑤朱先生指出了艺术思维之根本——“意匠经营”[(91)]。“意匠经营”起于对物的直觉。“意匠经营”的过程,即是“对于感觉素材有所选择,有所排弃,根据概括化和理想化的原则作新的安排和综合,甚至有所夸张和虚构”的过程[(92)]。在这种经营过程中,“他的意识形态总和,也即他的文化心理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93)]。“意匠经营”的结果,即是“物乙”,也即创造出“物的形象”或“艺术形象”,创造出了“美”。所以“意匠经营”是艺术思维之关键、枢纽。这正如刘勰所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比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94)]朱先生说:“审美活动本身不只是一种直观活动,而主要地是一种实践活动”,[(95)]其所以说是一种实践活动,即是因为它是创造艺术形象、创造美的“意匠经营”。
朱先生上述关于艺术思维的理论,对于推动、深化我国关于艺术思维的讨论,起了很大的作用。
朱先生的美学思想,在国内的影响是很大的。美学界中他的晚辈不论是跟他学习的还是批评他的,都在他的思想中受到教益。朱先生在解放以后所以能取得这样一些成就,这是和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分不开的。对于这一点,他是深有体会的。他在八十年代为青年朋友写的小册子《谈美书简》中就这样告诫青年人,他说:“学美学的人入手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还是学好马列主义。”[(96)]并在书的开头谈了他的切身体会和经验,他说:“在我所走过的弯路和错路之中,后果最坏的还是由于很晚才接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长期陷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泥淖中,解放后,特别在五十年代全国范围的美学批判和讨论中,我才开始认真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从而逐渐认识到自己过去的一些美学观点的错误。学习逐渐深入,我也逐渐认识到真正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并不是一件易事。”[(97)]在书的中间他又说:“就我个人来说,尽管我很晚才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近二十多年来一直还在摸索,但已感觉到这方面的学习已给我带来了新生……”[⑨⑧]这都是朱先生的肺腑之言,朱先生的美学思想的转变,及其深化和发展,确实是得益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朱先生的治学是很谨严的,他的态度是老老实实的。他错了就检讨改正,认为是正确的他就坚持,并再三地进行解释、说理。他的这种努力学习,实事求是的精神,我都深为佩服,并一定在自己的学习、治学过程中,好好地学习。
注释: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⑩《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一集,第12,13,121,264,81,82,118,119,45,122,123,116,117,102页。
⑥ (11) (12) (13) (14) (15) (16) (17)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8) (49)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88) (89) (90) (91) (92) (93) (95)《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三卷,第19,60,35,34,38,34 109,46,74,69,120,360,99,104,313,354,401,61,62,66,273,283,306,307,367,283,485,442,367,60,61,289,290,291,439,70,56,84,85,116,117,77,121,75,69,121,120,69,120,58,23,434,425,358,356,71,76,62,364,68,46,46,61,61,62,63,66,87,102,308,442,485,70,450,451,455,57,35,362,363,56,60,56,58,69,58,58,367页
(18) (94)刘勰 《文心雕龙·神思》。
(47) (50) (96) (97) (98) 《谈美书简》第65,151,163,9,37页。
(72)转引自《文艺理论与批评》1994年第5期,第136页。
(51) (52) (53) 《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第3,9页。
标签:美学论文; 朱光潜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客观与主观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当代艺术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问题意识论文; 人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