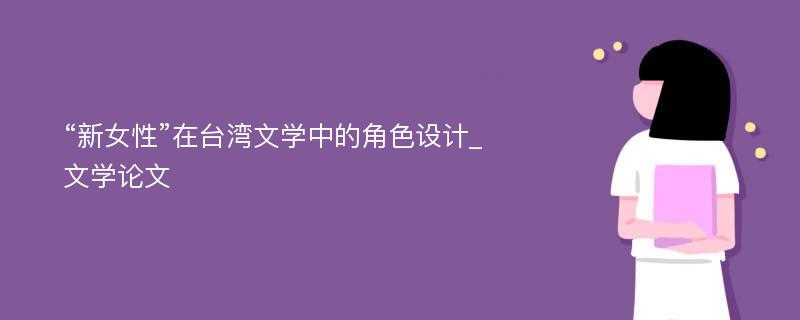
台湾文学中的“新女性”角色设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角色论文,女性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寻求妇女解放之途,不仅需要“破”——揭露、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打破数千年来妇女头上的枷锁,而且需要“立”——造就有别于旧传统的女性人格,树立新的女性形象。这种“新女性”的角色设计,至少可有如下三种类型:
一曰角色翻转,反客为主。这种女性对男权主义的压迫有深刻的体会和愤慨,不惜以各种方式加以反抗;或认定女性的能力并不比男性差,常以其超群出众的成就凌驾于男性之上,甚或“以其道反制其人之身”地对男性施于压迫和制裁。它以“女尊男卑”的关系式对传统两性关系作了180度的翻转。
二曰保持特性,呈示自我。这类女性并不否认男、女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但却不承认所谓男优女劣的传统认定,因此顺应自然地保持着女性诸多固有的特质,并以此显示了女性“自我”的存在和价值。它显现的关系式是两性的“并列”。
三曰双性人格、雌雄同体。这一类型认为男、女的性格中各有其优点和缺点,因此理想的人格应是取长补短,摈弃各自的缺陷,将双方的优点融于一体。它显示的两性关系式是双方的“融合”。
这三种类型的“新女性”,在近一时期的台湾文学作品中,均跃然可见。
一、角色翻转,女尊男卑
当女性文学走过凄哀地描写和控诉男权制度下女性之悲惨命运的层次,开始进行“新女性”的角色设计时,最早出现的,即是试图反客为主,取男子而代之的形象。深受男权主义之苦的女性,在冲出樊笼之际,将从来就在笼子外充当囚禁者和饲养者的男性作为效法的榜样,其实是很自然的。
80年代初袁琼琼就创作了这样的作品。《自己的天空》中的静敏,在丈夫外遇提出分居时,狠下心要求正式离婚,从此自谋生路,从一个绝少出门的弱女子,转变成一个有把握、能自主、事业有成的“新女性”。工作中碰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男人,虽是有妇之夫,但静敏“决定自己要他”,于是主动追求,最终如愿以偿。这时她所扮演的已是本来属于男子的阳性角色。相形之下,她的前夫则退缩为阴性角色。另一短篇《小青和宋祥》中的男、女主角更明显表现出角色的颠倒。
以长篇小说的容量,刻划出一个更为典型的“女尊男卑”家庭的,是萧飒的《如何摆脱丈夫的方法》一书。小说主角苡天是个有主见、性格泼辣的女子,怀着少女的浪漫离家出走,嫁给了她所崇拜的“才子”褚浩成。婚后迫于生活,她先帮丈夫找了个职低薪微的工作,后来自己也出外谋职,并因成绩突出而被提升为主管。家里逐渐形成了女主外、男主内的局面。褚浩成虽然懒散不思进取,但却安分守己,委屈求全,包揽了家务事。然而苡天有着十分强烈的进取心。丈夫越体贴,她越看不顺眼,甚至生出强烈的憎恨和厌恶。经过一段僵局,苡天最终找到“摆脱丈夫的方法”,得以与褚浩成离婚。
小说对于女性的特殊心理有着精细的刻划。如其感情的善变无常:“爱的时候,对方什么都是好的;不爱的时候,连看一眼都受不了。”(第57页)对于女性主义思想,小说也有着精到的表达。它通过苡天的嫂嫂之口表达了女人应改变将感情置于人生首位的观点。苡天从人鱼公主的故事中得到启示:女人实在不必盲目的只为爱情所缚,她要全力以赴的是事业,“要是没有了事业,我会连自己活着的价值在哪里都不知道,还谈什么其它呢?光有爱情,我也不会快乐的。”(第163页)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应取男子而代之,成为新的性别歧视者。小说最为深刻的,是对“新女性”成长中出现的“大女人、小男人”现象的观察、描写和省思。小说的结局显示着女主角并未能顺心遂意。显然,这场婚姻悲剧的主因在于苡天无法忍受丈夫的庸碌无为,而这实际上透露了男权社会传统观念尾大不掉的信息。这些“新女性”仍固守着一个亘古不变的准则——美满的婚姻必须有作为家庭支柱的“男子汉”的存在,因此无法容忍自己的家庭成为一个“女子主导型”的家庭;仍认准这样一个死理——事业有成是一个成功男子必不可少的条件和标志。她们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及足以自立的经济条件,却不能容忍一个在事业上比不上自己的丈夫。这说明数千年来沉积下来的女性“依附意识”仍牢固盘踞在这些“女强人”的头脑中。这种择偶上的刻薄要求,使她们的爱情、婚姻生活充满困厄和挫折,经常陷入苦闷孤独状态中。很显然,此道未必是理想的女性解放之路。
这种翻转角色、反客为主的现象,在一些“杀夫”故事中得到更强烈的刻划。萧飒早期短篇小说《姿美的一日》中因家贫而被迫做人姨太太的女主角,曾因丈夫的老丑而闪过勒死他的念头。这是“杀夫”的苗头,并未实施。袁琼琼的《烧》则是一个实施了的变相的“杀夫”故事。女主角安桃为了完全地占有丈夫,在丈夫生病的14天内,将他锁在屋内不让延医,导致丈夫的死亡。这样的故事在李昂的《杀夫》中得到极致的描写。小说的女主角林市,只有可供泄欲的女性身体作为其屠夫丈夫(陈江水)提供食物的交换,被迫忍受男性任意施加其身体的暴力。虽有寻求经济自立的企图,却为丈夫所不许;加上周围封建伪道德意识的诽谤和围攻,致使其心灵遭受致命的重创,终于在精神恍惚中效法男人杀猪般杀死了熟睡中的丈夫。这种受压制的女性采取极端方式报复男性的描写,在文学作品中时可看见,如曹禺《雷雨》中的繁漪。这些强烈报复男子的女人,几乎都是遭非人禁锢、压迫而产生心理变态的女人。她们总有机会(如男人睡觉、生病时)反过来宰制男人。在这短暂的时刻,她们由被压迫者翻转为压迫者,取男性沙文主义者而代之。正如张惠娟所言:“在陈江水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里,女子不能也不应寻求经济自立,因此等作为等于打破了传统两性的权力关系。林市最后将陈江水‘切斩成一块块’,在象征意义上,可说代表了对于女性遭受物化的反抗和控诉,将女性分崩离析、饱受切割的自我主体,投射到男性的肉体上。”〔1〕
显然,以极端方式报复男性也未必是女性解放之途,且极易引起男性的反弹。如古添洪认为:“《杀夫》这小说对妇女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社会里与男性相对待下的妇女问题,有震撼性的演出,但并没有带来什么能使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向前推进的东西。”〔2〕张系国则干脆写了《杀妻》与《杀夫》遥相对应。小说中的男主角受骄横妻子的欺压,引起精神幻想症而萌发杀妻之念。作者自述道:“我的《杀妻》,正是描述在女性已经获得了经济独立之后,丈夫地位下降,沦落成为无用的人的悲惨状况之一斑,并提出男人的传统自大心理,‘义和团思想’如何被打败,侧面指出妇女解放的积极意义。”〔3〕当然, 能引发这种反弹,本身就说明李昂等已达到其给“男性沙文主义猪”一个震撼和警告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类角色翻转的“新女性”形象,值得世上的男人和女人共同来加以反省。
二、保持特性,展示自我
上述翻转角色、反客为主的“新女性”之途未必行得通。另一些新女性主义者则承认男女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差别,并试图以此差别重新确认和强调女性自身的价值。她们力除父权文化认定的“男优女劣”的刻板印象,为此不惮于披露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真实内心世界,包括情、欲方面的特殊感受。这类作家可从阿德纳式图解中得到理论上的支持。阿德纳以两个相交圆(X和Y)来代表男性“支配团体”和女性“无声团体”的关系。这两个圆大部分是交叠的,但各有一未交叠的月芽形部分,代表男、女各自的特殊经验区域。大部分的Y无声圆被包括在X支配圆的范围内,唯有一月芽形Y在支配范围之外,这月芽形Y便能保持“原始状态”——它是一个完全没有男人的区域,代表着有别于男性的女性生活样态。本来也有一个严禁女人的男性X月芽形区域, 但所有的男性意识都在支配结构的范围之内(即整个X支配圆), 都可由语言表达或组合,早已成为传统的主题”,因此女人知道男性月芽形区域为何,即使她们从来没到过。而男人却不知女人的原始区域为何。对一些女性主义文学家而言,这个原始区域或“女性空间”就是建立一种真正女性中心的文学艺术和理论批评之所在,“她们的共同目标是要让女性意识的象征力量付诸实现,让不可见的部分变成可见,让沉默的开始说话。……当一个女人自愿进入此原始区域后,她便脱离‘男权空间的高压界限’而创作。”〔4〕了解到此, 就可理解为何立志描写女性特征的女作家们最多地涉笔于欲情题材,因这正属于所谓“原始区域”,为男性所不知,其内中的感受也与男性最为不同。通过此描写,最能达成对女性自我的探究。
黄有德的作品虽少,却几乎都对准着女性的“情欲”问题,并由此揭示了女性情欲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复杂性和婉曲性。詹宏志称她以“一个男女关系的光谱呈现”,揭示了欲望的“千种面貌”〔5〕。 《玉贞的手稿》中的玉贞是严守贞节的女子,因禁锢本能欲望而逐渐枯萎,终至了无生趣而自杀;《牛郎织女》中的陈太太则全无禁忌、完全按内分泌发情行事地放纵欲望。她们正代表着“性关系光谱”的两个极端。在他们之间的是《啸阿义,圣阿珠》、《异教徒之恋》等描写的情景。将几篇小说合起来看,可见女性“情”、“欲”的格外复杂的存在形态。
袁琼琼稍早的小说刻写“反客为主”的新女性形象,而在198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苹果会微笑》则试图通过女性欲情生活的描写,真实展现女性的内心世界及女性的心理成长。小说女主角赵光明在中年丧夫后与其他男人的关系,呈现出多种“面貌”,有的是无爱之性,如对那些老男人而言,有时则出于一种恋慕青春的本能,如对一些较年轻的男子,但有一共同点,是她对男人的一种习惯性服从。这种情况直到她与信德相识后才有所改观。两人的恋情是在“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自然状态下成长的,除了信德的相对年轻外,更主要的是信德比其他男人显得真率、诚实些。信德向光明“血淋淋的披露自己”,使光明“感觉了自己在信德心上占有了特别的位置”,她感到:“她一下子成了少女,在信德泛滥的热情里悸动不安。而心理影响了生理,她在展开身子接纳信德时,奇怪的觉得自己在做一件从前没有做过的事,她这具接受过无数男子的肉身,在信德的密语和自己的震动中被净化,变得纯洁和无知,而覆在她身上的,成为她此生唯一的男人。”(第149页)与此同时, 光明也逐渐认识到以往自己所过的是“没有自己的生活”,她决定在与海祥的婚姻中“豁开来”,自己“设法愉快”(第95页),也首次敢于拒绝一个求欢的男人(小彭),“居然把他给甩了”(第119页)。 女主角终于在欲情的海洋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小说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的曲折微妙极尽描写,展现了为男人所陌生的一个欲情世界,即上述阿德纳相交圆中的Y月芽形区域, 作者执意要探究的女性原真的内心世界。
这部小说一言以蔽之,就是“任性”、“诚实”和自然爱欲。作者曾称:“任性是不顾一切,不管别人,也不管自己。必须要任性才能诚实。”〔6〕一方面,作者是任性和诚实的。 她推崇濑户内寂听的作为,因这位日本女作家为避红尘而出家,却未能消减爱欲之心,于是也就安然的接受,“这也不失为一种诚实”。袁琼琼自述道:“这本书之所以会存在和呈现出来,其实也是根源于自己这点想诚实的任性,因为想试着来面对自己的肉体,来面对自己四十年来身为女子,对爱与性的感觉。”〔7〕另一方面,小说女主角也是“任性”和“诚实”的,她几 乎抛开了一切礼教习俗,诚实而任性地追求、展现自己的情感和爱欲,“很自然地去爱慕青春”(濑户内寂听语)。从这个意义上说,赵光明也是一个追求和实现女性自我的“新女性”形象。正如濑户内寂听所分析的:“人的心是善变的……在爱情终结之处,爱仍会茁长新芽”,许多人,已经有了贤慧的妻子或足可依靠的丈夫,为什么他或她还要移情别恋,更求肉体上的爱?“回答似乎只有一样:因为他们是人。自有人类以来,人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了。”〔8〕显然, 这种“任性”和“诚实”,正是实现女性主体意义和体现“人”的自我价值之所在。
顺应自然的欲情主题是李昂创作的重心所在。如早期作品《雪霁》“将性提升到劳伦斯的观念层次,性是原始的、纯真的、健康的、自然的,是一种冲破藩蓠自我更新的祭典。”〔9〕《转折》中的女主角通过自己选择的性爱而实现了自我——她爱上有妇之夫却难以结合,即在新婚前夜将自己给了那有妇之夫,虽是唯一的一次,却因拥有了最直接最忠诚的对方而从此不再遗憾。《莫春》一作以极为大胆的笔触直接刻写女性在性爱过程中的感受。女主人公唐可言觉得“唯一实在的只有那可证实自身的男性身体及由此引发的行为”,通过作爱“点细体知出新临的乐趣”和“一种”缓缓注入生命基础源泉的安慰”,觉察“潜藏体内的未知部分悉数被开发了”,从而证实自己“是一个完整的女人”。李昂对此解释道:“我们是为男性或女性,性别应具有何等意义和特性,必有一段混淆的时期,历经成长的转变,性是为一种自我存在的肯定。那也是何以性在我的追寻中占有这般重大的意义。”〔10〕
然而,李昂与大多女作家不同的,是她自觉地将男女的性爱和社会问题相连接,指出某些性爱行为乃是现代人孤寂、空虚心灵的一种慰藉。如对《莫春》一作她自我检讨道:“我没有将这小说推展到另一层次,去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产生这种病根,这种如此迫切的想要藉性来解决问题的矛盾。”并表示:“假如性与社会的一些问题是相关联的,我还是会以性为题材来写,可是,不再会像《莫春》只限定在两个人的关系。”〔11〕因此,她笔下的女主角多数是以苦闷的态度来面对性的接触,常呈现出一种绝望的激情和事后的空虚;这样的描写,“只给人强烈性反抗的象征……象征了女性的自我追寻、肯定和突破。”〔1 2〕
此外,李昂的另一个特出之处,在于描写女性“原始区域”的特殊经验的同时,还揭示了她们必须自强、自立、自尊的真谛。近作《迷园》是一部结合了性与政治、女权和人权主题的长篇小说,其中一条线索铺展女主角朱影红和暴发钜子林西庚的感情、婚姻纠葛。在这里,李昂仍发挥了真率地表达女性在情爱生活中的特有感受的特长,如描写了朱影红最初为林西庚所吸引时渴望被臣服的心理;描写了朱影红与Teddy 张的无爱的纯生理的接触也能带给她的回应和愉悦;更描写了与林西庚的建立在真正感情上的性爱所带给她的对女性自身的发现。但另一方面,李昂表达出,男女的情爱,毕竟与社会环境紧密相关,女性要获得真正的幸福,还需靠自强自立。当朱影红沉迷于感情,心甘情愿地“臣服”于男性时,节节败退,几乎沦为情妇不如的地步;后来她挣脱感情的枷锁,认识到自己必须是林西庚追求的对象而非他豢养的女人,因此一反以往以林西庚为中心的行为方式,毅然拿掉所怀着他的胎儿,并表示绝不纠缠,显露自强自立的决心。事实证明,这样反倒能挫杀大男子主义的霸气,寻回自我,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然,这类女性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能取得胜利的毕竟是少数。廖辉英、苏伟贞、蒋晓云笔下女性的“姻缘路”往往更为曲折和哀凄。她们着眼于“以女性的本性来写出两性关系中的潮流与危机”〔13〕,所谓“女性的本性”,即女子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不同于男子的观念意识、情感态度和处理方式。苏伟贞塑造的女主角,多是有知识,有教养,如出尘的莲花,清明高洁,又具有一份“无可理喻”的真情。她们有的“情到深处无怨尤”,明知寡情的对方终要离开,反而格外疼他惜他,心甘情愿地要陪他走一段(《陪他一段》)。即使能逃出“痴”境而淡然释然,取宁缺勿滥的姿态面对“爱的阙如”,其内心仍有着对“爱”的执着,才这样毫不放松的要求有“真爱”的婚姻。在与大多数男性角色对爱情态度的自私、轻率乃至龌龊的对比下,苏伟贞写出了一个女性独特的感情世界。然而这些女性角色最多也只是洁身自好,从未有求取男女平等地位的诉求和举动,相对于《迷园》中的女主角能反制男性而取得某种意义上的“胜利”,她们显得软弱而无力。廖辉英同样致力于刻写女性特殊的情感世界——她们往往更需要情爱的慰藉;更由于社会长期的压抑和束缚,至今仍难以消除种种怯弱和自卑的心理。如《不归路》中的李芸儿,出于寂寞,结识一有妇之夫并失身于他,从此欲向他托付终身,乞讨温存。而《窗口的女人》中的朱庭月亦属同一类型。
苏伟贞、廖辉英等笔下的女性虽然缺乏抗衡男权主义的锋芒,但她们与那种从一而终,死守贞节的传统女性,已有很大区别,可说已进入了“新女性”的行列。只是她们仍保持着较多的“女人味”——一种不同于男性的独特的女性气质和情感特征,不管这些特征是根植于女性生理或心理的固有特质,或者其实是男权社会长期以来强加于女性的观念意识。这些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凄恻命运,说明这些纯女性化的角色,和那些反客为主,试图凌驾于男性之上的纯男性化角色一样,均难称完美的人格。女性不能模仿历史上的男性成为新的性别歧视者,同样,女性也不能在父系文化限定的女性精神内求得自我的完善和解放。
三、雌雄同体,双性人格
无论是男、女角色的翻转或两性角色的并列,显然都未尽人意。部分女性主义者则提出了所谓“雌雄同体”或“双性人格”的设想。凯若琳G.赫布兰在《双性人格的体认》一文中写道:“我相信未来的救赎全赖超脱性别的两极化和禁锢,而迈向一个允许自由选择角色和行为模式的世界。……这个理想称为‘双性人格’(androgyny)”, 它“指两性之间水乳交融的精神”,这不仅是男女“对待彼此如兄弟姐妹”,而且是更深一层的“自我重新结合两性”;正如戴奥尼色斯那样“呈现自己为男人中的女人或女人中的男人”,在其身上“刚健与柔弱混合,威凛与妩媚并存”。或者说,这种角色设计要求性格的划分与生理性别彻底分手,女性可以涉足原本属于男性的精神领地,而男性角色也可以具有传统的女性风度,男女之间取长补短,互通有无,从而建立一种兼具两性优点的更完善、和谐的人类。
从艺术形象看,朱秀娟的小说较多地塑造了这类人物。如《女强人》中的女主角林欣华一改传统女性自卑畏缩、依附性强等弱点,面对联考挫折,毅然选择通过社会实践以求成才的道路。无论是起步阶段的超常人的刻苦学习,或是稍后在竞争激烈的商业运作中独当一面,敏捷、果断地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和魄力,确令人有“巾帼不让须眉”之叹;而她在爱情婚姻问题上表现出的以事业追求为重、自尊自爱、不为“情”字所役的理性态度,也与传统女性判然有别。然而,作者在赋予人物这些似乎属于男性专利的优点后,却让她仍旧保持着若干女性固有的性格特征——或称传统的女性美德。如在家庭中能忍辱负重,表现出对家庭成员的孝心和亲情;在工作中表现出作为一个女性的较能与同事协调配合的特点,以及对所服务公司的某种程度的忠诚——在职权被解除后,她并不采取恶意报复手段,而是保持超逸的姿态,必要时仍为公司的利益工作。正如论者所言:“这种胸襟与气质,乃天性之至刚至强,始能具体表现出甚柔至弱的修为。”〔14〕
小说不仅塑造了性格向男性方向滑移的女主角,同时还刻划了一位性格向女性方向滑移的男配角——叶济荣。女主角在先后两次倾心于两位家境豪富、风度翩翩的“白马王子”,终因无法忍受他们对她的限制而相继告吹之后,终于回头选择了这位从小青梅竹马、后走求学之路而略显隔阂的男友。其实,这位似乎缺乏所谓“男子汉”气概的留洋回台博士,在女主角遇到困难时总能给以智慧的忠告,行动的指南。这一人物的塑造,有意无意正吻合了“双性人格”提倡者的这样一种认定:富创造力的男性比创造力稍逊者更常表达天性中女性化的一面。赫布兰曾引用心理学家麦钦南在一项性别倾向测验中的研究成果:“富有创造力的男人在女性化方面的得分也相对较高,虽然他们整体看来并无女性化的外表,对同性恋也没有较高的兴趣或较多的经验……他们对情绪和感受保持开放的态度,也具有敏锐的智性,善于体谅的自觉,及广泛的兴趣——甚至包括许多被美国文化视为较女性化的活动。”〔15〕无独有偶,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的中国大陆学者孙绍先也认为,知识男性比非知识男性更带有女性化的特征,因为:“知识的积累是以理性形式出现的,那种冲击秩序、冲击理性的鲁莽性格,不能不在知识世界中一再退却。”〔16〕由此看来,朱秀娟着力塑造男性化的女子形象和女性化的男子形象,并让他们双双成为胜利者——事业上和爱情上的胜利者,似乎正寄托着作者的理想——一种融合两性固有优点的“雌雄同体”的“双性人格”。
朱秀娟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丹霞飘》塑造了类似的“女强人”形象,只是这位女主角尹桂珊保持着更多的传统女性品德特征。她具有超乎一般男人的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禀赋,也取得了不少男人无法企及的辉煌成就;但她又具有自洁自爱的品格、亲切大方的风范、刚柔兼济的素质。小说的男主角刘炳弘则与《女强人》中的叶济荣相似,扮演着以其宽阔的胸襟、坚强的毅力和聪颖的智慧鼓励、协助、支持妻子攀登事业高峰的“新男性”角色。
另一位倾向于刻划“双性人格”的作家是吕秀莲。在《新女性知多少》一文中,她断然否定新女性崇尚男性化、重女轻男、要与男人为敌等说法,并明确肯定新女性能兼具阳刚与阴柔,主张权力的平等也强调义务的均衡,愿和有理性、重人道的新男性携手缔造更融洽的两性社会。这一理念,在其《这三个女人》、《贞节牌坊》、《小镇余晖》等小说中得到艺术的体现。
首先,吕秀莲让她笔下的“新女性”仍保留着若干传统女性固有的品质。面对男人试图将她们“纯女人化”的企图——如《这三个女人》中的许玉芝受到丈夫“本本份份地做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象单细胞植物那样,越单纯越好”的要求——她们或迟或早都能加以抗衡,克服依附于男子的阴柔性,求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但她们并没有走上凌驾于男性的另一极端。如许玉芝在突破贤妻良母的角色后,仍珍惜其家庭生活,较好地处理了施展自我抱 负和维持美满家庭的关系。她的同学汪云,其传统女性的梦想被现代生活撞得粉碎,终能深自反省,体察和理解丈夫生前外遇的原因,并对“情敌”表现出女人之间的姐妹相惜之情。即如典型的“新女性”高秀如,对于人生原则有着格外的坚持,但她并不拒绝婚姻和感情,遭遇挫折时,也“渴望能有一双笃实的臂膀相提携”。在介入一场三角恋爱时,她同样表现出“姐妹团结的觉悟”。正如陈菊所言:这显示作者笔下女性刚中有柔,柔中有细,“作者尝言是什么象什么,这不一定是女性的委屈求全,或可言之为东方文化形态所塑造出来的产物”〔17〕。其次,吕秀莲又不忘“新男性”形象的塑造。因她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离不开两性的相依互勉、相互扶持,而这就需要男人克服其“大男子主义”等观念。《小镇余晖》中的俊、《贞节牌坊》中的叶明就都是这样的“新男性”。俊对妻子以前与别人的一段旧情,能够给予充分的体谅和容忍。叶明在蓝家遭变故时,仍不改对蓝玉青的爱情,并宽容后者为偿还父债而当伴舞女郎,真心地给予同情,时时予以督促,使她不会迷失自我。这样的人物,与朱秀娟笔下的叶济荣、刘炳华等颇为相似。
更重要的是吕秀莲对“贞节”观念作了新的诠释。小说中明确、反复地表明了如下观念:贞操不是某种生理表征,而是心理的忠贞,因此它不以传统的“性”关系为限;它应是两性共同的责任,而不应是单方面的苦守,更不是为了光宗耀祖,满足男性片面的虚荣;“贞操应该从礼教的桎梏提升为人性的修练,从被动的束缚转换成主动的操持,更从女性片面的伦理扩充为两性全面的道德戒律”。显然,吕秀莲并不想完全废除“贞操”概念,而是力图加以改造,注入新的内涵。一方面,她向本无关乎“贞节”的男性头脑中注入“贞节”观念——一种对自我尊严和生活原则的操守和坚持;另一方面,她使女性在“贞节”问题上由被动改为主动——从被迫的压抑人性的举动变为主动坚持的精神上的操守。这样,吕秀莲小说中的男女分别从两性对峙的两个端点相向滑移,终能在某一点上相遇拥抱、握手言欢。而这一会合处,呈现的即是融合两性优点的“双性人格”。
然而,所谓“双性人格”也许是人格完善的终极目标,但在当前现实环境中仍只不过是一种理想。妇女的不同于男子的心理特征和社会角色尽管有着令人愤慨的历史因由,但既已形成,要在短期内完全消除并不现实。另外,这种十全十美的女性,实际上乃应合了一般人(特别是男人)对女人的期待。因此,这类作品经常显得过于理想化或概念化,乃至有媚俗之嫌。张惠娟就曾对朱秀娟的作品有较为中肯的评价:“赵光明的故事(指袁琼琼《苹果会微笑》——笔者按)尽管结局突兀,其通篇潜藏的嘲讽至少提供了另一层反省的深度。相较之下,朱秀娟的《女强人》则‘完美’得象‘一本中规中矩的女性励志小说’,其情节安排屡屡予人以不真实之感。女主角欣华的故事充满了巧合,其迈向成功之途所遭逢的困顿皆得以轻易解决,甚至作者所刻意铺陈的婚姻与工作冲突的主题,也在结尾以一个新式婚姻的乌托邦远景轻轻带过,浪漫有余,而深刻不足。”〔18〕
结语
综言之,世间女子只有在两性关系式中建立起自己的新人格和新形象,才算为妇女的解放找到了明确的方向。上述三种女性角色,虽然不同程度地冲破了男权主义的樊蓠和传统贞节观念的枷锁,但都还有不尽人意之处——或本身人格尚非完美,或过于理想化而缺乏普遍性和现实性。这显示了妇女解放课题本身的复杂和艰巨,而并非都是作者在创作上的缺失。相反,台湾女作家笔下“新女性”形象的多样化,说明其艺术思维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开拓,这也是近年来台湾女性主义文学不同于以前女性文学的一个明显的进展。
注释:
〔1〕〔18〕张惠娟:《直道相思了无益》,《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第55页。
〔2〕古添洪:《读李昂的〈杀夫〉》。
〔3〕《杀夫·杀妻·沙猪——张系国V.S李昂国际传真对谈》,《沙猪传奇》第221页。
〔4〕伊兰·修华特:《荒野中的女性主义批评》,《中外文学》14:10,1986.3。
〔5〕詹宏志:《欲望有千种面貌》。
〔6〕〔7〕《苹果会微笑·后记》。
〔8〕濑户内寂听:《你能赤裸着从男人面前走过吗? ——〈苹果会微笑〉代序》。
〔9〕〔12〕〔13〕贺安慰:《台湾当代短篇小说中的女性描写》,第99、94、88页。
〔10〕〔11〕林依洁:李昂访谈录《叛逆与救赎》。
〔14〕济贤:《现代社会的心路标志——〈女强人〉读后印象》。
〔15〕凯若琳G.赫布兰:《双性人格的体认》。
〔16〕孙绍先:《女性主义文学》第76页。
〔17〕陈菊:《无情人生有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