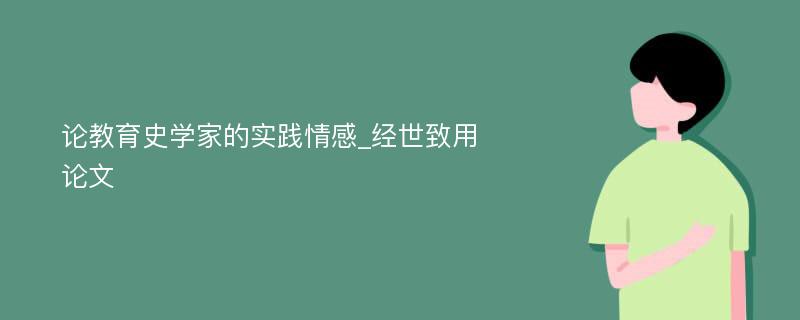
论教育史学者的经世致用情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世致用论文,教育史论文,情怀论文,学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2-0097-05
晚近十余年,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焦点论题。尽管学术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特征及其作用等论题尚众说纷纭,但是论者似乎大都公认:大凡公共知识分子,都会对当下公共的社会问题予以由衷的关注,并且通过权威性的学术判断和呼吁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感召力。相形之下,那些在象牙塔里专事学院式教学和研究的教育史学者,其社会影响力的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似乎可以断定,以既往的史实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史学者,与对当下现实问题予以探究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学术团体,二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对特定受众的影响似乎也应该是泾渭分明的。尤其是在公共知识分子被社会大众赋予能够“点石成金”的使者光环,而教育史学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逐步趋于边缘化的境况下,前者的荣耀和后者的式微态势就愈加显而易见。本文拟从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以及教育史学者在立足既往客观史实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和如何关照现实问题的层面,对后者应然的现实价值取向等问题予以初步的探究。
一、中西方知识分子的知识论比较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舶来品”。要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探究我国教育史学经世致用的问题,如果离开我国知识分子历史发展的地缘文化特征,就无从谈起。反之,如果离开西方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特征,所谓的地方性就会失去参照的框架。
我国传统的“士”阶层,是知识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关于“士”的起源,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局之后逐渐演变为“文士”。如果以儒家的鼻祖孔子推算,我国“士”的传统及其知识传承至少延续了2500年。孔子早先提出的“士志于道”的学问人生品质,不仅规定了“士”阶层的历史使命,也成为历代“士人”知识诉求的楷模。孟子也曾对“士”予以阐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隋末唐初创建的科举制度,将做官与做学问捆绑在了一起;此后的知识阶层具备了“学而优则仕”的外在功利色彩。但是“由士而仕”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秉承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豪情为理想的境界。“士人”的“明道”与“救世”是统一的,并无先后顺序之分。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和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即为此意。
反观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其知识阶层的价值取舍与我国“士人”有诸多不同的旨趣。古希腊三哲之首苏格拉底,曾提出过“知识即美德”(knowledge is virtue)的命题。在苏氏,“知识”本身即意味着真善美的标准。亦即,一个人只有知道(“知识”)何为“对”何为“错”时,他才能够去做“对”的事情,其结果就是“美德”。没有人会知“恶”而故意去做“恶”。“知识即美德”的反命题是“无知即恶”(ignorance is evil)。亦即,倘若一个人不知道(“无知”)所做之事属“恶”,那么他就会继续做“恶”,其结果必定是恶性循环。苏氏试图获得的是关于真善美的“真知”(true knowledge),而非市井的“俗见”(public opinion)。尽管苏氏最终被判“蛊惑雅典青年罪”饮毒酒而亡,但是他秉性诉求的只是“为知识而知识”(“明道”)而已,并无“救世”的致用目的。挨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将“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划分得泾渭分明。在他们看来,世界由流动不居的“现象”界和亘古不变的“本体”界组成。前者经由感官获得“影象”(image),而后者则是只能经由理性才能获得的“真知”(form);哲学家的全部天职即在于超越纷扰模糊的“影象”,达致永不坏缺的“真知”。以“精神贵族”自居的古希腊哲学家,关注的是属于理论理性的“真知”,而非属于现实实践的“影象”。这种“二分思维虽非西方所独有,但确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与实践的二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1]3
由此可见,在“轴心时代”里,中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明道”的不懈追求是一致的,二者的分殊在于是否“救世”上。对于“为知识而知识”的古希腊知识阶层而言,中国“士人”所秉承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伦日用特征,不免掺杂着对纯粹的“知识理性”打折扣的功利色彩。而对于将“明道”与“救世”合而为一的中国“士人”而言,西方古代哲人摈弃“形下之器”的人伦之用而偏执于“形上之道”所谓的“真知”,是对“知”与“行”的割裂甚至于“良知”的泯灭。孜孜以求于“传道授业解惑”,甚至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似乎是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和天职所在。
近代伊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武力叩关之后,我国被迫进入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此后,我国传统“士人”所秉持的“明道”和“救世”传统,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启蒙”和“救国”的两大历史使命。如果说传统“士人”的“明道”具有“为天地立心”的理性意义的话,那么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则主要是借用“西学”开启普罗大众的心智。如果说传统“士人”的“救世”主要是通过“诤谏”进而达到“政通人和”的话,那么近代知识分子的“救国”则试图通过“追赶”西方列强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以西学“启蒙”,当然要译介西方的作品。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就断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在“天下兴亡”的时刻,近代知识分子以“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关切的主要是如何“经世致用”的问题。正如章太炎所言:“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2]可以说,这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观点。显然,章太言所说的“应用”,主要是以“西学”为楷模,用于“启蒙救国”。这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具有迥然不同的旨趣。就思想史来看,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康德曾对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予以扼要的总结:“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著名学者余英时曾经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则显然代表一种崭新的现代精神。和基督教的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在天上;和希腊的哲学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1]5西方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以无畏的理性担当两种角色:一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二是知识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进而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可见,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西学”为楷模承担起“启蒙”的重任时,他们只能充任“西学”的传播者,而非新知识的创造者。一旦拜“西学”为师,“师道尊严”的传统似乎只能演化为对西学的解释和传播,知识创造者的角色似乎早已属于作为先行者的西方同行。批判意识的缺失、理性的匮乏和创新能力的不足等,似乎成为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不可逾越的屏障。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对我国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等都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对于教育史学者而言,其影响亦复如此。
二、教育“信史”与教育“良史”
史学研究的客观性抑或说真实性,业已成为通达的史学家判断其是否为“信史”的首要标准。于此,中外史学界概莫能外。无论是对于当下的抑或是过往的事情,经由客观性进而达致真实性的不懈诉求,可谓人类的本性使然。人类的意识、记忆和理性,一直在不断地提醒着自己,在既往的时空里必定存在着一部客观真实的人类发展史。历史,可谓人类永远无法亲手割舍的脐带。他知道,他自己即生活于瞬间即逝的历史之中,或毋宁说,他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除非他确信过往历史的真实性,否则他就无法相信他自己当下存在的真实性。故而,对于自己乃至于先祖真实历史的穷究,一直并将永远是人类长此以往昂然不衰的兴趣。自人类有意识地开始口述历史和书写历史以来,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历史的客观性或者说“信史”,也一直处于探索之中,但却始终尚待完善。究其缘由,人类本身意识的模糊性、记忆的缺陷、理性和技术手段的乏能等,是导致人类信史可望而不可及的主要原因。当然,无意识的误解甚至于有意识地歪曲和篡改历史,更使得信史的达致愈加艰难而曲折。可幸的是,人类并没有因为自身天性的缺陷以及人为的阻挠而放弃对于历史之客观性的探究。
同样,人类对于自身教育发展史之客观性的探索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作为地球上万灵之长的人类,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是唯一能够通过自身意识不断地自我改善并试图超越自身和外在限制的种属。这种有意识的改善和超越,离不开有意识的教育。如果说繁衍和生存是所有物种的本能,那么在此之上不断地追求自我改善和超越,却需要有意识的代际传授和教育活动方可实现。正是借着代际教育活动的不懈积累和反思,人类的教育经验才得以不断地丰富和趋向完善。但是,经验的获得并非一蹴而就,没有错误和教训的经验并不足以引起人类的珍视。故而,只有客观真实地记载和保存人类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并对之予以切己的反思、修正和改善,人类才能达到不断地改善和超越的目的。可见,能否对人类教育发展的状况予以客观真实的研究,也是判断其是否为“教育信史”的首要标准。
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教育信史”与“教育良史”之间的区别问题。可以说,这是长期以来学术界见仁见智的议题。从词源来看,西文中的“history”(历史)一词,是由词根“hiu”(意为“老人”)加上“story”(意为“故事”)简化组合而成。可以设想,在书写文字没有产生和普及之前,先祖们主要是通过“口口相传”来传递历史,这也是日常生活和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此,“老人”和“故事”,是构成“人类历史”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之所以赋予“老人”作为历史的传递者,大凡因其亲历历史之久远,并且具备族群心智和道德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大凡“故事”,皆有开头、具体情节和结尾三个部分组成。作为已“故”之“事”的“故事”,其真实性当然是首要的,但是若“故事”的情节和结尾都不能引人入胜并且具备一定的启发性和教育性,则口述“故事”的“老人”无论具备何种高度的权威性,也不能保证其能够引起后代倾听“故事”的兴趣,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文和道德教育价值。为了达到代代相传的目的,历史“老人”在保证“故事”之“真”的基础上,就必须赋予“故事”以特定的“善恶”和“美丑”的价值取舍。正是通过这种价值取舍,人类文明和教育发展初期的“信史”和“善史”才达到了完美的融合与统一。直到19世纪教育史学在西方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得以确立之前,人类教育的“信史”和“善史”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统一。
19世纪初期西方出现的史学运动,促使西方史学逐步迈入了科学支配的时代。凭借科学技术带给人类“形下之器”的万般便利,科学主义亦随之成为风尚。科学主义史学家自信,通过万能的科学治史方略,即可以达致“信史”;而史学研究应该止于“信史”,史学研究不应该也不允许带有任何人为的价值负载和取舍。科学史学家认为,“历史是科学,不少也不多。”[3]更有科学主义史学家甚至认为:“史学家唯一能够做的,只是‘呈现史实,然后让史实自己说话’而已。”[4]可见,科学主义的史学观,没有给史学家留下任何人为的价值取舍余地。在他们看来,“信史”的唯一标准就是对史实之“真”的呈现,史学家无须对史实予以“善恶”和“美丑”的价值判断,抑或说,“信史”本身就是最好的“良史”。
经由科学史学运动而产生的三大流派,即量化史(quanto- history)、社会科学史(social science history)和心理史(psychohistoty),的确通过精确的治史方略促进了“信史”的长足发展。但是,反对科学主义史学观的人文主义史学家却认为,“历史是艺术”,是一门靠设身处地的想象、移情、同情、理解和推理等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艺术”。正如有学者在批判科学主义史学时所言:“量化研究对于史学家而言,是好的奴隶,坏的主人。”[5]针对科学主义史学家坚信史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仅在于呈现历史事实的观点,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也曾经指出:“‘事实本身不会说话。’概念不是从证据中‘浮现出来’的。‘只有当历史学家光顾事实时,事实才会说话:历史学家决定哪些事实可以有发言权,按照什么顺序和在什么情况下发言’。”[6]亦即,在史学家光顾既往的事实之前,它们只能是自在的“一般事实”;只有当史学家“让”它们发言时,它们才能成为“历史事实”。史实的选择尚且如此,对于史实的理解、解释乃至于最终的价值取舍就更不待言了。
应该说,执著于史学是科学抑或是艺术之争,皆有失于偏颇。仅就事实的获取而言,科学家可以采用直接观察法,而史学家对事实(史实)的获取和观察则主要是间接的。再者,科学研究的通则通常在于,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研究的结果是可重复的且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无论是史学家抑或是教育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都是既往的并且具有永远不可逆转的特征。通达的教育史学家大都会公认,科学的治史方法与人文史学观的融会贯通,方是治史的良策,也是获致教育“信史”与教育“良史”和谐统一的不二法门。
三、教育史学者的专业性与致用性
人类知识的分化和专业化,开始于19世纪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由科技发展造成的工业化、劳动分工、社会分化和科层管理等特征,引发了知识的规模化生产和学科专业的分化。当知识的专业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必定要求某一专业的从业人员必备某种有别于其他专业的特定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基本素养。高度的专业化宛若一把双刃剑,它在赋予人类知识精耕细作、高效生产和精细认识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知识整体的条分细割和各种不同的专业人员之间的隔膜和漠视。当某一专业领域的门户一旦划定并且专业升迁的评价标准业已既定时,从事该专业的人员只需循规蹈矩地付出一定的专业劳动即可获得“行规”的认可及其相关的利益。尤其是当现代的制度化专业研究与传统的作为人生终极价值诉求的学问之间逐渐疏离,进而演变为谋生的职业时,传统的士大夫阶层所终身秉持的“明道救世”情怀,似乎只能成为现代专业化知识分子梦思魂游的美好回忆或理想而已。
美国学者雅各比(Russell Jacoby)于1987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通常被认为最早提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认为,在高等教育尚未实现大众化和专业化的时代里,知识分子是作为“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坚定独立的灵魂”而存在的。但是在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和专业化之后,“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大学教授,校园就是他们的家;同事就是他们的听众;专题讨论和专业期刊就是他们的媒体。”[7]这种业已体制化的专业发展安排,使得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自娱自乐的象牙之塔俱乐部,他们的专业话语和作品只限于在俱乐部成员之间分享。换言之,仅仅沉迷于专业探究和专业发展,似乎成为制约现代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问题予以公共关怀的主要原因。雅各比所关心的,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专业化业已不可逆转的时代背景下,如何重建知识分子“公共性”的问题。
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和功能,美国学者萨义德(Edward W.Said)的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干成员。”并且,“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人。”[8]在萨义德看来,大凡在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都属于公共知识分子,并不仅仅局限于体制内的专业人士。问题的关键是,公共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向”和“为”公众表达观点的“能力”。由此可以推断,在教育尚没有得以普及的近代以前,中国的“士人”和欧洲中世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贵族和牧师等知识阶层,无疑是唯一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但是他们却未必能够和愿意“向”和“为”公众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现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打破了传统的精英阶层对这种“能力”垄断,而知识的专业化又使得专业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向”和“为”公众利益表达自己观点的兴趣和使命感。可见,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专业化不可逆转的背景下,如果专业知识分子要重返社会良知、公平、正义和自由“守夜人”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其前提必须是首先立足于专业的积累和发展,进而凭借其专业造诣的权威性为依托,拓展社会公共领域的话语资源权、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当今教育史学科的发展逐渐趋于边缘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审视本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如何在坚守本学科专业发展的前提下关照当下的公共领域议题,是任何有志于教育史研究的学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可以说,对于教育史学科所面临的危机予以应对和挑战的重任,只能由教育史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来担当。可以肯定的是,应对学科危机的良策莫过于拥有雄厚的专业化挑战实力。1919年,马克斯·韦伯在为德国慕尼黑大学青年学子们发表的《以学术为业》的讲演中曾经指出:“无论就表面还是本质而言,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在韦伯看来,“最彻底的专业化”即意味着虔诚的学术热情、视学术为天职的孜孜以求以及勇于承担各种学术风险的敬业精神等。抛开学术的外部环境等制约因素而不论,我国教育史学发展所面临的危机似乎主要在于“最彻底的专业化”精神的缺失。当对教育史学研究的选择并非出于兴趣并且被降格为一门区区的谋生职业时,当教育史学者屈服于“不出版即灭亡”(publish or perish)的职称评定规则时、当浅尝辄止的研究成果成为获取仕途利禄的工具时,教育史学“最彻底的专业化”就只能是奢望而已。尽管学术界对“由博致约”抑或是“由约致博”的治学途径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是毋庸置疑的是,没有经过“约而深”的专业化洗礼,即以专家自居而对现实的公共问题“指点江山”,那只能是浮光掠影式的沽名媚俗而已。可见,如若教育史学者要达到淑世致用的学术理想,其立足点首先应该是“最彻底的专业化”,以教育“信史”之“真”关照和审视当下的现实问题;在此基础之上,以教育“良史”之“美”与“善”的价值取舍,对相关的现实公共问题予以评判和呼吁,从而达到“明道救世”的价值诉求。
收稿日期:2010-02-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