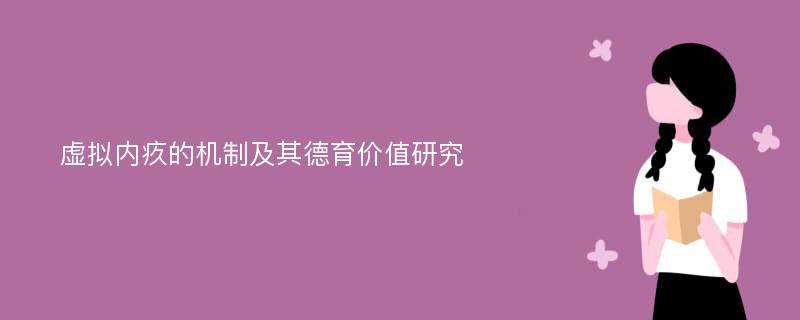
王蓓[1]2003年在《虚拟内疚的机制及其德育价值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虚拟内疚的涵义、类型、发展等方面总结了虚拟内疚理论的研究现状,并通过实证与理论研究探讨了虚拟内疚的影响因素、发生机制及功能。实证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结果表明:关系的亲疏、结果的轻重、移情水平的高低是虚拟内疚产生及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自我责任归因是虚拟内疚产生时的主导归因,随着虚拟内疚易感程度的降低,归因呈现多元化,责任归因由指向自身逐步转为指向外界,自我责任归因受到关系、结果及个体移情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虚拟内疚产生后的补偿行为倾向呈现等级性,以安慰行为居多,而物质补偿行为较少,虚拟内疚与各补偿行为倾向正相关,关系、结果、移情水平影响补偿行为选择。综合现有文献与本次实证研究结果,认为虚拟内疚的影响因素包括:既往经验、移情能力、道德水平、关系亲疏以及结果严重性。虚拟内疚的发生经由叁个环节:既往经验诱发移情性悲伤;移情性悲伤驱动认知归因;认知归因的自我指向引发虚拟内疚。而虚拟内疚的道德功能表现为:促进个体道德自我的形成与完善;促进个体道德内化的进程;促进个体道德行为的实施。因此在学校的德育过程中,可以通过适当引发学生的虚拟内疚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
刘金梅[2]2009年在《不同虚拟内疚类型下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选择研究》文中认为内疚是一种与人际交往紧密联系的负性自我意识情绪体验,霍夫曼把内疚分为违规内疚和虚拟内疚,亲社会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是一种普遍的行为。作为对个体所经历的不良事件进行评价和认知的产物,内疚可以引发亲社会行为。本研究用情境故事法探讨了10-18岁青少年的不同虚拟内疚类型与亲社会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青少年对不同类型的虚拟内疚的体验强度存在年级差异,虚拟内疚的体验强度随年龄的增长逐渐加强,在初中阶段,对虚拟内疚的体验出现出现反增长;2.对家人与对同伴在不同虚拟内疚类型中其体验强度存在差异;3.在不同虚拟内疚类型中移情水平影响个体的虚拟内疚体验强度;4.在不同虚拟内疚类型中,不同年级青少年对亲社会行为类型的选择无显着差异,其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存在差异;5.不同虚拟内疚类型中,对家人和对同伴选择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存在差异;6.对亲社会行为选择的可能性受到虚拟内疚体验强度的影响。
孙杰[3]2014年在《虚拟内疚理论视阈下思想政治课德育路径述略——以“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教学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于虚拟内疚的发生机理,思想政治课教学可尝试创设虚拟违规场景,激发学生的虚拟内疚,以既往体验诱发悲情换位,促成"情绪充予"的道德审视;以悲情换位趋使自我归因,趋于道德自我的"理想"抉择;以自我归因催生虚拟内疚,获致道德情感的"应然"内化,从而跃升受教育者的道德责任与由心之境,化"实然之我"为"应然之我"。
孙杰[4]2016年在《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学生道德抉择能力培养策略研究》文中认为伴随学界对基础教育改革中素质教育理念的“再认识”,包括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在内的基础教育阶段各学科的“核心素养”问题开始广受关注。而直面道德冲突作出道德抉择的能力,无疑是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由此,如何着眼学生学习与生活中的某些德育要素,基于思想政治课伦理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交叉背景,探新其作为中学德育首要途径的路径范式,实现化解学生因道德冲突所致角色迷失等“心理隐疾”、培养学生包括道德抉择能力在内的德性“核心素养”,就成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的当务之急。藉由“基于病灶—引入范式—实践推进”的德育实践路径,笔者尝试以“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一节教学为例,就“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学生道德抉择能力培养的策略”试作探新:(一)当下思想政治课,更多的是一种非善不教的德育单面论证。而这只会由于“认知不协调”而加剧学生的心理冲突与道德困惑。笔者尝试“接种防疫”,以“双面论证”促进道德抉择: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引入“负面道德”以双面论证,藉以增强学生的道德免疫力,化解其情感困惑与心理失调——“预警”以诱导个体应激,“接种”以“分泌”“免疫抗体”, “防御”以作出“免疫应答”。(二)基于“宏观”视界与“社会本位”教育路径的思想政治课抽离与失却了“思想”。笔者尝试“思想咨商”,对道德抉择予以解构重构:从受教育者的“思想问题”出发,实现思想政治课复归“思想”的德育关怀“格式塔转换”——沿循“基于思想咨商的倾听审度以思想寻‘症’”“基于思想咨商的意义解构以思想分析”“基于思想咨商的价值重构以思想调适”。(叁)人的本质在于游戏,教学的本质亦在于游戏。基于此,沦为“苦役”的思想政治课,应找寻藏匿于教学“背后的某物”,实现其游戏旨归的还原,创生思想政治课悦趣化德育范式。笔者尝试“悦趣化德育”,“用形”游戏以道德抉择:设计“鲧计划”的教学游戏,以“游戏—教学”的方式推进教学——扮演游戏角色,规划任务路径:促成认知转化;“挑战—技能”匹配,快意血酬激励:获致沉浸体验;试误探索结果,增益核心能力:促进学习迁移。(四)传统德育往往剥离“道德情感”、失却“道德思维”。旨在“复归生活本态,具象道德界说”、“补位决策语境,纾解道德冷漠”,笔者尝试“道德想象”,促发道德抉择的可能指涉:转换道德教育的视界,培植道德主体更为周详地道德思忖与充满活力的判断抉择——依托道德“叙事”提升学生的道德敏感,活跃其“共情能力”,假以角色“排演”触发学生的道德省察,激活其“理智自觉”。(五)道德选择判断,就其本原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负荷情绪的情感直觉“无意识”过程,其具有助力价值范型体系的自明与道德理性“良知”的意会、促成道德主体价值评估判断的自选与行为选择“良能”的积淀等价值意蕴。基于道德直觉“隐逻辑”思维决断的进路,笔者尝试以“道德直觉”,促成学生“无意识”的道德“隐逻辑”抉择——“基于建构‘道德图式’以厚积基于意象观照的直觉敏感”、“基于决断‘隐逻辑’以促发直觉抉择的‘无意识’驱动”。(六)尽管个体所为并无违背社会公德或并未实际实施伤害他人之举,但如若其认为自身行为“有错”或间接导致他人遭遇不幸,则会产生虚拟内疚。笔者尝试以“虚拟内疚”,聚焦“崇高”促成学生道德抉择:既往体验诱发悲情换位,促成“情绪充予”的道德审视;悲情换位趋使自我归因,趋于道德自我的“理想”抉择;自我归因催生虚拟内疚,获致道德情感的“应然”内化,从而跃升受教育者的道德责任与由心之境,化“实然之我”为“应然之我”。(七)关怀,即投注接纳、动机迁置的关怀者与接纳、确认、回馈的被关怀者之间的一种联系与相遇。笔者试图以“关怀德育”,返璞道德抉择伦理本真:通过澄清关怀德性的“关系场”促进德育生态通体化,归因关怀动机的“情感场”致力教学伦理情愫化,以大德育的视角破题“重认知灌输,轻情意渗透”的传统德育范式。
刘鑫[5]2010年在《大学生虚拟内疚问卷的编制及应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虚拟内疚,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夫曼提出的基于移情的内疚理论中的一个概念。它是指在日常生活中,尽管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情,或者所作所为并没有违犯公认的社会道德规范。但如果个体认为自己做了错事,或者与他人所受到的伤害有间接的关系时感到的内疚。虚拟内疚包括:关系内疚、责任内疚、发展的内疚、幸存者内疚等不同的类型。为了了解我国大学生的虚拟内疚发展状况,丰富虚拟内疚理论的实证研究,本研究在综合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调查和访谈等方法,编制了具有良好信、效度的大学生虚拟内疚问卷。同时考察了我国大学生虚拟内疚的群体特征,探讨了大学生移情水平和虚拟内疚的关系,以为大学生道德教育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的结果表明:(1)编制的大学生虚拟内疚问卷共由23个条目组成,包括发展内疚、责任内疚、关系内疚叁个维度,问卷的信、效度指标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2)整体水平上,大学生的责任内疚、关系内疚得分偏高,但发展内疚略低于责任内疚和关系内疚的得分。(3)在性别变量上,女大学生在责任内疚维度得分显着高于男大学生,但发展内疚维度得分显着低于男大学生。(4)就不同专业的大学生而言,文科生在责任内疚、关系内疚和总问卷的得分上均显着高于理科的大学生。(5)是否为独生子女方面的研究显示: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发展内疚得分显着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而责任内疚维度的得分显着低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6)不同年级的大学生的虚拟内疚水平差异并不显着。(7)大学生的移情水平和发展内疚、责任内疚、关系内疚叁个维度及总问卷均有显着的相关,移情水平对虚拟内疚具有较好的预测作用。
王云强[6]2004年在《情绪体验对道德认知的影响及其德育价值研究》文中提出本文针对情绪与道德发展关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结合情绪心理学的新近研究成果,尤其是情绪对社会认知影响的有关研究,先从道德知识学习、道德判断推理、道德信念形成和道德自我意识四方面分析了情绪体验对道德认知的影响;再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了“情绪体验与道德自我觉知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进一步探明情绪体验对道德认知的影响。结果表明,情绪体验对道德自我觉知具有重要影响,行为情境、行为意图和归因倾向是道德情绪体验和道德自我觉知的重要影响因素。最后,笔者对情绪体验影响道德认知的集中体现和功能局限进行了总结,并从观念和方法两方面探讨了情绪体验影响道德认知的德育价值,尝试为学校道德教育提出建议。
朱丽娜[7]2017年在《初中生对说谎情境中内疚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文中研究指明内疚情绪作为典型的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起着调节作用,并在人际交往和社会关系的维持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近年来,在道德情绪和自我意识情绪的研究领域中,国内外的学者都很关注儿童的内疚情绪理解的发展,同时也有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本研究结合中国文化背景,分别探讨初中生对为个人、集体利益两种说谎目的中内疚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以及对学业情境和规则情境中内疚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并进一步探讨教师不同的教育方式对初中生的内疚情绪理解的影响。研究一结果表明:初中生对内疚情绪的理解在不同情境上存在显着的差异,相比较规则情境,有更多的初中生在学业情境中能理解内疚情绪。初中生对不同说谎目的情境的内疚情绪理解存在显着差异。在学业情境中,相比较为集体利益说谎,在为个人利益说谎时,有更多的初中生能够理解内疚情绪;而在规则情境中,情况相反。研究二结果表明:不同层次的内疚理解在行为结果变量上呈现出不一样的结果。在内疚第一层次理解上,单独批评和公开批评不存在显着的差异。在内疚第二、叁层次理解上,初中生对不同行为结果的内疚情绪理解存在显着的差异。相比较受到单独批评,初中生对受到公开批评,更能够理解内疚情绪。初中生对受到公开批评的内疚情绪的理解能力显着高于无批评的内疚情绪的理解能力,并且初中生对受到单独批评的内疚情绪的理解能力显着高于无批评的理解能力。
王亚芹[8]2017年在《情绪对网络利他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互网络的悄然兴起和逐步普及,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大众化,网络已然成为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并且有愈来愈依赖网络的趋势。如今,网络行为中负面的影响已经备受研究者的关注。近年来,网络的积极影响才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力,例如网络利他行为。网络利他行为是指个体在网络环境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有益而不求回报的行为。通过对网络利他行为的探讨研究,一方面可以丰富网络社会心理的研究内容,另一方面还可以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为构建文明和谐的网络环境贡献心理学的巨大力量。在查阅、梳理和分析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采用问卷调查和实验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研究集中探讨了情绪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鉴于以往研究者很少关注情绪和网络利他情境因素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着重从情绪与网络利他行为的关系切入展开研究,集中探讨了不同情绪类型和网络利他情境难度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之后,进一步探索了内疚这种消极情绪对网络利他行为的影响。实验1主要采用视频诱发被试情绪的研究范式,在被试体验到积极(快乐)、中性和消极(愤怒)情绪之后,通过手机在论坛上浏览他人的求助问题,然后自由选择回帖,以此作为被试网络利他行为的衡量标准。实验准备阶段,使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筛选出网络利他行为水平在平均数以上的59名被试,随机分配到叁组实验处理中。实验中采用的视频材料、网络利他情境都预先进行了有效性验证。实验2采用故事情境诱发被试情绪的研究范式诱发被试的内疚情绪,内疚组被试在阅读完内疚故事情境后,通过手机在论坛上浏览他人的求助问题,然后自由选择回帖,以此作为被试网络利他行为的衡量标准。而控制组被试只需通过手机在论坛上浏览他人的求助问题,然后自由选择回帖即可。在实验准备阶段,使用大学生网络利他行为量表筛选出网络利他行为水平在平均数以上的40名被试,随机分配到两组实验处理中。实验中采用的内疚故事情境、网络利他情境都预先进行了有效性验证。本研究实验结论如下:(1)网络利他行为在不同难度的网络利他情境上(高和低)存在显着的差异。相对于高难度的网络利他情境,被试在低难度的网络利他情境下表现出更多的网络利他行为。(2)网络利他行为在不同情绪类型上(积极、中性和消极)差异显着。相对于中性情绪和消极情绪,积极情绪会增加被试的网络利他行为;相对于积极情绪和中性情绪,消极情绪下被试的网络利他行为明显地减少了,即积极情绪能促使网络利他行为的发生,而消极情绪减少了网络利他行为的产生。(3)不同情绪类型和不同难度的网络利他情境会交互对网络利他行为产生影响。(4)相比控制组,内疚组被试的网络利他行为明显较多。(5)不同难度的网络利他情境和内疚感不存在对网络利他行为的交互作用。
宋姗姗[9]2009年在《关于在小学中实施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行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主要针对小学道德教育中“重说教、轻行动”、“重结果、轻过程”的现状,依据小学6-12岁儿童的品德发展现状与身心发展规律,提出以体验的方式与理念形成一种可操作性强的道德教育模式,主要目的是启动受教育者的情感系统,激发深层内核的情感体验,保障道德认知到道德行为通路的顺畅,培养和造就品德高尚、身心健康、行为端正的“人”,以期提高道德教育的实效性。本研究围绕叁个方面展开:一是厘定体验的内涵、体验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性以及道德体验的动态生成机理;二是建构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理论模型;叁是在实践层面验证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可行性与实效性。关于体验的涵义,笔者认为体验是一种动态情境生成的思维活动,强调身心上的“动”加上思维上的“动”,又根据情境,结合已有阅历进行自组织转换的动静结合、动态生成的方式。体验具有主体性、动态生成性、缄默性等特点。此外,在明晰体验内涵的基础上以教育学、心理学的视角强调了体验在儿童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并结合个体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从静态结构和动力系统两方面,重点阐述了体验在道德教育中的动态生成。第二部分是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建构。首先明确什么是模式,其次阐述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内涵,最后探讨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运行机制。此部分把研究重点放在体验活动过程展开的机理描述上,运用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移情理论,从深入体验情境、激发深层体验、体验的回馈、体验的引导与升华四个方面着手,探究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运行机制,形成可操作性强的理论模型。第叁部分是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践行。从小学道德教育的现状分析入手,围绕“尊重”、“责任”、“珍惜”几个主题,依据所建构的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展开具体的践行活动,运用行动研究中“计划——行动——观察——反思”的操作方法,在注入体验因素的前后,对学生显现出的道德行为进行对比观察,验证所注入的体验因素是否能有效的规范和改善学生的道德行为。在体验之后进行总体的实效性分析,以此确定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可行性、可操作性与不足,在反思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为其在教育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提供实证支持!
张捷[10]2006年在《责任性内疚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责任性内疚”是近四十年来受到西方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业已引起我国学者的研究兴趣。本研究在对国内外有关责任性内疚的理论、研究现状进行归纳整理的基础上,采用了开放式调查法、情境故事投射法、方差分析、偏相关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对责任性内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初步研究。通过研究证实了提出的关于责任性内疚产生及强度的影响因素和责任性内疚后继补偿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的假设,获得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是否直接接触造成他人伤害因素是责任性内疚产生及其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个体直接接触造成他人伤害比个体非直接接触造成他人伤害,所体验到的责任性内疚强度要高。第二,结果严重性因素是责任性内疚产生及其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结果越严重,个体体验到的责任性内疚强度越强。第叁,移情水平因素是责任性内疚产生及其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移情水平越高的个体体验到的责任性内疚强度越强。第四,自我责任归因是责任性内疚产生及其强度的主导归因方式。随着责任性内疚易感程度的降低,归因呈现多元化,责任归因逐步由指向自身转为指向外界。且自我责任归因受到是否直接接触、结果严重性以及移情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责任性内疚强度与自我责任性归因方式、行为可控归因方式正相关。第五,是否直接接触、结果严重性以及移情水平因素影响个体责任性内疚的后继补偿行为。责任性内疚强度与各补偿行为正相关。
参考文献:
[1]. 虚拟内疚的机制及其德育价值研究[D]. 王蓓. 南京师范大学. 2003
[2]. 不同虚拟内疚类型下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选择研究[D]. 刘金梅. 西北师范大学. 2009
[3]. 虚拟内疚理论视阈下思想政治课德育路径述略——以“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教学为例[J]. 孙杰. 中小学德育. 2014
[4]. 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学生道德抉择能力培养策略研究[D]. 孙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6
[5]. 大学生虚拟内疚问卷的编制及应用研究[D]. 刘鑫. 河北师范大学. 2010
[6]. 情绪体验对道德认知的影响及其德育价值研究[D]. 王云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7]. 初中生对说谎情境中内疚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D]. 朱丽娜. 杭州师范大学. 2017
[8]. 情绪对网络利他行为影响的实验研究[D]. 王亚芹. 赣南师范大学. 2017
[9]. 关于在小学中实施体验式道德教育模式的行动研究[D]. 宋姗姗. 辽宁师范大学. 2009
[10]. 责任性内疚的影响因素研究[D]. 张捷. 河南大学. 2006
标签:心理学论文; 道德教育论文; 情绪理论论文; 虚拟网络论文; 情绪和情感论文; 政治论文; 心理学论文; 思想政治课论文; 大学生现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