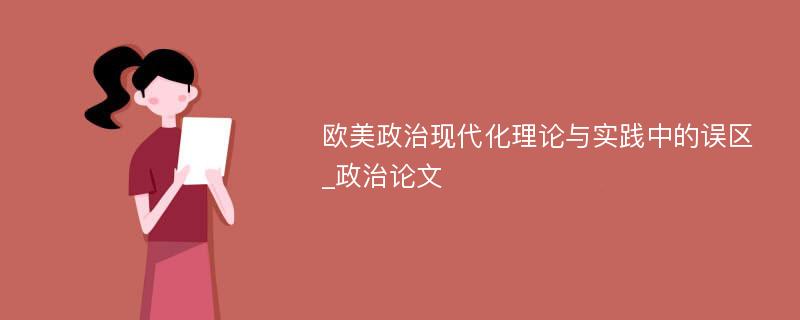
欧美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实践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6~0081~15 一、政党的“现代性”问题 18~19世纪现代化早期是欧美社会面临专制主义日渐衰落、政党政治日渐兴起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随着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与1783年美国独立,党派活动日益呈现出组织化、正规化的趋势,议会政治作为人类政治发展史上全新的一种权力运行形态也已日渐稳定。至19世纪中期,宪政体制下的政党政治与议会政治早已成为英美政体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的主要特征。①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政党议会政治已经稳定地运行了一百余年,以启蒙主义思想家为代表的欧美思想界,却仍然对党派活动厌恶、恐惧、排斥至极,对于打破专制主义统治之后政党政治的兴起,无论在心理上还是理论上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没有能够认识到传统社会中的“宗派”与现代“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更没有预见到政党政治在日后的大规模兴起。连当时欧洲最具政治眼光的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在深入全面地考察了美国的民主之后,也毫不迟疑地认为“党派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②正如施莱辛格总结的那样:“在政党开始形成时期,它每向前发展一步都遭到非议,被认为是个祸害。”③ 对于传统“宗派”与现代“政党”之间的本质区别何在、政党的现代性基础是什么、如何限制党派活动的自利与危害性等等一系列问题的模糊认识,自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中间同样也普遍存在。这些近代中国社会中的“先知先觉者”们一方面对于西方国家“政教之有序,富强之有本”“艳羡之极”④,另一方面却又对其政党权力之争大加挞伐,认为“此间国事分党甚于中国”,“其负气求胜,挚权比势,殆视中国尤甚矣”⑤,显然将英美的政党权力之争与中国的朋党之争相提并论,发出“倘能无党争,尚想太平世”的感慨,并由此得出结论“共和政体万不能施行于今日之吾国”。⑥即使是反清派、革命派阵营的知识分子,辛亥革命前后对政党政治的态度,简直判若两人。以“民主革命伟大先驱者”孙中山为例,辛亥之前对政党政治崇尚得无以复加,认为“政党政治,虽为政治之极则,而在国民主权之国,则未有不赖之为惟一之常轨者”⑦,认为“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⑧但辛亥之后稍遇民国政治的现实,其热情很快烟消云散,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在《总章》中公开宣示:“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⑨,迅速完成从“政党政治”理想到“一党建国”“一党治国”“以党治国”“将党放在国上”的蜕变。⑩ 在面对各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候,近代东西方知识分子对于政党的现代性基础是什么、政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何在、实施政党议会政治如何才能兴利除弊这类事关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严重缺乏认识,他们在党派组织与活动之性质与作用等问题上呈现出共同的思想特征,其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无论是孟德斯鸠、卢梭、托克维尔这些近代民主思想的引路人,还是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这些近代民主工程的奠基人,都未能预料到早期政党在日后的社会政治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不用说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政党理论指导政党政治的实践发展,促进宪政制度的运行。而在近代中国,孙中山的思想转变固有其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因素,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蒋氏政权顺手接过孙中山这套“党国”理论,完成中国国民党从一个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政党,蜕变成为一个专制独裁、阻碍民主进步的极权主义政党。 19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证明,没有政党议会制就不会有现代民主。如果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传统政治文化、政治经济环境等等主客观原因所限,对于政党政治对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性、对政党的现代性本质缺乏认知情有可原的话,自由民主发源地的欧美知识分子何以在政党已经在立宪体制下运行了150多年之后却仍然发出“党派是自由政府的灾祸”的感慨?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近代东西方先进知识分子对于政党现代性认知的共同误区?政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究竟何在? 二、党派纷争与启蒙思想家的政党观念 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随着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渐稳定,早期的英国政党日渐向组织化方向发展,国王与议会之间、议会各党派之间、国家与社会之间、社会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斗争与合作,交织成为这一时期英国政坛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英国以及欧洲开始了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度的民主转型过程,这一转型在中世纪以来的英国与欧洲历史上,同样也是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整个欧洲包括北美的思想界都在密切注视着这一变局,绝大多数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在呼吁自由民主的同时,对于处身民主与专制交战中心的党派活动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对于打破专制主义之后政党政治究竟是福还是祸,却与保王党人采取了完全一致的立场。这一时期欧洲与北美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包括伏尔泰、霍布斯、休谟、孟德斯鸠、马基雅维利、博林布鲁克、华盛顿、麦迪逊、杰斐逊等一大批当时世界级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始终对党派活动的自利性与危害性耿耿于怀,对于党派活动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党派活动如何才能促进而非阻碍宪政制度的建设,始终缺乏清楚的认识。整个18至19世纪,欧美即使是最进步思想家对于政党的主流观念,不仅与两千年前亚里士多德的认识一样,而且与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文化的观念毫无二致,都是对于人们“结党营私”败坏国家政治生活与公共利益的厌恶、恐惧与排斥。 最早就党派问题提出系统研究的英国学者博林布鲁克认定:“党派的统治……肯定总会以宗派的政府而结束……党派是政治罪恶,而宗派则是所有党派中最坏的一个。”(11)最早提出人民主权学说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主张:“国家之内不能有派系存在,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12)休谟在论及党派时,认定它们“颠覆政府,使法律失效,并在同一国家的人们中间造成最强烈的敌意”。(13)对党派活动的怀疑恐惧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达到高潮。尽管其时法国政坛上党派林立,党外有党、派中有派,君主政体派、布里索派、斐扬派、吉伦特派以及雅各宾派相互之间,矛盾重重,激烈争斗,但所有的政治领袖都坚决宣称自己及自己所在的团体组织是“爱国者”,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人充当“党派领袖”,并以此作为砍掉对手头颅的理由。孔多塞宣称“法兰西共和国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不要任何党派”;罗伯斯庇尔认为“凡是在我可以发现野心、阴谋、欺骗以及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地方,都可以找到宗派,而且所有宗派的本性就是牺牲共同的利益”;圣·茹斯特的言辞更为激烈:“任何党派都是犯罪……每一个宗派也同样是罪犯,所有的宗派都企图破坏人民主权。”(14) 如果说欧洲激烈的阶级对抗与法国大革命期间残酷的内外政治环境使得这些激烈的言行情有可原的话,阶级冲突并不激烈且处身和平政治环境的美国却也孕育出同样的对于“党派”的厌恶和恐惧。美国立国之父华盛顿认为:“党派性总是涣散人民的议会,削弱政府的行政机构。它以毫无理由的妒忌和虚假的警报使社会动荡不安,它点燃一方的仇恨之火反对另一方,甚至煽动骚乱和暴动”(15),大声疾呼:“假如我们要维护用血与泪换来的自由和独立,那么就必须抛弃并驱赶政党精神这个恶魔”并且一再“以最严肃的态度提出警告,绝不要受党派性的有害影响”。(16)麦迪逊认为“党争……把人们分为各种党派,煽动他们彼此仇恨,使他们更有意于触怒和压迫对方,而无意为公益而合作”。(17) 尽管在理智上清醒地意识到党派竞争的危害性,并且在口头上对党派活动大加挞伐,但是,一旦涉入实际政治,这些深具宪政民主精神素养的“近代民主工程的奠基人”,最后都身不由己卷入党派恶性纷争。美国独立后第二年,以杰弗逊、麦迪逊为一方,以汉弥尔顿、亚当斯为另一方的建国元勋们就开始“拉帮结派”,双方围绕各种政策、政治问题,各自组党,借助报纸、国会、选举动员、演说甚至往来书信相互攻击,不惜使用最恶毒的语言相互谩骂,双方“不管所讨论的是外交还是内政,是战争还是和平,是航运还是商业,对立观点……像南北极一样彼此分歧”。(18)无论时任总统的华盛顿如何“诚挚地祝愿和热切地希望,各方面都抛弃伤人的猜疑和刺激性的指责,而代之以胸怀宽大的容让、互相克制和妥协”都毫无效果,(19)以至慨叹“党派争执竟达到此等程度,真理受到如此的蒙蔽与歪曲,究竟通过何种途径方能明辨是非,实属难以捉摸”。(20)党争的火焰最后烧到一向以毫无党派、绝对中立自许的华盛顿自己身上。由于他在英法战争中采取中立政策,被共和党人阵营攻击为“一个全国的公敌,一个受其他国家势力影响的人”。(21)在华盛顿看来,污蔑他的人“使用了对暴君尼禄、对劣迹昭彰的盗用公款犯、甚至对普通扒手都很难使用的言过其实的下流的语言,来片面地、阴险地颠倒黑白”。(22)这些攻击谩骂最终迫使这个渴望保持超然政治中立的人也不得不在激烈的“路线斗争”中“选边站”,公开宣布“我应该站在联邦党人极力支持的一方”。 三、解释政党的现代性:启蒙思想家的研究误区 反对专制主义的压迫,宣扬宪政民主的理念,是启蒙主义思想家与实践者们共同的政治立场,但对于民主革命成功之后“自己人内部”也爆发如此激烈的党争,绝大多数启蒙主义者显然是始料未及。面对专制被推翻之后,当人们获得了集会结社的自由之后所必然出现的党派竞争公开化甚至白热化的局面,启蒙思想家们措手不及、束手无策,他们并未深入思考防范因应之道,而是匆忙得出“党派是祸害”必须予以禁止的结论,由此暴露出的,是他们对于政党政治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关系、政党的现代性基础,缺乏深度的认识。造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时欧美主流政党研究理论对于决定政党行为的关键变量的集体误判,这一误判典型地体现在他们对党派的分类研究上。这种政党分类理论根据政党的意识形态属性(保守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政策立场(在税收、财政、国防、对外政策、宫廷开支等问题上的具体主张)、成员构成(来自王室贵族还是来自社会精英)、领导人的品德、规模大小、历史长短等等标准划分政党,并试图在此基础上解释党派活动的行为、判断评价其对社会的影响,并预测其未来发展走向。 最早对党派活动进行系统分类研究的休谟,根据“利益、原则与情感”三条标准对党派进行区分,认为源自利益的党派古已有之,是“最具有理性……最可理解”的,源自情感的党派围绕特定家族或个人的纽带结成,尽管“通常非常暴力,并且……无法理喻”,但如果能有“慷慨大方的精神”却可以造就单枪匹马难以收获的好处。源自传统和原则(尤其是宗教原则)的党派则是现代的产物,是“最不寻常、最无法解释的现象”,这样的党派“造就迫害心态,从来就是人类社会的毒药,是每一个政府中党派的最根深蒂固的来源”。与源自利益的党派相比,它们“在受其蛊惑的追随者中间散播相互仇恨与厌恶”,因此“更加激情……更加狂暴和更加使人愤怒”。(23)与休谟一样,博林布鲁克的政党理论,也是建立在“政党的本性”或行为特征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政党区别于宗派在于“宗派产生于相互嫉妒和恐惧”,而政党则是意见、原则和公共利益的一致基础上的正派人士的“联合”。(24)此时欧洲思想界最杰出的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他对于党派的认识典型地反映了启蒙主义思想家们在政党问题上所共同具有的思维模式。在他看来存在两种政党,一种是“被称为大党的政党,是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一般来说,同其他政党相比,它们的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爽快和勇敢……小党与此相反,他们一般没有政治信念……没有崇高的目标,所以性格打上自私自利的烙印……大党激荡社会,小党骚扰社会;前者使社会分裂,后者使社会败坏”。(25) 休谟、博林布鲁克与托克维尔对政党的认知,代表了启蒙思想家的基本政党观念,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政党行为的分析,都着眼于党派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上,都着眼于政党追求的利益是否正当、所持有的政策主张是否恰当、党派的原则或意识形态立场是否合理、它们进行组织化动员的规模大小如何、其领导人个性与品德魅力如何、其成员的构成或社会基础等等这类因素,所有这些都属于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性特征,都只是政党为了谋求自身生存发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可以随时调整、变更的策略性行为,都不是决定政党行为的关键。传统社会中的党派与现代社会中的政党一样,都是人们聚集在一起协调彼此行动的政治组织,都具有追求其自身利益的天性,都必然从事程度、范围不等的组织化动员以实现权利与权力的最大化,也都同时具有作恶与为善的潜能。党派自身的组织-结构上的形态特征或许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影响其善恶与兴衰,但长期来看,它们都是政党组织根据其对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为了获取、巩固其权力地位可以随时作出的内部自我调整,不是也不可能是足以约束或解释政党行为的关键因素。东西方政党史上大量事例表明:今天宣称代表社会先进力量的政党,明天可能沦为落后势力的堡垒;掌权之前品德高尚、矢志奉献的伟大领袖,掌权之后就可能成为唯我独尊、滥杀无辜的独夫民贼;进入议会之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进入议会之后就可能成为“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政党(26);在某一时期、某一政策领域推动社会进步的政党,在另一时期、另一政策领域就可能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党派组织-结构上的自我调整以及由此而来的行为特征上的巨大变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任何政党组织存在的首要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权利与权力的最大化(27),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任何政党都必须随时根据内外因素的变化进行组织-结构上的相应调整,也只有当党内外、国内外各种环境因素汇集在一起足以影响到政党自身权利与权力最大化这一终极目标的时候,政党才有动力进行组织-结构与行为上的调整。(28)政党行为的根源,不在其组织-结构形态本身,而在其获取权力与行使权力的途径与方式上,要影响党派成员的行为,就必须影响其获取权力与行使权力的途径与方式。政党组织-结构上的任何重大调整,归根到底,是制约党派成员获取权力与行使权力的外部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致使其可以或不得不在组织-结构上采取相应的策略性调整。政党组织内部与外部对于党派成员获取权力与行使权力的既定的约束条件与约束程度的变化,才是决定政党如何设定其政纲、政策、意识形态立场、领导层配置与成员招募等等组织行为的关键变量;所有党内外、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变化,只有在足以影响到党派成员获取权力与行使权力的途径与方式、并因此危及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才会促使其进行组织-结构与行为上的调整。正如20世纪的政党理论家认识到的那样:“政党成员不是利他主义者,政党的存在根本不会消除自私和难填的欲壑。政治家们渴望权力的动力是一直不变的,可变的只是动力实现的过程和对这种动力所做的制约。”(29) 因此,启蒙主义者将传统“党派”与现代“政党”的区分标准建立在诸如:究竟是追求党派利益还是追求公共利益、是受到激情或野心的激励还是受到理性与理想的激励、是起到促进社会团结的作用还是起到导致社会分裂的作用、是代表社会进步力量还是代表社会保守力量等等标准之上,这种组织-结构层面上的分类方法,既不可能对传统的党派与现代的党派予以区别,也不可能对现实中的各个党派进行有意义的区隔。马克思、恩格斯对那个时代资产阶级政党的批判,称其为没有本质区别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可谓一针见血。在资产阶级控制了政党获取权力的途径与行使权力的方式的时代,也就是在资产阶级可以肆无忌惮利用金钱与暴力绑架选举的时代,所有政党确实都只能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一丘之貉。启蒙思想家借助组织-结构层面的分类标准对党派组织进行道德的归类与评判,根本不可能起到规范党派活动、使党派活动发挥促进社会和谐而不是制造政治动乱的功能。冀望以这种方式“整理党务”,不可避免地会招来“党同伐异”的指责。按照这套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确立的道德性、规范性的党派研究“范式”语言,根本无从归制党派行为。因为在一方看来是受激情野心蒙蔽、破坏社会团结、代表社会保守力量的党派活动,另一方看来完全可以是受公益、理想激励而凝聚进步力量的正义之举;一方看来利国利民之善举,另一方眼中或许就是祸国殃民之苛政。这种看待党派活动的视角,与当时所有欧洲王室对于政党的认知模式完全相同。英王乔治三世就标榜自己的宫廷党是真正的守护国家利益的“爱国者”,除此之外的“一切政治团体本质上都是搞宗派活动的,因此必须予以消除和摧毁”。(30)而乔治三世所代表的保王党人的爱国宣言,并非完全虚妄:没有14~17世纪期间历代英国国王近三百年的努力,英国不可能建立起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在一个社会生活的治理被领主、教会、骑士团、贵族领地、城堡、自治市等各种政治力量分割得七零八落的“破碎的世界”里,托利党、辉格党、乡村党这些形形色色的政党甚至不可能找到自己栖身的政治舞台。(31) 党中有党派中有派,党派之间存在政治分歧是任何政治共同体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不同政党组织-结构上的不同形态与不同的行为特征,说到底是不同社会集团争夺社会生存与发展空间、争夺权力资源的产物。要想打破专制、建立和谐社会,首先就必须承认利益分歧与利益冲突的现实,承认各方对于社会公共资源,尤其是权力资源,有其正当权利,而一旦承认这一权利,就意味着垄断权力的专制政权的瓦解,必然会迎来权力竞争的公开化甚至白热化局面,极可能导致社会政治动荡,而加剧的社会政治动荡反过来必将推动强人政治的到来,将社会拉回到专制主义的泥潭,整个社会都将为这一失败的转型付出高昂代价。 既不能回归专制主义的老路,又要避免专制主义退却过程中的党派竞争的公开化、白热化引发社会政治动荡,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关键,在于为党派权力竞争设置强大明确的制度化约束。启蒙思想家未能看清这一关键,错误地从党派自身的组织-结构特征角度分析、研究、评判政党,寄希望于以此区分“好党”与“坏党”以规制约束政党行为,这正是启蒙思想家们对专制主义退潮进程中党派竞争公开化、白热化束手无策的根源,也是其希望破灭后抵制政党政治、未能预见到近代以来政党政治“全球化”的最主要原因。这也表明绝大多数的启蒙思想家并未找到如何推动传统“宗派政治”向现代“政党政治”转型的政党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要推进政治现代化、推进政党的现代化转型,必须解决民主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从理论上回答启蒙主义思想家们未能回答的两个关键问题:政党议会政治何以是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必由之路?如何才能规制党派行为、避免党派恶性竞争、迫使其成为“国家与社会间桥梁”? 四、集体行动的双重困境:现代化早期英美宪政体制下公权力资源的滥用 当代政治理论家都熟知集体行动面临两大困境:“搭便车”心态与“公用地的悲剧”(32),两者都来源于人们趋利避害的天性,前者导致人们对于需要付出成本与代价的公益性的集体行动的排斥,以至社会的邪恶难以祛除、社会的进步难以实现;后者导致人们过度使用公共资源,以至社会的进步陷入不可持续的发展困境。要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既要解决专制主义退潮过程中政治动员的组织化问题,也要解决其制度化问题,前者意味着要克服“搭便车”心态造成的“集体行动瘫痪”的困境,后者意味着要克服“公用地的悲剧”造成的“集体行动过度”的困境。(33)为此,就必须将组织与制度作为具有密切关系、但又各自独立的两个分析变量。(34)组织就是对“偏好”(利益)的动员,就是具有共同利益的成员的集合,组织的作用就在于凝聚利益、克服“信息不对称”“监督成本”造成的“搭便车”以及由此而来的行动瘫痪问题;制度就是对行为的规范与规制,制度的作用就在于建立监督与奖罚机制、克服自利过度造成的“行动过度”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源滥用”问题。组织与制度的区别只是学理上、分析范畴上的区分,在实践中两者是紧密结合的。离开了组织,集体行动无法出现,专制主义的旧体制也就无从打破;而离开了制度,任何政党组织天生具有的权力最大化冲动行为也就无从规范、无法规制,人性中自利的本能最终将使得公共权力资源被滥用或过度占用至枯竭,组织也将最终灭亡,政治现代化也必然中断。任何国家的政治现代化都需要借助于促成集体行动的“组织”才能够实现;而每一个组织也都需要克服过度自利,并且建立起能够制约权力资源滥用的“制度”,才有可能实现可持续政治现代化。 启蒙主义思想家完全正确地认识到,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党派割据与党派恶斗对于社会与国家整体利益无疑具有莫大的危害,但是,他们的政党研究视野限制了他们对于如何制约党派自利危害性的制度的思考与探索。绝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们都没有认识到,在专制主义被打破之后,政党组织的兴起是必然的,因为作为一种组织,政党解决了集体行动中“搭便车”心态造成的“行动不能”的困境。(35)如果没有这些“拉帮结派”的党派组织对权力资源进行再分配,怎会有人愿意投身到这些吃力不讨好的党派活动之中?而没有日益发展壮大的党派政治,专制主义的枷锁怎可能被一点点地削弱?没有专制主义的日渐衰落,党派政治又岂能在专制主义的平台上实现政党的现代化转型?相比于专制主义衰落后的其他出路,包括法西斯军国主义接管国家(希特勒的德国与明治之后的日本)、军阀混战或专制主义的回潮(辛亥后中国),一个不完善的政党政治毕竟危害较轻,更何况其后果并非无法控制。因此,党派政治的兴起有助于克服“搭便车”现象造成的“集体行动不能”的问题,没有政党议会政治的存在,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道路将只能是疾风暴雨式的暴力运动,国家的民主化转型将为此承受更为惨痛的代价。 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党派割据与党派恶斗对于社会与国家整体利益无疑具有莫大的危害,但是,启蒙主义思想家没有意识到的是:组织化恶性竞争的根源,不在于政党政治本身,而在于党派对议会这一公共权力资源的无序竞争,归根到底,在于现代化早期英美国家的宪政体制之中,完全缺乏一个可以规范、规制和监督政党“过度自利”行为的强有力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作为政党政治的配套工程。18~19世纪的英美,就其宪政体制而言,英美其时的议会已经为政党活动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平台,使得政党能够借助这个平台稳定地发挥监督、制约专制王权滥用权力、中饱私利的职能。相对于19世纪“专制的洪流”,这样一种以权力制衡为基本特征的议会制度,削弱了国王或总统手中行政权力的专制性,但却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的权威性与渗透性,这样一种政体相对于专制主义政体具有无可置疑的、制度上的比较优势。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启蒙主义思想家就已经发现国家公权力在当时的英国和美国,其管辖治理社会的范围庞大且深入有效,英美国家公权力的渗透程度、其社会动员能力与整合能力远远超过了当时以法国为代表的实行专制主义制度的所有其他国家。当代学者对于国家能力的比较研究也已经证实,议会式宪政制度的兴起,对于英国国家财政的汲取能力(36)、战争动员能力(37)、减低社会动乱的频度与规模(38),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英国以相当于法国五分之一的人口与国土面积,却能率先实现工业化,投入一场又一场的与欧洲列强争霸世界的军事冲突,建立第一个“日不落帝国”,这不能不证明英国其时的政党议会体制在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方面具有强大的实际效能,这种组织的示范效应以及由此造成的地缘竞争压力,也是所有欧洲国家最后不得不纷纷向宪政民主体制转型的关键原因。 但是,政党与议会的兴起,并非宪政工程的完结,面对专制主义衰落过程中日渐开放的权力资源,政党与议会面对的最大挑战与危机就是由于选举制度、政党制度的缺失所造成的“权力资源恶性竞争”问题。“党派割据”与“党派恶斗”是造成良性的现代政党政治不能形成、宗派政治始终无法走向现代政党政治的两个最大的阻碍,而这两大关键阻碍,都是因缺乏约束政党行为的选举制度条件下,党派竞相滥用开放的权力资源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启蒙思想家们没有意识到,政党与议会的兴起是政治现代化启动的关键标志,但政党与议会说到底是两个政治组织机构,本身并不保证政党政治的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并不是简单地依靠议会中的政党成员们的“坐而论道”就能实现的,在缺乏足以约束党派权力竞逐行为的制度条件下,议员们的“坐而论道”只能是要么“坐地分赃”、要么“弱肉强食”。寄望于政党自身组织-结构的调整,根本不可能改变政党的行为。只有针对党派的权力竞争设置强大的外部约束,才可能从根本上制约其行为,推动宗派政治向现代政党政治的转型。 宪政制度区别于专制主义政体的根本标志,在于国家公权力资源是根据选票而非武力决定的。一般而言,在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只要选民的选举投票不受暴力与金钱的干扰和挟持,追逐选票最大化以便在政党竞争中胜出这一政党生存动机,必然迫使党派间的竞争趋向竞相“讨好”占多数人口的中间选民,最终导致“中间偏左”与“中间偏右”型两党政治成为政治生活的常态。(39)在这一政党格局的约束下,“党派割据”与“党派恶斗”的状况通常短暂,难以持久,因为代表极端主义势力与思潮的小党派组织难以获得足够选票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主宰国家的大政方针,最多也就是在个别特殊时期、个别席位、个别政策上干扰那些代表主流民意进入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主流政党的施政而已。(40)但是,上述稳定的政党竞争态势的出现,必须建立在能够有效地约束政党行为的选举制度基础上,而有效的选举制度必须具有两个关键原则:其一,金钱与暴力不能挟持与控制选民的投票选举;其二,选民范围必须涵盖所有成年人口。(41) 如果第一个条件未能出现,对选票的争夺必将转化为对金钱与暴力的争夺,政党将不再有动力去竞相讨好最大多数的中间选民,他们要么自己直接以金钱与暴力手段控制选票,要么利用中间集团去控制选民选票,由此形成权势集团与一小部分民众之间的裙带与庇护关系。(42)稳定的裙带庇护关系将使得控制了一部分选票的政党或政党中的某个派系,都没有动力去竞逐占主导地位的中间选民的支持,“还政于民”的宪政,必将演化成“还政于豪强”的局面,“党派割据”“党派恶斗”的局面将因此长期存在难以消除。相应地,如果第二个条件不存在,意味着社会共同体中有一部分人群被人为地排斥在政治参与过程之外,其直接后果是,要么这部分人群自己动员起来建立政党维护自身权利,要么被其他政党动员起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无论哪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样,即党派在时机条件合适时开发新的选民“根据地”争夺选票,从而引发政治动荡。要消除金钱暴力控制选票,并且保证选举资格涵盖所有成年人口,只能借助于作为议会政治配套工程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内部自身的党内选举制度的制约,而早期英美宪政体制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两个配套的制度工程,单纯的组织内部制衡,无论是议会内的权力制衡还是政党内的权力制衡,都无法保障选民的选举权利并制约金钱与暴力对选票的劫持,因此也不可能保障政治的长治久安。 早期英美以“有限民主”“议会制衡”为特征的宪政制度,缺乏强有力的、公开透明的、以保障大众自由平等的参与举权利为基础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这是导致党派割据、竞相争夺党派私利的根源,由于这一制度性缺失,早期英美宪政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精英民主”“寡头民主”。在这种“有限民主”的体制内,民众的选举权受到严格的限制。直至1832年英国才颁布第一个选举法,一直到1918年,最后一个被排除在政治参与过程之外的社会群体——妇女才被纳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此之前,表面上英国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是平民的代表,实际却远非如此。1711年《财产资格法》规定“占有年价值300英镑以上土地的人才有资格成为议员,获得代表郡的席位的最低限是600镑”(43),从而将没有土地或无钱购买土地的人排除在政治参与之外。 不仅有资格进入选举程序的选民数量极其有限,而且国家公权力对于金钱与暴力控制与挟持选民选票几乎没有任何的法律限制,1872年之前英国甚至没有建立秘密投票制度,以至“恐吓和贿赂选民非常平常”(44),竞选与当选的手段到处都是类似的,不外乎购买袖珍“口袋”选区、地方家族间的协商、或托利党与辉格党在势均力敌的选区相互妥协分肥、轮流坐庄,等等。竞选中的“拉票”成为议会选举中最热闹也最丑陋的一幕。 以“有限民主”“精英民主”“寡头民主”为特征的早期宪政体制同样也是19世纪美式民主的基本特征。早在1789年独立战争之前,英国在殖民地的所谓“市镇治理”模式就严格限制只有贵族才具有投票与当选资格。独立战争后,投票权的贵族特征开始被逐渐消除,但财产资格随之成为主要标准。独立战争后,有五个州率先开始用价值40~50镑的财产替代拥有不动产的规定。直到1817年,美国十三个州才取消了不动产或税收要求,直到1860年,所有的州才取消了财产资格的限制。(45)财产要求的废除扫除了投票权的障碍,扩大了合格选民的范围,为政党政治走向现代化提供创造了条件,但是,“随着旧的经济排斥界限的逐渐消失,其他的排斥界限得以延续,新的排斥界限又被加了进来”。(46)南北战争之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之前,南方各州甚至公然制定种种法律,剥夺黑人享有的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将其排除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没有选举权就什么权利都不会有。黑人在教育、就业、住房等等一系列权利上不可避免地遭受严重侵犯(47),为马丁·路德·金的体制外动员创造了绝佳的社会基础,引发了20世纪50~60年代持续十余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黑人民权抗争。(48) 早期美国政党名为代表民众的组织,实为小集团利益的联盟,根源在于政党内部的选举与提名机制毫无规范可言。政党内部的权力分配不是由广大党员的秘密自由投票选举决定的,而是由一小部分党鞭、党魁所垄断,权力资源的分配、公共政策的制定毫无公开性可言。这样的党派,名为政党,实与“江湖帮派”无异。美国的政党恶斗就是在缺乏大众民主的条件下日益恶化的。1800年之前,美国的总统提名制度就是由两党核心干部秘密会议(之后为政党委员会)所决定,与选民投票毫无关系,选民的投票甚至连个橡皮图章都不是,因为根本没有哪条法律规定政党内部的候选人提名必须向普通党员选民开放。1831年共和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总统提名的战场转移到全国提名大会上,但是,有资格参加选举“党代表”的选民不到总数的10%—15%,且选举程序也受到高度操控,金钱与暴力成为控制选民、剥夺其选举权利的最有效的手段。尽管20世纪初美国就已建立党内直接预选制度,但由于金钱与暴力的挟制,选民的意志根本无法对党派的行为有任何制约作用。 超越国家正式体制之外的党魁与党机器现象,说到底,是金钱暴力恣意横行的结果,是良性的权力竞争秩序无法确立的结果,它给美国的“宪政民主”带来了权力滥用的严重后果。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19世纪最后25年内……热衷于贪污腐化、营私舞弊的政客简直无法梦想还有比这更有希望的各种条件结合而成的客观环境”。(49)种植园主、工厂老板、银行家、种族主义极端集团,以及打着各种社团、协会、移民团体名义的各类组织,通过金钱与暴力控制选民的自由投票权利,党派领袖则与这些地方豪强势力集团相互勾结,前者借助于后者获取染着铜臭与鲜血的选票,后者通过前者提供的各种庇护、特权,开设妓院、赌场、从事地下非法黑市贸易等各种非法活动,或者包揽市镇工程,以劣质工程榨取国家的财政税收,并以到手的暴利建立与部分选民之间的裙带依附关系,进一步强化对选票的控制。法律与国家公权力机关对这种金钱与暴力挟持选票行为,要么毫无规定无法可依,要么毫无作为有法不依。正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制约,造成“城市的政党核心集团支配着政治,而党魁则操纵着核心集团”(50),也正是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制约,党派得以毫无顾忌地与各种社团勾结,双方利益都恶性膨胀。在这样的政党体制下,政党不可能成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桥梁”,而只能是国家与特定利益小集团之间的桥梁。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这样一种“宪政民主”底下“民主的虚伪性”有极为深刻的揭露。在这样一种所谓的“宪政民主”制度底下,指望党派代表民众利益并消除党派割据与党派恶斗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尽管选民资格的开放比欧洲国家更早,但党魁和党机器的垄断是美国立国之后一个多世纪里实行的美式民主与“政党政治”的典型特征,党魁与党机器现象是缺乏强有力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的必然后果。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金钱与暴力大量卷入选举,政党被一小撮党魁与党的组织机关所垄断,这样的政党自然不可能追逐占人口多数的中间选民的利益,而只能是黑恶势力之利益代言人,党派林立、政党恶斗的现象自然难以消除。缺乏强有力的选举制度与党内选举制度,其直接后果就是政党“以人民的名义”争相控制国家公权力,党魁则“以人民的名义”控制政党。直至20世纪后半叶,在黑人民权运动的强大压力下,美国肯尼迪与约翰逊政府时期通过了一系列以公民政治权利为核心的民权法案、政治献金法案等,才逐步消除金钱暴力绑架选票、部分选民人口被排斥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的现象(51),使得竞选活动逐步纳入法治化、制度化的轨道。 五、当代欧美政治现代化研究误区:“公共地悲剧”与苏联的崩溃 18~19世纪欧美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启蒙思想家未能准确预见到政党政治的大规模兴起、对党派权力竞争中的公开化与白热化措手不及、束手无策,20世纪的比较政治学者同样也未能预见到苏联东欧政权的集体性崩溃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兴起、对民主化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大量民主的“灰色地带”“权威主义回潮”现象同样猝不及防、束手无策。(52) 早在20世纪50年代,欧美学界就开始密切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拉大量新兴独立国家中的大规模的现代化现象。以美国比较政治学者为主体的大批年轻的研究者们并没有想明白他们自己的社会在追求现代化道路上曾经经历过怎样的艰辛坎坷及经验教训(53),却带着满脑子的“结构-功能主义”糨糊,在新兴的独立国家里到处粘贴出一幅幅“现代化”拼图(54),而现实世界似乎也不断提供满足他们学术期待的种种证据:在一个又一个散落着蛮荒的农业、落后的手工作坊、古老的图腾祭祀、远古遗留的部落酋长议事堂的传统社会中,不仅出现了机器轰鸣的现代工厂、人群喧嚣的现代城市、前所未闻的现代报纸广播,而且第一次出现了现代的政党、现代的大众参与、现代的政府机构、现代的职业军人、职业官员、教师和学生。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比较政治学者而言,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激情四射,仿佛只要把西方的这些“现代结构”搬入第三世界,功能的输出——经济的繁荣、政治的昌明、民族的凝聚——就指日可待了。整整十年之久,西方比较政治学沉浸在这种乐观主义的亢奋中。(55)但60年代的现实击碎了他们的幻觉。大批现代化中国家经济依然落后凋敝、社会依然分裂动荡、人民依旧懦弱麻木。现代化的成功者屈指可数,而失败者却遍地皆是。亨廷顿在其曾经风靡世界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详尽描绘了60年代“现代化竞技场”上哀鸿遍野的凄惨景象。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20世纪50~60年代第三世界传统社会中现代化转型的集体失败?在仔细对比了苏联、英美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道路的异同之后,亨廷顿提出了他极负盛名的研究发现:现代化失败的根源在于政治转型的失败,而政治转型失败的根源在于“很大程度上,这是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而同时政治体制的发展却又步伐缓慢所造成的”。(56)按照亨廷顿的研究,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独立的变量,对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政治现代化成功的关键,在于建立起“强有力的政党体制为吸纳新集团提供出制度化的组织与程序”。(57)在他看来,“政治发达社会与政治不发达社会的分水岭就是各自拥有的组织的数量、规模和效率”(58),亚非拉第三世界现代化失败的根源在于没有一个政党起到“疏导、解释、表达和调动公共意志的作用”。(59)这种对政党组织的强调并非只是亨廷顿一人的专利,而是70年代后期比较政治学者的集体反省。(60) 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权威主义现代化学派与19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们相比,其更加智慧之处在于,他不仅认识到政治现代化对于整个现代化的重要性,而且进一步认识到政党政治对于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意义。但遗憾的是,与启蒙主义思想家们一样,亨廷顿同样将政党现代化建立在政党自身一系列的组织-结构变量上。在“行为主义革命”的浪潮中成长起来学者们大都怀抱“价值中立”的崇高理想,亨廷顿也不例外。他不屑于像启蒙主义思想家们那样,把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政纲、政策、领导人的品格魅力等作为政党强大与否的衡量标准,但他用以衡量政党组织强大与否的标准,却依然是典型的组织-结构层面上的变量,包括:政党组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与“团结性”这四大标准。在他看来,所谓政党的适应性是“组织的寿命”与“组织领导人换代的次数”;所谓政党的复杂程度是“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所谓政党的自主性是“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独立生存的程度”;所谓政党的团结则是内部成员“对于解决彼此范围内出现的争端所遵循的程序”有“实质上一致的看法”。(61)亨廷顿所选择的组织-结构层面变量,甚至比启蒙主义思想家们还要狭隘。尽管他反复使用“政治制度化”这一概念,但他对政治制度化的定义是:“制度化就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过程”(62),由于并未对“价值观”的内涵进行界定,亨廷顿的政治制度化实质上不过是政治组织化的另一种表述而已。在他看来,缺乏权威是政治现代化失败的关键,政党则是“权威”这个产品的制造加工厂,能否制造加工出产品当然是第一位的,至于“权威”这个产品在制造加工过程中是否渗入有毒物质、如何设置产品质量管控以保障使用安全,则不在其考虑之列,如其所言:“问题不在选举,而在建立组织”。(63)只要建立起一个矢志现代化的、满足上述组织-结构建设四大标准的权威主义政党,政治现代化使命就算完成,全面的现代化也就指日可待。依据这样的标准,他对苏联与英美的政治现代化道路作出了大胆总结:“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的统治形式,而在于它们统治的有效程度……一般而言,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样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美国英国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都能安邦定国,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三个国家都具备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64)亨廷顿甚至满怀信心地预言:“有一件事情[苏联]共产党政府确实能做得到,那就是他们能统治得住,它们的确提供了有效的权威。”(65) 尽管对苏联的治理方式不乏道德批判,西方世界中几乎无人质疑其治理效能。(66)曾任卡特政府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也认为,即使在苏联爆发总危机,也即政治、社会、经济、国际对抗等等危机一起出现的情况,“苏维埃的联盟结构,各共和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仍会是巩固和紧密到足以使分离主义不会实现”。(67)然而,短短20年后,西方一流战略家们对于苏联的所有断言,包括“有效能的国家”“强大的、能适应的、有内聚力的政治体制”“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他们能统治得住”“分离主义不会实现”等等就统统成了笑话。现代性的报复来得既快速又猛烈:苏联及其一手建立的东欧政权几乎在一夕之间瓦解。苏联确实建立起了一个举世无匹的政党组织,但说好的“统治效能”哪里去了?曾经如此为人称道的“统治效能”何以会甫一接触“公开化”“民主化”的自我改革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呢?相形之下,那个每10~15年经受一次批判浪潮(68)、每4~5年因大选经受一次社会“分裂”的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历经大萧条与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其“统治形式”却依然能够安然无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 很明显,所谓“统治形式并不重要”的断言缺乏实证支持。“统治形式”重要与否取决于它如何被定义。如果像亨廷顿一样只是从政党的组织-结构层面上进行定义,这样的“统治形式”当然就不重要,因为根据这个标准衡量,苏联与英美的“统治形式”大同小异,无非就是一堆满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与团结性”这些标准的大大小小的组织机构而已,既无本质差异,何来重要意义?但是如果把“统治形式”看作是由“组织-结构形态”与“制度约束形态”这两个变量共同构成的,两者虽有内在关联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变量,那么苏联与英美之间“统治形式”的差异就极其巨大而且极为重要了。从这个角度看,组织-结构形态的现代化(现代政党组织的建立)与制度形态的现代化(规制政党获取权力的途径与方式的规范与程序的建立),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亨氏的失误在于,他把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生活的组织化现象,等同于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现象,未能清醒地认识到政治现代化不仅是治理国家的组织-结构的现代化,也必须是制度形态的现代化,对于可持续的政治现代化而言,两者缺一不可。 比较20世纪英美与苏联政党政治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一方面,政党政治是克服专制主义衰落过程中“搭便车”现象造成的“行动不能”的集体困境的必经之路,是推动宪政工程不断深入的动力所在,相对于专制主义衰落过程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回潮,政党政治无疑是一个危害相对较轻的选择。现代的政党组织,无论对于英美还是苏联的现代化都具有关键的意义。但另一方面,组织-结构的现代化并不代表政治现代化的完成。在利用政党的组织权威克服“搭便车”效应造成“行动不能”的困境之后,应立即着手建设与政党政治配套的强有力的党内外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借助于开放性的权力竞争秩序,克服党派组织的“自利过度”“行动过度”困境,防止公共权力资源被“滥采滥伐”,陷入资源滥用最终枯竭的“公共地的悲剧”。很明显,18~19世纪的启蒙主义思想家没有看清前者,20世纪亨廷顿的权威主义现代化学派则没有看清后者。以亨廷顿为代表的权威主义现代化学派正确地认识到,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急剧变革、新的社会集团被迅速动员起来卷入政治,确实需要“强有力的政党体系为吸纳新集团提供出制度化的组织与程序”以疏导、解释、表达和调动公共意志,能否建立起强大的政党组织以克服专制主义衰退进程中的权威真空,是政治现代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但是,克服了这一挑战并不等于政治现代化就已完成。当新的政党组织建立起新的权威之后,如何才能克服人性中的自利本能、防止新生的权力资源被滥用枯竭以致组织最终自取灭亡,这是政治现代化面临的第二个挑战。亨廷顿的误区在于他全然没有考虑,任何政党都有追求权力最大化的自利本能,真正的制度化就在于建立强制性的规则、程序以抑制这种“权力最大化”冲动,防止权力与权威这一社会公共资源被滥用和过度占用导致政党组织自身和整个社会的崩溃。苏联克服了第一个挑战却未能克服第二个挑战,它所缺乏的恰恰是这种抑制组织权力最大化冲动的制度化,以至最终崩溃。 纵观苏联的现代化历程可以看到,至19世纪末,沙皇政权实际上是欧洲最大、也是最顽固地抵制现代化社会政治变革的政权,其崩溃只是时间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下,国内社会政治势力蜂起,在其崩溃过程中,国内秩序一片混乱,境内先后出现了大大小小七十余个独立政权。布尔什维克凭借强大的政党组织,建立起新生的苏维埃政治共同体,有效地恢复了国内政治秩序,为现代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无可置疑,没有强大的苏联共产党,就不可能产生强大的、足以取代旧沙皇政权的组织权威,也就不可能迅速恢复国内政治秩序,建立起新生的苏维埃政治共同体;没有强大的苏联共产党所提供的强大的组织权威,要想在一个一盘散沙的落后的农业国家里实行赶超型工业化、并且最终建立起在重工业、军事与航天科技方面一度与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毫无疑问,与现实中追求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所经历的政治发展历程相比,苏联现代化的成功之处即在于借助现代庞大的政党组织,成功地填补并且重建了沙皇政权崩溃后消散的权力资源,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统一的苏维埃国家,这是其避免坠入现代化进程中的“卡夫丁峡谷”的关键。但其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失败,在于既未能从党外(自外而内)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制度程序规范以遏制苏共的权力最大化冲动,也未能在党内(自下而上)建立起一套强有力的制度程序规范以遏制党内上层权力最大化冲动,由此导致苏共及苏共高层过度占用并且滥用社会公共权力资源,正是这种滥用导致苏共组织权威的衰竭并最终引发了解体。 由于对权力资源的获取与行使的方式、途径没有任何明确的、刚性的来自组织内部与外部的控制约束,苏共权力最大化冲动一路高歌猛进、畅通无阻,最终从促进现代化的“集权体制”蜕变成为阻遏现代化的“极权体制”。从1923年起,苏共开始实行“官册制”,也即干部任命制度,所有党和政府的岗位,包括根据《党章》《宪法》规定本应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如苏维埃、共青团、工会、专业与民间的社团等,实际上统统都是由苏共党内上级组织机关决定并任命的。(69)此时苏联全部的权力资源封闭在苏共组织内部,组织内部的权力资源则逐级向上收缩,直至掌握在政治局甚至是总书记一人之手。权力资源的集中与各级领导层的更替,既不是借助自外而内的也不是借助自下而上的开放性的、制度化的公开竞争实现的,而是由上级组织机关内的几个甚至一个最核心人物,根据其巩固与扩大自身权力或利益的需要被编织起来的。(70)这样一种权力资源的配置方式与计划经济一样,都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而其为此付出的代价就是苏共的崩溃与国家的解体。尽管自列宁开始,苏共领导集团内的有识之士在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结构上作了种种调整与努力(71),但都因为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自外而内”和“自下而上”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最终不了了之。 缺乏一个建立在“自外而内”和“自下而上”的强有力的选举制度基础上的权力资源分配制度,意味着广大基层民众被排斥在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之外,它直接导致了精英流动停滞、社会分层两极化、颟颙守旧的官僚集团等等后果。(72)所有后果中与苏共崩溃与苏联解体关系最密切、也是最严重的两个后果是:其一,最高层领导人任职终身制导致最高层任何重大决策失误无法及时纠正;其二,权力垄断导致所有其他社会资源的垄断,继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垄断权力,必垄断生产,继而垄断一切。(73)计划经济就是官僚集团控制的经济,是权力滥用的终极表现。中高层干部集团特权化、帮派化,大肆占用高级汽车、别墅、出国访问名额、职称、勋章荣誉等等一切稀缺价值物(74),大肆打击政治异议分子,到处建立古拉格式的劳改营与精神病院(75),所有这一切都是权力垄断导致权力滥用的必然结果。“斯大林模式”不是时代背景问题,不是俄国历史文化问题,更不是“遇人不淑”的问题,而是政治生活的组织化未能与制度化携手并进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只要无法建立起足以遏制权力最大化冲动的强有力的制度化的规则程序,都必然导致社会公共权力资源的垄断与滥用,而权力资源的垄断与滥用,必然导致所有其他资源的垄断和滥用,因为政治就是对所有价值物的终极权威分配(76),谁控制了政治,谁就控制了一切。由于未能建立起权力与其他社会资源的开放性竞争秩序,苏式现代化所需的全部权威都来自苏共的权力与暴力,整个国家都依靠这一单一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纽带维系,对权力资源“竭泽而渔”式滥采滥伐,必然引发“公共地的悲剧”:苏共的组织权威因滥用而衰竭。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支撑苏共与苏联政治共同体的各种权力与权威资源,包括领导能力、社会控制能力、道德号召力、创新学习能力(77)等等,都已日渐衰竭。具体表现为政治信任危机、社会信仰危机(78)、官僚集团因循保守、整个社会底层(包括工人、农民、科研人员等)敷衍塞责拖延怠工、“夜间人”现象、“厨房讨论”现象(79)、地下刊物、社会不满情绪、犬儒主义、享乐主义、人际关系相互提防冷漠自私、社会酗酒成风、犹太人大规模移民等等。(80)国内外理论界所总结的苏联解体的一切具体原因,包括长期实行低效率的计划经济体制(81)、长期奉行工业经济军事化的发展战略(82)、党内形成官僚特权集团(83)、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误(84)、最高领导人及精英集团背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85)、族群联邦主义与民族分离动员的兴起等等(86),都可以归结到缺乏一个强大有效的纠错淘汰机制上,而没有强有力的党内、党外选举制度,强大有效的纠错淘汰机制从何谈起?制约权力滥用的力量从何而来?由于苏共权势集团尾大不掉,只有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没有自下而上与自外而内的权力交流与权力制衡,导致其既不能在组织内部自下而上淘汰,也无法从组织外部自外而内纠错,民众的积怨、政策的失误都无法通过选举这一制度平台、借助领导层的更换予以导引宣泄和纠正,民众与领导层之间相互的归属感、忠诚感与认同感无法产生,不得不在社会治理中不断开发并强化权力的强制性功能,最终导致权力纽带的绷断,这是苏联国家随政党最终一起解体的总根源,指望这样的政党化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爆炸”无异痴人说梦。(87)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旨在改造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极权体制以摆脱业已形成的爆炸隐患,本身并无过错。其失败的根源在于开放权力的竞争未能与建立权力竞争的秩序同步进行,这就如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未与建立市场竞争秩序同步进行一样。权力资源的每一点开放,都必须与建设一个严格规范竞争者的竞争行为的制度体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但戈氏的整个改革注重前者,忽略后者。各项重大政治改革措施,包括:“意识形态解禁”“党代表与苏维埃代表直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终止宪法第6条”(苏共领导地位)、“设置总统职位”“党政分离”“苏联总统及地方领导人公开选举”等等,都在短短2~3年期间连续密集推出,由于权力资源开放的速度与范围过快、过大,苏共的组织权威快速流失,根本来不及建立起权力竞争秩序,最终导致失速崩溃。 综上所述,从托克维尔到亨廷顿,当代政治理论家在政治现代化问题上的理论误区与启蒙时代思想家的政党研究理论误区,有着本质上的一致,两者都片面强调政党政治中的组织-结构因素的重要性,都忽视了政党政治的制度性约束条件的重要性。比较18~19世纪第一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英美与20世纪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苏联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可以清楚看到:一方面,打破专制主义的权威,必然要求开放权力资源的竞争,政党政治是专制主义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由之路,强大的政党组织是政治现代化不可缺少的环节,没有政党政治,就不会有以人民主权为基础的现代化政治权威的产生;但是,另一方面,要避免党派间权力竞争失控,就必须围绕政党获取权力的途径与行使权力的方式设置强大的外部制约,确保金钱与暴力无法绑架挟持民意,既要实现权力的开放性竞争,又要确保必不可少的竞争秩序。早期英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党派竞争恶质化以及苏共极权政体解体悲剧,究其根源,都在于两者对政党竞逐权力的行为缺乏制度性约束造成社会公权力资源的滥用。政治现代化,究其本质,是组织与制度的双重现代化,只有在组织-制度的双重现代化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党派成员与广大民众之间的稳定的、强有力的组织与制度上的联系,只有依靠这种联系,政党才有可能最终成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桥梁”、成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 注释: ①西方历史学界对于18世纪之前英国是否已经形成两党政治一直存在争议,参见程汉大:《关于18世纪英国政党结构的争论》,《世界历史》1997年第6期。当代英国历史学家布赖恩·希尔认为,光荣革命后议会地位逐渐稳定,虽然大众性政党尚未形成,但议会内政党政治已经兴起。见[英]布赖恩·希尔:《不列颠的早期政党与政治:1688~1832》,赖海榕译,荣敬本、高新军主编:《政党比较研究资料》,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②[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95页。 ③[美]小阿瑟·施莱辛格主编:《美国民主党史》,转引自王长江:《西方学者的两种政党观》,《团结》2004年第4期。 ④晚清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各国政治运作模式的观察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英轺私记》、曾纪泽《曾纪泽遗集》,相关评论见刘晓莉:《晚清驻英公使对英国政情的考察与反思》,《中州学刊》2008年第2期。 ⑤⑦《孙中山全集》第2卷,转引自徐思彦:《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文史哲》2000年第5期。 ⑥黄遵宪:《纪事》,转引自三更罗:《清朝人是怎么看美国总统选举的》,《小康》2005年第9期。 ⑧孙中山:《孙中山集外集》,转引自徐思彦:《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文史哲》2000年第5期。 ⑨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3卷,转引自徐思彦:《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文史哲》2000年第5期。 ⑩徐思彦:《试论孙中山的政党观》,《文史哲》2000年第5期。 (11)Bolingbroke,“The Idea of a Patriot King”,转引自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王明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6页。 (12)[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0页。 (13)David Humes,“Of Parties in General”,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pargener.txt. (14)[法]孔多塞、[法]圣·茹斯特、[法]罗伯斯庇尔言论皆转引自[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26页。 (15)(16)(19)(20)(21)(22)[美]华盛顿:《告别演说:致合众国人民》,《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19、319、276、303、309、309页。 (17)[美]麦迪逊:《第十篇》,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6页,。 (18)[英]英里森、康马杰、洛希滕堡:《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转引自徐希军:《华盛顿政党政治观评析》,《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有关美国立国时期的党争的描述,也可参见宋腊梅:《华盛顿的政党思想》,《江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刘祚昌:《杰弗逊麦迪逊与共和党的兴起》,《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23)David Humes,“Of Parties in General”,公法评论网,http://www.gongfa.com/pargener.txt. (24)Bolingbroke,“Bolingbroke Political Writings”,转引自李剑:《从“宗派”到“党派”:博林布鲁克与现代政党观的起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1期。 (2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196~197页。 (26)列宁对第二国际及考茨基的批判中对此有大量的分析陈述,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等,《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7)所谓无产阶级政党没有自身利益、只有全民利益的说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的莫大曲解。控制与行使政权同样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首要目的,没有政权,无产阶级政党如何为本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谋得福利?建立政党、夺取政权、以无产阶级专政维护巩固政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中最核心的内容之一。 (28)需要强调的是,某些情况下,制约政党获取权力与行使权力的外部约束条件客观上并未发生真实变化,只是被主观认定,同样可以导致组织-结构上的重大变化。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不断强化帝国主义入侵及资本主义复辟在即的危机意识,无疑推动了苏共强化无产阶级专政、强化中央集权。 (29)[美]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第52页。 (30)[英]伯克:《爱德蒙·伯克读本》,陈志瑞、石斌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31)排他性的、渗透性的、自主性的现代主权国家的建立,是欧洲及一切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基本前提,这一点已经是理论界的共识。参见[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与现代早期欧洲国家与政权建设》,郭台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5~244页。 (32)[美]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第5页;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Vol.162,No.3859,pp.1243~1248,December 13,1968. (33)[美]奥斯特罗姆就理性选择困境及其制度约束问题作了一系列研究,包括:《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余逊达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Rational Choice Theory and Institutional Analysis:toward complementarit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1991,pp.237~243;《规则、博弈与公共池塘资源》,王巧玲、任睿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 (34)将“组织”与“制度”混为一谈是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学派的主要传统之一。见[美]盖伊·彼得斯《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向民、段红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35)西格蒙·纽曼从追随者的角度,而非政党精英的角度,提供了政党政治兴起的另一个社会学解释。在他看来,快速的现代化迅速地瓦解了传统的家族结构、中世纪的行业组织,传统的、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并建立共同的认同与心理上的依附的社会组织(家庭、家族与宗族、行业协会等等)被工业化带来的大规模移民、城市化、工厂化所打破,个体被迅速地抛向社会,由此造成的社会疏离感,使得人们迫切需要重新组织起来,重建认同、依附和稳定。纽曼认为,权威主义政党兴起的原因,在于个体对于社会整合的需要以及政党满足这一需要的能力。Sigmund Neumann,“Toward a Theory of Political Parties”,World Politics,Vol.6,No.4,1954. (36)[美]托马斯·埃特曼:《利维坦的诞生:中世纪与现代早期欧洲国家与政权建设》。 (37)Stephen Biddle and Stephen Long,“Democracy and Military Effectiveness:A Deeper Look”,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48,No.4,2004. (38)[美]蒂利:《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陈周旺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 (39)法国学者莫里斯·迪维尔热与美国学者唐斯都注意到选举制度对于政党行为的约束,他们发现简单多数选举制度可导致两党竞争,而比例代表制度则容易导致多党制,见[法]迪维尔热:《政党概论》,雷竞璇译,香港:香港青文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1年;[美]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姚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40)比例代表制在某些情况下有可能使得一些小党在议会中获得一定的议席,并获得与主流政党的讨价还价能力,但不应夸大这些小党的政治能量。 (41)蒂利在研究早期欧洲民主化进程时就已指出,“类属不平等”是导致19世纪欧洲抗争性政治的关键原因,见其《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 (42)许多美国学者研究了早期美国的政党“机器”现象,发现党派领导人或各种社团组织,利用慈善事业、代理诉讼、安排婚丧嫁娶、馈赠礼品、组织社会救济等途径操纵控制选民选票的现象极为普遍。见M.Ostrogorsk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Longdon:The Macmillan Co.,Ltd.,1902;[美]J.布鲁姆与S.摩根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杨国标、张儒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43)实际上18~19世纪英国各地的选举与被选举资格规定并不统一,各种限制资格十分复杂,包括房产所有权、地方税收缴纳数量、市镇合作组织成员资格等等,虽然规定复杂,但总体的方向是一致的,都是借助各种资格规定排除非精英的民众进入国家政治生活。见[英]布莱恩·希尔:《不列颠的早期政党与政治:1688~1832》,第17页。 (44)[英]布莱恩·希尔:《不列颠的早期政党与政治:1688~1832》,第18页。 (45)(46)罗德岛除外,见[美]埃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上卷),王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4、446页。 (47)Michael Parenti,“Power and Pluralism:A View from the Bottom”,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32,No.3,1970. (48)姬虹:《走向自由:罗莎帕克斯的时代》,《世界知识》2005年第22期;傅林、夏志刚:《美国公立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形成与终结》,《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 (49)(50)[美]J.布鲁姆与S.摩根等:《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第76、77页。 (51)Desmond S.King and Rogers M.Smith,“Racial Order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9,No.1,2005;王伟:《民权法案对黑人民权运动的影响》,《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52)对20世纪民主化转型研究理论的批评,见Thomas Carothers,“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Journal of Democracy,Vol.13,No.1,2002; 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Foreign Affairs,Vol.76,Issue 6,1997。 (53)李普哈特与柯利曼都曾批判过政治发展学派对西方现代政治制度认知的狭隘,认为他们大多不了解西方现代民主体制相互之间差异更不用说形成历史,却轻易地将现实中第三世界的“传统政治”与他们脑海中的“西方现代政治”进行比较,而他们据以参照的所谓现代西方政治,充其量只是“英国政治”或“美国政治”,根本不能代表整个西方政治发展的复杂与多样性。见Lijphart,Arend,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Coleman,James S.,“The development syndrome:Differentiation equality-capacity”,In Leonard Binder,James S.Coleman,Joseph La Palombara,Lucian W.Pye,Sidney Verba,and Myron Weiner,Crise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1。 (54)帕森思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政治现代化学者们用以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的最主要的比较分析框架。有关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参见吴清:《国家范畴与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55)Frances Hagopian,“Political Development Revisited”,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3,No.880,2000. (56)(57)(58)(5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4、344、24、24页。 (60)20世纪60年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白鲁恂也认为:“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够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转引自亨廷顿书,第25页。 (61)(62)(63)(64)(65)[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11~19、10、6、1、17页。 (66)20世纪90年代苏东事变之前,西方政界与学界中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异类”,以惊人的准确性预测到苏联有可能一夕之间崩溃,其中最著名的是“X论文”的作者乔治·凯南,作为美国驻苏联的职业外交官,早在1947年他就在一篇8000的电文中预言“苏联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变为一个最弱的、最可怜的国家之一”。见[美]乔治·凯南:《苏联行为的根源》,张小凯译,《政治学研究》1988年第1期。原载Foreign Affairs,July,1947。 (67)[美]Z.K.布热津斯基:《苏联民族问题的政治含义》,陈观胜译,《民族译丛》1979年第2期。 (68)自1918年[德]斯宾格勒出版《西方的没落》后,英美西方世界平均每隔15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自我怀疑甚至自我否定的浪潮:1930年代期间大萧条期间、1960年代苏联首发载人卫星期间、1970年代越战期间、1980年代美苏全面对抗期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欧美知识界都曾出现过对其治理能力的大规模质疑。亨廷顿在20世纪70年代自己也曾卷入其中,见[法]米歇尔·克罗齐、[美]塞缪尔·P.亨廷顿、[日]绵贯让治:《民主的危机》,马殿军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年。 (69)相关研究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5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彭雪莲:《苏共干部任命制的特征、危害与启示》,《上海党史与党建》2011年第10期。 (70)有关苏共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的研究甚多,见高放:《苏联共产党的党内民主怎样被破坏殆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沙舟:《赫鲁晓夫的暴落》,《决策与信息》2006年第8期;郑异凡:《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制度》,《当代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10期;王立新:《党内组织制度的衰落与苏共败亡》,《理论学刊》2004年第10期;等。 (71)有关赫鲁晓夫时期干部制度改革及其结局,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 (72)相关研究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 (73)如希莱尔·贝洛克所言“对财富生产的控制,就是对人类生活本身的控制”,转引自[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眀毅、冯兴元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74)有关苏联社会两极化研究,见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第3~4章。苏共党风、干部特权问题论述,见李慎明等:《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教育参考片解说词,2006年。 (75)有关苏联克格勃权力之研究,见[苏]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田大畏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6年;[美]约翰·巴伦:《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沈思清编,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郭永胜:《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意识形态僵化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张雪峰:《苏联劳改营史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7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洵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77)郝宇青:《苏联缘何不能成为一个学习型政党》,《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5期。 (78)郭春生:《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与社会的离异》,《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2期;[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79)“夜间人”现象指白天说假、大、空、官话,晚上说真话;“厨房讨论”指私下抨击时政现象。 (80)犹太人移民情况见[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81)[俄]E.T.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王尊贤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82)左凤荣:《苏联走向衰落于解体的深层原因探析》,2001年。 (83)黄苇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南方周末》2011年8月18日;徐迅雷:《权力不受制约的必然趋势》,《领导文萃》2011年第5期。 (84)左凤荣:《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1年第79期。 (85)有关苏联体制内精英利用中央政府弱势的机会,鼓动地方民族分离主义脱离苏维埃联盟、鲸吞国家财产,见[俄]尼古拉·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美]大卫·科兹与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炙热的头脑》;李慎明等:《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八集教育参考片解说词,2006年。 (86)[美]菲利普·罗德:《苏维埃联邦政治与族群动员》,王娟译,《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10年第61期;Suny,Ronald Grigor,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87. (87)Philip Roeder,“Moder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Leninist Developmental Strateg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3,1983; Ken Jowitt,“Soviet Neotraditionalism:The Political Corruption of a Leninist Regime”,Soviet Studies,Vol.35,No.3,7,1983.标签:政治论文; 政党政治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政治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