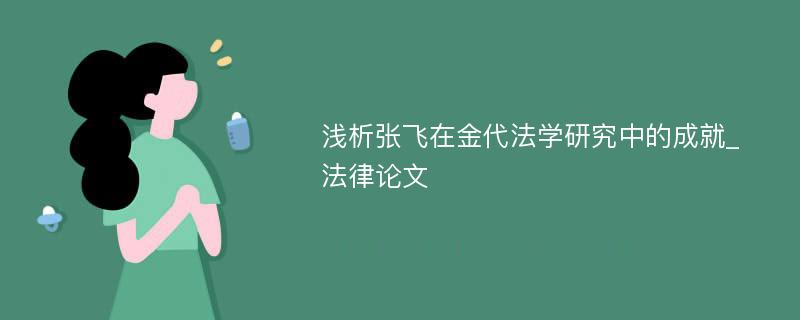
浅析晋代张斐律学成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晋代论文,成就论文,张斐律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173(2001)04-0058-04
晋代是中国古代律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曾经出现许多颇有影响的律学学者,张斐便是其中之一,他的律学成就对晋代法制产生极大的作用,他的理论涉及到法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审判学等领域,他的律学研究从抽象的理念到具体司法实践活动均进行了较为精辟的论述,促进了晋代以及后世律学研究和发展,是我国古代法律学者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代表,他的律学成就不仅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而且为中国古代律学的研究奠定了雄厚的理论基础,并且为我国现代法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法律文化素材。
一、律学的概念及其成因
中国古代法律发展从尧舜时期的“皋陶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1]到夏朝国家法制的初步建立;从西周奴隶制的“周有乱政,而作九刑”[2]的“九刑”,到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从《秦律》、《唐律》一直到《大清律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和艰难而曲折的继承演变过程。以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律学在我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却书写出了绚丽的一页。法律的产生和发展是律学赖以诞生和发展的前提,只有当法律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会有律学的问世,律学的出现又是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现象。
我国的法学理论学者曾对律学的概念下过定义,如“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研究法律的学说理论称为律学”[3];“律学是专门研究、解释法律的学问”[4]。“律学是法学在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展史上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主要研究的是以成文法典为代表的法律的编纂、解释及其理论”。[5]“律学是依据儒家学说对以律为主的成文法进行讲习、注解的法学。”[6]笔者认为,律学是对我国古代法律理论科学的高度概括,是以我国古代法律作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形态。所以它既包括立法原则的确定、法典的编纂,也应包括法律的解释、法律的研究等内容。
早在我国西周初期的刑法原则中,已经有了犯罪人主观心理状态的故意(非眚)和过失(眚);惯犯(惟终)和偶犯(非终)的明确划分,诉讼程序上也出现了刑事(狱)和民事(讼)的区别,说明当时的法律从形式到内容上已经有了质的变化,开始从理论的高度上探讨法的现象和适用问题。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从概念的角度来阐释法的含义,他认为:“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7]战国时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韩非曾经为法律从形式上下定义,他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8]1975年2月在我国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记载秦代律令为内容的历史资料“竹简”,简称《云梦秦简》。《云梦秦简》的出土为研究我国秦代法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依据,其中的《法律答问》是关于法律条文、法律术语、法律适用、诉讼程序等问题所作的问答,它可以作为下级官吏办理法律事务的依据,是一种有效的法律解释。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曹魏的司法机关中开始设置了解释教授法律的文职官员“律博士”及后期的“明法椽”、“律生”等讲解注释法律的司法制度的设置,以及大量律学者的出现对律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中国古代律学的正式诞生,一般认为是从汉代开始。如“汉代的引经注律及律令章句之学的出现,则是律学正式形成的标志。”[9]“从汉代起,在法学领域中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律学’。它不仅从文字上、逻辑上对律文进行解释,也阐述某些法理,关于礼和法的关系,对刑罚的宽与严,肉刑的存与废,律、令、例等的运用,刑名的变迁以及听讼、理狱等。”[10]但是律学的出现也并非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以前人在立法、司法过程中形成的经验为基础的。“汉末之时,法学再盛之世也”[11]前人法律理论研究以及法律解释的出现为法律的发展进步无疑起到推动作用,并且为晋代律学兴起及其以后法制建设和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张斐的律学成就
晋代是我国古代律学发展的全盛时期,律学的代表人物诸多,张斐、杜预、刘颂等人尤为突出。由于张斐、杜预两位律学者曾为晋《泰始律》作注解,后经晋武帝批准而“诏颁天下”赋予法律效力,后世将张斐、杜预对晋《泰始律》的注解合称“张杜律”。张斐、杜预为晋《泰始律》作的注释是在总结以往的立法、司法之成败经验并且从理论的角度进行阐释,丰富了法律文化的内涵,已经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反映了当时律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他们的律学成就为后世法律的制定并且指导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唐律疏议》的影响巨大。
张斐一生有许多的著述但已经失传,惟有《晋书·刑法志》中尚存有张斐《律注表》一篇,这是我们研究张斐律学思想及理论的宝贵史料,是中国法制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源。张斐的律学理论内容丰富,见地精深,确实是我国古代法律学者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人物,就其律学理论的层面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张斐的法哲学理论
作为世界观组成部分的法律观一旦上升到系统化、理论化的高度则已经进入到哲学的范畴,尽管在我国古代没有现代哲学的概念,但是,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和理论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是不可否认的现实。晋代张斐研究律学已经从具体的内容上升到抽象的哲学范畴并且在自己的律学研究中注重法理的探讨和解释。《周易》是闪烁我国古代哲学思想光辉的著作,无论是《周易》本身还是阐释《周易》的系辞都是具有深厚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张斐从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者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12]中得到启示,形成他自己律学宏观上的方法论。系辞的这句话是说抽象超出形体之上的,称作“道”,道在这里是指万物的事理、方法。具体有形可见的称作“器”,器在这里指器具、工具。器具与道理不可分离,将抽象的道理与具体的器具,适当变化剪裁,发生作用,称作“通”,通即通达之意,是融会贯通的意思,然后,倡导设置以供天下人民使用,称作事业。
因此,张斐认为从理性高度阐释法律,应当是“道”、“器”、“格”三者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理论体系。他根据上述《周易》系辞,演化成自己的律学总的理论:“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格。”[13]他认为“道”、“器”、“格”三者有机结合,道居其首,“道”是形而上的,即是法律无形的精神和灵魂,是包括法律在内万物所必须遵循的事理,在这里“理”其实就是经过汉代董仲舒改良后上升为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儒家思想的“礼”,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器”则属于形而下的各种法律外在表现形式,是在“道”的支配下显现出的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是道在法律范畴中的物化方式;“格”是古代官吏处理事务的规则,是一种法律形式,在这里应该是指司法实践与衡量罪刑的执法尺度。“道”、“器”、“格”不仅不可分割而且顺序也绝不允许颠倒,依据“道”的精神实质制定法律,依据法律定罪量刑,审理、裁判案件。道是灵魂,器是法律,格是实践,依据“道”的事理制定的法律必须要通过“格”贯彻推行,在社会的实践中来体现“道”的大义,因为,“道”是抽象的,“理”只有将其具体化才能落到实处,才可能产生功效。而司法官吏在执法的同时也应当以“道”的理念作为指导司法实践的总原则,这样法律就不会只是一种僵化的“器”,而是运用灵活、调整通畅、治理有效的法律规范。在理与法的关系上张斐作了这样的论述:“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之;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14]可以看出,张斐认为“理”是精深玄妙无形的法则,所以,不能简单机械的理解,只有把握住“理”的精髓,才称得上真正理解“理”;而在“器”(法律)之中具有隐藏着幽深奥妙的“理”,所以执行法律时就不能固守条文,简单操作,必须要用“理”的精神指导司法实践。这就近似于现代的从法理上探讨法的实施所产生的问题。如何用“理”指导司法实践,张斐也作了具体的阐述:“或计过以配罪,或化略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趣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以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使用法执诠者幽于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力于机格之上,称轻重于豪铢,考辈类于参伍,然后乃可以理直刑正。”[15]这段话的意思是执法要符合“理”的需要,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适用刑罚不可简单从事,有时可以将过失行为进行定罪,有时还可以对有罪的人免除刑罚,定罪量刑一定要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社会的需要既可以使用重型以防范犯罪,也可以使用轻刑以体现恤民的仁政。官吏犯罪应当区分是因公因私,公、私罪处理轻重有别。针对上述各种情况,执法者都应本着因时制宜原则,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全面衡量,仔细分析,力求贯彻“理”的精神,达到“理直刑正”封建社会法制的要求,最终体现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需要。
张斐在论及礼与刑的关系时说:“礼乐崇于上,故降其刑;刑法闲于下,故全其法。”[16]意思是说礼乐是社会生活中的最高原则,是根本性的社会规范,为使礼乐能够得到普遍遵守,则应制定法律来作为保障;刑法是治理下层的统治工具,所以应当制定得详备全面。这样就可以达到尊卑有叙,仁明义彰,九族亲睦,天下太平。
这样的律学理论不仅涉及到哲学、法理学、也涉及到司法审判等法学领域。应当指出的是张斐的律学理论是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不可避免的带有欺压人民的反动性质和效忠君主的封建正统思想,由于其赖以建立的律学体系是源于唯心主义,因此具有消极的一面。
2.刑法概念理论
《刑法》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典中的重要一篇,在整个法典中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其内容近似于现代刑法的总则部分,张斐对《刑名》一篇的解释为:“《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之纲领。”[17]可见刑名的地位及其重要性,刑名不仅是统帅全律的灵魂而且对于法典其他篇具有原则性的指导作用,罪行轻重加减之量刑,立法不足的补充等,刑名于其他各篇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对于刑法中的一些常见概念,张斐也从逻辑上以定义的方式加以界定。如“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理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失,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群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财货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18]张斐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又难以分辨的二十个刑法概念内涵进行本质性的抽象并且做了较为明确、精练的界定,这些律学成就无疑对当时的司法实践在查明犯罪人主观、客观方面产生巨大的影响,使难以掌握的法律概念问题从而成为操作性较强的衡量尺度,在错综复杂的具体案件中司法官吏亦能凭借明确的概念准确判断、把握案情,及时准确的处理案件,极大地推动了晋代法制建设的发展。虽然,张斐对刑法一些概念所下的定义还极为简单,内涵和外延上缺乏更为科学形式与内容,但是,张斐的律学理论研究在当时水准也是较高的,标志着律学研究的蓬勃发展,与过去律学相比更趋向进步与科学。尤其是对犯罪主体主观的罪过,故意与过失辨析界定可谓是言简意赅的反映了两者的本质特征,对何谓造意,何谓共谋,何谓盗,何谓赃都界定清楚明白,易于司法官吏裁断。
基于以上理论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张斐是当时在法学领域中颇有建树的律学者,其律学成就之大,堪称晋代律学者之楷模。
3、司法审判理论
张斐的律学理论,还涉及到较多的司法审判理念,并用于指导司法审判实践。如“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绪,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19]他认为:犯罪是由于犯罪人内心的驱使,由于内心的驱使,从而在言行上反映出来,驱动犯罪行为的发生,张斐这个理论观点已经涉及到心理学范畴中的意识和意志的相互作用问题,这也是现代刑法学理论研究犯罪主体主观罪过的两个重要因素。有鉴于此,张斐认为:“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必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后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是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欢,貌在声色。奸真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20]以上论述,张斐显然是受到了董仲舒“原心论罪”的理论影响,但却不限于此,可以说他将“原心论罪”的理论又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张斐从分析“犯罪人内心的犯罪起因驱动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出发,提出罪犯会由于违反社会规范内惭愧而显于面色的理论,这就为断狱创造了辅助性的条件,要求司法官吏要善于运用对罪犯察言观色的方式审理案情。用察言观色审理案件源于《周礼秋官小司寇》的五声听狱制,“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眊然)。”[21]张斐是在前人以“五声听狱,求民情,”,审理案件的基础上将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贵在阐述了犯罪行为主客观的统一性并以此为依据推断犯罪人的由于实施犯罪活动而产生的内心恐怖(心理现象)会通过面部表情反映出来,这就极大的发展了前人理论,这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也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单凭察言观色是不能概括案情的整体以及复杂情况下的各种具体情形,所以这种审讯的方式必须要与其他方式相配合,最终还是要建立在事实证据的基础上。
他还强调司法官吏既要严格依法办案,又要依据“理”的原则灵活运用法律:“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22]法律要灵活掌握,但要非常慎重,变通要视其是否符合“理”。执法必须公允,绝不能任意妄为“夫奉圣典者若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23]执法应当是不枉不纵,要求执法者审慎刀绳,切不可滥用刑罚,伤害无辜。为确保审慎执法,就要提高办案质量,就要提高执法官吏的思想品德和业务素质,所以张斐的这一理论主张,对执法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确是不容易作到的事情,所以张斐也多少带有一些感慨的口吻说道:“欲令提纲而大道清,举法而王法齐,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通天下之士唯忠也,断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远也,弥天下之务唯大也,变无常体唯理也。非天下之贤圣,孰能与于斯!”[24]
三、结语
张斐的律学研究是多方位的,他的法哲学(法理)价值在于他能够从法律的理念上探讨抽象的“理”与具体的“器”、“格”从形而上(理性)到形而下(感性)之间依赖和依赖于的相互关系,形成新的理论体系。“理”从宏观上指导具体的法律的创制、法的实施、法律实践,而在法律具体执法之中又必须体现“理”的精神实质,认识到法律这一事物发展过程中抽象的思想体系与具体法律形式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他分别阐述了“理”与“律”的相互关系;“礼”与“刑”的相互关系,以礼率律,律为礼用,这些内容表现在《晋律》的体例上。《晋律·刑名》中有“始于刑名,所以定罪制也;终于诸侯,所以毕其政也”。这种结构体现了“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故有三才之义焉。其相须而成,若一体焉”。“礼乐是贯穿晋律各篇的基本精神,所有的律条都必须折中于‘礼乐’,与之相符合”使封建统治阶级的礼教与封建法制形成统一有机的整体,力图通过二者相互作用使法律产生最佳的社会效益。这种以“礼”为内容,以法律为形式新的律学思想注入封建法制体系之中,从而丰富了法律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形成了他自己的法哲学观点。张斐这种建立在理论基础上的法治观,经统治阶级认可而上升为封建法制核心思想并且成为指导法的制定和实践的方法论,开创了律学理论体系的新纪元。
在刑法理论中张斐注重法律概念的确定性,十分重视区分各种复杂的案件情况,从具体司法实践各种案件中运用形式逻辑抽象、概括出诸多的法律概念、刑罚原则等具有文明的法律理念,从犯罪人的心理上分析犯罪动机对犯罪行为的驱动关系和作用。这些刑法理论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社会价值。开辟了古代刑法学的新思维,对后世律学的刑法研究发展以及司法实践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
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张斐强调法官须具备相应的品德和业务素质,有能够用“理”指导司法实践的能力,审慎用刑;他主张将“理”的精神和要求贯穿到具体的执法当中,不拘泥形式而灵活运用法律。他还主张运用罪犯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判断是非曲直。这其实是将律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相结合,这在律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张斐的律学研究是卓有成效的,反映出他对其以前历朝法律现象严肃的态度和深刻思考,他总结了前人的律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经验认真分析了法律的社会效用,虽然他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但是,他的律学思想和成就却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这对于现代法学的研究和探索我国法律源流的理论思路提供了重要历史线索。张斐的律学成就非常显赫,它是中华民族文明进程中法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收稿日期 2001-02-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