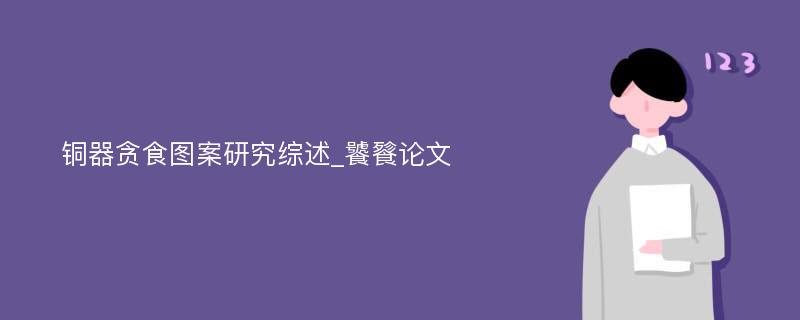
青铜器饕餮纹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饕餮论文,青铜器论文,述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饕餮纹是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不可回避的一个概念。虽然近世也有学者不断地提出新的名称(注:李济有“肥遗”之说,马承源有“兽面纹”之说,邱瑞中有“立体龙”之说,……诸说各异,详见下文。),但却无法在中国青铜文化中淡化“饕餮纹”一词的重要性。甚至西方东方学学者吉德纬(David keightley)曾说:“你如果不懂饕餮,就无法了解商代文化。”而他自己更认为饕餮是“一个甲骨文卜辞所无法解答的巨大谜团”。(注:吉德纬:《商史材料》页137,转引于艾兰(S.Allan):《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1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如果我们暂且不介入有关这一名词是否合理的争论中,那么此词的始作俑者是谁呢?谁创造了这一“谜团”以致后人为之而困惑不解?是商人自己?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因为商人只是在青铜器上创造了这一视觉形象,但并未给它命名(注: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商人称这种纹饰为什么,无论甲骨文、金文或青铜器铭文,都没有涉及这一纹饰的名称或者是“饕餮”一词。),据现有资料看,最早把这种纹饰称为“饕餮”的是《吕氏春秋》。其书云:“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注:《吕氏春秋》卷一六《先识览》,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于是后世自北宋以来,所有金石学书籍一直称商周青铜器上这种神怪性的纹饰为饕餮纹。
至于《吕氏春秋》为何将它名为“饕餮纹”,我们已经无从确知,但有一点却可以判定:即这一定名并没有太多的依据(注:《吕氏春秋》成书于战国末年,距殷商之时已属久远,且其书之成乃吕氏门人拼凑之作,言多不实。再者,饕餮纹与饕餮之称存在较多名实不符的逻辑问题,故笔者认为《吕氏春秋》定名之举并无根据。)。《吕氏春秋》的著述者可能是从饕餮纹的视觉特征——狞厉感出发(注:饕餮纹从视觉感受上看具有一种神秘的狞厉感。此说可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第一节“狞厉的美”,《美学三书》页39,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再联系传说中神怪之名而加以命名的。因为饕餮在文献记载中属于上古神话传说的怪兽或恶人形象,多见于战国秦汉的相关著述。饕餮之名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用作人的称呼,注云:“贪财为饕,贪食为餮”,“饕餮”即贪财贪食之意。将文献中的“饕餮”总结归纳,我们可以得出二点:一、饕餮是上古传说中野蛮的部落名称,如“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注:《尚书正义》卷三,北京大学藏《四部从刊》本。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春秋经传集解》、《左传》等。);“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注:《吕氏春秋》卷二○《恃君览》,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类似记载还可见于《淮南子》、《通鉴纪事本末》等。);“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好自积财,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注:《神异经·西南荒经》。),等等。二、饕餮非人,乃食人之怪兽,如“饕餮,兽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肋下,食人”(注:《十三经注疏·左氏传文公十八年》服虔引《神异经》注。);“为物贪婪,食人未尽,还害其身,像在夏鼎,《左传》所谓饕餮是也”(注:《山海经.北次二经》中郭璞注语,原句为:“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枭,是食人。”)等等。
青铜器中的饕餮纹是否就是上述文献中的饕餮,我们暂且不论,单就这种纹饰而言,在商周青铜器上是极为常见的。它集中出现在三个时期:二里冈期、殷墟期和西周初期。二里冈期青铜器纹饰简练,大多为带状,少有通体满花的器物。此期饕餮纹亦较简洁,多带状长条,上下夹以联珠纹,一般为单层,没有作衬底的地纹,多以凸出的线条来表现,或细或宽的线条组合方平,转折处流畅自然。殷墟期青铜器器形厚重,装饰华美,形成了层次分明、富丽繁缛而神秘的新风格。此时的饕餮纹已不再是简单的带状布局,而是占据了器皿较大的空间,向通体满花的方向发展,且向立体多层装饰发展,绝大多数都饰有地纹(即在饕餮主纹的底部空白处刻上匀密纤细的云雷纹作为衬托),地纹上饰主纹,主纹上又刻以阴线重叠加花,形成所谓的“三层花”饕餮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还出现了大量面部完整而具象的饕餮纹。西周初期青铜器与晚商基本相同,难以截然分清,饕餮纹亦然。但这一时期的青铜器也出现了简化的趋向,饕餮纹在器物中逐渐淡化,向周代中期的“素面”过渡。如“父癸鼎”只在口下有一圈纹饰带,且纹样简单模糊,三足作翘尾夔形,余则为素面。
西周中期青铜器的风格转向“以素为贵”,原先“以文为贵”的繁缛狞厉的饕餮纹便渐渐失去了昔日的风光。与此相应,此后的青铜器在“王权下放”之“礼崩乐坏”的进程中逐渐走向生活化的装饰性,以人的生活为中心的宴乐攻战图等代替了饕餮纹的地位。于是饕餮纹便成为一种过去的形象记忆,在历史流变中逐渐丧失了它原有的内涵,令后人为之惊诧而困惑。
除二里冈、殷墟与西周初期为饕餮纹集中出现的时期外,其上限还可以推至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牌饰、山东日照两城镇玉锛纹样和龙山文化玉圭上的纹样,甚至还有学者将它推到良渚文化(注:持此说者甚多,如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冯其庸:《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第5期;王仁湘:《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文物》2000年第3期;岳洪彬、苗霞:《良渚文化“玉琮王”雕纹新考》,《考古》1998年第8期;韩湖初:《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等等,都有类似观点,但却都未曾系统地给予论述,多是兼带论及罢了。惟李学勤先生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证,见下文。),把良渚神徽与饕餮纹作比较,指出二者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的密切关系。李学勤先生将这种观点进一步深化,直接称它为良渚玉器饕餮纹,并从8个方面对两者进行了详细而系统的比较,认为两者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它们显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中介便是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当然,他也有所保留地认为这些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尽是直线的,还有待于更多的发现与研究(注: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饕餮纹的下限应以西周中期为妥。因为至西周中晚期,饕餮纹的主体地位被窃曲纹所取代,而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则以表现现实生活的画面为主,如狩猎、攻战、采桑、宴乐、建筑等,虽也有表现神话与宗教思想等方面的画面,但却仅仅是一种叙述性的情景图式而非饕餮纹。后世亦偶有以饕餮纹为饰的器血,甚至还出现了类似饕餮纹的铺首,但它们均非原生性的商周饕餮纹,而是一种次生性的摹仿纹饰,不能作为饕餮纹合乎逻辑的下限。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补充说明,即有关窃曲纹的理解。窃曲纹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的主要纹饰,但何谓窃曲纹,其状如何?仅以“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注:《吕氏春秋·适威篇》,北京大学藏《四部丛刊》本。),似不易确认。容庚先生在《商周彝器通考》中按《吕氏春秋》之说,列出15种窃曲纹的图像,成为近世确认窃曲纹的依据。但容庚先生后来又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对窃曲纹进行了重新梳理,只保留了其中的3种纹样,并认为“窃曲纹中多含有目形和兽角的形状,故知其从动物形状变化而来”。后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发展了这一看法。他从西周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变化的角度来分析研究青铜器的纹饰,并认为所谓的窃曲纹实际上是从具有浓厚宗教信仰气氛的兽面纹(注:马承源先生主张废除饕餮纹这一概念,改用兽面纹,故此处兽面纹实际上就是本文所谓的饕餮纹,下同。)蜕化而成的变形兽面纹。所以他把这类纹饰分别归入变形兽面纹、兽目交连纹、兽体卷曲纹等,从而废弃了窃曲纹之称谓(注:以上一段文字参见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中“西周青铜器上的窃曲纹”一节,页182-185,文物出版社,1999年。)。
容庚、马承源二位先生独具创见的观点对窃曲纹的认识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揭示了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纹饰与西周早期青铜器纹饰在形态上的继承性,使两者在纹饰风格发展的连续性上取得了统一。但这一看法对“饕餮纹以西周中期为下限”的观点产生了某种冲击与质疑,因为如果承认窃曲纹是饕餮纹自身演变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饕餮纹在西周中晚期便仍占有一种主导地位,乃至于延续到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笔者认为窃曲纹对饕餮纹的继承仅仅是一种表面形式上的延续,因为它在形态继承上这种面目全非的延续恰恰反映了它在纹饰内涵上与其继承对象的割裂与非延续性(注:从饕餮纹的共性上归纳,这种纹饰至少应该同时具备以下两个特征:1、正面的对称性;2、目部突出。但这两点在窃曲纹上并不具备。)。而且笔者认为判定两种纹饰的关系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式的相似性上,而更应该注重形式下所蕴涵的内容。特别对于中国早期历史图像的研究,尤其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它们往往都是内容大于形式的象征,具有一种意旨上的符号性。据此,笔者认为窃曲纹并不是饕餮纹自身演变与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它与饕餮纹在形式上的相似也仅仅是一种新生纹饰对传统纹饰在形式上的某种借鉴与吸收。并且,这种新旧纹饰的此消彼长恰恰是商周文化发展的某种投射(注:殷人崇鬼神,具有浓厚的宗教性,周人崇伦理,以人事为纲。具有神秘宗教气氛的饕餮纹在西周中期被窃曲纹取代,恰恰源于这种崇伦理文化对崇鬼神文化的取代。而西周初期对殷墟期饕餮纹的继承则主要源于制作上的延续和文化惯性上的延续,并非周人文化的形象代表。王国维称商周之变为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巨变,是由神性的巫术时代走向了伦理化的人性时代,那么由此进而推论饕餮纹虽然在西周早期有所出现,但却仅仅是一种对商人的重复与模仿,他们自己并没有为饕餮纹增添或改变了什么。),或可以认为饕餮纹在新的文化背景中被另一种新生的纹饰所取代具有其历史必然性。那么,以西周中期为饕餮纹的历史下限便仍是一种可行的或是较为科学的划分。
饕餮纹自《吕氏春秋》定名,后世一直沿用,如吕大临在《考古图》“癸鼎”下曰:“中有兽面,盖饕餮之象”,但对它究竟是何兽或何象却一直未能明确。
如果说早期对饕餮纹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精神相一致,属于感性体悟式的著录方式,那么从20世纪上中叶开始便出现了对饕餮纹系统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早在1964年,李济先生便说过:近30年来,有两部研究青铜器花纹的著作为学术界所重视,一部是容庚的《商周彝器通考》,另一部是高本汉(B.Kalgren)在《远东博物馆馆刊》23期(1951年)讲早期青铜器花纹的文章(注:参见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述成果拉开了现代“饕餮纹”研究之旅的序幕。此后,这一商周青铜器上最重要的纹饰便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各个方面的重视,文化学、考古学、美术史学、美学、人类学乃至东方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或研究,观点众说纷纭,各持己见而难以统一。
现对学术界各种主要观点归纳评述,笔者认为可以在四个层面上进行:一、有关饕餮纹的名实考;二、有关饕餮纹的起源论;三、有关饕餮纹的类型说;四、有关饕餮纹的内涵说。也可以认为,现在学术界对饕餮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问题上,即饕餮纹是否应该以饕餮为名,否则又该如何定名;饕餮纹与早期历史图像有怎样的继承关系;饕餮纹有哪些类型;饕餮纹到底代表了什么。当然,这四个问题并不是孤立分裂的,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比如说饕餮纹代表了什么就影响并决定了饕餮纹的命名问题。这里,只是出于论证的方便才加以相对的划分。
(一)饕餮纹“名实考”
对于饕餮纹是否该以“饕餮”为名,答案很简单,无非“是”或“否”两种选择。现代绝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后一种答案,即否认“饕餮纹”定名的科学性。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在其著述中仍然沿用饕餮纹的名称,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同意饕餮纹就是一种名实相符的称呼。他们或出于研究上的继承性,或出于论证的方便,以约定俗成的法则为准,既不肯定饕餮纹就是饕餮,也不废弃这一称呼。如容庚先生虽然使用“饕餮纹”一词,但却仅仅是对纹饰形态的一种称谓。他在《商周彝器通考》中将饕餮纹区分为饕餮纹和蕉叶饕餮纹两类(注:参见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从蕉叶饕餮纹的定名来看,“饕餮纹”对容先生而言,与其说是一种纹饰概念的定义,不如说是一种纹饰形态在语言上的代表符号。另如高本汉(B.Kalgren)先生,倾其一生之力对大量饕餮纹分型分式,试图从纹饰形态的演变上建立青铜器风格发展的坐标并证明他关于由写实饕餮纹向几何形纹发展的假说(注:参见艾兰(S.Allan):《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25-226,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但同容庚一样,他虽然在论述中采用了“饕餮”的名称,却也回避了“饕餮纹是否就是饕餮”的问题。从其论证的角度上看,他和容庚相似,是从形态区分上来展开研究的,“饕餮纹”对他而言,亦仅仅是一种习惯的称呼,而并不是这种纹饰所代表的内容或是一种科学的命名。
真正肯定饕餮纹代表文献中所记载的饕餮,在今日学术界已不多见,但亦有少数学者在其论述中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如李泽厚先生曾论述道:“因之,吃人的饕餮倒恰好可以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吕氏春秋·先识览》说,‘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是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注:李泽厚《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第一节“狞厉的美”,见《美学三书》页45,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这里,李泽厚所论述的饕餮纹之狞厉感,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饕餮,那么这样的论证中便隐含了“饕餮纹就是饕餮”的前提。类似的又如韩湖初在其《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感”》中,为了说明饕餮纹代表牛首,以文献考证的方式由饕餮推至缙云氏,再由缙云氏推至“牛首”炎帝,其中无疑也隐含了“饕餮纹就是饕餮”这样的前提(注:原文论证为“问题是作为青铜饕餮最有代表性的商人(兽)面大钺中的兽是何种动物呢?……笔者认为是牛……《帝五世纪》和《补三皇本纪》都说炎帝‘人身牛首’,说明炎帝族原是以牛为图腾的。……《左传·文公十八年》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可见饕餮一族是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的后代。”此文发表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最直接承认“饕餮纹就是饕餮”的提法,据笔者所涉及的材料看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他曾说:“卜辞构成了中国远古宗教的画卷,而与卜辞同时的饰有动物的青铜器艺术品是这幅画卷的重要补充。特别能引起人兴趣的是吞食人的怪兽:饕餮。它的形象极其古老:公元前3千多年的龙山文化的一把石斧上就有它的形象。”(注:安东尼奥·阿马萨里:《中国古代文明——从商朝甲骨刻辞看中国上古史》页8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阿马萨里的原名无查,然有中译文本)。)
更多的学者否定了“饕餮纹”这一名称,较早提出类似观点的是李济先生。他将原来的饕餮纹一分为二,其中有首无身的称之为动物面,而有首有身的则称之为肥遗(注:李济:《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3本页69-70,1968年。)。此说最著名的拥护者是张光直先生,虽然他没有采用动物面的提法而保留了饕餮纹(注:张光直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列出了饕餮纹的名称,但他又言:“一是其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的关系不能明显地看出而需使用古文献里的神话中的动物名称来指称的。”似乎也表明了他对饕餮纹的一种习惯性沿用的态度。该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但却完全接受了肥遗之说。“历来讲金石学者将神怪性兽面纹,无论有身与无身都称为饕餮,但《吕氏春秋》专指‘有首无身’的兽纹为饕餮。《山海经·北山经》:‘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李济建议用肥遗这个名字指称青铜器上当中是正面兽面而左右都有较细长的身体向外伸展的花纹。”(注:张光直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列出了饕餮纹的名称,但他又言:“一是其与自然界中存在的动物的关系不能明显地看出而需使用古文献里的神话中的动物名称来指称的。”似乎也表明了他对饕餮纹的一种习惯性沿用的态度。该文发表于《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然而李济之说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自相矛盾。他否定“饕餮纹”而改用动物面,其中至少隐含了两个观念:1、以神话传说的名称来为纹饰命名不妥,应多以实际形象,哪怕是综合性的;2、饕餮不是饕餮纹的内涵,故而在论证中亦不能用有关饕餮的文献来作论据或论证的条件。但他的肥遗说却完全违背了以上两点,首先在结论上违背前者,肥遗亦为神话传说之物,以它命名与以饕餮命名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其次在论证上也违背了后者,他认为高本汉(B.Kalgren)和容庚将无身的饕餮纹也称为饕餮而加上有身的形容词,与《吕氏春秋》饕餮有首无身的说法相抵触,故而根据《山海经》“有蛇一首两身”而称之为“肥遗型”图案(注:李济:《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3本页69-70,1968年。)。这里,肥遗说产生的论证前提便是《吕氏春秋》有关饕餮的文献记载,显然与他坚持不用饕餮纹的原则相矛盾。故而,此论并非可取之说。
继李济之后,在饕餮纹的命名上突破较大并被广为接受的是以马承源先生为重要代表的“兽面纹”说。他早在《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中便废弃了“饕餮纹”的提法,改用“兽面纹”(注: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著《商周青铜器纹饰》前附属论文,文物出版社,1984年5月。)。虽然他不是最早提出“兽面纹”的人(注:陈梦家早在1954年《考古学报》第7册《殷代铜器》中曾言:“自宋以来所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从其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已有较多学者改用了“兽面纹”一词。而马承源先生也曾言:“实际上这类纹饰是各种动物或幻想中的物象头部正视的图案,后来不少著作中称它为兽面纹。”(见《中国青铜器》页32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版)实际上,兽面纹一词亦与饕餮一样,可见于宋人著录,只是未能如同饕餮之称成为洪流。),但却无疑是“兽面纹”一词最重要的推广者。特别是他在上海博物馆所做的革新之举(注:上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没有沿用饕餮纹一词,而全部更改为兽面纹,对“兽面纹说”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与推广作用。),使兽面纹的名称被更多的人接受。他曾明确指出:“兽面纹这个名词比饕餮纹为胜,因为它指出了这种纹饰的构图形式,而饕餮纹一词却只限于‘有首无身’这样的定义,但绝大多数纹饰并非如此”(注:马承源:《中国青铜器》页324-32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7月。)。此后,“兽面纹”一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渐有取代“饕餮纹”的趋势。
虽然马承源先生在其论述中出于慎重以文献中的饕餮形态与饕餮纹大量存在的事实进行比较,没有完全否定饕餮纹的称谓,只是推导出“兽面纹”较“饕餮纹”为胜的观点,但他却比任何人都坚定地抛弃了“饕餮纹”的概念,彻底地改用“兽面纹”,并不遗余力地推广了这一名词。这对更科学地认识饕餮纹无疑是一次深化,它使我们的视野更加开阔。因为抛开了饕餮一词,就使我们完全从秦汉文献记载中走出,进而也就避免了完全以后世文献证前世纹饰的路子,这是包括现代很多著名学者在内的研究饕餮纹时容易走入的误区。当然,我们首先要明确一点:饕餮纹在《吕氏春秋》中的定名距殷商有千年之远,是时,古史已因材料不足而难以明辨,历史在与神话传说结合的流变中早已面目全非,虽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含着历史的真实性,但这种真实更多地体现在情节性的纲要上,而不在那种细节化的描写与传说中。那么,用秦汉有关饕餮的文献来论证饕餮纹就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一者秦汉文献本身多以讹传讹,甚至随意编撰,在已经甚为简略的历史主干上添加了大量充满神异想象性的细节,而用这样的材料引论上古图像,便很容易产生人云亦云的错误。二者,抛开引用材料的真伪,就其名称而言,饕餮纹的命名也没有什么依据与确证,那么用这种名实是否相符都不能肯定的“名”的材料来论证图像之“实”,在方法论上便是不可取的。就如同我们研究一个水果,还不清楚它是什么,就假定一个苹果的名称,再以有关苹果的材料来论证它,结果它却可能是一个橘子。于是我们曾经做的一些工作可能成为一种徒劳。从这个意义上讲,兽面纹的提法自然地避免了上述误区,成为饕餮纹研究深入化的一种标志。
除兽面纹外,较为类似的命名还有野兽纹、动物纹等。但此类提法在概念上都带有一定的模糊性,因为他们使用了一个比饕餮纹涵盖面要大得多的名称来指称这种纹饰,并且量还不甚确定,那么作为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在其论证中有时又不得不重新采用旧有的称呼,以明确这种不同于其它动物性纹饰的特殊纹饰。或者可以这样理解,他们只是在尽量回避饕餮纹这一概念,将它与其它动物性纹饰合并在一起,名之为野兽纹或动物纹。在一般性的论述语境下,他们选择新的名称。但一旦需要进一步确认论述对象,或是为了避免概念上的含混,他们又不得不使用饕餮的说法,如列·谢·瓦西里耶夫在《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的有关论述便是较为典型的代表(注: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中有“殷代的艺术·‘野兽纹’一节”,页319-333,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为饕餮纹真正更名,他们面对饕餮纹纷乱复杂的形态变化无从下手,于是便采用回避与淡化的方式来消解饕餮纹的复杂性。但这种做法无疑是失败的,因为他们时常又不得不重新面对一个旧有的名称。虽然兽面纹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涵盖面比原有名称要大的情况,但由于其使用者运用这一名称时指向性确定与清楚,使它避免了概念上的含糊,从而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替代“饕餮纹”的新名称。但野兽纹、动物纹却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这种提法在学术界并没有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有关饕餮纹的命名问题,还有建立在对饕餮纹含义进行重新诠释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些新的名称,如立体龙、牛头纹之类。前者如邱瑞中所论:“侧身龙纹、立体龙纹(即饕餮纹)都是彼时祥瑞的象征!商周饕餮纹应更名为立体龙首纹。”(注:邱瑞中:《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后者如陈梦家所言:“自宋以来称为‘饕餮纹’的,我们称为兽面纹的,实际上是牛头纹。”(注:陈梦家:《殷代铜器》,《考古学报》1954年第7册。)但此类说法大都因为在诠释饕餮纹意指时范围过小,难以界定所有饕餮纹的内涵,故而皆不适用(注:作为意义指向的纹饰名称,应该能够覆盖纹饰在各种主要场景中的各种功能,否则便会产生名实相矛盾的冲突,这在符号化使用的宗教纹饰中是应避免的现象。)。
(二)饕餮纹“起源论”
有关饕餮纹的起源问题就是指饕餮纹的产生与其他早期历史图像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和继承关系,它相对饕餮纹“名实考”显得更为复杂而敏感,因为它甚至涉及到中国文明是自发产生还是他发产生的问题。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文化传播学的方法论上做一些反思,即我们不能单单以不同文化在某一局部产生某种相似就得出一定是某某文化影响并决定了某某文化的结论,这是研究人类早期历史的一个重大误区。文化传播的效应应该首先建立在文化传播的手段之上,抛开当时历史背景下文化传播方式的极端落后而妄言文化传播的结果是一种极端不负责任的和非常危险的行为。对此,笔者提出:在早期历史中,除了“文化传播”,还存在着另一种情形——“相同问题情境下的相似解决方式”。
所谓“相同问题情境下的相似解决方式”,就是指当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人群因为某种相同的问题背景而采用了大致相同的解决方法。诸如“刀耕火种”农业形态的产生,可能就是人类在早期农耕问题情境下做出的相似的解决方法,它们之间不一定存在着某某决定某某的单一的文化传播上的因果关系。再如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中的野牛形象与阴山岩画中的野牛形象,没有人会认为两者间存在着必然的文化传播,虽然它们也会因相似的表现手段而具有某种相似的形态。那么,饕餮纹在形态上的野兽特征就不一定源于其它文明中相似的野兽纹,因为这种相似或许仅仅出于一种偶合。
然而,却有着相当多的学者将“文化传播”作为一个万能的手术刀,也不论他们解剖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多大的差距,盲目地抛开传播途径可能性的探讨,用他们解剖出的一丝一毫的相似性,大胆地想象出各个文明之间的影响与渊源关系。饕餮纹的研究也不例外,并且还得出了饕餮纹源于西亚草原乃至更为西方的论断。
这种观点在近代西方中心说的影响下产生颇早,19世纪末德国的研究家赖内克(P.Reinecke)便注意到斯基泰和米努辛斯克青铜器同华北鄂尔多斯青铜器的风格相似,从而拉开了饕餮纹外来说的序幕。此后,许多探索饕餮纹起源的知名专家都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兴趣,人们开始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C·A·帖普楼霍夫(Tennoyxob.C.A)是把斯基泰人的“野兽纹”同西伯利亚(卡拉苏克)及华北“野兽纹”(注:此处的野兽纹乃列·谢·瓦西里耶夫的命名,即本文中的“饕餮纹”。)联系起来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随后,汉学家们也都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其中包括安特生(J.G.Andersson)、马伯乐(H.Maspero)、萨尔莫尼(A.Salmony)、列·谢·瓦西里耶夫等在内。其后,一些专家对它的起源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结论:如塔尔格伦、罗斯托夫策夫、赫茨菲尔德、屈恩等人倾向于认为这一风格起源于伊朗—美索不达米亚世界,然后传播到欧亚草原,这样也就传到了西伯利亚和华北;而博罗夫卡(G.Borovka)、明兹(E.H.Minns)等则认为它发源于西伯利亚,再向外发射传播(注:此段参考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页328-329,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由于转引文献中人名原文未注出,故此段所涉人名未注者皆待进一步查证。瓦西里耶夫的原名亦无查,然有中译文本)。)。
除上述结论之外,国内的芮传明、余太山两位先生则更进而提出饕餮纹与希腊传说中的戈尔工面具以及亚述神话中的胡姆巴巴像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从身份、遭遇类似;容貌、特征相仿;与蛇关系密切三个角度阐述了三者间的相似关系,从而推论:“饕餮、蚩尤、胡姆巴巴、戈尔工等东西方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生物,相互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借鉴和交流。虽然目前尚不能断定何种神话生物为原型,但是它们之间曾经互有借鉴——甚至是反复的‘输入’和‘输出’——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注:芮传名、余太山:《中西纹饰比较》页338-34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1月。)。
与饕餮纹西方外来说相对的是中国本土说。郑德坤在他的《中国商代及史前动物种类》中认为:“尽管关于‘野兽纹’及其斯基泰—西伯利亚诸类型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中国从新石器时代就有动物纹了。如果说它的主要倾向——如写真的、装饰性的、写实的、程式化的倾向等——常有改变,那也只是中国人的祖先们审美情趣变化的结果,别无原因。它以现实的原型为基础,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它存在着什么外来的直接影响。”(注:Cheng Te-k'un:Animal styles in prohistoric and shang china——BMFEA No35 1963。)高本汉(B.Kalgren)在《商代之武器及工具》中则认为:“殷代中国的年代早于卡拉苏克,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殷人会从北方借用这种风格,倒是卡拉苏克可能借用了殷代的这种风格。”(注:Karlgren B: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MFEA No17 1945。)从而坚持了饕餮纹乃华北土著现象的看法。
华北土著说相对西方外来说要显得慎重而严谨得多,但它产生的背景却是中国南方考古资料的缺乏与平庸,这使得他们感到论据的薄弱,不能充分说明这种风格完全源于殷代或殷以前的中国。然而这一缺憾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充实而日益得以解决,特别是南方玉器的出土更为饕餮纹起源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研究的方向。实际上早在1917年,金石学家王崇烈为所藏玉璜题识,便认为它是三代以前的饕餮纹(注:参见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这一推断被1936年后良渚文化的发现逐渐证实,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良渚文化大规模发掘出的玉器实物。其中以1986年6月发现于浙江反山M12:98琮和M12:100玉钺上最完整、复杂的神人兽面图(注:渐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最为著名。这些材料的出土使得很多学者开始关注饕餮纹与良渚文化的关系,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饕餮纹源于良渚文化的观点(注:持此说者甚多,如王明达:《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初论》,《文物》1989年第12期;冯其庸:《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第5期;王仁湘:《中国史前“旋目”神面图像认读》,《文物》2000年第3期;岳洪彬、苗霞:《良渚文化“玉琮王”雕纹新考》,《考古》1998年第8期;韩湖初:《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等等,都有类似观点,但却都未曾系统地给予论述,多是兼带论及罢了。惟李学勤先生作了较为详实的论证,见下文。),但却大都未能进行系统的论述,多是兼带论及的一种推测,没有从形态、传播可能性上进行科学的论证。相对而言,李学勤先生倒是作了较为翔实的论证。他在《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一文中将良渚玉器神人像称为良渚玉器饕餮纹,并从8个方面对商代青铜器饕餮纹与良渚玉器饕餮纹作了比较:1、兽面为两者主体;2、良渚无角,而二里冈期亦多无角;3、良渚之目为卵圆形,二里冈期近于卵圆形的仍占较大比例;4、良渚有口无下颚,且口部多朝下,商代兽面之口亦多向下;5、商代纹饰的额头保留有良渚玉冠的痕迹;6、商代纹饰两侧常饰有衬托的花纹,良渚亦然;7、两者纹饰都具有整体展开法的表现手段,且爪皆向内;8、两者都填以云雷纹或用云雷纹衬地(注:参见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
李学勤先生的论述将“饕餮纹源于良渚”的观点深入并系统化了,他从上述8个方面对两者进行详细的比较,对饕餮纹起源论的研究不无裨益。他认为两者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它们显然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而两者之间的中介可能就是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餮纹(注:参见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李先生的这一观点对理解商周青铜器饕餮纹与良渚玉器纹饰之间的联系与继承关系无疑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但李先生之说却仍然多停留在推论的层面,且没有从功能、形态、传播形式与手段等全方位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其成果还停留在以文化表象上的相似性说明文化间的传播关系,诚如先生自己所言“今后需要进一步探索和了解”。
(三)饕餮纹“类型说”
所谓饕餮纹“类型说”就是用考古学分型分式的方法对青铜器纹饰进行归类,以型式演变为立足点建立纹饰发展的风格史。它是饕餮纹基本形态的系统研究,是梳理纹饰发展、断代、源流及内涵的最基础性的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中国考古学的滞后发展,所以这种研究方式首先产生于西方。20世纪30年代,高本汉(B.Kalgren)率先开展了这项工作,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研究。在一系列有关青铜器纹饰的文章中(注:这一系列文章都发表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上,最重要的包括《中国青铜器中的殷与周》(Yin and chou i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8 1936年);《中国青铜器新论》(New studies on chinese bronzes-BMFEA No9 1937)。),他以有铭器物为标准器,试图为中国青铜器的断代分期创立一个自圆其说的“科学”体系,并借以揭示器体上纹饰组合的规律。他将所有纹饰分为A、B、C三组;A组较图形化,包括饕餮头、饕餮身、牛状饕餮、蝉纹、竖龙纹和素面6种;B组较抽象化,包括分解饕餮、三叠动物带纹、分尾鸟纹、有目螺旋纹带、有目斜角纹带、联珠纹带、云雷纹、复合菱形纹、乳钉纹和蕉叶纹等11种;C组常见于次要部位,包括变形饕餮纹和龙形化饕餮纹,以及各种象鼻、鸟喙、张腭、顾首、加羽、有翼、S形和变形的龙纹、鸟纹、蛇纹、涡纹、叶片纹和螺旋纹带等16种。虽然这种分类并不是单单针对饕餮纹,但却无疑是饕餮纹类型说最重要的开篇之作。
高本汉(B.Kalgren)将这些组合又按一定的模式与商代及周代早期的器物联系在一起,以统计学研究的证据说明A组和B组不共存的原则是普遍的,即A组和B组分别可以和C组共见,而AB之间却是相互抵触的。至于饕餮纹,他认为A1-A3是真正的原生型式,B1是派生的,它们的变化是由A组饕餮头、饕餮身演变为C组的变形饕餮、龙形化饕餮,最后再变化为B组的分解饕餮。但高本汉(B.Kalgren)之说却存在着一个并不正确的前提:饕餮纹一定是由写实化过渡到抽象化。而且,他所使用的材料极为庞杂,有的甚至还是流行于文物市场的赝品,所以难免有许多主观上的臆断。这一点,艺术史学家戴维森早在1937年便曾提出过批评:高本汉(B.Kalgren)把两种不同的抽象化混合在一起,如其B1分解饕餮实际上就是二里冈期饕餮纹)和B2三叠动物纹带,便是一早一晚(注:J·Leroy·Davidson:《中国古人青铜器分组试探》Parnassus 9.4(1937年4月)页29-34,转引于艾兰(S.Allan):《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26。)。
与高本汉(B.Kalgren)的学说建立在各种纹饰的统计分析与写实先于抽象的前提上相反的是罗越(M.loehr)的学说。罗越(M.loehr)所依据的材料主要属于商代以及安阳出土的青铜器。他的分析也不仅仅依靠孤立的因素或纹饰,而是依据器物的总体特征、形状、装饰(纹饰的组成、形状及排列)和工艺特征(注:参考张光直:《商代文明》页28,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并且他也没有依靠考古学或铭文的材料,而是完全以艺术史的标准,成功地建立了殷商青铜器五种型式先后相承的序列:型式1由平面上的细线浮雕构成,纹饰呈带状,常缘以成行的联珠纹,纹饰含有斜线、弧线,缀以卵形的目;型式2与型式1的区别是花纹为阴线;型式3纹饰细密流畅,比前期更曲线化,花纹不再限于带状而扩充到器面,在饕餮的体上有竖立勾线的立羽;型式4中,饕餮的轮廓清楚,与衬地分开,雷纹地出现,但花纹仍与器表相平;型式5的花纹已自地纹上凸起,轮廓鲜明,略有简化而布局严整(注:罗越(M.loehr):《安阳时期的青铜器》“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美国中国艺术学会集刊》7(1953年)页42-53,参考艾兰(S.Allan)《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28,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罗越(M.loehr)有关前三式应居先的推论随即被郑州、辉县发掘成果的公布所证实,使得此说大为盛行。但这种单线发展论导致了将种种型式变化归结为序列先后的问题,有些过于简单化与机械化。正如沃森所批评的,饕餮纹中的种种浮雕花纹,就不能以单线发展说来解释(注:沃森:《商代的五个阶段》,罗越(M.loehr)《中国青铜器时代的礼器》书评,《艺术新闻》67.7(1968年11月)页42-47、页62-64,参考艾兰(S.Allan):《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28,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随着中国国内考古学的不断发展,这种以类型学为方法的纹饰研究在国内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其始作俑者且影响深远者为容庚。他在《商周彝器通考》(注:容庚(希白):《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的花纹一章中,详细罗列了青铜器上的各种纹饰并附图说明,他把饕餮纹区分为饕餮纹和蕉叶饕餮纹两类,前者有16种不同的型式,后者有3种型式,合计19种。后来他觉得这种分类过于繁琐,有必要进一步加以整理,遂在《殷周青铜器通论》中加以合并与简化,分为12种类型:1、有鼻有目,裂口巨眉;2、有身如尾下卷,口旁有足,纹中多间以雷纹;3、两眉直立;4、有首无身,两旁填以夔纹;5、眉鼻口皆作雷纹;6、两旁填以刀形;7、两旁无纹饰,眉作兽形;8、眉往上卷;9、身作两歧,下歧往上卷;10、身作三列,全作雷纹,上列为刀形,下二列为雷纹;11、身中一脊,上为刀形,下作钩形;12、身只一足,尾向上卷,合为饕餮纹,分则为夔纹(注:容庚、张维持:《殷商青铜器通论》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二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此后,李济先生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工作,他从51件有纹饰的青铜器上举出9种不同形式的饕餮纹和36种不同形式的连体饕餮纹,以代表殷墟青铜器上所见的各种不同的饕餮纹(注: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插图二十九——三十二,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2年。)。
但是此类研究过多侧重于纹饰的差异性,在区分时没有找到固定而统一的标准,使其分类过于纷乱而难以继续深入到饕餮纹源流、内涵及其背后宗教思想方面的研究。对此,笔者认为应该着眼于纹饰宏观的共性,避免许多次要的、随机性较强的装饰性纹饰对分类标准的混淆。具体而言,作为青铜礼器的主要纹饰,能称之为形态代表性特征的应该是承载着宗教文化意义的符号,而不是一些装饰性的花纹,它们之间存在着主与次的差别,那么这两者在分类的过程中应该加以区别对待。比如说饕餮纹的眼睛和角与作为衬地的云雷纹就不能同等对待,不能将它们作为同一级的分类标准。如果我们将前者称为主体纹,后者称为装饰纹,那么前者代表的是饕餮纹的思想及文化功能上的意义,而后者则仅仅是一种艺术史上纯粹的风格因素。我们在具体分类的过程中应该充分注意到这种标准等级的差别,因为每一个标准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然容庚、李济等却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继容庚、李济之后,马承源先生在饕餮纹的分类上开始注意到这种区分标准统一的问题。他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饕餮纹的分类中便以角为主要标准,将它们划分为:环柱角型兽面纹、牛角型兽面纹、外卷角型兽面纹、羊角型兽面纹、内卷角型兽面纹、曲折角型兽面纹、双龙角型兽面纹、长颈鹿角型兽面纹、虎头型兽面纹、熊头型兽面纹、龙蛇型兽面纹(注:前揭《中国青铜器》页328(注:此处兽面纹即饕餮纹)。)。此说较之容李在分类标准上获得了较大的统一性,但却没有顾及饕餮纹的身、目等重要因素,没有将饕餮纹三个主体形态综合在一起考虑,使之有失于片面。类似的如林巳奈夫在《殷周青铜器纹饰之研究》中的分类,也同样以角为第一级的标准,将饕餮纹分13类,似较之其他各种分类更为繁复(注:转引于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究其原因,仍然是没有注重纹饰各个部位在功能上可能具有的共性以及它们在宏观角度上所具有的形态的相似性。
另外,在饕餮纹类型说上值得注意的还有近年陈公柔、张长寿二位先生在《殷周青铜器容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中的分类。他们以饕餮头与身的关系为主要区分标准,将这种纹饰分为独立兽面纹、歧尾兽面纹、连体兽面纹和分解兽面纹四型,其中第一型下分12式,第二型下分6式,第三型下分16式,第四型下分6式(注:此中兽面纹即饕餮纹,转引于陈公柔、张长寿:《殷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断代研究》,《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但这种分类的主要目的是以纹饰艺术的流变过程来确定青铜器断代的标准,对于饕餮纹本身在源流、内涵及意旨等方面的研究仍然显得缺乏指向性而过于杂乱,缺乏深入研究的有效性。
(四)饕餮纹“内涵说”
饕餮纹代表了什么?商人为什么会在青铜礼器上大量使用它?它身上蕴涵了商代历史怎样的面貌?它用那种炯然的眼神到底向我们暗示着怎样的一种信息?从一定意义上说,饕餮纹“内涵说”是构成饕餮纹研究的整个价值指向的核心,也是饕餮纹研究的终极目标——它是怎样记录和传承历史的。如果我们沿着这种思路深入下去就会进而发现,早在战国时期,这种纹饰被名为“饕餮”,其本身就是《吕氏春秋》作者对纹饰内涵的一种诠释。也就是说,这种纹饰真正的意旨在历史的消亡中逐渐地被淡化以致被遗忘,当人们重新关注它时,首先便会去探寻在它的表面形式下所蕴涵的符号意义。
但是这种探寻因为文献的不可信,也因为其本身面貌的神秘多变而显得扑朔迷离,直至今日仍是众说纷纭,难以统一。现将各种学说总结归纳,大致存在着以下几种认识:
1、将饕餮纹视为某种单个再现性的动物形象。持此类观点的学者多以一个具体的动物形象来作为饕餮纹概念的阐释内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将它视为牛首,这可能源于很多饕餮纹在形式表象上具有牛头的特征。李泽厚便明言:“……本书基本意它是牛头纹……”(注:前揭《美的历程》第二章“青铜饕餮”,见《美学三书》页43。);韩湖初亦言:“……但在笔者看来,从神情和形貌上看更像牛……”“……可见饕餮一族是以牛为图腾的炎帝族的后代……”(注:韩湖初:《略论青铜饕餮的“狰狞美”》,《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4期。)。此外,还有很多学者或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这一看法,如顾立雅(H.G.Greel)在《中国的诞生》中也将饕餮等同于水牛(注:H·G·Greel:Birth ofchina-New York,UNGAR 1937,p117。);亨采(C.Hentze)在他的《月的神话和象征》中也倾向于饕餮为牛头的看法,并由牛角因形曲而代表月推断饕餮也是月神,代表着死亡和黑暗,是光明与生命的解放者(注:前揭《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31。)。除了牛首之外,还有较多学者倾向于饕餮是虎头的观点,这可能一方面源于饕餮纹狞厉如猛兽的视觉效果,另一方面可能是受张光直先生以萨满教来解释“乳虎食人卣”的著名论断的影响。持此观点者如冯其庸认为“它的面部是猛兽头部(我认为主要是虎头)的理想化的美术化”(注:冯其庸:《良渚玉器上神人兽面图形的内涵及其衍变》,《中国文化》1991年12月第5期。);另如弗罗伦丝·瓦特培里(F.Water-bury)在《中国象征文学》中也把它说成是虎(注:前揭《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21,《山海经.北次二经》中郭璞注语,原句为:“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钩吾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铜。有兽焉,其状如羊身,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枭,是食人。”),而他在《古代中国的符号和文献:遗迹与推想》中亦称饕餮是虎,并进而认为它代表着日神,具有驱邪及保护农业生产的作用(注:Frorance Waterbury:Early Chinese Symbols And Literature:Vestiges And Speculations,Published By E.Weyhe,New York City,1942.)。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将它解释为羊首、鹿首等,可谓众说纷纭。如丁山在《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中认为:“宋以来所谓‘饕餮纹’,那是人面环角的羊头,名为‘枭羊’可也,名为‘苋羊’可也;它是公直无私、敢于阻击凶邪的吉祥大神。”(注: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页281-296,龙门联合书局,1961年。)但是这类观点都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它们大都属于不完全范围中的推测,无法涵盖全部饕餮纹所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兽面特征,故而是不可取的,也即饕餮纹绝对不可能是某一种动物形象的再现。
2、将饕餮纹视为两个对称性的组合动物或立体动物形象,此类观点源于饕餮纹对称性的组成部分各自具有的一种表象性,即很多饕餮纹在视觉上仿佛是由两个独立的个体动物面部相对而成。持此说者并未直接用以解释饕餮纹的内涵,更多的是在形式的分析中加以暗示,如张光直先生曾言:“合观之则为饕餮纹,分观之则为夔纹者”(注:张光直:《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亦有直言者,如邱瑞中曾明言:“饕餮纹到底是什么?……其实,它是彼时的龙纹对首产生的动物面孔。立体地观察它,正是那个时代的龙纹之立体形态的平面展示图……”(注:邱瑞中:《商周饕餮纹更名立体龙首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4期。)。这里,邱瑞中的观点已由两物对称构成饕餮纹过渡到将其整体看作一种立体纹饰。他所谓的“平面展示图”,说白了就是把动物头正面留下,把后面的身子一剖为二,拉开使之与面部处于同一个平面上。这种表现方法被马承源先生称为“整体展开法”:“兽面纹既表现为动物正面的形象,同时也是表现物体的两个侧面,我们称这两种结合的方法为整体展开法”(注: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但这种观点在两方面无法自圆其说:一者,商人有没有这样的平面立体思维能力?即使有,他们又为何要使用这种方式来表现礼器圣物上的动物形象?二者,饕餮纹除了此类图案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纯平面化的面部表现形象,“对称”与“立体”显然不能诠释全部饕餮纹的内涵与意义。
3、基于饕餮纹各类形象的差异性,有学者认为它绝对不会是某一种动物的形象,而应该是多种兽面的综合,或者干脆就是一种现实中不存在的神话动物。前者突出代表如马承源先生,主张改“饕餮纹”为“兽面纹”(注:详见上文“饕餮纹名实考”一节。);后者如休果·曼斯波格(H.Mun-sterberg)在《中国古代艺术里的象征主义》中,经过大量对饕餮纹诠释的讨论后提出饕餮纹是一种“神话动物”(注:Hugo Munsterberg:Symbolism in ancient-chinese art,New York.Hacker 1986.)。然而,由于饕餮纹的形象并没有相对的固定性,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所以以兽面综合或神话动物作为饕餮纹的内涵就面临着一种逻辑上的困惑:产生这种艺术形式多发性的原因何在?也即这种分析缺乏将饕餮纹放置在整个商代文化的背景中阐释其发生的心理性因素,从而难以明晰饕餮纹在当时的社会功能,忽略了作为文化意义存在的饕餮纹。
4、针对饕餮纹所具有的文化意义,亦有学者否认饕餮纹是任何一种动物性形象的再现,无论它是单个性的动物、还是动物的综合、抑或神话中的动物。如艾兰(S.Allan)教授认为“……我们说这些青铜礼器的饰纹创造出一种‘另一个’世界的意味。它不受我们这个世界物质真实性的限制,也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艾兰先生的观点侧重于饕餮纹的文化性的饰纹母体,她进而认为:“……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商代的饰纹并不是从挑选所要再现的动物开始的,每一件器物的饰纹都是创作,从以前的形式演化而来,但又经过变形,赋予了它新的形象和形式。……”(注:前揭《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12。);也还有学者如左丹·派泊(J.Paper)认为饕餮纹是一个萨满教面具的再现(注:Jordan Paper:The meaning of"tao-tieh",History of religions 1978.),而江伊莉也认为饕餮纹是萨满教面具,并强调面具带有精灵变形的意味(注:江伊莉:《商代礼仪艺术中的祖先神与兽面》,1987年9月10-16日在安阳举行的“国际商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
此类观点对于诠释饕餮纹宗教文化性功能无疑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但忽略了它与动物形象的相似性,避而不谈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是不可取的,甚至再进而推导它为某种宗教的祭祀工具,则更显得缺乏证据与可信度。
5、否认饕餮纹具有任何方面的内涵,无论是形象上的再现性还是文化上的反映性。这类观点显然是对饕餮纹的一种虚无化的认识,将它从文化史乃至艺术史中剥离成为一种纯粹的图像形式。此说首要倡导者是罗越(M.loehr),他认为“如果商代青铜器上的纹饰从来就是纯粹的图案,由图形到图形,是与显示无关或者至多是现实的模糊暗示的结构,那么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种纹饰没有任何确定的意义——宗教的、宇宙的、神话学的,以及任何见诸文献的哪种意义。”罗越(M.loehr)的学生也继承了他的这一观点,最突出者如沃伯·白戈立(W.Bagley)曾声称:“饕餮纹虽然暗示出动物的世界,但它不是真正的图画,画幅的线条安排变化不定,无法确定固定的形象……换句话说,这些青铜器的制造者不是把某种动物视觉化,也不是在一个背景上描绘动物的轮廓剪影。”“纹饰的历史表明,商代的花纹是一种纯粹的图案艺术,各个母题并无特殊的象征性。晚期的龙纹和饕餮纹的变幻莫测,看来就证实了罗越(M.loehr)首先提出的这一观点”(注:前揭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页230。)。这种观点侧重于饕餮纹形式发展的图案性,对于理解纹饰本身的形式演变有着一定的好处,罗越(M.loehr)本人的“五型发展说”即为这种思想产生的最为突出的成果。但,这一思想显然与商人重祀的风俗相背,因为如果饕餮纹是无意义的,那么对祭祀如此虔诚的商人为何要在祭器上大量重复地使用这种纹饰而不采用其他的形态呢?
总而论之,上述观点也许并不能包含所有现在有关饕餮纹研究的成果,但却基本上是这一课题现行研究的主要状况。这些论述在一定意义上都有自圆其说的合理性,但从整体上考察却都不完善,或是臆断的因素较大,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以期得出更为合理而全面的结论。
标签:饕餮论文; 青铜器论文; 窃曲纹论文; 肥遗论文; 考古论文; 文物论文; 商周彝器通考论文; 考古学报论文; 吕氏春秋论文; 四部丛刊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