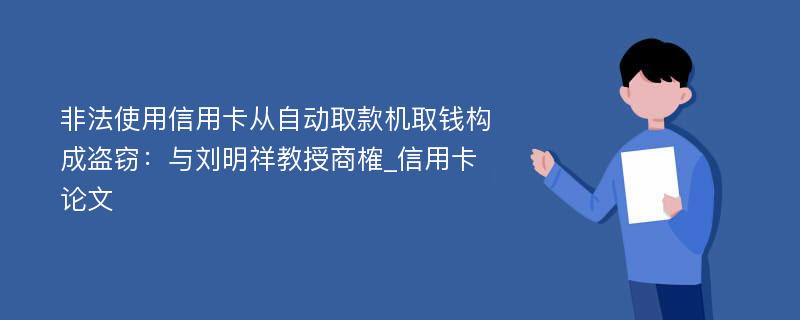
非法使用信用卡在ATM机取款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再与刘明祥教授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盗窃罪论文,卡在论文,教授论文,信用论文,ATM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笔者在《清华法学》2008年第1期发表了《也论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性质》一文(以下简称《也论》),对刘明祥教授所主张的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取款的行为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刘明祥教授的《再论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性质》一文(以下简称刘文),依然主张用信用卡(包含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成立信用卡诈骗罪。①本文按照刘文的结构与顺序,对刘文的观点与理由,再次予以商榷。
一、“机器不能被骗不妨碍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的观点难以成立
刘文承认,机器不能被骗,但同时认为,“由于机器是按人的意志来行事的,机器背后的人可能受骗”,所以,机器不能被骗并不意味着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不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其解释根据正是德国、日本刑法关于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规定,亦即,在德国,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可能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这就意味着机器不能被骗并不妨碍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成立,同样的行为在我国也应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此外,刘明祥教授有时还引用瑞典刑法的规定,②说明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构成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由此看来,笔者仍有必要再次分析国外刑法的相关规定。
利用包括ATM机在内的计算机非法“取得”他人财物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又由于诈骗罪的受骗者只能是一定的自然人(如不包括儿童与严重精神病患者),且大陆法系国家刑法规定的盗窃对象仅限于普通财物,而不包括财产性利益,便出现了处罚上的空隙。于是,出现了两种立法例。
第一种立法例是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如《德国刑法》第263条a、《日本刑法》第246条之二、《韩国刑法》第347条之二。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当然不要求自然人受骗,否则就丧失了增设此罪的意义。刘文指出:“在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刑法中,都有计算机诈骗(或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规定,立法者和学者们也并不因为其中有‘诈骗’二字,就要求其与普通诈骗罪一样,必须有自然人直接受骗和自然人直接交付财物。”然而,第一,笔者在《也论》中就指出,德国、日本等国刑法虽然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纳入广义的诈骗罪,但其对构成要件的表述,并没有使用“诈骗”、“欺骗他人”等表述,只是罪名中有“诈骗”二字(国外的罪名不一定是法定的)。可是,对构成要件的解释不是以罪名为根据的,而应以罪状为根据。况且,也有学者不采用“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罪名。③第二,德国、日本刑法关于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表述与我国《刑法》第196条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表述,并不相同。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表述的内容是向处理财产事务的计算机输入不当指令,而后者依然要求进行“诈骗”活动。而且,《刑法》第196条所属的刑法分则第三章第五节的标题就是“金融诈骗罪”。根据体系解释的要求,“如果某个法律章节的内容受其标题的限制,则该章节中的某种规定亦受此限制。”④刘文却无视这一点。第三,笔者不得不重复说明的是,德国、日本刑法规定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本质上是处罚迄当时为止只能作为盗窃利益而不可罚的行为”;⑤是将“盗窃利益的一定的情形类型化了”;⑥是“为了避免一般性地处罚盗窃利益、侵占利益的事态”。⑦所以,强调德国、日本刑法中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属于诈骗性质,是只看到了表面现象;认为德国、日本刑法对使用计算机诈骗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使用了“诈骗”一词,并不符合事实;认为德国、日本学者“并不因为其中有‘诈骗’二字,就要求有自然人直接受骗和自然人直接交付财物”的说法,更难以成立。相反,德国、日本刑法理论之所以不要求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成立以自然人受骗为前提,正是因为其对构成要件的描述没有使用“诈骗”一词。
第二种立法例是设置拟制规定。例如,《瑞典刑法》第9章第1条第2款规定:“输入不正确或不完整的信息,或者修改程序或记录,或者使用其他手段非法影响自动数据处理或其他类似自动处理的结果,致使行为人获利而他人受损的,也以诈欺罪论处。”但是,这些规定也不能说明在我国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成立信用卡诈骗罪。
《瑞典刑法》第9章第1条第1款规定:“欺骗某人为或不为某行为,致使被害人获利而被欺骗或其代表的人受损的,以诈欺罪处2年以下监禁。”显然,只有“某人”可以成为诈欺罪的对象。正是因为机器不能成为诈欺罪的对象,而诈欺机器取得利益的行为不成立盗窃罪(《瑞典刑法》第8章第1条规定,盗窃罪的对象仅限于财物),所以存在处罚上的空隙,于是《瑞典刑法》第9章第1条第2款将向机器输入不当指令而获利的行为,拟制为诈欺罪。根据瑞典刑法的规定,倘若没有第9章第1条第2款,对于向机器输入不当指令而获利的行为,是不可能成立诈欺罪的。换言之,如若没有第9章第1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向机器输入不当指令而获利的行为,也能认定为诈欺罪,《瑞典刑法》就没有必要在1986年增加第9章第1条第2款。不难看出,《瑞典刑法》第9章第1条第2款是一种拟制规定。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诈骗罪的构造决定了其欺骗的对方必须是自然人。但是,我国刑法并没有像《瑞典刑法》第9章第1条第2款那样规定,既然如此,就不能将《瑞典刑法》第9章第1条第2款的规定,适用于我国。如同没有规定事后抢劫罪的国家,不能按照我国《刑法》第269条处理案件一样。概言之,以外国刑法中的拟制规定为根据,认为在我国机器可以被骗,或者认为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不要求欺骗自然人,是不合适的。
刘文虽然承认机器不能被骗,但强调信用卡诈骗罪不同于诈骗罪,所以,认为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行为,即使没有欺骗自然人,也不妨碍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刘文指出:“我国刑法第196条对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中确实有‘诈骗’二字,但不能由此得出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必须要有‘受骗的自然人’的结论。因为张文忽视了这里的‘诈骗’之前还有‘信用卡’这一限定语,即该条所说的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而不是进行一般的诈骗活动。”但是,第一,既然《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是“诈骗”,其中的“诈骗”当然与《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的含义相同。这是因为,根据体系解释的原理,“如果法律在不同的地方采用相同的概念与规定,则应认为这些概念与规定实际上是一致的。有疑义时某项概念的内容则与另一处的相同。”⑧刘文也承认《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要求有受骗的自然人,这一点没有疑问是正确的。从学界的争论局面来看,《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是否必须有受骗的自然人,则是有疑问的。既然如此,就需要按照《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来理解《刑法》第196条的诈骗。第二,《刑法》第196条规定的“诈骗”,不仅表明信用卡诈骗罪的诈骗性质,而且从其规定方式来看,要求其所列举的四种类型都必须是“诈骗活动”。既然诈骗活动需要欺骗自然人,那么,取消这一要件就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第三,“信用卡”只是“诈骗”的限定语,是对诈骗的限定,意味着要求利用信用卡诈骗,而不意味着可以不欺骗自然人,更不意味着只要非法使用信用卡就属于诈骗。换言之,信用卡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是否欺骗自然人,而在于是否非法使用信用卡欺骗自然人。显然不能因为限定语是“信用卡”,就不要求欺骗自然人。如同“诈骗”与“合同诈骗”一样,不能因为合同是限定语,就不要求行为人欺骗自然人;如同“杀人”与“使用计算机杀人”一样,不能因为使用计算机是限定语,就不要求行为人所杀的是人。第四,正如刘文所言,“对‘信用卡诈骗’不能与普通‘诈骗’作完全相同的要求”,但这只是意味着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要求行为人非法使用信用卡,而不意味着信用卡诈骗罪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普通诈骗罪不同。
读者会发现,刘明祥教授不仅按照德国、日本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解释我国的信用卡诈骗罪,而且还将德国刑法规定的滥用信用卡罪(其中的部分情形)也包含在我国的信用卡诈骗罪之中。但其理由与结论,难以被人接受。
第一,刘文指出:“我国《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中包含有部分不具有诈骗性质的滥用信用卡行为。”但是,信用卡诈骗罪怎么能包含不具有诈骗性质的行为呢?认为一个犯罪类型同时包含具有诈骗性质和不具有诈骗性质的行为,是否导致犯罪类型的丧失?
第二,根据笔者的观点,即使恶意透支型的信用卡诈骗罪,也必须具备诈骗罪的构造,即受欺骗的自然人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财物。刘文针对笔者的观点指出:“我国有不同于日本的国情。在我国,用信用卡可以在ATM机上透支,如果是从ATM机取款恶意透支,自然不具有诈骗的性质(张文也持此看法)。但在日本,一般不能用信用卡(有透支功能的信用卡)从ATM机取款透支,只能在特约商户用信用卡购物或消费。至于恶意用自己的信用卡在特约商户购物或消费,大量透支后不归还透支款项,日本的判例和通说之所以将这种情形解释为构成诈骗罪,是因为日本刑法没有像德国等国刑法那样规定滥用信用卡罪,对恶意透支这种典型的滥用信用卡的行为不当犯罪处理不合适,要当犯罪处理就只能在解释上做文章,因而将恶意透支解释为诈骗,为处罚这种行为找出路。”但是,刘文的说法存在疑问。一方面,即使在日本,具有透支功能的信用卡,也可以从ATM机上透支,就此而言,与我国没有区别。⑨另一方面,在日本,并不是将任何恶意透支行为都解释为诈骗罪,只是将欺骗自然人的恶意透支解释为诈骗罪;从ATM机中恶意透支的,当然成立盗窃罪。这是因为两种行为完全分别符合诈骗罪与盗窃罪的要件。即使日本的这种解释与其刑法没有规定滥用信用卡罪有关,也不能认为这种解释存在任何缺陷。
第三,德国刑法是否规定以及如何规定滥用信用卡罪,不影响我国应当如何解释信用卡诈骗罪。对案件事实的归纳应当以本国法定的构成要件为指导,但刘文却习惯于以德国的滥用信用卡罪的构成要件为指导,将原本在我国、日本属于盗窃的案件归纳为“滥用信用卡”,再将滥用信用卡的行为解释为信用卡诈骗罪。这似乎存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换言之,不能因为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滥用信用卡罪,就将德国刑法所规定的滥用信用卡罪的行为解释到我国的信用卡诈骗罪中去。如同德国、日本刑法都规定了背任罪而我国没有规定,但不能据此将背任罪的行为都解释到财产罪中一样。刘文一方面接受“德国学者普遍认为恶意透支不存在诈骗问题”的观念,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我国恶意透支是信用卡“诈骗”,有时又说“如果是从ATM机取款恶意透支,自然是不具有诈骗的性质”。言下之意,恶意透支不是诈骗,而我国《刑法》第196条将恶意透支规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类型,所以《刑法》第196条所规定的不是诈骗罪。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刘文对于德国、日本刑法中没有使用“诈骗”一词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强调其诈骗性质,而对于我国刑法明文使用“诈骗”一词的信用卡诈骗罪,反而否认其诈骗性质?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德国学者普遍认为恶意透支不存在诈骗问题”,我国《刑法》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就不要求欺骗自然人?
第四,在德国刑法将恶意透支规定到滥用信用卡罪中之后,恶意透支或许不存在诈骗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恶意透支中既可能存在两者间诈骗(如隐瞒不归还的意图,在发卡银行柜台透支),也可能存在三角诈骗(如隐瞒不归还的意图,在非发卡银行柜台透支或者在特约商户购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在ATM机上透支的行为,当然也是诈骗。其实,德国也并非普遍认为恶意透支不存在诈骗问题,只是对部分恶意透支案件否认其诈骗性质。⑩笔者也可以认为,倘若恶意透支不存在诈骗性质时,就不能适用《刑法》第196条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只能认定为盗窃罪。
第五,按照刘文的观点,日本的学说与判例,是因为其刑法没有规定滥用信用卡罪,才将欺骗自然人的恶意透支解释为诈骗罪,将没有欺骗人而在ATM机上恶意透支的行为解释为盗窃罪。可是,我国刑法也没有规定滥用信用卡罪,既然如此,我们也应当将欺骗自然人的恶意透支解释为信用卡诈骗罪,将没有欺骗自然人而在ATM机上恶意透支的行为解释为盗窃罪,而不是将盗窃行为也解释到信用卡诈骗罪中去。
第六,诚然,“用自己真实有效的信用卡在ATM机上透支,已成为信用卡的一种很普遍的使用方式,这种形式的恶意透支也很常见”。但这并不能成为将这种行为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理由。因为本文也可以这样说:“用自己真实有效的信用卡在ATM机上透支,已成为信用卡的一种很普遍的使用方式,这种形式的恶意透支也很常见,应以盗窃罪论处。”
刘文认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自己的信用卡在银行柜台让业务员刷卡提取现金交给自己,与自己用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这两种不同形式的恶意透支也很难说在性质上有何差异,但按张文的观点却要分别定信用卡诈骗和盗窃两种不同的罪名,这也很难说具有合理性。”就侵犯财产而言,二者当然没有差异,但是,就是否欺骗了自然人而言,因而就犯罪类型而言,二者就存在根本差异。在我国,犯罪构成是犯罪类型,既然行为人实施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为,当然应认定为两种不同的罪名。在此没有不合理之处。盗窃罪与诈骗罪是两种传统的犯罪类型。行为人在盗窃时使用何种工具或手段,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同样,行为人在诈骗时使用何种工具或手段,不影响诈骗罪的成立;二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否实施了足以使对方产生处分财产的认识错误的欺骗行为,对方是否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产。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既可能利用信用卡实施诈骗行为,也可以利用信用卡犯盗窃罪。但是,按照刘文逻辑,只要使用信用卡的,就不可能成立盗窃罪了,只能是信用卡诈骗罪或者无罪。这是本文难以同意的。
刘文反复强调“ATM机的特殊属性”,认为ATM机“在法律地位上相当于一个电子营业员”,于是,“在ATM机上恶意透支存在作为电子营业员的ATM机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的问题”,具备交付罪的特征,与直接夺取他人占有财物的盗窃罪不同,因而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在本文看来,刘文对交付罪在一定程度上做了片面理解。第一,ATM机的“特殊属性”是什么?在什么“法律地位”上相当于一个电子营业员?“电子营业员”究竟是机器还是自然人?“相当于”又是什么含义?这可以由刘明祥教授事后任意做出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解释。第二,是任何机器都可以向行为人交付财物,还是只有作为电子营业员的ATM机才能向行为人交付财物?倘若是前者,那么,行为人向自动贩卖机投放铁币后,自动贩卖机吐出饮料时,自动贩卖机是否也在向行为人交付财物,从而使行为人的行为成立诈骗罪?倘若是后者,为什么又只有作为电子营业员的ATM机才能向行为人交付财物?第三,在诈骗罪中,交付是指被骗者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而不是单纯地吐出现金、递交财物。这也是刘明祥教授接受的观点。(11)然而,ATM机不存在所谓认识错误问题,只要程序操作得当和密码正确,就可能从ATM机中取出现金;反之,即使持卡人将其真实有效的信用卡插入ATM机中,但只要其程序操作不当或者密码错误,也不可能取出现金。所以,ATM机吐出现金,不等于财产罪中被害人的交付行为。另一方面,在盗窃罪中,客观上也可能存在交付的情形。因为完全存在利用被害人的间接正犯的盗窃罪,换言之,被害人没有处分意识时,客观上也可能交付财物,但在这种情形下,行为人只能成立盗窃罪,而非成立诈骗罪。例如,行为人将一包糖给3岁女孩,要换取女孩的项链;女孩将项链“交付”给行为人时,行为人依然成立盗窃罪,而不是成立诈骗罪。所以,仅凭客观、外表上有无“交付”行为来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是不合适的。换言之,诈骗犯罪中的被害人的交付,是以受骗为前提的。既然刘文承认机器不可能受骗,就不应该主张机器有交付行为。
笔者主张信用卡诈骗罪以欺骗自然人为前提,所以,认为将《刑法》第196条中的“冒用”、“使用”解释为对人的冒用、使用。刘文对笔者的批评意见,难以被笔者接受。
第一,刘文认为,盗窃也可能是冒领,因而“冒用”不意味着欺骗自然人,“使用”是中性词,无疑可能在ATM机上恶意“使用”。可是,刘文突然“冒”出一个并非属于法律概念的“冒领”来说明“冒用”的含义,这是不合适的。即使“冒领”不需要欺骗自然人,也不意味着《刑法》第196条的“冒用”不需要欺骗自然人。冒领并非法律术语,它与冒用也非等同含义。刘文举例说:“甲将提包寄存在存包处,服务员给其一张领取牌;或者是甲将提包存放在一自动存物柜,得到一张领取牌。后来无论是甲自己领取,还是将领取牌交给乙去代领,或者是丙窃取甲的领取牌去冒领、丁拾得甲的领取牌后冒领,都不存在要根据有无自然人受骗来确定其是否冒领的问题。”显然,在刘文设定的这几例中,行为人并不都构成诈骗罪,也不都构成盗窃罪。但这并不成为刘文结论的理由。因为笔者通过上述之例也可以说明:“冒”的行为可以构成盗窃罪,故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也可能成立盗窃罪。即使从字面含义上看,行为人“是在特约商户购物消费使用,还是在ATM机上提取现金,都在‘冒用’之列”,也有理由将在ATM机上使用的行为排除在外。因为刑法条文的字面含义,不等于刑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分则条文的文字表述不等于构成要件,构成要件是经由解释才形成的犯罪类型。盗窃与诈骗之所以成为两种不同类型,就是因为前者需要欺骗自然人,后者不需要欺骗自然人。
第二,笔者之所以一方面说《刑法》第196条中的“冒用”、“使用”一词本身就包含了欺骗的含义,另一方面又说将该条中的“冒用”、“使用”解释为对人的冒用、使用是一种限制解释,一是因为以刘明祥教授为代表的观点,将冒用、使用作了过于宽泛的解释,为了限制这种过于宽泛的解释,而对冒用、使用的含义进行了限制;二是就“使用”而言,将其解释为仅对自然人使用,当然是一种限制解释;三是旨在说明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因而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刘文指出:“如果对‘冒用’、‘使用’作张文所主张的限制解释(即采取盗窃罪说),不仅在定罪上存在问题,而且还可能造成处罚上的明显失衡。例如,某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知悉密码后,到ATM机上取款10万元,按张文的主张定盗窃罪,那就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依照《刑法》第264条的规定,应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如果他是到银行柜台刷卡后由银行工作人员交给他10万元,那就应当定信用卡诈骗罪,属于诈骗数额巨大的情形,依照《刑法》第196条的规定,应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两相比较,可谓天壤之别。既然作上述限制解释无论在定罪和处罚上都有这些明显的缺陷,其合理性何在?”套用刘文的话说,刘文对笔者的观点也存在误解。不可否认,根据笔者的观点,某人拾得他人信用卡并知悉密码后,到ATM机上取款10万元,成立盗窃罪,也属于盗窃金融机构,但并不必然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情形。刘明祥教授当然会说,根据司法解释规定,盗窃10万元已经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可是,一方面,司法解释并未明文对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作解释;(12)另一方面,即使盗窃10万元属于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也只是司法解释,而不是立法规定;此外,即便认定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也可以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减轻处罚,不可认为适用该款就是异常现象。
第三,刘文针对笔者的观点指出:“将《刑法》第196条中的‘冒用’、‘使用’解释为仅仅是指对自然人的冒用、使用,这是一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解释。”因为“特别是当某人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轻罪的成立条件时,但司法者却对轻罪的成立条件作限制解释,将其行为排除在外而适用重罪的法条来处罚,这显然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也是我国刑法所禁止的。”诚然,如果对消极的构成要件要素和有利于被告人的减免处罚的适用条件作限制解释,可能(但不是必然)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轻罪的构成要件都不能作限制解释,更不意味着对轻罪的构成要件作限制解释就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况且,对轻罪的构成要件作限制解释,也不意味着原本符合轻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一定构成重罪。不可否认,按照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刘文的观点在部分情形下会导致对被告人较轻的处罚。但是,这并不意味只要解释结论对被告人有利就是合理的。换言之,有利于被告不是刑法解释原则;存疑时有利于被告(In dubio pro reo)也仅适用于事实存在合理疑问的场合;当法律存在疑问或争议时,应当依一般的法律解释原则消除疑问,而非一概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13)法律上的疑问是需要解释来消除的。人们在对某个法条进行解释时,可能同时使用多种方法,也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方法,而目的都是为了追求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当各种解释方法得出不同的解释结论时,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目的论解释,而不是有利于被告。“因此当法律问题有争议时,依一般的法律解释之原则应对被告为不利之决定时,法院亦应从此见解。”(14)倘若对被告人处罚轻的解释结论就是合理的,那么,刘文为什么不主张将使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认定为侵占罪呢?
刘文不承认,《刑法》第196条相对于《刑法》第266条而言是特别条款,也否认《刑法》第196条是补充条款,似乎认为二者是交叉竞合,并认为二者的关系如同招摇撞骗罪与普通诈骗罪的关系。本文认为,刘文的辩解与观点难以成立。
第一,《刑法》第196条与第266条是什么关系,取决于如何解释第196条。如果认为只有欺骗自然人才成立信用卡诈骗罪,二者当然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刘文指出:“大多只有用信用卡对自然人行骗,才可能出现同时符合第266条与第196条规定的法条竞合现象。由于规定用信用卡这种特定的手段骗取财物的法条,相对于规定普通诈骗罪的法条是特别法条,因而要适用该法条来定罪量刑。至于采取不完全具备普通诈骗罪构成要件的方式进行的信用卡诈骗活动,如恶意透支、用信用卡从ATM机恶意取款,则不存在同时构成普通诈骗罪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选择适用哪一法条的法条竞合现象,无疑是要按信用卡诈骗罪来定罪处罚。”不难看出,一方面,刘文承认了在欺骗自然人时,《刑法》第196条与第266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当然要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另一方面,在没有欺骗自然人时,即使符合其他罪的构成要件,也要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于是,《刑法》第196条成为特权条款,即无论如何,只要行为人非法使用信用卡取得财物,都必须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可是,交叉关系时(不管是交互竞合还是偏一竞合)所采取的处理原则,是重法条优于轻法条,(15)而不是刘文所称的只能按其中某个特定的条款处罚。当然,也许刘明祥教授会认为,其所称“恶意透支、用信用卡从ATM机恶意取款”不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存在竞合问题。可是,在刑法增设信用卡诈骗罪之前,对于使用他人信用卡在ATM机中取款的行为都认定为盗窃罪,为什么在刑法增设了信用卡诈骗罪之后,这种行为反而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呢?认为使用信用卡从ATM机恶意取款,“无疑”是要按信用卡诈骗罪来定罪处罚的说法,是有疑问的。
第二,刘文认为,将利用信用卡从ATM机恶意取款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与《刑法》第287条的规定相冲突”。对此,有必要提出以下几点:其一,《刑法》第287条只是注意规定,而不是法律拟制,只有当某种行为符合基本条款规定的构成要件时,才能以相应的基本条款论处。例如,只有当利用计算机实施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为贪污罪;而不可能认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计算机取得了财物,就理所当然成立贪污罪。(16)同样,也不能因为利用了信用卡与ATM机,就理所当然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其二,《刑法》第287条也规定,“利用计算机……盗窃……的,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既然如此,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也属于利用计算机盗窃,当然应认定为盗窃罪。刘明祥教授或许会说,这种行为使用了信用卡,所以要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可是,不能因为行为人使用了信用卡,就否认其利用计算机,否认其构成盗窃罪;更不能认为,凡是非法使用信用卡的都必然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其三,笔者并不是像刘文所说的那样,认为“用拾得的他人的信用卡从ATM机大量取款,是利用计算机实施信用卡诈骗”。相反,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从ATM机大量取款,是利用计算机盗窃。
第三,刘文指出:“《刑法》第196条确实有缺陷,正如前文所述,将‘恶意透支’也纳入信用卡诈骗罪,与使用伪造的、作废的或他人的信用卡骗取财物的行为同样看待、同等处罚,这确实不够科学合理,有必要将这种行为抽取出来规定独立的‘滥用信用卡罪’,并规定比信用卡诈骗罪轻的刑罚。但在刑法未作修改之前,还只能依法行事,否则,就会违反罪刑法定主义和有法必依的宪法原则。”刘文一方面利用德国的刑法理论,以恶意透支不存在诈骗为由,主张我国《刑法》第196条的信用卡诈骗罪不要求欺骗自然人,另一方面又认为,将恶意透支规定在信用卡诈骗罪中不够科学合理。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研究方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刘文完全认同德国关于信用卡犯罪的立法例。但是,既然我国刑法不同于德国刑法的规定,就不能按照德国刑法的规定解释我国刑法的规定。
第四,在笔者来看,认为《刑法》第196条与《刑法》第266条是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是合适的。分则条文中的“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的表述,是表明此条与其他条文具有特别关系的基本特征。旧刑法没有规定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所以,旧刑法在规定诈骗罪的条文中,没有“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的表述。而新刑法增加了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所以《刑法》第266条增加了“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的表述。应当认为,规定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法条,相对于《刑法》第266条而言,就是特别法条。当然,刘文可能认为,《刑法》第266条的规定,不能直接表明《刑法》第196条是特别法条。然而,我们有什么理由,将明明写着“诈骗”二字的第196条排除在特别法条之外呢?我们又有什么理由说《刑法》第196条不是特别法条,而关于金融诈骗罪的其他规定是特别法条呢?
让人不得其解的是,虽然我国《刑法》第266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在文字上没有要求欺骗自然人,但刘文承认机器不能被骗,进而认为《刑法》第266条的诈骗罪要求欺骗自然人;而《刑法》第196条也没有从文字上没有要求欺骗自然人,刘文却认为对机器实施的行为可以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可是,既然两个条文都有“诈骗”二字,为什么做出不同的解释呢?刘文或许发现了其中的问题,故有时将ATM机视为所谓电子营业员,似乎又将ATM机当人看待,有时候称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中恶意取款的行为欺骗了背后的人,有时又说信用卡诈骗罪不需要欺骗自然人。在笔者看来,刘文之所以将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取款但没有欺骗自然人的行为解释为信用卡诈骗罪,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刑法》第196条没有从字面上要求欺骗自然人。但是,对法条不能进行孤立的解释,将条文之间联系起来进行体系解释,才能实现刑法的正义性。要求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成立以欺骗自然人为前提,正是考虑到它们与盗窃罪的关系,进行体系解释的结果。倘若仅作字面解释,许多犯罪的构成要件就没有边际了。例如,从字面上看,我国《刑法》第263条所规定的抢劫罪也没有要求对人使用暴力,但砸坏ATM机进而取走其中现金的行为,并不成立抢劫罪。另一方面,倘若将ATM机当人看待,那么,将ATM机砸坏后取走其中现金的行为,就成立抢劫罪了。因为行为人对机器“人”实施了暴力,使机器“人”丧失保护现金的能力,进而取走了现金。这恐怕是不会被任何人接受的。
二、盗窃罪说具有合理性
笔者一直认为,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盗窃罪。因为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刘文认为笔者采纳了日本刑法理论关于盗窃的定义,而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我国刑法规定了抢夺罪,故笔者的定义不当。刘文指出:“事实上,自古以来,所谓盗窃都有窃而取之的含义。我国的通说也认为,盗窃是行为人采用自认为不使财物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发觉的方式窃取(即秘密取得)他人财物。”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给盗窃下定义呢?
首先,不得不再次说明的是,刘文所赞成的通说,存在重大缺陷。
通说要求盗窃具有秘密性,是为了区分盗窃与抢夺(盗窃是秘密的,抢夺是公开的)。但是,这种区别难以成立。根据通说的观点,“‘秘密’是指行为人自认为没有被所有人、保管人发现。如果行为人已经明知被被害人发觉,公然将财物取走,不构成本罪(指盗窃罪——引者注),而应认定为抢夺罪。”(17)据此,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认识到自己是在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就属于盗窃;如果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是在公开取得他人财物,就成立抢夺;至于客观行为本身是秘密还是公开,则不影响盗窃罪与抢夺罪的成立。但通说存在以下问题:(1)通说在犯罪客观要件中论述盗窃罪必须表现为秘密窃取,但同时认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自认为”没有被所有人、占有人发觉即可,不必客观上具有秘密性,这便混淆了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区别。(2)根据通说,在客观上同样是公开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当行为人自认为所有人、占有人没有发觉时就成立盗窃罪,当行为人认识到所有人、占有人发觉时就成立抢夺罪。于是,形成了“尽管客观行为类型相同,却完全按照行为人‘自认为’的内容定罪”的不合理局面。(3)实践中经常发生行为人在以平和方式取得他人财物时,根本不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被他人发觉的案件。根据通说,便无法确定该行为的性质;或者不得不以客观行为是否秘密为标准区分盗窃与抢夺,但这与通说定义的秘密窃取相冲突。(4)由于盗窃行为客观上完全可能具有公开性,所以,通说只好将“秘密”解释为行为人“自认为”秘密。可是,通说不能说明故意的认识内容。众所周知,故意的认识内容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内容是一致的,换言之,客观构成要件规制着故意的认识内容。一方面,凡属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事实,都是故意的认识内容(客观的超过要素除外)。另一方面,凡不属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事实,就不可能成为故意的认识内容。但是,通说一方面认为,客观的盗窃行为既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秘密的,另一方面又要求行为人必须“以自认为不使他人发觉的方法占有他人财物”;换言之,即使行为在客观上表现为公开盗窃时,行为人主观上也必须认识到秘密窃取。这便不可思议了!既然客观上可以表现为公开盗窃,主观上就可以表现为认识到自己是在公开盗窃。如果认为客观上公开盗窃时,主观上也必须认识到秘密窃取,那便意味着,一方面,行为人不必认识到客观构成事实(不必认识到公开盗窃),另一方面,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客观构成事实之外的内容(必须认识到秘密窃取)。(5)在犯罪对象为金融机构资金与珍贵文物时,盗窃罪的法定刑明显重于抢夺罪的法定刑。可是,根据通说,对自认为秘密地窃取金融机构资金的盗窃行为的处罚,远远重于对自认为公开地抢夺金融机构资金的行为的处罚。然而,从非难可能性的角度来说,后者应当更为严重。这表明,要求盗窃具有秘密性也不可取。此外,通说对盗窃的定义,仅指出窃取的对象是公私财物,而不说明是他人占有的财物,也没有说明窃取行为的具体内容,因而不利于准确认定盗窃罪。
其次,刑法是否规定抢夺罪,并不必然影响盗窃的定义。例如,旧中国1928年刑法就规定了抢夺罪,但当时的刑法理论并不一概将盗窃限定为秘密窃取。如有学者指出:“窃盗,指夺取他人财物之行为而言。所谓夺取,即丧失他人之所持有,而移入自己所持有是也。”(18)再如,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了抢夺罪,但许多学者依然认为盗窃行为不要求秘密窃取。如林山田指出:“窃取只要以非暴力的和平手段,违反所有权人或持有人的意思,或未得所有权人或持有人的同意,而取走其持有物,即足以当之,并不以系趁人不知不觉,且以秘密或隐秘之方法为必要。因此,物的所有人或持有人虽于行为人窃取时有所知觉,或行为人的窃取行为并非秘密或隐秘,而系另有他人共见之情况,均无碍于窃取行为的成立,而构成窃盗罪。”(19)张丽卿在论述盗窃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时指出:“对于破坏持有的手段,并不要求必须‘秘密行之’。……窃取只要是以非暴力的手段,未经持有人同意或违背持有人意思,而取走其持有物即可,行为是否秘密或公然,和持有的被破坏无关。因此,持有人虽于行为人窃取时有所知觉,窃取行为虽非秘密或隐秘,乘他人对物的一时支配力松弛之际,即使在有人看见的情况下,均无碍窃取行为的成立。”(20)曾淑瑜在论述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的区别时也指出:“‘密行’并非界定窃盗罪及抢夺罪、强盗罪之主要不同所在,毋宁认为窃取是使用非暴力之手段,未经持有人同意或违背持有人之意思,而取走其持有物即可,行为是否秘密或公众,和持有的被破坏无关。因此,乘他人对物一时支配松弛之际,即使在有人共见之情况下,均无碍窃取行为之成立。”(21)可以肯定的是,上述持盗窃行为不限于秘密窃取的学者,不可能否认盗窃与抢夺存在区别。这说明,刑法理论完全可以在秘密与否之外寻求盗窃罪与抢夺罪的界限。
最后,将盗窃定义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没有不当之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得盗窃罪与挪用资金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相区别,后者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使得盗窃罪与诈骗罪(以及职务侵占罪中的骗取行为)、敲诈勒索罪相区别,因为诈骗罪与敲诈勒索罪是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财物的;“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使得盗窃罪与侵占罪(以及职务侵占罪中的狭义的侵占行为)相区别,因为侵占罪是将自己占有的财物或者将脱离他人占有的财物据为己有;“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使得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破坏生产经营罪相区别,后两种犯罪并不是转移财产的占有,而是毁弃财产;“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表明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盗窃行为破坏或者排除了他人对财物的占有;另一方面,盗窃行为建立了新的占有,使行为人或第三者具有类似所有人的地位。(22)行为是否具有秘密性,并不直接决定是否存在排除占有与建立占有的事实。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盗窃罪的成立是否以行为人“采取平和手段”为前提?本文采取否认回答。(23)就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盗窃罪与抢劫罪具有竞合关系,当行为符合较重犯罪构成要件时,当然应认定为重罪;而且,盗窃与抢劫行为能够在重合的限度内成立共同犯罪。在此意义上说,抢劫罪同时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但这并没有增添认定犯罪的难度。因为即使承认抢劫行为同时符合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也只能将其认定为抢劫罪。另一方面,盗窃案件中也可能存在某种暴力、胁迫等行为,倘若将盗窃限定为“平和手段”,对这种行为就无法处理,显然不当。(24)就盗窃与抢夺罪的关系而言:抢夺罪的成立需要对物暴力,需要有致人伤亡的可能性,但盗窃罪并无这种要求。(25)概言之,构成要件所要求的是成立犯罪的最低限度,要求盗窃必须“采取平和手段”的做法,则在最低限度的基础上附加了不应有的要素。附带指出的是,刘文认为笔者“是从广义上理解盗窃罪的”,“包含了部分诈骗、抢劫”,但其实并非如此。一方面,盗窃与诈骗是对立的犯罪,就同一结果而言,一个行为不可能既是盗窃又是诈骗,所以,笔者关于盗窃罪的定义,并不包含诈骗。刘文之所以认为笔者关于盗窃的定义包含了诈骗,是因为刘文将部分盗窃纳入诈骗(如认为使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取款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另一方面,盗窃与抢劫不是对立关系,因而存在重合部分。
综上所述,通说关于盗窃罪的定义并不可取。按照各国通行的盗窃定义,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完全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即使按照刘文所采纳的通说关于盗窃的定义,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也完全具有秘密性,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盗窃罪。(26)
刘文指出:“用自己的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透支的行为,自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这在日本固然可以解释为盗窃,但正如前文所述,若在我国也解释为盗窃,那就与刑法的规定明显不符。”在笔者看来,刘文似乎偷换了概念。换言之,将用自己的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透支的行为解释为盗窃,不是与刑法的规定不符,而是与刘文的观点不符。因为用自己的信用卡在ATM机上恶意透支的行为,也具有秘密性;行为人所取得的是银行占有的现金,也是“窃而取之”。既然如此,当然与刑法规定的盗窃罪的构成要件相符合(也与刘文主张的盗窃罪定义相符合)。
刘文还指出:“诈骗虽然是被害人因受骗而交付财物给行为人的,但如果他明知真相就不会交付财物,因此,也可以说是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给自己占有。很显然,若这样宽泛地来解释盗窃,就无法将我国刑法规定的盗窃罪与多种侵犯财产的犯罪区分开来。”如所周知,诈骗罪的受骗者是基于有瑕疵的意思而处分。刘文称诈骗罪也“违反被害人的意志”显然是就事后而言的,而不是就行为当时而言的。至于刘文强调的盗窃与多种侵犯财产罪的区分,正是笔者近来发现的我国刑法理论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大问题。(27)况且,即使按照笔者所采纳的盗窃罪定义,也完全可以理顺盗窃罪与其他财产犯罪之间的关系。众所周知,财产罪分为取得罪与毁弃罪。取得罪可以分为转移占有的取得罪与不转移占有的取得罪。侵占罪是不转移占有的取得罪,盗窃、诈骗、抢劫、抢夺等罪都是转移占有的取得罪。事实上,盗窃罪是转移占有的取得罪中的兜底犯罪,即凡是值得科处刑罚的非法转移占有进而取得他人财产的行为,只要不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的,一定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发生抽象的事实认识错误时除外)。
盗窃与侵占罪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所取得的财物由谁占有。但盗窃罪与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的对象都必须是他人占有的财物。诚然,如何判断财物由谁占有,是国外刑法理论长期讨论的问题。刘文不赞成笔者关于占有的判断,这是本文不可能展开讨论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有两点:其一,ATM机中的现金,不可能是遗忘物,而是银行事实上占有的财物。这一点刘明祥教授也不否认,所以,刘明祥教授认为,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行为不成立侵占罪。既然如此,ATM机中的财物当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所以,关于占有的判断的分歧,并不能说明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中恶意取款的行为成立信用卡诈骗罪。其二,用自己的信用卡善意取款者(即取出的现金没有超过其存款数额),并不是像刘文所称的那样“存在夺取他人占有的财物的问题”,也没有违反银行管理者的意志,当然不成立盗窃罪。
刘文对笔者在《也论》一文所举之例作了选择性的评析和说明,有必要再予讨论。
例一:关于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贩卖机而取出商品的行为。刘文指出:“如果我国刑法规定有类似德国等国刑法的“骗取给付罪”,自然是要按此罪定罪处罚,而不是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我国刑法也有必要增设此罪。”其一,刘文似乎认为,即使这种行为取得了数额较大的财物,在我国现在还不构成犯罪。这种结论难以令人赞成。其二,《德国刑法》第265条a所规定的骗取给付罪,共有三种类型,其共同点是,“在只有支付对价,有关机关才会允许享受娱乐活动或者利用其设施的场合,行为人不支付对价却享受娱乐活动或者利用其设施”。(28)无票进入演出场所、盗打电话、无票乘车,是其适例。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贩卖机而取出商品的行为,是否符合骗取给付罪的构成要件,还存在争议,并不是“自然”按骗取给付罪定罪处罚。其三,德国刑法规定的骗取给付罪,是一个补充规定(或从属性规定),即只有不符合其他更重犯罪构成要件时,才能认定为骗取给付罪。概言之,在德国,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贩卖机而取出商品的行为,最终成立的犯罪不可能是骗取给付罪,只能是盗窃罪。(29)既然如此,在没有规定骗取给付罪的我国,对于这种行为更应当认定为盗窃罪。
例二:关于使用某种工具打开汽车的智能锁开走汽车,将别人住宅大门安装的智能锁打开、用铁丝将金库门打开,尔后进入住宅、金库,拿走其中的财物。刘文也主张认定为盗窃罪。因为“没有自然人或者机器代替自然人交付汽车”。可是,按照刘文的这一思路,倘若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侵入他人无人驾驶飞机的电脑控制系统,使无人驾驶飞机飞入自己控制的场所的,也可以认定有交付行为,进而认定为诈骗罪;倘若被害人门前安置了智能的机器人管理家务,行为人通过技术手段,使管理家务的机器人“交付”财物给自己的,也成立诈骗罪。这是难以被人接受的。刘文只说诈骗罪要求有交付(处分)行为,不提(尽管其在其他论著中提到)要有交付(处分)意思。然而,财产处分行为不限于积极的举动,或者说,“处分行为这一构成要件要素,不应在民法意义上理解,而是包括了被害人的一切作为、忍受与不作为。”(30)倘若不强调交付意识,就可能认定为不作为的交付行为,因而使上述行为成立诈骗罪。一旦明确了交付行为以交付意思为前提,就会发现所谓“机器代替自然人交付”的说法并不成立。刘文主张认定为盗窃罪的另一理由是,被害人没有将车交给行为人,而是行为人开走了车;被害人没有向行为人交付财物,而是行为人直接拿走了住宅、金库中存放的财物。可是,当行为人使用信用卡在ATM机中取款时,ATM机也没有直接将现金装入行为人的口袋或者交到行为人手中,也是行为人拿走的;作为被害人的银行管理者更没有将现金交付给行为人。
例三:使用工具打开ATM机背面的智能锁取出其中的现金。笔者认为,这种行为与将拾得的信用卡插入ATM机中取出其中的现金并无区别。因为二者的行为都违反了银行管理者的意志,而不是基于银行管理者有瑕疵的意志;二者都是将银行占有的现金,转移给自己占有。刘文则认为二者“有性质上的差异。前者没有交易存在,没有ATM机这种银行电子营业员向甲交付现金,而是甲直接从ATM机存放现金的柜子中拿走了现金。”可是,一方面,有没有交易存在,与行为是成立盗窃还是成立诈骗没有直接关系。有交易存在时,也可能构成盗窃罪。换言之,有无交易存在,只是案件的边缘事实,不是构成事实。另一方面,电子营业员的交付没有交付意思,不可能与欺骗自然人基于交付意思的交付行为相提并论。
例四:在ATM机上存入假币后取出真币的行为。刘文指出:“仅就取真币的行为而言,不难发现行为人是在卡里无存款记录或存款数额不足的情况下,取出了银行的现金,只要对这种行为做一点实质评价,对‘恶意透支’做一点不同于银行法的扩张解释,就可以将这种行为评价为‘恶意透支’,依照《刑法》第196条定信用卡诈骗罪不成问题。”可是,其一,完全存在行为人在卡里仍然有存款记录、并无数额不足的情形。例如,甲的信用卡中原本有1万元存款,其后将1万元假币通过ATM机存入卡中,后来从ATM机中取出1万元,卡中仍记载有1万元。对此,刘文的观点是无法处理的。其二,当行为人持有的是借记卡时,刘文的观点也不成立。诚然,根据立法解释,借记卡也属于信用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借记卡也可以透支。恶意透支是与善意透支相对的概念,就透支的外观行为而言,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并无区别。借记卡不可能善意透支,当然也不能恶意透支。根据刘文的观点,借记卡原本没有透支功能,但只要ATM机的某个环节出了问题,就表明其借记卡已具有了透支功能。于是,非法使用借记卡是否属于恶意透支,就取决于机器是否出现故障。这便使构成要件丧失定型性,导致行为构成何罪取决于外界的偶然事项,难以被人接受。其三,按照刘文的逻辑,在ATM机上恶意透支的行为也符合了贷款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因而与贷款诈骗罪相竞合。因为行为人以借款的方式实施行为,但隐瞒了不归还的意图,机器替银行管理者向行为人交付了现金。刘明祥教授可能会说,贷款诈骗罪必须欺骗自然人,故在ATM机上恶意透支的行为不成立贷款诈骗罪。可是,在法条对构成要件的表述均使用了“诈骗”一词的情况下,为什么贷款诈骗罪需要欺骗自然人,而信用卡诈骗罪却不需要欺骗自然人呢?
例五:甲向乙借款,乙将自己的真实有效的信用卡交给甲,并告知了密码与信用卡内的金额仅有2000元。但甲一次性地从ATM机上取出5000元。甲事后隐瞒“透支”事实,将信用卡还给乙。显然,在本设例中,甲具有归还2000元的意思。根据本文的观点,甲对多取出的3000元成立盗窃罪。刘文指出:“如果甲没有还款给乙的意思,骗取乙的信用卡使用,尽管是乙将信用卡交给甲并告知了其密码,也由于不是经有效授权而使用他人信用卡,应视为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的,当然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看来,刘文也觉得认定为冒用他人信用卡不合适,只得“视为”冒用他人信用卡。不能不认为,刘文的观点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刘文还说:“按张文所持的盗窃罪说,甲无还款的意思骗取乙的信用卡,一次性地从ATM机取出5000元,其中, ‘透支’的3000元成立盗窃罪,那么,非法取得其余2000元应如何评价呢?如果评价为诈骗、信用卡诈骗、或者借款,那就意味着同一取款行为,既含有盗窃又含有诈骗、信用卡诈骗或借款的性质,这样来解释,可能难以令人信服。”其实,在本例中,2000元当然不存在犯罪问题。因为在法律上乙可以支配2000元,甲对2000元具有归还的意思。在此情形下,即使按照刘文的观点,就取出2000元而言,甲依然是合法的,就取出3000元而言,甲是信用卡诈骗。这导致一个行为既包含了合法部分也包含了非法部分,并不奇怪。既然如此,一个行为对一个结果是盗窃、对另一个结果是诈骗,就更为可能了(再次声明,一个行为对同一结果不可能既是盗窃又是诈骗)。倘若甲当初就不想归还2000元,对2000元现金本身是成立普通的诈骗罪还是成立盗窃罪,可能因人而异。但是,即使认为甲对2000元成立普通的诈骗罪,而对3000元成立盗窃罪,也没有不当之处。再如,行为人甲进入刘教授的办公室后,欺骗刘教授说:“您的好朋友张教授希望您送给他一本《错误论》,特意让我来取的。”刘教授说:“就在门边的书架上,你拿一本给张教授吧。”甲却一把抓走了两本《错误论》。甲的同一拿书行为,就具有两个性质:对其中一本是诈骗,对另一本是盗窃。同一行为(当然包括同一取款行为)触犯两个罪名,是常见的想象竞合的现象,不知道刘文为什么难以信服。
附带说明的是,已有部分银行的存折与储蓄卡(属于刑法上的信用卡)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如存折与储蓄卡都可以在ATM机上取款和转款,但存折不是信用卡。按照刘文的观点,用拾得的存折在ATM机上取款的,不可能是信用卡诈骗罪,恐怕只能是盗窃罪(或者无罪);而用拾得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的,是信用卡诈骗罪。可是,二者实质上也没有区别,刘文却主张定不同的犯罪。这大概是刘文也难以解释的。
三、我国没有必要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
就笔者于《也论》一文所举之例而言,刘文也承认,其观点“难以说明行为人利用信用卡以外的磁卡从ATM机上取款的行为性质”,也“难以解决行为人使用他人存折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于是,刘文指出,这不能归责于自己的学说,“而是立法不完善造成的”,因此,需要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
笔者在《也论》一文中已经说明,我国没有必要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只要将作为盗窃罪中的财物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财物即可。
刘文首先指出:“张文对德国、日本等国刑法为何不把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对象的解释,可能有失偏颇。”其实,笔者关于德国、日本等国刑法为何不将财产性利益作为盗窃罪的解释,主要来源于日本权威学者的论述与判例。“倘若承认盗窃罪的对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则会无限扩大盗窃罪的范围”,正是根据日本权威学者的论述得出的结论。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关于财物的概念,日本的通说是有体性说,而非管理可能性说。(31)诚然,在德国、日本,并非盗窃一分一厘都会被认定为盗窃罪,但是,在德国、日本认定为盗窃罪的行为,其对象的价值远远低于我国。而且,从司法实践上看,在德国、日本,是否认定行为构成盗窃罪,并不是单纯看有体物本身的价值。例如,在日本,倘若行为人盗窃了记载有商业秘密的一张纸,也会被认定为盗窃罪。(32)但盗窃的对象却不是商业秘密本身,而是一张纸。这正是笔者所称的“许多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事实上被评价为盗窃了有体物而认定为盗窃罪”的情形。亦即,商业秘密本身只是财产性利益,但由于它不是盗窃罪的对象,所以,认定行为人盗窃了作为有体物的一张纸。
笔者在《也论》一文中指出,由于德国、日本刑法要求盗窃罪的对象是狭义的财物,所以,不能解决盗窃财产性利益的案件。“例如,甲得知了X的银行存折账号与密码后,将X存折记载的10万元存款,转入自己的账户内。但还没有取出现金。再如,乙得知Y的银行存折账号与密码后,通过电话用Y的存折上记载的存款为自己缴纳1000余元的水电费。”这类行为在德国、日本不成立盗窃罪。刘文却说:“张文所举盗窃他人存折、银行卡后又取出现金或者在特约商户消费的,这并非是取得了财产性利益的实例,而是取得了财物。”显然,刘文自己加上了“取出现金”和“在特约商户消费”后,说笔者的说法不当。这是不合适的。如所周知,在日本,行为人盗窃他人存折、银行卡后,并不使用的,对存折、信用卡这种有体物成立盗窃罪;行为人利用所盗窃的存折、银行卡在ATM机中取出现金的,另对取出的现金成立盗窃罪;行为人利用所盗窃的存折、银行卡从银行柜台取款或者在特约商户消费的,成立诈骗罪,与对存折、银行卡本身的盗窃罪实行并罚。(33)但是,笔者所举的上述两例,的确是盗窃财产性利益的实例;在德国与日本等国,于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之前,甲、乙的行为不成立任何犯罪,只是在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之后,才成立使用计算机诈骗罪。而且,在上述两例中,甲、乙只是盗窃了他人的存款债权。在我国,只要承认财产性利益是盗窃罪的对象,即可认定甲、乙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根据刘文的观点,对甲、乙的行为既不适合以盗窃罪论处(因为甲、乙没有窃取狭义的财物),也不能以信用卡诈骗罪论处(因为甲、乙没有使用信用卡),当然也不能以诈骗罪论处(因为没有欺骗自然人)。这恐怕不妥当。
刘文指出:“债权等财产权利不能被人事实上占有,只是在民事法律的观念上才可以被占有,因而不能成为刑法中盗窃罪的侵害对象。如果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规定或解释为也可以成为盗窃罪的侵害对象,那显然与侵犯财产罪的刑法理论不符。正因为如此,即便是在今天使用计算机已很容易转移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并且,也正如张文所述,只要在刑法中规定或在理论上作出解释,将财产性利益纳入盗窃罪的侵害对象范围,那就完全没有必要规定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了,但德国、日本等许多国家还是单独规定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根本原因就在于,使用计算机转移债权等取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在性质上不同于盗窃,与传统诈骗罪也有差别。”其一,诚然,在民法上,“占有的客体仅以有体物为限,对于不因物的占有而成立的财产权(如商标权、专利权或地役权等),仅可成立准占有。”(34)但是,刑法上的占有并不同于民法上的占有。质言之,只要可以转移支配的对象,就可能成为盗窃罪的对象。与诈骗罪相联系,也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在诈骗罪的场合,当对象是债权时,受骗者处分的不是债权本身,而是债权的占有。对于债权而言,虽然不存在与财物相同意义上的占有,但存在与占有对应的准占有(进而成为刑法上的占有)。而且,即使受骗者没有转移所有权、债权的意思或表示,行为人也可能取得财产上的利益。(35)其二,德国、日本之所以增加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并不是因为财产性利益不能被盗窃,而是为了避免扩大处罚范围。倘若德国、日本不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不担心扩大处罚范围,就无必要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但在我国,刑法并没有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处罚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不会扩大处罚范围,所以,完全可以将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其三,德国、日本刑法规定的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当然既不同于盗窃罪,也不同于传统诈骗罪。这是因为德国、日本的盗窃罪仅限于盗窃财物,诈骗罪要求欺骗自然人,而使用计算机诈骗罪所取得的是财产性利益,也没有欺骗自然人。可是,在没有规定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和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对象的我国,上述说法并不成立。因为在德国、日本成立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行为,在我国完全成立盗窃罪。况且,在我国没有规定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情况下,不能将案件事实归纳为使用计算机诈骗。
刘文指出:“盗窃罪的特点即‘窃而取之’决定了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其侵害对象。按张文的逻辑推论,我国《刑法》第267条和第275条规定的‘抢夺公私财物’、‘故意毁坏公私财物’之中的‘财物’,也可以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但现实生活中有可能发生抢夺、毁坏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吗?”首先,盗窃财产性利益的现象,已经成为客观事实。例如,通过侵入银行电脑终端,将他人存折上的存款转移到自己的存折中。在行为人尚未取出存款时,便属于盗窃财产性利益。否认这种行为属于盗窃财产性利益,恐怕不是务实的观点。其次,在法国、瑞士,将他人存折记载的存款转入自己的账户内的行为,成立盗窃罪。(36)即使在德国、日本,虽然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但“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表述几乎屡见不鲜。所以,财产性益完全可能被盗窃。再次,称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并不意味着抢夺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对象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正如刘文所言,这不是单纯的对象问题,而是需要与行为本身、犯罪的特点相联系进行考察。例如,在规定了出卖、陈列淫秽物品的国家,出卖储存了淫秽图像的硬盘的行为,可能构成出卖淫秽物品罪;但对于陈列储存了淫秽图像的硬盘的行为,则难以认定为陈列淫秽物品罪。最后,有谁能担保现实生活中不会发生抢夺、毁灭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呢?任何人都不要将自己知道的有限事实强加于法律,不能认为法律所规定的犯罪类型,只限于自己知道的部分事实。况且,在司法实践中,将低价抛售公司股票的行为认定为故意毁坏财物罪的判决,已不罕见。这说明,故意毁坏财产性利益的案件不仅可能发生,而且已经发生。
笔者在《也论》一文中指出:“在我国,盗窃罪的成立以数额较大为起点,对单纯盗窃财产性利益的凭证的行为,不可能以凭证本身的价值认定为盗窃(《刑法》第196条第3款的规定就表明了这一点),因而不利于保护财产性利益。只有通过肯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才能有效地保护财产性利益。”刘文却仅以盗窃支票后冒用的行为可以认定为票据诈骗罪为由,得出了“不存在‘只有通过肯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才能有效地保护财产性利益’的问题”的结论。显而易见,刘文在这一点上也存在方法论的缺陷。以笔者在上一段所举案件为例(将他人存款转入自己的存折),不肯定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就不可能有效地保护财产性利益。
笔者在《也论》一文中提出,“我国刑法的规定与审判实践也肯定了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刘文却说:“我国《刑法》第265条将盗用他人电信设备、设施的行为规定以盗窃罪定罪处罚,这实质上是一种拟制性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将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设施规定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也有相似的性质。”并以《德国刑法》规定了“盗用电力”罪、“交通工具的无权使用”罪(第248条b)以及《挪威刑法》第403条的规定说明,“通过解释将其纳入盗窃罪的处罚范围,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其实,没有任何立法可以根本上解决问题,近年来德国、日本对刑法典的修改频繁的令人惊讶,就说明了这一点。在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人可以制定一部完美的刑法典。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经验充分表明,成文法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刑法的解释。大体而言,刑法完善的路径为,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后,解释者根据正义理念与文字表述,并联系社会现实解释法律;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正义,解释者不得不对法律用语做出与其字面含义不同的解释(对刑法的解释当然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立法机关会采纳解释者的意见,修改法律的文字表述,使用更能实现正义理念的文字表述;然后,解释者再根据正义理念与文字表述,联系社会现实解释法律;再重复上面的过程。这种过程循环往复,从而使成文法更加完善,使司法不断地追求和实现正义。所以,不要认为对刑法的解释只是权宜之计。即使是权宜之计,也没有不合适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对本国刑法的解释,要尽量做到使法条之间相协调,在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使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受到处罚,防止处罚的漏洞。诚然,解释刑法不可缺少比较方法,尤其是在刑法条文表述相同或者相似、条文适用背景相同或者相似的情况下,参考外国的刑法学说与审判实践解释本国刑法规范,可能得出发人深省的结论。但是,在进行比较解释时,不可忽视中外刑法在内容、体例上的差异,不能仅从翻译成中文的字面含义做出解释(刘文对德国刑法关于骗取给付罪的规定、法国刑法关于盗窃罪的规定,明显存在误解)。例如,就某类犯罪而言,有的国家刑法规定得非常详细(可能有多个罪名),有的国家刑法则规定得十分简单(可能只有一个罪名)。在这种情况下,后者的一个罪名可能包含了前者的多个罪名的内容;而不能简单地认为,后者只处罚一种情形,前者处罚多种情形。例如,《德国刑法》第211条、第212条、第216条、第220条a分别规定了谋杀罪、故意杀人罪、受嘱托杀人罪、灭绝种族罪;而我国刑法仅第232条规定了故意杀人罪。我们显然不能认为,谋杀、受嘱托杀人以及灭绝种族的行为,没有被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处刑;相反只能认为,这些行为都包含在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的故意杀人罪中。反过来的情形也值得我们思考。中国刑法规定了抢夺罪,但日本刑法不见有此罪名;日本的学者与法官面对我们所谓的抢夺行为时,不会做出如下判断:该行为属于抢夺行为,虽然中国刑法规定了抢夺罪,但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故不得定罪量刑;相反,在日本,抢夺行为分别被认定为抢劫罪与盗窃罪。(37)由此看来,我们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与犯罪的名称,而应注重规定某种犯罪的条文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了解相同用语在不同国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义。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能因为国外刑法将某种行为独立于盗窃罪之外,就认为我国刑法所规定的盗窃罪不包含这种行为。例如,《德国刑法》第248条b规定了交通工具的无权使用罪,我国没有规定此罪。但不能据此认为该行为在我国一概无罪。一方面,即使在德国,无权使用他人交通工具的行为,只有不符合更重犯罪的构成要件时,才认定为本罪;倘若行为符合了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则会认定为盗窃罪。另一方面,对于无权使用他人交通工具的行为,客观上可以评价为转移了占有,主观上可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在我国就应认定为盗窃罪。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判例,对于无权使用他人交通工具的行为,除时间极为短暂的以外,都认定为盗窃罪。(38)
刘文在介绍了德国、日本关于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的争议后指出:“德国、日本的立法者最终采纳了最后这种意见,在刑法中增设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既保证了执法上的协调统一性,又避免了理论上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一立法经验已被许多国家所采纳,同样也值得我们借鉴。”其实,这是在德国、日本的既有立法体例下的争论。正如笔者反复指出的那样,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是因为德国、日本的刑法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盗窃罪没有数额较大的限制。与之相反,我国没有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盗窃罪有数额限制。所以,我国没有必要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
刘文指出:“如果我国刑法增设了使用计算机诈骗罪,并且规定该罪的对象包括财物与财产性利益,那么,张文所说的‘信用卡诈骗罪说难以说明行为人利用信用卡以外的磁卡从ATM机取款的行为性质’,‘难以解决行为人使用他人存折获取财产性利益’的案件,就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说明或处理了。”在本文看来,这是刘文在方法论上存在的重大问题。我们是在既有的立法之下,从解释论上讨论对各种值得处罚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既然如此,从协调保护法益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出发,对于值得科处刑罚的行为,只要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排除在犯罪之处。刘文既扩大信用卡诈骗罪的范围,又不当缩小盗窃罪的范围,导致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能受到应有处罚。于是,又从立法论上主张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然而,倘若将立法论与解释论混杂在一起,就没有办法争论。笔者显然不能为了反对刘文的观点,而从立法论上主张删除《刑法》第196条,乃至删除所有的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也不能因为有人批评笔者的盗窃罪定义导致盗窃与抢夺无法区分(但并非如此),就从立法论上主张取消刑法关于抢夺罪的规定。
此外,刘明祥教授反复强调的是,完全用传统诈骗罪的观念来解释信用卡诈骗罪是行不通的;“因受欺骗而处分财产”固然是诈骗罪的本质特征,但使用计算机诈骗(包含信用卡诈骗)犯罪现象的产生对此提出了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么是在解释上做文章,要么是单设新罪名。所谓“在解释上做文章”,就是“不能完全用传统诈骗罪的观念来解释信用卡诈骗罪”。于是,刘明祥教授既在解释论上做文章,使信用卡诈骗罪包含了并非属于诈骗的所谓滥用信用卡的行为,又在立法论上做文章,要求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乃至骗取给付罪。
刘文的思路是,不将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解释为诈骗罪的特别条款,不管是否欺骗自然人,只要非法使用信用卡取得财物的,都成立信用卡诈骗罪(这样理解不符合“诈骗”的构造);同时否认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将没有欺骗自然人、也没有使用信用卡但非法转移了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解释为无罪;由于解释为无罪不妥当,所以进一步建议刑法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骗取给付等罪。刘明祥教授通过“扩大”信用卡诈骗罪的范围,在解释论上仅解决了部分问题,于是主张修改刑法、增设新罪。
笔者的思路是,将刑法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解释为诈骗罪的特别条款,只有欺骗自然人而取得他人财产的行为,才可能成立信用卡诈骗罪(这样理解符合“诈骗”的构造);同时承认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对象(这样解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将没有欺骗自然人但非法转移了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为盗窃罪。笔者通过扩大盗窃罪的对象在解释论上解决了所有的相关问题,于是刑法不必增设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与骗取给付罪。
与刘文的思路相比,笔者的思路或许更合理、更可取吧!
注释:
①本文所称的非法使用信用卡,即刘文所称的使用信用卡恶意取款,既包括用拾得、骗得、抢夺的信用卡在ATM机上取款,也包括持卡人利用ATM机的故障超出其存款额从ATM机取款等行为。
②参见刘明祥:“在ATM机上恶意取款的定性分析”,载《检察日报》2008年1月8日,第3版。
③如日本学者林幹人将本罪概括为“作出不实电磁记录得利罪”。参见〔日〕林幹人:《刑法各论》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版,第255页。
④伯阳:《德国公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⑤〔日〕井田良:《刑法各论》,弘文堂2007年版,第126页。
⑥前注③,〔日〕林幹人书,第256页。
⑦〔日〕山口厚:《刑法各论》,有斐阁2005年补订版,第270页。
⑧前注④,伯阳书,第24页。
⑨读到刘文关于日本的信用卡“一般”不能在ATM机上透支时,笔者立即询问了日本成蹊大学的金光旭教授。笔者询问的原话是:“想请教一个问题:在日本,当持卡人持有的是具有透支功能的真正的信用卡时,倘若其卡中没有钱了,能否在ATM机上透支现金?”金光旭教授的答复如下:“即使银行账户里没有余额,应照样可以在ATM上透支现金。因为信用卡透支的法律性质是信用卡发行公司为持卡人提供的无担保贷款,所以取款时银行里有没有钱不应影响透支,只要在期限内(次月决算日)偿还就可以了。当然,信用卡公司在发行信用卡时,会根据你的收入等信用情况限定透支限度。”
⑩参见〔日〕长井圆:《カ-ド犯罪对策法の最先端》,日本クレヅット产业协会2000年版,第103~106页。
(11)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页以下。
(12)参见张明楷:“许霆案减轻处罚的思考”,《法律适用》2008年第9期。
(13)参见〔德〕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145页。
(14)同上,第145页。
(15)参见陈兴良:《规范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第277页以下。
(16)参见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6页以下。
(17)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70页。
(18)郑爰诹:《中华民国刑法集解》,朱鸿达修正,世界书局1929年版,第394页。
(19)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作者发行2005年修订5版,第311~312页。
(20)张丽卿:“窃盗与抢夺的界限”,载蔡墩铭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504页。
(21)曾淑瑜:《刑法分则实例研习——个人法益之保护》,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98页。
(22)参见Vgl.,Wessels/Hillenkamp,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2,23.Autl.,C.F.Müller 2000,S.51。
(23)笔者以前也认为窃取行为应限于平和手段。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727页。
(24)例如,被害人在公园草地的长椅上午休,手上拿着手机。行为人用竹竿轻轻敲打被害人的手,没有将被害人打醒,但使手机滑落到草地上,然后将手机拿走。用竹竿敲打被害人的手,也可谓暴力。上例中的暴力行为并没有达到抢劫罪所要求的暴力,只能以盗窃罪论处。倘若认为盗窃罪不得有暴力,则上例不成立任何犯罪。这种结论难以被人赞成。
(25)参见张明楷:“盗窃与抢夺的界限”,《法学家》2006年第2期。
(26)此外,刘文意识到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于是认为笔者采取日本刑法理论关于盗窃罪的定义不合适。笔者要知道的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使用计算机诈骗罪与滥用信用卡罪,刘文又为什么可以按照德国刑法的关于这两种犯罪的规定解释我国的信用卡诈骗罪呢?
(27)参见张明楷:“犯罪之间的界限与竞合”,《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28)〔德〕Ulrich Sieber:《コンピヱ-タ犯罪と刑法Ⅰ》,西田典之、山口厚译,成文堂1986年版,第238页。
(29)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售货机而取得商品的行为是否符合《德国刑法》第265条a的构成要件,在德国刑法理论上还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这种行为根本不符合《德国刑法》第265条a的构成要件。因为第265条a中所说的“给付”只能是“自动机”本身所能产生的服务,如电话机的通话服务、影视机播放的影视节目。而自动售货机中的商品并不是自动售货机本身所能生成的服务,所以自动售货机不属于第265条a中所说的“自动机”。因此,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售货机而得取商品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售货机而取得商品的行为仍然符合《德国刑法》第265条a所规定的构成要件,但是由于第265条a相对于其他财产犯罪(尤其是盗窃罪)而言是从属性条款(该条最后一句明文规定在成立其他更重罪行时不适用本条),所以在定罪时排除第265条a的适用,结果仍然只定盗窃罪。总之,在德国,从最终的定罪来看,对于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售货机而取得商品的行为,不可能适用第265条a认定为骗取给付罪。对此,德国刑法理论上没有疑问。上述两种不同学说的差别仅在于,一部分学者在构成要件层面上否认上述行为成立第265条a规定的犯罪,主张将上述行为直接认定为盗窃罪;另一部分学者主张在讨论罪数(法条竞合)的时候,鉴于第265条a的从属条款性质,将上述行为认定为盗窃罪。需要说明的是,即使持后一种观点的人也认为,将普通铁片投入自动售货机而取得商品的行为,并不成立盗窃罪与骗取给付罪的想象竞合犯,而是因为第265条a的从属性质,排除适用第265条a。参见(Vgl.,Arzt/Weber,Strafrecht Besonderer Teil,Verlag Ernst und Werner Gieseking 2000,S.535ff。
(30)前注(28),〔德〕Ulrich Sieber书,第254页。这里的作为与不作为显然只是借用了犯罪行为的作为与不作为的概念,即处分行为可以表现为积极的处分行为与消极的没有任何举止的处分行为。
(31)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概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7年版,第200页;〔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成文堂2007年(新版第2)版,第207~208页、第260页;〔日〕西田典之:《刑法各论》,弘文堂2007年版,第131页;前注⑦,〔日〕山口厚书,第171页;等等。
(32)参见张明楷:《市场经济下的经济犯罪与对策》,中国检察出版社2005年版,第235页以下。例如,在大日本印刷事件中,公司职员擅自将本公司的秘密资料窃取的行为,被认定为盗窃罪;公司职员用公司的复印纸复印商业秘密,然后将该复印件拿走的行为,也被认定为盗窃罪(参见东京地方裁判所1965年6月26日判决,日本《判例时报》第419号)。再如,将载有商业秘密的原件拿出公司外复印,然后将原件返还原处,而将复印件保留的行为,也被认定为盗窃罪(参见东京地方裁判所1980年2月14日判决,日本《判例时报》第957号;东京地方裁判所1984年6月15日判决,日本《判例时报》第1126号)。
(33)参见前注(31),〔日〕大谷实书,第207~208、260页。
(34)崔建远等:《物权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
(35)参见〔日〕平野龙一:《犯罪论の诸问题(下)各论》,有斐阁1982年版,第337页以下。
(36)参见〔德〕K.Tiedemann:《经济犯罪と经济刑法》,〔日〕西原春夫、宫译浩一监译,成文堂1990年版,第175页。
(37)参见〔日〕前田雅英:《刑法各论讲义》,弘文堂2007年第4版,第231页。
(38)参见前注(31),〔日〕西田典之书,第149页;前注⑦,〔日〕山口厚书,第196页。
标签:信用卡论文; 信用卡诈骗罪论文; 盗窃罪论文; 诈骗罪论文; atm论文; 刑法理论论文; 构成要件要素论文; 犯罪构成要件论文; 自然人论文; ATM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