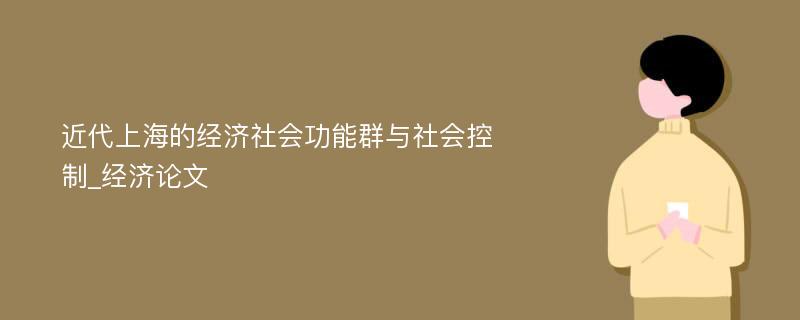
近代上海经济社会功能群体与社会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论文,上海论文,近代论文,群体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01)10-0064-06
(一)
从汉语原生字义看,“社”为祭祀土地神的地方,“会”指人的积聚。宋代儒学大家程颐 的《二程全书》中有“乡民为社会”之句,意谓乡民积聚于祭礼的地方,可见人群聚集并进 行一定的活动是“社会”的原意。在前近代,对于个人来说,社会仅仅是个自在的“共同体 ” ,而不是自为的关系化的“事物”。在专制体制下,一切社会活动不可能有“自主”的结果 。传统社会除了区域行政组织和会馆、书院等组织外,几乎没有社会化的功能组织,因为封 建朝廷严禁民间结社,而区域行政组织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功能组织。没有社会化的组织来承 载、发挥社会功能,社会自然不可能成为一个自为的“事物”。近代上海市场社会的兴起, 即是经济社会功能群体的确立和功能作用的发挥。
近代上海经济社会的功能群体主要有大小企业组织和各式自发的经济结社组织等。这些功 能群体在一定的政治体制下,对经济社会的形成及其运作和社会控制均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企业属经济社会微观层面上的组织,更多地具有经济学的属性,我们这里主要分析企业以外 的社会化(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性功能组织及其社会控制的关系。
功能群体的产生以社会功能分化为前提,是为了实现或承担某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社会功能 而建立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组织。晚清以来,上海社会解组中孕育出了新的功能群体,有 些是旧群体功能的蜕旧出新,职能扩展延伸,有些是新萌生的现代化的社会团体。
晚清时期,上海租界当局和清道、县政府并没有专门化的经济管理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和 市场运作的规范和约束主要靠民间的约定俗成的习俗,而实现这种规范,控制社会均衡的社 会化组织早期来自传统的社会资源——上海地区的会馆和公所。
会馆公所等原是商旅组织,古已有之,主要为异地的同籍联络乡谊所建,提供住宿等福利 性服务,一般设有义冢、丙舍、庙堂等。晚清沪地移民积增,会馆公所林立,其功能和性质 逐步扩展嬗变,由一般的客籍组织演化为具有较多社会、经济功能的社会组织。其一,协调 、统一同籍、同业的社会化活动;如晚清沪地宁波人两次与法租界当局的冲突,进行罢市, 号令和指挥群体的机构就是四明公所。清末上海商界的不少全国性的政治通电由公所、会馆 的名义签署。其二,制定行业制度、条文;由于同乡共业,不仅公所为行会组织,会馆实也 是行会组织,行业内的制度,惯例等往往由公所会馆的会董集议而定。其三,调解、平息同 人经济纠纷和冲突;沪上著名的广肇公所1872-1902年间所作议案143个,调解纠纷案97个, 其中包括合资纠纷42件,一般经济纠纷29件,劳资纠纷1件。(注:宋钻友:《一个传统组织在城市近代化中的作用——上海广肇公所初探》,张仲礼主编 《中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416页。)其四,提供一定的经济资助 和福利性服务。一些著名的会馆、公所在清末,其同人的福利事业有进一步的扩张,如四明 公所在1905、1906年先后投资八万元在公所大堂和西厂宁寿里设立医院,贫民不收费,民初 还建立四明医院。宣统三年,在会员中产生“宁波同乡会”,“援助鳏寡孤及残疾者亦所费 不赁”。(注: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1984年出版影印本,第303页。)晚清的会馆、公所等不仅执行经济上行业协调职能和扶贫济困的福利功能,还设 立祠庙祭祖拜神,举行岁时祭奠。这些经济协调、福利事业和浓郁的宗教般活动使同人产生 了深厚的向心力和归属感,而会馆、公所大都有一定的章程和约定俗成的法规约束会众,使 之成为晚清时期上海市场社会中极重要的一个功能化组织,具有明显地社会集散和社会控制 的功用。开埠前(1644-1842年),上海有同乡同业团体30个,开埠后(1842-1911年),迅速增 加至100多个,其分布几乎遍及各行业。这些社会化的经济团体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协调和均 衡功能,维持着民间市场的正常运作,具有很强的自治效率。1911年在四明公所中成立的“ 宁波同乡会”,明确地提出“以团结同乡团体,发挥自治精神为宗旨”,这个宗旨反映了晚 清会馆公所重大的功用和职能扩展。
(二)
组织即是一种制度,会馆公所的功能群体实际构成了晚清上海市场制度条件的一个极重要 的支架。
结构决定功能。传统会馆、公所的社会组织虽在市场化经济发展中,不断嬗变,但其旧式 的制度框架不尽能适应市场社会新的需求。20世纪后,一些传统的会馆、公所内有见识的会 董、议员力倡改革,以求改变理念,担负起新的社会功能,但积习太久,往往进程迟缓,其 社会作用日见萎缩。随着市场的发育扩展,一方面原有的行业分工细化,分化出新的行业; 一方面,许多新的现代化的工商、金融、建筑、运输行业兴起;市场运作日趋复杂化、多样 化,也出现了无序的倾向。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新的社会组织的协调和管理,整饬经济活动 的秩序。近现代经济社会进化有两个维度——市场化和合理化。在市场化和合理化的推动下 ,新的经济社会功能组织产生。在市场分化的情况下,行业化,专业化的同业组织普遍兴起 ,成为清末以来上海经济社会进行行业管理的主干性社会化组织。社会群体进一步朝着功能 化职业化发展。
同业组织的形式、名称有所不同(注:近代上海同业组织有协会、联合会、商会、公会等多种名称。),民国年间最一般的组织形式是同业公会。1917年和192 9年,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分别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工商同业公会法》。1929 年5月上海市社会局根据南京政府的《工商同业公会法》整理和改组工商同业组织,要求一 地区同业行号在七家以上时,均要依法组建同业公会。据统计,1936年上海工商同业公会总 数达236个,其中工业同业公会40个,商业196个(注:黄汉民:《近代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进步中的作用》,张仲礼主编《中 国近代城市企业·社会·空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78页。),同业公会的组成有两大块:一为20世纪 后新建,一为旧式公所依法改制。
关于上海同业公会的社会化功能,学术界研究尚少,上海经济史专家黄汉民先生的“近代 上海行业管理组织在企业发展与城市进步中的作用”一文,对此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上海 同 业公会的社会化功能,主要有:(1)在政治经济活动、社会互动中,团结同业,代表同业利 益,与政府和社会各方交涉和发生关系;如在国内税制改革、进出口关税改革中,代表同业 向政府陈述同人的要求和愿望,为会员企业提供融资和贸易诸方面的担保等。(2)在生产经 营中,为会员企业提供各项服务;如组织商品展览会、设立实验场所推广优良品种、先进工 艺、成立产品质量研究会等。(3)协调规范同业经营行为,维持企业生产、销售和市场秩序 ;各同业公会对本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工艺制造、产品质量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不同质量等 级的产品有不同的售价要求,不允许以次充好,也不允许随意跌价。(4)在市场环境或供需 条件变化的情况下,以企业协调为基础,统一同业意志,进行行业决策,以强化同业市场行 为的有效性;如20世纪二十年代上叶的华商纱厂联合会的各厂纱锭停工的决定和实施,等等 。(5)投资组建一些本行业的辅助性“公共”经济实体,如联营所、银公司等,为本行业的 产品营销和社会融资提供特殊服务。
同业公会的社会功能与传统的会馆、公所比较是个更具市场化、合理化的社会功能团体。 首先,它的章程规定和组织结构具有民主化、公开化的特点。只要符合规定,本行业的厂商 都可以入会,会员企业的权利义务平等享有;公会领导人由行业会员选举产生,内部设立董 事 会、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等;任何会员企业如对公会决议有异议都可提请公会重新 审议。其二,公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会员企业的会费,其形式有一次会费、周期性会费、自 动捐募等,也有一些经费来自公会的经济实体可获得一定的利润。其三,公会功能专业化, 公会的服务对象定位为行业厂商,对本行业的企业提供产、供、销等方面深入细致的专业化 市场化的服务(一些大的行业内分有不同的专业性同业公会),而非传统会馆、公所对移民的 较宽泛的福利性服务,行业中人个人的福利等社会性事宜一般不再包括其中,这些功能大致 转移至企业和其他职能部门。其四,同业公会对同业的管理权威主要来自市场化的因素;一 方面缘于公会对企业的真实而周到的服务,一方面源自民主式的集中意志。公会的领导成员 大都是行业的领班人物,而非过去会馆公所的名流士绅,这些行业大业主对行业市场具有很 强的左右能力,会员企业对公会决议的遵从,与其说来自会议决定,毋宁说源自市场意志和 市场权威。
民国年间政府的职能有了比晚清进一步的分化,但仍比较粗放,政府要求各地区成立同业 公会,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借用”它的社会化功用。上海同业公会按政府的社团法律组建, 其负有配合、协助政府管理行业的职能。行业公会在经济社会中是个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中介 式的组织,对行业企业具有社会化管理和控制功用。但应该指出的是,正由于同业公会一定 程度含有“第三部门”的性质,其社会化的权利不具有强制力,所以它对企业的约束是有一 定限度的,超越行规的“不法”企业行为在民国时期的上海还是屡见不鲜。
民国期间上海有数百个大小不一的行业公会,其在各行业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协调和社会控 制功能,维持着专业市场和区域市场的秩序。这些行业公会在整个上海市场社会的影响力有 所不同,一般而言,行业公会的社会影响力与其涵括的经济总量、市场关联度成正比。大的 行业公会,如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上海丝厂茧业总公所、上海面粉业同业公会、上海绸缎 业同业公会、上海橡胶业同业公会、上海洋货九业公所、上海百货商店同业公会等,因其行 业大,产值高,职工多而影响大,另一类如上海银行同业公会、钱业同业公会、轮船同业公 会等因其市场关联度高而社会影响力大;特别是银行、钱业两同业公会,不仅因市场金融关 系,而且其资产实力雄厚,其在上海市场社会的影响力最巨,颇有呼风唤雨之能事,各业公 会莫不关注之。另有大量中、小同业公会,大都不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在社会群体中地位较 低,社会能量较小。
民国以后,国货运动得到朝野的关注,民国初年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现了一批国 货团体;如中华国货维持会、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中华国货产销协会等,由于这些经 济团体大都为跨行业的组织,并有上海实业界著名厂商的参与,得到经济社会头面人物的支 持和政府的鼓励,在二三十年代展开了一系列有效促进国产商品产销的活动,颇为社会各界 所瞩目,社会影响很大。
(三)
上海经济社会影响最大,全局性的社会化组织为上海总商会。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 立,是为全国最早的省级商会;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1912年民国立,公定名称为上 海总商会。20世纪前三十年间,上海总商会为沪上各行各帮之集成,不仅为上海经济社会领 袖组织,也为全国工商业之翘首,号令议决颇孚众望,组织张阖关联社会风潮。
据文献考察,自1920至1929年间,上海总商会的社会功能体现如次:
(一)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反映上海工商界中上层意向。在清末新政、地方自治运动、上海 光复、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五四运动、齐卢战争、北伐战争等历次重大历史 事件中,上海总商会以中上层绅商和资产阶级立场为出发点,或通电、条陈意见书,或组织 集会活动,或出示资助,或决议号令商民等方式介入社会政治变革,表示态度背向。上海总 商会被视为这一时期沪上实业界的代表,成为最为活跃,最有份量的社会组织。在清末民初 的社会政治运动中,总商会所起的积极作用较多,自五四运动后,总商会的政治态度渐趋保 守。
(二)抵制政府的不良经济举措、经济政策,维护商界利益。民国后,政治环境变化,商人 社会地位提高,上海总商会的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 特别是税收政策,敢于表明真实的态度,或请愿,或条呈,或通电对政府施加影响。如1915 年上海总商会同沪南商会三次致电北京政事堂、财政部要求收回货税加征二成之成命;1916 年总商会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拒绝日本与华合办汇业银行,发行纸币;1918年严词反对苏省利 用厘改税加重商民负担;1920年总商会对政府裁厘加税问题拟定办法六则,集会陈说;1922 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各金融机关,请一致拒绝为政府承募一切公债;1923年2月总商会致 电北京政府,要求政府于4月30日前公开财政;1924年8月,要求北京政府取消收征路、电、 邮、航的关税附加税;1927年总商会电致南京政府反对内债认购债额十分之一的盐余国债券 办法;1928年8月上海总商会组织请愿团赴南京,提出十项请求,呈文保护商人利益;同年9 月电致国民政府要求迅谋恢复关税一切主权;1929年上海总商会发表宣言,反对政府借裁厘 改办特种消费税,等等。上海总商会不仅对本地政府和中央政府的不良政策进行直接抨击, 也进谏其他地方政府的损商政策,颇有中国第一商会的气概。1926年上海总商会致电福建省 长:“贵省举办面粉税,……事属隔省,似未便带为吁请,第念机制面粉为国内重要实业, 经部处核准,概免税厘有案。年来以国内小麦原料缺乏,成本昂贵,洋粉乘机源源输入,该 业已日处风雨飘摇之中。仅恃免税免厘,一线生机籍以支持。若再征值百抽五捐款,则销路 更 滞,何以立足。”(注:“请取消面粉捐致闽当局电”,《上海总商会月报》第6卷第6号,<会议纪载>,第5页。)急公好义,据理力争,以天下为己任。在20世纪三十年代前,上海总商 会对政府的不良政策和征收恶税,反映敏捷,敢于抗争,对各级政府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压力 和舆论压力。
(三)发挥一定程度的上海全局性的经济协调作用。上海地区一些全局性,或跨行业的经济 问题往往由上海总商会出面协调斡旋。如1910年,应上海各业商人要求,函致上海华商地产 公司各房东,指出房租日高,商民被迫歇业迁徒,十室九空,租安出自,要求顾全大局,普 减 房租;1911年总商会与汇丰银行订约,借款规元200万两,以济市面紧急之需;1916年北京 政府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兑现银,上海中行分行抵制,总商会为此迭开会议,发布公告要 求各商号对中国银行发行之钞票一律照办,维持市面;1919年现银外流加剧,总商会发布公 告,提醒华商勿贪一时厚利,致贻重大危机;等等。调节本市商事纠纷,会同别地商会调节 跨省区商事纠纷也是总商会的一大职责。
(四)助商护商的社会化服务功能。总商会内部设立一些机构,旨在为商民服务,如1919年 添设外交、商务、统计、研究四科,扩大功能,以资应付。总商会还创办了一些附属单位和 团体,提高社会化的服务。这些单位有:1921年8月附设商品陈列所,1921年创办《商业月 报》(后改为《总商会月报》),1922年创办商业图书馆,1922年建立商业补习学校,1927年 组建社会童子军等。1917年总商会针对会审公廨如遇讼案,不问商人体面、信用将商人立刻 拘 押捕房之状况,致函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要求凡被控华商系总商会会员,即应视为体面商人 ,一律改提为传,顾全华商名誉信用。租界当局复告自应妥筹办法,交通办理。总商会的服 务性功能与同业公会相比,不及之细致和具体,主要是社会性的而非专业性的。
(五)组织沪上工商界的社会性活动。总商会在上海历次的抵货运动、国货运动和二十年代 的“废督裁兵”、“民治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1905年的抵美运动中,上海商务 总会议董曾铸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慷慨激昂,领衔通电清廷要求拒签新约,发挥了积极的 推进作用。7月上海总商会再次召开会议,当场许多商董签允不定美货,并决定向全国35个 商埠发电,宣布抵美行动正式开始(注:以上上海总商会活动史实资料来源,参考徐鼎新著《上海总商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1991年,附录“上海总商会大事记”和其他有关报章资料。),成为抵美运动的发动者。二十年代初的国民运动,上 海总商会是重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废督裁兵”之说由上海总商会首倡。1923年反对曹锟 贿选的民治运动中,上海总商会成立“民治委员会”,发布政治宣言,公陈政治主张,俨然 为民间社会的代表和领袖。
功能化组织是社会产业化、城市化及合理化的载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经济社会的 工商社团组织结构大致为三个层次,总商会为第一层次,其会员为全市的大中企业业主(注:加入晚清商务总会,成为会员需缴年费300两,1912后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年费降为100两
,不久团体企业入会缴年费50两,年缴30两者为会友。一般小企业和店家限于财力入会较少
。), 会董为各业的领班人物;此外沪南商会、闸北商会为略次于总商会的市级大型商会组织,有 上海南北商会之称。第二层次为各行业公会,会员有各业厂商组成,会董为各业实力派人物 。第三层次为区域性的马路商会,由一条马路的店家和小商贩组成,成员为一些小行业、手 工业的业主。在这三层结构中,具有较强现代化社会功能的是第一、第二两个层次。第一层 次——以总商会为代表,承担的主要是政治化功能,组织社会,集中民意,为民请命。第二 层次——行业公会,承担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功能,指导企业经营生产,维护市场秩序。行业 公会中的主要势力来自行帮:行帮一直是上海经济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民国后行帮势力虽 有所消褪,但影响力仍在,对行业仍有较大的约束力。总商会与行业公会及马路商会之间, 并不存在形式上的隶属关系,主要是一种联络、指导关系,行业公会及马路商会的一些头面 人物往往是总商会的会董;总商会的意志、决议精神通过个人及媒体传达渗透及下层商会。 由于总商会的代表性和社会地位,使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各业公会、下层商会大都能瞻其 马首,应其号召。
(四)
清末民初是上海市场社会功能群体最为活跃的时期,也是最富独立性的时期,特别在民初 与军阀政府的抗争中,以上海总商会为代表的上海工商团体,敢于直言政府之弊端,抨击军 阀之窳政,颇有豪迈之大气。示一例:1922年北京政府发行毫无保障的“十二年公债”,上 海总商会“通电中外,在政府未实行裁兵及财政整理以前,(各金融机关)万勿再行承受借款 。政府现拟发行新债,殊于国民期望相反,誓不承认”;(注:上海总商会“致全国各金融机关请一致拒绝政府承募一切债券电”,《上海总商会月报 》第3卷,第2号;转摘自徐鼎新著《上海总商会史》,第309页。)指出“立宪国家,国民皆有监督 财政之责任”,并要求政府公开财政;态度强硬,措辞激烈,直接与北京政府对抗,表现出 了强烈的独立意识。穆藕初在《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撰文道:“是以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 适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方 法逼迫政府改良内政,则商业庶有恢复之望”。(注:参见赵靖主编:《穆藕初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3页。)上海经济社会群体的政治勇气来自市场经 济崛起的内在驱动。
上海商会的这种独立性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很快消蚀。蒋介石在上海资产阶级的资助下上台 ,但蒋氏上台后不久即不容于上海总商会的“政治干预”的作风。南京政府借接收整顿之名 ,一步步实施对上海商会的控制,1930年依据国民党政府的《商会法》建立的上海市商会成 立。市商会在政治上属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领导,在行政上受上海市政府 和社会局领导,商会已受到国民党党政的着力控制。在这之前,上海社会局颁布条令对行业 公 会进行了整顿。1930年后,上海市商会虽然仍展开着各项社会化的活动,但以往商会独立的 政治功能已大大地萎缩了,由商会策动的自主性政治化、社会化的活动渐趋偃息。
1929年后上海总商会渐为南京政府所控制,处于依附地位,整个上海市场社会的发展变化 也逐步由市场主导型变迁向政府推动的强制型制度变迁过渡。在视统治和控制为政治权威之 要义的社会中,政治势力多元化时,社会群体成为倚借之“砝码”,受到重视,比较活跃; 当政治力量统一后,社会势力、社会组织往往被视为异己,受到抑制。清末和北京政府时期 ,上海总商会颇有代表上海工商实业界,为商众利益冲锋陷阵的气概;至1929年后,这种独 立气质、慷慨勇气逐渐消褪,其深层原因乃在于中国的集权体制下“社会活动空间”的张缩 。 清末朝廷、北洋政府一方面统治力较弱,一方面其统治重心在北方,南方控制相对疏略,而 南京政府统治能力强化且统治重心在东南,对沪控制尤其严密,这就是上海总商会政治能量 和活动空间渐为缩小的根本因素。资产阶级以政治独立性为代价换取政治上的“有序性”。 在政府与社会功能组织的关系上,政府始终处于主动的,强势的地位,社会群体的兴盛取决 与政府的政策态度。
经济性社会功能组织是社会群体的基干,往往是最先发育生长的。近代上海经济社会组织 变革的压力来自“内生”和“外来”两方面。传统社会的一体化被打破后,新的社会同构性 远未形成,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异质性到处存在,充满了形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现 象。这种不协调现象表现在社会经济群体的运动上,其“有效行为”与正式的组织机构的一 致性往往是短暂的,当组织“正规化”了,其“有效行为”却消失了。
市民社会构建有两大要件,一为产生“公共领域”,此为解决政治民主化的空间和环境问 题;一为生长出自立的社会化功能组织,此为培育政治民主化的“法人”和集合主体,形成 与公共权力制衡和搏弈的社会力量。这两个要件的形塑正是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和“自由 竞争”原则向社会政治局面渗透的进程。近代中国崎岖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和运作形态,在 此基础上“公共领域”和自主性社会群体都不能真正发育起来,也难以形成“政治社会学” 意义上的实质性的“市民社会”。
收稿日期:2001-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