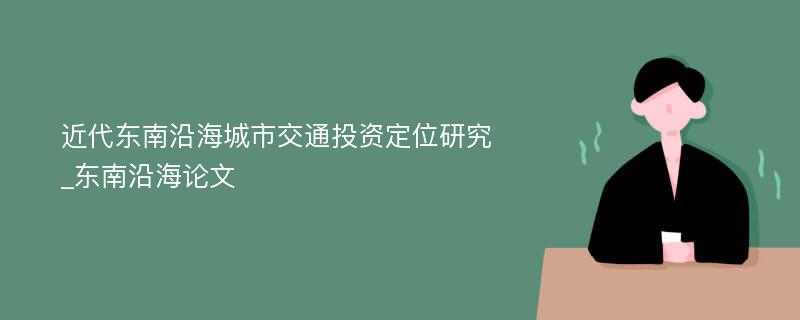
关于近代东南沿海城市交通投资取向问题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交通论文,取向论文,近代论文,沿海论文,东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交通企业的投资与一般企业投资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以城市作为基点的一般企业投资,如:商店、工厂、银行等等的投资,都可以视为点上的投资。它(它们)的资本绝大部分集中投放于这一城市之中。因此,一般企业的投资额可以统计在该城市投资总数之内;由这一项投资产出的产值,也可以统计在该城市国民经济总产值之中;它(它们)的盈亏状况,可以成为衡量该城市经济兴衰的参数。
交通事业的投资不应视为点状投资,而是线状分布形态的投资。尽管交通类企业的总公司或总管理机构设在某一城市,因而在城市企业资本统计时也可以将其总资本额统计在内,然而,重要的是不应当停留于此,而应当(或者说必须)进一步依据这一项投资所形成的诸交通线作分割统计,因为该项总资本客观上是沿着它所开拓的各条交通线作不均匀状态分布的。它(它们)的盈亏状况不再应当简单地成为总部所在城市经济兴衰的衡量参数,而应当成为交通线沿线区经济兴衰的衡量参数。
交通事业投资线状分布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对交通投资取向进行考察。这不仅涉及区域交通布局以至区域经济开发合理性的研究,涉及交通投资经济效益的研究,而且涉及科学评述近代外国资本在华投资交通事业的历史地位。
近代东南沿海城市交通事业,在投资取向上有哪些特点?
(1)发人深思的第三位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以上海为枢纽的国内轮运三大航线中,长江航线上的投资量居于首位,北洋航线居于第二位,东南沿海航线上的投资量却屈居于第三位。
对近代中国轮运业投资线状分配状况,至今还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聂宝璋先生所编的《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史料丰富、详实,收录了大量关于以上三航线中轮运业兴起、发展的史料,尤其是对沿海、沿江主要城市交通企业均有记载,然而,基本上还是以口岸城市交通企业为基点编篡史料,或者以某些著名企业的形成,发展及兴衰加以编篡的,而没有就交通投资线状分配情况作系统的统计。在另一些关于企业投资研究的相当著名的专著如:中国学者刘大钧的《1929年外人在华投资》,日本学者樋口弘的《日本对华投资》、 美国学者雷麦的《外人在华投资》等等,虽然作了一些区域交通投资的统计,但是,还是以城市区域的交通投资进行统计、分析的,也没有按照交通线(航线)的投资进行统计。这样,我们进行投资取向研究工作时,就难以找到现成的统计资料了。因此,本文只能依据各轮运企业在各条航线上的轮船及吨位配置的粗略估算作为参照指数,因为它们基本上可以反映三大航线上投资分配状况。
轮船航运业的投资在近代东南沿海诸省的交通投资之中是强项。
1843—1860年间,外国资本在我国埠际航运业的投资,主要地还集中于东南沿海航线上,而且,至少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南中国海航线之枢纽点还在广州、香港。只要看一下这一时期广州以北开新口岸城市船舶航行状况就足以证实了。据记载“1846年在上海的十七艘美船(五千三百二十二吨——英国统计数字)中,全部都是来自和开往香港的。”而美国则是最早,也是早期最有势力的沿海航运投资者。厦门港进出的船舶之中,最早出现的“定期班轮”是“航行在香港、汕头、厦门和福州之间的”小轮。福州的记述则是“本港与香港之间有四艘沿海轮船航行,这些船舶轻易不离开这条航线”;由福州“外销的茶叶通常由帆船来承运,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帆船承运木材等货物。这些帆船装上货物后驶往上海与宁波”。〔1〕近代中国第一家专业的沿海轮运公司“省港邮船公司”(Canton,HongKong Steam Packet Co)早在1850 年便“每日”有轮船“航行在广州和香港之间”。
1860年以后,由于长江及北方沿海口岸相继开放〔2〕由于各国在华轮运业的投资取向急剧变化。不仅“一涌而上”地取向于长江航运投资。〔3〕而且, 在北洋航线上的投资也开始超过东南沿海航线上的投资额。从此以后,在以上海为枢纽的三条国内航线上,东南沿海的轮运业投资,长期处于第三位了。
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称雄于中国国内航线上的投资者是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它在三条主要航线上的投资配额如何呢?据1872年的统计,旗昌公司在长江航线上有9艘轮船,16819吨;北洋航线上有6 艘5780吨;在东南沿海,它仅保留了沪——甬航线,只配置了轮船2艘, 仅2719吨 。〔4〕虽然,旗昌轮船公司减少南方航线投资是受到它与怡和、宝顺等洋行船队协议之约束所致,那么,取代旗昌而堀起于南中国沿海航线的怡和船队的投资状况如何呢?在上海与福州之间开辟定期航线的怡和船队,以更大的“热情”,在“几乎所有外国商界的支持”下,同时开辟了上海——天津航线,1870年就投入了4艘海轮,1872年, 又进一步筹集50 万两资本, 组建华海轮船公司(China
Coast SteamNavigation Co)投入北洋航线。〔5〕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起而取代旗昌轮船公司霸主地位的是太古轮船公司(China Steam Naviga tion Co)。尽管创办时的目标就是“旨在与旗昌公司就长江航运问题决一雌雄”〔6〕但是,它对于“将成为一种主要的获利来源, 即运送大豆饼”的北洋航线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874年取得了专门从事这一业务的海船组合(The Coast Boets Omery)的代理权, 并于1883年兼并了海船组合。〔7〕所有这些事实都证实了, 当外国资本得以大规模楔入以上海为枢纽的三大航线之后,它们的投资取向,第一位的是长江航线,第二位者为北洋航线,东南沿海航线则列入第三位。
这种状况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变化没有? 让我们看一下1913年三大航线上轮船及吨位配置情况便清楚了。这一年, 长江(仅以沪——汉航线作统计)航线上有轮船31艘,81035吨,北洋航线上,23 艘,27355吨;东南沿海航线上,17艘,20812吨。〔8〕中国国内航线投资取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仍然维持着上述状况,以1937年,三大交通网络各口岸出入轮船总吨位作比较:长江航线,4196.6万吨;北洋航线,至少在2967万吨以上;东南沿海航线,约为2923万吨。〔9〕虽然,这时由于中日战争的影响,华南各口岸航运业受战火影响当小于东北华北地区,以东南沿海为取向的航运业投资额却仍然处于第三位。
以东南沿海各省(江、浙、闽、粤)陆上交通的投资而言,更不及北方以及腹地各省,更为明显地处于第三位。我们将就此与东南沿海陆上交通投资的特点结合起来,在下文中集中讲述。
(2)陆上交通投资滞后, 投资额远不及北方和中原地区。
我们现在从中国铁路史上看到的,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是1881年建成通车的,位于北方的唐胥铁路。富于戏剧性的是近代中国第一条铁路原本应当是1876年建成通车的第一次淞沪铁路,但是,因为它建成不足16个月就全线拆除了,于是,原本东南沿海地区应当领先一步的陆上交通投资,一下子比北方地区滞后了17年。直到1898年,东南沿海地区才有了第一条铁路,那就是重建的淞沪铁路。而此时,北方以及腹地已投资建成(或部分建成)的铁路已有唐胥、唐芦、津沽、大冶、关东、津芦、芦汉等八条铁路,其中通车的已有572.8公里。〔10〕
如果从投资意向的角度考察,东南沿海地区实际的铁路投资要比投资意向滞后近40年。 早在1858 年, 上海的美商琼记洋行(AugustineHeard&.Co)就提出了投资修筑上海——苏州的铁路计划。 这以后的近二十年之中,西方人一直在策划投资于东南沿海开筑铁路,只是都没有实施。
公路的开筑在整个中国近代交通史上起步都比较晚。尽管如此,由于北方地区原有大量商道为基础,加以地区间的交通运输不象东南沿海有密布如网的水道可以依赖,因此,起步还是比东南沿海早。这里,以河北与浙江,天津与上海作个比较。
当浙江省长吕公望于1916年拟订以杭州为中心开筑公路计划之际,河北省的个别商人已经购置了汽车在张家口到库伦(即今乌兰巴托)之间试运营了。1917年,就在原有古商道基础上修筑了河北省第一条长途汽车路“张库汽车路”,长达2345里(1172.5公里);而浙江第一条近代化的公路——杭余公路,要到1923年10月才筑成通车,当时所筑全长2.88公里。〔11〕
上海与天津相比,由于上海之开埠比天津早了十余年,因此,市内(租界内)马路当然比天津更早形成,但是,就近郊公路而言,天津的起步却早于上海。早在1882年天津就“采用国外筑路方法”在当时“尚属城郊”的院浮桥到紫竹林租借地之间开筑了第一条“官道”,它的“施工工艺与现今修筑碎石路的施工方法无甚出入”,实际上它只是沿用了“官道”这一旧称的近代公路。上海的第一条近郊公路——军工路(吴淞蕴藻浜到杨树浦今平凉路底,当时也属城郊),却迟到1919年才竣工通车。近代化的长途公路,天津的“京津大道”始筑于1917年,上海的沪太路则要到1920年才动工修筑。〔12〕
东南沿海近代陆上交通的投资额远不及北方和腹地诸省。
从公路、铁路在各地区的配置状况考察。据1930年的统计,全国已筑成通车的公路约有27410公里,其中,江(包括上海)、浙、闽、 粤四省加在一起仅有5018公里约占总数之18%;辽宁一省却有3923公里,要占总数之14%;山东一省有3629公里,占总数之13.2%;与腹地诸省相比,东南沿海各省的公路数量也显得十分微薄,江、浙两省的公路合在一起只有1343公里,而湖南一省的公路却有1838公里,以一省之公路要超过江、浙两省公路总长的36.7%。〔13〕铁路的地区配置同样说明这一状况。以外债形式的投资在近代中国铁路投资总量中占着绝对主要的地位。据统计,清末铁路外债总额为34801万两以上,其中, 投放于东南沿海的铁路外债(不包括贯穿南北的京汉、粤汉铁路)约为5157万两,东南沿海诸省所占的比重仅为14.8%。〔14〕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是1949年的统计数字。这时,全国已筑成通车的铁路,约为288291公里,其中,以东南沿海江、浙、闽、广区域内交通为投资目标的淞沪、沪宁、沪杭、浙赣、广九、漳厦等铁路在一起(不包括以贯通南北为投资目标的津汉、粤汉等铁路),总共约为1450公里, 只占全国铁路总里程5%左右。〔15〕
(3 )与江海航运复合取向的陆上交通投资多于向内陆山区独立取向的交通投资。
从江、浙、闽、广四省铁路、公路取向上看,以外国资本投资为主的铁路,与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公路相比是有一定差异的。
铁路取向,大多与江、海航运线平行,属复合取向。
沪宁线:上海——苏州——无锡之间基本上与运河平行在运河北岸行进;无锡——常州——丹阳在太湖及其水网地区行进,在丹阳与镇江之间跨过运河后一路紧贴长江西行直至南京。
沪杭线:浙路段沿运河东岸、杭州湾行进;苏路段在太湖水网区及运河沿线行进。
广三线:自广州沿西江北行,直至西江与北江合会之处,即三水站。
潮汕线:自潮州沿韩江西岸直通汕头,沿线各站,如:枫滨、益巢、华美、庵埠等均在韩江岸边。
南浔线:从江西南昌沿着鄱阳湖与修水北行直到长江边的九江。
漳厦线:全线基本上与九江龙江平行。
唯独1930年以后兴筑的浙赣铁路(最初所筑当时称杭江铁路,杭州——江山段)稍异。虽然它出杭州以后一路上也沿着西兴江、苏溪、浦阳江、金华江、信安江、兰溪等内河向西南行进,过玉山以后则沿着江西四大江之一的信江开行,然而,它终究是跨越了浙西山区(丘陵地带),对于内陆开发应当说是有积极作用的。然而,由于中日战争,它时建时拆,多为军事所征用,客观上直至1949年以前还难以发挥其经济开发之功用。
从有利于向腹地发展的角度考察,近代东南沿海诸省公路投资的取向状况优于铁路。总体上考察,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沿海一线之公路,大体上还是沿着传统航路取复合投资之态势,但是,二、三十年代之交,由上海、杭州、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各大城市向腹地开筑了一些公路,它们大多穿越了浙西、皖南、赣东北、闽北、闽西等山区。以浙江而言,三十年代初已开筑的公路有五大干线,其中唯独“京杭国道”(南京至杭州)基本上沿着长江、太湖、运河等内河航路取复合投资形态。另外四大干线,都穿越了相当长的山区(丘陵地带),其中,杭福国道穿越了闽北山区;杭南公路(杭州至南昌)穿越了浙、赣山区;杭安公路(杭州至安庆)穿越浙西、皖南山区;衢福公路(衢州至福州)穿越了浙西、闽北山区。
以福建而言,除了上述两条闽浙公路以外,三十年代初已开筑的还有两条闽赣公路,一条闽粤公路,都穿越了闽、赣、粤北山区地段。
江苏省东有上海经济中心,西有南京政治中心之故,在二、三十年代公路发展更为系统化一些。在上海为枢纽的三大交通网基础上,已形成了诸如南通、淮阴、宿迁、徐州等等区域交通中心,完成了近三十个县之间的公路交通线伸入苏北腹地。
广东直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才较有规模地修筑近代化的公路。广州作为航运、铁路、公路等复合型的交通中心,它的地位在东南五口之中仅次于上海。这一时期修筑的粤闽公路、粤赣公路,以及两条粤桂公路,都以广州为始发点。这些公路的走向,虽然,基本上与珠江内河航线、粤汉铁路呈平行的复合状态,但是,它们又都有不少路段伸入了岭南山区。〔16〕
辩证地认识近代东南沿海城市交通投资取向问题。
在我们初步了解近代东南沿海城市交通投资取向的三个主要特征以后,需要进一步考察这些特征是在什么样的主客观条件下形成的?
交通事业是社会经济运动的一个环节。对交通事业投资取向作出判断的过程中,既要受到投资者主观意识的支配,同时,又必然受到客观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所以,必须以辩证的观念去加以考察。才能获得科学的认识。近代东南沿海城市交通投资取向特征形成的条件是十分复杂的,这里,我们从市场和投资效益两方面作初步分析。
(1)市场——幻想与现实,决定东南沿海航运业投资处于第三位的根本原因。
迅速占有商品市场的欲望首先推进了东南沿海近代化航运业投资。
到北方去!到新开辟的通商口岸去!这是鸦片战争后广州洋行大班们迅速作出的反应。早在战前,他们已经确信,进入这些口岸城市就意味着“和三万万或四万万人开放贸易”。英国商人相信“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那么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美国人也相信“连贯该帝国各部分的口岸”开放后,“对于美国产品的需求之扩大”也是“必无疑义”的。〔17〕因此,数以百计的洋行、散商争相北上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或者一举北迁,或者开设分行,他们当然必须在东南沿海航线上投入大量航业资本。或则让自己的船队,包括帆船、飞剪船、趸船等等,定期航行于五口之间,或者雇佣来自美国、挪威的散户船商的各类船舶,北往南来,不绝于途。与之同时,来自英、美、德、法等国的远洋商船,在开辟直接进入新开四口的远洋航线的同时,不同程度上参与东南沿海的航运业务。各国商人将大量航业资本投入东南沿海航线以后,并没有能迅速占有中国的商品市场,1843—1845年之间,迅速增长的进口工业品在东南五口严重地积压起来。在中国封建小生产农业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强固壁垒面前,他们占有商品市场的欲望碰了壁。
尽管,当时的现实已经十分明显地证实了,外国商人战前对中国商品市场的估算,只是一种幻想中的市场状况。外国商人却不愿承认这种现实。他们既不愿意承认罪恶的鸦片贸易造成大量的中国白银外流,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外之间正常的商品交易;更没有意识到中国封建小生产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强固壁垒,对于他们“挖掉”“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18〕这一“神圣”使命而言,是前所未遇的难题。
于是,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交开始,他们重新弹起鸦片战争以前的老调。指责中国政府关税壁垒阻碍了他们的商品去占领市场,大部分中国沿海、沿江市场不开放是最大的障碍等等。而且在这类舆论先导之下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增开天津、牛庄、登州、镇江、南京、九江、淡水、潮州、琼州、台南等地为通商口岸,迫使清政府开放长江航线,开放北洋豆石贸易。
与之同时,各种形式的旅行、考察、探险活动,沿着长江及其众多支流,伸向腹地。时过不久,各种旅行记、考察报告应运而生。外国商人不仅逐步地深入了解中国广阔腹地的自然、地理风貌,而且,逐步摸清了内地的出产、物流状况,以至社会状况。
他们以敏锐的商业眼光衡量着长江及其支流的商务价值:“扬子江自上海至汉口(长六百哩)一部分,为一极优良之内河航路(冬季可航行之深度至少八英尺至十英尺,夏季至少二十英尺至三十英尺)。汉口以上,在夏季期间,倘以特种船舶行驶,则可再航行八百哩。且其支流之大者,大部分可以行驶帆船与小汽船,而达至离总流百哩或百哩以上”。他们尤感兴趣的是“与各支流河口相近之处,各有一个‘开放商埠’,足为往来上海货物之补助集中地点。”“在扬子江口三角洲上”,有“约五万平方哩之地”。“人口达四千万名以上”;而“扬子江全部流域,广约七万五千平方哩,共有人口一(亿)万八千万人,超过全世界人口十分之一”,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世界未有任何他埠,其潜蓄之供求范围,有如上海之大者。”〔19〕
这一切,对于前期“碰了壁”的各国商人无疑又是一贴兴奋剂,再一次煽起了占领内陆市场的欲火。因此,在上一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们又一次集中地扩大航运业投资,投资取向则集中于长江航线上。
1861年,美商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Co )定造的“火箭号”(Fire Dart)率先从上海直航汉口。这以后, 上海的“几乎每一家二流以上的洋行都置备轮只参与长江航线上的竞争活动”。〔20〕以长江航线为取向的航运业投资一下子升到了第一位。
应当指出,长江航运业的迅速发展,也没有能够让西方工业品在短期内占领内陆贸易市场。那么为什么长江航运业的投资从此就一直居于第一位呢?另外,为什么取向于北洋航线的投资也超越东南沿海航线而居于第二位呢?
关键在于传统的埠际贸易中的物流量,已经为近代化的长江航运业及北洋航运业,准备了可观的、现实的投资市场。
这里,仅以传统埠际贸易中两项主要商品:粮食和布匹为例。它们合在一起,在传统埠际贸易总额之中占66.75%。
战前传统的埠际贸易中,进入长途贩运的粮食,总数约为225 万吨。长途贩运的两条最主要的航线如下:
A、川、湘、皖、赣大米经长江东下,形成芜湖、九江、 苏州枫桥三大米市,总运输量约为112.5万吨, 占长途贩运商品粮运输总额的50%。
东北(奉天)豆麦经北洋航线南运(即著名的豆石贸易)至天津、山东者约7.5万吨,至上海者约75万吨,合在一起约为82.5万吨。 占粮食长途贩运总额的36.7%。
战前传统贸易中,进入长途贩运的布匹,总数约4500万匹。其中产于苏松太、常锡的布约占88.9%,总计4000万匹。其中300 万匹经内河(运河)运往淮、扬、高邮、宝应地区,不列入长江统计。在3700万匹之中,有三个去向,一是东南沿海航运,运销浙、闽以至南洋,二是沿北洋航线运销山东、河北以及东北,三为沿长江西运汉口而后转运西北。据估算,沿江西进汉口甚少,总计不会超过400万匹,北运关东、 河北、山东最多,至少在1800万匹,另有1500万匹左右南运浙、闽、南洋。〔21〕
上述传统埠际贸易中长江及北洋航线之物流量,会引起外国航运业投资人怎样反应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1861年2月,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人金能享(E.Cunningham)的信,他说:“仅以两湖茶叶而论,总量便估计有7万吨, ”而“回头货”,由上海运销“汉口出售的外国棉织品,估计一开始就会达到2.5万吨”。面对他已经比较有把握的9.5万吨货运量,他已经急急忙忙地敦促福士,必须“不失时机地”,“比他人抢先成事”,要赶在其他外商之前投资创建轮运公司。〔22〕9.5 万吨的物流量已引起他(们)如此激动,那么对于200万吨粮食、近2300 万匹布的物流量所构成的航运业现实的投资市场,势必趋之若鹜是无可怀疑的了,事实上,前文已讲述了六十年代以后长江航线投资迅猛增长,北洋航线上,1862年直接参与豆石贸易运输的外国商船已有86艘,1865 年更是直线上升到274艘之多。
总之,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对于幻想之中的内地商品市场的占有欲,以及对传统埠际贸易提供的现实物流量的航运业投资市场的强烈占有欲,趋使各国航业资本迅速的投向长江及北洋航线。东南沿海航业资本投入虽然也在增长,三者比照之下却已处于第三位了。
(2)辩证地分析、认识地理环境与经济杠杆与之间的关系, 投资效益居于决定性的地位。
在我们考察东南沿海城市水、陆交通发展进程、布局特征,以及它们与北方地区作比较研究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东南沿海水网密布,水运价廉,沿海及内河航运因此而为先导,而且占主导地位;北方地区水运不便,因此陆上运输(铁路、公路)先于东南沿海,而且远比东南沿海发达。这些都说明地理条件在确定交通投资取向过程中的重大影响。但是,应当注意,不能过分地强调地理条件的作用。
中国近代铁路投资序幕在东南沿海地区拉开是经济杠杆在起着主导作用,它们之所以偃旗息鼓是政治杠杆起着主导作用。
铁路投资序幕在东南沿海地区拉开。
最早提议在中国建造铁路是在1849年7月。 提议内容是从上海“修建两条短短的铁路,一头扩展到杭州,一头扩展到苏州”。
最早制订详细的铁路投资计划的是上海琼记洋行(Augustine haerd& Co),1859年它制订计划建筑上海至苏州的铁路。
最早筹组的铁路公司是1863年,由上海琼记、怡和、宝顺、沙逊、旗昌等十七家洋行联合筹组的“上海苏州火车局”。
最早在海外集资,准备在华投资铁路事业的是1865年在英国伦敦成立的中国铁路有限公司(China Railway Co,Ltd)。它准备集资214万两白银建造沪苏铁路和广州——佛山铁路。〔23〕
最早在中国建成并试行一时的是1876年的上海——吴淞铁路。
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起着主导作用。
最早提议在苏州——上海——杭州建造铁路时,所提出的明确意图是“在那两个城市中如果允许外国人自由访问和贸易,那么上海的国际和国内贸易,就会同时在大得多的幅度上进行”。〔24〕恐怕这也是早期一系列筹划投资开筑沪——苏铁路的共同的动机。
1865年的计划更为宏观一些。这一计划中,沪——苏铁路只是英国著名铁路工程专家斯蒂文生(M.Stepbenson)拟订的“综合的铁路系统计划中的第一步,按照该计划修建的铁路要贯通津——汉——沪——广(州)。它的动机在于全方位地“进入黄金之国”。〔25〕
1876年开筑淞沪铁路直接的动机,在于黄浦江航道日益不适应于大型轮船出入,为了便于它们在吴淞泊岸起货而筑此路。
总之,早期东南沿海铁路投资拉开了中国近代铁路建筑史的序幕,期间,起着主导作用的是经济杠杆。为什么这些活动最终都偃旗息鼓了呢?关键在于中外关系没有恰当地处置,即政治杠杆起着主导作用。我们将在《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现代化》一书中集中讲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投资效益在近代东南沿海地区公路投资特征形成过程中,客观上起着重要作用。
东南沿海地区,公路投资起步晚,数量少于北方,伸入内陆山区更少,以及绝少外资投入等特征形成原因十分复杂。
水运价廉,这是基本原因。苏南浙东北一带,直至二、三十年代,物资流通,仍然主要“藉河之便,使用木船竹筏为多”。〔26〕即使在闽西,“长汀、连城之纸,永安、上杭之菸”绝少翻山越岭运销厦门出口,它们还是充分利用内河运输,依靠汀江南行转入广东之韩江,而后运到广东汕头“转口”。〔27〕
汽车技术之传入、推广应用为时较晚,运费昂贵,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追求更高的投资效益则决定了外商绝少投资于内地公路开筑。
所谓投资效益之考虑,单位物流量运价,水运远低于公路汽车运输,这是其一;广大农村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即便在山区,以步行肩挑,运价也远比公路汽车运价低廉,这是其二;早期买办的契约制度及担保制度所确定的中、外商人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外商从投资效益衡量的角度考虑,不会去投资于内陆的公路建设。
输入贸易虽然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状态之中,但是,外商根据与买办所订的契约,只需要将商品运抵主要通商口岸,如:上海或福州、厦门等,以后货物怎样运向内地销售都与洋行无关,买办必需在货物运抵之日起的一个月之内付清货款。也就是说按照买办制度,洋行只承担运抵主要口岸的责任及费用,不承担由主要口岸到内地二级、三级城市、集镇之间的运输责任和费用。
虽然沿海主要港口城市向内陆城镇运销之顺畅与否,最终总会影响洋货的贸易总额,但是,就具体的每一笔交易而言,洋行不必为之承担直接的经济责任。
土货输出贸易长期处于买方市场状态。根据买办契约制度,规定买办将土货购办齐全后,在口岸城市交货,货到口岸装船完毕,才由洋行向买办付清80%的货款,另外的20%要在装船之日起的四个月内才结清。洋行对于由内陆到口岸之间的运输更不需要承担经济责任和任何风险。
在洋行与买办之间,除了订定契约以外,还有“担保制度”,即充任买办者必须有中国富商担保,订立担保合同甚至交付一定的担保物,如:道契等。〔28〕
上述买办制度之下,作为近代交通事业主要投资者,外商对于内陆公路投资当然不会有多少兴趣。这是由追求投资经济效益所决定了的。这是其三。
最后应当充分重视的是交通投资线状分布,对于近代东南沿海陆上交通,无论铁路还是公路,所起的严重阻滞作用。关键在于它们必然要大量征用土地。1906年以后,虽然由商部制订了《全国铁路购地章程》,定有凭契按地方之地价折合收赎,以后公路购地也参酌办理。但是,在此之前,(也包括1906年以后)实际上,或出于实际经济利益,或因与传统习俗、观念相抵触,发生了大量的纠葛。以1874年吴淞铁路开筑之际而言,吴淞、宝山乡民每每“激动乡民公愤”,“叠次拔去木桩”,“殊形棘手”。〔29〕以往,有些论著总以此归之于中国乡民的愚昧、狭隘,其实,不尽公正。一旦涉及实际土地利益,即使洋商往往也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以沪宁铁路为例,当该路要以地价收赎“上海县21保11图产”的土地时,由于“内有洋商基地,且并无道契”,中国政府还是给以地价准备收赎,可是该“洋商却不甘愿”,拒绝沪宁路局使用他所租之地,以致沪宁路局“办理益难”。〔30〕
东南沿海各省为当时农业经济发达之区,地少人多,矛盾原已尖锐,因此,陆上铁路、公路线,跨县越省,进展越广,此类矛盾、纠葛越形复杂,对于东南沿海近代陆上交通投资的阻滞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注释:
〔1〕聂宝璋《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页。
〔2〕〔3〕〔4〕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7、268、271页。
〔5〕张仲礼著《太古集团在旧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以下简称《太古》)。
〔6〕聂宝璋,上引书,第512页。
〔7〕张仲礼等《太古》,第27页,第29页。
〔8〕参阅《上海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第226页,“以上海港为起点的国内航线,船舶艘数及吨位表(1913。该表“上海至香港线(寄港地厦门、汕头)”栏内有轮船10艘,20137吨, 鉴于沪港贸易与国内沿海有别,多半属经港转出入口贸易,大多统计资料均与埠际贸易分列这里,考虑有厦门,汕头两中途港,所以,将半数(5艘10069吨)计入。
〔9〕参阅《国营招商局七十五周年纪念刊》,1947年版,第157—196页。其中南京镇江两口岸无统计数;东北各口岸原未列入统计数。这里,依据杜恂诚著《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页,第118 页资料核算,东北各口岸1937 年日籍轮船叫吨位81730吨,以平均最低航次为116航次计算,约为1078.8万吨,将它加上华北、华东长沙芭北口岸的1888.4万吨,合计北洋各口岸总数为2967万吨。
〔10〕统计数来源:马里千等编著《中国铁路建筑编年简史》中国铁道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11〕《河北公路运输史》、《浙江公路运输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
〔12〕《天津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59页、87页、109页;《上海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13〕张心澄《中国交通史》,第183—184页。
〔14〕《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5页、第842页、843页。
〔15〕马里千,上引书,第10页及相关各线统计数。
〔16〕参阅张心澄,上引书,第184—188页、第200—204;浙江省情展览会编《浙江省情·浙江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三编,第1—3页, 第5页,第9页及《浙江全省公路细图》,《浙江全省航线管理船舶事务所区域全图》。
〔17〕转引自汪敬虞,上引书,第84页、268页、473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19〕参阅《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一卷, 1931年版第510—511页。
〔20〕转引自汪敬虞,上引书第268页,473页。
〔21〕参阅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第255—263页;潘君祥、沈祖炜《近代中国国情透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185页。
〔22〕刘广京《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第7页。
〔23〕转引自汪敬虞,上引书,第473页、268页、84页。
〔24〕转引汪敬虞,上引书,第434页—438页,原载《旧中国当局与各国外交机构》NA 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n Office 1948rh thgc,tx113页。
〔25〕转引自汪敬虞,上引书,第434—438页。
〔26〕《浙江公路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27〕福建省政府编《福建省对外贸易统计》,1935年版,第2—3页。
〔28〕参阅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87—10页;汪敬虞,上引书, 第108—109页。
〔29〕《申报》1887年1月27日。
〔30〕《外务部咨南洋通商大臣》见《交通史·路政篇》第一册,第4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