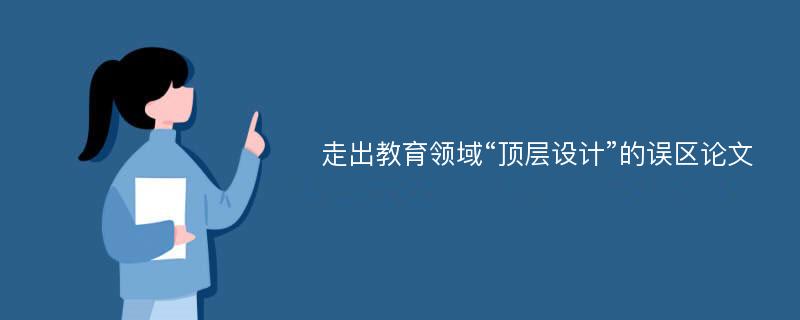
走出教育领域“顶层设计”的误区
苌光锤1,3;刘剑虹2
(1.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浙江金华321004;2.湖州师范学院,浙江湖州313000;3.上海海事大学人事处,上海201306)
【摘 要】 “顶层设计”在政治领域一经提出,立刻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关注,教育领域也在大力宣扬。然而,“顶层设计”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尺度,并非适合所有领域。选取从“顶层设计”的概念作为切入点,分析了什么是“顶层设计”,又从发生学角度、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角度以及战略规划等不同视角对教育领域改革的“顶层设计”的提法不可取做了相关论证,并呼吁借鉴迁移他域用词需谨慎。
【关键词】 顶层设计;改革;教育;战略规划
2010 年 10 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由此“顶层设计”作为一个政治概念首次在政府的正式文本文件里被提出。该“建议”颁布后 ,立刻引起了各个领域的专家与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现在每每触及改革的议题,各个领域都在谈“顶层设计”,毫无疑问,“顶层设计”这一概念有明显被泛化的迹象。这也似乎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错觉:但凡社会上出现了问题和状况,都是因为没有做好“顶层设计”的缘故,只要做好了“顶层设计”,就不会发生现在的问题,即便发生了也可以顺理成章地得以解决。总之,顶层设计已泛化为解决一切问题的良药。果真如此吗?实际上并非如此,事物都有自己的适用性,并不是所有的概念都可以迁移或借用的,也不是所有的规划都可以叫做“顶层设计”的,“顶层设计”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和尺度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正确理解“顶层设计”,谁有资格做“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与具体规划之间是否矛盾……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是需要我们正确把握和理解“顶层设计”提出的初衷。
一、关于“顶层设计”的若干解读
(一)“顶层设计”的内涵
“顶层设计”最初是系统工程学领域里的一个概念[1],本义是为了统揽并兼顾项目在不同层级及其关联要素,用整体观的方法论整合零散的局部结构,以期在最高层级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顶层设计是一项工程“整体理念”的具体化[2],在社会改革领域里是一个外来词,不是专门针对社会改革问题而提出的。
3.3造成各项调查数据偏低的原因:1)农民居住分散、大多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经济收入低的地区,难以接触到无偿献血的宣传,因此对无偿献血没有正确认识。有部分农民对献血存在错误认识,甚至恐惧心理,认为献血会影响身体健康,传染疾病。2)因为农民文化程度普遍较低 ,大多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对血液生理知识、献血意义的理解有一定的难度 。3)受传统思想的束缚 ,农民普遍担心献血会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和影响生产劳动。
在维基百科中,将“顶层设计”翻译为“top-down design”,而“top-down design”又是相对于“bottom-up design”来说的,两者的联合(top-down and bottom-up design)则被译作“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设计”[3],这是把两个词组耦合在一起来解释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设计”是信息处理系统设计中的一种算法,也是一种知识分类的策略,亦可视作一种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方法的综合。
例如:在进行小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全班的学生都要做到一视同仁,这也是尊重学生的表现。比如,在进行一个语文考核之后,成绩公布的时候,老师对于成绩较好的学生要说:“表现得很棒”,对于成绩稍微不太理想的学生要说:“不错,有进步,继续加油”。这样的鼓励式教学可以激励学生进行学生,同时也做到了尊重学生。又或者老师将成绩稍差的学生叫到办公室进行辅导,让全班的每一位学生都可以被顾及到。这些都是尊重学生的表现,也是加强师德建设的有效途径。
通过对教育领域内已发表的文献进行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即教育的学科领地内不同分支领域对“顶层设计”的认识基本上是各说各话,都是基于各自研究领域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及不足之处,然后再提出一套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或方案,这个对策或方案通常都会被冠以所谓的该领域的“顶层设计”,而且文本中阐述的那些现实问题的出现也基本上是归因于没有做好“顶层设计”的缘故。这种简单的归纳方式、仅仅冠以“顶层设计”为关键词的设计方案,甚至把具体某个学校层面的改革方案当做是“顶层设计”,显然是对“顶层设计”的一种误用和滥用。吴敬琏先生也认为“把‘顶层设计’局限于某一部门或某一项具体的工作,多少是一种误读”[25]。“顶层设计”不是某个单一研究方向的顶层设计,而是综合性的设计;当然也不是地方某一层级上的设计,而是全局性的设计。
其一,系统工程学方面的“顶层设计”。在系统工程学中,顶层设计是指理念与实践之间的“蓝图”,总的特点是具有“整体的明确性”和“具体的可操作性”,在实践过程中能够按图施工、避免各自为政造成工程建设过程的混乱无序[4]。 在工程技术行业,“顶层设计”就是从最高层开始,站在一个战略制高点[5]。其二,制度总体设计说。马晓河认为顶层设计是国家层面的,以及与国家层面相关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民主与法治体制、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总体设计[6]。高尚全则认为,就整个国家的改革而言,顶层就是最高层,就是全党全国这一层,要求全面设计,统筹规划[7]。其三,决策与战略管理说。顶层设计就是“在高层领导下,以基层建议和专业论证为基础,就目标模式、体制机制、重点领域、重大工程和关键项目等,作出战略性、系统性和实践性总体安排与部署”[8],“是最高决策层对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等进行整体设计”[9]。政府以一种高瞻远瞩的姿态统筹布局各大战略决策,以便使改革与发展能够遵循当初谋划的蓝图发展。
“下面,我们来变换一下角色,谁想来试试说‘大风吹’?”我问孩子们。孩子们都高高举起手,嘴里喊着“我,我,我”。“你来吧,鲁哲恺。”只见鲁哲恺整了整衣服,清了清嗓子大声喊:“大风吹。”我和孩子们一起喊:“吹哪里?”“吹李炜琛。你为人诚实,对人真诚,所以很多人都愿意和你交朋友。”炜琛得到了认可,很开心。孩子们十分踊跃,都用欣赏的眼神观察着每一个同学。
个人认为:不是所有的规划或设计,都能称之为“顶层设计”的。一个所谓的“顶层设计”必定是长远的、较大尺度上的战略规划或设计,而不是微观层面或者短期的规划。顶层设计是一种具有总体布局和全局视角的理念与战略统筹,能够做到跨越时空维度的,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量的,是终极的或极为接近终极目标的一种长远的战略性规划。如果仅仅是以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上百年为限度的一个规划,是不能称之为“顶层设计”的。简单立场的所谓的“顶层设计”缺乏产生完整思想的能力,它关注的是局部问题,排斥了包含局部问题的整体问题。这样的思考方式和思考立场会忽略局部问题的基础,从而使得整体问题的思考非常有限,而且以对局部问题的思考去代替或者认为可以代替整体问题的思考是极为不可取的。
(二)教育领域中学者对“顶层设计”的认识
教育领域中,不论是学前教育、民办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地方高校发展,还是学校课程建设领域,将“顶层设计”嵌入其中的相关研究都不乏其人。
在微观层面,有学者用“顶层设计”研究我国学前教育政策问题的,主要是针对当前的学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其不足之处,探讨其解决的办法[12];有研究关于民办高等教育政策的,着重分析了目前国内民办教育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建议[13];有探讨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分析了目前国内研究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结合作者自己所在单位为例子,阐述研究生教育是如何进行“顶层设计”改革的[14];有研究关于地方高校发展的改革设计,也是结合作者所在单位的改革措施先后从办学指导思想、办学定位、发展目标、发展思路、战略举措和发展规划等六个方面入手,阐述“顶层设计”在地方高校发展中的重要性[15];还有的是研究学校课程设计的[16][17][18],分析了课程设计缺失的基本原因,聚焦课程设计和完善的基本元素,给出了具体课程设计的路径规划等等。此外,还有针对学术期刊、图书馆建设、国培计划、教育信息化、人才培养模式、教育扶贫等等其他方面的微观层面的研究[19][20][21][22],由于篇幅的限制就不再一一介绍了。
在宏观层面,有学者从政府与高校间的关系入手,呼吁政府应注重作为战略统筹者的地位,弱化其对高校过多的行政干预的角色,为高校释放出最大的自主空间,并对中国高等教育宏观改革给出了基本取向:宏观政府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微观层面高校“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23]。也有学者另辟蹊径,认为教育改革应从基层出发,不能只依靠顶层设计,必须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有机而辩证地结合起来。顶层设计容易出现失灵、走样、低效等问题,基层探索是关键;基层探索体现民众意志与民众智慧,为改革提供将理念具体化的实践参照[24]。
通过在教材中渗透“数学建模思想”,培养学生的数学应用意识与能力。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考虑:第一,让学生认识到每一个数学概念、公式、定理。从广义上说都是数学模型,如从实例中抽象出导数概念即给这类问题建立了数学模型;第二,让学生了解数学建模的方法和过程。教材从经济函数关系的确定到经济问题的建模求解,应给出分析和说明;第三,课程末另设专篇介绍综合运用数学知识建模的几个范例,培养学生初步应用数学建模的创造能力,同时为参加数学建模大赛做好准备。
部分学者对“顶层设计”的内涵也做了考察,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三)对“顶层设计”的另一类解读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尽管不同学者对“顶层设计”内涵的阐述略有偏差,但却存在着高度的共通性:顶层设计是一种“系统的谋划”过程,用系统论的方法,以整体为架构,对系统内部的各要素进行统筹谋划与整合,并谋划可行的操作方案和策略的一种全面的规划和整体设计。持“制度总体设计说”观点的部分学者将行政职位最高层的决策者所做出的设计称之为“顶层设计”,这显然是不妥的,这就牵涉到谁有资格来做“顶层设计”的问题。将侧重点放在设计者是否处在社会地位以及权力阶层顶端的那些当权者身上,而忽视了设计本身的顶层的设计,这是对“顶层设计”的误解。“顶层设计”的“顶层”着重点应体现在设计水准的高度和深度上,而不应该只关注设计者是否处于行政职务的最高层,这“不是几个精英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所能胜任的”[10]。仅以设计者所处的社会阶层的高低这种单一的读取字表含义的方式来划分、确定是否为“顶层设计”的话,与其说这是一种“顶层设计”,倒不如说是一种“高层设计”显得更名副其实。“顶层设计”的设计者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也可以是来自最底层的普通老百姓。“顶层设计”不是高层领导的个人设计,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顶层设计”也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指令式安排,因为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没有开展明确的“顶层设计”的实践[11]。概括地来说,目前关于“顶层设计”相关话题的着眼点及讨论大多集中在概念性、宏观性、战略性、原则性等几大方面,且论述略显泛化与空洞。而对于如何从理论上的“顶层设计”过渡到具体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方面的探讨甚少。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26]的议题就是对时代的精准的把脉,这是结合现实对人类命运与生存之道所作出的“顶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发展最终面临的价值体现,此观念才是人类归宿真正的“顶层设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跨越时间、跨越文化、跨越国度、跨越种族界限的,关乎人类持续长久发展下去的大系统工程,用“顶层设计”来阐述恐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当然,事物都具有一定的适应性和适用范围,并不是所有领域的改革都适合使用“顶层设计”这个说法的,比如教育领域的改革或规划就不适合使用所谓的“顶层设计”的提法。下文主要从发生学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及战略规划等不同视角来阐述教育领域改革采用“顶层设计”的提法不可取。
二、发生学视角下走出教育领域的“顶层设计”误区
发生学原理是基于分析事物发生发展,以揭示事物发生发展最一般规律的学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是阐述事物演化的历史阶段、形态和规律的方法。通过发生学视角考察大学职能和教育目的的分化,以此阐述教育领域设置“顶层设计”不可取。
师:这几位同学真不简单,敢于大胆的质疑教材,还能分析得如此深刻。这种怀疑精神,我们每一位学生最好都应该具有的。
(一)大学职能分化的历史演进
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承担着特定的职责,并由此产生相应的功能,也就是被社会赋予了一定的职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是公认的现代大学三大职能[27],然而这公认的三大职能并非在大学诞生之日起就与生俱来的,而是大学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衍生出来的,是在满足社会需求过程中不断被人为所赋予的,是被动形成的。
14-16世纪长达二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欧洲社会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启蒙和与之伴随的资本主义思想萌芽的诞生,都为后面工业革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但18世纪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蜷缩在庄严陈旧的哥特式教堂内的古老的教会大学,依然固守着传统的单一教育理念与目标——培养举止优雅的绅士,没有对外界悄然变化的时代环境给予积极的回应与反思,这也导致了传统而又古老的大学与社会发展的需求衔接不上,而最直观的后果就是传统大学在时代激荡中走向衰落。
大学衍生出科学研究的职能肇始于1810年德国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所创建的柏林大学(也称洪堡大学),柏林大学创建之初就提出“教研合一”的主张,在洪堡的带领下柏林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改革,科学研究成了行之有效的发展原则。
到了20世纪初期,美国莫里尔法案通过后赠地学院威斯康星大学按照“州立大学要为州的经济发展服务”[28]的指导理念,再一次迎来了大学职能分化的契机,由此服务社会的职能成为了大学继教学、科研之后衍生出来的第三大职能,且是三大职能里发展变化最快的一个。
大学的职能在不断分化与拓展,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关系也越来越紧密。大学已不再是人们心目中高不可攀的象牙塔,逐渐由社会的边缘走向了社会的中心,成为整个社会中最具活力的机构和代表。大学服务社会的范围也在无限地膨胀,以至于被誉为是社会发展的“服务站”“动力站”“社会轴心机构”等等。大学在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为社会提供服务,社会也在反哺大学为大学的发展提供平台与资源,正是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大学才不断地完善自身职能的更新与外延的拓展。
中国近现代的百年不堪回首,内忧外患,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此起彼伏,积贫积弱的中国风雨飘摇。那些仁人志士把教育作为寻求救国救亡真理的圭臬。1912年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了“五育”的主张。民国时期,教育上模仿苏联“以党治国”的模式,强调政治上的一切都以党纲为依据,即所谓的“党化教育”[31]。教育依旧被政治裹挟着在缓慢发展,培养目标并未因时代变迁而有实质性的改变。尽管也有诸多爱国人士试图通过立身践行,像晏阳初发起的“平民教育”运动,梁漱溟倡导的“乡村教育”运动……尝试用一种新式教育以改变旧中国的精神面貌,尽管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终因力量微弱,无一例外被历史的车轮所吞噬。这些教育实践活动也只是成了一种有限的改造下层民众境遇的工具罢了,而教育被异化为外部世界工具的命运一直未变[32]。
通过上述对大学职能衍化史的梳理,可以发现:时至今日,还没有哪个机构或组织能像大学这样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由羸弱的社会边缘机构发展成今日举世瞩目并对社会发展起到如此重要作用和不可替代的学术组织。大学在经历由被动接受服务,过渡到主动适应,再过渡到现在引领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成了角色的定位,也完善了大学职能的扩充与丰富,这一过程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学职能的扩充史”或“大学职能的分化史”。在大学职能发展道路上可以看出,大学的职能是在不断丰富和增加的,人们对大学的认识也是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在不断修正和动态调整的。如果最初就为大学的职能划定好了唯一一个“培养人才”的“顶层设计”,那么大学的其他职能也就很难被分化出来。正是因为没有一个顶层框架的限制和约束,大学职能才发展出今天这样的多样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大学职能的分化史。今天的大学依然在发展,依然在分化,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大学不是在分化,就是在分化的路上”。大学与大学的职能一直行走在分化的路上,如果用一个事先设定好了的框架去捆绑大学发展的所谓“顶层设计”,这样的理念显然就不适应了。
(二)中国教育目的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出现过很多种教育目的观,从价值取向上来看,有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观,还有这两者的混合(如文化本位、伦理本位等)。以时间为主轴对中国教育目的观进行梳理,考察一下教育目的的历史嬗变。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总是围绕着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这个中心。忧国忧民总是围绕着国家的统一、安宁、稳定、发展为主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孕育了许多具有爱国精神的民族伟人。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基本源泉,也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
首先,生产前沿面的构造、投入要素、期望产出及非期望产出均同上文所述一致。假定 为动态要素,则每个生产决策单元期的投入产出值可以表示为
与古希腊几乎处于同一时代的我国春秋时期,也是思想和文化极为辉煌灿烂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盛况,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到了汉代,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一枝独秀,形成了“一花开尽百花杀”的局面,自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两千多年。儒家思想旨在培养君子和圣人。教育的意义在于通过自我修身,发扬人的德性,实现人与道的同一,即止于至善,最终以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理想。在此过程中,人伦教育是基础和根本,天伦教育是目标和归宿[29]。诞生于隋唐时期的科举更是平地一声春雷响,为整个社会阶层的跃迁打开了一扇门。“学而优则仕”为生活在底层的民众带来了新希望,得到后世的极力推崇。宋代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新儒学”主张,强调教育目的要“明人伦”。明代著名心学大家王守仁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格物致知”。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等在1904年的奏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时指出,立学在于“造就通才,慎防流弊”[30]。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教育是根植于阶级统治的需要,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服务于帝王政治,培养目标是趋向于培养具有完美人格的“圣人”。
通过对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国教育目的的梳理可以看出:其一,教育目的总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变化而变动不居,虽然变来变去,却鲜有涉及教育的终极价值或终极目的问题。其二,中国教育目的的功利性很强,不是基于人自身的角度出发的,而是将人物化,将人作为一种工具性的物格来培养,忽视了对教育“终极善”[37]的关照。大学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具有复杂性。具体而言,其复杂性表现为结构的复杂性、人员构成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复杂性、目标构成多样性等等,这些大学的构成要件及大学行为都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得越来越复杂。不论从大学职能分化与大学教育目的的发生学视角看,如果当初用这所谓的“顶层设计”的思维来对其做出“顶层”规划的话,那么今天见到的大学绝不是今天大学的这个样子。
21世纪迈入了信息化时代,整个社会大环境与此前的几千年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信息化所带来的产业革命成果更是让人目不暇接,交叉学科领域的大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界限,基因修复与筛选、量子纠缠、3D打印、无人操控系统、超算、天眼、可控核聚变(人造太阳)、高速磁浮、5G物联网技术……所有的这些都在源源不断地刷新着人们原有的认知范畴。这多元化的高新科技异军突起、瞬息万变的时代,将会使高等教育本身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应对这些变化趋势与时代潮流,这也将是高等教育发展亟须要思考的问题。
3.1949年后——“为社会服务”的教育目的观
1949年后,从政治到经济都在模仿苏联的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教育为政治目的服务[33]。从教育目的的内容表述上看,从培养“劳动者”和“人才”到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34]再到培养“社会主义公民”[35],虽然教育目的的表述有所不同,但它为阶级服务、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取向性一直没有改变。从1949年后的教育目的演变来看,教育目的不是基于人性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而是从政治、经济发展的外部需要来构建的,用既定目的来代替人的整体发展,单向度地张扬人的素养以迎合社会发展之需。结果学生成为理性能力的“巨人”,反思批判的“侏儒”。在这种教育目的观中,导致了现实教育的极度功利化和受教育者的物化[36]。
1.古代——“圣人”的教育目的观
2.近现代——“工具人”的教育目的观
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视角下的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可取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可知的,人们不仅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现象,而且可以透过现象认识其本质。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多次反复、无限深化的过程[38]。
要想把农民变成产业农民,首先,农民不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工作,除了给农场干活,自己家地里还得打理,这种情况,他们不会专心工作,应该投的投入品也很难保证按时,定量施用。其次,农民必须有学习能力,能够按照专业公司提供的农业种植方案,严格执行。再次,服务对象和技术提供方必须现场驻人,进行过程监督,否则达不到与其目标,双方均会遭受损失。最后,农业技术服务方最好能够把技术服务方案和现场田间管理作为统一的农业服务接管,否则技术方案的落地将会有所折扣。
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则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律:首先,认识具有反复性。从认识的主体来看,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制约,如主体自身的知识储备、所受的科学规训、年龄、成长环境、个人的成长经历……这些因素都会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产生影响。从认识的客体来看,客观事物是变化着的,其本质的展现也是在不断发展过程中逐渐显现出来的,而不是一开始就把最本质的东西裸露在世人面前。所以,不管是从认识的主体方面来看,还是从客体方面来看,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往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的一个过程。其次,认识具有无限性。认识的客体是变化着的物质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事物自身的发展状况也在发生变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自然也会与时俱进,也会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第三,认识具有前进性与上升性。认识是一件反复性活动,从现象到本质,从本质再到现象;从感性到理性,再从理性到感性的不断循环的活动,对真理的追求是一种波浪式的前进或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心肌肥厚的确定 给药8周结束后,处死大鼠,迅速开胸取心脏,分离左、右室,用滤纸蘸干后分别称取左室和室间隔重量 (LVS)以及右室重量(RV),计算LVS-BW比和LVS-RV比;并取部分左室组织,用4%多聚甲醛溶液固定24 h,石蜡包埋、切片,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大鼠心肌组织病理形态学变化。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具有阶段性的,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如测量工具、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会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也是动态不居的,具有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对事物的认识可能在前后短时间内就会出现截然相反的态度或结论。
教育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真实发生的,人们在面对教育现象及教育问题的认识时,也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认识规律的。当宗教大学不能适用工业化大生产时,通识教育便产生了;当绅士教育不能适用社会化大发展时,专业教育便诞生了;当学术型教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时,应用型教育便乘势而起。社会发展越来越快,高等教育更是经历了由原来的社会边缘,走到了社会中心,出乎意料地完成了角色互换。教育职能出现了分化现象,以及教育目的不断更迭,这些都是人们对教育认识、再认识的结果。可以说,在民族国家阶段,教育目的依然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而且教育目的多趋向于工具性,但为国家发展做贡献的出发点的现实要求是不会改变的。对事物发展的认识具有阶段性,所以很难用一个带有统括性的设计,涵盖事物的方方面面,教育亦如此。即便是战略规划,也是要建立评估反馈机制,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反馈信息及时做出修正和调整的,更何况是“顶层设计”。需要不断做出修正或调整的“顶层设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当然,如果一个“顶层设计”中的“顶层”是另一项“设计”的“中层”或“底层”的话,也同样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
《庄子》有云,“始生之物,其形必丑”,如出一辙,教育还处在发展的路上,我们对教育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还有很多教育问题在“悬置”[39]。教育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是不适宜用一个所谓的“顶层设计”将其框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试图将教育按照其设计好的框架去发展的,否则,必定会限制其发展的其他可能性。
四、战略规划——更替教育领域所谓“顶层设计”的最佳镜像
教育领域中想借鉴“顶层设计”既然不适用,那么有没有其他用词更适合表达这种语境用词?答案是肯定的,教育领域所谓的“顶层设计”最佳镜像没有比“战略规划”更适合的了。所谓的战略规划是指“对重大的、全局性的、基本的、未来的目标、方针、任务的谋划。战略事关政党、国家、社会组织、集团的重大问题,属于大政方针的制定。它所规划的范围涉及大方向、总目标及其主要步骤、重大措施等方面”[40],是“指导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41]。
通过对“战略规划”的内涵分析来看,本质上,战略规划其实就是一种计划,是指导全局的计划,比较长远的计划,是对环境变化、组织变革的适应机制,是对正在出现的问题的反应。这不正是那些学者们提出的“顶层设计”所要表达的意思吗!尽管学者们提出的各种“顶层设计”应接不暇,但事实上,那些所谓的“顶层设计”推敲起来不过是原来的“决定”“意见”“办法”“规定”“条例”“纲要”等等方案的别称罢了,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顶层设计”。
有了战略规划也不一定是完美的,战略规划由谁来设计,又由谁来执行实施、监督、评估等一系列后续事情,这些都会对战略规划的成效构成挑战。处在政治生态的顶端施政者所签署或发布的行政指令,虽然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在法制还不健全的社会里,伴随着领导人的换届,带来的政策不连续性,改革的人为性和随意性很大,使得战略规划“朝令夕改”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是目前战略规划不完善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来说,“改革是社会历史长河中的阶段性现象,改革是一种普遍的历史存在”[42],战略规划正好承接了这个具有阶段性的改革要求。所以,无论是从时间跨度上看,还是从内涵要求上看,“战略规划”都要比“顶层设计”更符合教育领域的改革诉求。
在这里,除了路面、建筑物、少量的麦地和玉米地外,其他地方几乎都被草地所覆盖。铺天盖地般舒展开来的绿野为荷兰奶牛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新鲜的青草,换来的是新鲜的牛奶,最后便是奶酪了。这里的奶酪品种之全,让人叹为观止。
五、结语
不是说社会上一出现热点、焦点问题,就可以一窝蜂似地蜂拥而上、摇旗呐喊,就可以习惯性地生搬硬套,而是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领域与研究问题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不同领域中的新命题的诞生具有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背景及使命,其概念内涵也具有一定范围的适应性,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领域中最先出现的专有名词或概念。教育不同于那些领域,教育具有公共性,针对的是对人的培养活动,借鉴到教育领域的时候,需要格外的谨慎。“教育学界是敏感的。某种哲学、某种技术、某种方式在其他领域的‘巨大’成功对于教育学界而言,总是充满了诱惑或激励。”[43]在经济学领域中人们关注的是“效率”“市场”“利润”等等一系列的具有强烈展现其经济学色彩的概念。当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而来的时候,市场经济成了时代的弄潮儿,经济的市场化也让人们切实感受到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所带来的物质生产的极大丰富与生活的快捷便利。教育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紧跟其步伐,有部分专家学者将“市场化”这一原本经济学领域的专有名词引入到教育领域,倡导教育也应该市场化,并为其摇旗呐喊。但这显然与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具有公共性的属性相抵触,弊端多多,没过多久便遭到了社会的反对和批评。对于系统工程学以及社会改革领域中的“顶层设计”不能随意地引入到教育领域中,不是所有的改革规划都能称之为“顶层设计”的。教育学科领域内的所谓的“顶层设计”充其量不过是“战略规划”罢了,还上升不到顶层设计的高度和深度。这种蹭热度搭顺风车、不严谨的学术态度还需谨慎处之。
【参考文献】
[1][25]吴敬琏.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与改革的顶层设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5-13.
[2]汪玉凯.准确理解“顶层设计”[N].北京日报,2012-03-26(17).
[3]Top-down and bottom-up design[EB/OL].[2018-10-11]. http://www.answers. com/topic/top-down-and-bottom- up-design.
[4]竹立家.改革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J].人民论坛,2011(1):32-33.
[5]章文,申妙.顶层设计基层做起——专访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J].中国新闻周刊,2011(10):34-35.
[6]改革杂志社专题研究部.顶层设计的宏观情境及其若干可能性[J].改革,2011(9):14.
[7]尚全.加强改革顶层设计[J].改革与开放,2011(13): 7-8.
[8][11]王建民,狄增如.“顶层设计”的内涵、逻辑与方法[J].改革,2013(8):140-141.
[9]迟福林.改革的新形势与顶层设计[J].决策,2011(8): 11-13.
[10]陈家刚.“顶层设计”之辩[J].人民论坛,2012(6):7.
[12]庞丽娟,洪秀敏,孙美红.高位入手:顶层设计我国学前教育政策[J].教育研究,2012(10):104-107.
[13]徐绪卿.关于民办高等教育政策顶层设计的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13(21):60-64.
[14]卓志,毛洪涛,赵磊.加强顶层设计 深化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J].中国高等教育,2014(10):33-37.
[15]李志义.地方高校发展的顶层设计[J].中国大学教学,2016(1):8-13.
[16]李臣之.学校课程顶层设计[J].教育科学研究,2015(7):53-58.
[17]李松林,贺慧.中小学校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J].课程·教材·教法,2015,35 (6): 8-12.
[18]洪峻峰.当前学术期刊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底层回应[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0(3):50-59.
[19]张兴旺,李晨晖.“互联网+图书馆”顶层设计相关问题研究[J].图书与情报,2015(5):33-40.
[20]茶世俊,付钰,靳伟.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国培计划”运行机制探讨[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50(1):124-131.
[21]任友群,卢蓓蓉.规划之年看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J].电化教育研究,2015(6):5-14.
[22]代蕊华,于璇.教育精准扶贫:困境与治理路径[J].教育发展研究,2017(7):9-15.
[23]阎光才.高等教育改革顶层设计的逻辑[J].中国高教研究,2014(1):5-8.
[24]程红艳,周金山.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教育改革与学校变革关系辨析[J].教育研究与实践,2018(2):57-62.
[26]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OL].(2012-11-18).http://cpc.people.com.cn/n/2012/1118/c64094-19612151.html.
[27]邬大光.大学分化的复杂性及其价值[J].教育研究,2010(12):17-23.
[28](美)德里克·博克.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M].徐小洲,陈军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46-252.
[29]朱丰良. 教育目的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索[J].江苏高教,2014(4):137-140.
[30]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76.
[31][32][36]张运红,冯增俊.中国教育目的观的转型[J].现代教育管理,2013(1):1-6.
[33]赵联,孙福平.试论我国的教育目的及其完善[J].江西社会科学,2010(8):241-245.
[34]周常稳,周霖.论现阶段我国教育目的观的局限及改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7,37(28):3-7.
[35]扈中平.教育目的应定位于培养“人”[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2(3):24-29.
[37]金生鈜.教育的终极价值与教师的良知[J].教师教育研究,2012(4):1-6.
[38]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EB/OL].[2018-10-15].https://baike.baidu.com/item/ /10774152,2018-10-15.
[39]眭依凡.论大学问题的悬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7(6):82-156.
[40]萧浩辉.决策科学辞典[Z].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4.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2012:1637.
[42]陈金钊.法治与改革的关系及改革的顶层设计[J].法学,2014(8):3-16.
[43]杨开城.教育何以是大数据的[J].电化教育研究,2019(2):5-11.
Out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 Top -down Desig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Chang Guangchui, Liu Jianhong
Abstract: Since the“ top-down design” was put forward in the political field, it immediately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in various fields of society, and was also vigorously promoted in the education field. However, the“ top-down design” has its own scope and scale, which is not suitable for all fields. Selecting the concept of“ top-down design” as the entry point, this paper analyzes what the“ top-down design” is. Also,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occurrence, the epistemological perspective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planning, we argue that it is not advisable to apply“ top-down desig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reform, and it is necessary to be cautious in drawing on the words in the migration of their domain.
Key words: top-down design; reform;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ning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章编号】 1003-8418(2019)08-0031-0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236/j.cnki.jshe.2019.08.005
【作者简介】 苌光锤(1986—),男,安徽泗县人,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博士生,上海海事大学人事处;刘剑虹(1959—),男,浙江杭州人,湖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利益相关群体感知下的高校学术权力运行机制:路径分析以及模型重构”( CDA160163)。
(责任编辑沈广斌 )
标签:顶层设计论文; 改革论文; 教育论文; 战略规划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论文; 上海海事大学人事处论文; 湖州师范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