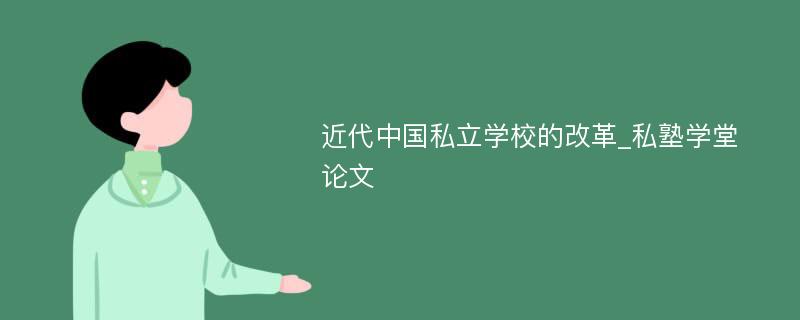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私塾论文,中国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栏目特约主持人:田正平 教授
私塾,属“私学”一种,过去一直被称为“家塾”、“馆”或者“书房”,直到清末民初分官、私学堂后才有此名称[1](p.31)。它主要分塾师自设的“散馆”, 官绅、商贾等延聘老师设立的“专馆”,以及由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开办的“义塾”。
清朝末期,一些把教育看作社会改良动力的有识之士积极推动科举制度改革, 建立新式学堂,推行新学制。维新人士对改革小学教育尤为重视,并主张实施义务教育,以期实现“使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受教,无一人不知学”[2](p.434)。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改良传统私塾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成为当时整个社会改良运动的一部分。
一
中国近代的私塾改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因为传统初等教育一直主要是靠私塾来完成,人们对其多存有信赖心理。面对要取代私塾的新式学堂,人们在固有理念撑持下难免产生怀疑,甚至认为“开设新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也”[3](p.44)。类似看法尽管有失偏颇,但也反映了传统私塾教育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牢固地位。《粤教育界争废止读经问题》一文曾提到,当时民众“误会废止读经之条文,以为圣经贤传万无可废,硁硁然有抱残守缺之思,儿童父兄以此相要,顽固塾师以此相市”[4],所反映的正是传统教育观念与教育近代化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 这两者矛盾发展到极端,导致各地出现了毁学风潮,如1909年、1910年,江西袁州、江苏宜兴、浙江慈溪等地相继发生乡民焚毁学堂事件。这些事例说明初等教育近代化起步之艰难,也说明私塾教育作为传统教育的承载者所具有的惰性。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私塾在客观上也有其继续生存的现实土壤。比如, 为方便学生求学,私塾一般就近设学;在时间上则不似学堂有严格的作息规定,且每日上学时间长于学堂,让民众觉得“实惠”。私塾所缴费用大大低于学堂,“学生入私塾每季纳修数角”即可,而“初等学堂学费至少须五角,多且一元或二元”[5](p.21)。私塾通常也不像学堂那样,“有操衣费、运动旅行费、 听差节赏等之额外费”[6],这就使许多“贫寒之徒,往往不问校之良否, 以收费少者为入学之视的”[5](p.21)。
另一方面,当时小学教育的不完善,也为传统私塾教育继续存在提供了条件。 近代意义的小学直到清末才发展起来,尽管类似性质的小学早就零星出现,如1878年张焕纶所办的正蒙书院(1882年改为梅溪书院,1902年改为梅溪学堂),1895年钟天纬在上海创办的三等学堂等,但小学教育真正大规模兴起还是在戊戌之后。1898年,清朝政府公布《定国是诏》,命各省、州、县、府开设中西学堂,州县书院改为小学[7](p.422)。相应地,清政府还制定了建立小学的计划,特别是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对小学的学制、管理、课程、师生等都做了统一规定,这也标志着中国初等教育走上了近代制度化的轨道。
近代小学主要来源有三:一是新建的新式小学堂, 如江苏两级师范学堂之附属小学堂、上海龙门师范学堂之附属小学堂等;二是书院改建的小学堂,如杭州紫阳书院改为仁。和高等小学堂、甘肃凤林书院改为临夏县立第一小学校等;三是私塾改良的小学堂,如杭州宗文义塾几经改组,成为市立中正桥小学。这三者中,由私塾改良的小学占很大比例。正因如此,整顿、改良私塾,提高由私塾转化而来的小学的质量,成为晚清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发展初等教育的重要工作。但小学教育在创立之初存在很大困难:(1)经费缺乏。当时各地学堂大都办学经费紧张, 甚至无法正常运行,一些学校不得不发动学生“假舞台演剧,以博经费”[8](p.11)。许多地方的小学还长期拖欠教员薪水,《教育杂志》载:“溧阳各学校自本学期(1929年)开学迄今,业已四月,教育局仅发出教费一月。”“苏州市小学教员自要求发清欠薪,未有圆满解决后,即于十一日(十二月)起停课索欠。”[9](p.182)类似事件在全国多处出现。(2)办学模式落后。 许多小学教员对新式学堂宗旨及教育管理方法几乎从未接触过,更不用说在实践中运用,这使新学堂往往沿用私塾老办法,以致“门悬初等小学堂之牌,入视之,则十数儿童拥护一师,几案错杂,或读百家姓千字文,或读学庸论孟”[8](p.11)。 庄俞在《小学教育现状论》中谈到:“吾见所谓小学教育者矣,教室也、教案也、教科书也、教具也、教员也,学校之能事,已毕。讲演也、批改也、训诫也、上课散学,教员之能事,已毕。进而求之所谓原理也、心得也、方法也、精神也,不曰无暇及此即斥为迂腐焉。”[10](pp.34—35)这种名不副实的小学当然会受到民众诟病。(3)课程改革难。拿清末来说, 清政府学部规定,小学课程除修身读经等传统科目外,还必须增加诸如国文(必修)、算术(必修)、体操、图画、唱歌等课程。可当时人们对“各种学科除国文、算学、历史、地理外,如理科、图画、唱歌、体操等均诧为怪异,愕然不知其用意之何在,甚至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一若怨毒之于人甚深者”[6]。在这种舆论下改革课程,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1908年,李搢荣在调查武清县东北两路各学堂后,曾报告各村镇初等小学堂的课程。报告云:“体操有纪律而少精神。观其课程表,历史每周二小时,读经一堂,时间长至七十分钟(河西务村)。”“体操一科尚缺,闻系风气不开,学生父兄皆避(大域厂村)。”“学生十余人,皆面壁坐,仍用《三字经》、《四言杂字》等书(杨村)。”[11](pp.279—284)
所以,尽管许多教育改良者希望私塾“在小学发达之后,自当归于消灭”[12](p.112),可私塾非但未消灭,反而时有增长趋势,且已改良者远少于未改良者。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在1935学年度对全国私塾总数的统计,就反映出这种现实(见表1)。从表中可知,直到20世纪30年代,无论学生、塾师还是全年所收经费, 在数量上未改良私塾都远远高出改良者。这也集中反映了近代中国初等教育的基本格局: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私塾并未因改良政策的实施而消失,一些地方的私塾甚至在解放前仍大量存在。1946年,仅对苏皖边区的粗略统计,私塾就至少还有两万所左右[13](p.319)。到1949年,仅广东省化县就有私塾158所,占全县小学总数的33.83%;学生2855人,占小学生总数的11.82%[14](p.1348)。
表11935学年度全国私塾统计情况
项目 合计 已改良者(实数)未改良者(实数)
私塾 110144 38525 71619
塾师 110953 39191 71762
曾受师范教育 94836784 2699
曾受中小学教育24805
15116 9689
学生 1878351 7544651123886
全年所收经费(元)7195883 3188853
4007030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2页。
二
近代私塾改良走的是从民间到政府这样一条实践道路。1904年, 江苏学务处委员沈戟仪在川沙龚镇创立私塾改良会,成为近代改良私塾之嚆矢。但真正使私塾改良发生制度性变革的,靠的还是晚清以来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大力倡导。学部于1910年提出:“盖欲求国民教育之普及,必以初等小学为始基,而学堂未及普遍之时,为取便童蒙就学之计,则私塾亦不能不设法维持。”[7](p.754)改良私塾成为清政府提倡的教育改革之一。从晚清直到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为改良私塾陆续颁布了一些法规,主要有:1910年晚清政府学部《改良私塾章程》;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整理私塾办法》;1915年袁世凯颁定《教育宗旨令》和《特定教育纲要》;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改良私塾办法》。部分地方政府还先于中央政府颁布了类似的法规,如1906年《上海私塾总会改良章程》等。但这些法规内容并不一致,也很少能落实,且对私塾的态度基本都偏于“补助”小学教育,使其“合于官学之程式”[7](p.754)。 具体的改革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改良私塾管理体制
1904年实施《癸卯学制》后,全国才有了近代意义的学校系统。 但随着新学制颁布,引发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清政府于是在1905年专门成立学部,设专职人员管理学务。1906年,清政府又在各省设提学使,在各厅州县设劝学所,管理辖区内学务。至此,全国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形成了完备的教育行政机构。另外,行政职员更趋于专业化,“于教育学、教授管理诸法及教育行政、视学制度,皆须随时研究”[7](p.591)。这些都为变革私塾管理体制提供了保证,其内容包括:(1)增设地方教育管理机构。清政府学部规定,“府厅州县城治设劝学所,佐府厅州县长官办理学务”[12](p.284)。为此,各地陆续设立了私塾改良会或劝学所, 由专职人员进行管理。(2)监督考核私塾办学质量。包括调查、评定私塾,考核塾师,实行劝导。调查包括私塾种类、塾师资格等,评定是根据优劣把私塾分等。如1937年教育部《改良私塾办法》规定:“主管机关对于所辖私塾,除已核准改称改良私塾者外,其成绩较优者得酌改为短期小学、简易小学或代用小学。”[15](p.680)劝学所除考核塾师教授管理方法外,还有劝导塾师改良的责任。(3)统一管理经费、书籍等私塾资产。劝学所每年需筹集经费,推进辖区内私塾改良活动,还要统一教科书和各种教学用具。如1936年《湖北省各县改良私塾暂行办法》中,就规定私塾设备最低应具备总理遗像、遗嘱及黑板、讲桌、讲椅等。另外,对私塾学生的清洁卫生、节假日等也作了统一规定。(4)管理具体教学活动。如组织会课、考试等教育活动,设立师范讲习所,制定学规等。以制定学规为例,针对私塾授课时间长短不定的问题,为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私塾改良部门专门对此作了规定。该规定要求:“每日作课,以六点钟为限(十岁以内之学生减去一课,每日五小时已足)。每点钟作课五十分,休息十分钟。”[12](p.107)
总之,改良私塾教育行政机构和管理体制,既促进了私塾制度化、正规化发展, 也加快了私塾与近代小学接轨进程。
(二)改良私塾课程
晚清以来,随着科举制度改革的深入,私塾固有的课程设置受到人们的广泛批评。有一《村学诗》对此进行过入木三分的讽刺:“一阵乌鸦噪晚风,诸徒齐逞好喉咙。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元黄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鉴略》,《百家姓》毕理《神童》。就中有个超群者,一日三行读《大》、《中》(《学》、《庸》也)。”[16](p.402)还有人认为:“旧时蒙馆所教读者,白块字、《三字经》、《千家诗》、《学》、《庸》、《论语》、《孟子》而至五经古文等。读书数十种,费时五六年,无一非所学非所用之物。”[6]所有这些,既暴露了私塾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反映了人们兴办新学、改良私塾,从而推进初等教育近代化的要求。
私塾课程改革主要是依照小学的课程标准进行的。清末《改良私塾章程》规定,小学课程分完全科与简易科两类。鉴于私塾大多地处偏僻,设备简陋,师资缺乏,因而,当时规定私塾“不能仿照初等小学办理者,准其设立小学简易科”[7] (p.748)。简易科又分必修科和随意科两类。必修科包括修身、读经、 中国文学和算术四门,随意科包括手工、图画、乐歌等。体操一科,学堂设在城镇者为必修科目,学堂设在乡村者暂作为随意科目。民国成立后,教育部废除清末的修身、读经课,增加了常识课,使课程设置更趋科学。为展示私塾与小学课程趋同的事实,现选取不同时期部分小学、私塾课程进行比较(见表2)。
表2不同时期部分小学、私塾课程比较
小学(初等小学)① 私塾
时间 教授科目时间 教授科目
1903年 完全科:修身、国文、算术、体操、手工、图1906年
必修课:修身(兼讲经)、国文(包括地理、
画、唱歌,三年起加读经讲经;简易科:修 历史、理科、习字)、算术、体操;随意科:
身、国文、算术、体操、手工、图画、唱歌 图画(毛笔画)、乐歌②
1910年 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乐歌、读经1910年 初等改良私塾:至少须授修身、国文、读
讲经经讲经、算术四科.高等改良第一级:至
少须授修身、国文、读经讲经、算术、历
史、地理六科;高等改良第二级:酌加格
致、体操③
1915年 国民学校:修身、国文、算术、体操、手工、 1915年 修身、读经、国文、算术、体操④
7月 图画、唱歌
1929年 党义、国语、社会、自然、算术、工作、美 1928年 必修课:党义、国语、常识(包括公司、社
术、体育、音乐 会、自然、卫生等科)、算术、体育;随意
科:艺术、音乐⑤
1932年 公民训练、卫生、体育、国语、社会、自然、 1937年 国语(包括读书、作文、写字)、常识(包括
10月算术、劳作、美术、音乐
社会、自然、卫生)、算术(包括笔算与珠
算)、体育⑥
*资料来源:①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开明书店1934年版,第422—423页。
②《上海私塾总会改良章程》,载《大公报》1906年4月23日第2版。
③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2页。
④《整顿私塾之通饬》,载《申报》1915年9月25日第10版。
⑤《江西省取缔私塾暂行条例》,载蔡鸿源编《民国法规集成》第28册, 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187页。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79页。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 私塾与小学在某些课程的废止与提倡上基本是呈平行发展的。这既是私塾改良的结果,也是处于变革时期的小学教育与私塾教育互相融合、互相妥协的结果。
(三)改良教学内容
近代教学内容的变革主要围绕两点:一是西学在学校教育中应处的地位; 二是西学的哪部分应被引进,引进程度如何。从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争论,到全国大、中、小学校陆续增设西学课程,这一进程反映出中国人教育观念上的转变,同时也在教学内容上体现出极大的变化。这一点,仅从教学内容载体——教科书演变上就能看出来。因为“初等学校教材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整个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17](p.663)。在发展近代小学之前, 传统蒙学教材一般采用《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幼学琼林》等。它们尽管有合理性,但到近代,问题也日益明显:既脱离实际,又艰深晦涩,以致“读书而能明经书之理者,百人中不得一人,大抵一二年、三五年即罢业,‘四书’多不能竟读,且圣言幽远,即与讲解,亦骤难明白”[16](p.402)。这样, 近代意义的初等教育兴起后,改革教学内容就与改革传统教科书、编辑新教科书紧密结合在一起,后者也成为教育界集中关注的问题。1895年,钟天纬在上海三等学堂编辑教材,这是中国人自编教科书的开始;1897年,南洋公学由陈懋治、杜嗣程、沈庆鸿等编纂《蒙学课本》,共三编;1904年以后,商务印书馆相继编辑出版了《最新教科书》,包括国文、格致、中国历史、地理、修身、笔算、农业、商业等,还有各种专供女学用的教科书。到此时,“教科书之形式方备”[7](p.653)。这一时期教科书的编辑基本上是模仿外国(主要是日本),其中不少教科书就是外国教科书的译编。但是,这些教材已经开始尝试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科学地设计教学内容,即“专取习见习闻之事物,演以通俗文字,要使童子由已知而达于未知”[7](p.659)。民国成立后,教科书得到进一步改革。商务印书馆的规定反映了当时教科书的特点:“(甲)各科互相联络,期教授之统一。(乙)力求浅显活泼,期合儿童心理,不以好高骛远,致贻躐等之弊。(丙)初等小学之教材,男女并重,以便男女同样之用。(丁)关于节候之事物,依阳历编次。”[18](p.423) 教科书的变迁体现了教育教学内容变革的基本趋势,对教育近代化起着推动作用。
新教材使用范围的逐步扩大表明,近代中国私塾教学内容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传统蒙学教材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1928年,广州市96所私塾所用教科书的情况即反映了这种变化趋势:其“课本多用中华书局新制单级教科书,其次为商务印书馆之单级教科书,间亦有用世界书局之单级教科书及经史、信札、四书等类旧书籍”[19](p.235)。
(四)改良塾师
私塾改良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塾师。 清末民初的塾师大部分是未取得功名的秀才或童生,很少有人能熟练掌握近代初等教育一系列新的教育教学方法。他们往往把自己受教育的方式原样照搬过来再教授学生,因此很难达到近代初等教育的要求。对塾师的无能,时人讥讽道:“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想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塾师把《论语》“郁郁乎文哉”错读为“都都平丈我”)[20](p.38)。而梁启超更是对塾师的迂腐做了批判:“窃念近世塾师,限于积习,开蒙即训《学》、《庸》,于古者小学之教,已漠不过问。其上者,高视阔步,聪明自负,即有浅近诗歌,足资童蒙启发者,又多不屑教读。其庸庸者,则又墨守成例,《千字》、《百家》、《神童》、《千家诗》之外,不敢稍改旧章,说到讲解,则又以为童蒙何足与于此。”[16](p.401)这些批判表面上是质疑塾师的能力, 从根本上说,批判的还是塾师作为落后思想观念的传声筒的角色。因此,改良塾师实际上是整个私塾改良的最关键环节之一。这其中兴办师范教育、培养新型教师,已成为改良塾师的主要途径。
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 要求京师及每个省城各设一所优级师范学堂,各州县必设一所初级师范学堂,大大促进了师范教育的发展。清政府还制定了其他一些强化师范教育的措施,如:(1)组织塾师入师范讲习所学习,提高其业务素质。在讲习所内,由师范毕业生讲演或与各私塾教员共同研究教育理论、教授管理方法,塾师还必须补习算学、舆地等课程。除理论学习外,还进行实地观摩,参观附近优良小学。学习时间主要是利用晚上、星期假以及寒暑假。(2)考核认定塾师资格,确保质量。 责成相关部门定期考核塾师,只有合格者才允许开馆设塾,不合格者需继续学习,直到通过考试为止。(3)制定实施一系列奖惩制度。对成绩优良或开办合法的私塾, 其塾师可酌量免受训练或讲习,有些还可获得奖金;对于塾师不入师范讲习所者,其酬劳费须酌减,对于塾师“默守成法不接受改进之指导者,指定在假期训练或讲习而不到者”[15](p.681),则予以警告并令其改进。
在改良塾师过程中,相继回国的一部分留学生也充实到小学教师队伍里, 直接提高了小学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其中一些人还积极参与政府的教育改革,广泛研究国外教育理论,向国内介绍各国教育制度以及国外著名教育家的思想;很多新教学方法被引进并得到实践,如单级教授法、五段教学法、设计教学法、道尔顿制等。这些也间接推动了塾师改良,使学校和改良私塾的教育质量不断提高。
(五)改良私塾教学方法
与近代学校相比,私塾的教育教学方法虽然也有某些优势, 但其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梁启超在维新运动时期对此做过猛烈批评:“今之教者,其姑以授之,而希冀其万一能解也,则是大愚也。知其必不能解,而犹然授之,是殴其子弟,使以学为苦而疾其师也。”[2](p.451)而1911年5 月《大公报》一篇题为《讲训蒙当改用善法》的文章也认为:“先生给讲书,说了些个之乎者也,也不明白那里的奥妙……整天的诗云子曰天德王道的乱念……照着老法子念了十年八年书的人,一个说条也不会写,拿起什么书来,也不懂得,真是可怜的很。”[21]针对这些问题,私塾教学方法的改良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要求以启发式为主,重讲解不重背诵;二是要求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三是要求考虑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激起儿童学习兴趣,禁用体罚。1937年制定的《改良私塾办法》规定:“私塾得视学生之年龄程度及其家庭状况编级教学;教学时须以引起儿童学习之兴趣为主,并须注重理解,不得专重背诵。”“私塾训育应以部颁小学公民训练标准为标准,须注重积极诱导方法,绝对禁用体罚;平时并须指导儿童作课外活动,以养成儿童运动及守纪律之习惯。”[15](p.680)这些规定大致反映出当时改良私塾教学方法的基本内容和主导方向。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努力,私塾在教育管理及教学等方面的质量都有了提高。 如《大公报》就曾报导过改良后的私塾变化:“内容异常完善,大有初等小学规模,现更每晚附设简易识字学,塾生四十余人。”[22]当然,对私塾的批评并未因此而停止,很多人仍认为私塾的存在严重阻碍了小学教育的正常发展。如沈颐《论改良私塾》就提出:“今之所谓改良私塾者,乃蒙马以虎皮,沐猴而人冠之类,而欲加以法令使生效力,其如莠草足以乱苗,郑声足以乱乐何哉?……目前强迫教育犹未实行,而使此类私塾与学堂同操教育国民之柄,谬种流传,遗毒无尽。”[11](pp.316—317)诸如沈颐的这类批判,并不足以完全否定整个私塾改良的成就,倒恰恰说明了私塾改良的艰巨性与迫切性。
三
改良私塾是时代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私塾改良历程反映了近代教育在晚清民初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基本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出中国初等教育在近代发展的总体趋向,而这正是后来的各种教育改革值得注意的。
第一,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融合。在改良过程中, 无论私塾或小学,甚至其他各级各类学校,由于更多地受到当时社会变革思潮的影响,因而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还坚守着诸如“中体西用”等信条,但传统的四书五经再也难以占垄断地位了,西学和体现近代气息的思想文化在悄悄渗入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争取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古今、中西之间的矛盾对传统教育起着破坏甚至革命的作用,这些矛盾同时也是促使私塾改良,使其逐步走上近代化道路的催化剂。所以,传统私塾与近代小学并存的这种中国近代初等教育的基本格局,实际上也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缩影:中国传统教育理念与西方近代办学思想有冲突有融合,教育改良与整个社会变革互相促进。
第二,私塾改良先是自下而上进行,但最终还是通过自上而下实现的。 私塾改良最早是从地方开始的民间行为,1904年在江苏首先展开,随后政府介入,对全国的私塾改良进行统一规划。改良的内容突出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二是国家制定推动私塾改良的法令法规,如《简易识字学塾章程》、《改良私塾章程》、《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以及陆续出台的其他配套的教育法令、法规,如小学校令、师范教育令等。这些都促使近代教育包括私塾的改良逐渐走上制度化轨道。不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模式,使私立教育日益被国立或公立教育取代,学校这种特殊的组织随之越来越同一化、标准化,这也削弱了学校在教育与教学方面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第三,教育与教学观念的变革是促进私塾教育近代化的主要动因。 所谓“教育教学观念的变革”,其实既有洋务派教育思想的烙印,也有资产阶级改良派等的影响,是当时社会思想解放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传统教育的改革往往体现近代改良的诉求,而在近代的改良中又不时显现出传统的影响。特别是在教育与教学观念的变革中,变革因素和保守因素既是不断斗争的两个方面,也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这集中体现在张之洞后来提出的所谓“中体西用”原则上,因为类似“中体西用”这样的教育观念本身就涵括着保守和变革的成分。应当说,这种长期被各种教育改革奉为圭臬的“中体西用”原则,尽管在洋务运动式微,特别是清政府倒台后,已不再被人们作为口号而刻意提倡,但其影响却长期存在着。不过,近代的私塾改良实践表明,教育观念中的变革因素最终还是战胜了保守因素,尽管这一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且“变革”与“保守”时常发生着妥协。
综上所述,私塾改良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初等教育的近代化, 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私塾改良的不断深入,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就不可能完成。同时,私塾改良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更能集中反映中国初等教育近代化的一些本质规律,对当今我国的教育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