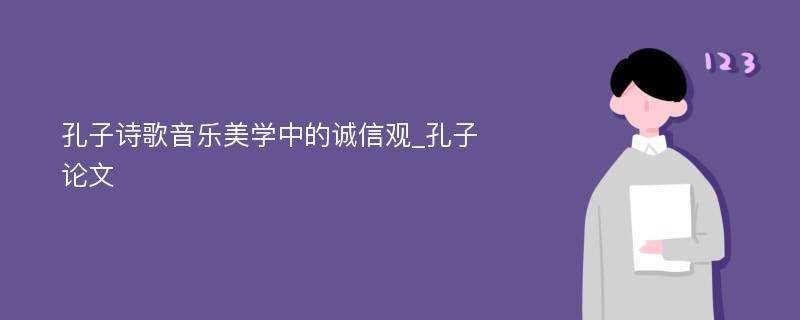
孔子诗乐美学中的整体性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整体性论文,学中论文,概念论文,诗乐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从尧舜到周公的礼乐之治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在孔子的时代已感到那是一去不复返的乐园,在孔子之后,那更是一种“永恒的乡愁”(注:礼乐之治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是徐复观的动人诠释。见《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23页。)。用现代的语言来说,“礼乐之治”是一个美学化的社会,在此,政治的最高境界并不只是获得民主、自由、平等、正义,而是达到了美的境界,在这样的社会中,上述那些政治领域中的积极价值都不是在法制规范中勉力获得的,而是在美的涵泳陶冶之中自然而然达到的。因此,儒家理想中的政治是一种无政治的政治。按照孔子对先王之道的理解,这个美的社会是经由礼乐教化而达到。
就诗礼乐的实际关系而言,乐在典礼中演奏,诗是乐的文辞,因此诗礼乐有不分的情形。或者在典礼之外,在日常生活之中,人们鼓瑟而歌,此时则是诗乐不分的情形。不论是典礼中的诗礼乐一体演出的盛况或日常生活中歌咏自娱的经验都是孔子亲身体会过的,因而是其诗乐美学的现实基础。整部《论语》通过片段的对话传达了孔子的美学思想,其中包括对诗乐本身之“艺术美”的思考,以及对于由诗乐而来的“社会美”的思考。用思想的语言来说,“整体性”可能是最有助于理解孔子诗乐美学的概念。“整体性”不仅体现于艺术品本身,也体现于作者与听者(读者)的互动,更是“社会美”的理念基础(注:对整体性的说明参考陈昭瑛《艺术的辩证:黑格尔与卢卡契》,台湾大学哲学所硕士论文1985年版;陈昭瑛:《美学的面向·译者导论》,台北南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7~59页;陈昭瑛:《刘勰的文类理论与儒家的整体性世界观:一个辩护》,台湾大学外文所比较文学博士论文中文本1993年。)。
简而言之,“整体性”(totality)或指两个以上之实体的合一,或指两种以上之存在状态的交融。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学派,这合一与交融的获得是通过双方之冲突、矛盾而终于达到。在儒家,冲突、矛盾虽然没有被特别强调,但是“中和”、“节制”等看法的提出,事实上仍带有压抑的痕迹,不能否认在“合一”之前曾有“不合一”的过程。在黑格尔和马克思学派,包含了矛盾而又克服了矛盾的整体性是世界的本质,因而人这一认知的主体与实践的主体也惟有通过整体性的思维才能认知世界并改变世界。兴起于二千多年前的先秦儒学不可能用概念性的语言建构任何与整体性相关的哲学体系。然而因着华夏民族在轴心文明时期所感受到的“人文精神的跃动”和“忧患意识”的觉醒(注:这两个词出自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二章。),孔门提出了对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真知灼见,而其中包括了美学见解。在这里,美学不是关于官能享受的心理学分析,也不属于认知实在的知识论部门。孔子自然不会否认美带有情绪享受的成分,同时也是认知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但更重要的,美是具有改变世界、美化世界(所谓“移风易俗”)之能力的人文精神。于是在美的领域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整体之间的互动成为关注的焦点。
中和:情理相得
孔子认为艺术创作者、艺术品本身及艺术品的接收者应达到“中和”的精神状态。“和”在《论语》并不是很重要的概念,《学而》篇记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和”被连系于“礼”(应包括“乐”),也被连系于“美”,更被联系于先王之道。朱注认为“和”是“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为可贵。先王之道,此其所以为美”(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以下同。)。朱子以“体用”来说明“和”,视“和”为功能性概念,而非实体性概念,是合乎文本之意的。但仅以“从容不迫”形容“和”仍有不足。孔子在《八佾》的一段话:“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被认为是孔子较具体说明“中和”的地方。朱注中针对这一段的解释也涉及“和”字。朱注:“淫者,乐之过而失其正者也;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者也。”徐复观则引述荀子之言来说明,如“诗者中声之所止也”、“乐之中和也”。(《荀子·劝学》)“故乐者,中和之纪也。”(《荀子·乐论》)并强调“不淫不伤的乐,是合乎‘中’的乐”。“中与和是孔门对乐所要求的美的标准。”(注:礼乐之治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是徐复观的动人诠释。见《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4页。)“快乐而不太过,这才是儒家对音乐所要求的‘中和’之道”(注:礼乐之治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是徐复观的动人诠释。见《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22页。)。李泽厚也认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了“中庸”的“哲学尺度”,也是“乐从和”“所讲求身心、人际、天人的和谐”的“标准尺度”(注:李泽厚:《华夏美学》,香港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页。)。他更从中西美学的差异,强调此中所呈显的中国美学特色,他说:“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具有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柏拉图)或心灵净化(亚里士多德)”(注: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第51页。)。在和西方美学的比较之下,若说“中和”是中国美学的特色并不为过。
《论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中和”概念,但是若“乐而不淫”包含着“中和”思想的主张可以成立的话,则“中和”亦被视为“君子之美”。在《尧曰》篇,孔子提出君子“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的看法,句式与“乐而不淫”相同,涵义也在于“适中而不太过”,可以说对孔子而言,“中和”不仅是孔门诗乐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君子的美德。甚至还应该这样推论,体现“中和”的诗乐正是陶养君子“中和”美德的必修科目,从艺术的创作欣赏到君子的修为乃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适中而不太过”是如何做到的?即在于情绪的抒发当中有理性的调节。因此中和可以说是情理相得的结果,广而言之,也是对立性的解消与多样性的统一。针对《左传·昭公二十年》中的一段话:“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徐复观指出这段话中的“相成相济,即是尧典所谓的‘克谐’,即是和”。且作一深刻该要的总结:“就和所含的意味,及其可能发生的影响言,在消极方面,是各种互相对立性质的东西的解消。在积极方面,是各种异质的东西的谐和统一。”(注:礼乐之治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是徐复观的动人诠释。见《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6页。)针对上面《左传·昭公二十年》的那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正好显出多样性之间可以“相成”;而下面一段“清浊”、“大小”、“长短”、“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等十组对立的性质之间可以“相济”。从这段话中,我们甚至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先秦儒家对“和”的思考体会是从“乐”得来的启发;脱离了“乐”,也就无法真正掌握“和”与“中和”的核心。而“中和”的境界正体现于情欲和道德的融合无间,针对这一点,徐复观的阐发最引人入胜,他说:
道德之心,亦须由情欲的支持而始发生力量;所以道德本来就带有一种“情绪”的性格在里面。乐本由心发,就一般而言,本多偏于情欲一方面。但情欲一面因顺着乐的中和而外发,这在消极方面,便解消了情欲与道德良心的冲突性。同时,由心所发的乐,在其所自发的根源之地,已把道德与情欲,融和在一起;情欲因此而得到了安顿,道德也因此而得到了支持;此时情欲与道德,圆融不分,于是道德便以情绪的状态而流出……道德成为一种情绪,即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道德与生理的抗拒性完全消失了,二者合而为一……所以孔子便说“兴于诗,立于体,成于乐”。(《论语·泰伯》)“成”即是圆融。在道德(仁)与生理欲望的圆融中,仁对于一个人而言,不是作为一个标准规范去追求它,而是情绪中的享受。(注:礼乐之治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是徐复观的动人诠释。见《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27~28页。)
徐复观在此强调通过“乐的中和”,情欲最终与道德“圆融不分”,而道德也成为“情绪中的享受”。这段话的另一个重点是“乐”,亦即惟有在艺术中,才能达到情欲与道德水乳交融的境界(注:艺术之外,人也能在“爱情”中达到相同甚至更完满的境界,只是儒家总是与爱情有隔。)。相较之下,理学家的“存天理,去人欲”,朱子的“人欲尽处,天理流行”的二元对立的表述就显得有点简单而且公式化了,甚至完全不符合现代人尊重个体解放、主体自由的思想倾向。让道德成为我们可以在感性生命中去享受它的东西,亦即让道德成为我们的感性生命的一部分,这或许提供了被指为泛道德主义色彩浓厚的传统儒学得以继续存活于二十一世纪的新的思考方向。
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论语·公冶长》记录子贡称美孔子的一段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朱注云:“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威仪文辞皆是也。”“德”虽未出现在上面这段话中,但朱子的注解仍十分确当,一方面指出文章与道德的关系,一方面指出文章是一种外显的形式。
儒家对“文”的重视本来就和其实践精神有关,因为“文章”是一种显现,不论情志的内容、本质、深度如何,只有发为文章,才能够传达,亦即文章是“可得而闻”的东西,能使“不可得而闻”的东西显现出来,这涉及“文”与“质”的关系。
不仅诗乐有文与质的问题,政治也有文与质的问题,事实上,儒家所谓“文章”最初是指涉政治的表现,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能无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文”在这儿都指礼乐法度的具体表现。孟子则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孟子·离娄上》)这段话不仅指出仁与义必须实践于日常生活,还指出“礼”是仁与义之有节有文的表现,更指出“乐”即是以仁义之实践为乐。因此“文章”既指政治的表现,也指道德生活的表现。
但是为什么政治与道德的表现都要求文采?荀子提出他的解答:“文”是道德表现之合宜,亦即文是一种抒发,又是对抒发之规范,过与不及之表现皆在“文”当中受到调整,荀子说:“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疆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荀子·不苟》)其次,荀子有“养欲”之说,主张以“礼乐文理”来“养情”。也就是说,“文”一方面是使政治道德之表现合宜的规范,一方面又是培养提升情欲所不可或缺的。儒家认为政治的目的在于养民、教民,而文之养民教民的功用如斯之大,统治者不可不察,故荀子指出先王圣人都认知到“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荀子·富国》)荀子并且批判墨家之“非乐节用”之说是不了解美文的大用。
儒家虽然重视美文的大用,但是也警觉到文质、文实不符的弊端,不仅道德之表现受文制约,文亦受道德实质内容的制约。虽然“好其实而不恤其文”是“腐儒”之征,(《荀子·非相》)但是文过其实也是不好的。
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即暗示了礼并非只是玉帛等外在形式,乐也不等于钟鼓之音而已。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可见他企图以“仁”来充实礼乐的内容。孔子主张形式与内容必须维持平衡,以成一不可分割之整体:“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论语》还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这两段记载显示了孔子认为尽善尽美才是音乐艺术之最高成就,且唯有尽善尽美之作才能达到“三月不知肉味”的艺术效果。固然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显出孔子的高超音乐修养,但也显出音乐可以使人超越于肉味的感官享受之上,而获得更高层次的享受。尽善尽美也可以说是艺术和道德的统一(注:礼乐之治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是徐复观的动人诠释。见《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3页。),韶乐以美的乐舞显现了尧舜仁政中的善的精神,是艺术和道德统一的典范之作。
文质彬彬之说受到荀子的继承和阐发,他说:“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创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尽;三年之丧,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荀子·礼论》)荀子指出三年之丧虽是丧礼的节文,但是此一节文是由于丧亲之创痛至巨至甚,因而相应于情之巨痛乃有三年之久的服丧之文,即“立文”乃是“称情”而后立的。而情过文或文过情都是不好的,都有违中道,他说:“文理繁,情用省,是礼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是礼之杀也。文理情用相为内外表里,并行而杂,是礼之中流也”。(《荀子·礼论》)“礼者……达受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故文饰麤恶,声乐哭泣,恬愉忧戚,是反也。”(《荀子·礼论》)“反”就是指形式与内容不相符合。唯有“文理情用相为中外表里”才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才是“中流”。
从孔子的“文质彬彬”、“尽善尽美”,至荀子的“称情而立文”,再到《礼记·乐记》的“情深而文明”,都是从政治、伦理生活中的情文并茂出发,再延伸到音乐;并且都指出内容的深浅好坏影响到形式的艺术效果,情愈深而文愈明,亦即艺术之整体表现中的感人力量与其内容的深浅好坏成正比。相反的,如果没有“文”为“外”为“表”,则情不论多深都无由感人,情文乃是相互依存的。对儒家而言,从礼乐制度到诗赋文学,都要能掌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才不流为“俗儒”。
兴、观、群、怨:主客合一
如果说“中和”是关于情、理关系的论述,“兴、观、群、怨”便是关于主、客关系的论述。对于《论语》中的“兴观群怨”,历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笔者将广采古今各家之说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大师卢卡契的文学理论,作此推论:“兴”是“主体”的觉醒,“观”是主体在觉醒后对“对象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人生等等)的“观察”(此时是采取“旁观者”的态度);“群”和“怨”在同一层,是主体“参与”“对象世界”的两种方式(此时采取的是“参与者”的角色),其中“群”是主体与对象世界之正面的、积极的、亲和的关系,“怨”则是主体与对象世界之负面的、消极的、疏离的关系;“群”表现“和谐”,“怨”传达“批判”。因此“兴观群怨”并不是平行排列的,而是主、客由互不相干发展为主客合一的过程的诗学表述。
《论语·阳货》中的这段话全文如下: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兴”字在《论语·泰伯》也出现于两处,一处是“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另一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针对“兴于仁”的“兴”,从包咸到朱子都释为“起”。针对“兴于诗”的“兴”、包咸、黄侃、朱子都注意其中的道德内涵。如包咸曰:“兴,起也,方修身当先学诗也。”黄侃《论语义疏》引江熙云:“览古人之志,可起发其志也。”朱子云:“诗本性情,有邪有正……故学者之初,所以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如此而得之也。”(注:上述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第二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29页。)朱子在这里并未提及“发”、“志”等字,不过“兴起其好善恶恶之心”已指出“兴”有激活善恶之心的意思。在针对“兴观群怨”一段,朱子则释“兴”为“感发志意”,显然是受前人注疏的影响。针对“兴”,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言:“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刘勰是在“赋、比、兴”的脉络中论“兴”,但释“兴”为“起情”,很值得注意。合起来看,可以说“兴”是感发情意志。近人对此亦多有阐发。
马一浮特别凸显“感”字,他认为“兴于诗”的“兴”有“感而遂通”之意,引申而言,“兴”也有“仁”的意思,他说:“《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此心之所以能感者,便是仁,故诗教主仁。”又说:“兴便有仁的意思,是天理发动处,其机不容已,诗教从此流出,即仁心从此显现。”(注: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页。张亨、蒋年丰接受马一浮的看法而进一步加以阐发,张亨认为“《论语》以‘仁’为人的真实生命,又以‘兴’就是显现这一真实生命。”见张亨《〈论语〉论诗》,《思文之际论集:儒道思想的现代诠释》,台北允晨公司1997年版,第91页。蒋年丰认为马一浮的看法是一种基于“仁的存有论”的“兴的精神现象学”,见蒋年丰:《孟学思想“兴的精神现象学”之下的解释学侧面——从马一浮论诗教谈起》,李明辉主编:《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学哲学研究所1995年版,第269页。)不论是感发志意、仁心,或起情,“兴”可以视为“主体的觉醒”。
“可以观”,郑玄注为“观风俗之盛衰”,朱子注为“考见得失”。两人皆着重“观”的冷静观察和考察的涵义。“观”在《论语》其它地方也出现,如《学而》中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朱注云“观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恶”,未直接释“观”,显然“观”的意思十分明白,即“观察”,目的是“知”,故“观”主要是认知活动。《公冶长》也记孔子之言:“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朱子同样未直接释“观”,显然也是认为“观”字意思清楚,不须多注。“观”可以说是主体在觉醒后与对象世界的第一类接触,此时主体是采取“观察者”(observer)的角色,从事一种不介入的、不作价值判断的认知活动。“诗可以观”主要即指出“诗”是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但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一样,不能满足于认知世界,一定会进一步主张改变世界。“可以群,可以怨”便是强调诗具有改变世界的能量。
朱子以“和而不流”释“群”。“和而不流”句最早出现于《荀子·乐论》,朱注可谓确当。“群”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可延伸出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和谐”应是主体有自觉的参与对象世界、与对象世界发展出良好互动的成果,因此“群”与“观”的差别便在于“观”是不介入的观察,“群”是积极的参与。“怨”与“群”在同一层,此时主体皆采取“参与者”(participant)的角色,不同于前一阶段仅作为“观察者”(注:卢卡契认为小说中现实主义(realism)与自然主义(naturalism)的差别正是“叙述”(narrate)与“描写”(describe)的差别。在“叙述”中作家采取“参与者”的角色,参与在人物的命运之中;在“描写”中,作家追求的是“专论式的细节”(monographicdetail)和“钜细靡遗的细节”(meticulous detail)。参见Georg Lukács,'Narrate or Describe?,'Writer and Critic,London:Merlin Press,1978,pp.110-113.本节所论主要受卢卡契的启发。)。若说“群”表现主体和对象世界的和谐,则“怨”是表现主体和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但朱子以“怨而不怒”释“怨”,比《诗大序》的“怨以怒”来得保守,自然也没有孟子在和齐人高子辩论时以“仁”释怨(《孟子·告子》)那么深刻。孟子认为“怨”由“仁”起,且怨的程度与仁的程度相应,这是多么深刻的理解,无所关心、麻木不“仁”,当然就不需要“怨”了,个体既然还感受到与家庭、社会、国家的连带关系,则对不平之事不可能无怨。也可见“群”是“怨”的基础。而“可以怨”指出诗对不公不义的社会具有批判精神。此中亦可看出“诗的正义”(poetic justice)是中西方美学在发源之时都加以强调的。
综合上述,“兴观群怨”涉及诗歌活动中的主客问题,“兴”是主体的觉醒,“观”是主体对对象世界采取旁观的立场,倾向认知活动;“群、怨”则是主体对对象世界采取介入的、参与的立场,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怨”的出现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故“怨”的真正目的仍是追求“群”,于是“怨”是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假如在“观”之中主、客尚未合一,则在“群、怨”之中,主客已经达到或趋向合一。
共鸣与启迪、沉醉:听者与作品的交融
儒家既重视艺术的化人之功,自然会重视听者(读者)的反应,当听者在诗乐作品中感受到相应的精神特质,会引起强烈的共鸣,艺术造诣高超的听者甚至会在共鸣中进入沉醉的精神状态。
“知音”的故事自然以《吕氏春秋·本味》所记载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最著名。伯牙因钟子期的死而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可见知音之难求。《文心雕龙·知音》有言:“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虽然伯牙和钟子期的“知音”故事表现了楚文化的特色,其浪漫激情的朋友关系也与《论语》中偏重伦理学内涵的朋友关系非常不同(注:参考陈昭瑛《性情中人:试从楚文化论〈郭店楚简·性情篇〉》,“郭店楚简国际会议”论文,武汉大学、哈佛燕京学社主办,1999年10月。),但“知音”的描写在《论语》中至少也出现了两次:
1.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
2.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宪问》)
第一条引文显示孔子是一个和钟子期一样已入化境的知音之人。韶乐之所以尽善尽美,是因为“尧舜的仁的精神,融透到韶乐中间去”(注:礼乐之治为“儒家在政治上永恒的乡愁”是徐复观的动人诠释。见《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中国艺术精神》,台北学生书局1974年版,第15页。),而孔子在欣赏中因其仁的精神与尧舜之仁的精神之间发生了强烈共鸣,故而感动到“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解释孟子以音乐为喻称赞孔子为“集大成”的一段,杜维明便强调集大成者所演奏出来的“伟大协奏曲”所给予听者的正是“内心的共鸣”所带来的“启迪”,他说:“两颗共鸣的心灵发出的微笑,或是两个彼此响应的精神气质的相遇,对呆滞的眼睛或迟钝的耳朵是无法说清楚的。美的语言不仅仅是纯粹的描述,美的语言是暗示、指引、启迪。并不是语言本身是美的……但是,语言所指涉的语言外的东西——内在的体会、心灵的欢乐或转化的精神——无论在美的创造或欣赏中,都是美的真正基础”(注:杜维明:《孟子思想中的人的观念:中国美学探讨》,《儒家思想:以创造转化为自我认同》,台北东大公司1997年版,第123页。)。
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则认为共鸣所能达到的是“沉醉”。他认为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一种“超越式的沉醉”,他说三月形容时间长,肉是美味的代表,三个月连味觉也忘掉了,表示精神已从形体的世界即肉体世界中解放出去了,达到了“精神的解放”、“精神的自由”、“精神的纯粹的超越”(注:今道友信著,蒋寅等译:《东方的美学》,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05~107页。)。
共鸣所引起的不论是偏于道德实践的“启迪”,或偏于美学的“沉醉”,都显示听者与作品之间进入了水乳交融的境界,呈现艺术创作与欣赏合一的整体性。
但知音并不完全引起共鸣,如上面《论语·宪问》的引文中,虽然荷蒉者听出孔子磬声中所传达的孔子心声,“有心哉,击磬乎!”也确是知音之言,但荷蒉的隐者并不体谅孔子知其不可而为的用世之心,而讥为“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这是知音而无共鸣的例子。
儒家对共鸣的重视、对听者的重视、对诗乐化人之功的重视,影响了后世的文学理论,塑造了中国文学理论中特别重视读者这一特色。理论家中甚至有人认为“读者的受用”比“诗篇的了解”更重要(注:朱自清:《诗言志辨》,台湾开明书店1982年版,第92页。),几乎发展成为以读者为中心的诗学。
礼乐之治:“社会美”的概念
儒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一样,认为美不只是艺术的范畴,还是社会的范畴。社会应该力求合乎美的规律。对先秦儒家而言,社会美还先于其它范畴的美,因为美文最早即指三代的典章文物、礼乐制度,后来才引伸到文学。
儒家所谓“先王立乐”、“先王制乐”是一件历史事实,显示西周君王对音乐教育的重视,以当时的人口来估计,周朝的音乐机构十分庞大,“大司乐”领导下的工作人员,除了“旄人”这种民间乐舞表演者人数不定无法计算外,共有1463人,从音乐行政、音乐教育、音乐表演一应俱全。杨荫浏认为,即仅以教育论,周朝即创建了世界上最早的音乐学校(注:参考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稿》第一册,台北丹青公司1987年版,第13页。)。如果不是深刻体会到音乐的大用,便不可能有这么庞大的音乐组织。儒家的乐论,是从仁的概念、人民的立场、对周朝乐制所作的理论上的总结。孔子以仁来充实礼乐的内容,他说“里仁为美”。(《论语·里仁》)是以道德、以善为美,而不耽溺于礼乐的形式之美。但是礼乐的外在节文还是不可或缺,因为我们看到孔子弟子子游为武城县令时,城中处处是“弦歌之声”(《论语·阳货》),孔子相信唯有在“弦歌之声”的潜移默化之下,一个社会才能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理想社会。
孟子主张统治者应“与民同乐”,即主张在艺术活动中,达到君王与人民融合为一的境界,而这便是“仁政”。儒家以仁作为个体与群体的统一,当把仁落实于具体的脉络,即常指涉统治者、知识分子和人民之结合,“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的“己”就是指君王、士大夫阶级。孟子认为乐之古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乐是否为群体所共享,不再为贵族阶级所垄断。对孟子而言,在弦歌声中,君民同乐,这便是理想的世界。
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他认为王者应“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荀子·王制》)什么样的政府算是美政?荀子以养民为政之先务,他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慈爱百姓,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荀子·王制》)“养民”亦包含教民,真正的王者“其知虑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诚美其德也,故为之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藩饰之,以养其德。”(《荀子·富国》)养民除了提供充足的物质需要,还需要提供美育,以培养提升人民的日常生活。孟子的仁政、善政之说在荀子转为“美政”,美政包含仁与善,并更进一层突出美育的重要,美育上以美政,下以美俗,使社会成为一合情合理、文采焕然的社会。“美政”之名的提出宣告儒家通过礼乐之治所提出的社会美概念的完成。
社会美的感性显现便是“吾与点也”一章(《论语·先进》)。可惜朱熹忽视孔子所重视的艺术化生活,而附会上“存天理、去人欲”的理论:“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事实上,“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生活中正寄托了人欲。孔子对其他学生所言之志并非不称许,然而觉得曾点所言涵盖其余而更进一层,即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段话。孔子认为,道德实践的最高境界在于以之为爱好、乐趣乃至享受。因此,道德的艺术化是孔门伦理学的目标;艺术的道德化则是孔门美学的主旨。“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和一群长者(包括曾点)一起出游,这分明是“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老者安之”这一社会理想的图像化,“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些话使这幅画流动起来,并唱出歌来,补足了原先“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老者安之”所欠缺的美学内容,这一大同之世乃是和“咏而归”的艺术化日常生活互为表里的。
美的社会对个人而言成为可居可游的家园,个人在其中感到自在自得,是其中的一部份。卢卡契便曾以人和世界所构成的整体来描述史诗世界,并以“家”来形容这种整体性:
在那些时代,星罗棋布的天空是一切可能路径的地图,因星光照耀出这些路径。一切事物皆新鲜而熟悉,充满着冒险。世界是一个广阔的家园,因为燃烧灵魂的火与星星同其本质;世界和自我,光与火,是明显有别而又彼此永不分离,因为火是光的灵魂,光是火的外衣。这样的时代就是幸福!(注: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Novel,Cambridge:MIT Press,1978,p.29.)
这是忍不住的希腊风采!但是到了近代,个人与世界发生了断裂,个人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他感叹:“康德的昭昭之星的碎片仅仅闪耀于纯粹认知的黑夜,它不再照亮一切踽踽独行的流浪者的旅途”(注:Georg Lukács,The Theory of Novel,Cambridge:MIT Press,1978,p.36.)。近人的星空不再如史诗时代一般,构成孤独旅行者的地图。
三十岁的卢卡契在他的前马克思主义时期的作品《小说理论》中,如此咏叹他对整体性的无尽乡愁,这乡愁贯注他一生的著作。
当徐复观说“礼乐之治”成为儒家“永恒的乡愁”时,他也是使用“家园”的意象。无家的乡愁是一种失落了整体性的惆怅与悲哀。乡愁成了永恒,是否意味着再美好的诗乐也唤不回整体性的灵魂?不过知其不可而为的新儒家因着一分对人性之无可救药的乐观,肯定仍会继续向整体性招魂。
标签:孔子论文; 论语论文; 国学论文; 儒家论文; 徐复观论文; 论语·八佾论文; 中国艺术精神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荀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