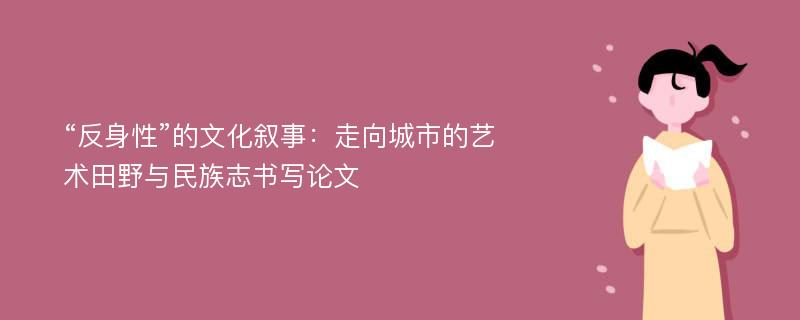
“反身性”的文化叙事 :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与民族志书写
吴震东
[提要] 聚焦于当下城市文化及社群性艺术事项的人类学研究,是针对“自者中的他者”所进行的“反身性”文化叙事。在此,“艺术田野”不仅作为具体的研究方法,用于解读城市中“大传统”与“小传统”,“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知识形态”与“时代症候”之间的结构性关系;更在方法论的层面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学科观念,使其在面对艺术活动时,为活态而流动的感性符号留出诗性的阐释空间。而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民族志制作,则既包含着一种入场经历的“诗学视域”也关涉着离场反思的“诗学书写”,并形成了从“审美事实”到“交互阐释”而至“意义文本”的艺术民族志写作范式。
[关键词] 城市文化;反身性;艺术田野;艺术民族志;文本叙事
近年来,部分人类学者似乎回归到一种“本土”的自觉,将田野点从“他乡的异域”迁延到了我们所熟知的文化场景中;与此相呼应,以文化“异质性”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学科,其观照的视域也由“乡村地头”扩展到了“城市街头”。质言之,经典人类学研究对于封闭式的原始社会或“异域的他者”关注较多,而对当下城市中的艺术文化活动则较为忽视。虽然越多越多的人类学者开始关注城市中蓬勃兴起的艺术文化事项,如广场舞、城市艺术区、艺术酒吧等,并将其纳入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视域之中;但这不免让我们思忖:人类学者在对“自者”文化域界进行观照时,其“田野点”应该如何理解?在此基础上,又该如何阐释当下城市社会中“大传统”(前卫艺术文化)与“小传统”(城市新民俗文化)之间的弥合与差异?在研究城市中的艺术文化活动时,人类学原有的理论形态又如何与艺术学、美学相融通而形成一种“艺术田野”的复合性视域?作为一种“反身性”的文化叙事,其民族志的书写又该遵循何种文本范式以完成一种“知识的宣称”和“诗性的阐释”?基于以上问题的导引,便是本文展开的逻辑线索。
一、“田野”:“反身性”与城市中的文化他者
人类学关注“城市”研究有其学科的历史性脉络。人类学“不仅关注‘空间上的他者’(原始人),同样也关注‘时间上的他者’(他们自己的过去)。”[1]而对“时间上的他者”所进行的研究,也大体相当于对“自者文化”的研究。由于受到早期学科分类意识的影响,自人类学学科成立以来,学者们更倾向于将“田野点”定格在“远方的异域”,其研究的对象也主要聚焦于“异域中的他者”。因此,人类学对于“自者文化”抑或是“城市文化”的相关性研究在21世纪之前,并未得到太多的重视。R·E帕克(Roert Ezra Park)这样说到:“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迄今为止基本上只注重了原始人群的研究,而文明人类其实倒更是引人入胜的研究课题。同时,文明人类的生活也更便于考察和研究……当今的城市生活需要更为深入而公正的研究。”[2](P.3)在他看来,“城市”不仅是社会个体或者基础设施的简单聚合,而是一种关涉着特定礼俗传统、思想情感的文化结构体。
如果将“城市”视为“文明”的栖息地,它则更少地出现在人类学文化研究的“田野点”之中。在一般意义上,“田野点”是隐含着与“自者文化”相异的地方,而“田野”的过程便是对“他者”(other)与“他者文化”(other culture)进行“参与观察”(participate observation),并对其整体性特质进行经验化描述的过程。进而言之,人类学负以文化研究为名,意在揭示特定人群在日常生活及其社会行为背后所涵摄的“文化语法”。有鉴于此,人类学的“田野点”并非是以与本土社会相隔的时空间坐标来衡量,而是为“文化共同体”中所呈现出的异质性所圈定。在此,“田野点”亦成为文化原生性与多样性的分析和确证之处,人类学研究也并不局限于远方异域之中的“他者”及土著文化,也应该对“自者”中的“亚文化”或“属文化”群体进行解读和分析。事实上,人类学研究已然从早期所专注的原始社会,渗透到迥异于“主流”和“中心”的边缘性文化群落之中。“田野点”轨迹的历史性游移也昭示出:人类学施为的重心亦从社会结构、文化功能游移至日常生活、身份认同等更具时代性的文化论题上。这既体现着人类学对于自身学科传统的反思性回应,也反映出人类学进入了文化批评的“实验时代”(experimental moment)[3](P.vii-ix),其研究目标不再限于采撷或描述一个“种属”或“类属”的文化活动,更聚焦于对特定人群之生存状态的穿透和理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学以“问题”和“对象”为中心,进行了诸多跨学科的交叉性研究,并延展了新的研究视域和理论边界,城市艺术田野便是以此作为其学理性的起点。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展开,市民性的艺术实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诸如广场舞、城市艺术区、艺术酒吧、汉服“雅集”等文化形态悄然成形。有关学者说到:“中国人民的艺术生活由于都市化进程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动向,这就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空间和无限多的可能性。”[4]而“艺术田野”便是以特定的艺术现象为切入口,进而考察这一文化生产群体的整体性特质,以及该现象背后所关涉的社会动因与时代态势。在此,城市人群的艺术实践,既反映着个体化的审美取向,也关涉到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结构预设。质言之,不论是较为精英前卫的艺术文化(如北京“798艺术区”、“宋庄艺术区”、艺术酒吧等);还是大众所参与的“民俗性”文娱活动(如“广场舞”、“KTV”、“汉服雅集”等),这些表面上呈现为“双极化”倾向的文艺事项,不仅表征着城市人群按自身文化需要所各自结成的“共同体”,还于一种结构化的并置中彰显着当代城市生活的整体性和通融性。雷蒙·威廉斯曾提出以整体性的生活方式来定义文化:“我们在这两种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指一种全部的生活方式——共同的意义;指艺术和学问——发现和创造性努力的特殊过程。有些作者用该词表示这些意义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而我坚持的是两者,是两者结合起来的重要性。”[5](P.4)因此,人类学将其文化研究的视域延伸到城市人群,这既是对学科自身的时代性回应,也是对现代城市人群的知识生产、文化消费以及整体性生活方式所进行的“反身性”透视。质言之,当原本熟悉的“自者”,在特定的场域中成为边缘化且具有异质性的“他者”或者“类群体”时,它便涉及到一种“反身性”研究。
在此,“反身性”是基于自身经验对“我者”所进行的反思。从内容上来说,城市的“艺术田野”不同于经典人类学所关注的“远方异域”,它聚焦于研究者自身所处的城市文化人群,即“自者”中作为某一“群”或者“类”所进行的知识生产及艺术实践;而在形式上则呈现为一种悖论性的消解与建构,研究者需要在“田野”中对“熟悉”进行“去熟悉化”和“再熟悉化”。“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离开‘家乡’而是不加鉴别地赋予异地考察点以差异性。”[6](P.14)换言之,“田野点”被视为隐含着差异的地方,而我们将新近的城市大众文娱活动纳入人类学的“田野”之中,其“差异性”的来源有二:其一是艺术文化活动本身所呈现出的“异质性”和“类属性”;其二则是民族志者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曾经熟悉的“自者”,即对“自者”进行“去熟悉化”的处理并进行一种“反身性”的文化叙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结果”出发,去考察当下城市大众文娱活动中有关“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质性与分类,进而获得一种“整体的想象”。
二、现代城市的文化消费:“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弥合
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表述,来源于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于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他这样写到:“一个有其独立自主文化的社区里必然会存在着一个复合性的文化结构,这个文化结构里就包含着一个大文化和一个小文化。”[7](P.115)在此,他提出一种关于文化形态的二元分析框架:其中“大传统”是指以城市为中心的文化,其受众人群多是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而“小传统”则是以农民阶层所主的文化。个体成员若要进入“大传统”需要通过“训练”、“考核”或“授权”以获得某种“身份”,其文化扩散的范围也较为封闭;而“小传统”则大多凭借“亲缘”和“地缘”为中心的村落化、民俗化的方式得以传播,成员之间相沿成风,相染成俗而逐渐形成以中心向周围扩散的文化圈。相较于“大传统”而言,“小传统”则是一个较为开放的途径。而我们当下城市文化生活,即“自者文化”中也存在一种“大传统”与“小传统”的知识形态。如果仅从扩散途径的层面来分析当下的城市文娱活动,我们进入以“798艺术区”、“音乐酒吧”等较具前卫性气质的“大传统”,与进入“广场舞”、“汉服雅集”为代表的“小传统”之间,并无太过严格的身份区隔。就这点而言,这两者作为城市艺术田野的对象,并无传统社会中所体现的绝然对立。
进而言之,在艺术田野的工作中,民族志者既要秉承经典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研究范式,也要在“写艺术”的意义关怀下,阐述艺术创作者、接受者以及研究者自身对于城市文化艺术的情感性真实;在多方参与的策略性对话中使复调性叙事的文本注入一种建构性的张力,其“制定”(enact)抑或是“叙事”(narrate)的意味也由此彰显。“许多具有自觉意识的民族志作者发现很难从一个固定的、客观的立场来谈论定义明确的‘他者’。差异干扰了文本;它再不能被陈述(represent);它必须被制定(enact)。”[13](P.104)而艺术民族志所要传达的,既不同于“隐匿作者”的客观陈述,也不仅限于表述主体单方面的情感态度或理性意图,而是在多方参与的文本中创构复调对话的叙事范式,这既是“阐释的阐释”也是一种“建构的建构”。就如克利福德所言:“重点在于文本化的创生特征(emergent character),文本化只是最初的揭示步骤,它提供了一个供读者参与解释的协商文本。解释的过程并不限于读者与文本的关系,而同样包括了最初对话各方的解释实践。”[13](P.127)在创生性、协商性、对话性的文本写作范式下,叙事者的声音与作品角色中的声音(受访谈者)也许存在一定的矛盾,但也正是矛盾中所蕴含的张力,才体现了艺术作为一种情感符号所具有的流动性与多义性。
城市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并置互彰,喻示着“艺术”、“审美”作为一种文化消费方式而融入日常生活,“换言之,每一个群体的生活世界是由这个群体的文化所塑造的。”[8](P.8)而群体的结成则放大了这种氛围的体验,“个体的生活世界由他们所属的不同群体中相互交织的文化力量所组成,并为他们所处的社会语境所结构。”[8](P.8)在此,艺术活动不再被视为一种“固定的符号”,而是更依赖于一种“在场化”的连接和激活,这使得艺术超脱出自身的“自足性”存在,而构造出一种氛围化的体验场域。以此作为理论阐发的起点,城市田野的对象——“大传统”与“小传统”的艺术文化活动作为一种“表征的媒介”,将参与者引入到一种“审美活感性”之中,并获得即时性的氛围体验。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人类学视域下“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所存有的差异性,也就在“艺术”(引入)——“氛围”(进入)——“体验”(消费)的这种动态链条中得以弥合。艺术在此作为一种介质,将观者引入特定的氛围之中,这种“氛围”类似于本雅明所提出的“灵晕”(aura)。在本雅明看来,“艺术品中,对其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艺术品本身存在的灵晕,这并没有从它之前的礼仪功能分离。”[9](P.8)他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灵晕”最初来源于人与自然对象的审美距离,而这种“距离感”则与时间、空间以及心理状态相关,并关涉着美与艺术的“神圣性”和“唯一性”。
杂散电流腐蚀防护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依靠供电专业,它需要多专业相互协作和共同维护。保持轨道交通道床面的清洁、干燥和对于不符合绝缘要求的钢轨绝缘垫进行及时更换,看似是轨道工务专业的职责,其实却是从“以堵为主”的源头治理杂散电流的好方法。但是,这些往往是在运营维护工作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事情。
针对于此,艺术民族志的功能就不再拘囿于艺术活动的文本记录,更应在“写艺术”的层面上去设立一种意义生产的诗性空间。因此,“城市艺术田野”在艺术审美与事实观察的复合性视域下,其艺术民族志的文本形制,则是一种遵循着情感、经验和文化事实的意义性叙事文本。事实上,这种文化叙事也常常包含着一种修辞的维度,而成为一种修辞化的叙事。在关注前见、情感以及个体化经验的前提下,“写艺术”总包含着一种“通过语言、想象和象征在建构现实的结构。”{19](P.128)不可否认的是,当人通过感知和理解形成经验并对其加以阐释的时候,他们就在进行一种叙述性的编排。因而,艺术民族志文本中则无法避免地掺杂着主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因素既不应该被“放大”,也不应该被“无视”,而应该在叙述时被修辞化地“处理”。当“自者”对“他者”进行替身性叙述的时候,那么这种叙事就不仅仅只是“讲故事”(story-teller),更是一种裹挟着多层次声部的行动和策略,并暗合着某种“互文的叠加”(intertextual overload)。首先是“他者”或“当地人”向民族志者讲故事,然后是民族志者向读者讲述叙述者的讲述,期间还掺杂着民族志者本人的讲述以及“他”作为“他者”的讲述,这样不同的声音就成为了整个叙事结构中的组成要素,并形成了一种复调的对位。质言之,“当讲述者的内容成为了作者建构整体叙事中的一个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一个层面上的讲述,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变成了被讲述的内容。”[20](P.8)通过一种“并置”的方式,即讲述与故事相互渗透叠合的修辞性手法,使得意义超出了文本之外。它作为桥梁维系着事件历史和意义生产之间的流动,这便是一种“诗学化”的文本叙事。在此,意义得以被解读和建构,并赋予“事件的真实”以“时空分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美学纵深。
当下城市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纵然作为分属于不同文化人群的两种知识形态,但当其作为一种追求体验效用的消费途径,并作为一种对抗城市“异化”经验的艺术实践活动,两者所存有差异性便趋于弥合的状态。前卫性、精英化的“大传统”与大众性、民俗化的“小传统”集合成一种整体性的文化结构体。这里的“集合”不同于以社会生产为旨归的“机械化团结”(mechanic solidarity),而是旨在去形塑一种风格性、多元性的“有机化团结”(organic solidarity),以获得共通性的审美体验和集体记忆。在此,知识形态的差异性已不具有“高雅”和“低俗”的明晰边界,亦不能看做是毫无关系的相互对立体,“人们在文化上更具有‘杂食性’(omnivorous),因为他们用新颖和折衷的方式将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掺杂、混合在一起。”[8](P.75) 借用“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文化结构分类,以“广场舞”、“KTV”为代表的大众俗文化所构成的“小传统”,与以“艺术区”、“画廊”、“音乐酒吧”等具有先锋化、精英化气质的“大传统”之间,脱去了传统社会中所存在的对立和区隔,而成为当下城市文化生活中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其文艺活动的展开也指涉着一种“场地美学”(grounded aesthetics)的发生。那么针对于此的城市“艺术田野”又该如何展开呢,则有必要重新梳理整合人类学、艺术学与美学的相关理论。
乡村产业兴旺与经济振兴需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发挥引导作用,重点在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投入引导、示范引导等方面发挥作用。即使是一些具有公共性的项目建设与持续供给问题,也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好市场机制的作用。以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践为例,许多乡村之所以能实现可持续的村容整洁和生态宜居,除了政府重视、增加投入、强化考核和发挥村规民约的作用,也离不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特别是将村容整洁、生态宜居建设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持续推进的动力。
三、“间性的透视”:身份与视域
在一般意义上,人类学的“田野”理论可以概括为三大问题:第一,看什么,对象是谁;第二,在哪个位置,以怎样的身份去看;第三,用什么样的文本形态来表述自己的“看”。这三大问题,构成了人类学理论的总纲:第一是“对象”的问题,第二是“视域”的问题,第三则是“书写”的问题。
进行“艺术田野”时,“看什么,对象是谁?”这一问题比较好回答。就城市艺术区的田野工作而言,其研究对象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对于“艺术家”的研究;二是作为“他者”的文化消费群体之研究;三则是对特定文化艺术形态的研究。其一,针对于艺术家的研究,传统的问卷调查及访谈法完全可以适用。当然,如果访谈对象是“798”艺术区中的职业艺术家,则需要有一定的艺术知识和美学素养,才能进行较为专业的对话。其二,研究文化消费及接受群体,其方法基本可以同上,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接受者”往往也具有“生产者”和“参与者”的身份。其三,对于文艺活动及其艺术生境①的研究,则需要“在那里”的经验性实证,又要在不囿于“实证”的诗性视域中去捕捉其中所蕴含的审美情态,以求对活态化的文艺活动进行细腻而精到的把握。以此作为论述的前提与逻辑起点,我们尝试来回答城市艺术田野中关乎“视域”与“身份”的问题,即“艺术田野”在认识论层面究竟如何获得一种“事实”与“假设”、“实证”与“情感”、“经验”与“意义”之间的辩证性平衡。
诚然,人类学知识来源于对“他者”文化事实的分析和阐述,通过“到那里”(being there)的实证经验作为话语表述的基础,而“在那里”则大体意味着通过田野工作完成一种从“局外人”(outsider)到“局内人”(insider)的身份性转位。在此基础上,民族志者从特定的文化扇面切入,“以点到面”的进行一种“整体观”(holistic paradigm)的勾勒。“整个部落文化区域的所有方面都必须加以研究。从每个方面所取得的连贯一致性结论、定律和秩序,也就能够将这些分散的方方面面整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12](P.9)即从艺术符号的观察记录到象征意义的揭示延展——“田野作业”的首要意旨便在于此。因此,“艺术田野”既是特定的时空场域,也是一种进行观察的“亲在性视域”。这里的“亲在”或者“此在”(Dasein)②并不意味着一个抽象的存在者,而是特指“为此”、“在那里”(da)的一个“存在者”(sein)。在一定意义上,这种特指性由观察对象的阐释特性所规定,因为对于艺术活动及其美学情态的理解和把握本就存在着个体上的差异性。然而,如果说人类学将“艺术”作为文化枢系中的一个节点,在“符号能指”与“意义所指”之间呈现出规律性的参照系,那么这就涉及到了一种客观性与普适性的定律和结构。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现代民族志的代表作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说到:“民族志田野工作首要而基本的理想便是,清楚而明了地勾勒出所研究社会的结构,把所有文化现象中的定律、规则从不相干的事物中梳理出来。”[12](P.9)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田野-民族志”组合范式便是经典人类学的研究模式,要求研究者至少在田野中完成一年以上的参与观察,以“民族志照相”的方式来表达立于经验之上的文化分析。但是,艺术及其审美的质性却通常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感性化片段之中,并潜藏着一种符号化的隐喻。这就对传统的“民族志照相”,提出了认识论上的质疑。
以城市艺术田野的对象之一“广场舞”为例,这种灵晕所带来的“距离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民众“身份上的转位”。质言之,“舞台上”与“舞台下”的身份之间存有着一种距离,在一种即时性环境(氛围)所规定的秩序中通过转换身份的表演而获得一种“被看”的陌生化舞台体验。诚然,广场舞作为群众性的艺术活动,不仅只是简单的“个体集合”更指向了一种“群体的狂欢”。巴赫金这样表述到:“在狂欢化的世界里,一切等级都被废除了。一切阶层和年龄都是平等的。”[10](P.285)正是如此,他们得以成为一个共同体,“个体感受到自己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巨大的人民肉体的成员。在这个整体中,个别肉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再是自身了:仿佛可以相互交换肉体、更新(化装、戴假面具)。就在这个时间里,人民感觉到了自身具体感性的物质——肉体的统一与共性。”[10](P.290)人们在集体文化实践的过程中塑造了一种组织化的“团体”。广场舞作为城市社会中人群交涉互动的技能,“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一种制度性媒介、一种渠道亦或是一种场合”[11](P.202)实现了成员之间的互动性自我调谐,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个体意志与集体行动、个人需要与公共秩序之间的裂隙,成为现代城市生活中特有的大众文化现象。
然而,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人类学对曾经笃信的“文化科学”进行了反思和质疑,而民族志“权威”(authority)亦发生了消解和断裂,并在“部分的真理”(partial truths)[13](P.1)中得以被承继。在此基础上,民族志文本成为一种“文化的意义阐释”而非“文化的客观本体”。诚然,从来就没有统一而凝固的文化质性,它更多地呈现为一种生成流动的经验集合体,而民族志作品则是将其进行再次的文本化集合。正如格尔茨所说的:“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种文本的集合,其文本自身也是一种集合,这些文化原本属于这些当地人,而人类学家则努力隔着这些人的肩头去解读他们。”[17](P.452) 因此,民族志既是在从事文化翻译工作,同样也是对异文化进行一种文本化的分析和批评。尤其是在对地方性人群的社会话语、交往行为等文化要素进行分析时,格尔茨将其视为一种活态性的符号意义系统。在此,文化亦即成为一种可供解读的文本(culture as text)。这也昭示着后现代民族志理论在认识论层面上所呈现出的双向流动性:我所理解的对象即是对象中向我所敞开的东西,同时也建构了我作为主体自身的理解可能性;而对于对象的理解既是体验之后所留存在记忆中的东西,也是“当下”融入到“历史”与“整体”之中所形成新的阐释基础。因此,民族志文本不再只是“知识的传送带”③,而在格尔茨、詹姆斯·克利福德等人的集体影响下走向了“书写”和“阐释”。无论是“深描”(thick description)抑或是“铭写”(inscription),后现代民族志理论的“写文化”对于艺术民族志的“写艺术”颇有启发意义。
测试软件安装在测控组件的PXI系统的计算机上,是全系统的控制核心和数据信息处理中心,与测试仪硬件构成完整的测试系统,共同完成对产品的测试任务。测试软件与测控组件、测试平台和气源单元之间的外部接口主要包括模拟量采集,总线通讯控制,接口关系如图1所示。产品输出的信号由电气转接单元引入多功能卡AD通道由测试软件进行信号采集,测试软件对产品的加电、状态控制通过多功能卡DO通道控制电气转接单元的继电器动作来实现。测试软件通过RS422总线与程控电源和测试平台进行交互,通过RS232接口与气源单元进行交互。
进而言之,在城市区进行“艺术田野”时,研究者并不只是作为一个拷问“真实”的“冷眼者”和“文化照相”的记录者,更是参与其中的创造者和实践者。这就要求他既要有“入乎其内”的情感认同,又要具有“超乎其外”的价值中立;既要能够以“局内人”(作为观众的一员,甚至作为参与者)的眼光来理解其艺术活动的感性形态,也要能够以“局外人”(文化研究者)的视域进行知性的美学判断。在此基础上,“艺术田野”则形成了一种关涉着视域和身份的“间性透视”:其一,田野者不仅在“自者的背景中观看他人,也在他者的背景中观看自己”[13](P.199),更要去观看在熟悉的背景中成为“他者”的“自者”;并作为“局内的局外人”(insider as outsider),以“异化”眼光来看城市文化中的形态转换和规则变迁。其二,他需要在艺术审美与文化事实之间做出提炼和判断,以特定的“期待视野”去感知艺术文化活动中的“召唤结构”。其三,田野者在“陌生”与“亲熟”之间,去体验“经验的接近”(experience-near)从而达到文化相对论意义上的理解;而在“经验的远离”(experience-far)的基础上,提炼出“另类知识”中所具有的规律和意义,而非事无巨细的去记录一种片段化的“盲目的清晰”(blinding clarity)——这便是城市艺术田野的视域,也是将“熟悉”进行“去熟悉化”(defamililarzing the familiar)的过程。最后,田野者不仅从“自者”中抽离出“他者”,也让“自者”成为“他者”而进行“反身性”的观照,以“直观”和“共情”的方式去理解作为“另类知识”的艺术,并进行“模糊的推理”(abduction)[14](P.14)以获得艺术活动中所连带的文化层属性和社会制度性。这也使得田野者在一种“复合性”的视域下去理解不同于实证科学的艺术之“美”,并将“他者”之美、“自者”作为“他者”所理解的美,以及“自者”作为主体对艺术对象所体察到的美进行比照和阐释。这种过程就呈现为一种诗学向度上的“间性互渗”,而在此之上所“制作”的艺术民族志,则昭示着一种“写艺术”的文本叙事与诗学阐释。
四、“写艺术”:文本叙事与诗学阐释
张朝,云南彝族人,是当代著名作曲家,年幼开始学琴,16岁就创作了处女作《海燕》和《诙谐曲》两首作品,并在首届“聂耳音乐周”上公演,随后这首《诙谐曲》便发表于《音乐创作》这本书,年仅18岁的他便与交响乐队成功合作的演出了《山林》钢琴协奏曲。张朝的音乐创作涉猎面非常广泛,不仅仅包括钢琴曲、交响乐、民族器乐,还包括室内乐、舞剧、歌曲、影视音乐及大型广场艺术音乐等方面,他的很多优秀作品都在国内外获奖,其中代表作:《春嬉》《风》《图腾》《山晚》钢琴曲《滇南山谣三首》及无伴奏合唱《春天来了》分别获得第二、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不同于社会结构、制度权力、亲属关系等经典人类学所能进行实证分析的对象,“艺术田野”的首要研究对象是特定人群所进行的活态艺术实践及其背后连带的审美文化观念。“艺术”作为一种情感化的符号,在不同生境中呈现出各异的情态指涉,并根据接受者的个体性差异从而解读出具有多元性的意义内涵。因此,“艺术田野”的工作不同于社会科学实证意义上的“民族志照相”,它更多是对于特定艺术形态及其审美观念所进行的考察和体认,并关涉着想象、经验、趣味等一系列混杂而流动的情感质素。传统田野工作中所标榜的“科学之真实”并无法有效地阐释“艺术田野”中的事项,因为艺术美学研究本就不具有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实证唯一性。“艺术田野”依托于人类学之大写的文化研究,其田野工作更注重艺术现场的活态质素以及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主体性情感。质言之,“艺术田野”旨在通过经验性的参与观察,以求达到对艺术话语与美学情态的感知性把握。因此,不同于经典人类学的田野研究,“艺术田野”是一种“亲在性”体验的获得和“诗性”视域的生成,它不仅强调在具体的时空场域下对于艺术活动的经验化记录,更在于通过一种“主体”与“对象”之间所生成的双向性意义体认——依靠田野作业中所获得的感性瞬间来定格出关于城市艺术区、文化人群及其艺术实践的“印象”化呈现。因此,“艺术田野”的要旨更在于获得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情感真实”,但是它又和专注于艺术技法、审美自律及哲学思辨的一般性艺术美学研究不同;它由于“人类学性”的统摄而试图在经验和现象的基础上去谋求一种“主位理解”与“客位观察”、“个体化呈现”与“整体性表征”之间的平衡。因此,“艺术田野”不囿于一个实质意义上的空间坐标,而是寄寓于一种“间性化”的身份和视域,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种复合性观感状态。
艺术民族志作为对“他者”艺术实践和审美观念的理解和阐释,也必然存在着一种文化的距离,这种距离也会导致文本的表述只能观照到“部分的真实”。因此,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及其民族志书写,并非要以经典民族志的文本形态去追寻“绝对的真实”,而是在立足于艺术经验和审美情态的基础上去趋近一种“情感真实”或“诗性真实”。质言之,“写艺术”的阐释学范式,便是基于对城市人群的“存在状态”及其“文化症候”的观照分析,以“身份”与“视域”、“书写”与“阐释”的双重诗性去弥补“自者”与“他者”、“读者”与“作者”、“艺术审美”与“客观事实”之间的文化距离感。诚如保罗·利科所言:“整个诠释学的目标之一是要抵制文化上的距离;这种抵制本身可以通过纯粹时间性的方式理解自己,就像一种对长期疏远的抵制;或者通过更加诠释学的方式理解自己,就像一种对从意义本身来说——也就是说文本得以建立的价值体系来说的——疏远的抵制;从这个意义上看,诠释就是‘靠近’,‘使平等’,使‘同步和相似’,就是真正地让首先是陌生的东西成为自己的。”[18](P.165)实际上,在后现代民族志的文本写作里都极力避免着“观察者——被观察者”的表述权利问题及其意识形态的区隔,而是关注特定知识情境下所发生的“话语生产”,其最终的“文本”便是一种制造故事的对话性语境呈现。就如克利福德所强调的:“民族志可能正是对话自身;或是关于共同环境的一系列并置叙说,就像同观福音一般;或者也可能仅是探寻共同主题的一系列独立叙说;甚至是各种叙说或一个主旋律和多个变奏曲的对位交织。”[13](P.126)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独白式的“单声部文本”让位于田野情景中的“对话性生产”;从静态的、单一的知识论到包含着“主体”和“对象”,“参与”和“理解”、“介入”和“阐释”、“体验”和“移情”、“当下”与“历史”等诸多要素的“间性阐释学”。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文化表述的权利性差异得到最大程度上的弥合。艺术民族志也在此“对话性”的多声部表述中,成为一种诗学向度上的文化阐释文本,旨在观照艺术审美经验之中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意义生成的问题。
然而,就两者的差异而言,则首先体现在受众群体的文化素养上。“大传统”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如欣赏“798艺术区”中的绘画、雕塑以及一些先锋性的艺术作品,则需要有一定的美学常识并知晓一定的艺术技法才能更为有效地实现文化消费;而后者如“广场舞”、“KTV”等作为“小传统”的艺术样式则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大众皆能投身参与。诚然,前者更多地标榜着“为艺术而艺术”的架上化做派,而后者则更倾向于民俗性文化娱乐活动中“为生活而艺术”的态度。正如雷德·菲尔德所说的:“从表面上看起来,不同种族的人们似乎都同样地在活着,但其实他们各自的活法是大不相同的,而且他们各自生活的地点和条件也是大不相同的。”[7](P.115)但是,若将“文化”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层面来看,无论是具有一定前卫性、精英性气质的“大传统”,还是倾向于大众性、民俗性的“小传统”,两者都是当下城市生活中人们对于文化艺术消费的一种选择,其关注的核心是一种审美体验的获得,而非仅将其视为身份象征的表意符码。伴随着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当下城市人群的物质生活逐渐富裕,人们对于精神性、体验性的文化消费也日益成为主导。这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着“大审美经济”(aesthetic economy)时代的到来,其特征就是商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超越了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其消费的最终指向则是有关快乐和幸福的效用维度。
现代城市“制度化”与“机械化”的生活,夹杂着“异化”的痕迹;而“反抗”的手段之一,便是在休闲娱乐、艺术审美的活动之中寻求不同于日常生活的陌生化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城市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则为“反异化”的体验性消费提供了一种艺术性、审美性和实践性的导向。人们借由在“大传统”中的“遁闭的消隐”或“小传统”中的“群体的迷狂”来暂时摆脱现代城市社会生活的烦闷,亦借此实现一种“卡塔西斯”(katharsis)的净化或宣泄,希冀用“陌生化”的审美体验来对抗日常生活本身的“异化”经验。如“大传统”中的“798艺术区”,它以废旧厂房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室,因其炫酷而新奇所以满足了部分民众的猎奇心理,人们置身其中,便可获得一种“陌生化”的场景体验。而“小传统”也同样如此,“广场舞”营造出与“日常身份”不同的“艺术身份”,通过“台上”和“台下”两种不同身份之间的“碰撞”与“互动”作为过程,以参与性的方式获得一种“群体的狂欢”,进而建构异于城市日常生活体验的“陌生化”文化空间。
1.2.7 随访 所有病例随访至生后18个月,采用gesell量表进行神经系统预后评分,gesell量表评分:包括动作能、应物能、言语能、应人能。预后不良定义为死亡,gesell量表两项以上评分<85分,或合并听力异常。
身份与视域的定位直接影响了文本化表述的经验叙事,而“在经验性叙事中,认识模式与讲述模式几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层面。”[15](P.157)前者关乎着如何理解事件的“发生”,而后者则是让“发生”以艺术民族志的形式被阐释和还原。作为阐释“自者”的阐释,城市艺术田野的经历在以民族志文本的方式进行重塑时,“作者‘在那里’,但是如何将其显现在文本中,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比完成亲自‘在哪里’的任务更容易。”[16](P.33)对此格尔茨这样说到:“后者的最低限度需求毕竟不过就是旅行预订和入境许可;情愿忍受一定程度的孤独、隐私侵犯和身体不适;坦然面对长出的古怪的包和无法解释的发热;面对不那么明显的羞辱而不为所动的能力,以及能够支撑大海捞针般无休止的调查的耐心。而‘作者式的在那里’一直都是越来越不易的。”[16](P.33)民族志文本中的表述及其在场问题一直都是关注的焦点,但其根本要素是要从“在那里”(being there)的亲身经历中获得一种可供读者信赖的表述权威性。
此外,在“艺术接受”的层面上,艺术民族志文本即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或“意义载体”,而在将来的读者中继续被阐释和创作。这个过程便涵摄着“可读文本”(readerly text)与“可写文本”(writerly text)④之间的关系性张力。因此,不但艺术民族志文本的写作是关乎阐释和对话的生产,而且对其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同样是一种关涉到读者“二度阐释”以及多方参与的“跨时空”对话。尤其是读者,他会依据个人的经验而回溯到文本所记录的活态情景之中追寻未定的“空白点”进行补白。在此,“写艺术”不仅是主体自我确证的产物,它同样也依靠着读者、氛围和时代而实现其意义的繁衍,因为“事件发生的框架或环境与事件本身一样重要。”[21](P.61)而以此作为“编排”素材的艺术民族志作品则成为一种媒介体,读者依靠媒介而面向事实本身。此处的“事实”并非意指着普适性的、科学的、唯一的“真实”,而是在选择、合并、自我揭示以及交互阐释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种关乎情感及美学向度上的“流动的真实”。“人类学者的描述只有跟读者进行交谈才能达到效果,成为有目的的积极表述而非劝说,因为劝说常常被批评为具有方法论上的错误,并在职业道德上受到质疑。如此一来,就只能希望读者通过文本所呈现的效果和召唤去寻找意义。”[11](P.90)艺术民族志作品既作为一种情境化的叙事,又作为一种具有“未定点”和“空白点”的意义文本连带着阐释学的介入;而阐释又会依据作者、读者的个体经验、知识效力以及时代社会的差异而具有着无限的可塑性,并在“阐释学循环”中以趋近一种“整体化”的目标。就如斯蒂芬·泰勒所言:“整体的意义既非文本决定也非作者所独享的权利,而是文本-作者-读者间的功能互动。”[13](p.132)
(一)投资风险问题,投资风险主要是由于公司面临外部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造成公司的实际投资收益与预期投资收益出现偏差的风险问题。投资风险大致可以分为实物投资风险和金融投资风险。前者主要包括经营投资、流动资产投资、无形资产投资风险;后者主要包括了市场、通货膨胀以及利率等风险问题。
如果以此来定义艺术民族志在认识论层面上的功能性,那么它也昭示着其文本形态的历史性复相:一方面它承继了经典民族志(现实主义民族志)的写作意图,即从“文化切割”到“文化全观”的视点游移中去探究个别文化要素在整体社会文化枢系中的位置和效用;又在另一方面整合了后现代民族志理论中对于“事实描述”与“意义解释”、“叙述范式”与“修辞策略”的“诗学化”调解。因此,城市艺术田野及其民族志研究的要旨,便是通过感知艺术话语,重构美学指征,以“间性”的理解和“诗学”的阐释所进行的一种“反身性”文化叙事。
结语
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最终目标之一,就在于解释人类生存图景背后所蕴含的普同性(universality)与相对性(relativity);也正因如此,它要求对“自身”与“他者”所处的文化域进行质疑、比照和反思,并从不同的侧面去制定一种民族志意义上的“文化叙事”抑或是“寓言”,以求为特定人群的行为话语提供可信且易懂的经验证据、阐释框架和意义枢系。在城市艺术田野的研究中,“主题—方法”、“视域—对象”的综合分析,昭示着一种“间性”的透视和“写艺术”的意义关怀;前者借助“艺术田野”的方法对审美事实及其文化主题中夹杂着“情感性”和“经验性”的事项进行复合化解读,而后者则通过选择、编排和想象的“诗学阐释”对“观看的对象”进行文本化的“制作”和“提炼”,以实践一种艺术民族志的话语策略和权威模式,进而通达一种美学意义上的文化批判(critique of culture)。在此,“批判”并非“贬低”或“反感”,而是在澄清城市艺术文化事项的本体质性与结构功能的前提下,区分其事实、价值与意义的边界。当一种新的艺术文化实践开始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领域,“我们会更加清晰的看到文化和日常生活本身的微妙之处,矛盾之处和模糊之处。”[8](P.99)因此,关于城市艺术田野及其艺术民族志写作范式的思考,是立足于本土文化自觉之上的“反身性”追问,其目的不仅在于尝试对中国人类学理论范式作出时代性的回应,更是对当下城市文化空间的一种理解、阐释、建构和表达。其中也部分触及到人类学中关于“他者”话语的临界点:为了使“他者”显现为“他者”以及剖析使“他者”成为“他者”的内容;“田野”就须扭转并返回自身,以“反身性”的姿态去展示“对象性主体”的内在生成性和外在特征性,其背后所涵摄的则是作为“他者的自身”所营构的“反己性”人文关怀。
注释 :
多主体梯级水电参与日前市场下游电站自调度投标策略//张粒子,刘方,许通,蒋燕,李秀峰,徐宏//(19):27
①在此,用“生境”而不用“空间”的原因是:生境是生态、人文、社会、情感等要素所交互生成的流动性场域,它不范囿于一种空间的形制,更包含着一种审美的契机。参见:吴震东《“审美生境”:一个民族美学关键词的知识谱系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②参见: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ax Niemeyer Verlag,1976年,第143页。德文原文为:“Dasein ist Seiendes,dem es als In- der-Welt-sein um es selbst geht.”中文翻译为:“此在是这种存在者,对它而言,它作为‘在世存在’,只与自身相关。”彭富春认为“理解揭示了此在之此,借助于它使为之所故和立于其中的意蕴趋于明晰。”参见:彭富春《论海德格尔》,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页。
③相对于现实主义民族志作品中民族志者作为一个权威叙述者在叙述客观的事实,后现代则更强调一种多主体的对话与协商。参见:James Clifford.“On Ethnographic Authority ,” in the Predicament of Culture :Twenties -Century Ethnography ,Literature ,and Art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年。
语境:大可想与女友罗佳结婚,罗佳的妈妈不同意。对话中,大可极力说服罗佳妈妈,试图让她同意他们俩的婚事。
④罗兰·巴特认为,“可读文本”指的是“经典文本”(classic text),它的意义较为封闭固定,其特征是默认读者被动地接受文本中所预设的意义;而“可写文本”则是读者主动地参与到文本的意义建构之中,它是一种“永恒的当下”(perpetual present)其意义会不断增殖。参见:Roland Barthes.S /Z ,trans by Richard Miller.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2年,第3-5页。在此,若将民族志的“书写”和“接受”视为“文化”-“民族志者”-“民族志作品”-“读者”的阶段性过程,则此处的“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之间就有相互转换的可能。“文化”作为最原初的“文本”,被民族志者从“可读文本”转化为“可写文本”即“民族志作品”;而“民族志作品”又作为“可读文本”被读者转化为“可写文本”以进行再次的意义生产。
参考文献 :
[1]吴银铃.城市——从城邦研究到城市人类学[J].西北民族研究,2014(2).
[2][美]R·E·帕克,E·N·伯吉斯,R·D·麦肯齐.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城市研究文集[M].宋俊岭,吴建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George E.Marcus,Michael M.J.Fisc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
[4]周星,安丽哲,王永健.城市里的艺术田野——艺术人类学三人谈之二[J].民族艺术,2015(2).
[5]Raymond Williams.Resources of Hope :Culture ,Democracy ,Socialism [M].London: Verso,1989.
[6]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Discipline and Practice :The Field as Site ,Method ,and Location in Anthropology ”[A]//Anthropological Locations :Boundaries and Grounds of a Field Science [C].edited by 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Berkeley and Los Angeles,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7][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8]David Inglis.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M].London: Routledge,2005.
[9]Walter Benjamin.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 [M].trans by J.A.Underwood,London:Penguin Books,2008.
[10][苏]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宪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
[11]Nigel Rapport,Joanna Overing.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s [M].London: Routledge,2000.
[12][英]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M].张云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3]James Clifford ed.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C].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
[14]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M].Oxford: Charendon Press,1998.
[15]Robert Scholes,James Phelan,Robert Kellogg.The Nature of Narrative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
[16][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论述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M].方静文,黄剑波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17]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M].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18][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到[M].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9]Susan Langer.Philosophical Sketches [M].New York: Mentor,1964.
[20]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 :Technique ,Audiences ,Ethics ,Ideology [M].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6.
[21][美]伊万·布莱迪(编).人类学诗学[C].徐鲁亚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5—0037—09
基金项目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艺术学)一等资助项目“走向城市的艺术田野及其民族志方法论研究”(2018M630874)、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生境话语的审美人类学研究”(CSY19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震东,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文艺理论,文化研究。湖北 武汉 430074
收稿日期 2018-12-30
责任编辑 王启涛 刘立策
标签:城市文化论文; 反身性论文; 艺术田野论文; 艺术民族志论文; 文本叙事论文; 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论文; 武汉大学哲学博士后流动站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