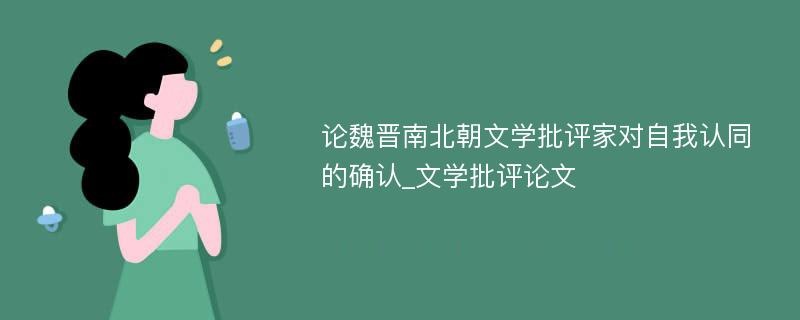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家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家论文,身份论文,自我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文学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批评家是怎样认识自己的呢?批评家是文学批评活动的主体,他凭什么认为自己就是批评家而有权评论批判别人的作品呢?也就是说,他对作为批评家的自我身份究竟是怎样认识的,他有没有身份的自觉,这对文学批评活动是否自觉,是否独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也可以这样说,批评家对自我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活动的认识越准确,批评家对自我身份所应担负的责任认识越清楚,批评家对自我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活动与其他文学活动——如文学创作与文学鉴赏——辨析得越明晰,其文学批评的自觉性与独立的程度也就越高。
一
许多作家往往也从事一些文学批评活动,魏晋南北朝批评家认为,如果以作家身份来进行文学批评,一定会产生某些弊病,曹丕把它称作“文人相轻”现象: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典论·论文》)
此中所说的“文人相轻”,有狭义与广义两方面的意味。从狭义来说,作家以自己所擅长的体裁的作品来比较他人所不擅长的体裁的作品,即“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从广义来说,作家认为自己在创作上各方面都优于他人,即“暗于自见,谓己为贤”。这里,曹丕所指出的人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所产生的谬误与偏差,一是从批评方法上来说的,一是从进行文学批评的人们的身份及其所具有的心理来说的。至于批评方法,只要把创作体裁分类,同类体裁之间进行比较就行了,问题似乎很简单,但是,由于作家所具有的身份及其“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心理所产生的问题则比较难于解决。对此,曹丕也说:
(建安)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骐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同上)
其实,这种“难”就难在这些人是以文学创作者的身份来从事文学批评的,他们在进行批评时经常处在一种既要评述他人的作品,又要评述自己的作品的境地,处于一种要将自己与同时代的作家进行比较的境地。对此,曹丕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意见:
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同上)
所谓“审己”,意义是比较含混的,但大体上不出仔细地查核自己的才力与慎重地审察自己的作品二义,曹丕希望以之来避免“暗于自见,谓己为贤”的偏差。当然,上述这些只是曹丕的理论表述,曹丕也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在批评同时代的作家作品时是如何处理这些作品与他自己作品的比较关系的呢?从《典论·论文》及曹丕的其他批评文字(如《与吴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曹丕极其潇洒地不评述自己的作品,不把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其他人作任何比较,当然,这样就无论如何不存在什么“谓己为贤”的问题了。曹丕让自己具有一种超脱的身份,超脱于作家之间相互争较高下之外,这种超脱就意味着自己要超脱作家的身份而以批评家的身份来进行文学批评,这就是在肯定批评家要有一种独立身份。自曹丕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批评家在进行文学批评时,一般都不将自己的创作列为批评对象的,亦即表示要超脱作家身份而以批评家身份来进行文学批评。
二
批评家的批评对象是作家及其作品,作为批评对象的作家是怎样看待批评家的呢?此中,曹植的意见是典型的,他在《与杨德祖书》中发表了这样的意见:
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为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曹植自视甚高,他“常好人讥弹其文”,他当然不会认为那些“讥弹其文”的人在整体上就比自己高明,但他承认那些“讥弹其文”的人在某一点比自己高明,所以他请求别人给自己的作品提意见,为的是使自己的作品在某一局部上提高质量。丁敬礼的话,同样是这个意思。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又说: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涉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呰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
曹植认为要有高出对方的才华才可以进行批评,显然,此处的“才”是特指创作才能。曹植对以评判者面目出现居高临下臧否作家的批评家流露出天生的敌意,认为他们不负责任,专以诋毁、贬抑作家为事。曹植当然十分不满意这些批评家的信口雌黄,所以他要以作家之所长来反诘这些人,要他们先具备了作家所具有的创作才能再来评判别人!
因此,无论是从局部上提高作品质量的企望还是从作家的心理自尊来说,作家都认为批评家具有相当水平的创作能力应该是第一位的。
三
但批评家自诩的却是自己的理论水平,而不是创作水平。比如作《文赋》的陆机,他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批评家,他在《文赋序》中介绍自己的撰著原则说: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其放言遣词,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尔。
《文赋》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陆机自称可以把这个“作文之利害所由”谈得“曲尽其妙”。此中,他只是说从自己的创作中更深地体会到“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的问题,而不是说在自己的创作中解决了“意不称物”和“文不逮意”的问题。他强调是从总结概括“先士之盛藻”来解决这些理论问题的。
又比如沈约,他的创作水平亦很高,但他论述理论问题时并不强调自己的创作成就,也不以自己的创作成就作为论证的依据,他只是以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自傲。其《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先对历代诗人运用声律作一总结:
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
他认为这些诗人都不曾自觉地运用声律,但其诗中“取高前式”的“音律调韵”,或是因为诗人在创作诗歌时以反复咏吟而达到的一种效果,并非是有意识的自觉行为,只是无意识凑成而已。沈约又曾讲述作为批评家的自己对声律进行详尽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
此中提出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理论原则,而提出这种理论原则是经过“敷衽论心,商榷前藻”等艰苦的理性思维活动才得到的。此后,沈约才提出“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这是讲批评家对理论的重视及对创制理论的自信心。从中我们看到,作为批评家的沈约有一种为世人创制理论的自觉意识,这是比总结创作经验更深刻的理论活动,这是有别于创作活动的理论思维,比如梁武帝不喜好作诗运用四声,便问周舍“何谓四声”,周舍回答说:“天子圣哲是也。”(《梁书·沈约传》)这里的“天子圣哲”就完全不含文学意味,而“天子圣哲”又是完全针对文学创作提出来的。正是这种为世人创制理论的自觉意味,成为批评家自觉区别于他人的标记。
四
上述陆机与沈约,他们虽不以创作自诩,但他们提出来的理论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创作又反过来指导创作,他们的理论与具体的、直接的文学创作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我们相信,他们卓绝的文学创作才能与其理论的提出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还有许多批评家,如作《文章流别集、志、论》的挚虞与作《抱朴子》(其外篇涉及许多文学问题)的葛洪,他们两人也都有卓越的创作才能,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晋书·挚虞传》),葛洪除《抱朴子》外,“其余所著碑诔诗赋百卷”(《晋书·葛洪传》)。他们的文学批评或许与具体的、直接的文学创作关系不大,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他们的卓越的文学创作才能对他们的理论论述起着支持作用。但是,南朝时又出现了一类文学批评家,他们除了文学批评著述外,文学创作很少,他们或者很少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而专门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或者在某一门类的创作水平并非很高,却专门从事这一门类的批评活动。
如刘绘(士章),钟嵘《诗品序》说他想作“当世诗品”: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
而这位“欲为当世诗品”者的五言诗创作水平却并不怎么样,《诗品》列其于下品,称:
(士章)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譬应变将略,非武侯所长,未足以贬卧龙。
专门品评五言诗的钟嵘,他就不是诗人,今不见他有诗存世。但钟嵘在评价其他批评家时,则也认为批评家的创作才能应有相当水平,如《诗品》卷中论曹丕说: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所计百所篇,率皆鄙直如俚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
他认为曹丕“铨衡群彦,对扬厥弟”之类的文学批评,其自信应该源于其自身的创作成就。
再说刘勰,《梁书·文学·刘勰传》载,他除了《文心雕龙》外,其“为文”在当日以“长于佛理”出名,“京师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请(刘)勰制文”。虽然刘勰当日有“文集行于世”,但不知是否作过诗赋等文学作品,今不见他有诗赋作品传世。
尽管钟嵘说过批评家批评别人时自己应有较高创作水平,但他并不以自己诗歌创作成就不显著而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有丝毫胆怯,刘勰更是如此。他们确认自己的批评家身份,对自己作为批评家的所作所为充满信心。如《南史·钟嵘传》载:
(钟)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道,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范,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此报约也。
假如此说可信的话,从中即可看出钟嵘对作为批评家所应具有的地位还是十分自信的,即认为批评家确实具有这样的权威。假如此说只是当时人们的一种传言的话,那也表明当时人们对钟嵘作为批评家所应具有的地位还是十分崇尚的,即认为批评家确是具有这样的能力。又如《梁书·文学·刘勰传》载:
(《文心雕龙》)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刘)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侯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刘勰“自重其文”,这也是“自重”其身份的表现,所以敢于拿给当日的文坛领袖人物沈约去看,终于得到社会承认。
而刘绘,则是以自己谈论评述诗作的杰出才能建立起自己的“欲为当世诗品”的自信的,《南齐书·刘绘传》载:
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刘)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时人为之语曰:“刘绘贴宅,别开一门。”言在二家之中也。
从中可以看出,他论诗“别开一门”,有自己的独特见解。
时代在呼唤具有独立意义的批评家出现。他们如果有着较高的创作水平,自然使他们有坚实的依据来进行批评,但要求他们超脱于创作而以地位独立的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如果他们对创作并不见得擅长,但他们具有文学批评的理性思维,要求社会给予他们批评的权利,而不是禁止他们进行文学批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就实现了自己的独立身份。
五
当批评家明确认识到自己的批评家身份,他也就明确地认识到,当自己面对作品时,不仅仅是个鉴赏者,不能以鉴赏来代替批评,因为批评自有批评的规律与要求。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提出某种对待作品的态度:
人各有好尚:兰苣荪蕙之芳,众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对作品的鉴赏,那么,这完全是无可非议的,鉴赏确实具有如此的个人性、直观性的特点,但以个人“好尚”来进行文学批评则不可。
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曾提出正确的文学批评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及要摒弃哪些不正确的态度:
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醖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楼,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
刘勰在这里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对待作品的态度。一是少数与大量的区分,有的人只阅读少数作品便进入批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这是刘勰所反对的;他主张“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即要大量阅读作品,这该是批评家所要进行的第一步工作。二是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有些人对待作品强调个人的爱好,于是,“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而正确的文学批评应该是客观的,即“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应该是“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三是情感参予与理性观照的区分,有的人直接把个人感情投射到自己的阅读的作品中去,于是或“击节”或“高蹈”或“跃心”或“惊听”,但对批评家来说,要对作品作全面的理性分析,如“六观”,要尽量避免陷入情感冲动之中,因为不超脱个人情感就不能对作品作出公允的评价。对鉴赏者来说:多读作品当然可以提高自己的鉴赏能力,但只读少数作品也可以进入鉴赏;其次,鉴赏作品“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另外,鉴赏作品时有情感参予,正是鉴赏的特点,也正是作者对读者的期望所在。就此我们可以说,刘勰在此强调的是批评家要确认自己的身份,不可以一个普通读者(鉴赏者)的身份来批评作品。
六
批评家们确认了自我身份,便会自觉地思考自己的社会责任,他们把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事业定位在较高层次上,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学批评或对国家社会人生或对创作或对批评自身都是有益的,是时代所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树立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有一类批评家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文学批评事业是“成一家之言”的一部分,这些批评家是把自己的文学批评论述归类于自己对整个社会、人生的看法的著作之中,即所谓“子书”。如曹丕的《论文》是其《典论》的一个部分,曹丕《与王朗书》曾这样评述其《典论》:
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
曹丕是把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这些论述当作可以使人“不朽”的事业来对待的。又比如葛洪,其所著《抱朴子》内外篇,内篇是神仙家言,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抱朴子·自叙》),其中有涉及文学问题的篇章,即《钧世》、《尚博》、《辞义》、《应嘲》、《文行》等篇。其中《尚博》中认为子书可以增进道德,有益教化:
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途殊辟而归于进德,虽离于举趾而合于进化。
从上述言论可知,把文学批评归类于子书的这些批评家们,是把文学批评视作其批判社会、指导人生的言论的一部分。
另一类批评家把自己的批评视作对创作的指导,或是对具体创作实践的指导,或者是对创作风气的指导。前者如陆机《文赋》,论述文士写作时的“用心”,即文学创作的全过程,其意当然是指导人们创作,又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提出声律问题,也是企望人们用此理论贯穿于实践之中。后者如钟嵘《诗品》,其品评历代五言诗的优劣,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纠正社会上“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的创作风气。
有一类批评家对社会上流行的批评风气不满,他们指出他人的批评的缺点错误所在,进而要以自己的批评树立批评的样板。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人相轻”、“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与“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两种错误的批评风气。又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出要纠正社会上“淆乱”的评诗,其称: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钟嵘深恶这种“王公晋绅之士”人人都想当批评家而“随其嗜欲,商榷不同”的风气,故作《诗品》以立准的。
当然,有些批评家是把几种社会责任都视为自身所应当肩负的,如刘勰即是这样的批评家。他在《文心雕龙·序志》中称:自己撰写文学批评著作,亦是“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表现,“岂好辩哉,不得已也”。他称自己是受到孔子召唤而撰写文学批评著作的。他又称自己是为了纠正“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创作局面而撰写文学批评著作。他又称自己是为了纠正“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诰,无益后生之虑”的诸种错误的批评而撰写文学批评著作的。
可以这么说,批评家们越是准确地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当然也就对自我身份有着更为准确的认识。
七
与批评家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同时,批评家对批评这一活动的职业自身责任问题也有了思考。曹植《与杨德祖书》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然此数子(指建安数子),犹复不能飞骞绝迹,一举千里也。以孔璋(陈琳)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曹植所说对某人某文的赞赏与否,尚称不得为纯粹的批评,但他所引证的钟子期对伯牙的正确赞赏一直被人们视为批评的典范;批评家切不可利用自己进行文学批评的便利就随意褒赞,这样会引起后人嗤笑的,即“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这种情况应引起批评家深深的警惕。但世上又确实有“妄叹者”,后世批评家对之有所抨击,如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载:
士衡(陆机)才优,而缀辞尤繁;士龙(陆云)思劣,而雅好清省。及云之论机,亟恨其多,而称清新相接,不以为病,盖崇友于耳。
陆机为文“缀辞尤繁”,其弟陆云也不讳言,而且,陆云论文又最赞赏“清省”,但照顾到兄弟关系,又利用自己进行文学批评的便利条件,便说其兄为文虽繁,但“清新相接”而“不以此为病”,且“人不厌其多也”(陆云《与兄平原书》)。这种利用职业之便的“妄叹”自然被后世所嗤笑,这种对职业自身没有责任心的作法,被后世批评家引以为戒。
作为一个批评家,是否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自傲自恃,高居于一切创作者之上?是否就有权利骂倒一切?这种作风,首先引起作家的不满,如前引刘季绪“好诋诃文章,椅摭利病”,作为作家的曹植就反诘他没有作家的创作才能就别开口讲话,还期望有人来驳斥他,巴不得使之“终身杜口”。后世批评家又把“历诋群才”、“竞于诋诃”列为批评的忌戒,这也是讲求批评的职业自身责任的表现。刘勰《文心雕龙·程器》称:
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
韦诞“历诋群才”,见《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
仲将《韦诞》云:“仲宣(王粲)伤于肥戆,休伯(繁钦)都无格检,元瑜(阮瑀)病于体弱,孔璋(陈琳)实自粗疏,文蔚(路粹)性颇忿鸷。”
他对后人所注目的作家一一诋诃,无一句好话。刘勰对这种号称批评却利用职业之便骂倒一切的做法十分不满,特标出以示忌戒。《文心雕龙·奏启》又称:
是以世人为文,竞于诋诃,吹毛取瑕,次骨为戾,复以善骂,多失折衷。若能辟礼门以悬规,标义路以植矩,然后逾垣者折肱,捷径者灭趾,何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哉!
这里本指“奏”中的情况,但从中也可看出作为批评家的刘勰对有人利用批评这一职业便利而“历诋群才”的不满。刘勰提出,解决的方法是树立规矩与标准,而不必“躁言丑句,诟病为切”,这或许更适合于文学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的作家偏颇地认为,批评家应该比作家更有创作水平,否则免开尊口。而批评家则开始认识到,有创作才能的作家只有超脱自己的作家身份才能正确地进行批评,批评家们以自己的理论水平自诩,他们或者就是偏具批评才能的人。批评家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批评家的独立身份,于是,他就要求自己不是以一个读者身份鉴赏式地对待作品,而是要有理性、自觉地进入批评状态;同时,批评家认识到自己有着批评家独特的社会责任与职业责任。上述一切都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家成熟了。
标签:文学批评论文; 典论·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诗品论文; 抱朴子论文; 典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