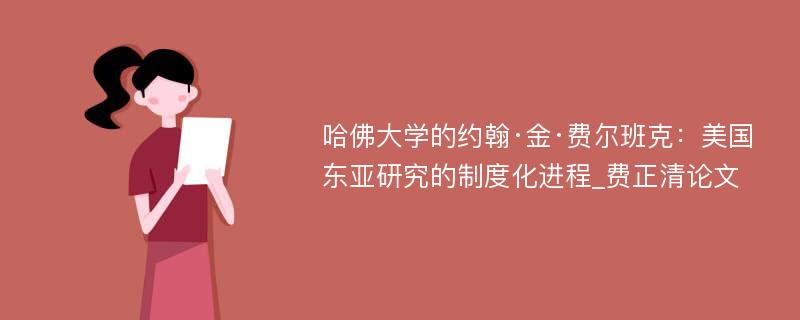
费正清在哈佛: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哈佛论文,进程论文,在美国论文,机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3-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1)04-0117-05
费正清的东亚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作为现代东亚学的开拓者,费正清完成了从古典汉学向以地区研究为标志的现代东亚学的过渡。1929年秋,费正清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到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伦敦期间,结识了查尔斯·韦氏(Charles Webster)。在韦氏影响下,费正清选择中国海关外籍税务司制度作为研究课题。1932年,费正清来华,一面进修汉语,一面在清华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国牛津,获得博士学位,学位论文题为《中国海关的起源》。这篇论文曾以《中国海关的贸易与外交(1842-1854)》为题,于1935年出版。1936年费正清获博士学位后,即返回哈佛大学任教。从1939年起,他与赖肖尔(Edwin Reischauer)在哈佛大学开设东亚文明课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四个月,他应征召到情报协调局工作,中间两次来华任职。1946年8月,返回哈佛,担任区域研究(中国)项目主任,取得哈佛大学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成立哈佛东亚研究中心。
费正清建立了近现代东亚研究的基本框架和模式。虽然他把近现代中国作为东亚学的主体,但这种研究在目的、内容和手段上都与传统汉学有着根本区别。费正清不仅博学,而且也长于学术组织。首先,费正清以哈佛为基地,在美国高等院校中创建了多所学术研究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东亚问题学者。经历了麦卡锡主义的肆虐之后,中国问题研究异常艰难。他认为:“对付麦卡锡主义的办法只能是办教育。”[1]有赖于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东亚学在美国的机构化进程开始有了长足进展,一些私立大学着手筹划远东研究。费正清于1954年开始筹建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到1955年,首先建立了为期两年的“区域研究——东亚”硕士班,每年约培养14名研究生。1956年,招收了26名攻读历史和东亚语言联合博士学位的研究生。50年代后期,研究中心开始有计划地出版书籍。到60年代,这项工作全面展开并进入高潮。哈佛从此进入硕果累累的全盛时期,短短几年便超过了斯坦福、伯克利等其他学校。
除了作为哈佛东亚研究中心主任之外,费正清还担任了许多学术组织的领导工作。1959年,他担任“亚洲问题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主席,1968年,出任“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在实践中,费正清慎重处理政府、教育研究机构和基金会三者之间的关系。费正清后来在区域研究中取得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据统计,从1958年到1970年间,由私人基金会和政府有关部门所提供的基金达4000多万美元。其次,费正清不仅开创了美国的现代东亚学,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把东亚问题研究看作“一项世界性的事业”[2]。
费正清在中美关系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作为学者和思想家,费正清的研究触及现代中国的各个方面。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涉猎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历史人物。自1929年以来,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均成了他整个学术生涯的焦点。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作为历史学家,他致力于19世纪中叶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传统中国社会的特征及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变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作为资深望重的历史教员,费正清在哈佛教授了数以千计的本科学生,在他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学者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任教的达100多人。其次,费正清极力推广东亚研究,其中包括现代中国史研究,哈佛几乎可称之为他的学术研究基地。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为他的终生信仰。最后,费正清还为推进中美关系的进程做出了不懈努力。他认为,为了美国的未来和世界的发展,美国人必须重新认识中国,重新审视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费正清的持久影响与他漫长的学术生涯和当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当1929年费正清在牛津大学开始他的汉学研究时,哈佛大学只开设一门东亚研究课程。费正清半个世纪之久的学术生涯伴随着美国在亚洲扩张的历史。他对中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精辟见解,影响了美国公众和政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举措。在中美关系史上,美国对华政策也出现了几次重大调整,中美关系也因此经历了几次重大转折。在变动不定的形势下,许多学者昙花一现,而费正清则能够始终主宰史学主流。正如许多评论家所指出,费正清是最严谨、最执著的思想家。
有关费正清本人的学术争议历来众说纷纭,我们对费正清的认识也离不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如费正清与其以前的学术传统的关系、费正清思想的发展轨迹、中美关系的曲折过程以及他在亚洲、美国的实际经历对他的学术思想的影响,等等。费正清是一位理性学者,他坚持认为文化价值体系决定人的信仰和行为准则,坚持知识的价值在于指导行动这一原则。他在1977年退休后的一次接受采访中说:“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应当以能够指导实践为最终目的。研究者并不一定要有伟大的思想,但他必须勇于实践,将理论付诸行动。”[3]费正清的学术生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了大部分西方中国观察者的共同经历,他的现代中国理论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相对主义(1923-1944);反对中国文化价值观,提倡激进社会变革(1944-1951);困惑与沉默(1951-1960);接受与理解(1960-)。
费正清之所以选择东亚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这一领域是理解现代社会的必修课”[4]。东亚是一片神秘诱人的处女地。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1932年费正清来华时已经树立了人生目标,那么他在1936年离开时已有了总体构思,致力于东亚研究。他首先以19世纪中叶为现代中国的始发点。他认为,美国人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尤其是现代中国,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1935年,哈佛大学同意了他的申请,聘任他为历史系政治经济学教员。
费正清在哈佛的研究工作是开拓性的。当时哈佛的历史系相当封闭、守旧,“狭隘、西方化”。费正清几乎是从零开始,把现代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学科在课程中确立下来。1904年,古利志(Achibald Cary Cool-idge)开设了第一门课《1842年以来的远东历史》。斯坦利·K·亨贝克(Stanley K.Hornbeck)曾于1924年至1926年执教哈佛,后来在美国国会工作,他把这门课加以扩展,涵盖了从1793年麦卡内计划到1842年《南京条约》这段历史。1936年费正清执教哈佛,代表了与古利志、亨贝克、艾利斯弗等一代学者完全不同的学术风格。古利志等人强调语文学和古代汉语,而费正清的学术背景主要是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费正清执教的第一个学期可以说是惨淡经营,只有西尔·怀特一个学生。汉学系学生首先要掌握两种欧洲语言然后才能学习古代汉语,确立研究题目。美国学者联谊会执行秘书长麦地梅尔·格利弗于1937年指出:“现行的教育体制妨碍了英语东方学在美国的发展。依我之见,对中国、日本、印度、苏联和阿拉伯世界的研究足以确立一套美国化的研究方法。尽管十九世纪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我们已不能继续沿用十九世纪的汉学方法,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活生生的文明社会而不是僵死的木乃伊。我们不能光凭几本干巴巴的书本,闭门造车。我们需要参与,要知道东方人在干什么并设法帮助他们。”[5]
费正清与哈佛燕京学院以及远东语言系的汉学家的分歧是不言自明的。费正清没有拿到1933年哈佛—燕京奖学金自然心中不快,但费正清更为关心的是学术问题。尽管他与艾利斯弗观点和性格上存在很大不同,但两人合作得仍很愉快,共同开发了许多科研项目,其中之一是艾利斯弗发起创建的历史系与远东语言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研究生。该项目始创于1940年,二战后期开始招生,历时15年,吸引了大批大学、学者。作为学术带头人和学者,费正清并未完全摒弃传统汉学的研究方法,而是力求创新,以“美国式”的方法予以补充。1937年春季,费正清开设《1793年以来的远东历史》课。在后来的几年里,该课不断更新,人数由24人增加到53人,与赖肖尔的《汉语》课一道构成哈佛大学本科东亚学课程的基础。费正清在1938年指出,远东史课程应当全面深入、宏观地介绍东亚文明史。而当时哈佛19世纪和20世纪东亚外交史课程显然不能适应现行的任课要求。为此,哈佛历史课经历了数次调整,包括政治、历史、文学和艺术。费正清的东亚史讲义成为战后系列教材。
除了教学,费正清还承担培养东亚学学生和教师群体的艰巨任务。这样,从机构、教学、课程设置和社会舆论各方面都为二战后美国东亚研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战前东亚研究还是个很不起眼的领域,不仅缺乏美国的学术传统,而且也没有支持该领域学术研究的中介机构。全美国的东亚史学者总共不到50人,开设研究生课程的学校屈指可数,开设本科生课程的就更少,开设这类课程的学校之间更很少沟通合作。于1842年成立的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也不健全,主要从事圣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古代文明的研究,研究方法局限于语文学。非职业性团体如“太平洋关系学院”(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和“对外政策协会”(Foreign Policy Association)在一定程度上对东亚学者有所支持,但总显得势单力薄。由于美国大学教育忽略东亚,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心目中根本没有东亚。费正清所在的历史系及哈佛大学的状况基本体现了美国学术界的欧洲中心论倾向。除了克服机构设置上的障碍和学术兴趣冷漠外,费正清认为,真正的远东研究需要建立相应的课程,讲授东亚历史、语言、艺术和哲学[6]。
20年代末,“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美国学者联谊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开始了一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远东研究的计划。首先,他们资助一些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培养新一代的亚洲问题学者。另外,由格雷弗斯(Graves)发起、“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远东学教授聘任制也在三所美国大学实行。
1937年3月,费正清写信给格雷弗斯,支持他的计划,联合远东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专家学者,费正清把美国《远东研究通讯》改为《远东季刊》。1934年以来,美国学者联谊会(ACLC)也组织了多次会议,把分散的远东问题专家集中在一起。费正清本人参加了1937年和1939年的会议,主持了1940年8月在哈佛举办的会议,并和德克·彼得(Derk Bodde)主讲中国文明史,爱德文·赖肖尔和波顿·法斯(Burton Fahs)主讲日本史,亚瑟·文利(Arthur Wenley)主讲日本和中国艺术。虽然学生不如预期那样多,但也相当成功。
1940年8月的学术研讨会相当成功,与会的有“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大卫·史蒂文斯(David Stevens)、格雷弗斯以及15名青年学者。这次会议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对推动远东问题专家学者的合作,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41年夏,厄尔·普里查德(Earl Pritc-hard)和塞莱斯·比克(Cyrus Peake)随后又召开了相关专题讨论会,此会的论文便形成第一期《东亚季刊》,于1941年11月问世,费正清任编辑并撰文。二战以后,“远东协会”(Far Eastern Association,后更名为“亚洲研究协会”AAS)成立。
1941年的会议以后,费正清声名雀起,成为东亚学中的核心人物。1940年后,费正清重新开始1936年访问北京回国后中断了的大学调研项目。这次,他代表美国学者联谊会,对美国现在已开设或准备开设东亚课程的大学进行访问。为此,他还特意上访华盛顿美国教育部,提出在美国中、小学开设亚洲文化课程的设想。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费正清的一系列卓有成效、力度非凡的学术举措可谓高瞻远瞩。1941年6月,太平洋战争尚未开始,费正清就已经对东亚地区日益加剧的危机做出预测:“美国面临在亚洲的抉择。美国人民对亚洲尚一无所知,但无论如何,美国需要制定一套对日本和中国的积极的、行之有效的对外政策。民主的理念应当建立在对人民的充分理解基础之上。愚昧无知以及在亚洲政策上的失败势必导致民主的失败。时下加强远东教育迫在眉睫,减少招生量,冻结大学教育经费则无异于釜底抽薪。这是该领域的学者们必须面对的巨大危机与挑战。”[7]
费正清一方面向学界同仁呼吁加强美国教育和学术界对世界的承诺,同时要求教育机构加大向美国公众的传播力度。费正清指出,美国对东亚的研究具有战略意义,因为远东直接关系到美国和全球的稳定与安全。东亚研究是美国制定该地区政策的基础。[8]费正清的呼吁在美国政界和学术界得到响应。时值美国卷入二战前夕,这一呼声更具紧迫感。在后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费正清不遗余力,劝诫美国政府和人民关注东亚,认识东亚。1940年,费正清指出,如果把东亚列入美国学校课程将有助于美国民众认清美国在东亚的利益。1950年,他又进一步指出,美国对共产党中国大陆的正确反应取决于对当代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费正清呼吁美国政界、学术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个东亚地区,以便加速中美关系正常化和美国从越南撤军。1980年,他又强调东亚研究对改善美中贸易、文化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东亚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9]费正清还在哈佛发表了一系列以美中关系及美国对华政策为题的演讲,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
费正清在哈佛的一系列举措奠定了东亚学的学术地位,使后者成为有影响的学科,加速了东亚学在哈佛乃至在美国大学的机构化进程,哈佛也因此成为美国东亚研究中心。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内,费正清始终奉行历史服务于现实的主张,为增进中美两国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修复两国间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冲突所造成的巨大鸿沟做出不懈的努力。他始终抱有这样一个信念和希望,即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两个文明应该也能够和睦相处。
〔收稿日期〕2001-03-30
标签:费正清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哈佛大学论文; 美国史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远东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