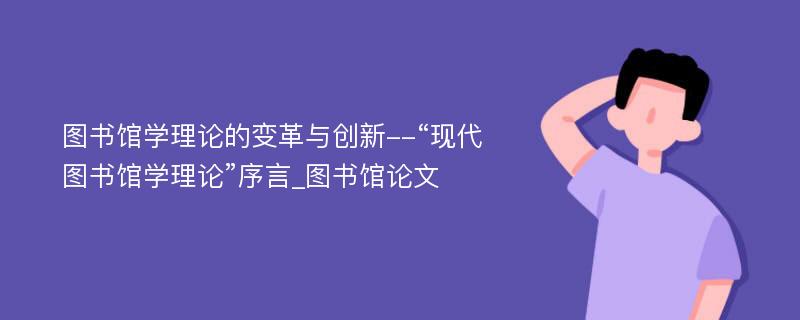
图书馆学理论的变迁与创新——序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序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我收到徐引、霍国庆著的《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书稿时,心中特别高兴,因为已有多年没有见到这样比较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新著了。这是作者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际送给中国图书馆界同行的一份厚礼。
由于我长期从事图书馆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图书馆学理论自然比较感兴趣,一般我只要见到有关图书馆学理论的新著,必定拜读之。《现代图书馆学理论》虽然篇幅宏大,但我仍集中一段时间通读了一遍。通读以后,受益非浅,有所启迪。
图书馆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永恒的现象,不管某些人喜欢不喜欢,它将永远存在下去。几千年来,尽管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思想意识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图书馆这种社会现象一直在延伸,一直存在,一直在发展。虽然图书馆这一现象的名词、内涵和外形有所变化,但它的基本结构、目的没有变化。今日社会进入信息化社会、网络化时代和知识经济年代,图书馆并没有消亡和衰退的迹象。事实证明,图书馆存不存在,不是凭个人愿望,也不是某些人写两篇文章说图书馆消亡就会消亡,而取决于社会的需要。正如本书所说“图书馆是与人类信息需求共存亡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就是人类信息需求体系的物化形式,哪里存在整体化的信息需求,哪里就会出现图书馆。”
话又说回来,图书馆这种人类社会的现象,几千年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但这并不说明这图书馆仍是原汁原味的,没有变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图书馆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外部形象变得更美。从它诞生之日起,或从16世纪以来,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图书与人相结合的传统图书馆时代;二是文献信息与人、计算机相结合的图书馆自动化时代;三是信息资源与人、计算机、信息网络相结合的图书馆网络化时代。今日它已跨入网络化时代。影响图书馆发展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技术的因素,但有一点是基本的,技术方法和手段是推动图书馆前进的动力,造纸术、印刷术、缩微技术、视听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数字化技术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图书馆的发展,使图书馆发生了质的变化。
20世纪即将结束,迈入21世纪的图书馆将是传统图书馆与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共存互补的时代。实际上,21世纪仍是以传统图书馆为主体,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在本质上没有区别,是一种事物的几种叫法,归根结蒂是一种现象。本书第八章说得好:“就实质内容而言,网络图书馆、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与虚拟图书馆没有什么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观察和认识的角度不同而已。”我很赞同这种观点。从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的构成来看,它们都离不开数字化信息、计算机、信息网络、操作人员、用户利用等要素;从技术方法来看,都需要数字化技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从运行过程来看,都需要信息输入、处理、存储、输出、传递的过程。离开了这些条件、环节、程序,都不可能存在。为此,我对本书“网络时代的图书馆”一章比较感兴趣,写得比较实在,实事求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很有启迪性。
图书馆学理论是为图书馆实践服务的。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反映实践、指导实践,两者既相互依托又相互促进。图书馆不存在,图书馆学理论自然也不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图书馆,也就无所谓图书馆学可论。如果不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那必定是一种游离图书馆,或与图书馆无关无用的理论。不解释图书馆,不说明图书馆的各种现象,不探索图书馆的发展规律,不指明图书馆的发展前途,不研究图书馆的具体操作与运行,不规范图书馆的运行程序,其理论怎样“新”,其名词术语怎样“时髦”,这种理论都是图书馆不需要的理论,不受实践欢迎的理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的两位作者,坚持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研究图书馆所处的环境与对策,探索信息化社会图书馆的特点、规律和基本问题,方向是正确的,值得称赞。
从图书馆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应该说图书馆学的理论发展,远远落后于图书馆实践。人类有了几千年的图书馆史,而真正的图书馆学史不到200年。这充分说明几千年来人们对图书馆学理论的忽视。图书馆学发展缓慢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图书馆界的认识问题。
19世纪以来,世界图书馆界一批先驱与有识之士,冲破阻力,不顾个人得失与名利,献身于图书馆学研究,从而使图书馆长期实践积累的经验与知识,得以上升为理论,逐渐成为一门为社会所承认的学科,从而走上人类伟大的科学殿堂,在人类科学殿堂中获得自己的位置,在高等教育机构中有了培养图书馆专门人才的专业。我们要感谢近200年来为此作出突出贡献的图书馆学先辈,他们是德国的施莱廷格、艾伯特,英国的帕尼兹、爱德华兹,美国的杜威、巴特勒、谢拉,俄国的鲁巴金,前苏联的列宁、丘巴梁,印度的阮冈纳费以及中国的一些研究者。
图书馆学从开创到逐步成熟,经历了图书馆学的萌芽时期、奠基与确立时期、发展时期。19世纪至20世纪的200年,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既有与世界图书馆学研究同步整合的时期,也有不一致不同步的时期。19世纪,由于中国社会封闭、落后,列强不断侵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基本无所作为。20世纪初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图书馆界产生了一批热爱图书馆事业的理论研究者,如杨昭晰、杜定友、刘国钧等。他们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基本上与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同步的,一点也不亚于西方同时期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本书第一章对此作了如下论述:“我国一些研究人员常常忽视了本国图书馆学家在世界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其实,无论就认识深度还是认识时间,杜定友等都不逊色于同代其它各国的图书馆学家。”笔者在不久前完成的“20世纪100年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进展及其评价”一文中,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认为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不管从认识的深度与广度,从内容到观点,从所提出的问题,从对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论述,基本与世界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同步的。
20世纪的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一是前面提到的20-30年代,二是80年代。80年代产生了一大批理论著作,数量之多,是历史上罕见的。9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所降温,发展缓慢。本书的出版,为9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成果增加了份量,添加了光彩,我相信对21世纪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近些年来,我们常听到一些人批评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脱离实际,我想这些意见不是全无道理,而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一下。时至今日,仍有许多理论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虽然已有一些人发表了这样或那样的意见,但大多数问题没有获得人们的共识。例如图书馆学的定位,定在什么地方是科学的,合乎逻辑的?图书馆学的上位类学科是什么?它应归到谁的门下才是科学的?图书馆学的结构、内容是什么?信息、信息资源、信息资源管理与图书馆的关系是什么?是所属关系,还是相等关系?是同一事物的几种说法,还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文献信息与文献信息管理是什么关系,有无区别?……总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任重而道远。
为了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必须:第一,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学术研究、理论问题,不能采用行政方法,更不是几个人开个会,炒作几篇文章,发个什么文件就可定论的,而要时间检验,要同行业大多数人接受,达成共识;第二,坚持与世界接轨。任何图书馆学理论,只有与世界接轨,在更大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具有通用性、适应性,才会有较强的生命力,才能体现理论的真正价值。要与世界接轨,就必须了解、学习、研究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当然了解、学习、研究外国的图书馆学理论,要尽可能搞清它的来龙去脉,做到全面、准确、实事求是,不要断章取义,张冠李戴,更不要捡芝麻,丢西瓜。本书在学习、研究、介绍外国图书馆学理论方面,其全面性、系统性、准确性、选择性都具有它的特色。
以上是我通读本书的一些感受与联想。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现代图书馆学理论》一书,由于作者坚持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因此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是一本值得充分肯定的图书馆学理论新著。全书视野广阔,思路清晰,有一定的时代特点和个人见解,具有一定新意。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1)本书对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作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在80年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发展。
(2)全书内容丰富,资料充实,特别是外文资料收集比较丰富,有些资料国内是第一次出现。由于作者掌握的资料比较丰富,知识面较广,视野广阔,从而全书论证比较有力,分析比较深透,说服力较强。
(3)概念明确、清晰,全书对主要概念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解释比较确切。
(4)本书作为一本专著,对当代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有选择性地进行论述是可取的,成功的。这样使全书重点突出,观点鲜明,论述深透,具有特色。由于本书不是面面俱到,重复别人过去的观点,所以给人以新意之感。
(5)我国80年代开始对图书馆学思想史作比较系统的研究,本书在原有基础上又深入了一步。作者对17世纪法国诺德以来的300多年图书馆学思想史,再次进行了梳理,补充了一些新的人物与资料,使其更加系统、全面,特别是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史划分为六个流派,具有新意。把20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图书馆界的理论研究成果和代表人物与祖国大陆整合在一起,使当代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显得更系统、完整、客观。本书一改厚古薄今的做法,在广泛的范围内对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评论,使全书的现实性和时代感更强。
(6)体系结构有所创新。从全书来看,“人类需求的图书馆”、“信息市场中的图书馆”、“网络时代的图书馆”等章节具有较浓的时代气息,紧扣时代脉络,反映了当代图书馆的新发展。“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学科体系”、“图书馆学流派与学说评论:西方”、“图书馆学流派与学说评论:东方”、“图书馆透析”、“图书馆类型的理论重组”等五章,在80年代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其结构、内容、观点均有新的发展,不少内容具有创新意义,如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及其认识的四个阶段,图书馆学的裂变、聚变、嬗变,西方图书馆学的技术、管理、社会学、交流、新技术、信息管理等六个流派的划分,图书馆结构与功能分析,图书馆类型的理论重组等。
(7)对未来图书馆的研究,属于预测科学,有关结论有待于实践去验证。由于本书是从总结20世纪图书馆实践入手,许多新的苗头已经显露,因此预测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对于一切事物要一分为二,本书优点很多,但仍有不足之处。如个别定义解释,似乎还不够准确;个别问题的论述前后有些矛盾;某些总题的结论缺乏说明力;国内资料的选择与国外资料比较,相对少了一些;对人物的选择与评价似乎缺乏一个统一标准。我所说的这些不足,不一定准确,也不影响全书的完美,只是个人看法,仅供作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