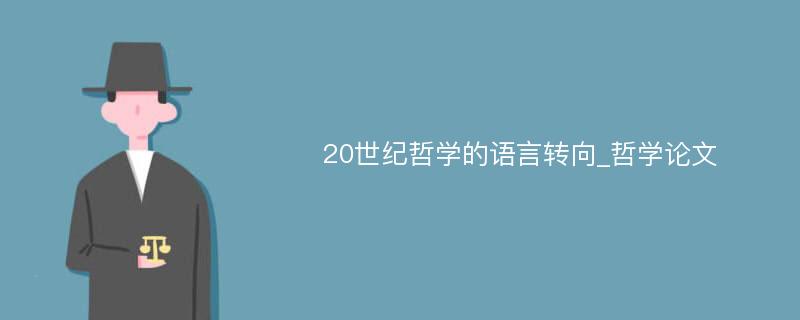
二十世纪哲学中的语言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世纪论文,哲学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世纪的思想特征或学术潮流既可能显得轻率与偏颇,又可能显示一种洞见。美国《导师哲学家丛刊》一套书中,称中世纪为信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期为冒险的时代,十七世纪为理性的时代,十八世纪为启蒙的时代,十九世纪为思想体系的时代,不由得不叫人叹服,这些标签表明了编者的俯瞰能力,在不同世纪和思想中穿梭往还、游刃有余,三言两语就把握了时代思想的脉动。
那么,我们期待编者如何称呼二十世纪呢?他们把本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初看起来,这个称呼和前面几个相比有些相形失色,但如果我们知道“分析”在这里指语言分析,就会感到意味深长了。用当代西方学术界中普遍流行的说法来表达就是:在本世纪,哲学中发生了语言的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个转向使语言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使本世纪哲学与过去的哲学,使现代哲学与古典哲学有了鲜明的区别。在语言转向之后,哲学的主题、内容、方法、风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之大,会使仅仅深谙古典哲学的人在阅读当代哲学文献时感到不知所云,确实,从柏拉图到黑格尔,什么时候看见哲学家翻来覆去地大谈“涵义”、“指称”、“能指”、“所指”呢?
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好像是地壳深处的震动,它的波动辐射到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尤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中,对语言的意义和结构的分析已经成了不少新派人物的看家本领。在此风潮之下,“话语”(discourse)成了学术研究和文化讨论中的关键词,“话语系统”成了指陈任何思想文化对象,诸如政治原则、意识形态、民族神话、叙事的结构与风格的最方便也最宽泛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一批中青年学术新人就理解和把握本世纪的“语言转向”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达成共识,认为掌握此点是全面、深入理解二十世纪西方思想具有纲举目张价值的大事。严肃、漫长的学术探索由此开始,到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时,曾议过要将“语言转向”的话题推向思想学术活动的前台,以期在“新三论”、“老三论”风靡一时的情况下,指明当代人文学术思潮另一不可或缺的维度,惜乎当时百废待兴,该急办的事接踵而至,直到九十年代前半期,关于语言转向的学术著作才正式推出。当然,在八十年代末,出了好几部关于西方语言哲学的著作,使广大学人在知识准备上有了相当基础。我们现在谈论语言转向,已经完全不带好新骛奇的心理,而是以平常的、成熟的学术心去探究西方这一思想转折的内在机理了。
《“哥白尼式”的革命——哲学中的语言转向》和《语言与哲学——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两书便是旨在帮助中国学术界、读书界从宏观上把握当代西方哲学潮流,从微观上深入探讨本世纪哲学问题的著作。两书的论述题材和论证方式初看起来大相径庭,但对语言的关注,对语言与哲学之间关系的梳理剖析,却像一根红线贯穿了两书的中心思想。第二本书的论域相对于第一本书是大大扩充了,但两书在两年之间相继出版表明了作者的一个明确信息:只有穿越语言之门才能对当代西方哲学登堂入室。
《“哥白尼式”的革命》论述的是发生在英美哲学界中的语言转向。相对于欧洲大陆各派哲学,英美哲学对于语言的转向似乎有更自觉的自我意识和更明确的阐释。这种自觉性和明晰性集中地表现为,对于语言转向的原因和内在机理,人们取得了基本一致的看法,这种看法可以无争议地载于各种教科书,以致于作者把这种公认的解释称之为“经典表述”。
根据这种表述,语言的转向是西方哲学发展中的第二次根本性变革。我们可以宏观地把西方哲学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古希腊和中世纪时期是第一阶段,这时,本体论问题,即“存在”问题占据哲学思考的中心地位,哲学家的观点学说各异,但他们都在询问这样的问题:“最根本的存在是什么?”“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世界是由哪些终极成分构成的?”以笛卡尔哲学的出现为标志,哲学进入了第二阶段,即认识论阶段,这时最基本的问题不是“存在着什么?”而是“我是如何知道的?”哲学家集中研究的问题是:人们认识的来源是什么,认识的能力有多大,认识有无限度,如果有,界限在何处?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显然代表了哲学思维的某种深化,因为从逻辑上说,回答“有什么”的问题以“人何以知道”为转移,虽然从历史或发生说的角度上说是先有世界再有对世界的认识。哲学的奥妙,哲学思维的秘诀就在于,一切都从人出发。所以古希腊的智者留下了这样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是事物存在或不存在的尺度。其实日常生活也提示我们,事物发生的顺序和对事物作断定的顺序是可以不一致的,先有罪行,再有对罪案的侦讯与判决,但断定有罪还是无罪依赖于证据,即对事件的认识。这第一次转向可以称为认识论的转向。
哲学的第二次转向即是研究的中心课题从人的认识、主客体关系转至语言。为什么?因为照前面的思路,表述、交流比认识更为基本。就像超出人的认识的存在物其实不存在一样,超出表达的认识,不能借助语言交流而使人理解的思想,也不能叫认识或思想。既然认识或思想要靠语言才能传达,那么在研究的顺序上(而不是在发生的历史顺序上),语言优先于认识。正如认识要为存在设界一样,语言也要为思想设界。
在认识阶段,主体处于哲学思考的核心地位,而现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即主体之间的可交流性)处于哲学思考的核心地位,研究的课题从思想、观念转移到了语句及其意义。明乎此,便可懂得当代哲学为何显得被语言学的概念和术语所充斥。
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被一些人欢呼为是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什么?当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时,哲学的课题和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但研究哲学的方式没有变,哲学的合法性没有受到挑战。语言的转向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和传统哲学相比,当代哲学已经面目全非(比如极其专门化、技术化、琐细化),更有甚者,在许多大师的眼里,哲学本身的合法性被置疑和否定。在哲学的传统方式的争论中,某个问题可以有互不相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回答,但问题本身始终存在。而在语言空间展开的争论中,问题往往不是遭遇到不同的答案,而是被拒斥、被消解,人们不去争论哪一种答案才是正确的,而是干脆宣布,问题就其性质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是注定得不到答案的,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抛弃它。罗素曾宣称,对许多哲学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澄清之后可以发现,它们本来并不是哲学问题,而是语言或逻辑问题。维特根斯坦说得更干脆:哲学是一种语言病。他在前期认为,哲学中之所以产生那么多虚假的问题,是因为人们误解了语言的逻辑,即语言的本质;他在后期则主张,语言的日常用法是唯一合理的用法,一旦人们“哲学地”使用语言,问题就出来了。哲学家唯一正当的任务是告诉人们不要搞哲学,并指点那些患语言病的人如何走出语言的迷宫。
尽管作者抱着同情理解的态度介绍和阐发语言转向中的各种观点,但仍然坚决和鲜明地反对“应该取消哲学”或“哲学即将消失”的观点。作者提出了两种自信相当有力的理由,第一,尽管维特根斯坦极其雄辩和极有魅力地证明了哲学的消亡,但半个世纪过去了,哲学事实上毫无消亡的迹象,它依然繁荣昌盛如故(中国近几年哲学陷入窘境是出于极为鄙俗的形而下的原因,没有资格拿上桌面来讨论);第二,哲学绝不会消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产生于人类独有的自我反思的本性,任何东西都可以当作对象来思考,包括哲学应否消亡的问题,一旦思考、争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式的思维。人们在捍卫哲学的合法性时,既可以作出深刻的回答,也可以作出机智的回答:它基于语言分析的技巧训练,在这个问题的辩论中,正方(捍卫哲学)处于与“语言悖论”正相反的有利地位。他可以这么说:你说哲学要消灭,我说不会,让我们来争论吧!由于这种争论既不是科学问题的争论,又不是对经验事实的争论,因此它是哲学争论。既然哲学争论是正当的、不可避免的,哲学研究的合法性就不证自明了。
作者在书中还表明了自己的这样一种观点:所谓“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的方法,既有明显的优点,又不可一味滥用。这既是对当今语言转向之后一种研究哲学的常用方式的评价和表态,又是对国内学界某种令人忧虑的做法的提醒。所谓语义上行,就是把问题提升到语言层面加以讨论和解决,它可以避免许多本体论和道德评价的难题。比如,关于“数”是什么,它是实体还是虚构的工具,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和数学家就争论不休,但是,人们其实可以对数的本体论地位存而不论,顺畅地研讨包含“数”的语句和文本。在我们学界,对于语言转向似乎有两种正相反的态度,一种是不太明白,进入不了语言维度进行思考,时时抱怨为什么要把问题扯到语言空间去解决,一种是自以为掌握了一种无坚不摧的“话语武器”,对不在语言层面上探讨问题表示鄙夷不屑,对任何问题都施以语言学或语言哲学的词语轰炸,管他问题解决没有都得胜回营。作者深感,只有对语言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有深刻认识,才算是对语言的转向有真正的理解。
当然,关注语言,透过语言来进行哲学探索,并不仅仅是二十世纪英美哲学的特征。在本世纪欧洲大陆各派哲学家那里,语言与哲学也有一种形至影随的关系。早在世纪之交,以叛逆精神著称的尼采就提出,“哲学家受制于语言之网”。他甚至假设,哲学思想和世界观的类似关系与语言的亲缘关系是相对应的。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句话现在已经成了脍炙人口的名言。法国著名哲学家利科说:“当今各种哲学研究都涉及一个共同的研究领域,这个研究领域就是语言。”他还说:“今天,我们都在寻求一种包罗万象的语言哲学,来说明人类的表示行为的众多功能以及这些功能之间的关系。”而当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它在本世纪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正是因为当代欧陆思想大师在阐发自己哲理时对于语言分析的态度,以及中国学界对此的兴趣和关注,才使得完成和出版《语言与哲学》一书显得必要和及时。
此书并非简单地论说语言转向的范围从英语国家扩展到欧陆各国。它的目的是进行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除了自身内在的学术价值之外,还指向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目标,它力图回答中国学界十多年来一直在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当代英美和欧陆两种传统、两大思潮的异同究竟何在,它们之间异常深刻的差别和对立源于什么?两大思潮有无合流的可能,二十一世纪的哲学会仍如本世纪那样多元杀阵、分崩离析,还是会呈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的趋向?从语言入手从事研究,既是最好的途径,也是唯一可能的途径。因为欧陆各家各派哲学,其内在理路歧异之深,几乎无法将它们作为等量齐观的审视对象,也许唯一的例外之处是它们都在语言维度中展开。而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更呈冰炭难容之势,或许语言是这两个怪异之数的公分母。当然,与上述宏大目标相比,本书的分量就太轻飘了。不管读者如何想,作者所言“抛砖引玉”确实发自肺腑。
作者从语言—哲学角度研究了本世纪英美与德法两大传统的异同之后,对于一种在我国学界流传甚久、流传甚广、至今几成定论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许多人认为,当今世界上主要流行两大相互对立的思潮,其一为英美的科学主义思潮,其二为欧陆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思潮。有人甚至由此进一步推论道,科学主义思潮代表了现代化精神、理性精神、物质技术精神,而人文主义思潮代表了后现代精神,与东方哲学有相同内涵。瞻望下一世纪哲学的前途,要么是人文精神战胜科技精神,人类向自己的本性回归,要么是人文思潮与科学思潮互补或结合,新的大而全、通达圆熟的哲学即将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指导。作者在对各家各派的语言哲学观条分缕析之后指出,科学—人文对立之说虽然捕捉了若干表面现象,其实并未准确把握到当代哲学的实质和走向。从英美方面看,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家族相似”、“生活形式”说,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胡塞尔对意向的重新强调,和科学有什么关系?从欧陆方面说,胡塞尔对严格性和客观性的追求,离人文精神近,还是离科学精神近?海德格尔对“此在”(Dasein)的精深分析,显然是对存在的追究,而不是一种人道立场的表达。事实上,在形而上的层面上,谈科学与人文的分野是不得要领的。
《语言与哲学》一书的重头戏是最后一章,作者在这一章中从语言观,对意义的理解,语言与世界、与人的关系等方面对英美和德法哲人的思想进行了对照和比较研究。应当承认,恰恰是这一章,显示了此书内容和深度的不足,可能会使期望甚殷的读者感到遗憾。也许谈得上有点新意的是,作者对若干最著名的哲学家进行了捉对比较研究:胡塞尔和弗雷格、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并论述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是如何影响了哈贝马斯的社会和文化批判理论以及如何在方法论上帮助利科阐释“自我”的意义的。在解释了两大传统的种种差别之后,作者表示同意罗蒂的看法:尽管英美传统以脱离认识论转向语言而引人注目,但从根本上说,英美思潮在精神气质上还是继承和发扬了认识论传统,而德法思潮是真正地、彻底地与认识论传统作了决裂。对英美传统而言,语言取代了认识或思想的中心地位,但思路却无大变,用英国哲学家达米特的话来说就是,哲学研究可以在逻辑上分成若干层次,形成一个等级系统,某个领域可能处于更基本的层次,是其他研究的前提条件。对于英美传统而言,把基础从认识论下移、深入到语言,仍然属于“基础主义”的思路,相比而言,欧陆哲学对于西方认识论主流传统的反叛要彻底得多,比如,对于后期海德格尔而言,诗歌似乎取代了哲学的位置,或者说,诗歌与哲学是合二而一的东西。
基于在语言维度对当代两大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作者认为,许多具有东方思维特征的中国人向往和预言的哲学在下一世纪的合流,没有可能发生,尽管罗蒂、伯恩斯坦、泰勒等人极力主张解释学在未来可以扮演统合英美和欧陆两大潮流的角色。因为,各家各派哲学并没有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它们仍然保有在各自传统中继续发展的活力,而且,世界上第一流哲学家目前的工作也集中于这个方面,而不是批判和背离自己的传统,致力于寻求新的统一。
(《“哥白尼式”的革命》,徐友渔著,上海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版,15.85元;《语言与哲学》,徐友渔等著,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九六年版,17.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