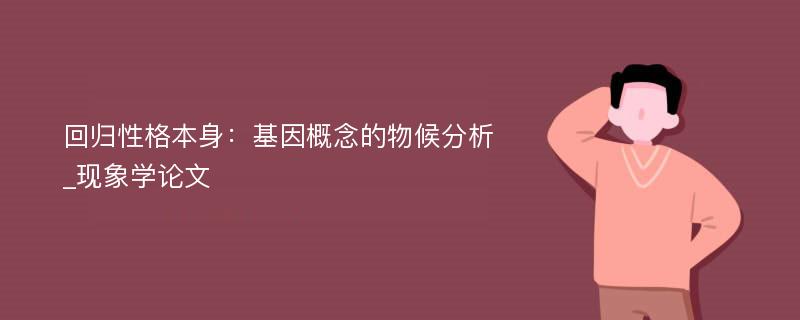
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性状论文,基因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062(2012)04-0008-07
导言:一个方法论说明
20世纪哲学界普遍流行着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对立的情绪。如果这种对立是就现象学的反经验论与分析哲学的经验论立场而言,无疑具有正确的方面,但是,如果将整个分析哲学完全归于经验论,那就是片面的。至于那种认为现象学应当拒斥分析哲学的明晰性和精确性的观点则完全是误导性的,并且是有害的。事实上,试图在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寻求统一基础的哲学家已经发现,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在起源上有着广泛的共同基础[1-5]。
本文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无疑是现象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本文将严格皈依于某一现象学经典作家的文本或原始方式,相反,笔者这里希望采取的方式是,依据现象学的基本精神对分析哲学中的方法论作出重构。我们称之为“分析现象学”方法。
关于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同一性,笔者已经在别的地方(并将继续)加以论述[6],我们这里着重改进与重建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7]。
在摩尔看来,如果我们要考察两个“对象”(例如“黄”与“橘子”或“善”与“快乐”)的同一性,即定义项与被定义项的同一性,我们总是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x是y吗”。如果在我们的心灵中x的出现与y的出现是同一的,那么,这样的问题就是封闭问题(closure question),我们回答“是”,例如,无论何时你想到一个“单身汉”的观念,你的心灵中都会出现“未婚的男子”的观念,因此,它们是同一的;否则,我们就只能回答“否”,并且它是一个“开放问题”(open question),例如,当我们的心灵中出现“快乐”这个观念时,我们的心灵中并不能总是出现“善”这样的观念,也就是说,“快乐”和“善”在我们的心灵中是两个不同的观念。
笔者已经论证,摩尔的这种方案是受到了伦塔诺的启发的[8],只是摩尔的方式更具有分析哲学的明晰性。事实上,这种方案在胡塞尔那里也有体现,例如,胡塞尔强调,我们总是能够通过三角形与四边形的差别来直观到它们的本质差别,这就是说,它们在我们的心灵中总是具有两个不同的观念形态[9]。
我们将要改进的地方在于,不仅两个对象在我们心灵中所产生的观念的不同反映其本质的不同,而且,两个事态在我们心灵中产生的观念的不同也反映着它们本质的不同。这里将摩尔由对象在心灵中形成的观念称为“对象观念”,而我们关注的事态在心灵中形成的观念称为“事态观念”。在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在遗传现象和基因概念的分析中,事态观念的分析将比对象观念分析更加重要。
(一)遗传观念的现象学基础
基因概念与遗传观念的紧密相关性不言而喻。
直觉地看,遗传现象就是亲代与子代的某种相似性。也许人类对遗传现象的认识首先基于亲代与子代之间个别特征的相似性,但一旦这种相似性扩展到更多的特征,遗传的观念就会必然地形成。
我们可以以孟德尔关于豌豆花色遗传的例子来考察遗传的观念。假如豌豆亲代的花色为红色,豌豆闭花授粉(自交)后,子代的花色也将是红色。如果这种现象也存在白花豌豆中,存在于其他植物甚至其他生物中,遗传的观念就可以确立起来了。
遗传观念的确立事实上就是一个现象学的还原过程,是一个不断悬置个别对象而获得一般现象(观念)的过程。我们可以更精致地作出如下考察。
单一的观察可以表述为:“某豌豆亲代花色红色自交,产生子代花色为红色”;
红花豌豆自交的规律则可以表述为:“任一豌豆亲代花色红色自交,产生子代花色为红色”(1)。
在每个单一观察中,不同的是特定的豌豆植株。这种特定的豌豆植株即摩尔所说的“自然对象”或弗雷格所说的“对象”。根据胡塞尔的现象学还原方法,这样的对象应该被括置,即进行现象学的“悬置”;而“悬置”之后就得到了一般的“豌豆”植株观念,即自交规律表述中的“任一豌豆”——它相当于摩尔的“思想对象”,或弗雷格的“概念”。也就是说,用胡塞尔的术语来讲,从自然对象到思想对象(摩尔式术语)或从对象到概念(弗雷格式术语)的过程,就是一个现象学“悬置”的过程。
如果人们继续将红花自交的规律运用于白花自交的豌豆,则可以得到白花自交规律的表述:“任一豌豆亲代花色白色自交,产生子代花色为白色”(2)。
比较(1)和(2),我们可以发现,“红色”和“白色”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也就是说,它们对于遗传观念的确立并不是必要的,从而是可以加括号或进行现象学“悬置”的;于是,我们得到如下表述:“豌豆亲代任一花色自交,产生子代花色不变”(3)。
不过,这个现象学“悬置”还可以对表述(1)-(3)中的“自交”方式进行。例如,红色与红色、白色与白色杂交(人工异花授粉)也会导致相同的结果,因此,“自交”与“杂交”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从而它们可以悬置为“交配”。于是,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表述:“豌豆亲代任一花色与相同花色植株交配,产生相同的子代花色”。
这种现象学“悬置”还并没有完成,我们完全可以将“花色”替换为其他性状,最后得到“豌豆亲代相同性状的植株交配,得到相同的子代性状”。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物种“豌豆”作为悬置对象,“豌豆”也可以“悬置”为任一生物“物种”,即将上述结果运用于其他生物物种,于是我们得到一个一般的遗传观念:“相同性状的亲代个体交配产生子代的性状相同”。
上述分析表明,遗传观念的获得经过如下几个平行的“悬置”过程:(1)将特定豌豆植株悬置为一般的豌豆植株,直至将特定物种(豌豆)悬置为一般的物种;(2)将特定性状(红花)悬置为一般性状;(3)将自交悬置为杂交。
上述悬置过程既可以得到分析哲学的说明,即弗雷格式的“对象处于概念之下”的说明,也可以得到现象学的说明,即胡塞尔式的“持续覆盖”。我们将这种“悬置”方式称为可替换“悬置”。
从弗雷格的角度看,“特定豌豆植株”这个对象处于“(任一)豌豆植株”这个概念之下;“红花”作为特定性状对象处于一般“性状”这个概念之下;同样地,“自交”作为特定杂交方式的对象处于一般“交配”概念之下;而“豌豆植株”作为一个特定的物种对象,处于“(任一)物种个体”这个概念之下。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关于“物种”、“性状”、“杂交”等纯粹概念之间关系的“遗传”概念。
从胡塞尔的角度看,特定豌豆植株的对象在我们的意识中获得一般“豌豆”的观念,进而获得一般“物种”的观念,而“红花”性状也在我们意识结构中获得了一般“性状”的观念,通过“自交”则获得“交配”观念。这个过程是一个由对象到观念,到更大观念的持续覆盖过程,在这个持续覆盖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反映纯粹观念关系的“遗传”观念。
在我们看来,弗雷格和胡塞尔的方式分别从外延和内涵的方面阐述了对象-概念关系和对象-观念关系。而我们的“可替换悬置”则试图表明,从概念外延的可替换中,我们可以把握到概念的本质,即观念。“豌豆植株”对象的替换(可重复的实验)可以获得它们所属的共同观念“豌豆”的本质,而从豌豆个体与其他物种个体的外延可替换性中获得“物种”的观念本质;从“自交”方式与“杂交”方式的外延可替换性中,我们获得“交配”的观念本质。最后,通过持续的外延替换,我们得到关于“遗传”观念的内涵即本质。我们的方式是摩尔式的,是通过外延替换获得内涵的理解,是外延-内涵法;在这里,自然对象是外延性的,而观念(思想对象)则是内涵性。如果自然对象(外延)的替换并不导致观念(内涵)的不同,那么,这些自然对象在我们的心灵中拥有共同的观念(即现象学本质)。这是开放问题的一个延伸:逻辑上可以证明,如果两个自然对象在我们的心灵中恰好引起了某序阶上的同样的观念,那么它们的关系在该序阶及其以上序阶上是封闭的;而在该序阶以下的序阶上,则形成了开放关系。
(二)形式遗传学的现象学分析:基因作为性状本身
在不同文化中共同存在的遗传观念,但它还并不“科学”,在遗传学上,它只考虑了基因处于纯合状态的个体,而没有考虑杂合个体,尽管它对于一个基于直觉的遗传观念已经是足够的了。
基于直觉的遗传观念的不“科学”性也表现在,它还并没有涉及基因概念。基因必然首先与具体的性状而不是被悬置了的一般性状联系起来;并且,基因概念的精确性必定还要与遗传学的实验结果联系起来。
我们还是以孟德尔的豌豆花色遗传为例来考察形式遗传学即孟德尔遗传学的基因概念。
从红花豌豆自交产生红花子代的现象,我们立即可以猜测这背后有一个因果“本质”,即有一个“遗传因子”或“基因”使得亲代与子代之间的表现性状相同,以遗传学的方式,可暂时称之为“红花基因”。红花基因因果地决定了豌豆花的红色。
但是,“红花基因”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所谓的红花基因决定的只是花的颜色,而并不决定红花本身。因此,严格的说法应该是花红基因,即决定花的红色性或红性。至于花本身的决定则是另一个基因的功能,它决定花的存在性,即花的有无。
从“花的红性”、“花的存在性”这样的术语看,性状本身的准确表达应该是形容词性的名词,即谓词性的。这使人想起摩尔所说的思想对象“黄”和“善”。
事实正是如此,花和花的颜色是如何形成的,是由什么样的色素引起的,是发育研究的主题,对遗传学、至少是对形式遗传学来说并不重要。引申地说,形式遗传学只关心性状与我们经验本身(现象或观念)相关的东西,而不关心性状背后的物质实在;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基因看做是性状本身,花红基因就是花红本身;花的存在性基因就是花的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形式遗传学的基因概念恰恰是现象学的,而不是经验论的。
然而,“科学”遗传学会立即向我们提出诘难:如果红花的花红基因就是花红本身,那么如何说明红花与白花个体杂交后得到的红花个体呢?这个子代的红花基因也是花红本身吗?
我们知道,在形式遗传学那里,纯合亲代的红花性状与子一代的红花性状,其基因的因果本质是不一样的:前者是纯合子的表现型,后者是杂合状态的表现型。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必须将遗传过程看做一个事态来对基因概念作出现象学说明。
首先,我们看看如下两组杂交结果:
红花*红花(自交)→红花
红花*红花(自交)→红花:白花(3∶1)
尽管上述杂交过程的左边在我们的视觉感官中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当我们联系右边出现的结果时,即将整个杂交过程看做一个事件或对象时,就会在我们直接被给予的经验中呈现出关于“花红”不同的观念来,从而,两种花红的“意义”是不同的。前者的花红是纯粹的花红本身,而后者是不纯粹的。
为了进一步说明,我们来看看测交的情形。在测交中,我们将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两种花红“意义”的不同:
首先,我们完成这样一组测交:红花*白花→红花。
在这组测交中,我们使用任何一棵白花植株与该红花植株进行杂交,结果都是一样的;这说明,白花是可替换的。这种可替换性说明所有的白花性状具有相同的本质“花白”。
然而,这种可替换性却不能适应于红花植株。如果使用任何一棵红花植株替换上述测交过程中的红花,那么结果就会改变,从而出现两种杂交结果:红花*白花→红花;红花*白花→红花:白花(1∶1)。其中,第一种结果与前面的测交结果相同,而后一种结果则不同。
这种不可替换性说明,同是红花的性状具有两种不同的本质,或者说,存在着两种不同本质的红花。
上述替换性说明似乎符合现象学所隐含的基本原则:如果两个对象的本质是同一的,那么它们相互替换后在我们的心灵中会形成相同的观念现象(即摩尔所谓的“封闭问题”);如果两个对象的本质或“意义”是不同的,那么它们相互替换后在我们的心灵中形成了两个不同的观念(即摩尔所谓的“开放问题”)。
但是,这种说明会立即受到反驳。因为上述的可替换性或不可替换性是在一个因果过程中发生的,而不是在一个意识过程中呈现的,它们的本质就应该只是一种因果本质,而不是现象学本质。在现象学意义上,两种红花都只能在我们的心灵中产生同样的观念。
那么,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困难呢?即如何对这种可替换性和不可替换性作出现象学的说明呢?
我们尝试将“红花”看做一个“意向象”①,它可以在我们的心灵中呈现出一个观念,即具有一个现象学的本质——“花红”;但是,“花红”观念只是“红花”意向象的一个侧显,它还可以有其他侧显方式,例如在测交实验中呈现的“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性的侧显和“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和白花(1∶1)”性的侧显。
现在,我们分析上述3种侧显方式相互组合形成的相关于红花的不完全意向象。
它们两两组合可以形成如下3种不完全意向象:
(1)“花红”且“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性;(2)“花红”且“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和白花”性;(3)“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性且“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和白花”性。
但是,“红花”意向象的两种侧显方式“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性与“与白花杂交可以得到红花和白花”性逻辑上是不可兼容的,即如果将这两种侧显方式统合为一个不完全的“意向象”,将像“圆的方”一样,在实在世界中找不到一个对应的对象,而红花则在对象世界中是实存的。因此,意向象(3)在具体的遗传现象中可以不予考虑。
“花红”这种侧显方式与两种“杂交”侧显方式组合,将形成(1)和(2)两个不同的意向象。
由于意向象(1)和(2)是不同的,那么,作为自然对象的“红花”必定是不同的②。这种判断符合摩尔的开放论证原则,即在我们心灵中呈现出两个不同观念(即意向象)的自然对象必定是不同的③。
这种解决方式的关键是将因果作用过程(测交)看做是与侧显方式相联系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因果过程本身并不包含在侧显方式中,毕竟侧显方式是属于意向活动的——事实上,这种处理将因果过程“悬置”为侧显方式④。
基于上述差异,我们可以给两种不同意义的花红以不同的名称,我们可以根据遗传学的分析,将上述两个第一组中的花红称为纯合态花红,而第二组中的花红称为杂合态花红⑤。
从上述结果看,现象学中强调的“直接经验中的被给予”与感官结果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内在的看,意义性的看,而后者是一种认知的看,心理学的看。因此,现象学“悬置”不仅包含了对个别对象的“悬置”,同时也包含了对感官的“悬置”,这两种“悬置”是在同一过程中伴随发生的。这也表明,本质直观乃是一种意义性直观,而不是感觉直观;或者说,意向活动始终是意义性活动,而不是感官活动。
我们将在上述分析过程中所呈示的对感官活动的“悬置”方法叫做“因果延伸法”。这种方法的基本意旨是,在我们对对象的最初感官活动所把握的意象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将它置于某一因果过程(即相同的因果背景)中,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不同,从而把握到它们不同的本质或意义。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是首先基于我们的感官,而感官认知所获得的意象是一个心理学的因果过程,心理意象有可能“遮蔽”我们对“意义”的把握,而因果延伸法就是运用另一个因果过程来对抗这种因果性“遮蔽”。
诚然,我们的方法可能受到这样的质疑:感官认知的因果性是应该“悬置”的,而因果延伸法中因果过程当然也是应该“悬置”的,用一种该悬置的方式去“悬置”另一种该“悬置”的过程,能够得到确定的本质或意义吗?或者说,一个因果过程对抗另一种因果过程的过程,也必定是因果性的,是应该“悬置”的,我们如何可以通过一个应该“悬置”的过程获得本质或意义呢?
这种质疑就像上面我们在具体分析“红花”意向象时所受到的反驳一样,是有道理的。但是,就像我们已经化解了这种反驳一样,我们还必须强调,意向活动本身总是超越性的(transcendental),因果延伸只是以相关于“意向象”侧显的方式去除“遮蔽”,而不是呈现“意义”;“意义”本身的呈现(例如“侧显”)总是依赖于意向活动本身的先验性直观。
因为“因果延伸法”必须借助分析的方式获得本质,所以,它也可以称为“本质分析法”,“本质分析”就是去除因果因素对本质的“遮蔽”;严格地说,“因果延伸法”中的本质分析并不是对本质的直接分析,而是向着本质进行的分析,本质本身是拒绝分析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意向活动本身并不需要这种分析,意向活动本身永远是直观性的。
最后,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方法的普遍意义在于,它肯定了在科学实验中使用不同的仪器或方法确认同一现象的方式,因为这些转换乃是在实施着意向活动对感官活动的“悬置”,因此,现象学并不应该拒绝科学实验。但是,我们也应该指出,现象学对科学实验的说明不同于经验论,后者认为科学实验可以使得我们比感官更逼近实在,而现象学则是通过此方式逼近意义。实验观察就是一种因果延伸形式,它以相关于侧显的方式展示了意向象更加丰富的“意义”侧面。
(三)对基因概念之经验论还原的“悬置”: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
在形式遗传学的本质分析中,我们还只是正面指出,性状本身就是基因,我们还没有从反面指出其他对基因作出因果理解的谬误性。
孟德尔本人对遗传因子也作出过一个因果设想,即遗传因子处于生殖细胞中。当孟德尔定律重新发现之后,细胞遗传学家(博维里和萨顿)立即将基因的行为与染色体的行为联系起来,并猜测基因位于染色体上;通过基因在染色体上的连锁分析,这种猜测为摩尔根具体化和形式化。接着,摩尔根和他的助手缪勒提出基因是一种有机分子的猜想。在早期的基因化学本质探索中,塔特姆和比德尔提出了“一个基因一个酶”的学说,而艾弗里则从一系列严格的实验得出一个模糊结论:基因是DNA;最终,赫希和蔡斯确证了艾弗里的这个结论。在沃森和克里克阐明DNA的结构之后,莫诺和雅可布探明了基因的分子结构,提出了操纵子学说。自此,基因概念沿着经验论的还原路线彻底地将一种生物学现象还原为一种物理化学的因果本质。然而,这种因果还原并不令人兴奋。事实上,在此之后关于基因结构的更广泛的研究表明,经验遗传学无法为基因概念提供一个精确一致的描述,分子遗传学可以谈论具体的基因,却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基因概念。
基因概念的因果还原困境也是因果还原本身的困境。我们的现象学分析将表明,基因的经验论还原是可以“悬置”的。
首先,我们要考察的是摩尔根连锁分析的可“悬置”性。
我们还是以豌豆的相对性状红花的基因为例来考察这种可悬置性。首先,我们选定与红花基因连锁的目标基因A,它产生清晰可区分的单一特征。通过摩尔根式的杂交分析,可以得到红花基因R与A之间交换率,从而确定R与A之间的遗传距离s1和基因R的位置S1。
现在,假定有另一个表现型完全相同的品种,这个品种与上述品种的唯一差别是染色体发生了突变,这种突变导致红花基因的位置发生改变。这在遗传学上是可能的(事实上,即使我们假定基因R位于另一染色体上,也不会影响该基因的遗传表型)。在该品种中,通过与上述杂交相同的过程,可以得到R与A的遗传距离为s2和R的位置S2。
显然,上述遗传距离s1≠s2,即R基因的位置S1和位置S2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说明,位置S1和S2是可以替换的。
S1和S2的可替换性可以得到遗传学的因果说明,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看,基因的功能与基因所处的染色体位置无关,只与基因的分子结构有关,只与它的操纵子结构和DNA序列有关;其中,操纵子中的启动子与启动基因决定基因的表达时序,而结构基因决定其所决定的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但是,遗传学的说明并不是现象学的。我们从现象学的角度考察基因位置的可“悬置”性,并不是要追究其因果机制,我们要表明的只是,不管基因的位置如何,都不影响基因的表达和表现型,也就是说,基因在染色体上的特定位置对性状并不是必然的,从而是可以悬置的。更清楚地说,不管基因R位于染色体的何处,它所对应的表现型“红花”在我们心灵中都占据同样的观念“花红”,这些染色体位置对“花红”观念来说是等价的。这就相当于无论一棵树生长在何处,它在我们心灵中都具有同样的意向象。
事实上,现象学具有更大的悬置范围,不论红花基因R的DNA基础,还是红花的生理基础花青素,在我们的意识结构中都是等价的,都可以悬置。
坚持经验论立场的人可能反驳说,尽管基因的位置不重要,但是基因的物质内容是重要的,即DNA和基因结构对红花的表达是不可或缺的,从而不能被“悬置”。然而,我们接下来要论证的恰恰是,基因的物质基础也是可以悬置的。
遗传学本身已经表明,基因不仅可以是DNA,也可以是RNA;事实上,从进化的角度看,任何满足遗传特性的化学结构都可以充当遗传物质,进化选择DNA作为基因的物质基础,可能是偶然的。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更为极端的情形,假定科学家已经掌握一个物种的所有基因的表达时序和表达结果(蛋白质的氨基酸时序),那么,我们就完全可以设计一个计算机程序在体外人工合成所需蛋白质,按照基因的表达时序注入细胞的特定区域。这时,我们可以完全剔除体内的DNA和RNA而不影响该物种个体的生长和发育。
在这种情形下,计算机程序完全替换了基因的物质基础;在此意义上,基因与程序是等价的,在现象学意义上都是可以悬置的。
现在,可以总结一下我们“悬置”因果还原的方法论基础了。
这里我们仍然使用了因果延伸法,但是,这种延伸不同于前一节的延伸。前一节的延伸导致了不同的意识结构,即不同的观念,从而,因果延伸与侧显方式相关。但是,这里的因果延伸与侧显无关,它并不形成新的侧显方式,因而并没有创造意向象的“意义”方面。前者是横向延伸,而后者是纵深延伸。我们可以将前者称为意义相关的因果延伸,而后者称为意义无关的因果延伸。
我们可以将两者的差别形式化如下:
首先,我们看看意义相关的因果延伸。我们假定红花具有两个本质,现象本质E和因果本质E′,因果本质E′与另一因果对象作用产生新的因果现象C′,这种现象在我们心灵呈现出观念现象C。于是,E和C构成同一意向象的不同侧显,它们都具有心灵“意义”。在这里,因果本质E′和C′在我们的心灵中呈现出不同的观念E和C,因此现象学上是不可替换的。
然后,我们看看意义无关的因果延伸。我们还是假定红花具有两个本质,现象本质E和因果本质E′,但是,E′作为因果本质是另一更深刻的因果本质E″的结果,E″并不在我们的心灵中呈现出新的观念来,即E′和E″在我们的心灵中呈现出同一观念。因此,E′和E″在现象学上是等价的,是可替换的。
(四)回到性状本身之后:结论及余论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基因就是性状本身(trait itself)。但是,我们必须区分“性状”和“性状本身”这两种表述。“性状”是“科学”遗传学的概念,即经验论的概念,它表示个别对象,是基于感官直观的经验论直观;而“性状本身”是现象学概念,是对“性状”的本质直观,是谓词性的。
“性状本身”这个观念的获得通过消除两类反例来达到:第一,同一表现型如何具有不同的基因型;第二,性状本身如何与基因的物质基础无关。
在消化第一类反例时,我们区分了感官直观和本质直观,并通过相关的因果延伸所侧显出的不同的意义来把握“性状本身”。在消化第二类反例时,我们通过因果延伸和外延替换“悬置”了基因的物质基础,从而维护了基因作为“性状本身”的观念。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探讨“回到性状本身”之后更重要的意义,这些意义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任何可以在我们意识结构呈现意义的生物学特征都可以作为性状;第二,遗传观念可以扩展到非生物学的过程。
现代遗传学确定性状的依据主要是感官特征,即感觉上可以明确区分的、稳定的生物学特征。这种方式忽略了太多的遗传学内容。而我们则希望通过“意义”特征来确定性状,即凡是在我们意识结构中与生物学相关的有“意义”的单位,都可以在生物学特征中找到其外延表象,即这些表象可以作为性状,例如,“求偶的成功”。依据“意义”的方式将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例如行为遗传学研究。
遗传观念扩展到非生物学过程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计算程序的遗传性,在此意义上,我们将基因的物质基础等价于一个计算程序。但是,这并意味着我们赞同计算主义的观点。在计算主义看来,计算程序既然可以替换基因的物理基础,那么,计算程序就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基因概念的基础,甚至是优先的基础;基因也就是一种广义的计算。计算主义只是用计算的观念来取代物理的观念理解世界,计算主义依然坚持一种实在的观念,即计算实在论。在这种计算实在论中,基因程序就像物理基因一样,是一种实在的对象。然而,在现象学的观点看来,基因的计算程序对基因的物理基础的可替换性并不能说明计算程序的优先性,而只能说明它们的等价性,这种可替换性恰恰说明它们各自对理解基因概念并不是必须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通过它们其中之一理解基因观念本身;这种观念只能存在于我们的意识结构中,它是对基因计算程序和物理基础的超越,是先验性的。可以说,基因不是对象,而是意义。
最后,对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也可以为解决遗传学史研究提供一个洞见:孟德尔的成就是现象学的,而不是经验论的,而这也是他被同时代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原因。当时共同体的思想是因果还原论的,他们认为,遗传现象是远因(进化)和近因(发育)的共同结果,因此,要弄清遗传现象,就必须弄清它的原因,进化的原因和发育的原因;而孟德尔则“悬置”了这些因果关系,直接关注现象(亲代与子代形状)之间的关系和规律。显然,孟德尔这种不自觉的现象学方法很难为当时共同体所接受。
[收稿日期]2011-05-13
注释:
①“意向象”是noema的中文翻译,这种翻译综合了目前国内两种翻译,“意向对象”(李幼蒸)与“意向相关项”(倪梁康)。
②如果将现象学的这个原则运用于语言哲学,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意义不同,则指称不同。这一点不同于弗雷格的分析哲学结论,即意义不同的符号可以指称同一对象,例如“长庚星”与“启明星”指称同一对象“金星”。事实上,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就会发现,“长庚星”与“启明星”的指称同一性并非必然的,它只是相对于地球的观察者而言的;我们完全可以用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原则说明,两者并不是严格(或形式)同一的。
③必须注意,摩尔的开放性论证原则的逆命题是不成立的,即我们只能由观念的不同判断自然对象的不同,而不能由对象的不同判断观念的不同——事实上,两个在空间上分立的对象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意向象。
④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还将设计一个基于自然遗传现象与虚拟遗传现象之因果差异的思想试验来论证,为什么侧显方式是对相关因果过程的“悬置”。
⑤事实上,在显性不完全性的情形中,我们就用不着这种替换分析。在那样的情形中,处于杂合态的花色将会是介于完全显性与隐性性状之间的一种状态,例如,可能是粉红色。这样的结果即使在我们的感官直观中也是有差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