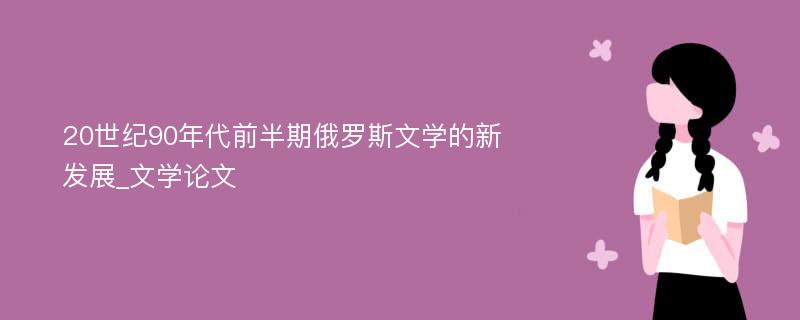
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文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新发展论文,年代论文,半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已经过去五年多了。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充满剧烈变动的时期,更是俄罗斯民族历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以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苏联从改革走向解体,俄罗斯联邦放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定语;政治斗争中的"8.19"事件,十月事件,车臣战争;经济方面的“休克”疗法、私有化措施等等牵动着每一个俄国人的心,涉及到每一个俄国人的利益和前途。90年代上半期的俄罗斯文学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生活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的。
自本世纪20年代起,我国的学者(外国文学评论家与翻译家)与读者就对俄罗斯文学,包括俄罗斯古典文学与苏俄文学,怀有浓厚的兴趣,从俄罗斯文学中汲取了大量的营养,用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在1949年后,我国就有过两起介绍、翻译和阅读俄罗斯(和苏联)文学的热潮,它们分别出现于50年代和80年代。在80年代的十年中,“译介成中文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是60-80年代的作品)已达五千余种。”而且这种译介“具有及时准确的特点”。①与80年代的情况相比,90年代上半期我国对俄罗斯文学的译介工作显得过于谨慎与迟缓。这种谨慎与迟缓表现在译介的作品数量剧减和对当前俄罗斯文学现象的批评增加上。这里除了版权等技术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认识方面的原因。
我想,要正确客观地评价90年代上半期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应当在认识上做到以下三点:首先,需要正视俄国的社会现实,即“尊重俄国人民的选择”,这不仅是我国政府的外交态度,而且也是我国人民和学者同俄罗斯人民进行文化交流时应当具备的科学态度;其次,要改变俄苏文学研究中的旧有话语,摆脱所谓苏俄文学典范文本的情境约束;再次,要充分阅读文本。做不到这几点,就会产生一种对放弃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这一定语的俄罗斯联邦的文学的排斥态度,就会依据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履”去削文学作品之“足”,就会浮躁地不去细谈文本而简单地宣称某作品不是好作品。我们的俄国文学研究就会停留在留恋苏俄文学的“辉煌”、抱怨与指责今日俄国作家的“离经叛道”上。再过上几年,我们又将会重复“文革”之后回眸苏联60-70年代文学时的那种恍若隔世的陌生感。
本文试图通过对某些具体作品的简析,粗略地展示90年代上半期俄国作家们的新探索和俄罗斯文坛的某些发展趋势。
90年代的俄罗斯文学是苏联文学,准确地说,是苏俄文学的直接继续。它继承了苏俄文学在80年代末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也继承了苏俄文学的传统和发展态势。
50-60年代描写当时苏联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区里的日常工作》、《解冻》、《不单是靠面包》、《征途上的战斗》等,和描写苏联历史的《一个人的遭遇》、《试用期》、《生者与死者》、《白昼的星辰》等都是从正面反映苏联社会的积极变化的。而在80年代中期开始的“改革”中,被僵化的体制和“停滞”长期困扰的苏联社会痛切地体会到“不破不立”的道理,陷入了“我们这是怎么了?”的思考。80年代下半期的苏联文学作品就表达了这种苦苦的批判思索。从“改革”初年发表的《火灾》、《禁忌!》、《悲伤的侦探》、《一切都在前面》、《死刑台》、《穿白衣的人们》、《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到80年代末发表的《日瓦戈医生》、《人生与命运》、《忠实的鲁斯兰》、《古拉格群岛》等作品都是如此。
如果说80年代下半期发表的文学作品对历史的批判反思多着眼于某一时期社会的外部生活事件的话,那么90年代上半期的文学反思则更着重于表现前苏联人的内心变化,表现人们对苏联历史的总体的哲理思考。例如叶·波波夫的《美好的生活》、格·谢苗诺夫的《心灵之旅》、马尔克·哈里托诺夫的《命运的轨迹,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马卡宁的《平常化话题和情节》、皮耶楚赫的《由魔力控制的国家》、科罗廖夫的《果戈理的头颅》、斯塔德纽克的《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自白》、奥古扎瓦的《被关闭的剧院》、阿斯塔菲耶夫的《被诅咒和被杀死的》等小说就是这样的作品。
皮耶楚赫在中篇小说《由摩力控制的国家》中,从古罗斯形成前的斯拉夫人所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开始,讲述了俄罗斯民族国家产生、形成和发展的上千年历史,分析了俄罗斯民族朴实的个性、丰富的精神生活,既有浪漫精神,经得起社会动荡,但又具有强悍、凶蛮的特点。作家还通过作品中的“我”之口说出了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并不是极权,沙皇时期就有控制言论、破坏法制、怂恿宪警、压制异己思想等很坏的做法,“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而在于国家传统,也许,甚至在于俄国奴隶和奴隶主的血液的化学成分。”
进入90年代后,马卡宁的创作格外活跃,他在中篇小说《平常化话题和情节》中从前苏联建国开始就司空见惯的购物排队现象出发,分析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引起的人们心理、思想的变化:排队购物,“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长队中我们完全因我们长久的站立而平常化了,也就是说,无论职位、名字、学位或手上老茧的硬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走到队旁,问了一个人,站了下来:这就是生活,这时你就平常化了。”马卡宁还用平常化情节形象而又独特地总结了近两个世纪的俄国文学。他说,在19世纪,许多文学作品的主人公被平常化“情节顽强地引向与普通女人结婚,引向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融于人民之中”,以摆脱贵族的自我,而作家们(如托尔斯泰等人)则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放弃自己的许多个人权利,在道德完善的过程中实现了平常化,登上了人类精神境界的顶峰。因此19世纪的俄国人与俄国作家虽然一开始就处在前人到达的平常化的高度上,但因为没有经过道德和艺术上的追求和努力,所以就只能暗淡无光地下滑、堕落。因此两个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可以比作一座大山,19世纪是长满葱茏茂密的森林的向阳面,而20世纪则是昏暗的平常化、平庸化之路越走越宽的背阳面。
科罗廖夫在中篇小说《果戈理的头颅》中假20-30年代改建莫斯科城时搬迁果戈理坟墓的史实,用果戈理的头颅漫游广阔时空的荒诞故事,把俄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联系在一起,指出革命变动中常常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反文化、反文明的沉渣泛起,如果听凭愚昧的沉渣泛滥,革命就会变质,就要失败,人民就将蒙受巨大的苦难。
斯塔德纽克在他的“回忆性中篇小说”《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自白》中,用自己在20年代的饥荒、肃反扩大化、所谓打击富农运动、卫国战争、反世界主义运动及战后岁月中亲身经历的事实,勾画出了苏联的历史,指出在前苏联有许多“由时代的恶风和我们过去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牧人的虚伪行为决定的”坏事,“但主要的是我们度过了充满信仰和为我们的人民的幸福而斗争的诚实的劳动的一生。”
奥古扎瓦在他的中篇小说《被关闭的剧院》中回忆了30年代他少年时期的生活及他的父母,两位正直的共产党员,在激烈的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坚持党性立场,不为错误路线所裹挟的表现,说明人的高尚道德是可以保证人胸怀坦荡,良心清白的。
阿斯塔菲耶夫的长篇小说《被诅咒和被杀死的》虽然是一部关于卫国战争的“士兵的长篇小说”,但它所描写的不仅仅是卫国战争的四年,它通过许多追叙和插叙把卫国战争同它以前的肃反扩大化、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以及战后对战争的评价联系在一起,也即把整个苏联史当作自己的艺术研究的对象,从普通士兵和农民的立场出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政府的政策符合普通百姓的利益时,国家就强大,军队就胜利;当政策违背普通百姓的利益时,国家就虚弱,军队就失败。
这里作为例子提及的作品虽然出自不同年龄、不同政治观点、不同艺术主张的作家之手,这些作家对自己祖国历史的反思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反思的认真态度和深刻程度却是共同的,也是空前的。应当说,他们每一个人都为人们提供了进行关于苏联及人类历史思考的食粮。或者说,正是“在(他们)所描绘的许多一个个积累起来的,互相排斥的图景中,才开始显出真理的影子。”②
直接反映当前的现实世界,及时、积极地干预社会生活是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80年代中期呼唤改革的作品《火灾》、《悲伤的侦探》、《死刑台》等几乎是同步地描写了当时苏联的社会生活,指出了苏联社会必须改革才能免于毁灭这一道理。但以后在80、90年代之交,如前所述,俄国作家大多热衷于反思历史,即以已知的历史事实回答俄国应如何改革,向何处去的问题。加上大量“解禁”文学和侨民文学作品的发表,一时间人们惊呼,反映当前社会生活的作品无处发表。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这样,当代俄罗斯的社会生活在近十年的,尤其是90年代上半期的俄罗斯文学中还是得到了及时的反映。
同步地反映社会生活最及时的自然是随笔、短篇小说、特写等“小体裁”的作品。在这一方面,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索洛乌欣等做了很重要的工作。阿斯塔菲耶夫在从事大部头作品创作的同时,不断地写他的短小的杂感和随笔──《砍在树上的记痕》。关于“记痕”,阿斯塔菲耶夫是这样说的:“我在创作时,常常遇到一些与当时我的创作主线无关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人、事、想法很有意思,弃之可惜,就随手记了下来。其中有一些后来得到加工、变成了短篇小说,有一些仍作为‘记痕’留了下来。它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和我当时的思想。”③其实,邦达列夫仍在写的《瞬间》,索洛乌欣还在继续发表的《掌中宝石》也是同阿斯塔菲耶夫的“记痕”一样的作品。当然,用随笔体裁表现当前生活的还有其他许多作家。
在中、短篇小说创作领域,巴克兰诺夫、邦达列夫、马卡宁、拉斯普京、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叶·波波夫、瓦·波波夫、米·波波夫、皮耶楚赫、卡巴科夫、爱·鲁萨科夫、克里蒙托维奇、谢庚、纳巴特尼科娃、斯·瓦西连科、谢·梅德韦杰夫等几代作家,都表现了自己对当前俄国人民的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
被称之为民主派作家的巴克兰诺夫在其中篇小说《自己人》中塑造了一个靠左右逢迎爬上高位的官员的形象,生动地刻画了他在“改革”中所表现的抵触、反抗及冀希于同僚(“自己人”)帮衬渡过难关的种种心态。
所谓保守派作家邦达列夫在他的中篇小说《诱惑》中塑造了两位正直的科学家德鲁兹多夫和塔鲁金的形象,他们因坚决反对修建破坏生态的水库而受到包括一些官僚在内的黑手党的迫害,结果,塔鲁金遭到谋杀,德鲁兹多夫顶住了要他缄默的诱惑,决心继续坚持自己的正确立场。
从表面上看,马卡宁的中篇小说《路漫漫》并不是讲当前的俄国现实的,但是小说中关于善与恶的思考,想象的主人公对环境的无奈及对光明前途的不自信的企盼却是90年代初大多数俄国人的心理写照。马卡宁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出入孔》则通过主人公在由出入孔联接的贫困、动荡的现实世界和富足、安宁的非现实世界之间的选择,表现了大多数俄国知识分子不愿作为侨民苟活于西方世界,而宁愿和祖国共渡难关的做法。
社会政治变动引起人们心理、道德的变化,造成人们生存的精神痛苦和悲剧,是90年代俄国作家所关注的焦点之一。青年作家谢·梅德韦杰夫于1992年写的《荒诞的故事》,老作家拉斯普京于1994年写的《谢尼亚上访》、《俄罗斯的年轻人》、《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城市里》等短篇小说真实地记录了作家们对政治变动中人的行动与心理的观察。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一些作家基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及对人生和社会规律的准确把握,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反映了现实生活,而且能在真实情况披露前揭示过去的“秘案”,准确地预见现实生活的未来发展。例如,以中篇小说《叛逃者》(1989)准确预言了苏联的经济危机、最高层政变与联盟解体而著名的卡巴科夫,他在199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写作家》中真实地“预言”了80年代末克格勃对某显要政敌的袭击事件,书中的描写后来被公布的文件档案证实。又如,爱·鲁萨科夫1990年在他的短篇小说《伊戈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罗曼诺夫》中讲了一个一心想出人头地的平庸的工程师的故事,这位叫伊戈尔·罗曼诺夫的工程师在竞选厂长不成后突发奇想,自称是在枪杀中侥幸活下来的尼古拉二世之子阿列克谢的儿子,并决定伺机接管俄国政权。这在1990年的苏联只是一个令人发笑的故事,但到了1992年,俄国王朝复辟势力积极活动起来后,在俄国各地着实冒出了一批自称是沙皇后代并声称有权接管俄国政权的野心家。
一些大部头的史诗性作品在叙述时常常把故事的时间下限拉到“改革”时期。例如,在普罗斯库林的长篇小说《弃绝》的第二部中,饱经沧桑的当年某集体农庄主席、卫国战争老战士扎哈尔·杰留金把他在杰日斯克护林所的工作交给了他的曾外孙──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杰尼斯。在这里,作家想从扎哈尔形象的“权威性”来说明,俄罗斯民族的健康力量和未来希望存在于广大的下层俄罗斯青年之中。阿斯塔菲耶夫在今年刚发表的小说《真想活呀》中,描写了一位古稀老人科里亚从“富农崽子”到红军战士、工人、领养老金者的艰难的人生历程。在小说的末尾,作家通过老人的感受绘出了一幅当代俄国城市的风俗图画:大家都在忙着赚钱,青年人追求享乐,老人们贫病交加,“改革”中涌现出的新领袖们在策划着新的不安定:呼吁人们跟他们走,要人们不惜牺牲地争取光明的未来。
如果说在50-60年代的“解冻”文学中,诗充满了高昂的浪漫激情,起了揭露与抨击个人迷信的错误,呼唤与激励苏联人民的理想和信念而斗争的作用的话,那么90年代的俄国诗坛就没有这么多浪漫激情,而是充满了诗人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如沃兹涅先斯基的组诗《苦难的国家》[1],对时弊的嘲讽(如卡扎科娃的诗《为一代人辩护》),对动荡的时局的不安和对突发事件的预感(例如1991年8月7日发表的舍弗涅尔的诗《斯托雷平车厢》似乎预言了当年的“8·19”事件),对诸多新事物的困惑(如叶甫图申科的诗句:“现在是蒙胧的黎明, /现在是特别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对待自由?/可我们这儿早就没有了/那些能解答这一问题的人。”),对人民前途的担忧(如弗·索科洛夫的诗《今天是圣诞节》)以及对社会和人生的冷静的哲理思考(如库什涅尔的诗《这些松树大约有三十岁……》)。这些可以说是诗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情绪反映和深层的干预。
随着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文学作品所描写的俄罗斯人的生活也并不都直接与政治斗争相关。托尔斯泰娅、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叶·波波夫、玛利娜·帕列依、克利蒙托维奇等常常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当前人们平淡的日常生活。他们试图通过这种充满枝节琐事和细腻感情的平淡却又复杂的生活图景,表现文学永恒的真善美的主题。
1990年起,苏联实行了新的出版法,其主要精神是:凡是不泄露国家机密,不煽动民族仇恨,不宣扬暴力、色情的材料都可以发表。作家协会的章程中也不再规定什么基本的创作与批评方法了。这样,俄国作家就处在一个较宽松的创作环境之中。因此,如同前面的叙述中所表现的那样,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文学的思想、题材、人物都更加丰富、更加多样化了。
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文学作品内容的变化,文学作品内容的变化又必然地伴随着文学作品形式的变化。在“改革”前和“改革”初,苏联的文学理论家们就较他们30年代至50年代初只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基本创作方法的前辈们前进了一大步,承认在苏联文坛上同时存在着多种创作方法④(50年代中期至80年代苏联文学的成就是与这一时期方法论上的宽容做法分不开的)。90年代上半期,俄国作家的创作方法就更趋多样化了。
1990年初,批评家丘普里宁提出了创作方法与苏联主流文学不同的“异样文学”这一概念。其实,所谓“异样文学”就是60年代开始形成的苏联与俄国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只不过它犹如一座冰山,80年代前在苏俄文坛上显露出来的只是马卡宁、比托夫等人的作品,90年代以来,随着人们审美能力的提高,心理包容能力的增加,这座“冰山”的上层,即优秀部分,很快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1991年在高尔基文学院召开了俄国第一次后现代主义文学研讨会。自此,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在俄国名正言顺地流行起来。一时间,比托夫、马卡宁、马·哈里托诺夫、叶·波波夫、维克多·叶罗菲耶夫、沃兹涅先斯基、奥古扎瓦、基列耶夫、伊凡·日丹诺夫、帕尔希科夫、卡巴科夫、纳尔比科娃、基比罗夫、叶尔马科夫、别列文、科罗廖夫、玛·帕列依等许多作家,都被称作是后现代主义作家。90年代以来,《旗》、《新世界》、《十月》等大型文学杂志陆续发表了许多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作品。另外,还创办了《独唱》、《黄金时代》、《暖营》等专登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的新杂志,许多出版社也把出版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当成自己的重要任务。于是,不少人断言,俄罗斯文学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
后现代主义原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概念。俄罗斯文坛在评论这一新主义时虽然也搬用了许多西方学者的论述,便更多地强调的却是它所处的时代与社会。库里岑说:“后现代主义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其间生活的氛围,是游戏的条件,是天气……”⑤斯捷帕尼扬则把这一“氛围”,“游戏的条件”和“天气”具体化为人们丧失了“对人的存在的最高意义和超个性目的的信仰”;统一精神瓦解后,“在精神领域只能用旧的残片来创造新东西”;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真理。⑥由于“后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必须用复数形式‘后现代主义们’来表示的多元概念,”⑦我们与其去苦苦寻觅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准确的总括性定义,倒不如干脆说,它是俄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俄国文坛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的一种创作多元化的倾向。
所谓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大都知识准备较好,思想比较活跃,他们中的许多人力图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来观察与思考人民的现实生活与历史路程,如同马卡宁在《平常化话题与情节》中及皮耶楚赫在《由魔力控制的国家》中所做的那样。皮耶楚赫在他的这部小说中把俄国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和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发展摆在一起,客观公正地进行对照(例如,他在讲述斯拉夫人之起源时写道:“当中国人已经有了方块字,印度已经创造了灵魂超度的理论,埃及有了税收制度和复杂的水利设施,希腊已在完善最初的民主制度时,……我们的古代祖先还穿着兽皮。”)全然没有沙俄与苏俄时期官方史学的沙文主义,甚至也没有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人类文化史上各种有价值的思想的借鉴,如叔本华的关于只有否定“生活意志”,才能从痛苦中解脱的思想(果连施泰因的中篇小说《伏尔加河上的最后一个夏天》)、萨特关于人可以进行自由选择的思想(马卡宁的《出入孔》)、老子关于“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思想(叶尔马科夫的短篇小说《冰雪覆盖的房子》)等等。
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们接受了国际文学理论界的研究成果,把世界当作大文本,运用现当代其他国家作家们的互文性(例如,叶·波波夫在其长篇小说《美好的生活》中就声明,他的这部小说无头无尾,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第1961章至第1985章,因为1960年前及1986年后的篇章没有列入;而每一章由两个故事及大量当年的报摘组成。很明显,其目的是强调作品文本与生活文本的一致。)、改变传统的作家与人物的关系(如卡巴科夫的《写作家》)、消解作品的统一风格(如哈里托诺夫的长篇小说《生命的轨迹,或米拉舍维奇的小箱》)等创作手段和讽刺性摹仿[2]、反讽、化用等艺术手法,创作了许多生动活泼、绝少训导气的兼有认知、审美、娱乐等多种功能的文学作品。在连续三届布克文学奖评选中,被提名的大多是后现代主义小说,而又是哈里托诺夫、马卡宁、奥古扎瓦相继获得了这三届布克奖,普里果夫获得了普希金文学奖,这些事实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俄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成就。
后现代主义是世界文化现象,但具体在俄国,它又是文学的求新规律作用的结果,俄国作者与读者在写够与读够了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文学作品之后,自然想写一些和读一些内容与形式都较新鲜的作品。所以说,俄国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文化影响和俄国本世纪初所谓白银时代文学传统(俄国后现代主义作家都强调他们继承了这一传统)的“显征”(雅各布森语)的共同产物。
如果把90年代上半期的俄国文坛看成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统天下,那就不符合实际了。首先,这与后现代主义本身的“无定形”、“流动性”和“漫射”等主张不合。其次,阿斯塔菲耶夫、拉斯普京、别洛夫、邦达列夫、斯塔德纽克等一大批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尽管他们也受着作为时代的后现代的影响)仍在创作。再次,后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在经过一阵喷涌之后,其势头已明显疲软下去。还在1992年,斯捷帕尼扬就预言,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将代替后现代主义。⑧这似乎应是情理中的事,因为文学的求新规律和传统的“显征”是一直在起作用的,后现代主义在领了一阵风骚之后必然会被其他的方法、流派所代替。1995年的凯旋文学奖被授于阿斯塔菲耶夫,这也是反映了人们正在恢复对现实主义的文学的兴趣和爱好。
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次社会动荡都会引起人们思想的动荡和文坛的混乱。在这种文坛混乱状态中,煽动民族仇视,宣传暴力、性与色情,渲染“秘闻”之类的文学作品都会抓紧时机,纷纷出笼,“风光”一场。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苏俄就曾有过一次这种文坛混乱的现象。高尔基在1917-1918年间写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一书第14章中就描写并痛斥过当时那些关于“专权的皇后”、“充斥着病态的、虐待狂式的‘文学’”。⑨后来,这类“文学”很快就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列昂诺夫、法捷耶夫、费定、普拉东诺夫、布尔加科夫等人为代表的俄苏新文学浪潮荡涤干净了。90年代初,俄国的社会动荡也引起了色情文学与黑幕文学的沉渣泛起。但如据此而认为俄国文坛只是“乱糟糟”,充满暴力、色情、凶杀,那也有失偏颇。实际上,具有深厚人道主义文学传统的俄国社会在这场文坛纷乱面前显示了很强的鉴别、批判和调节能力:日里诺夫斯基宣扬民族仇视的《向南方的最后一扑》被评为“最坏的书”,⑩著名作家纳吉宾、瓦西里耶娃、叶甫图申科以领袖的恋情、名士的稳私、国家的以往机密为题材的书[3]给作家带来的是文学界的冷谈、讥讽和嘲笑,维克多·叶罗菲耶夫因其色情小说《俄罗斯美女》而被人们称作“不错的批评家兼蹩脚的作家”。1994年叶利钦总统签署了重申禁止宣传民族仇视、色情、暴力的文件后,一些色情出版物的事主还吃了官司。(11)随着时局的逐渐稳定,前几年文坛泛起的沉渣已经被俄罗斯新文学潮流的健康成分压了下去。
与前苏联时期相比,90年代上半期俄国文坛的一个巨大进步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开始形成一种互相信任、依靠、要求、满足的“辩证的交往关系”。(12)以前,官方的批评界向全国读者推荐统一的“教育人民的”官办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印数很大,但实际上印出的书的三分之二未被读者购买而被当作原料拉进了造纸厂。(13)90年代以来,文学读者则按照性别、年龄、爱好、思想倾向、教育程度而自行分流,形成了一个个拥有各自作者、杂志、出版社的读者群。作家和出版社在职业道德和市场利益的双重驱使下再也不能无视读者了(哪一位作家,哪一个出版者甘心自己的书直接变成造纸原料呢?)。读者在作家心目中的地位从来没有这样高,他们在作家创作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来没有这样大。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读者推动着90年代俄国作家进行思想与艺术的探索。1994年底,俄国《今日报》的调查表明,俄罗斯人“阅读文学作品的时间平均增加35%”。(14)出版专家们估计,1994年俄国书籍出版种数已接近了前苏联时期创记录的1980年(15)(而运往造纸厂的新书肯定比1980年时少)。这些事实无疑是对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作家们的积极探索与辛勤劳动的肯定。
总之,90年代上半期,俄罗斯的作家们在乐此不疲地写作,出版社在起劲地出书,读者在更加投入地阅读,失却了神圣光环的俄罗斯文学在继续发展和获得新的成绩的过程中,不断地有杰作出现,只是这一切已不再和“轰动”有关,人们都以平常的心情冷静地对待这一文学发展的态势。
注:①倪蕊琴、陈建华主编《论中苏文学发展进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页。
②叶·波波夫:《请安静,先生们!》。见莫斯科《文学报》,1992年,第10期,第4版。
③1995年2月15日阿斯塔菲耶夫对余一中的谈话。
④伊·菲·沃尔科夫在1988年5月在《文学报》座谈会上的发言。见《摆脱幻影》,莫斯科,苏联作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406页。
⑤库里岑:《后现代时代》。见《新浪潮,80、90年代之交的俄国文化与亚文化》,莫斯科工人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页。
⑥⑧斯捷帕尼扬:《现实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最后阶段》。见莫斯科《旗》杂志,1992年,第9期,第233页、第235页。
⑦钱佼汝:《小写的后现代主义:点点滴滴》。见《外国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第59页。
⑨见莫斯科《文学评论》,1988年,第9期。
⑩莫斯科《图书评论报》,1994年,第52期,第8版。
(11)1995年初,莫斯科《还有》报的主编(也是“作家”)就因刊登色情材料被法院起诉。
(12)萨特:《为何写作?》。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05-206页。
(13)古德科夫:《杂志热的结束》。见莫斯科《文学报》,1991年,第1期,第9版。
(14)转引自《参考消息》,1994年11月27日,第6版。
(15)丘普里宁:《1994年文学的特征》。见莫斯科《旗》杂志,1995年,第1期,第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