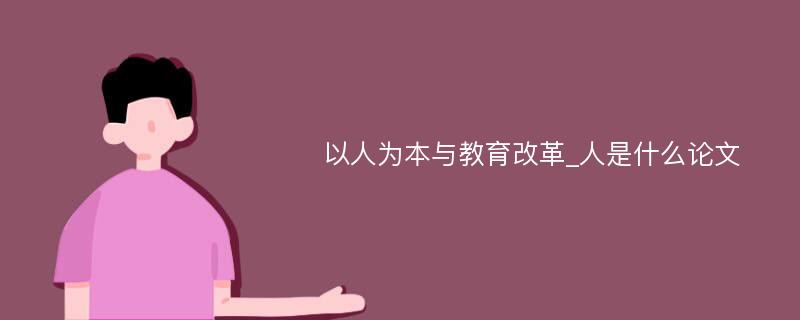
以人为本与教育学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学论文,以人为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在中国大地响起,这是不一般的政治口号,它象征着中国观念的根本变化。
比这更重要的是,人权已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件更伟大的划时代事件。
这两件事之间虽有相辅相成的关联,但本文将主要讨论以人为本的问题。
以人为本在中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想的过程并不像某些学者所叙述的那样轻松。这里,我们主要谈教育问题,一种不太轻松的感觉使人产生了对教育学改造的强烈意识。
一、人在哪里
“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这是常被我们引用的马克思的名言,可是,马克思紧接着说的话却不为人们所看重。“理论只要彻底”,“彻底”指的是什么?“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人是人的最高本质”[3]。这两句话被我们忽略只是一种偶然吗?只要再问问:我们在追求理论的彻底性的时候,人的地位有多高?而在一些“彻底理论”指导下的严酷政治运动中,人在哪里?只要问问这些,就不会有多少偶然感。
马克思的上述论断出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在这篇不长的导言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人就是人的世界”[4],“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人”[5]等一系列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命题。
“有了人,我们就开始有了历史。”[6]“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7],“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8],意识和理论的考察也就“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9]。这是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大量看到而在20多年前很少被关注的论述。为何会不被关注?人们由此并不难看到,“以人为本”来到中国大地决非轻而易举之事。
我曾询问过一位哲学专业的学生:“你喜欢马克思主义哲学吗?”答:“不喜欢。”我再问:“为什么?”又答:“从那里看不到人。”我感到十分惊奇,马克思主义学说本是从有了人就有了历史那里开始的,就是从现实的人那里出发的,就是为了人的解放的,怎么能说“看不到人”呢?
我想,或者是我们的哲学教材没有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华,或者,我们的哲学教学曲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讲准了、讲好了,学生怎么会不喜欢它?难道不是教育自身出了问题?
28年前,人在牛棚里,人在“五七”干校里,人在批斗大会的会场里,……那时,人们当然问:人在哪里?如今,这应当不再是一个问题了吧?可是,新的时期仍然有新的问题。
如今,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人在自由演说的讲坛上,人在充满激情的国际舞台上。可是,人们还在问:人在哪里?这似乎是一个原有的问题,可它确是一个崭新的问题,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人在我们的哲学之中吗?人在我们的教育学之中吗?或者说,哲学之中,人在哪里?教育学之中,人在哪里?
如果在教育学之中“人在哪里”确实是一个疑问的话,我们的教育学还谈什么以人为本?
二、谁的教育学
何谓以人为本?理解的困难有时并不来自概念和命题本身而来自现实生活,因而,困难最好也从生活中去化解。
2003年初春,“非典”爆发,可是,一些官员将此情加以隐瞒,使人民在这种具有极强传染性的疾病流行之时处于危险的不知情状态。为何隐瞒?为了“维护”某些人心目中的那个社会形象,实即为了某些官员的形象,却置人民安危于不顾。党和国家领导人得知,便立即采取行动,坚决地把隐瞒疫情的官员罢免了,坚决地将疫情迅速准确地告诉人民。后者就是以人为本,前者呢?叫做以“社会”为本,实则以官为本。
与以人为本相对立的命题,一则是以官为本,另一则是以物为本。还有所谓神本。以物为本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官为本是封建主义的特征,惟有以人为本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
朱镕基曾痛斥那些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官员,他们明目张胆地为着自己的“形象”和“政绩”,不惜耗费巨额财政、不惜破坏生态,亦即不惜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去打扮自己的“形象”,追逐仕途的“政绩”,这也是典型的站在以人为本对立面的官本位行为。
更不要说在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的大饥荒中大量官员不顾人民死活去编造大丰收的谎言那样的官本位了,但是,历史可以清晰地告诉我们,官本位决不是个别的、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如今,它还深深地相当普遍地存在于教育领域,危害着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
社会本位的思想、观念,还继续深深地潜存于教育学,还侵害着教育理论与实践。
社会是一个中性词,有较好的社会,有不太好的社会。我们需要变革不太好的社会;即使是较好的社会,对其尚存的不完善面还需要去变革。社会何以为好?就看它是否对人民好,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和幸福。社会何以还需要不断变革,就因为还希望它对人民更好,更有利于人的发展和幸福。这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根本,以人为出发点;教育学应当以人为根本,从人出发。若非如此,人们会进一步问:那是谁的教育学?
上述观点中并不存在着把人与社会一般地对立起来的因素,但是,当谈论两者的和谐与统一时,两者并不是半斤八两的,其中,人民是根本,人民不是一个中性词。至于官与民,其和谐与统一应基于什么,相信是更明白了。可是,现实生活却提示:不明白之事之人还多得很。这正是以人为本的思想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原因之一。
三、工具理性为何畅行
打开我们的教育学著作,特别是高等教育学著作,几乎满眼是“制约”、“适应”一类的字眼,说大学是受社会制约的,受政治制约,受经济制约;大学怎么办呢?大学就只有去适应,适应经济,适应政治,适应社会,进而说服务社会,服务经济,服务政治。大学当然就更像是工具。不是说大学培养人吗?人不也就具有工具性了吗?
在那些著作中,偶然有一些可以看到人;而另一些则偶然可以看到人。教育学本应是人的教育学,可是,我们连人都很难看到。教育学即使说到人,也是社会的人,而并非人的社会。教育学有一个分支,叫教育社会学,但教育学并非社会学。那个分支很重要,但也只是一个分支。就像哲学那样,它也有政治哲学、社会哲学这样的分支,但仍只是庞大哲学体系中的分支而已。
我们的教育学是深受哲学影响的,这本身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就受着那种看不见人的哲学的影响,而并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
几乎所有先进的思想家的社会理想都是基于人的。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怎样的理想社会呢?恩格斯回答说:那是“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的发展和发挥他们的全部才能和能力”[10]的社会,那是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11],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12]。与社会的发展相比,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基本原则。这种以人为本、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思想还不鲜明吗?如此鲜明的思想被忽略只是偶然的现象?
那么,我们的教育学论著是以此为基本原则的吗?马克思、恩格斯在人的发展上还用了自由一词,叫自由发展。在我们的教育学论著中有多少自由的字眼。马克思、恩格斯还在自由一词前面加了完全的字样,完全自由这样的词语在我们的教育学论著中能找得到吗?马克思、恩格斯如此看重自由,我们的教育学呢?
我们在以社会为基本时,甚至不问问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什么毛病,不问这个前提就去说为社会服务,为经济服务,为政治服务,而绝少看到经济要为人的发展服务、政治要为人的发展服务之类的话语。人是如此渺小,这样,我们还能指望相应的教育及教育学不渺小吗?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作为目的,而人的发展仅仅是为之服务的工具和手段,这种颠倒,正是教育学需要改造的一个要害所在。要害正在于:以什么为本?而改造之艰难亦在于,造成这种颠倒的工具理性曾是那样的畅行。
四、超越的声音怎样在低旋
以社会为本位的教育学反复叮嘱教育做一个适应者,适应论成为某种教育学的基调。
然而,也有深深关注着人的教育学。8年前,一位学者写道:“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实践活动,它必然具有超越的特性”,“教育的着眼点不在于使人‘接受’、‘适应’已有的,而在于为‘改造’‘超越’的目的而善于利用已有的一切”。[13]这样一篇在中国教育理论界罕见的论文,立即受到了批判。应当说,这种批判本身并无什么问题,更与20余年前的所谓批判有根本的不同。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下,学术批判是学术繁荣的珍贵伙伴,可惜的是,这种批判中止于对超越论的反驳而未能继续深入,亦使人感受到教育超越之声音的微弱。
次年,即有另一论者在同一刊物上撰文,直指上述难得一见的论文,这篇撰文把教育适应论更加系统化,它把教育的基本功能归结为适应,各种各样的适应:“维持性适应”、“动态性适应”、“改造性适应”、“前瞻性适应”。”[14]这种对“适应”的分类在逻辑上的毛病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它进一步强调,解放、革新、创造,都只是“适应的好策略”,解放被解释为“避免太多的束缚”,革新也不过是“调适”,创造则被理解为“主动地去适应”。[15]总之,它十分不愿意为超越留下一点点位置。即使教育改革看来“是历史的趋势,但这种改革决不会因教育的保守性特点而抛弃‘适应性教育’以‘超越性教育’取而代之,而是要强化和实现教育对社会的‘再适应’和‘更好地’适应”。[16]适应论的社会本位观是如此的清晰可见,也如此清澈见底。
后一论者在质疑了前一学者文中关于“超越现实”、“超越现实生产力”等论题之后说:“人的一切社会实践活动也逃脱不了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和社会的客观法则的制约。”[17]这句常见的大话又一次表明,适应论是制约论的派生物。后一论者在十分勉强地提到了超越之后说:“不管我们如何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超越性本能”,“也逃脱不了”“制约”,也逃脱不了社会的“主宰性”。[18]应当说这种社会“主宰性”的观念早已被马克思所批判过(请阅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三节),却仍在教育学中顽强地继续存在着。
那种以“逃脱不了客观法则”的口气说话的人,事实上是在把必然王国的模样竭力描述得十分威严,而自由王国又被描述得遥不可及。因而,他们总不能看到另一面。恩格斯曾说:“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越大”[19]。自由并非总在必然之后,人们更是在自由的前提下把握必然的。自由并不是必然的奴仆,人们正在不断的超越过程中揭开必然的面纱,关于必然王国威严的描述相信不可能阻止人们自由前进的步伐。
1978年,那是一个怎样的“现实生产力”?可是,邓小平超越那个现实,想到了未来的三大战略步骤;1999年那又是一个怎样的高等教育现实,许多人未曾想到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也开始向中国走来;……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包括高等教育事业)超越了人们的想象。全世界的眼光为何注目于中国?因为中国人不只是在适应,因为中国人主要在超越着,超越了西方许多戴着有色眼镜人士的预言。
当适应论把社会看得非常强大的时候,它忘记了这种强大来源于人的强大。当适应论把社会看得十分神奇的时候,它忘记了社会的一切神奇来源于人的神奇。
社会本位论的教育学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有幻想,为什么能异想天开,不知道人的眼睛居然可以“看到”亿万光年之外遥远的星空,不知道人为什么居然也能在纳米尺度下书写文明。
那种不能容纳超越的教育学远离了教育学本应有的品性,它还不需要改造吗?
五、人文课程的地位焉在
为了经济的发展,需要科学课程;为了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课程。还需不需要人文课程?人的发展在教育眼里并不是基本,不是前提,哪还有人文课程的地位?人文课程的遭遇跟教育学的遭遇一样不幸。
没有人的充分发展,如何能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是为了什么?连这样简单的问题,我们也未特别认真地去面对。这是何因何故?
上世纪40年代就有一种说法:世界上的知识只要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还有什么知识呢?没有了!——一种斩钉截铁式的说法。
还有没有人的知识呢?在“人类的一切知识中最有用、但最不完善的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20]。人的知识不仅存在着,而且是最有用又最不完善的,这种观点不只属于卢梭。
人的知识本存在着,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起对人性论持续20余年的批判,在中国社会造成了深深的,至今尚未完全抹去的误解,以为真的就只有两门知识了。我们有中国科学院,实即自然科学院,另外一个就叫做中国社会科学院。我们大学里的学报一般是两个版本,一个叫做自然科学版,另一个便叫做社会科学版。我们的课程也就是两大类,一类是自然课程(或自然科学课程),一类是社会课程(或社会科学课程)。人的课程呢?人文课程呢?人文课程何在?还是人文课程本不在?
语言学算什么课程?逻辑学算什么课程?还有文法、修辞、音乐、美学……这些算是什么课程?
人文课程从两个方面受到了沉重打击:一部分被取消,一部分被变形。于是,人们真的只看见两类课程了。我们不必过多地责怪历史,所需要自问的是:在今天如此宽松的社会条件下,为何还没有充分正视历史,还没有充分意识到人文课程的存在及其地位?
据笔者所触及的范围看,今天已获得了教育学学位的研究生当中,还不清楚什么是人文课程、有哪些人文课程的,决不是少数;而清晰地知道这一点的教学管理者、课程管理者,则更是微乎其微。
人文课程不仅面临课程麻木,也面临课程权力。在课程权力拥有者那里,人文课程地位之脆弱更令人吃惊。由此可见,对于以人为本的理念,在教育和教育学那里,反应是多么的迟钝,多么的可悲。
殊不知,经济越发展,社会越发展,人文课程的地位越将显得重要。物质文明要靠物质生产,精神文明要靠精神生产,而物质生产亦需精神的引导,而所谓精神者,实乃人文精神也。
六、人是什么
本文第一节的标题是“人在哪里”,最后一节则标题“人是什么”。这是密切相关的两个问题,首尾相映,事实上,如果不知道人是什么,就很难知道人在哪里;反之,也有道理。以本文之主题,自然还促使我们问:如果对人是什么还不太清楚,又何以以人为本?
教育是什么?这是人们常议的论题。可是,大都以为,只要弄清了社会是什么,就能弄清教育是什么。然而,如果不清楚人是什么,就既弄不清教育是什么,也弄不清社会是什么。
1984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著的《教育学》,在阐述学生的属性时,第一个论断即“学生是人”[21]。这句话是如此的平凡,好像什么话也没说,可是,这是在历史的沉重中感悟出来的最珍贵的命题。
在那种只是把学生作为工具训练的教育中,学生被视为人了吗?在那种把学生只看做是知识容器而以灌输为基本形式的教育中,学生被视为人了吗?在那种不容纳个性而实际上绞灭学生灵性的教育中,学生被视为人了吗?……“学生是人”,这是对那种徒有教育之名的教育的铿锵有力的回应。
在卢梭直言关于人的知识“最不完善”之后两百多年的今天再说“最不完善”,也许仍不为过。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关于自己的知识一直停滞而未曾增长。
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在观察人、探索人、思考人,伟大的马克思实乃其中最杰出的一位,他对人有许许多多精妙的论述。然而遗憾的是,我们这里,或者是把人大大简约了而没有去注意马克思的那许许多多的精妙论述,或者是因为没有注意那些精妙论述而把人大大简约了。如果半个世纪以前,中国就响亮地喊出“以人为本”,恐怕就不至于不注意了。
我们的教育学说人是社会的产物,可是,马克思却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22]。
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取消美学课程,可是,马克思说:“人也是按照美的规律构造”自己的。[23]因为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并不在意学生构造自己,因而也不在乎给学生以关于美的规律的知识。
我们的教育学家不断地强调教育去适应社会需要,经济的需要,政治的需要,可是,马克思更关注了人的需要,“人有许多需要”,“他们的需要就是他们的本性”。[24]
我们的教育学爱说教学过程(教育过程)是一个认识过程(或特殊的认识过程),可是,马克思说“人有许多需要”,认识需要不会是惟一的需要吧?还有,马克思说人有“多种多样的志趣”[25],教育过程难道不包括意志过程、情感过程以及多种多样志趣发展的过程吗?
我们的教育是那么的呆板和单一,而当我们听到马克思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的特性”[26]的时候,我们难道不因自己在人的知识上的贫乏而感到惭愧吗?
马克思说“人的活动本身”是“对象性活动”[27],人的“生命活动本身”,是“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28]而我们的教育学基本上是主客体分离的,人们感觉到了这种分离生成的许多为我们所欣赏的信条是多么荒谬吗?
马克思说人是“历史的经常前提”,我们的教育史是以人为经常前提的吗?是经常还是有时以其为前提?我们曾曲解了历史并将这些曲解传递给学生了吗?
教育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其所以那样艰难,是因为“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十分艰难。以为“教育是什么”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那多半是由于误以为“人是什么”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问题。相信任何真正伟大的科学家(人文科学家、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惟有在“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不会有他们必然会有的那种高傲。
相信教育学家们会虔诚地看待“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否则,即使我们感到教育学需要改造了,也很难弄清楚如何去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