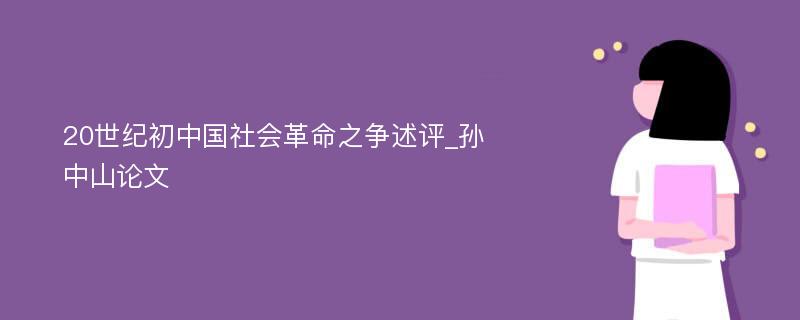
20世纪初中国社会革命之争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之争论文,初中论文,世纪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53(2001)04-0033-09
早在上个世纪初年,正当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刚刚提到议事日程之际,欧洲卢梭、孟德斯鸠以及马克思的学说都以崭新的面貌介绍到中国,让中国知识分子眼花缭乱。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资本主义托拉斯高度发达的产物,当时欧洲的劳资社会危机严重,社会主义革命似乎已提到议事日程。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眼见欧洲社会矛盾的激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主张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初期,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试图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任务毕其功一役,以免将来社会革命之产生。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另一批知识分子,亦眼见欧洲社会劳资矛盾的激化,社会革命在中国将来亦不可免除,但他们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充分发展资本主义,以抵御国际资本的大量入侵,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虽是人类的最高理想,但那是中国将来的事。孙中山、梁启超各执一见,由此产生一场影响深远的论战。论战内容包括中国社会走向的方方面面,诸如革命对象、任务、政体建设及社会经济政策等等方面。本文仅将两派关于社会经济政策和主张,较为详细地重新展示在读者面前,以便寻找中国民主革命曲折的轨迹。
一 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
社会革命之争,即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社会经济纲领之争,革命派提出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立宪派认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政策是不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实际的,而主张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
社会革命之争,盛行于同盟会纲领提出以后。这里先谈谈革命派的民生主义政策。
孙中山伦敦蒙难后,于1896年底至1897年夏秋在英国、加拿大等地,潜心研读和从事著述,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当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已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及私人垄断生产资料的矛盾已很尖锐,一方面是资本家拥有巨额财富,穷奢极欲;另一方面是劳苦群众的贫困潦倒,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西方产生了以马克思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学说,及亨利·乔治(注:亨利·乔治(1839-1897),旧时也译为亨利·佐治,美国经济学家,著有《进步与贫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单税社会主义等经济理论。孙中山鉴于“国家富强”、“民权发达”的西方国家“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和“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于是,“复在民族、民权主义之外”采取民生主义。[1](P6)早在1899年,孙中山在日本同梁启超谈论土地问题时指出:农民苦于沉重的地租,如果实行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而后授以田,直纳若干租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朘削之,则农民可以大苏”。[2](P348)这种“土地国有”及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基本上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当即遭到梁启超的反对。孙中山也就暂时放弃了这种主张,而选定了亨利·乔治的办法,他在与章太炎等人谈及土地问题时,说他“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之单税论”,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经济之改革”。[3](P41)此后,孙中山就采用亨利·乔治及约翰·穆勒(注:约翰·穆勒(1806-1873),英国经济学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学,创造了“平均地权”的办法。1903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造了秘密革命军事学校,其入学誓词中首次完整地规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宗旨。“平均地权”被列入孙中山的革命纲领。他试图通过以“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建立一个没有社会革命危机的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1906年5月《民报》4-5号,相继发表冯自由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及朱执信的《论社会主义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章,对为什么要进行社会革命,为什么要使社会革命并行以及社会革命的方针、办法作了较为具体的说明。
革命派的民生主义,由西方的社会主义一词移植而来,他们常把英文社会主义(Socialism)译为中文民生主义。(注:民意《告非难民生主义者》一文中对“民生主义”一词作了重新解释:“孙中山曰:民生主义一名词,当为Demoslogy而不为Socialism,由理想而见诸实践之意也。”)他们把社会主义区分为科学社会主义及国家社会主义两种,他们主张国家社会主义[4](P434-435),亦称国家民生主义(State Socia-lism)[5](P420)。
为什么要实行民生主义——“社会主义”呢?他们认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产生,是由于贫富不均引起的,贫富不均造成的根源是资本家垄断产生的结果。托拉斯的出现,“遂驱使一般之劳动阶级,而悉厕为大资本家之奴隶,且次第蚕食中等资本家,而使之歼灭无遗。”[5](P425)托拉斯的出现,是资本主义“放任政策”造成的。“不由放任竞争固不得致贫富悬隔也。贫富悬隔,由资本跋扈,不放任竞争,则资本无由跋扈也”,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制”造成的,如果对私有财产制“加相当的限制,则资本无由跋扈”[4](P36)。“托辣斯者,中国未来之大毒物,救治之法,舍实践民生主义末由”[5](P422)。在今日之中国,“绝灭竞争,废除私有财产,或不可即行”,但加以限制则是必要的。社会革命即变不平之制为平,“此其真义也”[4](P436-437),故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以救正贫富不均,而图最大多数之幸福故”[5](P419)。
民生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实行主要企业国有及土地国有。
关于企业国有的要旨,“道在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而次第干涉之”。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凡一切关于公益之权利,皆宜归入国家所有”。“若收回私人可垄断之权利,而使之归公,则其收回事业所得之利益,即不啻全国人共享有之”。[5](P425)但是,他们又声明说:“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夫社会革命,固将以使富平均而利大多数人民为目的”。其进行的方法,将在制度上加以改革,“以至秩序至合理之方法,使富之集积休止。集积既休止矣,由其既已集积者不能一聚不散……散则近平均矣。此社会革命之真谊也。故其进行之时,亦无使富者甚困之理也”。“决无损于今日之富者”。又说,“社会革命,富人所失者为将来可幸致之钜获,而非已集积之富。社会革命固亦行以渐分散已集积之富之策,然分散者,合理的分散,不可言失”。[4](P437,442,443)从上述冯自由、朱执信的发言看,革命派企业国有化政策的主要内容为:凡一切公益事业收归国有,对现有之资本家实行“止富”、“散富”的政策,防止在中国出现托拉斯,达到财富平均的目的。
关于土地国有政策亦即“平均地权,不许私人有土地而已”。“森林矿山及交通机关等,应为国有,无可待言,即都会耕地亦万不可不收为国有。”土地是自然要素,本不应由地主垄断。地主垄断土地,不特使贫民陷于地棘天荆之苦状,抑亦为商工界之一大障碍物,“亦为造成贫富不均及社会革命之一大根源。”国家果能以雷厉风行之政策,“而一旦收回土地家屋于一私人之手,以付之社会公共之所有,则地主之野心逐无从施其伎俩,而土地家屋之价格,于是保其平准,大多数人民乃得脱却地主专制之牢笼,如登春台矣”[4](P427-428)。
怎样实行土地国有呢?胡汉民在《民报之六大主义》中说,中国革命后,“使人民不得有土地所有权”,只能有地上权,永小作权、地役权等,“且是诸权,必得国家许可,无私庸亦无永贷,如是则地主强权将绝迹于支那大陆”,胡汉民解释的是一种“均地”政策,土地“非躬耕,无缘授诸田”,即耕者授其田,但耕者并无土地所有权,是一种没有雇工、没有剥削的自耕自给的小农经济。冯自由对限制地主剥削作了专门解释,他说,“土地国有之制,固非横领强占之谓也”,不是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是采用土地单税法及核定天下地价涨归公的办法,来实现土地国有。冯自由认为,单税法“于各税法中为最善之税法”,国家除征收土地税外,“一切租税俱捐免之”。实行单税制,既可“调和社会上贫富不均之弊害”,促进产业社会生产力之发展,又“单简易行”,收入也有保证。他说:“试观近年来欧美列强之财政收入表,其全国地租(政府所征集及地主所得)之总额,实浮于其岁出之总额多倍。中国诚能实行土地国有之制,则凡地主所得概为国家所有,以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其地租总额之收入,可埒于欧洲全土之地租。一旦得此重大之国用,则政治上社会上充分改良,且旦夕间事耳”,他认为那种行单税地租恐不敷他日政治改革及扩张海陆军备之用之担心是毫无根据的。[4](P430-432)
然则,社会革命何时进行最为合适呢?革命派认为,“民权、民族、民生三大主义而毕其功于一役”,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而且最好的办法是在革命初起时即实行民生主义,“过此则无可实行”,[5](P424)这是因为:
第一,贫富悬殊不大时易行社会革命。冯自由、朱执信说:“中国经济上放任竞争之制虽久行,而贫富今尚不甚悬隔,此由物质进步之迟,大生产事业不兴,而资本掠夺之风不盛,从而无积重难返之患,社会革命之业轻而易举”,如不及早进行社会革命,将来贫富悬殊时再进行社会革命,就更为困难了。[4](P444,437)因为,“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亦不可不行社会革命”。[4](P441)与其将来进行社会革命时困难倍增,不如早行社会革命。
第二,乘政治革命之威力,易行社会革命。冯自由说,中国之实行社会革命,“不可不以武断政治行之”,假使俟共和政府成立之后,再次第举行,必惹起资本家反对,以致“上下制肘”[5](P425),难以进行。革命派认为,他们不在中国实行绝对的共产主义,故不会引起“豪右”富翁的巨大恶感,但“豪右”之抵抗是难免的。朱执信说,“凡对于社会主义为抵抗者,必甚富者始力,而中产户者乃中立无所属而已。西方政治革命之际,彼素封之家,先已望尘畏避,何俟社会革命之驱之耶”?[4](P443)朱执信在解释孙中山“易于行社会革命”的原因时也说:“先生当时语彼实只云政治革命之际,人多去乡里,薄于所有观念,故易行”。[4](P435)即当政治革命时,人们处于患难之中,“乃于公共之利害明,而为一己冀饶获之念不切,故行社会革命于平时者,其抗拒者必多,以与政治革命并行,则抗拒者转寡”。[4](P440)即借政治革命之威力以行社会革命比较容易。
第三,就社会心理上讲,“政治革命时,人心动摇,不羡巨富,于是垄断私利之念薄,而公共安全幸福之说易入于其心也”。[4](P440)即在政治革命时,命大于财,对财产之损失亦在所不惜,易于接受社会革命;而在革命后的和平时期,人们不得不千方百计保护财产,于是拼力反抗社会革命。
第四,当政治革命高潮,必有大多数人参加,“此大多数人之必什九为社会革命运动之主体”,当政治革命胜利进行时,“则同时以其力起社会革命,非甚难事也。”[4](P446)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革命派认为,社会革命必须与政治革命并行,错此时机则难于进行。他们宣布了土地国有及重要企业国有的政策,冲击的对象是“豪右”即大资本家及地主,但到1906年时,这些政策仍然不够明确,甚至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说,社会革命不涉及豪右已集积之富,另一方面又说乘社会革命恐怖及豪右避居乡里之际易行社会革命,这是不是意味着要对豪右已集积的财产进行“散富”呢?“散富”的内容是什么?是否是将铁道、银行、轮船、烟酒等一切“公益之权利”收回为国有。是“赎买”还是没收。如果采“赎买”办法,将不会引起“豪右”之恐惧逃避,如果采取“没收”办法,革命派又一再声明,“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如何理解这个声明,是不是“富民之财产”还是要夺的,只是不“散诸贫民”而归诸国有而已。只有如此解释,才会出现“豪右”畏避革命的设想。
革命派依靠谁来进行社会革命呢?他们冲击的对象是“豪右”即大资产阶级及地主,使中产者“中立”,朱执信宣称,他们依靠的力量“固不纯恃会党”,“而出于细民”,将来成立议会时,贫民议员必占多数,富者居少数。只有平民握权,才能有利于进行社会革命。
革命派主张平均地权,部分企业国有,使富者止富,贫者不贫的社会革命政策,其理论渊源,一方面来自西方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等人的学说;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平均”思想亦有一定的联系。关于孙中山采用亨利·乔治的学说,本文已有多处论及,不再赘述。只将革命派社会革命理论的历史联系略加补充。朱执信在谈到中国速行社会革命之有利条件时说:“中国社会政策于历史上所屡见,不自今日始”。“抑豪者而利细民者,中国自来政策之所尚者也。”[4](P444)冯自由在论到民生主义之根源时说,“抑民生主义之滥觞于中国,盖远在希腊罗马之文明以前矣。三代井田之制,人皆授田百亩,后世以为主治。”“民生主义实为中国数千年前固有之出产物,诚能发其幽光,而参与欧美最近发明之新理,则方之欧美,何多让耶!”[5](P422-423)他又说,满人入关以来,“颁布一条鞭法,纳丁于地,而中国本部之行斯制者,既二百数十年矣。一条鞭法即轩氏(按即亨利·乔治)唱道之单税法,其条理虽有不符,而大旨则无以异。”[5](P430)由此可以充分说明,革命派把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王田”制,“一条鞭法”等,也作为他们“平均地权”,单税制的重要理论根据之一。
经过一段激烈辩论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的内容作了规定性的发言。1906年秋冬间,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第一次对“平均地权”的内容作了重新解释:“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生命者,与众弃之。”[6](P297)12月,他于《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再次申明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必须并行和实行民生主义的必要性,但对民生主义的内容作了规定,他没提到冯自由、朱执信抑制“豪右”企业国有的种种主张,明确指出:“中国现在资本家还没出世”。他讲的民生主义,仅限于平均地权及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及单一税问题。他说,实行了这个办法后,“文明越进,国家越富,一切财政问题断不至难办。”“中国实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孙中山说,总而言之,“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坚持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以为这三样目的达到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6](P327-329)
二 社会革命不能行
以上是革命派关于民生主义政策即社会革命的基本内容。这些政策是在与梁启超论战时阐发出来的,许多言论又是针对梁启超的批评进行的反批评及驳辩。梁反对暴力革命,主张用和平的办法达到政治革命的目的,反对“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帆并张,反对革命派的民生主义及社会经济政策。
梁启超为了反对革命派的社会革命理论及办法,专门写了《社会革命果为今日之必要乎?》(1906年9月)、《再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1907年),全面反对社会革命,认为今日社会革命是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的。
“所谓中国不必行社会革命者何也?”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的情况不同,欧洲自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造成“积重难返之势”,“一将成功万骨枯”,今日欧洲之经济社会正是如此,“军事上一将成功之后,处乎其下者乃永沉九渊而不能以自拔。此富族专制之祸,所以烈于洪水猛兽,而社会革命所以不能不昌也”。今日我国之情况与欧洲不同,我国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中产之家多,而特别富豪之家少”,我国尚无“极贫极富之两阶级存”。欧洲股份公司股东“则旧日少数之豪族也”,中国今日之股东,则多数为“中产”之家。“大股少,而小股多,则分配不期均而自均。将来风气大开,人人知非资本结合不足以获利,举国中产以下之家,悉举以率循而无大轶于旧。则我国经济界之前途,真可以安辔循轨,为发达的进化的,而非为革命的也”。并由“现今的社会以孕育将来社会”。我国经济既可和平发展,目前更无社会危机存在,“所谓不必行社会革命者此也”。[2](P332-339)
“所谓不可行社会革命者何也?”革命派的社会革命论,“以分配为趁均匀为期”,主张在中国抑制“资本家之专横,谋劳动者之利益也”,指责梁启超不该“以奖励资本家为务”,至不惜牺牲劳动者之利益。梁启超指出,行社会革命,此在欧美“诚医群之圣药,而施诸今日之中国,恐利不足以偿其病也”。因为今日欧美各国,“以资本过剩为患”,他们相与“彷徨却顾,临视全球”,争先恐后地争夺中国市场,“世界各国,咸以支那问题为唯一之大问题”,纷纷侵略中国,严重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民只能“结合资本”,利用西方的文明机器,利用我有利之人力物力资源以求利,“则国富可骤进,十年以往,天下莫御矣”。否则若对资本家采取抑制政策,以现在“资本之微微不振,星星不团,不能从事于大事业,而东西各国为经济公例所驱迫,挟其过剩之资本以临我,如洪水之滔天,如猛兽之出押,其将何以御之”。今日“我若无大资本家出现,则将有他国之大资本家入而代之,而彼大资本家既占势以后,则凡无资本者或有资本而不大者,只能宛转瘦死于其脚下,而永无复苏之一日”。“若他国资本势力充满于我国之时,即我四万万同胞为牛马以终古之日”。因此,“我中国欲解决此危险之问题,惟有奖励资本家,使举其所贮者,结合焉,而采百余年来西人所发明之新生产方式以从事于生产,国家珍惜而保护之,使其事业发达以与外抗,使他之资本家闻其风、羡其美、而相率以图结集,从各方面以抵挡外竞之潮流,庶可有济”。
梁启超还认为,从当前国家利益看,面临国际资本的经济侵略,“今日中国所急当研究者,乃生产问题,非分配问题也”,因为“生产问题者,国际竞争问题也,分配问题者,国内竞争问题也。生产问题能解决与否,则国家之存亡系焉”。因此说,分配问题即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虽然是一个“隐祸”,但那是将来的事,“急则治标”,不得不先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分配问题留待以后去解决,所以说,目前,“不可行社会革命者此也”。[2](P339-341)
“所谓中国不能行社会革命者何?也”中国社会发展之条件尚未成熟。今有人“倡社会革命者之言,谓欧美所以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者,因为未能解决土地问题,若一但解决土地问题,则社会问题即全部问题解决者然”。梁启超指出,这种看法是“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也。近世最圆满之社会革命论,其最大宗旨是列举生产机关(按指生产资料)而归诸国有”,不仅土地归国有,资本亦归诸国有。而欧美社会分配不均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生产机关”私有所决定的。至于地价所腾涨,“亦资本膨胀之结果”。因此,欲解决社会问题,“当以解决资本问题为第一义,以解决土地问题为第二义”。他认为,只有资本、土地皆由国家所有,那才是社会主义的最大宗旨,若能如此,当然是一件好事。如现在私有之“经济社会”制度,工人劳动的结果,“地主攫其若干焉,资本家攫其若干焉,而劳动者所得,乃不及什之一”。若革命后实行社会主义政策,“劳动之结果,虽割其一部分以与国家,而所自得之一部分,其分量必有以逾于今日。且国家割我之一部分,亦还为社会用,实则还为我用而已。如此则分配极均,而世界将底于大同。此社会革命之真精神,而吾昔所谓认此主义为将来世界最高尚美妙之主义者,良以此也”。但要实现社会主义,尚有许多困难,以文明如此发达之欧美,还有许多问题“未尽解决”,更何况文明及生产如此落后之中国。所以说,“中国尚不能行社会革命”。[2](P341-343)
从梁启超的以上论述看,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高尚美妙之主义,将来必同底于大同,而当时的中国,尚无条件实行社会主义,说明他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社会革命;再则,他对当时国际国内经济状况的分析,指出当时中国必须发展资本主义,否则,永无富强之日。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历史的发展必然呈现阶段性,既看到将来又看到目前,才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那种力排众议坚决反对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提前办,更是有胆略的政治家。革命派混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把资本主义发达后才能实行的社会革命,提前到封建主义极其严重的时候,欲将资产阶级革命及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不说是空想、盲动、急躁,结果一事无成。反对封建主义不彻底,亦未促进资本主义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革命派的平均地权即土地国有政策,试图通过核定地价及单一税的办法来实现。对此,梁启超也提出了种种质疑。
关于“核定地价”“涨价归公”及“照价收买”的问题,梁启超问道:核定地价后,土地可否买卖呢?政府照价收买,是在“核定地价时随时收买之”,还是“定地价后迟至又久方收买之?”土地收归国有后不能买卖只能出租,如果没有买卖、没有交换,土地即无价格可言,因为价格是在交换中实现的。如果土地不可买卖,土地没有价格和价格浮动,国家又依何标准而收取地租呢?如何实行涨价归公呢?如果官吏任意对土地估价以收租,民必不服;若在交换中估价,谁出高价则将土地租给谁。这样,就会出现“必有资本者乃能向国家租地,其无资本者无立锥如故也;又必有大资本者,乃能租得广大之面积良好之地段”,而小资本者则必然被排挤到偏僻之角落。如此,“则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之势,何尝用土地国有而能免也”。因此,梁启超说,核定地价、涨价归公的办法,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为财政开一新纪元”是说得通的,但“若绳以社会主义所以均少数人利益于多数之本旨,则风马牛不相及也”。[2](P346-348)
革命派说:“吾人社会革命之政策,为土地国有,土地国有之办法,为定价收买”。[7](P708)如何定价收归国有呢?梁启超猜测“其代价必以现金或以公债,要之皆有偿也”。他问道,《民报》所持土地国有论,能出现金以收归国有吗?他说,《民报》“第十号云,‘地主有土地值一千元,可定价一千至二千’。其第十二号云,‘普通地代(租)之价格为六元,则其地价为百元’。又云,‘中国现实地代总额有八十万万’,合彼报此三条以会通之,则全国值八十万万(按为地租)之地,其原地价应值一千三百万万余”。若土地以价值一千元的原价购买,地主必不同意,政府则加价或至二千元购买。如此,“其原价既为一千三百万有奇,倍价以购之,则当为二千六百万万有奇”,政府能拿出如此巨额之现金以偿地主吗?如无现金,必付之以公债证书。然公债又需付息,“国家负二千六百余万万之公债,以五厘利息起算,则每年应派息一百三十万万余。而政府土地单税所入不过八十万万”,所入不敷地价之利息,如此巨债,必偿还无期,“此项公债证书,必无复一钱之价值”。如此,“彼大地主之损失姑无论,而小地主之自耕其田者,畴昔不须纳地代(租),故足以自给,今则与无田者等,同须纳地代于政府”。他们仅挟一不可兑现之公债证书,前此勤俭贮蓄所得之结果,遂付诸东流。“此等政策,欲不名为掠夺政策安可得也”。
梁启超主张部分土地公有,反对将土地一律收归国有,他认为土地一律国有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公平的。他提出把土地分为邑地与野地,自由地与有主地。邑地即城市土地,包括铁路沿线及具有独占性质森林,矿山等的土地应收归国有,本部新垦及淤增土地应归国有,地广人稀之边疆未经垦辟之自由地应归国有。至于广大农村野地、有主地不应归国有。特别不应将耕农的土地收归国有,“就一般农民心理论之”,“不希望土地私有制之废止”。[8](P25,31,33-34)他说,在现金交易的经济制度之下,“人人皆以欲得财产所有权为目的”,如一旦剥夺个人之土地所有权,即将财产所有权的主要部分被剥夺,致使“个人勤勉殖富的动机将减去泰半”。[8](P24)
梁启超认为,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土地、企业都应国有,仅宣布土地国有是不公平、不全面的,土地一律公有也是难坚持的。他说:从中国及法国古代历史看,几度实行土地王有、公有,集中以后,不能持久,故“法国独多小地主”。[8](P28)革命派认为,“土地国有者,法定而归国有者也”。梁则提出,土地既为法定国有,又何必照价收买呢?革命派还认为,国家惟定地价,而不必继受私人之所有权,私人仍许世袭其固有之土地以收租,惟所收租额,有逾于法定价格之外者,则以归国家。梁启超建议,既然让地主世袭继承,何必“付此买地之代价”,而使国家负此莫大之国债呢?[8](P15)
革命派把土地单税制作为重要财政政策,梁启超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中,列举了三十三条行不通的理由。事实上,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多样性,决不是一种捐税所能包括无遗的,也不是一种捐税所能解决财政问题的,所以现代各国都不用单一税制而用复税制。因此,梁认为,中国绝不能用土地单税制,而应用复税制,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证他的观点。
梁启超具体估算了土地单一税收入的数目,远远不能满足如此庞大中国之财政支出。他说,实行土地单一税,收入也极不稳定,无保障,如地价不稳定,天灾影响,战争爆发后人民不租地怎么办?再说,海关关税不收,国内产业如何保护。治财政学者人人皆知,全国人民,“无论居何阶级,执何职业者,皆自然负担租税之义务”。单要土地所有者担负租税,是极不合理的。
梁启超对革命派所定地租收取标准尤为不满。革命派主张:“国有土地之后,必求地力之尽,则如小农分耕之,可获四分者,以为标准,而收其半或三分之一以为租”。[7](P205)梁启超指出,以农民土地所获一半或三分之一交纳国家,“真可谓奇悍之谈”。他以广东农民交与地主之地租为例说:“每亩岁可产米八石,每担值银二两四钱,则一亩之总收入为十九两二钱,而此等地之地代(租),约岁值四两,不过总收入五分之一耳”。[8](P37-38)如按革命派所定地租标准,昔日之佃农以四两之地租交于地主,“今以土地国有故,忽须纳十两或七两之地代(租)于国家,其谁能堪也”,特别是自耕农,“忽被国家掠夺岁入之半或三分之一,其苦痛自无待言。”[8](P39)梁启超指出,这种“重课地税之政策”,不仅不能“保护小农”,“实并小农而困之也”。[8](P43)
至于“大农”与“小农”何者为优的问题,革命派认为,“美国用机器之大农,与欧洲小农所耕之地,每亩而衡之,则美农之所获,不过欧农四分之一”。小农的产量多,交的租也多,大农之经营,“无利而有损”,故中国“资本国有之制行,而不患资本家之垄断农业”。[7](P705-706)认为小农优于大农,故不发展大农。梁则指出,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由此而得出排斥大农的结论,更为武断。梁说,办大农业需要有一定的条件,如适当的人才及资本、设备。只要这些条件具备,大农则优于小农。大农“能以种种设备,以从事于农业改良,而小农得资为模范,令全国农业也随而进步,其造福于社会,更不可量。故善谋国者,一面当保护小农,全其独立,一面仍当奖励大农,助其进步。实可以并行不悖,并不矛盾”。[8](P43)
三 发展资本与节制资本之争
革命派认为,应该抑制国内中产阶级及“豪右”的发展,主张外资多多输入,以便使中国富强。于是,在外资输入问题及如何对待国内资本家问题上,两派也展开激烈争论。
对于“资本”问题,梁启超早就主张外资输入,但输入的外资应用于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如此,则有利于我国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他又坚持主张保护及奖励我国资本家发展生产,与外资竞争,实行保护关税,以抵抗外资入侵。
革命派一再指责梁启超对待“资本”的政策,就是奖励资本家排斥外资的政策,是“主张奖励资本家,使与社会主义反对”,[7](P676)说梁主张的“保护贸易”,即“抵排外资之政策”。[7](P678)革命派“主张之社会主义”,“以国家之资力,足以开放一国之重要利源”,“不必奖励资本家,尤不必望国中绝大资本家出现”。[7](P679)革命派归纳两派的基本政策时指出,“奖励国内资本家,以抵制外资输入,其结果不能抵制,而徒生社会贫富阶级者,梁氏之政策也。以中国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则外资输入有利无损者。吾人所持之政策也”。[7](P680)因此,革命派大力主张外资输入,他们说外资输入有种种好处:
(一)“外资之输入,其初以补助本国资本力之不足,而产业既发达,则自身之资本,弥满充实于全国而有余,此殆以自然之进步为之,而非恃奖励资本家政策所能望。”[7](P679-680)
(二)又如外资输入,修筑西蜀夔峡水电站,“可供吾国东南诸省所有通都大邑一切制造机器之用”。然该公司之经营可能出现亏损之结果,“以供给过于需要,或作始过巨,而后无以为偿,势遂不自支,倾折而去乎?则此大资本家之资本,大半落于吾国人之手,其于我固利,兹事犹不成问题。”[7](P681-682)
(三)外资输入,会使我资本增殖,如“夔峡公司者,于我国能造成可发生几亿万马力之电机,即增长我国以可发生几亿万马力之生产额也。而为用于社会,可得减省其消费额之半,故直接间接,而皆使我资本增殖也”。“外资输入,而中国不怠于生产,则外国之资本,与国内之资本,其量乃真同时而进耳。”[7](P681,682,684)
(四)再从分配上看,革命派把外资企业利润的分配分为四个部分,即地租、工资、利子、利润。如此,利润分配如下,工资为中国工人所得,地租为中国政府所得,利润可能为中国经营者所得,外国资本家仅得利子一项。“其财货分配之所得,我实有其二分又半,而外国人则有其一分又半也。”[7](P683-684)
(五)土地归国有,外国人只能租地经营,“期满而契约解除,所营建大抵归诸我国家”,“纵令外人投资几何,何害于我”?[7](P699)外资输入愈多,愈能使中国富强。
梁启超坚决反对革命派抑制国内资本家的政策,指出革命派外资输入政策的严重不良后果。他说:“今日乃经济上国际竞争你死我活一大关头,我若无大资本家起,则他国资本家将相率蚕食我市场,而使我无以自存。夫所谓蚕食我市场者,非必其收我土地,建工场于我国中而使能然也”。“现在各国制造品之输入我国者,滔滔若注巨壑”,今后更将“挟托辣斯巨灵之掌,以与我殊死战”,我若不急谋支持资本家发展生产,则“全国人民,乃不得不帖服于异族鞭箠之下以糊其口”。今日我若能“鼓吹人民爱国心”,大力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闯过此难关,乃可以自立于世界”,所以那种“惟资本家独占利益是惧,鳃鳃然思所以遏抑之”的政策是十分错误的。其结果,只能“遏抑国内之资本家使不起,不能遏抑国外之资本家使不来”。[2](P341-345)梁启超指出,如按照革命派遏抑国内资本家而让外资大量输入,中国必陷入今日印度之境地。今日印度外资充斥,“其生计现象何如?”其社会问题不仅未解决[2](P345-346),而且更为严重。
应该指出,从当时中国的实际出发,梁启超主张在引进外资用于生产事业的同时,积极奖励保护民族资本家并力外竞的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反映了当时中国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本要求。革命派试图通过采取抑制中国大资本家的产生以预防将来社会问题之爆发,既是违背中国历史发展要求,又是一种主观的幻想,难道外资输入越多,就能使中国贫者变富吗?能够避免社会问题之发生吗?同时革命派对外资输入好处的种种设想,也未免过于浪漫。把外国资本家想象得过于简单,会因企业不支,轻易“倾折而去”,中国竟可坐收其利。在抑制民族资本家,或没有强大民族经济为后盾的情况下,他们对国际资本输入的危害,还缺乏必要的认识。
关于革命派对重要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梁启超说,他是“极表同情”的[8](P9)。赞成部分企业国有,但不能急于求成,不能说当新政府成立之初,即收土地国有,同时又举一国之最大企业为国家专办。实行企业国有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他引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耶氏所著《公企业》及英国《经济杂志》所载巴突博士《论英国公企业》等书文的论证,说明企业国有化后出现的六大弊端。1870年伦敦市电车、铁道、电灯等公用企业相继收归市有管理,垄断了各该行业,出现了一些弊病,如“技术上之发明改良,大生阻害”;禁止私人投资于电车等行业,而市营经济又不可能大力发展,以致“阻碍该产业的发展”;“市营企业之使用人增多,其影响及于市政”;“市有市营,比诸私营企业家之经营,其滥费殊多”;“缘此而市债之增加,市税之增征,在所不免”等等。梁接着说:“就耶、巴两氏之说合观之,虽在文明胎祖之英国,而以公共团体代私人之企业,其利之不胜其弊也”。[8](P52-53)如在中国举办国营企业,为了防止一些弊病的出现,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英国、德国、日本诸国先将铁道等企业委诸私办,等条件成熟后再收归国有。中国亦应如此,应等待条件之成熟。梁认为,这些条件是:第一,“待国中谙练技术之人渐多”,政府得选拔任用,以减少失败;第二,“待国中教育较高,人民公德心渐发”,使官吏认真负责,“舞弊不至太甚”;第三,“待国中法律大备”,官吏与人民皆知遵法守法,官吏如欲舞弊,制裁较易。[8](P10)
再从政治上说,条件不具备,过早地实行企业国有,必造成不良之影响。梁说:“以英国政体之良,然以公有企业膨胀之故,犹助长公吏之专横,驯致政界之腐败。况中国现在人民程度远不逮英,而新政府草创之际,无论如何,而法律未能遽臻完密,一旦举全国重要之生产事业,悉委诸官吏之手,则官吏之权力,必更畸重,人民无施监督之途。而所谓民主专制之恶现象,遂终不可得避,则其危及政体之基础,当更有不可思议者矣。”[8](P54-55)
为什么对国营企业官吏职员要求要有较高的文化技术及人民公德心呢?如无技术文化、无“公德心”,就不可能办好国营企业,求得发展。否则不如私营企业。梁说,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起于“财务归于自己支配之欲望”,“经济动机实以营利”为目的。“私人之企业家为此营利之一念所驱,故能累发明以发明,重改良以改良,冒险前进,有加无已。若大公共团体之企业,则公吏之执行庶务者,虽缘该事业发达之故而获大利,其利不归于己。反之,若缘冒险而致失败,则受行政上之责任,而己之地位将危,故为公吏者,常横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之心,而精神恒倾于保守而乏进取”。这是公有企业常常不如私有企业经营好的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梁启超在《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中指出,在目前国有企业尚无条件骤然组成时,如不鼓励私人大企业之发展,不仅铁路、电车、电灯等独占事业不能发展,即大型的非独占企业如煤油、钢铁等也无法发展,故从“国民经济全体”出发,鼓励私有企业的发展,是必要的。
在社会革命之争中,革命派认为,社会主义在中国应及早进行,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愈利于实行。梁则认为,目前主要任务应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是将来的事;革命派坚持平均地权、核定地价、照价收买及土地单一税的办法,由此而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梁同意部分土地国有,反对一切土地归国有,指出核定地价、照价收买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建议不必照价收买,以免负此巨大国债,建议否定土地单一税,而采用复税制;革命派主张抑制资本发展,不许私人垄断资本出现,梁则主张奖励资本家,允许私人垄断资本出现;在对待外资输入上,革命派主张自由开放,梁主张采取保护贸易;在农业问题上,革命派主张发展小农,制止农业资本家出现。梁则主张保护小农与奖励大农相结合。
在论争中,梁启超虽然亦有出言不逊之词,革命派亦指责梁“全不知社会革命之真”,对“民生主义毫无所知”,梁指责革命派“四不像的民生主义”对“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之区别认识不清。梁坦率地承认,他目前不赞成社会主义,而绝对同情于社会改良主义。[2](P357)他对革命派所提出的种种批评和建议,不无可取之处。说得确切些,梁启超的建议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客观现实的要求,是比较合实际的。
梁启超公开打出社会改良主义的旗号。他说欧洲社会问题严重,各国政治家及至学者,纷纷研究救治之方,出现许多派别,主要有两派:一派是俾斯麦实行的“社会改良主义”,“即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加以矫正者也”;一派是马克思所倡率的“社会革命主义派”,“即不承认现在之社会组织而欲破坏之以再谋建设者也”。“两者易于混同,而性质大相反”。他明确表示他赞成社会改良主义。[2](P356-357)他把这种社会改良主义称为“国家社会主义”。他说:“国家社会主义,以极专制之组织,行极平等之精神,于中国历史上性质,颇有奇异之契合也。以土地尽归于国家,其说虽万不可行,若夫各种大事业,如铁路矿务各种制造之类,其大部分归于国有。若中国人,则办此真较易于欧美”。[9](P42)
社会改良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梁启超说:“条理多端,不能尽述,略举其概:
“一、铁道、市街、电车电灯、煤灯、自来水等事业皆归诸国有或市有。其事业之带独占性质者,其利益不为少数人所专有。
“二、制定各种产业组合法,则小资本者及无资本者,皆得自行从事于生产事业。
“三、制定工场条例,则资本家不能虐待劳动者,而妇女儿童,尤得相当之保护。
“四、制定各种强制保险法,则民之失业或老端正者,皆有以为养。
“五、特置种种贮蓄机关,予人民以贮蓄之方便,则小资本家必日增。
“六、以累进率行所得税及遗产税,则泰富者常损其余量以责于公矣。”
梁说:“我国现在之社会组织,既已小资本家多而大资本家少”,将来生产方法按照上述设想改进以后,“大资本家之资本与小资本家之资本,其量同时并进,固已不至奔轶太远,造成如欧美今日积重难返之势”。他还说,欧洲工业革命后,社会革命使不能不出现者,是由于亚当·期密自由放任学说,助长其竞争之焰,故而造成惨剧。今日我国在“生产方法改良之始”,即在利用机器生产的同时,“鉴于放任之弊”,采用社会改良主义,就可避免欧美出现的社会问题。他十分自得地说:“我以本质较良的社会,而采行先事豫防之方针,则彼圆满社会主义家所希望之黄金世界,虽未可期,而现在欧美社会阴风惨雨之气象,其迹可以免矣。”[2](P358)
在社会经济政策上,革命派以“平均地权”的方法来防止社会革命,用限制资本特别是大资本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梁则主张奖励中小企业发展,用累进税办法限制大企业主之所获,防止贫富不均,防止社会革命。他们两者的共同点是实行部分企业国有,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贫富不均,防止社会革命,但二者都未提出解决工人阶级贫困的办法。梁公开反对“夺富民之田为己有”的平均地权政策,革命派不仅否认“夺富民之田为己有”,更未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办法,两者都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从他们的主观愿望看,都是同情社会主义的。这是孙中山、梁启超二人社会经济政策的某些共同之处。
但是,他们的理论基础和经济政策又是根本不同的。梁启超认为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是两个不同社会阶段的任务,必须分阶段逐步进行。在民主革命时期,必须充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只是对少数垄断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企业归诸国有,矿山及无主土地归国家经营,让中国资本主义得到充分发展,以便在与国际资本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同时逐步实行社会改良,以便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梁启超的这种社会发展理论,既坚持了社会发展的渐进性和阶段论,又没有忘记社会将来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代表了中国时代要求的主流,无疑是比较正确的。而孙中山一派坚持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无疑是混淆了两个不同时期的革命任务,脱离了时代的要求,是一种典型的激进主义狂想。
在甲午惨败后的中国志士仁人,受西方侵略的刺激和侮辱太深,救国心切;同时,也极其羡慕欧洲民主富强,急于振兴中华,并欲驾西方之上而后快。因此,一急再急,激进思潮总是占上风,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流。“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以及后来的“大跃进”、“超英赶美”,形成这种激流的最高峰。超前构想给中国带来超常灾难,这是近代中国历史最为沉痛的教训。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00年的理论、不能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改革力度速度与社会承受力关系的理论等等,这是对我国国情作了深刻而全面研究后作出的总结,是对我国人民近百年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纠正了我国人民长期以来求强求富求民主的急躁心情,从而迈向稳步建设的新时代。
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真实再现于今日书卷,并加以科学的评价。只有具有科学性,才能给后人以可信的借鉴。这是古为今用的真实意义。以史为鉴,鉴者镜也,如果史学家制作的镜子凹凸不平,是一面哈哈镜,反映的历史则面目全非,导致荒唐之事知多少,历史学家帮了不少倒忙;如批判梁启超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渐进论,鼓吹历史飞跃论,以至酿成历史性灾难。只有这面历史的镜子接近于水平面时,才能比较如实地反映真实,由此才能给后人以可靠的启迪、借鉴,不致发生误导。文后余言,望共勉!
收稿日期:2001-03-02
标签:孙中山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社会论文; 历史论文; 地主阶级论文; 土地政策论文; 梁启超论文; 民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