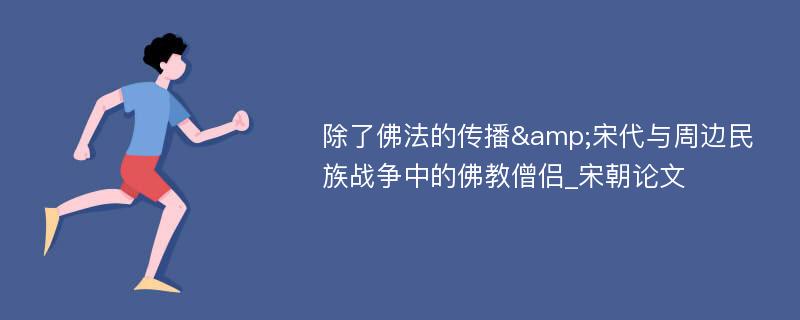
传法之外:宋朝与周边民族战争中的佛寺僧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僧侣论文,佛寺论文,宋朝论文,民族论文,战争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0—13世纪,东亚大陆陷入大分裂局面,宋、辽、西夏、金、蒙元、大理、交趾以及西南诸蛮、西北诸蕃并存或相继而立。就整个东亚大陆来说,当时各个民族最显著的共同点无疑是普遍崇奉佛教。①正因为如此,佛寺及其僧侣在当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僧侣成为各个民族间友好交往的最佳使者。②但同时,因为佛寺及其僧侣在各个民族政治、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中,佛寺及其僧侣也不同程度地成为战争的工具和倚重力量。历来研究宋代佛教,关注点多集中在佛教教义与佛教文化、佛寺经济与阶级属性、社会慈善事业与公共工程等方面,而对佛教与战争则很少关注,鉴于此,本文就宋朝与周边民族战争中的佛寺僧侣问题略加阐释。 一 佛寺成为开疆拓土的重要军事、情报基地,僧侣成为开疆拓土的最佳说客 宋朝开疆拓土以神宗熙宁开边最为典型。开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一是荆湖南路的梅山(今湖南雪峰山)以及荆湖北路的沅靖地区,即今天湖南省的中西部,二是秦凤路的熙河地区,即今天甘肃省的中南部。③湖南方面,熙宁五年(1072),章惇受命开梅山,六年(1073),以上梅山地区设新化县(治今湖南新化),属邵州(治今湖南邵阳),以下梅山地区置安化县(治今湖南安化),属潭州(今湖南长沙);熙宁七年(1074),收复溪峒黔、衡、古、显、叙、峡、中胜、富、赢、绣、允、云、洽、俄、奖、晃、波、宜等州,以其地置沅州(治今湖南怀化);熙宁九年(1076),收复溪洞诚州,后改名为靖州(治今湖南靖县)。甘肃方面,熙宁五年,王韶受命开熙河,同年,复置熙州(治今甘肃临洮);熙宁六年,先后复置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岷州(治今甘肃岷县)。 (一)湖南方面 北宋中前期,梅山、沅靖地区为瑶人所占据,溪洞林立,未入宋朝版图。“瑶人笃信佛法”,④早在仁宗天圣二年(1024),知溪洞古州向光普就曾创佛寺一座,⑤因此,在湖南开边的过程中,宋朝十分注意借重佛寺和僧侣的力量。 1.以佛寺为军事、情报基地 章惇开梅山,取道宁乡,入沩山,转由小路进兵,失利,退军沩山密印禅寺,“馈饷缺乏,寺僧为供应。”⑥诚(靖)州收复后,为进一步打通南下融州(治今广西融水)的通道,将湘西与桂西北连成一体,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知州吴天常建言:“自诚州抵融州道新通,请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择僧知蛮情者居之,诸蛮信佛,平时可使入蛮与之习熟,有警可用以间谍,而佛舍可因以储粮,其利边甚大。”⑦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诚州南至本州界一百八十里,自界首至融州四百八十里,⑧即使仅计算诚州段,按每三十里建一佛寺,也至少建有六座佛寺。佛寺“利边甚大”,在新占领区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僧侣平时可利用蛮人信佛的心理,从信仰和心理上拉拢蛮人,战时则可以提供情报服务(“有警可用以间谍”),而佛寺则成为军事基地(“佛舍可因以储粮”)。 2.以僧侣为说客 在刚进入梅山时,由于军事失利,章惇派人入峒招谕,不从,鉴于“瑶人笃信佛法”,于是改派密印禅寺长老颍诠等三人入峒游说。经过颍诠等人的“说法”劝谕,此支溪洞首领遂“悔悟”,率众出降。后来,为表彰密印禅寺在供给军饷和说降蛮人中的贡献,章惇在奏凯时特为密印禅寺请免各类科差。⑨或许是受到颍诠等人说降成功的启发,在后来的开边进程中,章惇有意招纳一些名僧随军前往,如开梅山中的绍铣。绍铣,潭州兴化禅寺主持“有度量,牧千众如数一二三四”,极善引诱俗人信佛入教,“长沙俗朴质,初未知饭僧供佛之利,铣作大会以诱之,恣道俗赴谓之结缘斋”,“其后效而作者,月月有之”。⑩绍铣的传法劝化为其赢得了众多的信徒,“荆湖人号为古佛”,(11)连蛮人都尊崇之,“湖之民向仰之笃,波及蛮俗”。鉴于绍铣在蛮族信仰中的影响力,章惇特意“与铣偕往”。绍铣也为梅山的成功开拓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蛮父老闻铣名,钦重爱恋,人人合爪,听其约束,不敢违,梅山平,铣有力焉”。(12) 梅山平后,章惇进一步经略沅靖地区,“或云蛮人多行南法,畏符箓”,而越州僧愿成“能为符箓禁咒”,遂偕成前往。章惇至辰州,遣张裕、愿成等人入溪洞受降。未想张裕等人秽乱当地妇女,该族首领田元猛不胜其愤,尽缚来使,刳斩于柱。愿成边打自己的脸边哀求,田元猛“素事佛”,乃不杀,押而遣之。愿成不以为耻,“更乘大马拥檛斧以自从,称察访大师,犹以入洞之劳,得紫衣师号”。(13)或许是因为张裕等人的“秽乱”行为惹怒了蛮族首领,这次游说以失败告终,章惇“知群蛮终不可以说下”,“即三路进兵,诛荡平之”。(14) (二)甘肃方面 北宋中前期,熙河地区由吐蕃诸部占据,亦未入宋朝版图。吐蕃“最重佛法,居者皆板屋,惟以瓦屋处佛”,(15)“城中之屋,佛舍居半”,“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之丽(罹)法,无不免者”,(16)已基本形成政教合一的统治体制。(17)鉴于此,在开熙河的过程中,宋朝更加注意借重佛寺和僧侣的力量。按常理,在熙河地区,宋朝也会借用佛寺作为军事、情报基地,但由于史料的缺失,目前尚未见有这方面的记载,兹仅就以僧侣为说客的情况加以申述。 相对于湖南蛮族,吐蕃的佛教信仰无疑更加地深刻,不仅信佛,而且有精深的佛学思想,因此,在征服吐蕃诸部时,宋朝显然不能派遣一般的僧侣作为说客,必须是成名高僧才可足以服蕃人之心。对于此说客人选,宋朝最终选中的是高僧智缘。智缘,北宋名僧,《宋史》有传(18),不仅佛学精深,而且医术高明,擅长把脉看相,“京师士大夫争造之”,与王安石、王珪等名公大臣关系甚密。王韶开边,因吐蕃部族首领董氊、木征等多与僧人亲善,而僧结吴叱腊主部帐甚众,故请与智缘一同至边。(19)智缘能言善辩,以“经略大师”身份“径入蕃中”,成功地说服僧结吴叱腊所属部族以及俞龙珂、禹藏讷令支等部族归顺。(20)当然,也不是每次说降都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有时,智缘前脚游说,宋方武装后脚即随之而来,如木征,王韶遣智缘往说之,“啖以厚利,因随以兵”。(21)智缘的行为事实上已使佛教成为“殖民”的工具。 正因为吐蕃诸部“重僧”,“人好诵经,不甚斗争”,给智缘提供了绝佳的游说环境,因此,当时就有人感叹,王韶之取熙河,“其实易与耳”。(22) 二 佛寺及其僧侣是战后新占领区统治的重要倚重力量 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23),“因俗立教”,“诱化其心”(24),对于不崇尚儒家文化的新占领区来说,佛寺及其僧侣或许是武力之外安定新区最重要的倚重力量,正如岷州《广仁禅院碑》所记载,“王师既开西疆,郡县皆复,名山大川,悉在封内。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复,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25)正因为如此,宋朝在新占领区采取了大规模兴建佛寺的政策。 (一)湖南方面 宋朝平定梅山蛮后,以下梅山设置安化县,知县毛渐谓瑶人畏果报之说,“因俗立教,创五寺以诱化其心,苗瑶始服”。(26)毛渐的思维和安蛮政策代表了湖南当时新占领区官员一般的思维和政策。正是在这些官员的扶持下,佛寺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遍布新占领区。 潭州之安化县:(1)启宁寺,在县东南,熙宁间,上、下梅山各建佛寺,以“熙”“宁”字分名,新化建承熙寺,安化建启宁寺;(27)(2)崇福寺,在县北七十里浮泥山,熙宁中建;(28)(3)报恩寺,在县治西,僧恺禅建。(29)据[光绪]《湖南通志》记载,章惇开梅山后,曾向朝廷为密印禅寺请赐寺名“报恩”,(30)但据释觉范崇宁中所写《潭州大沩山中兴记》,密印禅寺并未曾更名“报恩”,(31)因此,章惇所请“报恩”寺名很可能就是僧恺禅新建寺之寺名。(4)—(8)五寺,熙宁年间知县毛渐所建,但五座寺庙的名称已不可考,是否包括启宁寺、崇福寺、报恩寺也不得而知。 邵州之新化县:(1)承熙寺,在县南,熙宁中建;(32)(2)感化寺,在莳竹县上里堡,元丰中建。(33) 沅州:(1)报恩寺,在州城西南隅,熙宁中建。(34)(2)普明寺,在黔阳县东龙标山,熙宁中建;(35)(3)归化寺,在黔阳县西,熙宁中建;(36)(4)净化寺,在黔阳县西南,熙宁中建;(37)(5)天柱寺,在黔阳县东六十五里崖山,熙宁中建;(38)(6)同天寺,在麻阳县西,熙宁间建(39),在当地建筑物中格外醒目,“官舍民居类皆茅茨板屋,上漏旁穿,独同天僧舍,穹堂奥殿,楼阁环杰,门庑深邃”。(40) 靖州:(1)静化寺,在大步山,元丰中建;(41)(2)怀化寺,在古融城,元丰中建。(42)另据上文所述,自靖(诚)州至融州,“每三十里建一佛寺”,则靖(诚)州境内至少建有六座佛寺,远不止两座。 (二)甘肃方面 宋朝收复熙河地区后,“惟是人物之未阜,思所以繁庶之理;风俗之未复,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乃敕数州皆建佛寺”(43)。“敕”,即以皇帝的名义下令,表明在熙河地区兴建佛寺是宋朝的国家战略。 熙州:(1)大威德禅院,熙宁五年,赐秦凤路缘边安抚司钱一万缗,于镇洮军(熙州)建僧寺,以大威德禅院为额;(44)(2)东山(慈云)禅院,熙宁六年,赐熙州新修东山禅院名曰慈云;(43)(3)东湖(慧日)禅院,熙宁六年,赐熙州东湖禅院名曰慧日。(46) 河州:(1)广德禅院,熙宁六年,诏河州德广禅院(47)岁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48)(2)慈济寺,元丰元年(1078),“河州请以城东北隅附山不食之地二顷作墓园,瘗蕃汉阵亡暴骸,已择僧看管修葺,乞赐院额”,“从之,仍以慈济为额”(49)。 岷州:熙宁七年,赐岷州新置寺名曰广仁禅院,仍给官田五顷,岁度僧一人。(50) 上述佛寺中,唯有岷州广仁禅院有始创碑记传世,兹节录于下: ……岷州之寺曰广仁禅院。于是,守臣为之力,哲僧为之干,酋豪为之助,虽经历累岁而数百区之盛若一旦而就…… 初,岷州之复也,诏以秦州长道、大潭二县隶之。长道有僧曰海渊,居汉源之骨谷,其道信于一方,远近归慕者众。州乃迎海渊以主其事,其道勤身以率下,爱人而及物,始至则程其力之所及,必使力胜其事;事足其日,又有药病咒水之术,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 ……又得佛宫塔庙以壮其城邑,凡言阜人物,变风俗者,信无以过此也。 西羌之俗,自知佛教,每计其部人之多寡,推择其可奉佛者使为之……虽然,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非中土之教为之开示提防而导其本心,则其精诚直质且不知自有也。 《传》曰:用夏变夷,信哉其言乎。恭惟圣主之服远也,不以羁縻恍忽之道待其人,必全以中国法教驭之……知佛而不知戒,则塔庙尊严以示之。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余,必世而后仁,尽在于是矣。(51) 从广仁禅院的创建经历可以看出,宋朝对在新领占领区建设佛寺可谓不遗余力。朝廷拟定寺院的名称(“广仁禅院”)和规模(“岁度僧一人”),并提供寺院的日常开销(“给官田五顷”);地方政府负责具体的建设(“守臣为之力”),并负责遴选有道高僧(“海渊”)以为主持。当然,僧人和当地部族首领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哲僧为之干,酋豪为之助”)。 宋朝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在新占领区建立佛寺,是因为佛寺及其僧侣具有巨大的教化威力,具体有两点:一是迎合并拉拢蛮人之心。毛渐“因俗立教,创五寺以诱化其心,苗瑶始服”。同样,吐蕃俗“尊释氏”而“重僧”,宋朝为之修建宏伟壮丽的佛寺(“数百区之盛”),并请高僧主其事,这无疑会大大地拉近宋朝与吐蕃民众的心。高僧海渊来到岷州后,“老幼争趋,或以车致,或以马驮,健者则扶持而至,人大归信”,佛寺及其僧侣征服了武力所无法征服的蛮人之心。二是变革风俗。以吐蕃为例,吐蕃信佛由来已久,但吐蕃本土佛教与中原佛教有较大差异,“其人多知佛而不知戒,故妻子具而淫杀不止,口腹纵而荤酣不厌,非中土之教为之开示提防而导其本心,则其精诚直质且不知自有也”。变革风俗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同化,即“用夏变夷”“以中国法教驭之”。变革吐蕃风俗,纯粹中土式的“诗书礼乐”是不可能被接受的,因此,“求所以变革之道”,“诗书礼乐之外,盖有佛氏之道大焉”。 教化之外,僧侣还是战后善后工作的重要力量,尤其是祈福亡灵,安葬阵亡士兵遗体。熙河地区收复后,朝廷每年都要划拨大量资金,建水陆道场,由僧侣“追荐蕃汉阵亡人”(52),如熙宁六年,诏熙州大威德、河州德广禅院岁各赐钱五十万,“设道场,为汉蕃阵亡人营福”(53)。蕃汉阵亡士兵遗体也多由僧侣负责安葬,如河州收复后,专门在城东北隅作墓园,瘗葬蕃汉阵亡暴骸,并择僧人看管修葺,为此特建慈济寺。(54)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从根本意义上讲,所有历史皆为殖民史……甚至从更严格的政治或文化意义上讲,殖民主义不只是一个近代现象。文明这个思想本身就其假设来说就是一个殖民概念。这一假设是,同文明相联的规范在消除其他规范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中为转变文明的他者提供了手段。”(55)在华夷之辨,即文明与野蛮二分的思维范式下,宋朝佛寺及其僧侣同样“为转变文明的他者(即西南的蛮族、西北的吐蕃)提供了手段”。(56) 三 僧侣成为各个民族长期对峙中间谍的最佳人选 间谍深入敌方打探军政信息,最关键的是尽可能不引起对方的怀疑。就10—13世纪整个东亚大陆来看,能做到这一点的首推僧侣,因为僧侣是各个民族唯一共同顶礼膜拜的对象。各民族百姓在潜意识中多只有信奉,少有怀疑,因此,僧侣间谍,或假扮僧侣的间谍得以广泛活跃在当时各个民族之间。(57)兹仅以宋朝为主线分述如下: (一)宋与西南蛮 如吴天常所说:“自诚州抵融州道新通,请每三十里建一佛寺,择僧知蛮情者居之,诸蛮信佛,平时可使入蛮与之习熟,有警可用以间谍,而佛舍可因以储粮,其利边甚大。”(58)“有警可用以间谍”是建立佛寺的初衷之一。 (二)宋与吐蕃 “蕃俗,为僧尼例不杀”;(59)“僧之丽(罹)法,无不免者”;(60)“蕃法,唯僧人所过不被拘留,资给饮食”。(61)鉴于僧侣的崇高地位和巨大特权,在间谍战中,宋朝多喜欢派遣僧人或假扮僧人前往探事。如吐蕃著名首领唃厮啰逝世后,青唐吐蕃部族陷入内乱,为便于分化吐蕃,以夷攻夷,熙河经略司特意派遣蕃僧往青唐体访事实。(62)再如哲宗元符二年(1099),宋朝担心青唐吐蕃部族叛乱,为将朝廷最新旨意“密谕”守将王赡,“令严设备”,“乃以蜡封书,伪髠蕃官嘉木灿、伊费赫,置蜡封于衲衣中,遣间道,令四日至青唐,责报而还”。(63)“伪髠”,就是假扮僧人的意思。宋方密使假扮蕃僧,将密信藏于“衲衣中”,顺利地完成了使命。 (三)宋与西夏 西夏是佛教的国度,“至于释教,尤所祟奉”,“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64)1038年,元昊称帝,西夏脱离宋朝而独立,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在宋夏战争中,宋方多次试图实施离间计,挑拨元昊与其亲信之间的关系,其中野利旺荣是宋方主要拉拢对象之一,而在其间传递信息的多为僧人。野利旺荣,元昊妻兄,也是其亲信,“贵宠用事”。(65)知青涧城(治今陕西青涧)种世衡派遣本地僧人王嵩“以枣及画龟为书置蜡丸中遗旺荣,谕以早归之意,欲元昊得之,疑旺荣”。(66)知渭州(治今甘肃平凉)王沿、总管葛怀敏也曾派遣僧人法淳持书及金宝以遗旺荣兄弟。(67)种世衡等人的离间计并未马上奏效,旺荣不但未反叛,反而将王嵩交与元昊。(68)不过,宋方反复使用离间计,一定程度上也扰乱了元昊的心志。元昊颇疑旺荣“贰己”,“不得还所治”(69),从而加速了西夏向宋方求和,正如《长编》所记载,“元昊未通时,种世衡画策,遣嵩冒艰险间其君臣,遂成猜贰,因此与中国通”。(70) (四)宋与辽 “辽以释废”,(71)对佛教极为崇奉,宋朝同样尊崇佛教,因此,宋辽之间经常派遣僧侣间谍,或让间谍伪装成僧侣去对方探事。李允则知雄州(治今河北雄县)时,契丹曾派间谍身着紫衣,扮成僧人入城探事,(72)而李允则亦曾“令州民张文质绐为僧”,“入契丹刺事”,并得“补契丹伪官”。(73)正因为僧人身份常成为间谍的最好掩饰,宋、辽双方都对来自于对方的僧人有所提防。天禧三年(1019),河北缘边安抚使刘承宗就建议对界河北岸来的僧人严加审核,“僧人有从北走来者,自今望令勘会,如不系两地供输入及近里州军因掳到北界为僧来,即今(令)结罪保明,委无虚诳,试经申奏,给与祠部”。(74)契丹将“两地供输人”及沿边州军人掳到北界,并培养成为僧人,其主要目的当不在于发展佛教,而在于培养间谍。至和元年(1054),雄州又报告:“契丹遣蔚、应、武、朔等州人来五台山出家,以探刺边事。”朝廷及时下诏:“五台山诸寺收童行者,非有人保任,毋得系籍。”(75) (五)宋与金 “金以儒亡”(76),在宋朝的周边民族中,唯独金国的女真族对佛教持保留态度,“至今还没有发现有女真人出家为僧尼的实例”。(77)因此,僧人在金国与周边民族交往中的作用相对弱小,以僧人,或假扮僧人做间谍的情况也相对要少,因为这不但起不到掩饰的作用,反而会招来怀疑。南宋初,宋汝为、凌唐佐等陷于金国,“以机密归报朝廷”,结果,“唐佐等所遣僧及卒为逻者所获”。(78)女真人原本信仰萨满教,金朝前期虽然接触到佛教,“但还没有全面接受”,(79)凌唐佐等人不了解女真族文化,想当然而为之,或许正是僧人与众不同的装束暴露了凌唐佐等人所遣间谍的行踪。 (六)宋与蒙元 还在漠北时,蒙元“固已崇尚释教”,(80)因此,蒙元也深谙借助佛寺从事间谍工作的道理。蒙元间谍中最杰出者当推史称尤宣抚者。尤宣抚长期潜伏于江南佛寺,未引起任何人怀疑。据《遂昌山人杂录》记载: 伯颜丞相先锋兵至吴,是日,大寒天,雨雪。老僧者时为承天寺行童,兵森列寺前,住山老僧某,令其觇兵势,且将自刎,无污他人手。行童震栗,远望有以银椅中坐者,以手招行童。行童莫敢前。且令军士趣召之。将至,戒以无恐。既至,召令前,问住山某和尚安否,西廊下某首座安否。行童大惊。且戒令先往首座房致意,首座僧大惊。而银椅中坐者已至房,作礼,笑问曰:“首座如何忘却耶?某固昔时知命子,寺前卖卜者也,尝宿上房逾半年。”已而偕至方丈拜主僧,主僧错锷,谩不省,扣之,乃言曰:“我尤宣抚也,今日尚何言?”即命大锅煮粥啖兵人,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吴语诵榜文晓谕百姓。于此,始知尤公探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箓,取验于世祖皇帝云。(81) “尤公探谍江南凡八年”,其中半年多时间是潜伏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承天寺,江南寺庙众多,从其成功经验推断,其余时间潜伏在佛寺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久于江南探谍,南士人品高下,皆悉知之”,(82)除了对南宋高级官员了如指掌外,尤宣抚当还探听到很多重要的军政情报。这些情报都有特殊的记号,即以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龙虎山张天师符箓为标志,并直达元朝皇帝世祖忽必烈。(83)当元军达到时,尤宣抚立马恢复宣抚使的身份,领导元军安抚江南百姓,“令兵人持招安榜,而令行童以吴语诵榜文晓谕百姓”。让僧人(“行童”)用方言宣读榜文,也是想借助佛教的力量安抚信众。 平江府沦陷于德祐元年(1275),往前推八年,尤宣抚当在1268年左右潜入南宋。对南宋来说,1268年及其以后的八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1268年,元朝采取中间突破的策略,从襄阳开始向南宋发起进攻;1273年,襄阳沦陷;1274年,忽必烈下令向南宋发起最后的总攻,犹如秋风扫落叶,仅用三年时间,即在1276年,南宋降元。元朝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顺利地吞灭强大的南宋,与以尤宣抚为代表的间谍的出色工作当有莫大的关系。 尤宣抚,生平不详,按元朝官制,宣抚使为正三品。江南平定后,尤氏升任江浙行省平章,行省平章为从一品。从其官品来看,尤宣抚或许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级别最高的间谍。 四 结语 佛教历来倡导以慈悲为怀,普度众生,以善良为镜,诸恶莫作,因此,佛寺及其僧侣被普遍视为善良、和平的象征,归依佛门意味着去恶而从善。10—13世纪,东亚大陆几乎所有民族都信奉佛教,因此,在各个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中,为示和善之意,各个民族不乏有意派遣僧人作为交往的使者。仅以《宋史·外国传》为例,以僧人为国家使者的就有:(1)西夏,嘉定七年(1214),西夏遣二僧赍蜡书来西边,欲与共图金人;(84)(2)高丽,端拱二年(989),高丽遣僧如可赍表来觐,请《大藏经》。元丰八年(1085),高丽王遣其弟僧统来朝,求问佛法并献经像;元祐四年(1089),高丽王子义天使僧寿介至杭州祭亡僧,言国母使持二金塔为两官寿;(85)(3)于阗,乾德三年(965),僧善名、善法来朝,其国宰相因善名等来致书枢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国;开宝四年(971),其国僧吉祥以其国王书来上,自言破疏勒国得舞象一,欲以为贡;(86)(4)回鹘,乾德三年,西州回鹘遣僧法渊献佛牙、琉璃器、琥珀盏;(87)景德四年(1007),甘州回鹘遣尼法仙等来朝,献马,又遣僧翟入奏,来献马,欲于京城建佛寺祝圣寿,求赐名额;(88)(5)吐蕃,开宝六年(973),凉州令步奏官僧吝毡声、逋胜拉蠲二人求通道于泾州,以申朝贡。(89) 但在传法之外,在和善外衣之下,佛寺及其僧侣同样被卷入到民族征服和民族战争之中,甚至成为民族征服和民族战争的工具。正是鉴于佛寺及其僧侣在各个民族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宋朝在开拓新领土和安定新占领区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借重佛寺和僧侣的力量,以佛寺为军事、情报基地,以僧侣为说客,不战而屈人之兵,以传教怀柔,甚至同化蛮人;同时,在与周边民族政权的长期对峙和拉锯战中,僧侣身份可以成为间谍的最佳掩饰,各政权多有意招募僧侣为间谍,或让间谍假扮僧侣,这些真假僧侣间谍在各个民族之间的战争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典型案例首推蒙元灭南宋过程中的尤宣抚。 ①史金波先生曾指出:“综观10—13世纪中国宗教信仰分布,大体上是东部佛道并存,势力旗鼓相当;西部回鹃、吐蕃、大理以佛教为主,伊斯兰教渐从回鹘西部进入;中部西夏地区虽也兼容佛道,但佛教强势,道教弱势,是过渡地带。”(见于《西夏佛学与儒学的地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15日第7版) ②参顾吉辰:《北宋蕃僧考实》《北宋蕃僧考实(续)》,分别载《史学集刊》,1987年第1、2期。 ③荆湖南、北路的开边在神宗熙宁年间就已基本完成,而秦凤路的开边一直持续到徽宗大观年间,前后持续约三十七年(参[元]脱脱等:《宋史》卷87《地理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159—2169页;卷88《地理四》,第2196—2200页)。秦凤路开边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神宗开边,主要集中在今甘肃省中南部,后期为徽宗开边,主要集中在今青海省东部,为了与湖南开边时间统一,本文秦凤路开边只考察前期甘肃方面的开边。 ④[光绪]《湖南通志》卷末五《纪闻五》,《续修四库全书》第6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⑤《宋史》卷493《蛮夷一》,第14182页。 ⑥[光绪]《湖南通志》卷末5《纪闻五》,《续修四库全书》第668册,第523页。 ⑦[宋]张耒:《张耒集》卷60《吴天常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92页。 ⑧[宋]王存:《元丰九域志》卷6《荆湖路·诚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6页。 ⑨[光绪]《湖南通志》卷末五《纪闻五》,《续修四库全书》第668册,第523页。 ⑩[宋]释洪志:《禅林僧宝传》卷18《兴化铣禅师》,台北:佛光出版社1994年版,第362页。 (11)[嘉靖]《惠安县志》卷13《人物·绍铣》,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32册第20页。 (12)《禅林僧宝传》卷18《兴化铣禅师》,第362页。 (13)[宋]魏泰:《东轩笔录》卷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1—82页。 (14)[宋]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7《神宗开南江》,第2页,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影印本。《太平治迹统类》将张裕记载为“张竑”。 (15)[宋]孔平仲:《孔氏谈苑》卷1《羌人自相君臣》,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16)[宋]李远:《青唐录》,载《青海地方旧志五种》,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 (17)参[日]岩崎力:《宋代河西藏族与佛教》,《民族译丛》,1990年第2期;任树民:《从〈岷州广仁禅院碑〉看河陇吐蕃佛教文化的特色》,《西藏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汤开建:《宋〈岷州广仁禅院碑〉浅探——兼谈熙河之役后北宋对吐蕃的政策》,《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 (18)《宋史》卷462《方技下·僧智缘》,第13524页。 (1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下简称“长编”)卷226,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5501—5503页。 (20)《宋史》卷462《方技下·僧智缘》,第13524页。另参宋丽霞:《智缘及其与北宋熙河地区的汉藏关系》,《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3期。 (21)《宋史》卷492《外国八·赵思忠传》,第14168页。 (22)《孔氏谈苑》卷1《羌人自相君臣》,第11页。 (23)《史记·陆贾传》记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西汉]司马迁:《史记》卷97,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99页) (24)[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56《长沙府三·名宦·毛渐》,四部丛刊续编本,第8页。 (25)[清]张维编:《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石刻史料新编》本,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第37页。 (26)[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56《长沙府三·名宦·毛渐》,四部丛刊续编本,第8页。 (27)[光绪]《湖南通志》卷238《方外志一·寺观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61页。 (28)[光绪]《湖南通志》卷238《方外志一·寺观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61页。 (29)[光绪]《湖南通志》卷238《方外志一·寺观一》,《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61页。 (30)[光绪]《湖南通志》卷末五《纪闻五》,《续修四库全书》第668册,第523页。 (31)[宋]释觉范:《石门文字禅》卷21《潭州大沩山中兴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423—425页。 (32)[光绪]《湖南通志》卷239《方外志二·寺观二》,《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76页。 (33)《长编》卷345,第8277页。 (34)[光绪]《湖南通志》卷240《方外志三·寺观三》,《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84页。 (35)[光绪]《湖南通志》卷240《方外志三·寺观三》,《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85页。 (36)[光绪]《湖南通志》卷240《方外志三·寺观三》,《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85页。 (37)[光绪]《湖南通志》卷240《方外志三·寺观三》,《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85页。 (38)[嘉庆]《大清一统志》卷369《沅州府二·寺观·天柱寺》,四部丛刊续编本,第6页。 (39)[光绪]《湖南通志》卷240《方外志三·寺观三》,《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85页。 (40)[宋]黄叔豹:《同天寺记》,载[光绪]《湖南通志》卷240《方外志三·寺观三》,《续修四库全书》第667册,第485页。 (41)《长编》卷344,第8262页。 (42)《长编》卷344,第8262页。 (43)《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第37页。 (44)《长编》卷239,第5809页。 (45)《长编》卷248,第6055页。 (46)《长编》卷248,第6055页。 (47)从同期所赐“威德禅院”“广仁禅院”等寺名来看,“德广禅院”当为“广德禅院”。 (48)《长编》卷247,第6021页。 (49)《长编》卷289,第7069页。 (50)《长编》卷254,第6211页。关于广仁禅院的建立时间,《长编》记载为熙宁七年,而《陇右金石录》所录《广仁禅院碑》则记载为元丰七年,汤开建先生据《广仁禅院碑》推论《长编》记载有误(《宋〈岷州广仁禅院碑〉浅探》,《西藏研究》,1987年第1期)。其实,两则记载并不矛盾,只是各有侧重而已,《长编》记载的是宋廷下令建造的时间,而《广仁禅院碑》记载的是完工的时间,此点,《陇右金石录》编者张维已有所申述,“盖前后已近十年而后完兹巨构”(《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按语,第39页)。 (51)《陇右金石录》卷3《广仁禅院碑》,《石刻史料新编》本,第37—38页。 (52)[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69页。 (53)《长编》卷247,第6021页。 (54)《长编》卷289,第7069页。 (55)[美]阿里夫·德里克:《殖民主义再思索:全球化、后殖民主义与民族》,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13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5页。 (56)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辨实质是文明与野蛮之辨,并非种族主义,这一点与阿里夫·德里克的认识一致,阿里夫·德里克的“殖民”也是从文明史的意义上说,与近代以来欧美的殖民主义并不完全相同。 (57)需要强调的是,此处是从当时东亚大陆整体来看,如果从具体的两个民族之间的对峙来看,僧侣之外,还可以招募或假扮对方人员以为间谍。 (58)《张耒集》卷60《吴天常墓志铭》,第892页。 (59)《长编》卷514,第12222页。 (60)《青唐录》,载《青海地方旧志五种》,第10页。 (61)[宋]周煇著,刘永翔校注:《清波杂志校注》卷10《唃厮啰》,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426页。 (62)[宋]李复:《潏水集》卷3《又上章丞相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22页。 (63)《潏水集》卷6《震雷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第65页。 (64)《武威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载吴景山编:《西北民族碑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65)[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06页。 (66)《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第13998页。 (67)《长编》卷138,第3330页。 (68)《涑水纪闻》卷9,第175页。 (69)《长编》卷138,第3330页。 (70)《长编》卷155,第3773页。 (71)[明]宋濂等:《元史》卷163《张德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823页。 (72)《宋史》卷324《李允则传》,第10481页。 (73)《长编》卷105,第2447页。 (74)[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道释一之二三,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本。 (75)《长编》卷177,,第4283页。 (76)《元史》卷163《张德辉传》,第3823页。 (77)都兴智:《金代女真人与佛教》,《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78)《宋史》卷399《宋汝为传》,第12134页。 (79)都兴智:《金代女真人与佛教》,《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 (80)《元史》卷202《释老·八思巴传附必兰纳识里传》,第4520页。 (81)[元]郑元祐:《遂昌山人杂录》,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4页。 (82)《遂昌山人杂录》,第4页。 (83)宋理宗开庆元年(1259),时为藩王的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听说张天师神异,派遣间谍到龙虎山,请张天师预卜未来,张天师告诉蒙古间谍说:“善事尔主,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36《汉天师世家序》,《四部丛刊》初编,第15页),后来,潜入南宋的蒙古间谍以张天师符箓作为情报的特殊标志当与此有关。参杨倩描:《南宋宗教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84)《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传下》,第14027页。 (85)《宋史》卷487《外国三·高丽传》,第14039、14048页。 (86)《宋史》卷490《外国六·于阗传》,第14017页。 (87)《宋史》卷490《外国六·高昌传》,第14110页。 (88)《宋史》卷490《外国六·回鹘传》,第14115页。 (89)《宋史》卷492《外国八·吐蕃传》,第141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