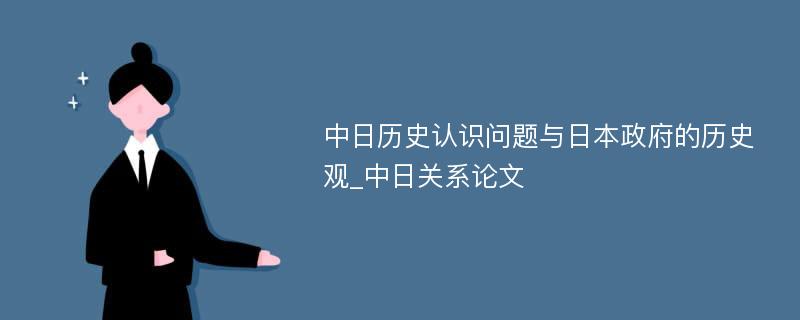
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观论文,日本政府论文,中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然也是日本战败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这60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中日两国而言,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惟一未变化的是两国地理位置,意即邻里关系。自古以来,中日本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尽管古代中日间也曾发生过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但在长达两千年的时间里,中日友好往来实为主流。在长期友好交往过程中,日本大量吸收中国的先进文明,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也从日本汲取了有益于自身文化发展的内容。然自近代开始,日本便忘记了来自古代中国的恩惠,转而加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行列。不惟如此,日本还在与列强侵略中国的角逐中,实行起独霸中国、灭亡中国的政策。只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在中国人民全民族的抵抗和世界正义力量的打击下,日本成为有史以来惟一遭受原子弹后而不得不宣布投降的战败国。战后,日本虽然很快便在战争的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日本并没有真正从战败的历史中汲取教训,深刻反思和清理历史问题。这使得近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在“政冷经热”的状态下徘徊,自今年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由日本右翼学者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以来,又雪上加霜地使中日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恶化局面。造成这种局面的责任完全不在中国方面,抛开美国等国际因素,完全是日本右翼势力蓄意制造事端和日本政府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处理不当所使然。
一、历史认识问题的三大内容
所谓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可以分为历史认识问题与历史遗留问题。前者主要包括教科书问题和日本首相等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后者则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和中国民间受害索赔问题等。这些问题无一不与现实问题紧密相关,但又无一不是由于日本过去侵略中国所造成。无论是历史认识问题还是历史遗留问题,都可以说是“冰封三尺,并非一日之寒”,但是相比之下,历史认识问题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历史遗留问题与现实政治关系更大,所以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历史认识问题,而历史遗留问题则拟另做研究。
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三大内容。
1.教科书问题
教科书问题最早可以追溯至日本战败。战前日本的“国定教科书”,全面宣扬“皇国史观”与军国主义思想,战后在美国的占领下,为日本制定《教育基本法》,允许民间编写教科书。1946年9月至1947年1月间日本文部省按照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令,陆续制定了中小学用《日本之历史》上下册和师范学校用《日本历史》上下册等历史教科书,这是战后日本第一次以批判战前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并期待日本往民主主义方向改进而制定的。它同战前宣扬“皇国史观”驱使日本人民对外侵略、献身于“圣战”明显不同。如1946年发行的中学生用《日本之历史》就把日本发动的对外战争明确记述为“这是基于极端的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的政治运动……同时对邻邦中华民国策划的侵略战争”。但应该说这种较为正确的历史观并不代表日本政府,这只是执笔教科书的日本有正义感、有良心的学者们的历史观。东京大学的小西四郎教授,当时任职于文部省教科书局,并是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执笔者。他回忆说:“为了创造民主主义的新日本,我认为教育应传达事实真相。全体执笔者也都抱着一股使命感。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所推行的战争只能以侵略二字形容。我认为那是侵略,所以我就如此在教科书上写着”。[1]这也是美国占领日本初期所推行民主化改革的结果,正确的历史观还可以在教科书中体现出来。然而,很快由于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出于利用日本的目的,大批释放了战前指导战争的战犯,并使其重新掌握政权。这些人对战后教科书的历史观极为不满,对“侵略”一词开始提出异议。1950年10月17日,文部省居然下发“升国旗,齐唱‘君之代’”的通知;11月7日,天野文相竟然在全国教育长会议上做“修身复活”的发言,几同鼓吹复活战前教育。1951年7月,文部省发表《改定学习指导要领》,此后“侵略”一词虽仍在中学使用,但高等学校使用的日本历史课本中则由“进出”一词所取代。至1955年2月本来在中学《学习指导要领》所保留的“侵略”一词也改为“进出”。60年代,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由于以公正的历史原则、严肃的治学态度,谴责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便被审定为不合格。70年代日本教科书问题亦无好转。有日本学者指出:“自1976年以后,日本在有关近代中日战争的记载上以日本为主记载日本‘侵略’实事的,可以说完全地绝迹了。”[2]及至80-90年代篡改教科书事件更是层出不穷,主张承认战争责任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1993年最终败诉,进入新世纪的2001年与今年,更大规模篡改教科书事件复又发生。被大肆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能多次通过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定,这并非什么“言论自由”,倒恰恰证明了日本政府顽固坚持右倾历史观的事实。
2.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原名“东京招魂社”,位于东京市千代田区,明治维新后建造。1879年改称现名,作为官营神社,初为祭祀明治维新过程中而献身的人士,后则扩展为祭祀历次对内对外战争中阵亡的日本官兵。一般情况下,每年春秋两季举行大祭。战前日本政府为培养和激励青少年效忠天皇,向其灌输军国主义精神,宣扬为国战死后可以进入靖国神社,成为万世“英灵”,天皇和政府首脑亲赴靖国神社进行参拜。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在美军的占领下,这个“军国主义思想支柱”被降为一个普通的宗教法人。50年代起,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加速对日本的扶植,原本就未清除的军国主义思想在日本迅速复苏,尤其是在与战前有密切关系的日本政府内更是如此。1952年日本政府主持了追悼全国阵亡者仪式,随后天皇便参拜了靖国神社。但由于战后和平宪法有关政教分离的规定,日本首相与政府对参拜靖国神社还是有所顾忌的。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还未见记载,1975年日本战败30周年的8月15日,当时的首相三木武夫便参拜了靖国神社,但出于日本进步力量的压力和顾虑国际影响,三木在参拜时,没有写明职务,未敢乘用公车,所以时称“私人参拜”。此后1978年福田首相也以同样方式参拜了靖国神社,并且就在这一年,在日本政府的默认下,被东京审判判为甲级战犯的东条英机等人的亡灵也被移进靖国神社。1980、1981、1982年铃木首相均参拜了靖国神社,后两次竟是率全体阁僚共同参拜。1983年中曾根首相居然在一年内4拜靖国神社,并且在签名时与铃木一样,写明身份为“内阁总理大臣”;至1985年,中曾根便不再遮掩,公开率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首开日本首相公开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的恶例。中经桥本龙太郎到今天的小泉上任后的4次参拜靖国神社,这一问题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顽症。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破坏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其中虽有所谓选举竞争和满足右翼的需要,但与首相及政府的历史观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3.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
60年前,日本政府宣布投降,结束了近代以来的对外侵略历史。但是,战后的日本政府从未对其侵略的历史有过正确的认识,更未对受其侵略的国家真诚地认过罪,而是一直顽固坚持不承认侵略的观点。
1945年8月的伦敦协定中首次导入了“反和平之罪、反人道之罪”的新的审判法理,并首次应用于纽伦堡军事法庭,使德国纳粹伏法。此原则的确立可以说是战争审判的一大进步,使战争审判从单纯的犯罪审判上升为杜绝战争、维持和平的手段。“可是,日本政府却从来没有从内心上承认过这一原则”。[2]1947年2月,东京审判进入辩护、反证阶段,日本律师团副团长清濑一郎在开头陈述中,即明确阐述了日本政府的见解:“关于主权国家行使主权的行为,或者因当时国家机关之故,如果说个人承担责任,作为国际法理是不成立的”,拒不承认纽伦堡原则的合法性,否认日本国家和战争指导者有战争责任。并声称“我国的当事者没有与德意共同征服世界的想法”,“如果即使说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本身也不是犯罪’,对苏联也没有侵略意图,毋宁说‘违反中立条约’的是苏联方面,‘太平洋战争’也只是自卫行动”。[3]清濑的发言,可以说是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的真实心声。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日本政府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拒不承认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仅从对掳掠中国劳工问题的态度上,即可看出这一点。1950年4月3日,在第七次日本国会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上,有人就日本报纸《国际新闻》报道的木曾谷御岳山中国劳工被虐杀一事提出质问。法务府官员高桥答:“御岳山的问题,我不清楚是何事,但即使笼统地说是俘虏,我认为那实际是华人劳务者……现在作为法务府的意见,报纸登载的事,与我们全然无关,那恐怕并非是有权威的东西”。[4]这位法务官员除了以“不清楚”支吾其词外,便是声明与作为政府机构的法务府无关,而且还否认报纸登载的事实。当另有人追问道:“今后打算采取何种态度呢?”高桥答道:“如我前面所言,现在才知道具体事实,我想进行调查与妥善处理,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4]在5年后的1955年12月日本第23次国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社会党议员田中稔男又向时任外务大臣的重光葵提出质问:“另一重大问题就是战争中强掳至日本的中国人遗骨问题……这个问题是人道问题,特别在国民感情上有很深的关系……希望政府不要把此事作为民间团体的事业,要自觉负起责任。这是一个向6亿中国人民表示日本国民诚意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希望外务大臣认真答辩”。重光葵回答:“关于政府如何做,现在不能马上回答,并且至今也没有计划,但是我想对此问题倾注全力”。[5]5年前,日本政府法务官员表示“决非知道后而不了了之”;5年后,日本外务大臣表示对中国劳工问题“倾注全力”,但事实上日本政府除了否定强掳中国劳工、掩盖侵略罪行,并未做任何有关中国劳工的调查。5年之间还“至今也没有计划”,便证实了日本政府的真实行为。日本政府非但不承认强掳中国劳工的罪行,反而于1955年和1957年两次通过日本驻日内瓦公使向我国提出要求归还战争中“情况不明的4万人”。[6]1958年,刘连仁事件发生,当时的岸信介政府非但不对此事向刘连仁本人及中国政府道歉,反而污蔑刘连仁为“非法入国者”。即便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关于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可以说在日本首相及阁僚中,发自内心、确实承认日本过去的战争是侵略战争者也少之又少。在他们内心深处,或者说骨子里根本就不认为战前日本政府发动的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被认为曾在中日建交问题上做出重大贡献的田中角荣,在建交谈判过程中也从未承认过日本侵华战争是侵略战争,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场战争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1980-1982年任首相的铃木善幸,他在1980年“八·一五”追悼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日本人员时说:“在那激烈的战斗中,300多万同胞祈愿祖国的安泰,思念亲人的未来,在战场、工作岗位上或在战火中倒了下去,还有的人战后死于异乡。当想起他们时,痛恨之情不禁满胸怀”。[7]这样的对外战争怎么可能是侵略战争呢?中曾根则说:“天皇陛下担忧我们民族的危亡,果断地做出结束战争的英明决断。结果,以维护国体为条件,同意我军无条件投降,接受‘波茨坦宣言’,从而终止了战争”。[8]竹下登也说过:“有关侵略战争的学说很多,依哪一个为基准,联合国也未做出定论,因此难以断定”。[9]森喜朗公然鼓吹“皇国史观”,更是众所周知的了。凡此种种都说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较之以前也没有多大的改变,根本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反省和“清算”。
二、日本政府右倾史观的原因
从以上历史认识问题的事实中,我们不难发现不论是教科书问题,还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问题,都与日本政府的历史观紧密相连。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顽固地坚持右倾史观呢?除了现实原因而外,历史认识问题还是需要从历史进程中寻求答案。
其一,战后美国的占领政策是使日本政府坚持右倾史观的根源。这里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由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采取了“间接统治”方式,保留了尽管是作为日本“象征”但却是战争首犯的天皇。当然,这里也有其客观原因,即盟军占领日本不像占领德国一样,将其政治组织彻底破坏,使之不能持续下去;而日本旧的国家机关和组织形态几乎未遭破坏地被保留下来。二是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应该说在日本战败前夕和日本战败后的短时期内,美国是想通过对日本的占领,达到削减或消灭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目的,并无扶植日本的打算。1945年5月,美国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在质问陆军部长史汀生时说:“对俄国在远东的影响,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我们要不要有一种力量来对抗其影响,如果有必要,那么这个力量应该是中国还是日本?”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明确回答道:“我们与俄国在政策上严重对立之时,中国任何时候都会站到我们一边”。[10]因而美国在占领日本初期,对于追究日本战争犯罪还是有所表现的,包括逮捕战犯、解散财阀,并制定战后民主宪法,在第九条中规定日本不许有正规军队,还推行了其它方面的民主改革。但正如前文所述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为了一己之私竟允许日本战犯重新掌握政权,这实际上等于为日本政府开辟了一条不承认侵略战争、坚持右倾史观的道路。
其二,正由于有上述原因,又使日本政府产生了坚持右倾史观的另一原因。这便是日本政府战前战后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政府”,重点不是字典中解释的“国家行政机关”,而是参加政府的决策人员。因为任何政府的方针政策、立场观点都是源自该政府的决策人员,如无此,所谓政府便不复存在。在政府决策人员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上面也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占领军信任的战前旧阁僚,二是战后受到惩处有战争罪行的战犯或战犯嫌疑者。前者如战后曾任首相的币原喜重郎、吉田茂,这类战前的旧政治家,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指导战争,具有所谓“自由主义”意识,但却积极拥护天皇,又具有强烈的国家主义和反共意识。此类旧政治家虽然反战,但对承认侵略战争、承担战争责任持消极、抵制态度。后者如曾因战争犯罪而被判刑的东条内阁外相重光葵、曾因“强行征用朝鲜人”之罪而被革除公职的椎名悦三郎、前文提到的也是被革除公职的清濑一郎、作为甲级战犯嫌疑者的岸信介,他们在战后不同时期分别任外相、内阁官房长官、众议院议长、首相。他们既是真正的参与指导战争者,又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刘杰曾指出:“从人的角度讲,许多活跃在日本战后政治舞台的政治家,都曾参与过指导战争的活动,这些人的战争观、历史观可以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就过渡到战后了”。[11]因而,他们具有右倾历史观是十分正常的,若他们有正确的历史观反倒是咄咄怪事。
其三,战后日本的周边环境,使日本的战争责任没有受到追究,这也使日本政府的右倾史观得以持续下来。战后日本与德国相比,虽然它们各自的周边国家都是深受其害的被侵略国,但在对待追究他们的战争犯罪问题上,却有很大差异。德国的周边国家战后很快恢复了以前一直比较稳定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在政治和外交上,有条件追究德国的战争犯罪。而在日本周边“新成立的国家,忙于国内的政治不稳与经济困境,加之又直面冷战的进行、大国介入的危机,在这种状况下,特别是非共产圈的国家,把与日本缔结和平条约与支付战争赔偿作为杠杆,以之强化国家基础,这并非不可思议……赔偿问题,与其说是日本的战争责任,不如说是他们巩固政权的工具”。[12]这种事实恐怕不容否认。
其四,亚洲各国对日本战争赔偿权的放弃。可以说,至今为止,日本政府从未对亚洲各受害国进行过真正意义的赔偿。关于日本战争赔偿本身问题,国内外学者多有论述,本文暂置而不论,只对放弃战争赔偿后果略抒己见。二战后,要求战败的法西斯国家向反法西斯胜利的国家以及受其侵略之害的国家支付战争赔偿,是不同于前此以往的战争赔偿,更不同于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仅是以战胜国的武力向战败国强行索取财物问题。二战后要求法西斯战败国进行赔偿,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所以决不是单纯的物质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物质上的赔偿来反省战争的犯罪,从而痛改前非,不再重蹈覆辙。日本没有进行认真的战争赔偿和各国对战争赔偿的放弃,客观上就使日本政府及日本人混淆了正义与非正义、侵略与反侵略之分。日本政府更失去了以侵略战争为训,进行真正的深刻反省的机会。这是放弃战争赔偿在日本政府的历史观上所产生的客观影响。
其五,日本政府内心赞同右翼学者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待侵略战争的看法上,在意识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日本政府其实同日本右翼学者们是一致的。如《南京大屠杀之伪证》的作者田中正明为了否定侵略战争,竟然不惜多处篡改松井石根的战地日记,将屠杀1万人改为“1千人”。东京大学的著名教授藤冈信胜居然声称承认侵略就是“自虐史观”,并要求把“从军慰安妇”问题在教科书中删除。这类人的行为完全是为了维护所谓的日本“形象”而死不承认侵略战争。认为承认了战争犯罪,就“伤害了日本民族的自尊”。[13]这一点恰恰是日本政府所需要、但作为政府自身又不便公开讲出的。
三、要理智而冷静地对待历史认识问题
综上可见,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和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关乎当前与今后中日关系发展的重要问题。由于历史的继承性和日本政府缺乏足够面对过去的勇气,这一问题是不会在短时期内获得解决的。先以教科书问题为例,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每次在审定期间都毫无例外地遭到亚洲等受害国及其民众、甚至是日本国内进步人士的强烈抗议,但是日本政府除了进行一些外交辞令式的支吾搪塞外,就是以“言论出版自由”为挡箭牌加以应付,根本无意制止和约束右翼肆意篡改侵略历史的言行。所以,教科书问题今后无疑还会出现。再以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言,小泉纯一郎自上任以来,一直不顾亚洲各侵略战争受害国及其人民的强烈反对,多次到靖国神社参拜包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亡灵,继续伤害着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今年4月,胡锦涛主席在亚非峰会期间,向小泉提出了处理中日关系的“五点主张”,其中就包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问题。小泉虽然没有相反表态和做了一些承诺,但是,今后他参拜靖国神社的可能性仍不可排除。可以预见,今后中日关系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决不会没有波折,或许会更加复杂与难于处理。但为了国家民族利益,我们应该以理性思维加以对待。
首先,我们要区分日本政府与日本普通民众的不同。在这一点上有两层含意,一是历史上,二是现实中。历史上日本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是日本政府发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所以侵略战争的责任理应由他们来负。战争中日本的普通民众具有双重身分,他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作为“受害者”是指他们在战争中,不仅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酷压迫,而且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死于前线与后方,并且他们还是世界上惟一遭受原子弹攻击的人;作为“加害者”则是在战争中,他们不仅相信日本政府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是“圣战”,而且还狂热地支持了侵略战争。但不论作为“受害者”,还是“加害者”,主要责任都应该由日本政府来承担,因为是日本政府驱使其民众从事侵略战争的。在现实中,日本政府的不断右倾化,使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越来越偏离正确的方向,以致于中日关系出现了目前的局面,这显然不在于日本普通民众,而关键是日本政府,这两者是不容混同的。
其次,我们在评价日本政府的历史观时,务必分清日本政府的历史观与主张中日友好的区别。综观日本战后历届首相不要说他们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谢罪,就连公开承认当年的战争是侵略战争的也只有细川与村山等绝无仅有的几个人,细川还因日本政界的反对,旋即改口为“侵略行为”。80年代给予日占时期台湾老兵的赔偿而称“补偿”,90年代不以政府出面而以“民间基金”的形式决定给予亚洲“慰安妇”的“补偿”,都是日本政府不欲承担战争责任、不欲谢罪的具体表现。田中角荣和大平正芳都未就过去的战争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过谢罪,就在1972年9月26日中日关于建交的会谈中,日方代表还顽固地声称中日赔偿问题已在日台和约中解决,对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的提法不欲承认时,两人对此均未置一词。田中还以“添了麻烦”一词轻描淡写地表述侵略战争给予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只是在受到周总理和中方代表的批评和反对后,大平正芳才说出“表示深刻反省”而不是谢罪一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多数日本首相和多届日本政府,为了日本国家的利益,在对华关系上,还是不得不主张中日友好的。
再次,我们要区分日本民众与极右势力的不同。致使当前中日关系恶化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日本的极右势力,他们不仅是篡改教科书的主要力量,而且要求和支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由于日本政府某些领导人的错误意识与言行,使得他们近年来愈发猖獗。但是,他们的行为不仅遭到亚洲各国的强烈谴责和抗议,即使在国内也受到进步人士及群众的批评。日本右翼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2001年采用率和今年预计明年的采用率均不到0.03%,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在国内遭到抗议和违宪的起诉,都证明了日本民众要求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呼声。《每日新闻》近日民意调查结果,有76%的日本人认为小泉在对日中、日韩关系问题上“努力不够”,也说明日本右翼并不占多数。所以,我们必须将主张中日友好的普通日本民众与逆中日友好潮流而动的日本右翼严格区分开。
最后,我们还要区分今昔日本人的不同。对待历史问题必须懂得历史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人”的内涵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指导和发动以及参加和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如今所剩无几。据日本去年7月的统计,8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日本总人口的1.4%,[14]这即是说在今天的日本人中,98%以上者没有直接参与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战争,他们并不是战争罪恶的直接制造者。就今日广大的日本民众来说,尽管有日本政府错误意识的导向和右翼势力的猖獗活动,他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和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但是,继续中日友好、不欲再次发生战争,肯定是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意愿。有鉴于此,我们就应该虚怀若谷,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标签:中日关系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日本教科书事件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靖国神社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