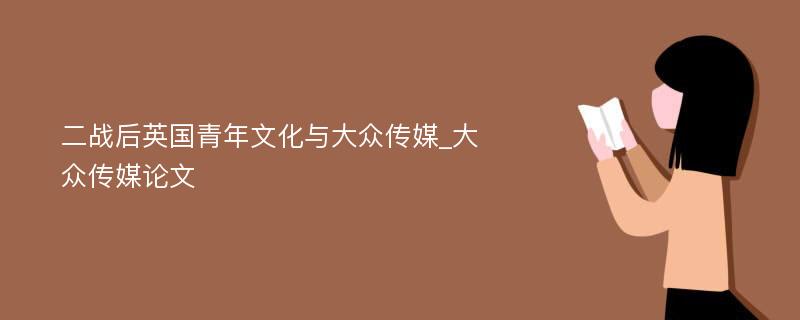
战后英国青年文化与大众传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战后论文,文化与论文,大众传媒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一个非常难以确切界定的概念,它可以涵盖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切成果,也可以指人类正在进行的一切活动。就研究青年文化与大众传媒来说,下面的解释也许更有价值。有的文化研究者将文化看成是各种各样的符号的体现,认为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都是文化的符号或文本。因此,文化的创造就是符号的创造,目的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这种传达的过程就是文化的传播。
从原始的口传文化阶段发展到近代的印刷文化阶段,再到现当代的电子文化阶段,文化与传播媒介相依相存的关系越来越明显,以至有了“媒体文化”这一词汇。青年文化主要是由青年创造、认同并传播的与生活主文化既关联又相对独立的,由观念、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组合成的亚文化系统。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的形成、发展以至后来的走向衰落,都是与战后英国媒体产业的发展分不开的。
一、文化与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所具有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文化传播与舆论扩散。大众传媒通过自己的报道,将社会中出现的现象、正在发生的事件和存在的问题传播给了普通大众,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文化传播与舆论扩散效应。发生在一地的事,通过媒体的报道能引起全社会的注意,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所知晓。随着大众报道的深入,公众对问题的认识也会随之加深,产生出不同的情感。但是,这种认识和情感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媒体报道导向的影响。媒体报道的视角和立场,会直接影响公众和社会权力机构对事件的评判,从而对整个事件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战后英国民众对青年亚文化的认识和接纳就受到媒体报道的左右。
另外,大众传媒本身也在塑造着文化,规范着人们的价值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人们原有的价值观受到挑战,处在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转换冲突中,对传统的社会有着本能的眷念,对新生的社会有着天然的抵触。这种冲突会使一部分人产生强烈的不适应感,使他们处于迷惘之中,对处于社会转型中的青年更是如此。对刚刚失去的世界他们没有老一辈的那分执著,对刚刚诞生的社会他们又有着太多的迷惑与失望。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诸多不满,大量的越轨、反叛行为随之产生。要结束社会上的这种无序现象,就必须来规范和引导大众建立新的价值观。大众传媒这时就承担起了这种职责。因为大众传媒的报道往往都暗含着主流社会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对大众的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人们建立起了与主流社会相适应的新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媒体文化在诱导个人认同于已经确立的社会价值观的同时,也为个人提供了反抗社会的种种资源。因此,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媒体所传达的意义和信息,他们对媒体文本有着自己独特的解读能力和批判性,从而创造出与主流价值观相抗衡的价值观,与主流文化不相符的亚文化,而这其中大部分都是青年。
大众传媒还有着构建个人、群体的文化认同性的功能。认同性是一种预订人的社会角色的功能,是一种传统的神话系统,它提供方向感和宗教性的支持,以确定人在世界中的位置,同时又严格地限制其思想和行为的范围。在传统社会里,个人的认同性是与其家庭出身、从事的职业相联系的;而在战后的消费和媒体化的社会里,认同性已经越来越和时尚、外表、形象以及消费等联系在一起了。这使得每一个人都不能没有自己个性化的外表、风格以及自身的形象。个人认同性的最终形成是依赖于他者的再认,这种再认过程的媒介就是大众传媒。“媒介在历史上对于想象国家社群发挥了核心作用;或许事实上,要是没有印刷媒介及随后的广播电视媒介的贡献,也不可能创建共同的文化群落和认同。”
传播、文化和认同三者之间有着一体的关系。传播技术是起决定作用的积极因素,而文化和认同是被动反应的因素。传播技术是因,认同是果,它因技术的“冲击”而形成并修正。媒体文化提供了构成人的世界观、行为乃至认同性的材料。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亚文化的群体和个人通过创造自身的文化符号、风格与认同性,来抵制主流文化与认同性的主导形式,在外表和行为上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二、青年文化与大众传媒
20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场伟大的革命,它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类文化传播的方式,文化自身存在的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战后,在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基础上,英国的传媒业也有了较快的发展。这时的发展不仅有技术的支持,还有社会的需求。在迅速变化的社会里,必然会出现行为方式、鉴赏方式和穿着方式的混乱。社会地位变动中的人往往缺乏现成的指导,不易获得如何把日子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知识。于是,电影、电视和广告就来为他们引路。
在英国,青年文化在爱德华时代,甚至更早的维多利亚时代就已出现,但只有到了二战后才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引起社会学家、文化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及普通民众的普遍关注。这主要是与战后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分不开的,更是媒体宣传的结果。传媒的发展给战后的人们带来的是新的价值观和新的生活方式,也为青年亚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战后,青年成为英国社会变化的代名词。媒体更是用一些闪亮的词汇来介绍青年,向大众传播这样一种观念:青年是一支新的社会力量,与令人厌烦的、老的传统社会秩序相比,他们是有活力的、令人振奋的。广告商也习惯使用青年形象,将他们富有活力的现代性、时髦的享乐的形象与产品的宣传相联系。但是,在媒体的报道中对青年一直存在着两面性:一面是对青年的需求积极的迎合,一面对他们的越轨行为却毫不宽容。媒体的这种两面性报道对大众产生了误导。
上世纪50年代初,英国媒体在报道两件犯罪案件时,就有意将这一犯罪行为指向某一个青年群体。一件是在1952年,19岁的德克·本特利用枪射死了一名警察,另一件是在1953年,20岁的米歇尔·戴维斯刺死了一名青年。媒体在报道这两个案件时,都特别关注了这两名青年的着装。他们华丽的“美国风格”的衣饰和行为被认为是与传统的文化和价值观相背离的化身。这一风格的着装经过媒体的渲染也就成了某一青年群的标志,任何穿着这一风格衣服的青年都被归入该群体,这一青年群体就是“特迪”。特迪(Teddy boy)又称无赖青年,20世纪50年代初在英国社会出现,主要由工人阶级青年组成,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特迪这一词是由媒体首先创造出来的,第一次出现是在1954年3月23日的《每日要览》(Daily Sketch)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将特迪描述为“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年轻暴徒”。1955年后,特迪就被认为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媒体将青少年犯罪与他们独特风格的服饰联系起来,服饰成为越轨的首要标志。1954年4月在肯特郡的一个火车站,两个敌对的特迪群体发生了一次帮派冲突,有超过50个青年参加。媒体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报道,这引起了官方对特迪问题的极大反应。特迪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犯罪行为的替罪羊,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摩擦增加。随后,任何穿着特迪风格衣服的青年都被禁止进入公共场所,穿着特迪服装的男孩不但被排除于青年俱乐部、舞厅、电影院和咖啡馆,而且在一个小镇他们被拒绝进入熟食店。
这种报道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甚至在特迪风格从主要城市消失后,他们留在人们心中的仍是流氓这一形象。实际上,特迪中倾向于暴力和流氓行为的只是少数。媒体对不同青年群体间的打架斗殴事件进行夸大其词的大肆报道,与社会控制机构、警察等对青年越轨行为持一致的训斥、指责的态度,致使越轨者更走向极端。这样媒体的宣传、公众的反应与越轨行为的增加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其实,青少年的胡闹、撒野与犯罪之间只存在着一条细微的界限。
60年代媒体对青年的态度仍没有多大变化。媒体将摩登派和摇滚乐者描述为一群“邪恶之徒”和“社会恶魔”,这直接影响到公众对这些青年群体的态度。另外媒体还渲染“道德恐慌”,认为青年的性开放已到了道德败坏的地步。媒体的这种报道起到了两种作用:一是使大众对青年产生误解,排斥青年文化;另一方面使青年文化在全国得到传播,使青年群体加强了自身的认同,使他们的风格也更加清晰起来。
在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上半叶,青年风格和青年文化主要是以某一地区为基础,只有有限的凝聚力和风格认同意识。然而,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媒体产业对青年市场越来越积极的回应,风格和时尚的变化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活力在普及。事实上,没有媒体的定格和宣传,像特迪、摩登、秃头等这些群体都只会局限在一地,不会有清晰的亚文化差异,不可能与19世纪就已存在的Scullter和 Peaky blinders等这些亚文化群体区别开来。
青年群体风格和认同性的形成是从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符号开始的。各种形象并不自身携带意义或“指代意义”的途径。它们积累各种意义,或通过一系列文本和媒介在它们的各种意义之间互相挑逗以获取新的意义。每一个形象负载着它自身特有的意义。起初每一个群体所具有的独特符号只有一个小范围内的人知道,但是媒体的宣传不仅使他们为更多的人所知道、辨别出来,而且也帮助他们最终确定了自身的风格。最明显、也最能表现不同风格的符号就是服饰。例如,嬉皮士们偏爱的是旧皮毛大衣、纱裙和军人大衣,嬉皮士女孩所追求的一般来说是古典式花边衬裙、纯丝衬衣、纱裙、天鹅绒短裙和1940年代流行的纯毛大衣,这些符号所承载的意义是他们对自然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特迪男孩模仿爱德华时代的服装式样,把自己装扮成密西西比投机商人的形象:披一件褶皱夹克、穿天鹅绒领、滚边裤、绉底鞋和靴带领结。特迪青年企图用盗用上层阶级的服装款式这种手段来掩盖他们是从事手工的、非技术的这种社会最底层的职业与更遭的生活境遇。这些亚文化群体必须展现一个足够独特的外形和风格,以便一眼便能被看出不同于他们的母文化。这些不同的符号就成为他们身份的标志,他们独特的认同性。
除了服饰,音乐、娱乐消费和其他商品都是构建文化认同性的资源。这种认同性通过媒体,特别是电视得到强化。美国的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在其著作《社会学》中,在解释嬉皮士运动的产生的原因时就提到了电视。他认为:“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对新奇事物的追逐”,是嬉皮士运动产生的三个关键的背景因素之一。战后,英国的电视对青年现象有着迅速敏捷的反应。五六十年代BBC和ITV的电视节目都向这一领域侵入。最初的节目像1952年的Hit Parade,1955年的Music Shop,1956年的Off the Record,对青年的欲求也是保持沉默的。然而到了50年代末,更正式的青年类型电视节目出现了,有1957年的Six-Five Special、1958年的Oh Boy! 、1959年的Fuke Box Fury。电视节目的制作目标也开始转变,从适合全家人观看到60年代早期就完全定位于适合青年人的欣赏口味。如1963年的Ready,Steady,Go! 就几乎没有考虑成年观众,节目的内容都是音乐、时尚和青年人喜欢的东西,特别是引进了60年代初时髦的亚文化。Ready,Steady,Go! 不仅仅是一档节目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是青少年模仿的一面镜子:他们的爱好、他们崇拜的明星、他们的穿着方式,所有这些都在这一档节目中有全面的反应。电视生动地强化了视觉象征符号的作用,视觉象征符号也构建了集体认同性。
在战后的英国,大众传媒与青年文化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二者互相借助,各谋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媒体积极主动地为青年文化作宣传,则是因为她已发现这是一个新鲜事物,蕴涵着无限的商机。通过对青年现象的报道和制作大量适合青年人口味的节目,媒体吸引了大批的观众,赢得了利润,这是它的目的所在。而广大青年乐于接受媒体的邀约,则是因为他们已认识到,单靠个人的口口相传的力量是有限的,不能产生全国的效应,不能扩大自身的影响。亚文化的风格通过媒体的宣传得以清晰化、大众化,最终定型下来。但是,英国的大众传媒一开始并没能很好地引导青年文化的发展,因而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今天,通过对它的回顾,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为我国青年文化的健康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媒体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