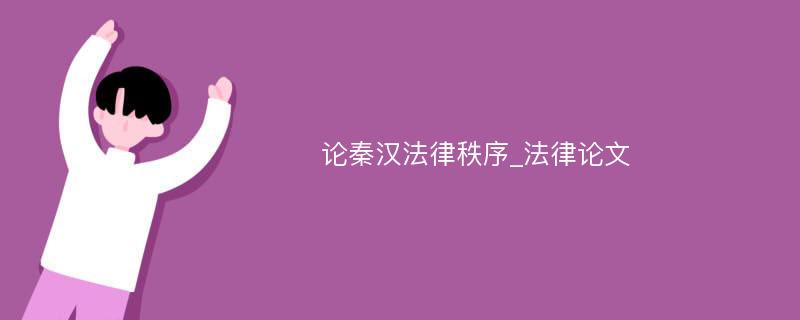
论秦汉的律与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92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18(2004)03-0024-08
律令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法律形式。自商鞅改法为律以后,律这种法律形式一直伴随封建社会始终。令这种法律形式在明朝中叶以后消亡,其内涵与律相比要复杂得多。令, 作为法律形式自战国以来就存在的事实,中国学者对此并无争议,倒是日本学者首先提 出了不同的意见。著名汉学家大庭脩先生在其著作《秦汉法制史研究》一书中通过对 睡虎地秦简的研究,总结了五项值得注意的特点,他认为:“睡虎地秦简中的二十七种 律是秦对商鞅六律的补充法,在秦代也有把补充法称之为律的可能性。这一点与在第五 项中提到的不存在秦令的文字这一特点有关。秦‘令’的文字之所以不存在,大概是由 于本来作为补充法的‘令’,把补充法称为‘令’的称呼制度在秦不存在。因此,笔者认为这个制度大概是在汉代创始的……在秦代,将正文的‘法’改称为‘律’,补充法也还叫做‘律’。……汉代以后的补充法也有对律的补充,大多被称为‘令’,只是秦令的存在与否目前尚不清楚。”[1](9—11)大庭脩先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在1977年发表的《云梦出土竹书秦律的研究》一文中仍然坚持己见。[1](64)他的观点 问世后,中国学界相当沉寂。20年后,张建国先生发表文章反对这一观点,他认为秦有 “令”这一形式存在,应当不是一个难于得出的结论。张先生还从典籍与简牍中滤出若 干条令文与令名。[2]2000年10月中旬,我和同仁们到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大庭脩先生 问我,你见到过秦令吗?当时,我对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一直不能理解,以大庭脩先生的 学识,他不会视史籍与简文中有关令的记载而不见,所以我只是说秦确有“令”,如《 商君书》中有《垦草令》。2002年5月5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日韩法律文化研讨会上,大 家又对此问题展开了讨论,中国学者都认为秦有令这种法律形式。大庭脩先生对自己 文章中“令”的含义作了说明,他说,秦未见汉代《令甲》、《令乙》这种起补充法作 用的令,这种作为律的补充的法律形式在秦是未见的。当时,限于时间关系,与会者未 能穷究,因此也一直未能真正理解他所讲的含义。因为《令甲》、《令乙》只是令在分 类编辑上的称呼,并不应涉及秦是否有令的问题。这说明我们与大庭脩先生对“令” 的理解上存在着距离,还没能理解大庭脩先生所谓“把补充法称为‘令’的称呼制度 ”的真正含义。现在,我们对秦汉律令的相关制度进行探讨,以期搞清楚这一争议已久 的问题。
一、秦律与秦令
秦汉两代的官文书与史籍中,往往律令并称,如湖南龙山里耶秦简JI 16 5、6的洞庭郡文书:“……它如律令。”[3]《汉书·司马迁传》:“汉兴,萧何次律令。”当时就同一项制度往往律、令并用,(注:秦汉出土资料皆见《金布律》;《汉书》卷78《萧望之传》:“故《金布令甲》曰……”颜师古注:“《金布》者,令篇名也。”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278页。)律与令在调整人们的行为时共同发挥着作用。但二者渊源不同,律的前身是三代的刑和法,以后演化为各朝的律典。令起源早于律,不同时代其内涵也不同。许慎《说文》:“令,发号也。”令最初为上级的命令,《论语·子路》“正其身,不令而行”,即指此意。《商君书》、《史记·秦本纪》等典籍都有秦国公布令的记载。由于令是国王的行政指令,因此令的法律地位高于律,律以国家名义颁布,律文不书年代;令以王的名义颁布,一般标书年代。由于令的地位高,故法律明文规定对违令行为的惩罚,睡虎地秦简(注:《睡虎地秦墓竹简》第211至212页,北京,文物出 版社1978。本文所引睡简皆出自该书,不另注。)(以下简称睡简)《法律答问》:
可(何)如为“犯令”、“废令”?律所谓者,令曰勿为而为之,是谓“犯令”;令曰为之弗为,是谓“法(废)令”殹(也)。廷行事皆以“犯”令论。
又睡简《内史杂》有“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史,犯令者有罪。”云梦龙岗秦简117亦规定:“田不从令者,论之如律。”[4](110)可见秦法对令的保护是相当严密的。
秦汉两朝的令在调整范围与方式上是有差别的,秦令文本身一般不包含处罚性条款,不服从令要按律的相关规定处理。江陵张家山汉简《奏谳书》18就反映了这种情况:
令:“所取荆新地多群盗,吏所兴与群盗遇,去北,以儋乏不斗论。”律:儋乏不斗,斩。[5](224)
这里令文对“儋乏不斗”做了补充解释,但是具体的处罚规则仍以有关律条为依据。二者规范的内容各有侧重。
秦国改法为律,当时律的制定频繁,调整范畴广泛,因此秦律内容丰富,篇名繁多。朝廷公布新律,增损旧律,不以令的形式发布,而以各种律名出现。从睡简可知,秦皆为单篇之律。律文不但规定刑事惩罚规则,也规定国家各部门及其官员的行为准则,亦即国家管理制度。对律文进行解释的有《法律答问》,廷行事具有判例法性质,这些法律形式从各个角度释义律,补充律。正是在商鞅改法为律和秦国变革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秦国以及后来的秦朝都无需以令的形式直接补充律文的不足,令的内容多侧重于国家的行政管理。这表现在:一方面它以令的形式颁布重要的改革措施,如《分户令》、《垦草令》等,这种措施具有紧迫性、临时性,随着形势发展,还可能转化为固定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上级官府也据令发布官文书,指导下级官吏的行动,如里耶秦简JI 16 5、6的洞庭郡文书:“廿七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卒史嘉、假卒史彀、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舂,隶臣妾、居赀赎责。急事不可留,乃兴繇。’……它如律令。”该令文规定的是移送官徒的制度。由此得知,秦令确实不是补充“六律”意义上的令。
这种情况到汉初有所变化,汉律篇目几十种,但以九章律为正律,刑律始终占据主导 地位。(注:《晋书》卷30《刑法志》:“……(《新律》)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 ,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据此推测,时人亦应以九章律为 正律。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25页。)汉廷对刑律的刑罚原则、刑制规范进行的修改,并没 有以新律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诏或令的形式颁发,如《汉书·宣帝纪》载:
(元康)四年,春正日,诏曰:“朕惟耆老之人,发龄堕落,血气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执囹圄,不终天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以上,非诬告杀伤人,佗皆勿坐。”
两汉时期,也以令的形式颁布新的惩罚规则,如《汉书·哀帝纪》绥和元年诏注引如淳曰:“名田县道者,《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令还规定新的行刑制度,《汉书·平帝纪》注引如淳曰:“《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这些诏与令是对“六律”的补充,也就是说是对刑律的补充。不过,汉令与秦令的法律意义不同,秦汉的诏、令内涵也不相同。诏最初是一种文体形式,其渊源久 远,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 者也。”始皇改制,命为制,令为诏。[6](卷6)后人往往诏令合称。然而作为国家法律 形式的令其内涵与诏相比要狭窄的多,有些诏可补令、入令,有些诏可补律、入律。有些诏只是单纯的一项命令,如《汉书·宣帝纪》:“(本始四年),诏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汉高诱《<淮南子注>叙》:“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应注意的是,有些诏虽是针对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事而发,但根据其性质,诏文的有些规定或著令或入律,这主要应从诏书的内容及其性质而定。诏入律或入令的过程,就是皇帝的指令由一次性适用到反复适用的过程,由特定的适用对象向一般的适用对象转化的过程。陈梦家先生考证:“令虽亦出于诏书,但著为令以后,书于三尺之木,而诏书所用木则短于此。据《汉制度》与《独断》,诏书之策‘长二尺,短者半之’,所谓尺一木或尺一版。”他在整理汉诏令简牍时发现,汉诏书简有二类,一类是各代皇帝当时所下的诏书,一类是作为“令”的诏书,二者长短有别。[7](275-289)这说明汉 诏、令有别是确切无疑的。在法律效力上,汉令与律是相同的,因此秦汉令是完全不同 的两种法律形式。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反映了西汉初年律令的内涵没有严格的区分 ,律令不但规定惩罚性规则,也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和人员的行为准则。(注:参见张家 山汉墓二四七号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二年律令>》所载二十七 种律令篇名,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1。)《二年律令》中的《盗律》、《贼律》等篇是刑罚规范,应归属九章律,为汉之正律,而《行书律》、《史律》、《赐律》、《秩律》等都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行为准则,属于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这些旁章之律在魏晋以后演化为令这种法律形式,(注:张建国:《叔孙通定<傍章>质疑》,《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张文认为,汉律分两类,凡不属于九章律篇目的,则为旁章。笔者认为,旁章即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类的律篇。)如汉时的《秩律》即相当于唐时的《禄令》。两汉律与令的区别在于,律是经国家有关机构制定的比较成熟的并以国家名义颁布的法律规范,而令则是根据统治形势的需要,经过一定的议定程序后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的法律规范,其主要作用是对律或对现有的令起补充法的作用,而秦之令则不具有这种内涵,说明令在秦汉两代的作用是不尽相同的。
二、补充法的汉令
汉令名称很多,有些令还没有名称,最初是以诏的形式下达的,算上这些诏令,数量更多。从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与程树德《九朝律考》等材料可知,有固定名称的汉令就达几十种,这些令在颁布形式和对律的补充作用等方面是不同的,上文已论证,两汉时无论是诏还是令,其调整范围比之秦令宽泛的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汉之诏令直接对 刑律起补充法的作用。我们将两汉诏、令总括起来,按其功用和调整范围,分为如下三 类。
第一类,这类令属国家制度规范,是为规范国家机构建制、各部门管理制度而制定的 ,包括五个方面:
1.国家管理制度规范。这类令是国家某一行业或某一领域内的规章制度,程树德《九 朝律考》所辑这类令有:《宫卫令》、《津关令》、《符令》、《戍卒令》、《功令》 、《祠令》、《斋令》、《水令》、《田令》、《公令》、《卖爵令》、《秩禄令》、 《品令》、《任子令》等。
2.国家机关行为规范。如《御史挈令》、《大尉挈令》、《廷尉挈令》、《卫尉挈令》、《光禄挈令》、《大鸿胪挈令》。
3.地方机关行为规范。如《乐浪挈令》、《北边挈令》、《兰台挈令》等。
4.诸侯、国戚行为规范。如《汉书·哀帝纪》绥和元年诏注引如淳曰:“名田县道者,《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后汉书·皇后纪》:“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置《令甲》”。
5.军事规范。其中包括军事管理之令,如《兵令》、《军斗令》、《合战令》、《□捕令》和特别事项之令,如捕斩单于令等。(注:参见《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塞115号汉墓木简》,《散见简牍合辑》第40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兵令》见《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II90DXT0114,《文物》2000年第5期,第37页。)
第二类是刑罚制度规范,其中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内容:
1.确立刑罚原则。这类令很多,汉廷确立新的刑罚原则都是以诏令的形式颁布的,如《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夏五月,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是汉廷首次以诏令的形式明确将“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这个规定对中国的法律制度影响至深。(注:梁治平认为,汉时“相隐”原则的出现要早于此时,可备一说。参见梁文《古法丛谈》,载《文史知识》1990年第1期,第77-78页。)
2.规定刑制。即以令确立罪名、罪状与惩罚规则,《汉书·韦玄成传》记高后时,定著令,敢有擅议汉宗庙者弃市。此为以令规定罪名。《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 月,顾山遣归。”(注:《汉书》卷12《平帝纪》注引如淳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1页 )此为以令规定对女犯的施刑方式。《汉书·江充传》注引如淳曰:“《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汉书·江充传》注引如淳曰:“《令乙》,‘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这些是以令规定对官吏违法行为的处罚。
第三类即图表中所列C类令,为讯系程序规范。这部分包括有《棰令》、《狱令》等。 《汉书·刑法志》:“(后元)三年复下诏曰:……。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 孕者未乳,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又《汉书·平帝纪》:“(平帝)四年,诏曰 :……其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 捕,它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定著令。”这类令规范内容属程序法范畴。《棰 令》、《狱令》虽也属国家制度,但属司法狱政范围,汉六律包括这部分内容,故划入 此类。
表1:汉诏令类别图表
A
1.管理制度规范(《金布令》、《津关令》、《功令》、《水令》等)
国 2.国家机关行为规范(《御史挈令》、《廷尉挈令》、《大尉挈令》、《卫尉挈
家令》等)
制 3.地方机关行为规范(《乐浪挈令》、《北边挈令》、《兰台挈》)
度 4.诸侯、国戚行为规范(《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后
规 汉书·皇后纪》:"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置《令甲》")
范 5.军事制度规范a.军事管理规范(《军斗令》、《合战令》、《□捕令》)
b.特别事项之令(捕斩单于令)
B
1.刑罚原则规范(《汉书·宣帝纪》:"是年五月,诏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
刑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
制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规 2.刑制规范(《汉书·韦玄成传》:定著令,敢有擅议汉宗庙者弃市。《令乙》:
范"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令乙》:"跸先
至而犯者,罚金四两。")
讯 《汉书·景帝纪》:"后元年,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
系 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棰令》
程 、《狱令》
序 《汉书·刑法志》:"(后元三年)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未乳、
规 师、侏儒当鞠系者,颂系之。"
这三类汉令反映了这种法律形式的丰富内涵。从三类令的作用看,国家制度规范、诸侯、国戚行为规范与军事管理规范属于“立制”法。由于这类令是以国家某一部门或某一类事项为调整对象,因此一般都有固定的令名。最初这类令都是诏,经过法定的程序议定后,才成为与律的效力相同的令。诏文中的“著为令”、“议为令”、“具为令”等就反映了这种情况。[8](258)这种规范国家制度之令的效力比较稳定,几经修订,仍会以令的形式出现。《汉书·儒林传》:“……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它如律令。”颜师古注曰:“新立此条,请以著于《功令》。《功令》,篇名,若今《选举令》。”《汉书·宣帝纪》注引文颖曰:“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说明天子之诏有的入律,有的为令。这类令与规范刑制的律泾渭分明,作用不同,为晋唐令的渊源之一,成为晋唐以后与律并存,形式及内涵都固定的重要法律形式。魏晋以后二者的区别才基本清楚,即“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唐六典》卷6《刑部》)“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新唐书》卷56《刑法志》)、“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太平御览》 卷638,《刑法部(四),律令(下)》)、“违令有罪则入律”(《晋书》卷30《刑法志》) 。
国家制度规范中的A2、A3两类令本质上不属于“立制”之令,这些令不是各部门自行撰定的法律,而是各部门根据其职责的需要对国家颁布之令的摘编。[9](34-39)秦汉官 府摘编国家律令是一个传统,《新简》EPF22:一五九、一六○:“檄到,宪等循行, 修治社稷,令鲜明,当侍祠者,斋戒,以谨敬鲜絜约省为故,如府书律令。”[ 10](481)这里的“府书律令”即有关职能部门抄录的国家法令。由于是摘编,各挈令之 间常常有重复的现象,《王杖十简》:“兰台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卅。”即此王杖诏令 在兰台令的第三十三篇,在御史令的第四十篇。又《王杖诏书令》:“□右王杖诏书令 在兰台第卅三”即王杖诏书令在兰台所编辑之令的第四三篇。[11](18)因此,这类令并 非创制之令。
B类令是调整刑罚制度的,其内容包括刑罚原则规范和刑制规范,均属实体法范畴。这类的诏、令对旧律增损变动,颁布时虽以诏或令的形式,其作用却与律同。这类的诏令显然不具备“立制”之令的作用,而是对律起补充法的作用。《汉书·杜周传》:“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讲的就是前代之诏入律,后主以诏、令的形式对律进行修补。这类令的内容具有转化为律的内在要求,国家修律之时,可入律,颁诏之际 则以诏令的形式干预律的实施。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讲的律是刑法规范,亦即正律, 而非旁章。人们对汉令律的理解常因这条材料产生误解,以为凡当朝之诏过后即成为律 。实则不然,根据前代诏令所规范的内容,有些诏入律,即“天子诏所增损”,“在律 上者”。而“不在律上者”,凡规范国家制度之诏,经过必要的程序后,则归属在令这 种法律形式之列。有些诏则只能是当朝之诏,永远不会成为法律形式的“令”。单纯的 将汉时律令理解为前主后主之间的时代关系,必将混淆律令的界限。杜周所言,一方面 说明了当朝皇帝诏令的地位高于律,另一方面也说明有些诏令适时必然入律。这类入律 之诏、令演化为隋唐时的敕格,它与上面所述A类令功用截然不同。不做上述类别的划 分,无法深刻理解汉律令的区别。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又可将汉令从调整功用上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真正的令,它 的制定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属于国家制度的设制之令,即除A5b以外的全部A类令。第二 类是补充律作用的令,即B、C两部分,这类令中虽然有些令起初是以诏的含义颁布,但 其功用主要是对刑罚制度进行调整,起刑律的作用。
我们特别注意到大庭脩先生所讲的,秦未见像汉代《令甲》、《令乙》这种起补充法作用的令,他认为这种补充法性质的令应当就是汉代创始的。秦律以各种单篇之律的形 式出现,修补增损亦以律的形式,也就是以律补律,而汉对律的补充、修改则先以诏的 形式下达,诏的地位显然高于律。秦之令即始皇改制后的诏,在法源分类上其实质就是 最高的行政命令,而汉令则是国家法律形式的一种,这是秦汉令在形式上的区别。汉令 繁多,西汉初年曾分为甲、乙、丙三类,这类令就其出台而言都需经过“具为令”、“ 议为令”、“著为令”的过程,一但诏成为令,其地位、性质与律异曲同工,二者效力 实相同。从这两点上分析,大庭脩先生讲作为补充法的令是汉代创设的意见是正确的 。如果认为大庭脩所说的只是秦未见像汉代《令甲》、《令乙》这种令集的形式,那 问题本身提的就没有意义了。
三、令甲、令乙与令丙
汉代律令繁多,以至当时就有人指出其不便,《盐铁论·刑德》载:“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 ?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愚民乎?”宣帝曾下诏清理律令,(注:《汉书》 卷8《宣帝纪》:(本始四年夏四月壬寅)诏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 ”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45页。)后虽经廷尉于定国主持整理,但律令仍达960卷。和帝 时大臣陈宠亦言:“……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晋书》(卷30)《刑法志》)律令如此繁多,必然需要按一定的规则编辑,我们所见典籍中的《令甲 》、《令乙》、《令丙》就是汉初所编之令集。但是,甲、乙、丙的分类标准是什么, 汉魏以来就没有统一的认识,至今仍然意见纷纷。总括起来,有如下观点:第一种是年 代先后说;第二种是篇目次第说;第三种是诸令各有甲、乙、丙说;第四种是集类为篇 说。徐世虹君以为,以上诸说中,1、2说就年代、篇次而言似无大碍,而对3、4说却颇 不以为然。她认为,“《令甲》、《令乙》、《令丙》是汉初皇帝的诏令集,所收诏令 在内容上不具有同类性质,排列方式采用序列法,按年代顺序列为第一、第二、第三… …。又根据文帝、景帝不同时期的诏令交叉出现于甲、乙、丙三令之中,可知甲乙丙除 表明篇次外还反映了整理者对诏令非单纯年代划分,而取其重要的选择结果。”[8](26 5)按她的观点,令甲最为重要,令乙次之,令丙又次之。她的观点从某种角度讲是有道 理的。不过,时代先后论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一点,陈梦家先生论证已详。[6](275-28 4)篇目次第说其本质仍然是以时间先后为序排列。诸令各有甲乙丙说,在《汉书·萧望 之传》中有一条材料似乎得到了证明,其文曰:“……故《金布令甲》曰:‘边郡数被 兵,离饥寒,夭绝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颜师古据此认为:“《金 布》者,令篇名也。……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但此说与其它有关汉令的所有记载 都相矛盾,如《晋书·刑法志》:“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若按颜说 ,则此三百余篇必为某一令之三百篇,其下还应有乙及丙,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故此说不足取。《萧望之传》中的《金布令甲》,其意应是《令甲》中《金布令》, 汉令绝不可能存在诸令各有甲乙丙的情况。汉令分类界限的歧义从另一角度也说明汉令 的划分并不是很科学的,这与当时的编辑技术水平有关。其时律目篇章亦多混杂,“自 典文者不能分明”,(《汉书》卷23)正如《晋书·刑法志》评说汉律时的情形所言:
“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无常。”
由此推知,汉令内容混杂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汉令甲乙丙的分类也并非绝对没有标准,汉令“集类成篇”的观点还是值得探讨的。
现所见涉及《令甲》内容的材料共有七条:
1.《汉书·吴芮传》赞:“著于《甲令》而称其忠也。”
2.《后汉书·皇后纪》:“向使因设外戚之禁,编置《令甲》”。
3.《宣帝纪》:地节四年九月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
4.《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六月“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注引如淳曰:“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遣归。”
5.《哀帝纪》绥和二年六月“有司条奏,诸王、列侯得名田国中。”注引如淳曰:“ 《令甲》:诸侯在国,名田他县,罚金二两。”
6.《汉书·叙传》:“……务在农桑,著于《甲令》,民用康宁,述《景纪》第五。
7.《续汉书·律历志》永元十四年“太史令舒、承、梵等对: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
上引第1、5条材料涉及诸侯国制度。第1条记载并非单纯的表彰吴王忠,应与诸侯王制度有关。第2条是关于外戚制度的规范,这当然属于国家制度的一部分。3、4所论为刑制规范。第6条是诏令郡国劝农桑,涉及对百姓农事的管理制度,也与侯国有关。第7条 是关于律历时刻的法律规定。从上可以推测,《令甲》所规范的内容为国家管理制度与 国家刑制规范。另甘肃居延地湾出土的5·3,10·1,13·8,126·12(甲2551)札所载 诏书目录中的县置三老、行水兼兴船、置孝悌力田、征吏二千石以上符、郡国调列侯兵 ,陈梦家先生认为可能是《令甲》目录,这些令也都是对国家管理制度的规定。[7]上 述材料说明,这类令规范的行为主体多为政府官员、诸侯王或外戚,基本上应属我上面 所划分的A类令。第4条材料虽为刑制规范,但为一种新的刑事处罚的设制,故归入《令 甲》。孔颖达对《易经》的一段正义对我们认识《令甲》的编辑原则颇有启示:
《易·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正义曰:“甲者,创制之令,既在有为之时,不可因仍旧令。今用创制之令以治于人,人若犯者,未可即刑罚,以民未习,故先此宣令之前三日,殷勤而语之。又如此宣令之后三日,更丁宁而语之。其人不从,乃加刑罚也。其褚氏、何氏、周氏等并同郑义以为甲者,造作新令之日。甲前三日,取改过自新,故用‘辛’也。甲后三日,取丁宁之义,故用‘丁’也。今案:辅嗣注‘甲者,创 制之令’,不云‘创制之日’。”
我们抛开“甲”到底是指创制之日,还是创制之令不谈,诸儒注甲,皆以甲有创制之 意。诸儒何以谓“甲者,创制之令”,因汉令编辑时将创制之令集为《令甲》。从现存 《令甲》内容看,都是对国家重要制度的创设,故称《令甲》为创制之令并无不当。
从《令乙》的有关记载,我们再来推测《令乙》内容。
1.《汉书·江充传》:“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尽劾没入官。”注引如淳曰:“《令乙》:‘骑乘车马行驰道中,已论者,没入车马被具。’”
2.《汉书·张释之传》:“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注引如淳曰:“《令乙》:‘跸先至而犯者,罚金四两。’”
3.《晋书·刑书志》引《魏律·序》:“《令乙》有呵人受钱。”
4.甘肃武威东汉墓简:“民作原蚕,罚金二两,在乙第廿三。”[12]
上引《令乙》各条,除武威东汉简外其规范的对象都是官吏的违法行为。(注:《汉书》卷50《张释之传》所载中渭桥犯跸一案,其行为人确为平民,但分析该条文的立法本意,最初应是规范官吏的,平民犯这些罪的可能性较小。)《魏律·序》涉及《令乙》的部分讲的是将汉时若干律令中的罪名整理归类,制定新律,其文曰:
《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晋书·刑法志》)
由此可知,汉时这些由《杂律》规范的内容,《魏律》将其归入《请赇律》。我们推测《令乙》规范的主要内容是对官吏行为的调整,汉时属《杂律》的范畴。这类令的内容属刑制规范,相当于上面划分的B2类令。
现存有关令丙的资料很少,共有二条材料,其一是《后汉书·章帝纪》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棰长短有数。”其二是《晋书· 刑法志》引《魏律·序》“《令景》有诈自复免。”(当时因避唐讳,改丙为景)推测《 令丙》所规范的一是讯系程序方面的内容,汉时在《囚律》范围;另一方面是对平民这 类主体的犯罪行为的调整。这类令一部分应归属于上面所划分的C类令中,另一部分应 属B2类令。
上面我们分析了秦汉律令的相关制度,说明两朝律令的内涵存在一定的差别。令虽然 至迟起源于战国时期,但在秦廷那里,令的属性还是王或皇帝的指令。由于秦国的法律 改革,律这种法律形式相对发达。两汉时期,诏的调整范围扩大,有些诏经议定后转化 为令。当时,除以诏、令“立制”外,还以诏、令的形式对刑律修补增损,起到了“补 充法”的作用。作为法律形式的令,在汉廷需要法定的程序,这种性质的令在秦是不存 在的,但却为汉廷重要的法源之一。秦汉律文除刑罚制度规范外,还包括国家各机关及 官员的行为准则,即国家行政制度。汉时刑罚制度规范在九章律中,为汉之正律,涉及 国家行政管理制度的律篇为旁章。晋唐令的形成除源于汉时的“立制”之令,即本文所 划分的A类令外,汉之旁章也是晋唐令的重要渊源。史载武帝以后律令篇目膨胀,以后 各代都曾修增蠲除,汉律篇目的增损只在旁章部分,至于正律九章,其篇目未变,只是 律文内容的变化。魏晋制律,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扩大了正律篇目,律的刑典地位 进一步得到确立,而原有的旁章之律则不宜再称之为律,故有依类编定令典之制。正是 由于曹魏编撰刑典《新律》十八篇,及两汉原本存在大量规范国家制度的令,才使两汉 规范国家制度的律篇不再称律,而统称为令,此时律令的形式、调整范畴与作用才分道 扬镳,各显其功能。汉时律令调整范围的交错,律令种类的丰富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律令 的形式与内涵还没有固定,还处在向魏晋律令演化的阶段。
收稿日期:2003-1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