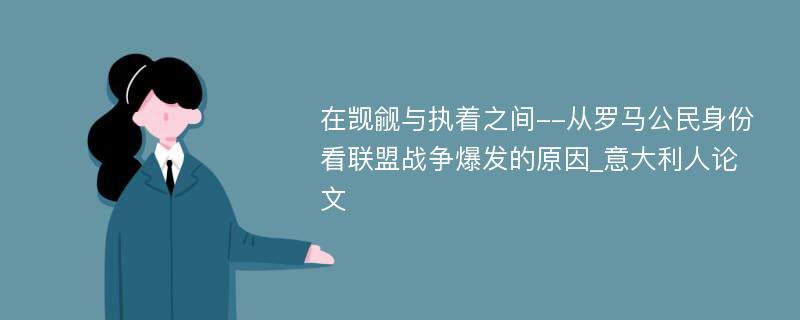
觊觎与固守之间——罗马公民权视角下同盟战争爆发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权论文,罗马论文,同盟论文,视角论文,战争爆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意大利人①罗马公民权问题是罗马共和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议题之一,对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乃至于国家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意大利人追求罗马公民权主要出于对平等政治地位的渴望,而罗马人之所以拒绝,则源于他们的短视——不论平民还是显贵,皆局限于各自眼前利益,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代价。②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国外学者逐渐发现上述观点并非与事实完全相符。谢林-怀特(A.N.Sherwin-White)认为,在绝大多数意大利人眼中,相较于政治权利,他们更珍视罗马公民权中具有人身保护功能的消极权利;③而伽巴(Emilio Gabba)主张,意大利人主要出于经济目的而垂涎于罗马公民权;④莫瑞特森(H.Mouritsen)则从城邦体制角度指出,罗马人之所以顽固拒绝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除维护既得利益外,更可能顾虑由此引发城邦规模与城邦体制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城邦的本质内涵阻碍了公民权的大规模扩散。⑤对此,国内学者似乎缺乏必要回应。虽然国内不乏对于意大利人公民权和同盟战争讨论,但主要基于罗马人的角度,鲜见从意大利人角度全面而具体考察他们的动机,并且在论及罗马拒绝的原因时,大多未站在罗马人的立场上,考虑由此可能给他们带来的现实困难,而是仅一味地指责罗马人目光短浅。⑥因此,在古典资料和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试图首先分析在意大利人眼中,罗马公民权具有的优势地位,说明意大利人为何千方百计追求它,继而考察意大利人追求罗马公民权的各种手段及其结果,最后从罗马角度分析其拒绝的真实原因,由此说明意大利人的积极追求和罗马人的执意拒绝造成了无法和解的困境,最终导致同盟战争爆发。
一、令人称羡的特权:意大利人眼中的罗马公民权
经过历次战争,至公元前3世纪罗马完全征服了意大利半岛,至前2世纪前半期,又相继获得对迦太基和马其顿战争的胜利,由此确立了其在整个地中海世界的霸权地位。而罗马公民权的优势地位与罗马帝国的霸权地位紧密相连。随着罗马霸权地位不断的强化,附属于罗马公民权之上的权利不断增加,因此罗马公民权逐渐成为一种令人称羡的特权。在意大利人眼中,它的优势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权利。前2世纪以降,随着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世界统治地位的确立,财富纷纷涌入罗马,公民因之大为受益。首先,免税权。前186年,赔款、战利品、行省的收益使得国库充盈,罗马当局利用这一收益,向公民补偿了近25年来所征收的附加税。⑦自前167年起,免除公民缴纳直接税(tributum)的义务。⑧很明显,不论一次性补偿还是长期免税权,都仅为罗马公民所独有,因为罗马人才是帝国的统治者以及最大的受益者,虽有部分利益流向意大利,但意大利各邦的受益程度远未使其免除本邦公民的直接税。因此,意大利人无法从帝国剧增的收益中获得相应比例的税收特权。
其次,土地权。按照罗马法律及习惯,只有作为城邦一员的公民才能参与土地分配和殖民计划。⑨虽然罗马也曾创建拉丁殖民地,允许拉丁人及部分同盟者参与其中,但前177年后,罗马再未建立此类殖民地。而在被征服过程中,作为曾经的失败者,意大利各邦的土地多多少少被罗马剥夺,无力为其公民提供土地分配和殖民机会。⑩并且前2世纪以降,意大利小农破产增速,要求参与土地分配和殖民的愿望更为强烈。在土地占有方面,罗马法为其公民的土地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护;意大利上层虽持有大量罗马公地,却因为无罗马公民身份,时刻面临着被剥夺的危险;特别在前2世纪后半期,罗马政坛分配公有土地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意大利人所占公地可能朝不保夕。(11)因此,在意大利人看来,相较于从前,罗马公民权带来的合法占有土地的权利显得更为可贵。
再次,商业权利。罗马公民权带来的商业权利也让意大利人羡慕不已。伽巴甚至认为,同盟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意大利商人阶层希望通过获得公民权,迫使罗马采取更富扩张性的对外政策,以满足其商业利益。(12)虽然他的观点遭到广泛质疑,(13)但综合而论,即使商业权利并无伽巴断言的那么重要,但从中亦可见罗马公民权具有的强大商业优势。例如罗马公民可获得利润丰厚的国家公共工程及税收的承包权等,而意大利人根本无法染指。此外,对于居于行省的罗马人来说,罗马公民权还能使他们免于当地捐税。更何况,公元前2世纪最后几十年内,意大利人更频繁地参与了罗马帝国对行省的掠夺。因此,对于意大利的商贸阶层来说,罗马公民权意味着更多的商贸机会和特权。
最后,其他经济权利。在社会福利方面,罗马公民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救济粮。自提比略·格拉古以来,罗马政府逐渐认识到国家对贫穷公民负有一定的社会救济责任,开始售发廉价粮食,且规模和力度不断增强。(14)而罗马公民资格是参与这一分配盛宴的门票。同时,在政治收益方面,附属于公民权的政治权利——投票权的收益也在增长。前2世纪以降,随着罗马社会财富的剧增以及政治竞争的激烈化,选票日益成为公开商品,价码也愈来愈高。一旦获得罗马公民权,公民可将手中的选票待价而沽。此项收入虽不稳定,但考虑到罗马每年召集的投票会议达50多次,城市贫民从中受益不一定丰厚,但大概足以弥补一时的生活短缺。此外,凭借着政治中心地位,罗马城娱乐活动,例如节日庆典、公共表演等,在数量和规模都有很大增长。各类娱乐宴饮聚会之后,往往伴有罗马当局或者政治家发放粮油酒肉之类物资的慷慨行为,(15)相对而言,意大利各城市因为缺乏罗马的地位和财富,与罗马相比,相关活动的规模和力度难以企及。这些皆是构成罗马公民权在经济上优势地位的重要因素。
第二,人身保护功能。人身保护功能,属于罗马公民权消极权利方面的内容,虽然很少为古典史家所强调,国内学者也鲜有关注,但却是罗马公民权不可或缺的部分。更关键的是,随着帝国霸权的建立,罗马官员帝国主义作风也日益增长,罗马公民身份对人身保护的优势更为突出。
罗马公民权的人身保护功能主要体现在申诉权上,“任何官员对罗马人加以死刑、鞭笞、罚款等处罚时,该公民有权上诉,要求人民裁判。在上诉期间,人民投票表决之前,官员不得对之施加惩处。”(16)因此它能使公民免遭罗马官员无限制的治权压迫和迫害。实际上,罗马法对公民人身保护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共和国建立之初,“他(普布利乌斯·瓦勒里乌斯)向公民建议,百人团会议通过的第一项法律是禁止任何行政官因某个罗马公民上诉而处死或者鞭打该公民。”(17)该法保护了公民不受行政官员擅权行为的侵害。前449年执政官卢修斯·瓦勒里乌斯·普提图斯和执政官马库斯·霍雷修斯·巴巴图斯提出一项法律对申诉权进行补充,规定不得选举不受上诉制约的行政官员。(18)前300年出台的瓦列里乌斯法进一步限制了行政长官的治权,禁止对任何上诉的公民实行死刑或者鞭笞,重申了公民向公民大会,对包括独裁官在内高级官员的判决提请上诉的权力。(19)上述立法使向民众申诉成为罗马诉讼制度的内在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罗马法对公民权益的保护还随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强化。“前2世纪以降,罗马对公民的保护力度又大大增强,相继颁布了三部保护公民的波西乌斯法,和一部禁止鞭笞公民的法律,同时立法将申诉权的范围扩展到军事领域。”(20)这意味着,即便战时,罗马公民也能够免于指挥官的即时任意制裁。其后“盖乌斯·格拉古颁布的森普洛尼亚法重申不经人民审判不得处以死刑的规定”。(21)事实证明,罗马公民资格是公民自我保护的强大盾牌。虽然威勒斯在西西里横行无忌,但面对西西里富裕的罗马骑士和商人对他的怨恨和反对,也不敢随意勒索或迫害他们。(22)
相较于罗马公民权的强大保护能力,意大利各邦显然无法为本邦公民提供有效庇护。随着帝国主义作风日渐增长,罗马官员把在行省作为征服者的姿态和行事作风带到意大利,视意大利人为属民而非同盟者。在汤恩比看来,罗马人已经变成了意大利人的残酷霸主,虽然意大利人的司法地位没有变化,但实际地位已经恶化了。(23)罗马官员到处抢劫神庙,勒索钱财,对意大利人随意使用暴力,而意大利人却无可奈何。一方面,意大利各邦的法律明显无法约束罗马官员、保护本邦公民;另一方面,意大利人也无法寄望于罗马法的保护。因为相对于罗马人,他们是异邦人,而异邦人处于罗马法治外,无法依据罗马法向罗马人民大会申诉。(2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古代城邦对其公民的保护能力是建立在城邦实力之上,而意大利各邦在实力上根本无法与罗马相提并论,因此,其公民权的保护能力必定逊色于罗马。
第三,政治权利。正如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以说他是那一个城邦的公民”。(25)可见,对公共事务特别是政治事务的参与被视为古代公民权的核心内容。公民权能够为其持有者提供相应的政治身份。一般而言,城邦地位高低直接决定着其公民政治权利的大小。
与罗马相似,大多数意大利城邦也实行城邦制度,公民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投票权和任职权。显而易见,作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罗马公民理所当然是世界之主,可以用投票权随意裁决帝国内的各项事务;意大利各邦虽为罗马同盟者,但被视为地位低下的属民,(26)不仅无法左右地中海事务,甚至城邦内部事务,也不时受到罗马人的直接干涉,无法完全自行决定。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意大利各邦公民的政治权利已被罗马人架空。因此,就投票权而言,罗马公民的选票无疑代表着更为充分和广泛的权利。
同样,对于罗马和意大利公民而言,附属于各任职权之上的实际权利相差巨大。作为地中海世界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罗马官员享有的无上的权威和尊荣,是帝国地位的外在体现。而意大利官员虽在本邦内部具有一定权威,但是这种权威仅限于本邦民众,无法囊括居于城邦内部的罗马公民。更何况,一旦走出城邦狭小的范围,其权威将不复存在。甚至即便在本邦内,如果他们不具备罗马公民身份,也可能遭受罗马官员的无情羞辱。(27)不仅如此,罗马的任职权背后暗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随着帝国的扩张,至前一世纪中期,罗马已经建立了十几个行省,由卸任高级官员全权管理。因为行省远离罗马,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一旦获得行省职位就意味着难以想象的厚利。即使号称清廉的西塞罗,在塞浦路斯担任一年官职后,也满载而归。因此,相较于意大利诸邦,罗马的任职权意味着更大的独断权力和更丰厚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除上述所论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实际优势外,作为征服者,罗马公民身份还能带来巨大的心理优势,为其公民提供无与伦比的心理满足感。(28)当然,罗马公民权各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截然分开。例如,罗马法能有效地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充分的政治权利必然又能够增强公民的自我保护能力。因此,对于意大利人来说,罗马公民优势地位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各个方面,并且罗马公民权作为一种复合权利,它的实际优势地位及对意大利人的吸引力可能超出了分列的各项之总和。
二、艰辛的斗争:意大利人为获取罗马公民权而进行的不懈努力
随着罗马公民权特权地位日益彰显,“利益使意大利对罗马的向心力增强”,(29)因而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渴望也逐渐增强。诚然,罗马公民权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但其扩散速度明显不能满足意大利人的需求。因此,意大利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来谋求。大体而论,其手段主要可分为两大类。
首先,利用迁移权、婚姻权、收养权等各种权宜手段。诸多手段之中,迁移权简单易行,是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最常用手段。据罗马法,常住罗马的拉丁人将自动获得罗马公民权。因此,如果拉丁人迁居罗马,便能够获得公民权。(30)虽然迁移权附属于拉丁权,在意大利诸邦中,仅拉丁人享有,但实际上,无迁移权的同盟者只需稍加迂回,同样可以借此谋取公民权。相较于罗马公民权,拉丁权易于获得,因此,同盟者先设法取得拉丁权,再移民罗马即可。(31)利用该方式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拉丁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前187年罗马驱逐拉丁人的数量多达1万2千。(32)不过,前2世纪以降,由于拉丁城市抱怨大量人口迁居罗马,致使当地人力资源短缺,无法为罗马提供足额的士兵,为此,罗马不断驱逐拉丁人,并对迁移设置了诸多障碍。前187年,罗马立法规定只有在原居城市留下一子的拉丁人才准许移民罗马。然而,这并未能有效抑制拉丁人迁移热情,因为他们完全可以通过收领养子的方式轻松规避该法。鉴于此,前177年,拉丁人再次向元老院投诉移民问题,驱逐事件便再次发生。(33)同时,在拉丁城镇的帮助下,罗马又一次收紧了迁移权。甚至有学者断言,此后,拉丁人通过迁移权谋求罗马公民权的合法途径可能就此堵塞。(34)
除迁移权外,意大利人还千方百计地采用其他迂回之策。例如享有通婚权的意大利人可以通过与罗马公民缔结合法婚姻,婚生子女可获罗马公民权;被罗马公民收养而获得公民权;假装使自己沦为罗马公民的奴隶,再由该公民通过合法的手段解放后,获得被释奴身份,进而取得公民权;在监察官进行人口普查之时,采取贿赂或者欺骗手段混进公民名录。(35)这些途径虽不失为谋取罗马公民权的可行之策,但是并不牢靠,因为罗马随时有可能再次实施驱逐政策。前126年,班努斯提出一项排除外国人的法案——班努斯法,数以千计的移民被剥夺公民身份,(36)至前95年穆西亚法(Lex Mucia)通过时,又有“一万人将会面临着被剥夺公民权之虞”。(37)虽然驱逐活动是应拉丁人的请求,但显然罗马统治阶层也乐意将非法公民赶出罗马。(38)历次驱逐行动表明,一方面,在欲望的驱使下,意大利人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罗马公民权;另一方面,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公民权充满风险,随时可能被罗马当局剥夺。反复出台的驱逐立法表明,此路并不畅通。
其次,支持罗马改革家旨在扩大公民范围的立法活动。当使用各种迂回策略追求公民权连遭挫折后,意大利人不得不另觅他途。前2世纪20年代后,意大利人致力于寻求并支持提出授予其公民权议案的罗马改革家。最先提出授予拉丁人公民权议案的是夫拉卡斯,(39)阿庇安记载,“福尔维阿斯·夫拉卡斯在他的执政官任期内第一次最早公开地煽动意大利人要求罗马公民权,使他们成为罗马帝国的共同参加者而不是属民。”(40)上述措辞可以看出,夫拉卡斯此举无疑是顺势而为,并得到意大利人支持。当议案被挫败后,他退而竞选保民官,设法使盖乌斯·格拉古成为同僚。前122年两人联合提出公民权法案,试图将公民权授予拉丁人,并将拉丁权授予意大利人。(41)该方案提出后,即刻得到意大利人热烈响应,甚至有一群意大利人闯入罗马表示支持,但被执政官法尼乌斯(Fannius)强行赶走。(42)不得不提及的是,此前,盖乌斯第一次竞选保民官时,可能也涉及意大利人公民权问题。大批意大利人赶赴罗马进行声援,其数量之巨,以至于部落大会的常用会场——罗马广场都无法容纳,主持者不得不将会场迁到面积更大的马尔斯广场。但仍有许多意大利人无法挤入会场,只好在附近的街道、屋顶上呼喊。(43)尔后,小格拉古被杀害,“意大利人更加激动了。……或者想到夫拉卡斯和格拉古为他们的政治权利奋斗而受到这样的灾难,这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44)
小格拉古失败后,意大利人公民权问题一度淡出罗马政坛,至公元前1世纪90年代,该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因为他们(意大利人)恳切要求,允许他们,说他将提出一个新的法案来,给他们以公民权。”(45)所以前91年小德鲁苏斯提出议案,拟将公民权授予所有意大利自由人。(46)但不幸再次上演,小德鲁苏斯被杀身亡,其议案随之流产。此时,罗马当局非但没有采取任何安抚意大利人的措施,反而通过了审判帮助意大利人争取公民权者的昆塔斯·发里阿斯法案,“当意大利人知道德鲁苏遇害以及其他的人被放逐的原因的时候,他们认为那些为他们的政治权利而努力的人遭到这样的暴行,他们不能再容忍了,因为他们看到没有可以取得罗马公民权的其他方法,他们决定完全叛离罗马人,以全力对罗马人作战。”(47)
总体而言,前2世纪以降随着罗马公民权优势地位日益凸显,它对意大利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大。为了获得公民权,意大利人采取了多种多样的途径。最初主要的举措是通过包括迁移权在内的各种合法或非法策略谋求公民权,不过这些途径逐渐受到限制,甚至被完全堵塞。然而,这并不能浇灭意大利人对罗马公民权的渴望。前2世纪20年代后,意大利人通过罗马的改革家,将问题捅到罗马政坛,竭力通过立法途径寻求根本解决。不幸的是,从夫拉卡斯到小格拉古,再到小德鲁苏斯,各种公民权方案相继以失败而告终。现实表明,意大利人无法通过和平方式达成所愿。战争,可能已经成为唯一的解决之路。
三、罗马的忧虑:拒绝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之缘由
虽然,扩散公民权是罗马的一项传统政策。自建城以来,罗马不断授予被征服者公民权,此乃其发展壮大的一大法宝。但是,总体看来,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大多建立在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在此情况下,小规模向外授予公民权并不会影响罗马统治阶层以及政治的稳定性。然而,前2世纪以降,面对意大利人日益高涨的热情,罗马人在公民权问题上变得越来越保守,不断执行剥夺、驱逐意大利籍罗马公民的政策;前2世纪20年代至前1世纪90年代,改革家们提出的公民权提案相继被否决,无一成功。究其原因,罗马人大致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量:
首先,罗马元老害怕意大利人威胁其绝对统治地位。面对意大利人对公民权的要求,“元老们一想到要使属民变为和他们平等的公民,就很愤怒。”(48)他们的愤怒主要基于对其绝对统治地位不保的担忧。在罗马城邦体制之下,常规官员由选举产生,唯有选票才能铸就显贵。然而,一旦普遍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选民的数量和分布将出现急剧变化,势必改变罗马现有的选举和权利分配格局,威胁显贵对罗马政治的绝对控制能力和统治权利。
长期以来,罗马元老和意大利精英之间建立了较为密切的保护关系网,他们分处于保护人和被护人地位。正如贝迪安指出的,这是一张不平等的关系网,某种程度上,正是通过它,罗马上层得以控制意大利精英。一旦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身份,取得与罗马元老相等地位,可能会造成“因为普遍的平等,罗马显贵将会丧失通过保护关系控制意大利领袖家族的能力。”(49)不仅如此,任职权也刺激着众多意大利精英跃跃欲试,一旦他们加入竞争本已相当激烈的官职争夺战中,就可能“使元老院本身被意大利人所淹没”,(50)削弱甚至颠覆显贵的绝对统治地位,这绝对不是罗马元老愿意看到的结果。
前2世纪末期以降,马略为代表的新人用事实证明了扩散公民权给罗马元老造成的威胁。“在这次当选之前,他(马略)对权贵就是敌视的。因此,一旦人民决定把努米底亚分配给他,他就坚持不懈,勇敢地攻击起权贵来:时而攻击的对象是个人,时而又是整个的显贵一派。他夸口说,他从权贵手里夺取的执政官职位是他的战利品,还有别的一些意在夸耀自己和激怒对方的话。”(51)“他们(权贵)瞧不起我卑微的出身,我还瞧不起他们的庸懦无能呢!”(52)当然,马略和权贵之间的敌视带有相当强烈的派别斗争色彩,但亦反映出新公民与把持政坛的元老之间对政治地位和权力的激烈竞争。此后的历史发展证明,罗马元老的地位确实因此备受威胁。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近三十年后,西塞罗感慨道:我们元老中,非自治市出生的人何其少啊。(53)
此外,普遍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还可能致使罗马元老的竞选成本大幅增加。一旦将公民权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集体的数量及分布范围将发生巨变。同盟战争前后公民数量情况是:“前93年,公民的数量40万;而前83年,猛增至103万”。(54)由此可见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后,罗马公民的数量膨胀之巨,且分布范围也将扩展至北到波河,南及墨西拿海峡的广大地区。公民数量和分布范围的变化迫使罗马精英不得不将游说范围扩散至整个意大利半岛,此举意味着他们必须为竞选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更高的成本。更重要的是,选举高级官员的百人团大会按财产等级规则运行,根据财产多寡,公民们被登记在不同的等级之中。其中,富人占有绝对优势,对选举结果起决定性作用。一旦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权,意大利精英阶层以及拥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农民将会凭借财富跻身较高等级,其选票对于罗马显贵来说极具分量。并且因为与意大利中下层往往缺乏联系,罗马精英必须通过刻意拉拢意大利上层以争取中下层的选票,这必然导致他们对意大利上层的依赖性更强,“如果意大利的统治阶层突然意识到他们集体的重要性和巨大力量,保护关系可能更难有效维持。”(55)
元老对新公民威胁其绝对统治地位的担忧充分体现在他们对待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法案的态度和具体行动中。对于任何建议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提案,他们总是最积极的反对者,先后成功地阻挠了夫拉卡斯、小格拉古以及小德鲁苏斯的公民权法案。甚至到战争爆发的前一刻,面对意大利人的最后请求,元老院依然冷漠如故,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意大利人。(56)可见,元老院宁愿将整个半岛拖入战争也不愿意赋予意大利人公民权。
不可否认,罗马统治阶层中,也不乏富有远见的政治家主张和支持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虽然其中不乏个人利益的考量,(57)但毕竟和帝国长远利益相吻合。不过上述夫拉卡斯、盖乌斯、小德鲁斯的命运已经表明他们终究孤立于统治阶层,无法获得大多数元老支持。
第二,罗马平民阶层不愿与意大利人共享权益。罗马平民对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的态度前后有所波动,但总体上还是持反对意见。前125年,夫拉卡斯首次提出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时,罗马平民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感。毕竟,相较于抽象原则或者统治权,平民最为关心的是实际利益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似乎和他们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能够得到自己的利益即可。”(58)据阿庇安的描述,平民大体是支持夫拉卡斯的,并为其离去感到惋惜。当夫拉卡斯归来后,平民依旧坚定支持他和小格拉古。(59)然而,在保守元老煽动下,平民的感情很快发生了逆转。保守元老成功地使他们相信其利益将会因此受到极大损失。前122年,在反对格拉古的演说中,执政官法尼乌斯(Fannius)向平民绘声绘色地陈述了他们可能遭受的损失:“如果你们给予拉丁人公民权,你们认为在大会上还有你们的空间吗?你们认为你们还能像现在一样参加节日庆典或公共事务吗?”(60)确实,这些并非无稽之谈。如上文所言,一旦广泛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除因罗马公民集体规模将剧增而削弱老公民选票的分量外,更重要的是,按照财产等级原则,意大利地区众多的精英以及地主大都会登记在高等级,其选票势必比罗马城市平民的选票更有价值,这无疑会压缩罗马平民的投票空间和选票力量,进而影响他们的实际利益。
虽然法尼乌斯的演说仅有片段留存,但从中已能推断,除了上述内容外,他接下来定会论述下列威胁。平民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损失可能是分配土地机会的缩减。如前所述,公民资格是参与土地分配和殖民的门票。大约在前177年后,罗马搁置了土地分配以及殖民计划。提比略·格拉古之时,为解决罗马小农问题,罗马再次启动土地分配计划,但参与者仅限于罗马公民,非公民并不在计划之内。(61)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后,意大利人将由此获得参与土地分配的入场券。这必会从两个方面压缩罗马平民的分配机会。一方面,土地的申请人数可能极大增加。如前所述,广泛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后,罗马公民集体规模将会大幅增长。更重要的是,与罗马小农一样,前2世纪以降,意大利小农破产现象也呈上升趋势。因此,有理由相信,相当数量的意大利人必将积极申请土地分配或殖民机会,分走相当大部分本应属于罗马平民的土地。另一方面,可能导致公有土地资源更加紧缺。实际上,罗马大量公有土地被意大利上层实际占有。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希望获得罗马公民权,因为“公民权能使意大利人获得对其占有的大量公地的合法控制权力。”(62)正如霍华德所言,“对意大利人来说,如果罗马公民权不是暗含着对土地的保护作用,那么它便一文不值。”(63)可见,一旦意大利人获得公民权,罗马就更难迫使其放弃公地,从而使可兹分配的土地更为有限。老德鲁苏斯提出在意大利建立12个殖民地方案后,民众立即放弃小格拉古而支持他,这充分说明罗马平民强烈希望通过剥夺意大利人所占公地而获得土地。(64)因此,对于罗马平民来说,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意味着大幅度减少自身获得土地的机会,这自然难以得到他们的支持。
对于罗马城市平民而言,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土地分配机会,还有其他一系列特权。西塞罗很好地概括了这些特权,“如果接受我的指导,罗马人啊,你们就能继续享有你们的影响、自由、选票、尊严、城市、广场、赛会、节日,以及其他所有欢愉。”(65)确实,相较意大利人,罗马城市平民拥有无可比拟的公共资源,例如赛会、节日庆典、会场以及救济粮等等,为城市平民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益处。但这些资源数量毕竟有限,当分配范围极大扩展后,每个人所得份额就会相应减少。对于已享有相关特权的公民来说,这无疑就是巨大损失。
因此,在法尼乌斯等保守元老的煽动下,罗马平民开始坚定地和显贵联合起来,反对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对于小格拉古方案,“他们不满盖乌斯将罗马人选举官员的权力授予所有拉丁人”;(66)至前91年,他们的态度并未有多大转变。小德鲁斯为了劝诱平民支持其公民权法案,“他领导了几个殖民团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去。”以换取平民对其方案的支持,“平民因为可以分得土地的原因,才对小德鲁斯的法案比较满意。”(67)但从根本上说,他们可能仍然不愿意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直至同盟战争,没有任何方式比建议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更能丧失人民支持。”(68)虽然巴迪安的话语有所夸张,但确实较生动地反映了罗马人民的态度。总体来看,改革家的公民权法案赢得了意大利人的支持,但终究无法获得罗马人民的支持,因而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
第三,城邦体制与公民权扩散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虽然与希腊诸邦有所差异,但从本质上讲罗马国家仍是城邦国家。(69)城邦是小国寡民的产物,其体制得以正常运行正是建立在其较小规模之上。希腊城邦一般不过数千人,最大也不过数万人。(70)早在前2世纪初,罗马公民数量已达到几十万。对于罗马城邦来说,“面对领土的不断扩大,简单的单一城邦组织已不能适应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的要求。”(71)一旦广泛授予意大利人罗马公民权,不论在观念上还是现实中,罗马城邦将都难以承受。从城邦角度看,广泛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可能会给罗马城邦造成下述难以弥补的恶果。
首先,财政负担加重。长期以来,罗马并不向意大利人征税,仅在必要时要求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士兵,其费用由意大利人自行承担。而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则意味着罗马要承担全部军事费用,罗马的军事支出将随之大幅上涨。因为同盟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罗马公民兵。同盟战争前夕,意大利人声称为罗马人提供的兵力是罗马本身的两倍;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证明,前2世纪以降,在罗马的军事扩张中,意大利人贡献了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兵力。(72)但与此同时,罗马财政收入却不会因为公民数量剧增而有所增加。因为自前167年,罗马已免除了公民缴纳直接税的义务。因此,对于罗马财政来说,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意味着收入保持不变,支出却成倍增加。
相较于财政困难,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后,老兵安置问题将会更加棘手。马略军事改革后,降低了征募士兵的财产要求,很多穷困公民得以入伍。战事结束后,他们有理由期望获得安身立命的一小块土地。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后,众多入伍的贫困意大利人将会和罗马士兵一样,寄望于兵役结束后获得土地;因其公民身份,罗马政府亦无法拒绝他们参与殖民活动和土地分配的要求,这将使土地的需求量大增。但提比略·格拉古设立的土地委员已将大量公地分配殆尽,可兹分配的公地所剩无几。因此老兵土地问题更为棘手。为解决此问题,苏拉、庞培、恺撒等不得不斥巨资购买土地,甚至屠杀灭绝城市以安置老兵,(73)可见,由军事改革以及扩散公民权所带来老兵安置问题将会关乎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存亡。
其次,行政管理和司法压力。如前所述,对于罗马城邦来说,“面对领土的不断扩大,简单的单一城邦组织已不能适应行政管理和司法活动的要求。”(74)公民权扩散到整个意大利后,城邦体制更难有效运行。因为,在城邦体制下,代议制度并未萌芽,公民必须亲自参加各项事务;官僚体系虽早已产生,但仍相当简单,且数量有限,必须依靠公民的配合才能有效行使职权。例如,对于罗马监察官来说,最重要的事务是人口普查,一旦公民权广为扩散,该事务将难以操作。按照罗马传统,监察官发出普查通告后,公民必须亲往罗马城,汇报家庭人口和财产状况。但意大利半岛面积如此之广,北部波河流域与南意大利远离罗马达数千里之遥。在古代交通条件下,一次往返需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更关键的是,民众或许根本无法知晓准确信息,更谈不上及时赶赴罗马登记。同样,军队征募和人民大会的召集也会面临类似困境。
从法律角度看,罗马公民权实质上是一种法律身份,其权利和地位是通过罗马法得以体现和保障的。随着公民权的扩散,罗马法的适用范围将扩展至整个意大利。但是,意大利半岛民族众多、地区差异颇大,各地区的法律习惯和传统风俗,甚至语言都不尽相同。在这些地区如何有效执行罗马法,实为难题。同时,法庭系统也会面临巨大压力。(75)罗马至格拉古时期才开始设置常设法庭,唯一有判决公民死刑的机构是人民大会,一旦意大利所有刑事案件都集中到罗马,罗马仅有的法庭和人民大会势必难以应付。
最后,社会问题。在公民权扩散造成的诸多社会问题中,移民问题无疑最为突出。其实,移民问题困扰罗马已久。如前所述,前188年、前177年、前126年、前95年罗马相继发生驱逐意大利人的案例。虽然主要缘于意大利之请,但也反映出罗马难以应付该类问题。一旦意大利人获得罗马公民权,移民问题无疑会极度恶化。前2世纪以降,因为征服带来的丰富资源以及各种福利措施相继实施,例如救济粮、各类娱乐活动、候选人的慷慨捐赠,使罗马城市平民享有各种益处,由此,罗马城魅力大增,必定会吸引大量意大利人来到罗马。无限制的移民必定会给罗马城市带来诸多社会问题。例如,秩序问题、就业问题等等。有些移民为生活所迫,只能出卖选票、良心和身体,充当罗马政客的鹰犬和打手,加剧着罗马政治环境的混乱,暴力活动的滋长。更重要的是,一旦意大利朝夕不保的贫民大量集中于罗马,势必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甚至会威胁国家生存。
除了上述可能产生的实际困难外,城邦观念与大规模扩散公民权的现实之间的冲突也阻碍着罗马授予意大利人普遍的公民权。“罗马是根据城邦的模式发展起来的,这种模式深深地植根于古代人的观念之中。”(76)小国寡民和直接参与制度是城邦的内在特征,一旦将公民权授予千里之外的民众,共同的城邦生活对于他们而言变成了虚设,这与人们根深蒂固的城邦观念相违背。仅从公民权角度看,传统上,罗马城邦的公民权具有强烈的排外性,与其他城邦的公民权不能兼容,即使前124年双重公民权概念出现,罗马公民权的排外性虽有所消弭,但古老的城邦观点和习惯并不会因双重公民权概念的出现就能马上消散。正如古朗士所断言。“只要是在共和国时代,没有人会想到罗马人及其他民族可合成一国。罗马虽然欢迎某些被征服者,准许他们居住在城内,使他们渐渐地变为罗马人,但它不能将整个异族都纳入罗马,将全部异族的土地都变为罗马的疆土。这并非是由于罗马的特别政策,实在是出自一种上古的普遍原则。”(77)
综上所述,前2世纪以降,随着罗马在地中海世界霸主地位的建立,附属于罗马公民权之上的实际权利不断增加。相较于意大利其他各邦,罗马公民权的优势地位非常明显,不仅体现在传统观点所强调的政治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作为一种复合权利,它的整体优势以及对意大利人的吸引力超过了各方面优势的简单相加,因而极大刺激着意大利人追求的热情。他们以种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谋求罗马公民权,但这些途径逐渐被堵塞。前2世纪20年代后,意大利人开始支持罗马改革家提出的公民权议案。但这些方案皆被挫败。究其原因,除了传统观点所强调的罗马人民目光短浅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城邦本身来说,此举不仅与罗马固有的城邦观念相冲突,也会造成城邦体制之下难以解决的实际困难。例如,在财政、行政管理、司法活动以及社会问题等方面。城邦体制及城邦观念也是罗马人长久以来拒绝意大利人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对意大利人的积极追求,罗马始终没有授予意大利人公民权。意大利人觊觎罗马公民权的狂热与罗马人固守城邦体制和城邦观念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最终战争成为解决矛盾的唯一途径,同盟战争由此爆发。战后的历史也证明,罗马公民权广泛扩散确实导致罗马城邦的规模和体制之间失去平衡,原有的城邦体制无法适应庞大国家的运作,加速了罗马城邦以及共和体制的崩溃。正如格兰特所言,“当大部分罗马公民不再能够参观首都的时候,旧的城邦体制已经过时了。”(78)
[收稿日期:2013年4月2日]
注释:
①本文“意大利人”指代对象包括拉丁人和同盟者。
②[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1、34页。
③A.N.Sherwin-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39-149.
④转引自A.N.Sherwin-white,"Review Le Origini della Guerra Sociale ela Vita Politica Romana Dopo 1'89ac by Emilio Gabba",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y,Vol.45(1955),pp.168-170.
⑤H.Mouritsen,Italian Unification,London: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1998,p.111.
⑥宫秀华:《论罗马征服和统治意大利的政策》,《史学集刊》,2001年第1期;宫秀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化”进程》,《东北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4—168页。
⑦Liv.39,7,5,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XI,trans,by Evan T.Sage,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239.
⑧Plut.Aem.Paul.,38,in Plutarch,Lives,Vol.VI,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453.
⑨C.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38.
⑩Randell S.Howard,"Rome,the Italians,and the land",Historia.Zeitschrift Alte Geschichte,Bd.48(1999),p.293.
(11)关于意大利人对所占公地的担忧见:[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6—38页。
(12)转引自A.N.Sherwin-White,"Review Le Origini della Guerra Sociale ela Vita Politica Romana Dopo 1'89ac by Emilio Gabba",pp.168-170。
(13)P.A.Brunt,"Italian Aims at the Time of the Social War",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Vol.55(1965),pp.90-109; A.N.Sherwin-White,"Review Le Origini della Guerra Sociale ela Vita Politica Romana Dopo 1'89ac by Emilio Gabba",p.168.
(14)[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19页。至恺撒独裁时,领取免费粮的人数量达32万之巨,参见Plut.Caes.55,in Plutarch,Lives,Vol.VII,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571。
(15)Israel Shatzman,Senatorial Wealth and Roman Polities,Bruxelles:Latomus,1975,pp.84-88.
(16)A.R.Boak & W.G.Sinnigen,A History of Rome to A.D.565,London:The Mcamillan Company,1977,p.81.
(17)[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 法律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81页。
(18)[古罗马]西塞罗著,沈叔平、苏力译:《国家篇 法律篇》,第81—82页;Liv.3,55,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II,trans.by B.O.Fost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85。
(19)黄风编著:《罗马法辞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66页。
(20)S.Hornblower & A.Spawforth eds.,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 ed.revis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268.
(21)S.Hornblower & A.Spawforth eds.,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 ed.revised,p.1268.
(22)A.N.Sherwin-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pp.143-144.
(23)A.J.Toynbee,Hannibal's Legacy,Vol.2,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106-115.
(24)[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8页。
(2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13页。
(26)[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19页。
(27)公元前2世纪罗马人欺凌意大利人的案例相当多,例如人身暴力侵犯、抢劫神庙、敲诈勒索、强制征募等,分别参见Gell.10,3,3-5,in Aulus Gellius,Attic Night,Vol.II,trans,by John C.Rolfe,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217-221; Liv.40,44,12; 31,12,1-5; 32,26; 42,3; 30,45,4; 26,14,9; 45,42,4-5; 45,43,9,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VII-XIII,trans.by Evan T.Sage,Frank Gardener Moore & Alfred C.Schlesing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2003,pp.137-144,37-39,347-349,299-301,359,57,397-401,403。
(28)[英]M.I.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3页。
(29)H.Mouritsen,Italian Unification,p.44.
(30)S.Hornblower & A.Spawforth eds.,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 ed.revised,p.790.
(31)[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第213页。
(32)Liv.39,3,4,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XI,p.225.
(33)Liv.39,3,4,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XI,pp.225,Liv.41,8,6-9,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XII,pp.207-209.
(34)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Oxford:Clarendon Press,1967,p.150; A.N.Sherwin-White,The Roman Citizenship,p.107.
(35)[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第213页。
(36)Cic.3,47,in Cicero,On Duty,Vol.XXI,trans,by Walter Mill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315.
(37)Diod.37,13,in 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Vol.XXI,trans,by Francis R.Walton,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p.217-219.
(38)Liv.39,3,4,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XI,pp.225; Liv.41,8,6,in Livy,History of Rome,Vol.XII,p.207.
(39)莫瑞特森认为授予对象可能更窄,仅包含占有罗马公有土地的意大利人。见H.Mouritsen,Italian Unification,p.113.
(40)[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31页。
(41)[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21页。
(42)[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21页。
(43)Plut.C.Gr.,3,in Plutarch,Lives,VoL X,trans,by Bernadotte Perrin,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03-205.
(44)[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31页。
(45)[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31页。
(46)[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33—34页。
(47)[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31页。
(48)[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19页。
(49)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179.
(50)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179.
(51)[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2页。
(52)马略出身于骑士阶层,其出生地阿尔皮努姆直至前188年才获得罗马公民权。参见[古罗马]撒路斯提乌斯著,王以铸、崔妙因译:《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第344—345页。
(53)Cic.3,15,in Cicero,Philippics,Vol.XV,trans,by Walter C.A.Ker,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205; Cic.24,in Cicero,The Speech in Defence of Publius Cornelius Sulla,Vol.X,trans,by C.Macdonald,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pp.335-339.
(54)杨共乐:《罗马社会经济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09页。
(55)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189.
(56)[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35页。
(57)M.Cary,H.H.Scullard,The History of Rome down to the Death of Constaintine,Hong Kong:Macmillan Press LTD,1935,287.
(58)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187.
(59)[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17—34页。
(60)转引自Fergus Millar,"Politics,Persuation and the People Before the Socal War(150-90B.C)",The Journal of Roman History,Vol.76(1986),p.10。
(61)C.Nicolet,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p.38.即便在提比略前133年提出的《森普洛尼亚法》中,仅有公民才是受益者,同盟者并无资格。
(62)Randell S.Howard,"Rome,the Italians,and the Land",p.293.
(63)Randell S.Howard,"Rome,the Italians,and the Land",p.293.
(64)[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21、22页。据莫瑞特森分析,小格拉古选择远赴阿非利加而非就近在意大利建立殖民地,源于大格拉古时期设立的土地分配委员会将罗马国家直接掌握的公有土地已经分配殆尽,剩下的基本上掌握在意大利上层手中,为了避免触怒他们,小格拉古只好去海外建立殖民地。而德鲁苏斯提议在意大利建立12个殖民地,大概基于剥夺意大利人所占公地的设想之上。参见H.Mouritsen,Italian Unification,p.145。
(65)Cic.2,27,in Cicero,On The Agrarian Law,Vol.VI,trans,by John Henry Freese,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339-401.
(66)Plut.C.Gr.9,in Plutarch,Lives,Vol.X,p.217.
(67)[古罗马]阿庇安著,谢德风译:《罗马史(下卷)》,第32—33页。
(68)E.Badian,Foreign Clientelae,p.152.
(69)[英]M.I.芬利著,晏绍祥、黄洋译:《古代世界的政治》,第17页。
(70)[古罗马]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第63页。
(71)H.Mouritsen,Italian Unification,p.42; P.A.Brunt,The Fall of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p.109.
(72)H.Mouritsen,Italian Unification,p.42; P.A.Brunt,The Fall of Roman Republic and Related Essays,p.109.
(73)[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1页。
(74)[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第158页。
(75)H.Mouritsen,Italian Unification,p.111.
(76)[意]朱塞佩·格罗索著,黄风译:《罗马法史》,第212—213页。
(77)[法]库朗热著,谭立铸译:《古代城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49页。
(78)[英]迈克尔·格兰特著,王乃新、郝际陶译:《罗马史》,第1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