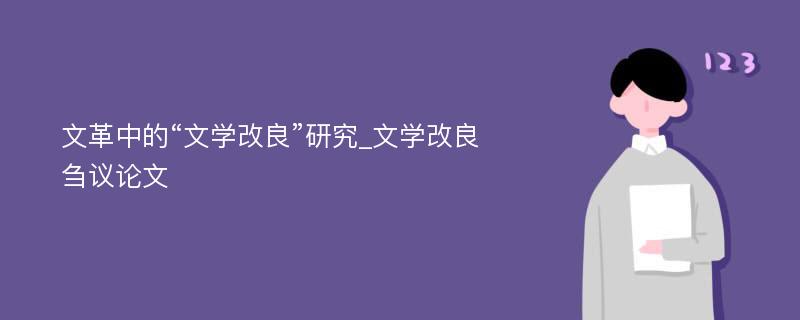
《文学改良刍议》考——关于文学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刍议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0)05-0017-05
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翌年,1919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于是,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这难免不使人想到,此事是否在三人的周密策划下进行的?实则不然,如同其它许多改革运动一样,它也是许多偶然的巧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云,当初他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是受了钱玄同的劝说,才动手写《狂人日记》的。同样,陈独秀与胡适二人也是不约而同的。个中原委,拙文拟详加陈说,并就《文学改良刍议》之产生、特征及在中国所引起的反响略作论述。
一、与陈独秀的接触
1916年3月3日,胡适曾给陈独秀写过一封关于翻译的信,也开始了两人关系的探讨。溯源应从此信说起。胡适在信中道:虽然翻译西方名著是新文学创造中不可缺少的,但应对作品进行严格选择,要选择一些与中国人心理相近的好作品。他指出,《新青年》(时名《青年杂志》)第1卷2期上连载的《意中人》并无翻译价值,他把自己据美译本翻译的俄国小说《决斗》同时寄给了陈独秀。后来,译作及信函一并刊于《新青年》第2卷1期。
胡适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8月)离开中国,此前是否有过与陈独秀接触的经历尚不能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陈独秀作为他的安徽省的同乡,他是早就对其有所注意了。在《新青年》创刊的初期,他就对该刊的未来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同年8月21日,胡适给陈独秀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已提到后来作为《文学改良刍议》基本精神的“八事”。该信后来刊到1916年10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2卷2期上。
陈独秀在10月1日的复信中,对“八事”的精神表示热烈赞同。可以想象,这会给胡适带来多大的鼓舞,其后不久,胡便寄出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这在他的12月26日的《留学日记》中有明确记载:“近作数文,记其目如下:一、《文学改良刍议》(寄《新青年》)。……”综上所述,将《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上,使之面世的确乎是陈独秀其人;但不能由此便断言,惟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先发动者,因为就在两人仅限于书信往还的阶段,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构想即已成型了。
二、留美体验
那么,《文学改良刍议》的构思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中之原委,胡适在自传性著作《逼上梁山》中有详细记述。我们从中了解到,在留美期内的1915年夏天,东美的华人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e and Sciences),并召开了年会。发言者有赵元任和胡适二人,他们都是1910年赴美的同届留学生。
赵元任发言的题目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赵元任就国语罗马字化的可能性作了论说,胡适就文言教授问题作了论述。胡文之主旨,我们从其《留学日记》中,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现阶段文言乃全国唯一通用书面语,终不可废置。2.汉字乃视觉文字,仅凭朗诵不能全面理解其意。3.教授半死的文字(视觉语言—文言),应废弃以诵为中心的方法,先行译为活文字(听觉语言—白话),再行教授。此外文章还有很多论述,而按作者主旨,纳其要者,大致为以上三点。
当时,将北京语音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尚未被世人所认同。赵元任生于天津,精通北京话,是位有天生语感的语言学家。年会之后,他即埋头于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汉语拼音化工作。然而,如果让胡适与之同行,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胡适出生于安徽,从广义上说,安徽亦属北方官话区,但安徽话与北京话却有不少分歧。而且,同许多外地出生的读书人一样,胡适年轻的时候,也并不热心于北京话的学习,这从他1914年7月4日的《留学日记》中便可窥知:
音韵之不讲也久矣。吾辈少时各从乡土之音,及壮,读书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读遂不复注意,今虽知其弊,而先入为主,不易改变。甚矣,此事之为今日先务也。
彼时,乡音各异的仁人志士们欲靠口语交流,恐怕要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还要难。他们为了让对方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不得不常常借助英语,当年他们在年会上发言,用的就是英语。
胡适关注语音的统一问题,始于留学时代,受赵元任影响非浅。然而,他虽对赵元任的主张深表敬意,却并未介入文字拼音化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更为有意思的是,那一时期,胡适非但没有提倡白话文,反而还充分肯定了文言文存在的意义。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他其后突然转变态度,提倡起白话文的呢?
三、文学革命的开端
胡适的转变,是从他把文言说成是“半死的文字”开始的。那个夏天,胡适同其他同学在东美的绮色佳度假,谈议中,他成了朋友们攻击的对象。其详情他在《逼上梁山》中是这样记载的:
这时我已承认白话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个夏天,任叔永(鸿隽)、梅觐庄(光迪)、杨杏佛(铨)、唐擘黄(钺)都在绮色佳(lthaca)过夏,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从中国文字问题转到中国文学问题,这是一个大转变。这一般人中,最守旧的是梅觐庄,他绝对不承认中国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为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变的更激烈了。我那时常提到中国文学必须经过一场革命;‘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
胡适是在那时第一次使用“文学革命”一词,而正是这个词,给后来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历史的大转折。从文中可以看出,“文学革命”并不是他预先即有运筹的,这从《逼上梁山》的题目上也看得出来。
五、从文字论争到文学论争
胡适何以称文言为“半死的文字”,而称白话为“活文字”呢?我们有必要作一定的探讨。
在汉语中,每一音节都有相对应的汉字,汉字总量超过5万,即使常用汉字也达数千之多。与此相矛盾的是,现代北京话的发音仅有400多种,即使按声调不同来计算,也只有一千上下。依靠听觉,用这一千上下的语音,去识别几千万的语义,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从前,赵元任曾用"shi"音的数十个汉字连成一句戏言,如用眼看,是很容易明白它的意思的;而用耳听,则是一连串的"shi"音,不知所云。这种矛盾,在以单音词为主的文言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民众不仅听不懂,也看不懂。
这种语言能够存在下来,靠的全是汉字。胡适把充满弊端的文言称作“半死的文字”,所据正在于此。本来,他未必曾非常在意新旧或雅俗的区别,更不用说执意追求废除文言,强迫他人守旧或革新了。但是他的朋友却不这样看他,在朋友的眼中,他是个赶时髦的传统破坏者,是个媚俗斥雅的俗物崇拜者。结果,是他出乎意料地成为了众矢之的。
如果争论仅仅停留在语言方面,情势还会和缓得多,虽然在此问题上,较之主张音标拼音的赵元任,他算是保守的。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问题,把争论的焦点从文字转到文学上来,情况就大不相同了。这从他的《留学日记》中就领悟得出来。
白话诗通过朗诵就能听懂,胡适立志于白话诗的写作为时甚早。归国后,他曾出版过《尝试集》,不过几乎没有新作。倒是留学以前就业已尝试的词的创作,数量陡增不少。
词最早出现于唐代,是从为广泛传唱的曲子填词发展而来的一种特殊样式。到了宋代,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固定下来。它在用词方面,白话词汇较多,比诗的语言简明浅显,句子也长短不齐富于变化。这些特点与现代白话诗虽有本质不同,但在格调类型中,却有很大自由。胡适可能从词的形式中,悟出了白话诗的刍形。
单就诗来说,较之唐诗,他更喜欢简明易懂的宋诗,并且还写下几首宋诗风格的作品。而单就唐诗说来,较之音律严谨、文法上破格较多的今体诗,他更喜欢简易的乐府和古诗。
那一时期,他还常有“文文字”、“诗文字”的议论。此处的“文”,系指散文;“诗”,系指韵文。他主张“要须作诗如作文”,即以写散文的格调去写诗。他认为这也是为现代白话诗奠基。他的这些关于白话诗的主张,也被朋友们视作向传统文化的挑战。
争论反而使胡适更深刻地认识到文言的特异性、守旧性和作为一般语言的缺陷。“他的反驳,我不能不细细想过我自己的立场。他越驳越守旧,我倒渐渐变得更激烈了。”这表明了他被“逼上梁山”的心境。
五、文学革命和“八事”
绮色佳争论之后,同年9月17日,胡适送给自己的反对派急先锋梅觐庄一首诗: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
百年未有健起者。新潮之来未可止;
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
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
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
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戡天差可疑。
梅生梅生毋自鄙!
这虽是朋友间“舌战”的打油诗,属“私人”文字,却是最早的有关“文学革命”的文字记载。其后,朋友间的争论暂告一段落。翌年2月,胡适给陈独秀写了最初的一封信;8月21日,又写了第二封信。第二封信中有如下内容:
年来思虑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语,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以上为形式上的革命。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语,八须言之有物。以上为精神上的革命。
以上仅录“八事”要点,笔墨所限,不拟赘陈。信中出现了“文学革命”字样,我们不难想象,它给陈独秀带来的冲击会有多大。陈独秀立即在《新青年》第2卷2期通信栏里,刊出了胡适来函和自己的复函。其中有如下赞成及恳请之词:
承示文学革命八事,除五八二项,其余六事,仆无不合十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倘能详其理由,指陈得失,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其业尤盛。
应约作复,便是那《文学改良刍议》。
六、“文学革命”之删除
《文学改良刍议》中之“八事”,依序为: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以上诸项均附有大量引证和详细说明。这里不但排列顺序和字句有所变化,而值得注意的是,“文学革命”一词在这里消失了。胡适在《逼上梁山》中是这样解释的:
可是我受了在美国朋友的反对,胆子变小了,态度变谦虚了,所以此文标题但称《文学改良刍议》,而全篇不敢提起“文学革命”的旗帜。
留学生朋友们的反对,比预料的要强烈得多,且竟持续一年多不曾中断。为了避开他们的反对与责难,他暂放下了“文学革命”的旗子。但更进一步讲,他还有另外的思索。
如前所述,胡适本来就不是激进的文言废止论者。他主张应在搞清文言和白话各自特征的基础上,进行同步教学,在现阶段至少应允许用白话写诗。他的这种想法是很稳健的,并不性急,但却被朋友们扣上了“文化破坏者”的帽子。他的苦恼,与其说是受到了朋友的反对,莫如说是自己的本意得不到理解和推行。
连受过美式合理主义洗礼的留学生们都不能理解,在国内就更不用说了,他由此而产生的畏惧念头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时时受到陈独秀的赞扬,但招致大多数人的反对也是显见的。我们还应看到,“文学革命”一词,是他在朋友们的“乱矢”下脱口而出的。所以,只要了解了他的本意,我们就可以认为放弃“文学革命”的旗子,对他说来还算不上什么大的牺牲。
七、“刍议”的用意
胡适以“刍议”为题是有其用意的。他在《文学改良刍议》篇末写道:
上述八事,乃我年来研思此一大问题之结果。……谓之“刍议”,犹云未定草也。伏惟国人同志有以纠科是正之。
他把“刍议”释作未定稿之意,然他选用这之于当时文人尚属陌生的新词,还另有用心。
“刍”即“刍荛”,即所谓樵夫,泛指匹夫野人之意。《诗经》大雅篇有“先民有言,询于刍荛”一语,意为古之贤人只要对治世有益,凡夫俗子之言也会采纳。《汉书·艺文志》中,也有“小道之一言亦须采纳,此亦刍尧狂夫之议也。”意为如同匹夫野人一样,小说家们的蠢言中也会有治世警言。也就是说,胡适是把自己比作匹夫野人,把读者尊为贤人,以示谦恭。但很显然,这既为躲避非难的韬晦之策,亦含有“不倾听匹夫野人之善言者非贤人也”的自负心理。谦卑背后藏暗矢,是中国古代文人之一大嗜好,可以说这也是在美国历经苦难的胡适的一个苦肉计。
八、关于文体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即与胡适的主张恰好相反,《文学改良刍议》竟然是文言体,是他所特有的不加修饰的简明文体,是毫无戏文因素的规范的文言文。文中所用大量引文也尽是文言,范围从《诗经》直到民国初年。
是时他已采用打油诗形式向友人述志,日记中也写下了后来收录于《尝试集》中的白话诗,足见其白话功力之雄厚。那么,为什么他此时不以白话写作呢?
胡适在给陈独秀写头一封有关“八事”建议书的同时,也给朱经农写了内容几乎完全相同的信。不同只有一点,在致朱的信中没提“文学革命”。朱是刚到美国不久的旧友。那时胡适非常冷静,在使用“革命”一词上非常谨慎,他打算在准确判断对方思想状况之后,再定夺是否该用此类字样。
信中在“八事”之后,他写道:“白话乃我一人所要办的实地试验。倘有愿从我的,无不欢迎,却不必强拉人到我的实验室中来,他人也不必定要捣毁我的实验室。”
此处已不见昔日用打油诗向朋友挑衅的天真和稚气,看到的却是戒备与自负的心理。他是执意在未被世人承认之前,决不把自己的白话文拿出来曝光的。
我们不难看出,《文学改良刍议》是经深思熟虑写就的。从遣词、结构,到文体,胡适都下了苦功夫。他如此周密的用心,陈独秀也未必是察觉得到的。
九国内反响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的附言中,写下了这样的评语:
余恒谓中国文学史,施曹价值,远在归姚之上。闻者咸大惊疑。今得胡君之论,窃喜所见不孤。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亲见其成,则大幸也。
这是针对第八点“不避俗字俗语”所作的议论。胡适在第八点中指出,曾被认为是通俗读物而遭轻视的《红楼梦》、《水浒传》,甚至元曲之类的白话文学,应该能够取代从前的文言诗文,成为文学的主流。在最初写给陈独秀的信中,这一项曾列在第四的位置上,后面附有“不嫌以白话作诗”的说明。而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上述附加文字被删除,取代它的是颠倒文学史中主流与支流的主张。就是说,胡适此时之见解,已从原来的作白话诗的实际问题,上升到了文学史的价值认识问题。他以欧洲诸国文艺复兴时期俚语文学的勃兴为据,断言白话文学将成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并将元明以后的白话文学置于文学史顶峰的位置。对此,胡适在《逼上梁山》中有如下自白:
这个新次第是有意改动的。我把“不避俗字俗语”一件放在最后,标题只是很委婉的说“不避俗字俗语”,其实是很郑重的提出我的白话文学的主张。
对于通俗小说的再评价,只得到了少数留学生朋友的支持,然而革命家陈独秀却为之大为动容。他立即举起了胡适掩下的“文学革命”的旗帜,在下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文学革命论》,提出了三大主义: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推倒迁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胡适读过《文学革命论》,致书陈独秀云: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日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吾辈已张革命之旗,虽不容退缩,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针对此信,陈独秀作复如下:
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其故何哉?盖以吾国文化,倘已至文言一致地步,则以国语为文,达意状物,岂非天经地义,尚有何种疑义必待讨论乎?
斯时莫说排除反对者,甚至连改革趋势表面化都未形成。正如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云,青年们仍苦恼于寂寞之中。而陈独秀对此却无所顾及,大胆刊出如此激进文字,其革命家编辑形象跃然而立。胡适在《逼上梁山》中引完陈的这段话写道:
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们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到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
陈独秀的武断态度,是胡适所不能赞同的,但他又不得不承认,若不借助这种武断的力量,他的文学改良的主张,是没有机会得到市民权的。
十、结束语
如上所述,“文学革命”在倡导者们微妙的分歧中,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即钱玄同。他对陈、胡文学革命的主张非常支持,他在《新青年》第3卷6期通信栏发表了一篇白话文,成为该刊所发表的第一篇白话议论文。这一期还刊载了胡适的《归国杂感》,这是他继在该刊第2卷6期(1917年2月)发表八首白话诗之后,又一篇白话文。作为白话散文,是他的首次尝试。除胡适、钱玄同外,投寄白话文稿的还有刘半农、周作人等。在第4卷4期上刊载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可视作《文学改良刍议》的白话文翻版。这时,胡适也名副其实地举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同年5月底,在钱玄同的劝说下,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山作。
中国现代文学就是这样在多个偶然相叠、相关联中诞生的。但与胡适慎重讨论的期待相反,中国文学界很快就卷入了“革命文学”论争的漩涡,而拘泥于传统文学的守旧派也大有人在。但在后来,在社会变革的激浪中,白话虽历尽坎坷,还是在文学语言领域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不过,这已是30年代的事了。
[收稿日期]2000-06-18
标签:文学改良刍议论文; 胡适论文; 陈独秀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逼上梁山论文; 狂人日记论文; 赵元任论文; 白话文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