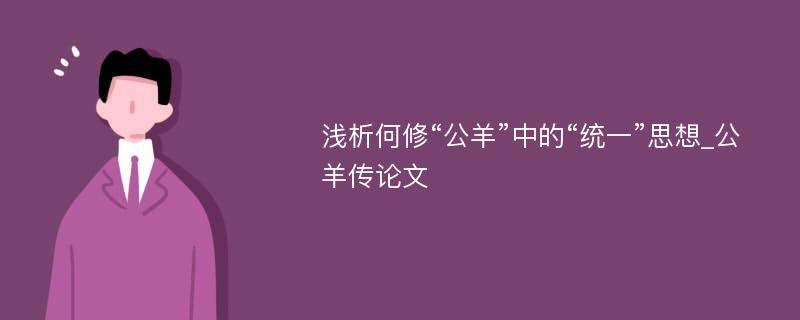
何休《公羊》“大一统”思想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羊论文,思想论文,大一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中国历经五千年沧桑,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始终如一,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越能增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感。(注:参见李际均:《中国军事史概论》,《中国军事科学》1998年第1期。)
造就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人们联系、团结在一起。而何休对“大一统”思想的阐发和弘扬,则在其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大一统思想的渊源与《公羊》学的一统观
“大一统”的本义是以“一统”为“大”。“大”在这里是推崇、尊尚的意思;“一统”,即以“一”“统”之,所谓“总持其本,以统万物”(《管子·五行》尹知章注)。“大一统”就是高度推崇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也即对“一统”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后来也有人将“大一统”的“大”理解为形容词,认为“大一统”就是“大的统一”,“高度的统一”,即描绘、形容统一的程度。何休《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解诂》在解释《传》“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时说:“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由此可见,何休所说的“大一统”,是指统一的程度与规模,是上述“大一统”的第二层含义。
“大一统”的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其中春秋战国是这一思想的基本定型阶段。当时西周礼乐文明遭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大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称雄,混战绵延。人们饱受这一政治无序所造成的苦难,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法合理的政治秩序。先秦大多数思想家都在其学说中反映了这个社会基本要求。虽然诸子各家在统一的方式和内容上存在着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乎一”则是他们的共识。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才有后来的秦统一与汉统一,才有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之举,才有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一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志第七《祭祀志上》李贤注引应劭《风俗通》)
当然真正在“大一统”理论构建中作出特殊贡献的,应首推儒家。按他们的理解,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不能像法家所鼓吹的那样统于暴力,也不能像墨家所提倡的那样统于人格化的天,而必须一统于“仁义礼乐”、“王道教化”,即孟子所说的“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孔子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奠基者。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局面,他一再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他褒扬管仲,着眼点也落在管仲能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维护华夏名义上的统一这一点上:“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为此,他提倡“克己复礼”,主张重建一统的社会政治秩序,并将这一“大一统”理念作为微言大义隐寓于自己所整理修订的《春秋》一书之中,遂成为儒家大一统思想的不祧之祖。
孔子身后,儒分为八。他们在某些问题上存有歧见,但对于“大一统”的理念,却是一致认同的。如孟子和荀子,一个大声疾呼“(天下)定乎一”(《孟子·梁惠王上》);另一个也明确指出“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在他们和其他儒家人物的努力倡导下,“大一统”的思想观念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
在“大一统”思想形成过程中,《公羊春秋》曾起过重大的作用。一般的看法是:《公羊》学产生于战国时代,当时中国历史正处于由诸侯割据称雄走向全国统一的前夜。《公羊》学作为儒家中接近法家的一派,在思想体系上与荀子相一致,也要突出地反映社会发展的这一趋势。《公羊传》隐公元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就是这种思想的集中反映。然而由于公羊属于儒家系统,因此它不能不带有一定的守旧性与复古性,即在其心目中,并不要求这新的一统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而是主张在旧基础上建立新的一统。于是公羊的“大一统”实质上便成了天下统一于周的“大一统”。《公羊传》文公十三年云:“然则周公之鲁乎?曰:不之鲁也。封鲁公以为周公主。然则周公曷不之鲁?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尽管公羊的“大一统”思想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然而它的本质属性是进步的,是属于为中国统一事业的发展而呐喊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它所主张的“王者无外”的“大一统”理想境界,为儒家的“一统”观增添了新的内涵,使之发展到新的水平。
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使“大一统”的理念转化成了客观的政治实际。尤其当汉王朝作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之后,更使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在政治操作的层面上获得了切实推行的基础。现实的需要,促进了“大一统”思想的丰富和深化,这就是《公羊传》作为儒家思想的主流占据了汉代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在当时,公羊学是儒家“大一统”理论的主要载体,它使这一理论更加系统化、精致化,成为适合当时封建统治需要的最高政治思想纲领。
汉代儒者继承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重视揭橥《春秋》中有关“大一统”的微言大义,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董仲舒在其“天人三策”中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也。”所反映的都是这一现象。然而汉代《公羊》学对“大一统”思想的贡献,主要不在于对它作形式上的肯定推崇,而是对其内涵作了实质性的丰富,从哲理的层次上对其进行了抽象和升华。董仲舒就在其著名的“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中集中阐述和发挥了“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以及“尊王大义”:
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而人之元在焉。安在乎?乃乎天地之前。(《春秋繁露·重政》)
《春秋》何贵乎元而言之?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
这样,就从哲学的高度,也即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这一点对何休的“大一统”理念的形成是有深刻的影响的。他在《解诂》中同样把“以元统天”、“立元正始”作为自己宣传、弘扬“大一统”主张的逻辑起点和根本宗旨:“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到了东汉后期,儒家的“大一统”理想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当时,政治上大一统的局面正处于瓦解之中,天子不尊,法令不一,豪强崛起,诸侯割据的形势正在形成。造成这种局面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从远因来说,它与东汉政权的性质有关。东汉王朝是建立在豪强地主共同体基础之上的,刘秀的功臣大多是一些有实力有影响的豪强,他们在东汉政权占有重要的地位。东汉的皇后一般都出于邓、窦诸大族,而朝廷的许多措施,如果得不到诸豪强大族的赞同,也往往不能顺利地贯彻下去。“度田”的不了了之,就证明了这一点。东汉豪族的嚣张跋扈,甚至连马援这样的名将也深为畏惧。在这样的情况下,专制君权无形之中便遭到了一定的削弱。就近因而言,豪族通过兼并土地,经济、政治实力不断提升,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遂随之出现,而朝廷政治腐败、吏治黑暗的现实更加剧了这种离心倾向。
在东汉的思想领域,势必会留下这种现实政治格局的痕迹,其统治思想《公羊》学的不少义法要有所变化,也就势所必然了。
反映这种变化的,始于《白虎通义》。它开宗明义便讲“天子者,爵称也”(《白虎通义·爵》),明确地将天子说成是爵位的一等,这或许是豪族们企图削弱或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王者太子亦称士何?举从下升,以为人无生得贵者”(同上)。“士”仅仅是“尊之渐”。现在王者之太子也只有从头做起,这实际是有意降低帝王的起点。天子不尊,于是《白虎通义·王者不臣》进而提倡“王者不纯臣诸侯”之义:“王者不纯臣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传子孙,世世称君,南面而治……异于是臣也。”它并且规定了王者不臣者三:“三王之后,妻之父母,夷狄。”这里,不臣三王之后,是旧义;不臣夷狄,是其狭隘的民族观;而不臣妻之父母,实际上曲折透露出东汉时期后戚势力的日渐强大。至于《文质》篇云“王者缘臣子心以为之制”,就更为明确地对君主们提出了扩大豪族权力,满足豪族利益的要求。
以上这一切,在《白虎通义》中婉转地表示了一点,即“明天下非一家之有”(《白虎通义·三正》)。这原本是一句充满民本色彩的言辞,《孟子》、《吕氏春秋》、《六韬》等先秦典籍中多言之。可是到了豪强离心势力那里,却变成了他们用来抗衡皇权的一面盾牌。
“尊王”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政治灵魂,现在《白虎通义》迁就豪门而贬低天子,这实际上是否定“大一统”,也是对《公羊》学基本精神的一种背叛。这当然是当时社会政治演变大势在学术思想领域中的客观反映,预示着世族强大、豪门拥兵、少数民族崛起、分裂割据重现的局面呼之欲出。
结合这种时代背景来考察何休为弘扬儒家“大一统”思想而作出的努力,对其所包含的进步意义不能不予以很高的评价。尽管“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弊端,如极权专制、禁锢思想、扼杀创造的生机等等;但是,与分裂割据、社会动乱的局面相比,它更符合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在社会一统格局行将瓦解的历史条件下,何休强调“一法度,尊天子”,意味着他恪守《公羊》学的立场,坚持“大一统”的原则,具有挽狂澜于既倒的意义。其维系中华文明之传统,表达人们追求统一、反对分裂之意愿,功在千秋,义昭日月,堪称是何休政治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
二、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内涵及其特色
何休的“大一统”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层次和显著特色:
第一,构筑“宇宙图式”理论,论证“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与哲学神圣性。从抽象思辨的高度,致力于解决大一统权力从何而来、天子大一统权力何以体现两个命题。
《公羊传》有关“大一统”的义理,集中体现在隐公元年的《传》文之中,但它比较隐晦,有些辞不达意:“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据此系统地构筑了近似于“宇宙图式”的理论,对“大一统”的实质含义与根本特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深刻的发挥:
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故上无所系,而使春系之也。不言公,言君之始年者,王者、诸侯皆称君。所以通其义于王者,惟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托新王受命于鲁,故因以录即位,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
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系天端。方陈受命制正月,故假以为王法。不言谥者,法其生不法其死,与后王共之,人道之始也。
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
这些言辞都围绕“大一统”这个命题而逐次展开,突出反映了何休本人对“大一统”内涵和特征的基本认识。它包含着这么几层意思:
首先,它是用汉儒常见的君权神授、“天人合一”形式来表述“大一统”的基本原理的。在何休看来,“大一统”是上天意志的集中体现,是“天人合一”宇宙图式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客观反映,即所谓“上系天端”,“故假以为王法”。
其次,“大一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结果。所谓的“天”,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客观意志的体现,是由“元”所统辖的。至于“元”,乃是“气”,作为世界物质性的基础,它“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由此构成天地万物,“造起天地,天地之始”。而在天地万物之中,王是“大一统”的直接负荷者,他作为最高权力的代表,赋有“继天奉元,养成万物”,总理一切的崇高职责。无论是阶级秩序“自公侯至于庶人”,还是自然秩序“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在由王所“养”这一点上,概莫能外。这样,何休就从事物演变发展的运动规律角度,深刻地阐述了“大一统”的逻辑合理性。
其三,从“王者当继天奉元,养成万物”的基本前提出发,何休进而系统说明“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与哲学神圣性。认为这种合理性与神圣性主要体现为天子(王)拥有至高无上的一统权力,所谓“大一统”实际上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而社会政治生活的“大一统”,又是以天子为中心的政治上的大一统:“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一国之政,莫大于正始”。为此,何休指出:“由‘元’、‘天’、‘王’、‘天子政事’、‘诸侯治国’构成五位一体的世界图式中,‘王’处于中心位置。由‘元’这一生成宇宙万物的来源决定天的意志,由天的意志决定王的政教设施,由王的政教设施决定诸侯的即位,由诸侯的即位决定境内的治理。”(注:陈其泰:《何休公羊学说的体系及其学术特色》,(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第196期。 )“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这五者以“王”为中心,相互联系,浑然一体,“五者同日并见,相须成体”,构成“大一统”的宇宙模式。何休强调,这乃是宇宙的法则,万物的根本,“乃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不可不察也”。
其四,何休的“大一统”理论,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人际之学,是着眼于社会政治大一统的现实政治哲学。何休不像其他《公羊》学家,注重于《易》与《春秋》的结合,而是将重点放在论述《春秋》与《孝经》之上,这是人际关系,以人际关系代替天人之际,是后汉学者的一种转变。(注:杨向奎师:《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6月版,第97页。)所以, 以往《公羊》学者之论大一统是“天人之学”,一统于天人,要改正朔、易服色以应天。而何休阐述发挥大一统,在肯定天人关系的同时,更把目光投放在“政教”问题方面,是“奉王之政”、“为政”、“以制号令”云云,而及于山川、草木昆虫。这一点突出体现了其现实主义特色,值得引起注意。
其五,何休认为“大一统”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表现是:“系于王,知王者受命布政教所制月也。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显然,和公羊学先师一样,并没有多少个人的独立见解和发挥。但有关公羊旧义的陈述,对于他大一统理论体系构建来说,仍是十分必要的步骤。因为它使得所谓的“政教”,有了具体实在的内容,便于“大一统”的理念进入现实操作的层次。由此可见,何休的“大一统”思想体大思精,既立足天人关系,又超越天人关系,不愧为公羊学“大一统”义理的杰出总结者。
第二,强调“尊王”大义,把维护中央权威,摆正和处理君臣关系,稳定封建等级秩序与纲常名理,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大一统”的中心内容。从社会政治运作的角度,致力于探索维持和巩固“大一统”政治格局的根本途径与具体方法。
何休认为,“大一统”虽然从抽象的义理来讲,是“天人之大本,万物之所系”,但是它还是要落实到社会政治领域,成为衡量中央集权程度的标志。其关键就是如何摆正和处理君臣关系,巩固尊卑有序的封建等级秩序,用何休自己的话说,即“重本尊统之义”。
何休认为,“重本尊统”的核心,就是要明确树立君主本位的原则,做到“一法度,尊天子”。天子是圣人受命于天者,“圣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谓之天子”(《春秋公羊传解诂》成公八年),他是大一统的体现者,“尊天子”实际上就是尊“一统”。因此他在《解诂》一书中利用各种机会强调“一法度,尊天子”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不言诸侯之大夫者,明所刺者非但会上大夫,并遍刺天下之大夫。不殊内大夫者,欲一其文见恶同也。至此所以遍刺之者,萧鱼之会,服郑最难,诸侯劳倦,莫肯复出,而大夫常行,政委于臣,而君遂失权,大夫故得信任。故孔子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十六年)
古者,诸侯将朝天子,必先会闲隙之地,考德行,一刑法,讲礼义,正文章,习事天子之仪,尊京师,重法度。(《春秋公羊传解诂》定公十四年)
然而,春秋时期的实际情况却是王权衰落,天子不尊,整个社会处于“礼崩乐坏”的大动荡、大混乱状态之中。何休回顾历史,联系东汉社会的现实,不免深受刺激,于是在《解诂》中对历史上的王权衰落导致“大一统”局面瓦解的事例一再抨击,借此向东汉统治者敲响警钟:
此象桓公德衰,强楚以邪胜正。僖公蔽于季氏,季氏蔽于陪臣。陪臣见信得权,僭立大夫庙。天意若曰:蔽公室者,是人也,当去之。(《春秋公羊传解诂》僖公十一年)
月者,危。刺诸侯委任大夫,交会强夷,臣日以强。三年之后,君若赘旒然。(《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十四年)
为了突出王权衰微、天子不尊对于“大一统”局面的危害性,何休还企图通过“天人感应”的道理来加深人们这方面的认识,指出王纲陵替、尊卑失序是导致天降灾异的主要原因,也即上天针对“大一统”局面遭到破坏而宣示的警告和惩罚。如《解诂》成公十六年解释《经》文“甲午,晦”言:“此王公失道,臣代其治,故阴代阳。”又如,《解诂》襄公十三年解释《经》文“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东方”言:“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居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于此旦见与日争明者,诸侯代王治,典法灭绝之象。是后周室遂微,诸侯相兼,为秦所灭,燔书道绝。”凡此种种,都是王纲衰微,“大一统”崩溃所带来的后果。何休一再强调,意在震撼统治者的心灵,使之警觉,采取措施,以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何休认为要确保“一法度,尊天子”的政治原则得以实现,维护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大一统”格局,必须落实一些相关的措施。
首先是天子(王)自身修道保法,改良政治,树立良好的形象,使分裂割据势力无隙可乘,从根本上奠定“大一统”政治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审法度”、“修法守正”:“书者起时,善其修废职,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春秋公羊传解诂》昭公三十二年)“明修法守正,最计之要者。”(《春秋公羊传解诂》隐公三年)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则中央集权就有了有力的保障,离心倾向就可以得到有效的扼制。
其次,要坚定不移、旗帜鲜明地反对大臣擅权、贵戚秉政。何休从大量而具体的历史事实中意识到,强藩、权臣、贵戚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离心力量,是天子“大一统”的对立面。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总是要有意无意地分割天子的权力,争夺天子的利益。而这种行为势必要给天子“大一统”政治格局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导致“大一统”局面的瓦解。春秋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东汉的现实又将这种危机再次置放在最高统治者的面前。于是,何休不能保持沉默了,抨击的锋芒直指大臣擅权与贵戚秉政:
时庶孽并篡,天王失位徙居,微弱甚,故急著正其号,明天下当救其难而事之……贬言尹氏者,著世卿之权,尹氏贬,王子朝不贬者,年未满十岁,未知欲富贵,不当坐。明罪在尹氏。(《春秋公羊传解诂》昭公二十三年)
宋以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政分三门,卒生篡弑,亲亲出奔。疾其末,故正其本。(《春秋公羊传解诂》僖公二十五年)
何休所议论的是历史,但是,他所针对的实为东汉的现实。当时世族豪强的势力已高度膨胀,外戚专权蔚然成风,分裂割据形势十分明显,“大一统”的局面受到威胁。何休无法容忍这一切,可又不能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批评,于是只好通过总结历史的教训,明确自己反对豪门擅权、贵戚秉政的立场和态度,希望维系政治上的“大一统”。从这个意义上说,何休的“大一统”理论,不是对《公羊》学“大一统”观的简单复述,而是富有鲜明的现实意义的。
何休不仅从史实叙述诠释角度表述“尊天子”“大一统”的观点,而且还从理论阐发的层面表白自己拥护和弘扬“大一统”的立场。这就是他全面系统地肯定和发挥《公羊传》“讥世卿”的重要原则。《解诂》隐公三年云:“礼,公卿大夫士皆选贤而用之。卿大夫任重职大,不当世为。其秉政久,恩德广大,小人居之,必夺君之威权。故尹氏世立王子朝,齐崔氏世弑其君光。君子疾其末则正其本。”
可见,何休对于世卿豪强掌握重大权力,因世袭而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以至威胁君权破坏“大一统”的危害性,是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的。这是一种值得肯定和赞赏的见解。已知问题的症结所在,如何解决,便成为维护“大一统”的不可回避的课题了。
何休对这一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简单而又明确的,就是所谓“弱臣势”,即想方设法限制豪门贵戚的威权,削弱和打击他们的势力,使之不再构成对君权和“大一统”的威胁,从而真正达到“一法度,尊天子”的目的:
时虽名诸侯使之恩,实从卿发,故贬。起其事,明大夫之义得忧内,不得忧外,所以抑臣道也。(《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三十年)
书者,善诸侯为宋诛。虽不能诛,犹有屈强臣之功。(《春秋公羊传解诂》襄公元年)
正是基于“尊天子”“弱臣势”的立场,何休充分肯定“堕三都”这一历史事件:
郈,叔孙氏所食邑,费,季氏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数叛,患之,以问孔子。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悦其言而堕之……善定公任大圣,复古制,弱臣势也。(《春秋公羊传解诂》定公十二年)。
也同样是基于“尊天子”“弱臣势”的原则立场,何休高度评价周公留守镐京,不赴鲁就国的举动,认为这正是周公高瞻远瞩,“一天下之心于周室”,维护“大一统”的英明之处:
周公,圣人。德至重,功至大。东征则西国怨,西征则东国怨。嫌之鲁恐天下回心趣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遥供养,死则奔丧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春秋公羊传解诂》文公十三年)
总之,在何休的观念里,凡是“一法度,尊天子”“弱臣势”等有利于维系和巩固“大一统”做法都应该肯定、赞扬;反之,就要受到谴责和贬斥。其积极宣扬“大一统”主张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三、余论
当然,何休的“大一统”思想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这一方面表现为他站在极端专制的立场,将君臣关系完全绝对化,排斥了早期儒家在这一问题上的合理因素。早期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等人,虽然肯定“君君、臣臣”的尊卑从属原则,但仍认为君臣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孔子尝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则明确宣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可是,何休为了一味强调“尊天子”“大一统”,遂背弃了早期儒家的君臣观,而把臣子对君主的驯服突出到不适当的地步,宣称道:“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春秋公羊传解诂》宣公六年)。在这一点上,他和董仲舒倒是很接近的。董仲舒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者,视地之事天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由此可见,高度专制集权体制下的儒者人物,已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而成为统治者的绝对顺从者,这乃是儒学发展的自身悲哀。
何休“大一统”理论的另一个局限,是他的思想也羼杂了一些背离“大一统”原则的内容,即其“大一统”观并不十分纯粹。这或许是其摭拾《传》文不加严格辨析之故,也不能否定他多少受过《白虎通义》的影响,以致使不少说法自相矛盾。如《解诂》隐公元年阐述“王者有不纯臣之义”时所谓“称使者,王尊敬诸侯之意也。王者据土与诸侯分职,俱南面而治,有不纯臣之义……天地所生,非一家之有”云云,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对于一位致力于提倡天子“大一统”的思想家来说,理论体系中保留着这种非“大一统”的因素,自陷于矛盾的窘境,这不能不是莫大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