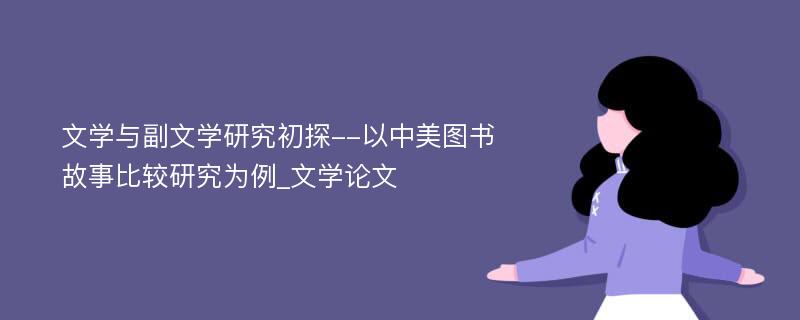
文学与副文学研究探——以中美“说书”的比较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文学论文,为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375(2004)03-0029-07
长久以来,文学研究、学校教学和教育机关都把公认的大作家和典范作品视作文学的“经典”;而“经典”的文学也就是学校教育、学者研究和有关机构都认定的大作家和典范作品。因而,“经典”文学也就是文学“经典”,这成了一个由上述部门作彼此往返的“公认”和“认定”的循环—“经典”标准。然而,这类“公认”和“认定”的“经典”常常会因时因事而异,而“经典”的文学也就随之因时因事而变,这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五四”前后,国人对中国文学及其经典的迥然认定,以及改革开放前后、对外国文学一些经典的不同定性,都足以证明这一情况。有趣的是,与此同时存在的另一种情况则更为普遍且持久。即上述研究机构和教育部门,既不“公认”,也不“认定”的文本一非“经典”的文学,却经过“大众路线”在大量生产并广为流传。像口述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等就是如此。当代法国比较文学家谢菲雷教授将之通称为“副文学”(paraliterature):“这个术语涵盖所有不被各类机构承认或接受的文本。”[1](P47)
由于对文学与副文学的研究,不仅涉及到文学学科的文学定性、作品价值、评判标准等重大问题,而且还关联到读者接受、发行路线等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因此自1970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6次大会起(大会主要议题是“文学与社会”,其中以“副文学”为题的就有好几个),对副文学的研究也就成为国际学界十分活跃的新领域,出版了《谈副文学》、《平庸文学?大众消费文学》等论著。到80年代,对口述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大部分不为人知的副文学作者及其“兰色图书”(在法国,这类无名氏图书因其封面为蓝色而得名)等的研究,不仅全面活跃并且还格外关注口头文学的调查和研究,出版了《口述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库》、《民间故事百科全书—叙述史与比较研究手册》、《从比较文学视野看兰色图书》等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著作。[1](P47)90年代,美国的学者白素贞、本德尔等博士,又进一步热衷于中国口述表演文学(我们传统称为曲艺)“一支花”—苏州评弹的比较研究,并成为近年来令人注目的中西副文学比较研究“新星”。可见,对副文学的研究,包括对中美说书的比较研究,既是同国际学界接轨的新研究方向,又是对振兴发展我国优秀口述表演文学有现实指导意义的比较文学研究新领域。
不仅如此,对口述表演文学的研究,还有更为重要的认知文化传统的深远意义。通常人们总认为文字文本记载的东西最为可靠,从中探求与认识社会文化及其传统也最为过硬和可信。但事实上,书面文本的撰写是作者的个人行为,有无接受者直接在场或参与,并不决定该文本的产生与完成。因此,就其创作过程与实现而言,并不直接与读者、与社会背景的方方面面文化发生关系,也不直接受其传统对制约与限定。然而口述表演文学的创作与完成,则并非只是演员的个人行为。如苏州评弹的表演,就必须有听众、有书场、有书场工作人员等文化背景的方方面面共同参与方能实现,否则光有演员的表演充其量只能说是排练。正因为说书表演活动的实现与完成,必须要有上述文化背景的方方面面共同参与,这就历史地要求参与各方,都必须遵守共同熟悉并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规则,方能顺利进行和有效实现。因此,这活生生的文化传统,也就在这活生生的口述文学表演活动中,由参与各方共同遵守和运用而得以传承保留和运用发展。这就使之成为了解与掌握自身文化传统的有效途径与生动课题。而进一步作中外口述表演文学的比较研究,也就成为认知自我与他者文化传统的重要研究领域。
一、中美“说书”概述
与我们“评弹”相仿的口述文学表演活动,在美国叫Story-telling,直译为“说故事”。英语中的Story,指实有的故事、历史、记实的事;它也指虚构或编造的故事、小说、传奇和传说等。而美国说故事人所说的内容,有普通的小说、浪漫传奇、虚构的科幻故事、童话传说和地理历史读物等;也还包括美国说书人协会和出版商,专门编辑出版的书刊故事。不管其说的是古代的历史、神话传说和童话,还是现代的生活小说、趣闻轶事和科幻故事;或者是重在娱乐的家庭琐事、滑稽故事,或者是重在教育或传授知识的异国风情和劝人为善的创作小品等。其说的内容大多取自书刊,因此也可叫“说书”。这不仅同评弹的又一名称“说书”一样,而且这一个“说”字,道出了口述表演文学的艺术本质:它们都是用我们的口头语言,通过主要塑造一个口语声音的艺术世界,来形象的、情感的并具美的魅力的再现或表现现实世界和人的意识情感。
同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苏州评弹相比,美国说书活动的历史并不悠久,最多不过百来年时间。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靠了电台的广播曾流行过一段时间。但后来有了电视,说书就消沉下去。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它又重新活跃起来,不仅成立了美国说书人协会,而且还定期出版会刊、通讯,说书人频繁演出,以及电视台现场转播等,如今已不仅拥有广大受众,而且还可同歌星、影星一争高低。
与苏州评弹的演出有固定书场不同,美国说书的表演场合,多样而又方便,十分适应其时代生活和本身规律。在少到只有十来人的寻常百姓的家庭“派对”(Party),多到成百上千人的电视现场直播,以及州议员们的轻松聚会、学校的教室、学生们的野营空地、乡村博物馆或观光点的院子、汽车加油站的休闲处等,凡有人集会的地方,都是他们一展身手的演出之地。他们没有固定的演出书场,对他们的事业和各自追求目标,毫无妨碍。倘若给他们一个固定的演出书场,他们反倒要问:“为什么?”因为按照他们的理论和经验,他们认为,没有固定的表演场所,只要有人的任何空间,他们都能随遇而安,这正是口述文学表演艺术得天独厚的优势:口语是人类社会交际中最主要、最方便、最自然也最本能的工具,基于口语并运用口语说书的表演艺术,就应当是“随遇而安”,就应当是随时随地能同听众真实而又自然的当面交流,这既是符合它的自身规律,又是显示说书人真实本领的机会,让听众在艺术接受上也返朴归真并满足其天然要求欣赏真实表演的心理。这使它既有别于当代靠“包装”推销的歌星、影星的表演,也使它能抗衡并优于影视娱乐的原因之一。
同我们评弹表演相比,他们说的故事短小,不像评弹多是长篇;他们的说书技巧和表演手段,用美国专搞苏州评弹研究的俄州大学马克·本德尔博士的话来说,美国说故事的表演技巧只能算是小学生。这话说得并不过分。苏州评弹的说、噱、弹、唱、表和演,其一言一行、一招一式、一曲一调等等,都是历经多少代演员、多少次锤炼才积淀成今天炉火纯青、光彩耀目的“一枝花”。弹词名家说《三笑》,讲到唐伯虎点秋香、秋香被召下楼时,噱头连连妙趣横生,可以细腻铺陈、添油加醋到每走下一级楼梯,就须说上一个晚上。听众不仅不厌,并还着迷的次次接着听下去。评弹艺术表演家蒋月泉说的《玉蜻蜓》,更是倾倒听众。他说的“庵堂认母”和“厅堂夺子”,都是脍炙人口的著名折子。前者说被迫出家的尼姑智贞,多年后与其无奈送人的私生子、新科解元元宰相会的一段,母子在庵堂菩萨像前,智贞面对日思梦想的亲子,又耳听元宰想娘盼娘要认娘的哀诉,她欲认又不敢认的悲喜交集和揪心苦楚,一层层一丝丝地细腻表说,说得催人泪下。后者说到元宰改姓归宗时,从小领养他又对他恩重如山的养父养母,此时已沦为无依无靠又年迈贫困的境地,却还要面对顿时失去养子的突然打击,气愤的养父不禁举起拐杖要打元宰三下。可慈爱的养母心疼养子而恳求老伴少打两下,并还对这最后一下也求情道:“你高高举起,却要轻轻放下……”说得回肠荡气令人心酸泪下。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就象评弹的书目,绝大部分都是过往的历史一样,其程式化的表演手段与技巧,也随之紧密服务于那些距今较为遥远而又生疏的过去。虽然历史题材完全可以并且应该赋予今天的时代精神,但也要求其表演艺术也应当随之具有今天的时代气息,符合今天的生活节奏。与之相比,美国的说书,不仅在内容上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而且其表演技巧和手段也随之吻合当今的时代节奏和审美时尚。这是当今美国说书比我们评弹活跃红火的重要原因。具体说,下面几点对我们探讨这个问题是颇有启发的。
一是美国十分讲究知识产权的国家,因此说故事人必须要自己加以改编再创造,绝对不能“剽窃”。如美国俄亥俄州一位演员说的一个故事,名叫《会讲故事的石头》。它取自八十年代出版的《创造性的说故事》一书,但说的人将它改编成了一个彰扬说故事艺术的故事。一个失去双亲的男孩,他为祖母在森林中打猎。是林中的石头突然开口给他讲了先于我们而最早住在天上的人们的故事。之后男孩每天都来听故事,每次都带礼物,而石头就像其父母一样,通过故事教会了他许多许多事情。多年之后,石头又对男孩说:“将来等你打不动猎的时候,我讲的这些故事可以帮助你生存,但在你把我说的故事讲给别人听时,一定要让听你讲故事的人给你一些东西作为回报。”说完石头就不出声了,任男孩怎么求、怎么哭,石头再也没有开口。等这位男孩后来年老不能打猎时,他果然因讲故事而获得了食物和爱戴。这就是“故事”形成以及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故事”的原因,因为我们无法停止讲那些由魔幻石头所说的、并先于我们而存在、但今天却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人们的事。[2]说书人赋予了它生动而又睿智的现实说故事意义,围绕这一主题,说故事人突出说故事不仅是谋生的技艺,而且是连接前人历史的桥梁,并再创造其动情又动人的故事情节,避开了“剽窃之嫌”。
二是这种“再创造”故事,必须适应当代生活的节拍,予以高度的场景化和情节化。他们的演出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小时,并且要说三到四个故事,开头和结尾的两个故事长些,中间的故事就短些,短些的故事都只有六、七分钟。这是因为美国的电视台,在播放故事片时,总是每隔六、七分钟就插播广告,使大家渐渐养成了这一时限的接受习惯。比如年近古稀的艾米尔先生,他说的是一个个子又矮、年龄又小的小人,被称作“小东西”,但他却在大家面临危难关头并束手无策时,献计出力解救了大家,因此艾米尔结束时说:“小东西并非意味着无用。”从头到尾只有5分钟。就是他们说的最长的故事之一《少女星》(THE STAR MAIDEN),也没超过18分钟。[3]这个故事是讲人和动物本是同源,理应和谐相处在这同一个地球上。整个故事情节就集中在天上、地上和猎人之家这三个场景,而且又同当前盛行的爱护动物、保护生态的思想与时尚合拍。
三是表演内容在表演时还要根据演出环境和听众需要,进行再次“再创造”,运用声音模拟、动作表演、现代舞蹈、吉他演奏、口技、绕口令等以获得最佳现场效果。唐娜·伍格福女士,是位文学博士,说书人协会会刊《说书人指南》中评介她道:“专讲传统的民间故事,并能根据听众的兴趣和表演场合的需要进行创造,以利于家庭生活的和谐与个人视野的开拓。”[4]她的表演深受当地中小学的欢迎,就因为她能结合学校的教学和野营等活动的特点,将地理、自然、民俗、传说和文学等知识,与说书的形象声音和笑话“噱头”等结合起来,说得妙趣横生,让学生在听得入神入迷之中,接受了教育。
这三条规则,使他们不仅是表演者,而且首先必须是位创作者、编导者,最后还得经他们自己的“再创造”,使所说的故事内容既不断翻新,又适应当代生活、契合现场气氛,从而能在最大的程度上,吸引听众并与之实现思想内容的交流和共鸣。因此,美国的说书人,起码都是大学毕业,有的还是硕士和博士,具有较高的文学、美学、理论和知识修养。平时都订阅有关的书刊和钻研有关的理论著作,参加专业学术会议。这使他们具备了编、导、评和说好故事的力量—知识。
可见,美国的说书人,是集编、导、演、说与评论于一身的表演者,其内容和形式技巧都是紧跟时代、博采当今各种艺术之长,并同听众接受欣赏的时代特点合拍的。这种强烈的创造性、时代性和通俗性,是同我们前辈评弹艺人的成功经验,也是不谋而合的。《南词必览》中记有:“昔人云,诗无新意休轻作,语不惊人莫浪传。余谓不独诗也,即书亦然。”这是讲的创造性要求。而该书中“姜万孚云,吾道中之闻名者,不外乎说书说势,说书说世而已。”这是讲的时代性要求。还有,“何云飞演讲《水浒》,现形说法改变京班派,登台动手开戏,听客说宛如看京戏。又说云飞手中一把扇子,表演象真刀真枪拿在手中。所以后辈都要学何公动手。还有一技之能,……可以拿听客三收三放之能,可称死后无人。”[5]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讲,何云飞博采当时京剧艺术之长,处处讲究同听众的时时沟通交流,使其演出具强烈的时代性和通俗性的特点。
二、针对口头表演文学特点的研究理论与方法
我们研究评弹所用的理论与方法,一般都是借用或套用文学的和戏剧影视的理论。前者是书面语言艺术的理论,不是口头语言表演艺术;后者有口语表演艺术,但主要是诉诸于视觉艺术而非听觉艺术。而美国的说书研究,则另辟蹊径,发展形成了针对口头表演文学特质的帕里—洛德的“口头诗学”等。而当代社会语言学家鲍曼教授的《作为表演的口语艺术》一书,(注:见:[美]欧贝特·B·路德:《咏唱故事的人》,纽约,1971年;[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语艺术》,伊利诺斯,1977年。本节引文均出自该两本书。)他“交叉综合了民俗学、社会学、语义学和文学批评”,系统地研究并阐释了口语文学表演活动的实质及其规律,对我们研究说书副文学是很有启发的。
首先,他揭示了口语艺术的表演实质,将其界定为“本质上,表演被看成和界定成一种交流的模式”,这种交流模式呈现为一种以基本言语为参照系的转换运作,并存在着一套有机系统的“阐释性套架”。
组成表演活动系统的“套架”,是一个源于格雷戈里·贝特生的文章《演戏与虚幻的理论》(1972)中的术语。贝特生首次提出并认为,“套架的意图是限定阐释语境以区分含义的顺序。”这种套架的意图或叫作用,是使描述、叙述如何组织起来,即表演是如何产生,如何转换,如何被“启动”运作的。它起了指导或协助接受者理解在这个套架之内的各种信息的作用。这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在其特定文化语境中约定俗成的一种双向话语交流的程式和套式。例如,日常生活中彼此交谈时所用的普通“套架”之一:“从前……”,这使说者和听者都进入了发生在过去的事情的具体语境中,使接下来的信息交流得以进行与实现。而在口语艺术表演中,其“套架”的种类很多。比较常用的有“暗示或含沙射影”将说的话语与被理解的话语的意思,成曲折或隐蔽的关系;“噱头”,不严肃的表达其话语本身的意思;“摹拟”,说的方式是模仿另一人或另一角色的言行方式;“转译”,将一种话语解释为另一种与之意思相同的话语;“引证”,是说书人说别人的话语等等。这些套架可以联合使用,也可以单独使用,从而使表演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表演组织,也使之成为同听众可以获得表演信息交流的关键。
“套架”的作用是“认同”。“认同”的本义为持证人与其所持证件相同。在文学批评中有时译作个性,但在此则指表演者、听众、表演场所和整个背景等,通过表演套架的实施,使表演者实现其为表演者、听众实现其为听众、场所实现其为场所、以及整个背景实现其为背景等的认同相符。由于对一个表演活动来说,表演者、听众、表演场所和背景是密切相连的,所以,每一部分的得以认同都必然要牵涉到其他部分的得以认同才行。这样,对每一部分,包括其要素的进程和认同的探讨,就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层面,多视角,多学科的运动性和综合性的研究了。
那么口语表演交流是怎样实现的呢?从本质上说,口语表演作为一种口头言语交流模式,是假设在说者向听众显示其交流才能这一职责上。这种才能依赖于知识,及其与社会性交流方式合拍的表述能力。就口语表演者的能力而言,又取决于他对内容、对交流方式的超越程度如何这一点上,如果其能力一般,则吸引不了听众;反之,若其能力卓越,则能抓住听众;而从接受者的听众这一面看,则是取决于表演者的表演方式、技巧与能力所呈现井施与听众的有效性评价。当然,另一因素就是现场欣赏中使听众会产生强烈的体验。归纳一下,表演的过程,实际上由双方的下列部分构成:表演者的知识、能力、对内容和交流方式的超越程度+听众对口语表演的方式方法、技巧、能力等的评价反应。由于表演活动的主宰者是口浯表演者,所以实现这一活动的要素可概括为三个:口语表演者的表述能力,表述技巧方法的能力以及刺激观众有效性反应与评价的能力。
正是这三个能力,在具体的口语表演活动中,对组成口语表演的套架起了关键的作用—“启动”(The Keying of Performance)。也就是说,“Key”,就是口语表演艺术的套架,是如何被产生与被转换的,即表演是怎样被启动运作的(how performance is keyed)。启动的是套架中所包括的一系列明晰的或隐含的信息(explicit or implicit messages),并靠它们又带动结构去说明别的被交流的信息,所以是靠启动是一种“有关交流的交流”(communication about communication),被称作“元交流”:“一个套架是具元交流性的。任何信息,不管是明晰的还是隐含地都规定进一个套架,事实上,如上面谈套架时所说,套架本身都给接受者以指示或帮助,以便他能力图去理解包含在套架之内的信息。”所以,这些组成了表演活动的套架,都是通过运用文化体系内的约定俗成之元交流来完成的。也就是说,是用文化中的约定俗成和特有的文化方式去“启动”这些套架的,这就使所有发生在套架内的交流可被理解,就象在一个社团内的通常表述能被彼此理解一样。
各种文化中至少有下列一些可作为“启动表演”(to key performance)所用:“特殊符码”,是处于某个或另一个语层或特色中的特殊用语,如古语,常须换声换腔换词。“比喻语言”,即通常所说的“打比方的话”。“对句法”,即重复或转换语言、语法、语意或韵律结构等。“特定的程式”,特殊文体的套语或特定的表演套式。以及“表演终止的落套”等等。这些都由表演者的表演能力来主宰,来通过“引起的期待值”以吸引听众参与。因为,一旦“你具有了掌握它们的趋势,它们就促进你参与进去”,既把听众注意力集中在表演者身上,又把观众的情感评价束缚在表演者身上,使听众对表演者有依赖性,从而为表演所着迷。表演者的能力也就体现为靠它们来控制听众,吸引听众和赢得听众。
最后,所有这些都成为了“表演模式化”(The Patterning of Performance),即上述的表演结构形式及其象征的特定行为,都只有包容在特定表演系统中方起作用,这是特定文化系统中固定的传统口语交流体裁,(traditional types of verbal communication),如有的民族这种固定模式就由“宫廷言谈”(court speech),“现代真实叙述”(true recent narrative)和“古语”(ancient words)组成。表演同其合成,就成为这种文化语言体系中有重大意义的固定表演模式。遵循并掌握它,你就能表演;熟悉和了解它,你就能欣赏。
可见,口语表演活动的实现,是套架、启动、认同、模式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又包括了场所,表演技巧系列,表演的基本法则,服务者(象书场的工作人员),表演者,接受者等等的积极参与,是一个社会文化各成分、各成员都起作用并都在运动中的过程。所以,研究口语表演艺术,也必须要综合的、全方位的并运动的研究它们,以克服长期以来狭隘静止借用文学理论、戏剧理论、影视理论等作研究的不到位弊病,这才符合口语艺术活动的特点和规律。
三、初步的几点比较疏理与思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的专治口头说唱艺术的这些理论方法,对我们的评弹研究与理论建树,应当说还是很有参考借鉴意义的。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只有周良、吴宗锡等不多的几位专家,发表过很有见地的研究论著,[6]然而大部分的研究也还停留在资料整理,经验总结或套用戏剧、小说等理论的狭隘而又静止的层面上。
据我所知,最早的评弹经验总结,应属清末马如飞编写的《南词必览》。需要注意的是,如同中国的传统文学批评一样,传统的评弹理论也同样不像西方的理论注重体系性,并都是大部头著作。但却如钱钟书教授所说的:“倒是诗、词、笔记、小说、戏剧里,乃至谚谣和训诂里,往往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7]我们将之同西方的口语艺术理论比较参照,就会发现,钱锤书的评价在这方面也同样是“精湛见解”。
首先,无论是以正面指出的“书品”要求,还是从反面提出告诫的“书忌”,[5](P173)它们都是着眼于主体说书人的表述技巧及其同听众的交流关系。这点是既同于西方的口语理论,又切合语言交流行为的本质特点的—说者与他人的对话行为。如“快而不乱,慢而不断,放而不宽,收而不短……”,就是要说者要说功好,结构好,能为听众着想,从而很好地实现话语意义的交流,达到演出的好效果。
其次,我们的传统评论非常注意表述的三要素,这同鲍曼的主张可谓异曲同工。如《南词必览》上讲的“小书中亦有五诀”中的“理”和“细”,就是要求说书人,无论是从整个故事脉络,还是人物、言行乃至细节,都应当“所讲事物和告知内容”的“指物意义”,须表述清晰。而《书忌》中的大多数告诫,也都是从反面强调了说书人的表述,应当对所说的“指物意义”都要有评价态度的“情态因素”。即“乐而不欢,哀而不怨,哭而不惨,苦而不酸……评而不判”等,这都是要求将自己的欢乐、哀愁、悲惨、辛酸的情感与评判的态度,倾注到表述话语中去。而巴赫金所要求的说者应引出听者的话语思想态度,即接受反应,同样说书“五诀”中,“味”、“思”占了其两诀,要求说书人能引起听众的“耐思”,并能让听众“解颐”而生趣。
再次,我们的传统评论,还很讲究说书制造一个艺术的声音世界的口语艺术特点。沈沧洲《杂录》[5](P175)中说:“书与戏不同何也?盖现身中之说法,戏所以宜观也。说法中之现身,书所以宜听也。”为了让听众“宜听”从而进入声音的艺术世界,所以《书品》要求说书时,声音的掌握要“放而不宽,收而不短”,要“高而不喧,低而不闪,明而不暗,哑而不干”,从而是使声音的艺术世界,比现实世界更美也更合符艺术的真实动人。
即便是那些讲究台风要求的“冷而不颤,热而不汗”和忌讳的“束而不展,坐而不安”,以及要求表演这防止出现的“指而不看,望而不远”等动作表演,也都是为了“宜听”而不是“宜看”服务的。
至于“套语”、“套架”、“套式”、“启动”等等概念及其作用,则在评弹的艺术行话中,比比皆是。“噱”作为产生笑科的“套语”或“套架”,就有“肉里噱”,“外插花”和“小卖”三种。作为“套式”的弹词曲调,就有“陈调”、“俞调”、“丽调”、“琴调”、“蒋调”等20多种,表演时又有“紧弹散唱”、“快弹慢唱”、“润腔”、“拖腔”等多种技巧方法。而“启动”,更是丰富多样且又传统悠久,为江南广大听众与艺人所共有。以至许多青年人,平常只看影视,一旦进了书场,对听书感到没劲,就根本坐不住;纵然是红得发紫的当今影星、歌星,倘若他(她)不懂评弹的表演,在书台上说个故事,也会不知所措;然而当评弹响档同老听众、票友同进书场,那就说的有劲、听的有味,可谓其喜洋洋者也。何故?就因为评弹的“KEY”,比美国的说故事真是太多、太久也太成熟,都成了“专业性”的“学问”了。所以,不会吴方言不能演、不能听,会了吴方言但不懂其“启动”,也同样不能演、不能听。真不知这对评弹的发展是福是祸、抑或兼而有之?
中国传统评弹理论中,也还有西方口语艺术理论所未论及的方面。“书品”中的“贫而不谄”,“闻而不倦”,“羞而不敢,学而不愿”。谈到了说书人的人品、学习钻研等说书之外的“基本功”,不仅重要,而且也是涉及到了口语活动的“前设”阶段的重要问题,即说书者同生活、学习和修养的关系。
当然,过去的传统,往往是精华与糟粕、合理与悖论并存。“书品”中的“慢而不断”、“新而不窜”等。前者所要求的“慢”,若是指说的技巧,该慢而不断,这是有道理的。但将“慢”列为上“品”级的正面要求,这在过去可以,所谓“试卜闲人一笑中”,然而在当今快节奏的时代,哪来多少“闲人”,最多也就是退休人而已。但对受影视熏陶具快节奏欣赏习惯的年轻一代人来说,既是格格不入也就只能远而敬之了。而后者的“新而不窜”,既要不断翻新,又不许大改,要求维持其总面貌不变,这也是矛盾而又背时。因为随着时代的变而变的内容、形式和技巧等,是不可能“不窜”的。不然,那就只能导致说书的“昆剧化”、“古董化”,缺乏时代感,难以吸引青年新听众,后最终进入“博物馆”。还有《南词必览》中毛菖佩的词评:“古今书意改无穷;劝孝悌,醒愚蒙,古今余韵敬亭风”[5](P174)一方面要求改无穷,另一方面又恪守明末柳敬亭的风韵风格,这也是矛盾的,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风格多样化、当代化的要求的;至于劝孝悌、醒愚蒙,既是封建的说教,又将听众视作“阿斗”,完全背离了艺术的美的规律及其功能。
总之,我们的评弹传统评论,既有十分丰富的优秀见解,也有相当数量的谬识悖论,面对悠久而又灿烂的评弹艺术,面对不景气的评弹市场现实,作为每个关心评弹“一朵花”的人,都会有所焦虑。因此,在这当今“全球化”的时代,在中外经济文化频繁交往的文化转型时期,我们如何立足国情、立足当代,吸收融会中外理论的有益成分,发展我们的现代科学评弹理论,以指导评弹研究和振兴评弹艺术,当是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