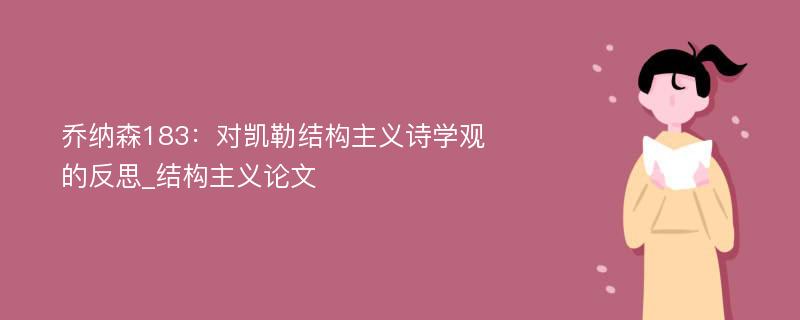
乔纳森#183;卡勒结构主义诗学观省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诗学论文,乔纳森论文,观省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5-0046-04
美国著名学者乔纳森·卡勒在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均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我国学界对此并不陌生,但我们在如何全面认识卡勒的学术理路,准确把握他的学术思想,客观研究和评价他的学术贡献方面做得还相对不足。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研究在他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成为他本人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之一。因而,分析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观,对他的结构主义诗学思想加以审视和评判,必将有利于我们对卡勒学术思想的研究和探索。
一、乔纳森·卡勒及其对结构主义的贡献
乔纳森·卡勒(Jonathan Dwight Culler)在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学者。他于1944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学术世家,父母皆为大学教授,良好的家庭氛围为卡勒后来的学术研究之路奠定了基础。卡勒中学毕业后入哈佛大学学习,于1966年以“最优秀成绩”(summa cum laude)获得历史和文学学士学位,并作为罗兹奖学金的资助学者(Rhodes Scholar)赴英国牛津大学深造,于1968年获比较文学学士学位,后又于1972年被授予现代语言学博士学位。1969年至1974年期间,卡勒受聘担任剑桥大学赛尔汶学院(Selwyn College)现代语言研究室的特别研究员和主任;1974年,他赴牛津任布拉斯诺斯学院(Brasenose College)的特别研究员和导师。次年,卡勒返回美国成为耶鲁大学法语和比较文学的访问教授,时年三十一岁。卡勒于1977年出任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英文和比较文学教授;从1984年到1993年,卡勒任康奈尔大学人文学科学会主任;从1993年至1996年,卡勒任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随后担任康奈尔大学英文系主任至1999年。此外,卡勒还先后荣任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执行理事、美国符号学会会长、美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等学术要职,并担任《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今日诗学》(Poetics Today)、美国符号学学报(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文学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等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
耽于新批评理论立场的英美学界沉湎于具体文本的阐释之中而难以自拔,对孤立文本意义阐释的倚重无法从总体的角度全面认识和总结文学的价值和规律。在《结构主义诗学》等一系列论著中,乔纳森·卡勒开宗明义,明确提出要超越新批评的阐释策略,为文学研究建立一种结构主义的诗学。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美国不啻为文学研究的一条新思路。卡勒在引进以法国为主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文论时,并不照抄照搬,而是为适应美国学界的实际做了一些独创性的修订和阐发,并结合本国的学术传统和资源做了创造性的发挥。他剖析了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基础和语言学模式,提出了“文学能力”的理论范畴,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自己的结构主义诗学思想,对结构主义的前景和性质做出了精到的分析。卡勒的研究把握住了结构主义的内在本质和精神追求,又结合美国学界的实际做了适当的变通和革新。这使得《结构主义诗学》一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在美国引进欧洲大陆结构主义文论最为成功的典范,卡勒本人也因而荣获美国现代语言学会的洛威尔奖(James Russell Lowell Prize),赢得了结构主义诗学家的美誉,成为结构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言人之一。
二、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观的内涵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D.Kellner)和斯蒂文·贝斯特(S.Best)在《后现代理论》中谈及结构主义时是这样概括的:“结构主义者把结构——语言概念运用于人文科学当中,试图把人文科学重新建立在较为稳固的基础之上。……结构主义革命运用整体分析法,把结构主义定义为一个共同体中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构受无意识符码或规律支配,譬如,语言就是通过一组独特的二元对立来构成意义,神话是依据规律或符码体系来规范饮食起居和性行为。”①诚如斯言,为了给人文学科找一个稳固的基础,结构主义具有了一种科学追求的情怀,它重新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重建了一个客体。据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的观点,结构主义本质上既非一种学派,又非一种运动,而是一种活动:“一切结构主义活动,不管是内省的或诗的,是用这样一种方式重建一个‘客体’,从而使那个客体产生功能(或‘许多功能’)的规律显示出来。结构因此实在是一个客体的模拟,不过是一个有指导的、有目的的模拟,因为模拟所得的个体会使原客体中不可见的,或者你愿意这么说的话,不可理解的东西显示出来。”②结构主义者把客观实体首先加以分解,然后再予以组合,形成客体事物的一个“类象”。这类象与客体事物之间的比照决定了结构主义所追求的可理解性,我们也就依此来发现和揭示这客体事物的意义。故而,巴尔特指出,“创作和思考在这里不是重现世界的原来的‘印象’,而是确实地制作一个与原来世界相似的世界;不是为了模仿它,而是为了使它可以理解。因此,人们可以说,结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模仿活动;这也是为什么,严格说来,结构主义作为理解活动与特别是文学或一般艺术并无技术性的差别:它们都来自模拟,不是在实质类似的基础上模拟,而是在功能类似的基础上模拟”③。通过这种模拟,通过重建客体,结构主义者使事物的某些功能得以显现,从而达到自己的研究目的,而这在本质上就是一种结构主义活动。需要明确的是,在这一结构主义活动中,得以重建的客体只是一个功能性的新范畴,对其赋予意义以及使这种意义最终得以可能的还是人类的意指过程。对于结构主义而言,这一过程是尤其重要的,也清晰地表明了意义的产生过程远比意义本身要重要得多这一条结构主义的真谛。
显然,对巴尔特深有研究的乔纳森·卡勒体味到了他将结构主义视为一种活动的目的所在,也理解这一观点的学术价值。但卡勒本人却是用另一种方式来界定结构主义的内涵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卡勒的论述更为直接,也更为通俗易懂。他说,“结构主义是二十世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的一种动向,这种动向比较不大看重因果说明,而强调指出:为了理解一种现象,人们不仅要描述其内在结构——其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还要描述该现象同与其构成更大结构的其他现象之间的关系。就比较严格的意义来讲,结构主义一词通常限于指现代语言学、人类学和文学批评中的一些思想流派。在这三个领域中,结构主义试图重建现实现象下面的深层结构体系,这些体系规定现象中可能出现的形式和意义”④。在这里,描述一种作为研究对象的现象与其他现象的关系,发掘某种“深层结构”,与巴尔特所谓基于模拟的结构主义活动并不矛盾,无论将结构主义视为一种活动,抑或一种方法,其实只是称谓上的不同而已。这种理论表述上的差异,都可以统一到探究意义何以可能、何以产生这一结构主义的最终目的上。
而且,对语言模式的倚重在他们两人身上也得到同样的反映,这当然与结构主义的内在品质有关,它本身就是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思想的启迪而萌发的。文化现象自身的实质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它与其他文化事实的关系;这些文化现象是具有意义的文化现象,所以也就可以把它们作为符号来研究,这也正是索绪尔留下的遗产。像巴尔特一样,卡勒对符号学也很重视。卡勒曾论述道,“结构主义研究关系的结构和系统,这种结构和系统使得文化现象得以界定和彼此区分。而符号学研究的是具有意义的文化现象这一符号”⑤。但卡勒还是委婉地建议,在结构主义阶段,两者之间的区分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这也与巴尔特的论述不无共同之处。当然,我们这样说只是基于结构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言,也就是说巴尔特和卡勒对结构主义本质的认识可以说是一致的,他们都以标举“诗学”研究的大旗而著称。但这一点也未能遮蔽他们之间的差异。巴尔特在其《叙述结构分析引言》等著述中对叙述的“功能体”以及“代码”等所做的论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卡勒却鲜明地提出了“文学能力”的诗学构想。
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并不以发现或派定具体文本的意义为旨归,而是要确定文学意义产生的条件。这种诗学诉求也把文学批评和研究导向了阅读活动,正是读者的阅读活动对架构诗学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因而,“建立一套有关(读者)文学能力的理论,这就是卡勒规定的诗学的任务”⑥。卡勒主张,文学研究的焦点既非具体的文本本身,又不是对传统的文学体系的过分倚重,而应从读者入手,从读者的文学能力出发,来探讨读者的阅读行为,探讨潜存于读者阅读行为背后的那一套约定俗成的程式系统,因为正是这些程式系统制约着读者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而这些程式一经内化,便成为了读者的文学能力。卡勒在乔姆斯基“能力”与“表现”这一对语言学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文学能力说。对于卡勒而言,诗学研究的真正对象不在于具体的文本本身,而在于文学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可理解性。“作品为什么可理解?在于读者的内在能力。因此要解释作品的可理解性,就必须阐明使读者能够理解它们的隐含的知识和常规——内在化了一种能力。按照这种解释,卡勒显然是想把注意的焦点从文本转向读者”⑦。虽然巴尔特也曾指出结构主义诗学必然导向对文学阅读的重视,但显而易见,卡勒在这一维度上做了更深更远的开拓。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既不同于雅各布森的诗学,又有别于巴尔特的叙事学,体现出了特殊的存在价值。
三、审视乔纳森·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研究
有一个问题历来为众多的学者所津津乐道,那就是结构主义的反人本主义倾向。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就此指出:“在说明文学原文(文本)潜在的统治系统的特征之后,结构主义者只能坐在一边,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把作品和它所写的现实联系起来,或者与产生它的条件联系起来,或者与实际研究它的读者联系起来,统统是不可能的,因为结构主义的基本态度就是取消这样的现实。”⑧这样的论断或许过于绝对化了,但它也反映出在结构主义者心目中“系统”的统治地位,作为文本生产者的作家消失在这一共时系统中,丧失了主体的地位,一切以个人主体为意义之源的看法遭到了根本的杜绝。“文学只能失去激情的意义苛求而成为结构性语言的乌托邦,或文学与神话的代码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获得反主体性的纯客观性价值诉求”⑨。这或许与结构主义产生的时代背景有关。西方社会自“上帝死了”(尼采语)之后,人的主体地位取代了神的主体地位。在科技力量的帮助下,人的主体性日渐膨胀,终于在19、20世纪交替时发展到了极致,生态环境的恶化让每一个人都有切肤之痛,世界大战又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精神创伤。对人的主体性地位加以反思成为时代的课题,而像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这样的思想家都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如果说近代以来的思想主潮是用人来代替神的主体性,那么,福柯的一代则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地位、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人”⑩。因此,结构主义者高呼“作者的死亡”也就不难理解了。为什么要在文学研究中逐出作者呢?卡勒曾做过探讨,他借用索勒斯(Philippe Sollers)的话说:“作者和作品的问题已不再是最为根本的问题,今天最为根本的问题是写作(writing)和阅读(reading)的问题。”(11)卡勒这里所谓的“写作”其实是指一种体制,而不是某一作者个人意愿的表达。如果把作者的地位凸显,那么势必引导我们对其表达意愿的关注,让我们确信这种意愿决定了作品的内容。这显然有悖于结构主义作为一种形式主义文论的初衷。
然而,“作者的死亡”却让读者走上前台,文学阅读的重要性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卡勒就是从文学阅读的维度着手,提出了读者“文学能力”的概念,进而探讨了“程式和归化”这种构建“文学能力”的诗学所必需的手段和步骤,还具体分析了抒情诗和小说中出现的具体情况,他对文学阅读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毕竟卡勒研究的对象是结构主义诗学,而不是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理论,这也就决定了卡勒的读者概念与某一个具体阅读文学文本的个体是有所区别的。实质上,他所谓文学能力的主体不可能是具体的个人,不可能是随意找到的一位读者。因此,我们不能轻易地认为,“作者死了”,读者的主体性地位便得以彰显;毕竟对于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而言,最终起作用的是他反复论证的约定俗成的程式和惯例系统。这种程式系统,在卡勒的心目中最具决定意义,而它本身却呈现出先验的性质。“按照索绪尔的观点,任何意义仅限于一个关系和差异系统的内部,正是这一系统决定了我们的思维和认知活动。很明显,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的核心——‘文学能力’的理论,正是与索绪尔、乃至康德以来强调主体先验认识能力的传统一脉相承的”(12)。盛宁先生的这段话点出了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理论基础的本质,并认为卡勒对文学的总体认识和文学意义的预设与新批评、弗莱的观点和主张并无二致,卡勒将后者所排斥的东西也悉数置于研究的范围之外,“这种视野上的局限势必有损于这种结构主义诗学的意义和影响(13)”。其实,从卡勒的分析中,我们也可辨析出其与新批评、与弗莱的明显区别,很多时候卡勒都在以他们为靶子调试自己的理论。
卡勒认定结构主义诗学的目的在于说明文学理解和阐释的程式,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尽管他所论述的读者的文学能力未必具有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王逢振先生就指出过,“人们的文学修养和语言把握,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形成意识形态,总是千差万别的,因此对某个特定时期出现的文本解释的分歧,不可能只用一种规则或常规来说明,而规则或常规也不可能都始于同一根源。卡勒强调读者的文学能力和阅读过程是对的,但对解释程序系统的设想却显得软弱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实的”(14)。但任何一种理论的提出,只要能对文学研究有所裨益,也就弥足珍贵了。任何一种学术范式的主观目的性都是和相对的学术规律性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规律不是绝对的,经常随着学术范式的变化而改变,任何一种学术范式的提出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解决所有的问题。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与欧陆学者的结构主义主张相比,也还是有着自己的特性的。从根本上说,从读者的阅读出发来探究意义之程式问题的这种思路是富于独创性的,它已经从狭隘的文本形式分析的限制中突破出来,从“语言的牢笼”中突破出来,寻求文学文本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但却没有舍弃结构主义语言符号分析模式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卡勒的结构主义诗学观为我们提供了颇多可资借鉴之处,尽管它也有自身的局限。
收稿日期:2009-03-10
注释:
①[美]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23-24页。
②③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15页,第416页。
④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1987年,第532页。
⑤[美]Donald Keesey.Context for Criticism.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1994,P281.
⑥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⑦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92页
⑧[英]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⑨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61页。
⑩赵毅衡:《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11)[美]Jonathan Culler.Structuralist Poetics,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5,P131.
(12)(13)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78页,第179页。
(14)郭宏安,章国峰,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第3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