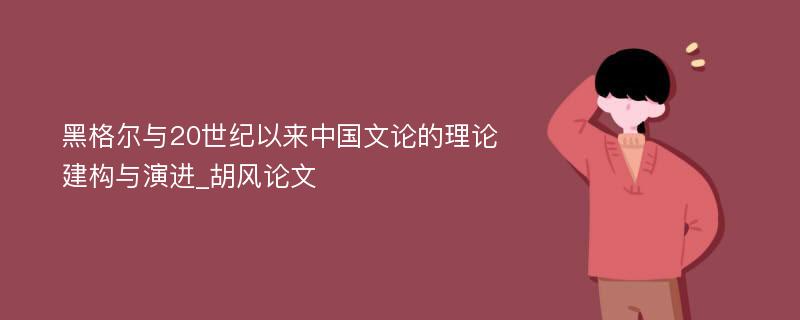
黑格尔与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学理建构及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文论论文,学理论文,中国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6-0120-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6.018 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话语建构,迄今已逾百年。在建国前的现代阶段,从古代“诗文评”传统破茧而出,筚路蓝缕,几多艰辛;在建国后的当代阶段,历经高歌猛进、风雨交加、云卷云舒;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仅众声喧哗,更有核心思路的更替。时至今日,文论界既需要、也能够在各种外来影响面前作出切合实际的独立判断,而独立判断是以深刻反思为基础的。反思的范围、方法与对象等,不应该有限定,但进入到深层次之后,也即文论发展的学理层次,像思维方式、核心范畴,体系建构等等,反思的范围将会聚焦于关键问题与核心人物。这种反思对于我们认清所走过的道路、选择未来的方向,进而推进21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百余年的文论话语建构过程,第一推动力莫过于中国近代以来社会政治变革的现实需要。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深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逐渐得到确立,并处于指导地位,当代文论领域中一些重大问题的探讨尤其亦如此,如批评标准、创作方法、悲剧理论、典型问题等等。同时,就文论话语本身的学理建构而言,西方诸多理论家的影响极为深刻、十分深远,他们的名单如果详细开列,将会是长长的一串,位于名单前列的,当为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作为“三尔”之首的,无疑是黑格尔。 一、黑格尔学说初步译介与中国现代文论雏形 1903年马君武在《新民丛报》发表《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①,该文是“我国第一篇介绍黑格尔生平及思想的专文”,②标志着黑格尔学说正式登陆中国。目前所见较早运用黑格尔美学观点的文章,有1907年《小说林》创刊号上发表的《小说林缘起》③,徐念兹在文中以黑格尔美学思想阐释小说的审美境界,其见识颇具现代风貌。在20世纪前20年间,黑格尔的学说由于相当晦涩,并未引起国人太多的注意;但黑格尔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末却逐渐超过康德,从而黑格尔开始成为影响中国最大的西方思想家之一。“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37年共发表了有关黑格尔的文章近一百篇,是康德的三倍,也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西方哲学思想家。”④其间,1931年在黑格尔去世一百周年之际所出版的《哲学评论》“黑格尔专号”,为黑格尔在中国的接受掀起了一波小高潮。 这一时期译介黑格尔学说的队伍中,主要哲学家有张颐、朱谦之、郭本道、贺麟、朱光潜、张君劢等诸位大师,其中贺麟先生的译介和研究最具代表性。仅就新中国建国前而言,贺先生积十年(1941-1950)之功翻译了《小逻辑》,还编译了一部分西方学者研究黑格尔的著作,如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开尔德的《黑格尔》等⑤。在《黑格尔学述》后序中,贺麟先生写道:“我之所以译述黑格尔,其实时代的兴趣居多。”⑥他认为我国当时的政治、学术都与黑格尔时代类似,黑格尔思想中对民族性的强调,于我国具有唤醒民族精神的作用;黑格尔学说与当时中国社会情状的这种契合,是其思想得到较为顺利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贺麟先生在黑格尔哲学范畴的定名、后续研究力量的培养、中西融汇等方面的努力,把黑格尔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可以说,他们那一批学者对黑格尔学说的译介,为黑格尔思想介入中国现代文论提供了文献基础,而苏联官方文艺学的初步引入,则为中国现代文论接受黑格尔思想提供了可直接模仿的范本。 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共领导人托洛茨基、列宁等人论述文艺的著作就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文艺理论著作也频频见于当时左翼文论家的著述中,而这些理论家同时也都深受黑格尔学说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一些文艺学教材已经在模仿苏联文论教材的基本框架和理论立场来讨论文学问题,大致确定了中国当代文论的雏形。 需要注意的是,从思想传统角度看,“除了德国以外,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偏爱黑格尔。”⑦俄罗斯文化中对黑格尔及其本体论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康德及其认识论的评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苏联文论界发生了较大变化:革命成功后,内部的异质声音逐步遭受压制,马克思文艺思想被庸俗化和教条化,关于文学观念的理解越来越同一化、标准化和黑格尔化,成为日益固化的意识形态构成元素。出于对俄国革命的憧憬和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期盼,一些左翼文论家在学习、模仿苏联文论的过程中,亦直接或间接受到黑格尔的影响:主要涉及文学本质、文学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文学理论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文论述说方式等等方面。 胡风、周扬等人虽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在关于文学根本特征的认识上却是基本一致的:文艺来源于生活、文艺是生活的形象反映这一关键原则是他们的共识。胡风认为:文艺和科学是认识真理的不同形式,文艺通过感象的个体去表现普遍性;周扬认为:“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是通过具体的形象去达到客观的真实的。”⑧这一从黑格尔到别、车、杜关于文学艺术的基本看法,是当时众多文艺观念中最具革命性的。该文学基本观念在巴人的《文学读本》、《文学读本续编》⑨,蔡仪的《文学论初步》⑩,林焕平的《文学论教程》(11)等文论教材中均有体现,影响深远,为建国后的文学反映论奠定了基础。 对于文学创作活动的认识,他们普遍采用黑格尔认识论的基本模式来规定创作中的主客体关系。周扬认为:“客观世界是离我们的主观而独立存在、发展的。主观和客观的结合,即人认识周围世界必须经过实践的过程。”(12)胡风在创作论上也强调认识的主客关系,不同的是他更多地强调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他认为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于外在生活绝不仅仅只是“看到”、“择出”、“采来”,而是要通过主观精神加以“肯定”、“拥有”、“蒸沸”和“提升”。(13) 在文论话语方面,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黑格尔在文论话语体系中的渗透已经初现规模,如内容与形式、典型、悲剧等概念范畴的运用,无不由黑格尔而来。胡风经常使用的“主观精神”、“客观精神”、“人格力量”、“思想力”等话语,亦与黑格尔哲学密切相关。胡风与周扬之间关于“典型”问题的论争,文字间充盈着黑格尔式的风格。周扬在批评胡风的“典型论”时,常引黑格尔的观点作为重要论据:“借一位思想家的说法,就是:‘每个人物都是典型,而同时又是全然独特的个性——这个人(This one),如老赫格尔(即黑格尔)所说的那样’。”(14)“这一个”的理论即来源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对“感性确定性”的论述。在争论中,胡风进一步学习黑格尔哲学美学并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文论,至20世纪40年代,黑格尔元素在胡风身上已经得到十分明显的体现。1944年写《人生·文艺·文艺批评》等文章时,胡风对黑格尔《逻辑学》和《美学》中内容与形式辩证法已有深入了解:“作品,有了某一程度完成性的,能够成为批评对象的作品,总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体。正像黑格尔所说:‘形式是向形式移行的内容,内容是向内容移行的形式’;就形式说,它是由内容产生,而且被内容包含的。”(15)1948年胡风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美学进行了一次认真的梳理,详细考察了黑格尔哲学的体系特征,大段引用黑格尔《美学》中的文字,还对黑格尔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反思。胡风认为:当时文论界流行的从概念出发的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机械反映论等,其根源离不开对黑格尔的解读;胡风的目的,在于通过对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来试图纠正庸俗唯物论的流弊。同时,胡风对黑格尔的悲剧冲突理论也予以改造,他的基本观点是“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16)。在对路翎小说《饥饿的郭素娥》和《财主的儿女们》的评论中,胡风认为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郭素娥、魏海清、蒋纯祖等都是有着性格局限的执着者,由于他们执着于并不一定崇高的信念,在社会变革中必然走向悲剧性的毁灭。胡风的这一结论,明显地体现一种思路:把黑格尔悲剧冲突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中强调历史视角的观点相结合。 此外,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论创作的论述风格体现出来,相当一部分文论家在写作中都主动借鉴黑格尔的辩证法思路。在行文风格上,胡风“时刻营造着概念相生相克、互相消长的契机”,(17)黑格尔辩证法色彩十分浓厚。蔡仪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新艺术论》(18),在论述过程中始终强调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一个命题中考察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中达到综合,相当系统地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在文论著作中的运用。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我国现代文论的学理建构取得长足进步,建国后当代文论前30年的基本形态和主要关注点,在这一时期都已大致登台亮相。黑格尔学说的译介与应用,对这种局面的形成发挥了巨大促进作用。 二、黑格尔学说的接受、融合与中国当代文论建构 自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当代文论一元化特征逐步形成并固化,从学理层面看,这其中不乏黑格尔同一性思维被普遍接受所发挥的明显作用。思想领域的同一化过程为促进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奠定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但同一性思维的极端发展也给当代文论的多元生态带来极大限制。建国以后,我国学界的黑格尔研究拥有较为可观的学术队伍,出版了一大批专著和论文。黑格尔哲学体系和美学思想中关于实践、对象化的思想,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中国文艺学学科的确立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时期我国对黑格尔的接受是以苏联模式为主的。俞吾金先生指出,从恩格斯、列宁到斯大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阐释路线,已经逐渐将马克思黑格尔化,其主要表现是哲学理论的思辨化、思维与存在的同质化和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化(19)。还有学者认为:黑格尔哲学中的整体主义、理性主义、认知主义、绝对主义和体系化思维等非辩证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了消极作用,“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啃着这个历史的苦果。”(20) 黑格尔同一性思维方式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文艺学尤其如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21)_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度涉及到政治上唯心唯物阵营的划分。正因为如此,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哲学界还展开了“思有同一说”问题的讨论(22),参与这一讨论的主要人员有贺麟、张世英、于世诚、姜丕之和汝信等诸位大师。他们对黑格尔哲学中这一基本问题做了多角度探讨,其结论正如姜丕之先生和汝信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看来,是否承认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既是唯心的又是辩证的,是否承认黑格尔在批判二元论、不可知论和形而上学观点方面有一定的历史贡献。一句话,是否承认黑格尔的这一理论中有‘合理的内核’,这就是分歧的实质所在。”(23)经过这次讨论,哲学界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思维与存在同一于思维,绝对理念衍生一切;马克思主义则把这一被颠倒的关系予以复正:存在先于思维,思维能动地反映存在。 这次争论的历史功绩,在于为人们更好地了解黑格尔“思有同一说”提供了契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基础在哲学原理层面得到正式阐明,也对建国初期的黑格尔研究提供了合法性。但是,在那个已经开始将一切意识形态政治化、口号化的年代,哲学领域的原理进入文论领域时往往被简单化,被教条式地普遍使用,从而促使文学创作和批评不是从社会生活现实出发,而是图解政治和政策,直至在“文革”中,概念化、公式化的创作方式和批评方式大行其道。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当代文论较为顺利地接受并融合黑格尔哲学美学思想的时期。黑格尔关于艺术本质、辩证法及其概念范畴、体系模式,比较自然地进入文论领域,被广泛运用于文论建构和文学批评。最先指出黑格尔美学对文论具有重要价值的是朱光潜先生,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西方数千年来在美学和文艺理论上具有科学价值而影响深广的著作只有两部,其中之一就是黑格尔的《美学》(24)。我国当代文论界的黑格尔美学研究也从此时进入第一个高峰期,主要代表有朱光潜、汝信、蒋孔阳等诸位大师。 朱光潜先生为黑格尔美学介入当代文论作出了开创性贡献。20世纪从50年代到80年代初,朱先生克服种种困难,陆续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美学》(中译本共3卷4册)。与此同时,朱先生还对黑格尔美学进行了最早的批判性研究,先后写作《黑格尔美学的评介》(25)、《西方美学史》中的《黑格尔》一章(26)以及《〈美学〉译后记》(27)等文字,对黑格尔《美学》思想进行了全面解读与批判,主要内容包括黑格尔美学体系、辩证法、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人化与对象化等处于萌芽期的实践概念、艺术类型与历史观念在艺术史中的运用等。由于朱先生的努力,黑格尔美学研究在学界呈现出勃勃生机。蒋孔阳先生对德国古典美学异常重视,认为现代美学的各个流派都可以追溯至德国古典美学。尤其是黑格尔美学,其《德国古典美学》一书初稿于1965年,是“我国第一部西方美学断代史研究专著”(28),而且蒋先生写作《德国古典美学》期间,黑格尔《美学》中译本尚未出版第3卷,他是在研读英文本《美学》的基础上完成该著作的(29)。 正是这些前辈学者对黑格尔美学的研究、消化和运用,使得黑格尔美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学术话语等开始对中国当代文论产生全面影响。同时,恰如现代文论那样,当代文论接受黑格尔还有另一条主线:通过具有浓厚黑格尔色彩的苏俄文论;长期占据当代文论核心地位的本质论问题,正由此而来。 除去传统因素,在学理层面上,我国当代文论可以说是在列宁哲学和别、车、杜文论思想的直接影响下,逐渐完成对文学基本特征的概括:“文学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建国以来主流的文论教材都秉持这一基本观念。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特点,在于它用形象反映社会生活。”(30)蔡仪先生主编的《文学概论》指出:“通过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基本特征。”(31)十四院校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强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用形象来反映生活”(32)。对文学基本特征的这一界定,最具权威性的理论资源在于别林斯基关于形象思维的观点:“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33)上述三本全国统编教材,都在显著位置引用别林斯基的这句话。稍加辨析就不难看出,别林斯基的这一观点,与黑格尔的“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34),在学理上同属一脉。黑格尔认为:艺术、哲学、宗教都是对绝对理念的认识,区别只是在于,艺术用感性形象、宗教用表象、哲学用概念来显现真理,它们分属于绝对理念的不同显现阶段。同时,由文学用形象反映生活这一基本观念,又直接生发出关于艺术真实的看法:“艺术的使命在于用感性的艺术形象的形式去显现真实。”(35)贯穿当代文学与当代文论主脉的真实性问题,在学理上与黑格尔艺术显现真实的认识论路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我国当代文论建构的主要平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体现为文论教材的编写。其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思想,因较易契合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的建构,自然得到结合,融入全国统编教材。 1954年到1955年间,教育部特邀苏联专家毕达可夫来北京大学讲授《文艺学引论》课程(36),毕氏本是卫国战争的战斗英雄,他对文论的理解始终不出其老师季莫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三卷本框架(37)。这两套教材都带有较明显的机械唯物论色彩,其基本结构成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文论教材的范本。之后以群先生和蔡仪先生独立主编的文论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和《文学概论》就深受其影响,基本架构亦未能超出毕氏师徒著作的范围。据统计,仅以《文学的基本原理》为例,该教材前后七次征引黑格尔《美学》中的观点,除了对其唯心主义特点有所批判之外,大部分是正面引用,集中在文学本质、内容与形式、典型等章节中,不是用来谈论文学的感性显现本质,就是以辩证法来认识内容与形式间的关系,以及典型的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以群先生与蔡仪先生主编的全国统编教材,基本奠定了我国当代文论教材的话语体系。此后,文论教材在论述上注重思辨化,并大致规范了文学史的处理格局:倾向于逻辑与历史的同一;黑格尔于此是功不可没的,其辩证法的影响甚至堪称居功至伟。 教材之外,当代文论的方方面面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之间,亦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学界普遍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正确地反映生活的本质和规律,而文论的基本任务则在于确认文学的本质,寻找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规律,并由此梳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乃至规律。以古典文论的研究为例,早年王元化先生以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科学研究方法为基础,从全新角度切入《文心雕龙》研究,其《文心雕龙创作论》虽然在中西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上采取“案而不断”的方法,但该书的确“是在我国创造性地用运用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逻辑和知性分析方法与乾嘉学派考证方法相结合的一个范例”。(38)早年的王元化先生对黑格尔理性哲学极为服膺:“自从读了黑格尔哲学之后,我成为黑格尔的景仰者。我觉得他的哲学具有无坚不摧扫除一切迷妄的思想力量。”(39)众所周知,创作论一直是古代文论研究中的“硬骨头”,陆机在《文赋》中就曾感叹“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40)王先生之所以甘啃这块“硬骨头”,选择《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论作为研究对象,与他自信掌握了黑格尔理性主义息息相关。王先生曾坦言:“当我开始构思并着手撰写它的时候,我的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41)《文心雕龙创作论》是成功运用黑格尔理论分析中国古典文论的代表作,标志黑格尔思维方式在中国古典文论研究领域的成功介入。 三、黑格尔影响的反思与中国当代文论转型 随着“文革”的结束、新时期拨乱反正的全面展开,当代文论界对“极左”政治思潮的反省也不断深入:先有解除强加在文艺身上的政治附庸的枷锁,继之创立文艺美学,从基本原理层面赋予文学以独立性。与此同时,对外开放的规模在不断扩大,西方文论的全貌也逐渐为学界知晓,迄今已达到能够基本同步了解西方文论进展的地步,对西方文论单一视角的接受局面一去不复返。这两大因素的合力,推动着我国当代文论以较快的速度脱离以往那种相对单一的发展格局,从整体上显现出多元发展的势头。客观地说,西方20世纪文论尤其是后现代文论,对中国当代文论转型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引发作用。在转型过程中,不仅始终伴随着对黑格尔的还原研究,甚至可以说对黑格尔的反思是文论转型的学理基础和先导。文论界日益认识到:黑格尔思想的体系性、同一性、先验性、乌托邦主义、理性主义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等等,在学理上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巨大促进作用已经发挥到极致,其不再适应21世纪全面开放的社会现实与大众文化等弊病,同样也尽数显露出来,虽然文论界不必像西方文论那样“叛离黑格尔”(42),但在当代文论领域,黑格尔的确正在成为训练学子的经典而非前行的指南了。 新时期以来,文论界对黑格尔早期思想特别是异化理论的研究,为打破“左倾”思想禁锢、解放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资源。1983年张世英先生节译出版德国哲学史家菲舍尔的《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43),对黑格尔早期思想做了初步介绍;1989年宋祖良先生出版其博士论文《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44),对黑格尔早期的神学理论、政治著作和耶拿时期的作品做了深入分析,阐明了黑格尔早期理论的主要形态。黑格尔异化理论进入学界视野后,王若水、汝信、高尔泰等先生对其进行深入考察,改变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异化的观念,并打破不能研究异化的局面,从而异化理论的探讨得以与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保持同步。这一时期文论界对黑格尔美学思想的研究进入第二次高潮。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树人先生、朱立元先生等。1985年王先生的《思辨哲学新探——黑格尔哲学体系研究》出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尤其是建构体系的理论思维进行了深刻反思;朱先生对黑格尔美学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突破了‘左’的路线的框框,能够比较实事求是地对待黑格尔”。(45)在对黑格尔美学思想和悲剧理论的具体研究方面,纠偏成为主流倾向,研究方法也呈现多样化形态。黑格尔早期思想中就种下的突破老年黑格尔体系的种子(如“承认”概念),在西方被解读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源头,该理论视角于此时开始得到文论界的日益重视。 对黑格尔思维方式中先验性、乌托邦主义和哲学一元论的反思,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黑格尔研究的发力点。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顾准先生遗著《顾准文集》,1996年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张中晓先生遗著《无梦楼随笔》,这两部书虽然篇幅短小,但无疑给90年代思想界带来了巨大冲击。张先生在随笔中摘抄了不少黑格尔《小逻辑》段落,对黑格尔概念的空疏与干枯予以非常直切的批判。单世联先生认为:在中国,张中晓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首创性”,“对于告别黑格尔的思想历程来说,他不但是第一声啼血的杜鹃,也给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真实而沉郁的背景”(46)。根据单先生的概括,张中晓至少在三个方面反思了黑格尔:一是先验史观:“历史的道路不是预先设定的,不是先验的途径”(47);二是绝对真理:“人们口中越是说绝对、完美、伟大……大吹大擂,则越是应当怀疑那种神圣的东西。因为伟大、神圣之类东西在人间根本不存在”(48);三是批判国家至上,呼吁个人价值和自由:“一个美好的东西必须体现在个人身上,一个美好的社会不是对于国家的尊重,而是来自个人的自由发展”(49)。王元化先生认为:张中晓的“无梦”正是对黑格尔乌托邦主义的告别。顾准先生则对黑格尔乌托邦主义的“终极目的”和哲学一元论展开批判。黑格尔认为历史的变化服从于普遍理性和“绝对精神”这一“终极目的”,顾准先生认为“终极目的”逻辑地包含着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一部分人自以为掌握着真理,承担着“建立天国”的重任,就把“终极目的”当做最高目的,并为此而拒绝、否定任何其他目的,把一切中间过程都当做手段,但是“终极目的”是唯理主义的推论,是认识论的向壁虚构。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顾准先生写道:“没有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50)在哲学上,顾准先生提倡多元主义,反对哲学一元论和政治权威主义。他认为“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一元主义和政治上权威主义的根据。”(51)因而,顾准先生提倡从理性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从哲学上和政治上对黑格尔的乌托邦主义和哲学一元论予以激烈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元化先生重点反思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义、绝对规律、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同一性思维方式等核心范畴与思维路径。值得注意的是,张中晓先生和顾准先生的遗著被整理出版时,王元化先生都为之撰写序言,并从中继承他们的反思成果。王元化先生本人对黑格尔的反思,与张、顾相比,显得更为具体些。黑格尔“理性的狡计”提出:任何人的一切活动都在执行理性的命令,受到理性的驱使,在悲剧中最终胜利的是代表理性的普遍伦理力量。王元化先生认为:“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为信念的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偏颇,认为人能认识一切,可以达到终极真理……一旦以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独断论者。”(52)王先生对绝对规律的反思,具体表现在他对文学规律的重新认识上。在1992年出版的《文心雕龙讲疏》中,他毫无遗漏地将1979年版《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规律”、“一般规律”、“普遍规律”、“创作规律”等字眼悉数删除,对阐释文学规律的段落亦全无保留。王元化先生对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律反思的结论是:“从历史的发展中固然可以推考出某些逻辑性规律,但这些规律只是近似的,不完全的。历史与逻辑并不是同一的,后者不能代替前者。”(53)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原则提出明确的质疑,这一反思对当代哲学史与文学史的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影响。(54)在此基础上,王元化先生对黑格尔同一性思维方式进行了深刻反思。 中国当代同一性思维的学理依据,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同一哲学,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的同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现象与本质的统一、是同一性思维的最高表现形式。王元化先生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把对黑格尔同一性的反思与卢梭的国家学说联系起来,指出黑格尔同一性思维运用于国家学说中的谬误和危险。在1993年7月1日的日记中,王元化明确写道:“朱学勤曾向我谈及,认为我说的不能用逻辑推演历史,他很赞同。今天我再向朱学勤谈到这一看法,批判过去自己也十分相信的逻辑与历史一致的观点。此说之根源乃来自黑格尔的同一哲学。”(55) 与此同时,哲学界与文论界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进行改造,为新世纪以来的文论研究确立了全新思路的基础。本质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是一种相对简单的认识模式,一旦面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复杂情况,往往难以给予符合实际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后现代反本质主义思潮开始进入我国学界,反响强烈、震动巨大,但对后现代解构一切的倾向,学术界始终保持着必要的审慎。张志林、陈少明在《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56)一书中,就试图改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在本质与反本质的中间腹地寻求建构的可能,这一思路为新世纪以来陶东风等人的建构论文艺学所继承。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古典诗性智慧,也于这时重新受到重视。张世英先生借助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重奏视角阐发中国古典智慧,对文论界走出黑格尔的影响功莫大焉。张先生是建国后前30年学界最重要的黑格尔研究专家之一,成果丰硕,为黑格尔思想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到了20世纪90年代,张先生通过海德格尔重新发掘中国古典智慧,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改造和超越,他提出主客二分认识论思维模式必须走向更高一层的天人合一和主客交融,把主客对立思维转换为包含中国古典智慧的主客统一。 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当代文论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观念变迁的速度明显加快: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文学活动论、文学建构论等不同文学本体论学说,不断被提出。美学领域里,在原来实践美学的基础上,涌现出和谐美学(周来祥)、意象美学(叶朗)、超越美学(杨春时)、生命美学(潘知常)、环境美学(曾繁仁)、实践存在论美学(朱立元)等等多元化发展格局。这一系列变化背后,都涉及到根本的学理层面,也都与对黑格尔的反思密切相关。 20世纪初期至三四十年代,黑格尔学说通过欧美哲学和苏联文论,进入中国现代文论的建构过程,在学理层面上影响着现代文论的话语建构。建国以后,随着研究规模的不断扩大,黑格尔对中国当代文论学理层面的影响也不断加深,并延及文论领域的方方面面。新时期以来,尤其是后现代思潮进入学界之后,文论界对黑格尔思想中包括同一性思维、乌托邦主义、理性主义、先验性等思维特征的反思日益深入,且至今仍在进行。黑格尔与20世纪以来中国文论的内在关系,是西方文论中国化过程中的典型个案,对它的深入研究,于西方文论的整体反思和中国文论话语的独立建构,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①马君武:《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新民丛报》第27号,1903年3月12日。 ②④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2、87页。 ③徐念兹:《小说林缘起》,《小说林》1907年第1期。 ⑤两书均于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⑥贺麟:《黑格尔学述·后序》,载开尔德、鲁一士《黑格尔学述》,贺麟编译,上海人民出版2012年版,第304页。 ⑦杨明明:《洛特曼符号学理论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3页。 ⑧周扬:《文学的真实性》,《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1日。 ⑨巴人:《文学读本》,上海珠林书店1940年版,《文学读本续编》,上海三通书局1940年版。 ⑩蔡仪:《文学论初步》,香港生活书店1946年版,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版。 (11)林焕平:《文学论教程》,香港中国文化事业公司1948年版。 (12)(14)周扬:《现实主义试论》,《文学》第6卷第1号,1936年1月1日。 (13)胡风:《为了电影艺术的再前进》,见《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15)胡风:《人生·文艺·文艺批评》,见《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16)胡风:《我读路翎的剧本》,载《胡风选集》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5页。 (17)红苇、周斌:《胡风文艺理论中的黑格尔因素》,《齐鲁学刊》2001年第1期。 (18)蔡仪:《新艺术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9)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289页。 (20)冒从虎、郜庭台:《黑格尔哲学:一个沉重的思想负担》,《学术月刊》1989年第5期。 (2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22)辛文:《关于黑格尔的“思有同一说”的讨论》,《光明日报》1962年5月18日。 (23)丕之、汝信:《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的辩证意义》,《光明日报》1962年8月3日。 (24)(27)参见朱光潜《美学·译后记》,见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7、336—366页。 (25)朱光潜:《黑格尔美学的评介》,《哲学研究》1959年第8—9期。 (26)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0—501页。 (28)郑元者:《在知识谱系中构筑学术个性》,见蒋孔阳《德国古典美学》,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37页。 (29)笔者上世纪90年代初在蒋先生处受教时,亲耳聆听先生讲述《德国古典美学》的成书过程。 (30)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版,第34页。 (31)蔡仪主编:《文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页。 (32)十四院校编写组:《文学理论基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33)别林斯基:《智慧的痛苦》,《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 (34)(35)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2、68页。 (36)课程结束后,讲稿翻译出版:依.萨.毕达可夫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译,《文艺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37)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第一部《文学概论》、第二部《怎样分析文学作品》、第三部《文学发展过程》,查良铮译,上海平明出版社1953年、1954年版。 (38)李衍柱:《重读黑格尔——谈黑格尔〈美学〉与中国文艺学建设》,《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 (39)王元化:《读黑格尔》,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40)陆机:《文赋》,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75页。 (41)(53)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228页。 (42)参见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俞宣梦、菀利均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章:叛离黑格尔。 (43)库诺·菲舍尔:《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张世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4)宋祖良:《青年黑格尔的哲学思想》,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45)蒋孔阳:《黑格尔美学论稿·序》,见朱立元《黑格尔美学引论》,天津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46)单世联:《告别黑格尔——从张中晓、李泽厚、王元化到顾准》,《黄河》1998年第4期。 (47)张中晓:《无梦楼随笔》,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6页。 (48)(49)张中晓:《无梦楼全集》,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128页。 (50)(51)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0、345—346页。 (52)王元化:《王元化文论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97页。 (54)当代哲学家俞吾金先生提出:“必须放弃寻求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无谓游戏,必须终止逻辑向历史的还原,而把探讨的基点真正地移到逻辑上来。”(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版,第349页)文艺学界也有人强调文学研究的多样灵活与哲学史的概念演变是不一样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是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参见田义勇《历史与逻辑统一:文学史研究的伪命题》,《南京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 (55)王元化:《九十年代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37页。 (56)张志林、陈少明:《反本质主义与知识问题——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扩展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标签:胡风论文; 美学论文; 黑格尔哲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学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规律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哲学家论文; 同一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