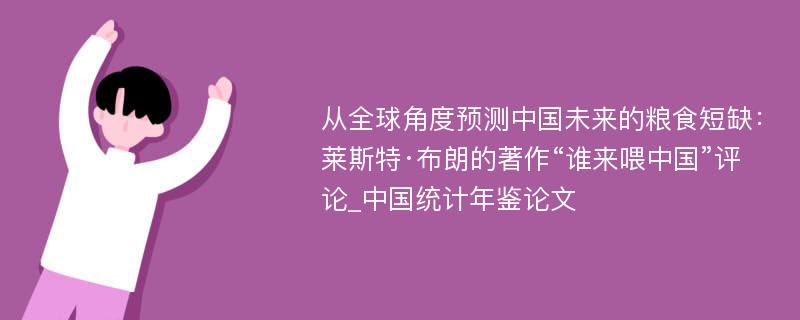
从全球角度看对中国未来粮食短缺的预测——评莱斯特#183;布朗的著作《谁来养活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布朗论文,谁来论文,短缺论文,角度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 言
布朗在书中的观点很明确:中国的经济增长加速了食物消费的增长,尤其是畜产品的增长,而畜产品的增长必须建立在谷物产量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中国谷物产量增长的潜力却很小,事实上还可能会下降。布朗预言,中国大陆会重演日本、台湾和韩国的历史——要依靠进口来满足几乎所有对小麦和粗粮需求的增长。因此,中国在今后会大量进口粮食,进口量将大大地超出其余国家净出口总量。其结果是粮食短缺,粮价全面上涨,从而导致一部分穷困人口的基本粮食需求,特别是低收入粮食进口国的需求将会由于高价而被挤出国际市场。布朗没有用表格系统地列出他所使用的数据和假定前提,所以很难使人一目了然他是如何得出这个惊人的结论的。在下文中我将首先表述一下我对布朗提出的一些数据和观点的理解,然后对有关中国的一些主要数据(如需求、生产、面积和产量等)及有关观点作出评价(包括中国大陆与日本、韩国、台湾的比较,整个国际市场谷物供需平衡情况的预测,其它国家可能的进口需求及中国粮食进口已经开始快速增长的观点)。
在评价布朗的观点及他对中国和整个世界2030年情况的预测时,需要用一些数字作为依据。由于没有看到过其它有关2030年的情况预测,在本文中我就使用了自己计算出的数字,这些数字是建立在合理的假设前提和现有的关于2010年及2010年后情况研究的基础上的。在文章中我还经常使用归谬法说明布朗的一些观点不能自圆其说,比如他对中国及整个世界粮食消费的预测。
二、布朗关于2030年的数据
布朗认为,中国的谷物产量到2030年将减少20%,即从1990年的3.4亿吨减少到2030年的2.72亿吨〔1〕。接着, 他将预测的产量与两个假定的2030 年的需求增长量进行了对比(他给出的1990 年需求量为3.46亿吨):一个假定是2030年总的年人均消费量仍维持1990年的290公斤(这意味着预测人口为16.5亿),则需求量为4.79亿吨;另一个似乎更合理的假定是2030年人均消费量还会增加,为人均400 公斤(这意味着人口将是16亿)〔2〕。这样计算出的2030年的净进口量分别为2.07亿吨和3.69亿吨。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将像日本、韩国、台湾一样走上粮食进口快速增长的道路,因为中国大陆正在步入收入快速增长、消费结构更多地转向畜产品的阶段,而这一切发生在土地资源极为稀缺,水资源更为稀缺的情况下。他认为,如果按他所称为的“现实检查标准”判断,这些关于短缺的预测将会是合情合理的。所谓“现实检查标准”即“如果中国大陆也像日本、韩国、台湾现在那样依赖进口的话,2030年中国大陆将进口多少粮食?”布朗由此得出结论,按照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计算,2030年中国大陆的净进口量将分别达到2.8,3.63和3.33亿吨。〔3〕
三、评 价
(一)需求
布朗的第一个假定即人均谷物消费保持290 公斤只是作为对照提出的, 第二个假定400 公斤才是更切实的, 切实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人均400公斤谷物是否能满足畜产品生产增长的需要, 而畜产品的生产必须满足两倍于现有水平的需求。辛普森(Simpson,1994)等预测, 中国每年大约有0.75亿吨谷物用于畜产品生产(其中包括相当于0.13亿吨以脱粒当量计的整颗粒米和碎米),相当于人均66公斤。这样,人均还有224公斤用于食物和其它。假定后者224公斤是不变的(基本食物的减少与用于啤酒生产和水产养殖的粮食的增加相抵消),则用于畜产品生产的谷物要从人均66公斤增加到176公斤(增加165%)才能达到布朗所说的2030年的400公斤。如果再考虑到畜产品生产力还会有显著提高,这些粮食足以满足两倍于目前畜产品生产水平(人均26公斤肉,5 公斤奶和6公斤蛋)的要求〔4〕。因此,布朗预测的人均400 公斤的消费量看起来足以满足饲料增长的要求,使畜产品消费量在将来能够翻一番〔5〕。在下文中我将用到这个数字并用它来乘以联合国预测的人口数得到2030年食物消费的总数为6.14亿吨。
(二)生产
布朗预言谷物生产要下降的主要理由有两个:①耕地面积(据最新的估计,1993年为0.951 亿公顷)及谷物种植面积(包括复种面积——据最新的估计,1993年是0.889亿公顷)都将或其中之一将大量减少; ②单位产量已经很高了,因此在单产上要继续提高的余地很小。
土地。在耕地的数据方面有许多问题。一方面,《中国统计年鉴》中有这么一句警告:“本表实有耕地面积数字偏小,有待进一步核查。”布朗并没有提醒读者,他的论证可能会因为这个极其关键的因素而无法严密可靠。另一方面,他过分夸大了土地的流失,并且认为谷物种植面积每年减少1.26百万公顷。在他看来,这就等同于耕地的流失,因为他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土地向非农业用途的转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关于1983—1985年和1991—1993年的三年平均土地面积的数据(单位是百万公顷,1993年是《中国统计年鉴》(1994)数据的最后一年),很显然可以看出他是在夸大其词。
1983—1985年 1991—1993年 年变化率(%)
耕地面积 97.7 95.4 -0.3
播种总面积
143.9 148.8 0.6
粮食播种面积
(谷物、薯类、大豆) 111.9 111.1 -0.1
其中谷物占①90.6 90.3
①中国资料中的小麦、大米、玉米、高梁和小米的播种面积,加上粮农组织对杂粮的估计数(包括大麦、黑麦、燕麦、荞麦和黑小麦)。
因此,实际上播种总面积是增长了,而谷物播种面积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其它作物在播种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增加了,这本身是一种良好的发展趋势。诚然,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1983—1993年间耕地面积累积起来下降了7.5百万公顷,但很显然, 这仅是指流失到非农业用途的土地总量,而没有考虑同期新开垦的土地。如将新垦土地考虑在内,同时期耕地面积只下降了2.3百万公顷。
谷物面积减少了多少使得布朗有了“2030年谷物产量下降20%”这个论点呢?他没有给出这个数字,但我们可以间接地从他的估测中找到——他认为谷物人均面积在1990年是0.08公顷,到2030年会萎缩至0.03公顷,也就是总面积从0.908亿公顷降到0.48亿公顷。 这个递减的速度是每年1.5%,这几乎与他关于1990—1994年间年递减速度是1.4%的说法吻合,而且“……只要经济快速增长继续下去,这个递减速度就将保持下去”。他没有说明他的假设条件——如果有的话——关于耕地总面积和所有作物的播种总面积变化的前提,但是他确实提到了复种指数(播种面积与耕地面积的比率)将比现在的1.55的水平要低。
不过,在没有搞清楚他的土地总面积数字是怎么回事之前,我不好对布朗的关于谷物种植面积递减的预言评论什么。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对耕地面积估计的不足有多么严重。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个问题,而现在我注意到,在布朗对谷物种植面积的预测中隐含着一层意思,那就是谷物种植面积在播种总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将明显下降,可能要从1990年60%下降到2030年的40%。这意味着大量的土地将向其它作物转产。这与布朗谷物严重稀缺、实际价格上涨的说法显然自相矛盾。单就这一点而言,布朗贸然预言谷物生产下降就已站不住脚了。他曾说,“在现实世界中,谷物的价格会上涨,一方面刺激生产和出口的扩大,另一方面使消费和进口减少,直至达到一个新的平衡”。好像就全球而言,他承认这一点。但是他没有继续讨论下去,让读者留下这么一个印象:好像这种过程不适用于中国,尤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不会对涨价作出反应以及作为决策者的政府根本就不存在一样。
单产。我不大清楚布朗在估计未来单产时使用了哪些前提,但考虑到中国单产已经很高,总的来说,他的口气是增长的余地很有限。但是,根据他所用的土地与产量数字,我们可以推出,在他的预测中,平均单产将从1990年的每公顷3.7吨提高到2030年的每公顷5.7吨〔6〕。 这是一个略偏低的数字,但总的来说还在现实许可的范围以内〔7〕。 因此,它可以作为后面对生产和贸易检验的依据。
关于低估的土地面积的解释。前面已提到过,《中国统计年鉴》承认它的耕地面积数据是不完整的。一份最近中国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出版物似乎证实了好多其它作者[如科鲁克(Crook),1992;孙颔(Sun Han),1994]的观点,中国的耕地面积在1989年是1.25亿公顷,而《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是0.96亿公顷。同时,中国县一级的资料显示,1989年播种总面积是1.92亿公顷(《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是1.47亿公顷),其中水稻、小麦和玉米的种植面积是1.07亿公顷(《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是0.83亿公顷),这里还应再加上700 万公顷其它粗粮的种植面积。如果这些数据是接近实际的,那么,或者这三种作物的平均单产低于或者生产量高于《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后一种可能往往受到一些作者的赞同〔如约翰逊(Johnson),1994〕,而且有农户调查的数据为佐证。〔8〕
如果实际情况真如这些新的资料所说的那样,那么,将来谷物生产的前景就会与布朗的预言很不相同了,而是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对这件事我们可以这么来考虑:假设①《中国统计年鉴》对1983—1993年所统计的每年30万公顷的耕地净递减速度〔9〕一直持续到2030年, 耕地总面积从1.25亿公顷减到1.13亿公顷;②到2030年复种指数略下降到1.5。这样,2030年播种总面积将会是1.7亿公顷。根据新的资料,其中谷物的播种面积在1989年是60%或者1.14亿公顷。如果2030年谷物种植面积是1.0亿公顷〔10〕,单产是布朗所预计的每公顷5.7吨,那么总产量将会是5.7亿吨。这样,2030年就会出现0.44亿吨的净进口需求, 这就与其它研究对2020年所预测的数字〔11〕相差无几了。在下面部分里,我在国际供求平衡中分析中国2030年的进口需求时就将采用0.5 亿吨这个数字。
(三)和日本、韩国、台湾的类比
布朗是基于以下两个共同点作这些类比的:土地(人均耕地或谷物播种面积)的稀缺和工业化带来的收入快速增长。工业化带来的收入快速增长可能导致耕地转作非农业用途、谷物播种土地转作种植其它作物以及复种指数降低。然而,我至少有四条理由可以说明中国大陆与以上三个国家(地区)是不同的,可以推翻布朗的这些类比:
(1)中国是一个大国, 它在国际市场上的行为会影响国际市场价格。因此,任何大量进口的趋势都会对生产和消费造成影响,进而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上升,而价格的上升最终又会使大量进口的趋势得到控制。
(2)预计中国大陆在2030年仍会有40%以上的农村人口(1990 年为74%)。这个比例是这三个国家(地区)的两倍。这个差别使得农业在2030年中国大陆的国民经济中占有比这三个国家(地区)重要得多的地位。
(3)在这三个国家(地区)刚开始大量增加小麦和粗粮的进口以满足粮食消费的增长时(韩国和台湾是在60年代后期,日本则更早一些),大米在粮食结构中占绝对的比重。60年代早期,大米在这三个国家(地区)的谷物产量中分别占65%、95%和76%。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目前的粮食结构分散得多,大米在谷物产量中只占37%。这以后,这三个国家(地区)人均大米消费量锐减(台湾减少了55%,日本42%,但韩国并没有减少):而与此同时,小麦的消费量和用作饲料的粗粮进口量一样飞速上升。
(4)在布朗的假设中,土地稀缺的类比显得不那么有力。根据新的中国土地数据,中国大陆的人均耕地面积是0.11公顷, 而其它三国(地区)在60年代中期是0.06—0.08公顷。
如果把日本、韩国、台湾原先的情况(农村地区的快速萎缩,人均土地占有量很低,农业经济中小麦和粗粮的比重有限)综合起来看,他们要靠进口来满足小麦和粗粮的消费需求以及用于谷物生产的土地减少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日本和台湾谷物种植面积的减少部分地是随着大米消费的减少由政策因素导致的。布朗却把谷物种植面积减少解释为耕地转作非农业用途,而实际上台湾和韩国的耕地总面积并没有减少。
当今的中国大陆并没有面临与这三国(地区)同样的情况,或者说并没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中国大陆的农业生态条件、种植小麦和粗粮的传统(包括消费自产粮食)以及农村人口的大量存在(其中一部分人口将继续生产这些粮食用来自己消费)〔12〕都能说明一点:在中国大陆,这些产品的供给对需求增长作出的反应将会是积极的,而且反应的能力高于其它三国(地区)。若不然,我们在这些小麦和粗粮生产地区看到的将会是越来越贫困的人口,而不是布朗所说的收入快速增长、人均粮食消费快速增长。因此,我的结论是:布朗关于中国大陆谷物生产前景的讨论是建立在一个对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验过于夸张的不恰当的类比之上的。
(四)未来国际谷物市场供求平衡的演化
布朗不仅仅是对中国,而且是对整个世界谷物生产增长的潜力十分悲观。他的预测数字显示,世界谷物产量将从1990年的17.8亿吨增长到2030年的21.49亿吨。就是说,在这40年中每年只以0.5%的速度增长,远远低于世界人口每年1.2%的增长率。 他虽没有说谁会成为人均消费量锐减的受害者,但言外之意是贫穷国家。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除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而事实上,这些国家的人均消费量一直在增长,从1961—1963年的177公斤增加到1989—1991年的214公斤,而生产量则在1990年前的30年中以每年2.8%的速度增长。 布朗关于世界谷物生产的鲁莽的预测与这些趋势相反,正如下面还要论述的,这足以证明他的预测的根据是十分不足的。
根据布朗最悲观的假设(即中国的人均消费量停留在290公斤), 中国在2030年的消费量仍将是4.79亿吨。从他所预测的整个世界的生产量中减去4.79亿吨,*9渌墓抑皇O*16.7亿吨(21.49减去4.79)。这个剩下的数量将如何在发达国家(1989—1991年的消费量为7.8 亿吨)和其余发展中国家(1989—1991年的消费量为6.2亿吨,即人均214公斤)分配呢?尽管发达国家的人口在1990—2030年间预计会增加15%,但我们仍假定发达国家的总消费量不变〔13〕,这样,2030年发展中国家(除中国以外)只能分得8.9亿吨(16.7减7.8)。但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在2030年将达到57亿,这就意味着,它们的人均消费量将从214 公斤降到156公斤。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将不得不推测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土耳其、拉丁美洲等)的谷物生产趋势将出现灾难性的倒退,平均年增长率降到只有0.35%〔14〕。然而实际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这些国家在1990年前的30年中谷物生产出现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年平均增长率2.8%。即使是在过去的5年中(1990—1995年),它们的谷物生产年增长率也达到了2.3%。
因此我认为,布朗对未来的天谕般的预见是建立在这些不现实的假设条件之上的,这次的预见并不比他早先曾作过的关于灾难到来的预言高明多少;他在1974年粮价高峰时曾预言粮食的实际价格将持续上涨〔15〕,而没过多久,粮价却再度出现了长期下跌的趋势[布朗和埃克霍姆(Eckholm),1974];还有一次他曾作过美国、 法国和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在70年代末将会停止的预言(布朗,1981)〔16〕。
布朗对那些认为食物生产方面取得进步,即使是缓慢而不平衡的进步的观点都持有偏激的态度,而且他总是曲解别人的意思。他说过这么一番话:“许多人认为海洋和土地上的食物生产将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不确定的持续增长,在这些人中有一些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里负责世界粮食供求预测的人。他们所作的这种简单的归纳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最后得出了一个‘没问题’的预测。这种预测对整个世界产生了误导,使人们产生一种自满自得的感觉。”他的理解实在太偏离事实了。世界银行的调查中只包括谷物,并没有渔业,而且预测的结果并不是谷物生产将继过去30年的增长势头而继续增长(1961—1990年之间年增长率为2.6%),而是预言,1990年到2010 年年增长率将大幅度下降到1.3%。粮农组织的研究(亚历山德拉托斯,1995)倒确实包括了渔业(有一整章是关于渔业部分的),指出海洋捕捞业的捕捞量只会出现十分有限的增长,尽管水产养殖的增长余地可能会大一些;同时粮农组织也和世界银行一样,预测在1988—1990年至2010年间世界谷物生产年增长率将剧减至1.6%。 这两个研究结果之间的比较及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研究结果,都刊登在《伊斯兰》(Islam,1995)上。
(五)关于中国已经走上粮食进口快速增长的道路的说法
中国从1991/92年度(7月/6月)和1992/93 年度的净出口国(分别是700吨和500吨)一变成为1993/94年度净进口量为0.14 亿吨的净进口国,据估计1994/95年度的净进口量是0.14—0.15亿吨。 布朗把这当作标志着中国由净出口国转为净进口国的转折点,并认为将由此导致他所预言的2030年粮食危机的爆发。然而,中国作为每年净进口0.1—0.15亿吨粮食的净进口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在中国实行改革后到1991/92年度变为一个净进口国的这段时间里,中国每三年中都会出现一次这个数量范围内的净进口量。
(六)关于其它国家的进口需求十分巨大的观点
布朗是这么认为的,而且他还对中国以外的一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净进口作了预测〔17〕,认为这些国家的净进口量将从1990年的0.32亿吨上升到2030年的1.9亿吨。他放弃了他在1994 年出版的一本书(布朗,1994)中所作的单是非洲到2030年就需要2.5 亿吨净进口的论点〔参见亚历山德拉托斯和德·哈恩(de Haen),1995〕。但实际情况是,布朗所说的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在1989—1991年间只有人均17公斤的净进口,在1979—1981年间是19公斤,而在1961—1963年间则是12公斤。
2030年这些国家的人口总数将达到33亿,而布朗的预测意味着他们的人均进口量将会达到58公斤。考虑到这些国家过去的情况以及它们已向人们证明过的近乎100%的自给能力, 再加上印度(其人口占这个国家群体总人口的48%)不大可能将其消费习惯转向畜产品,布朗所预测的这么快的净进口增长就显得令人难以置信了。即使进口量增长到人均30公斤,净进口量也只有1亿吨。在1989—1991年间, 其余的发展中国家(所有发展中国家除去中国,除去布朗所说的大国)的人均进口量从1979—1981年的31公斤上升到43公斤,在2030年即使它们的人均净进口量增至70公斤,总进口量也只会达到1.7亿吨。 把这三部分的净进口量加起来,即中国0.5亿吨,布朗所说的较大的发展中国家1亿吨,其余发展中国家1.7亿吨,我们可以得出2030 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净进口需求是3.2亿吨。
这个进口需求相对于发达国家在2030年能生产出的出口剩余是不是太大了呢?我们注意到,在1989—1991年间,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净出口为1.3亿吨,其中0.37 亿吨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作为净进口吸收了,而后者在1994—1995年间已把净进口减少到了0.025 亿吨, 而且将来它们还有可能变为净出口国(约翰逊, 1993)〔18〕。如果它们在2030年的净出口为0.3亿吨,那么,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需要把净出口从1979—1981 年间的1.3 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2.9亿吨才能满足上文所述的发展中国家的净进口需求。 考虑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国内需求增长十分缓慢(假设年增长率不超过0.7%,1990年至2030年人口年增长预计为0.4%),要使出口剩余达到2.9亿吨,则要求1990—2030年间的年生产增长率达到1.1%。按照常识性的推测,这是一个无需对生产系统作多大改进就可以达到的增长率。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是对这个问题做过长期预测的机构和个人之一。它的预测研究表明,经合组织国家在1990—2020年间的粮食生产年增长率为0.9%〔罗斯格兰特(Rosegrant)等,1995〕,但这个增长率所反映的仅仅是需求上的限制,因为这份研究预计,2020年发展中国家的净进口只有1.83亿吨,这个数字比起我在这里用的过分夸大的3.2 亿吨是有极大的差距的。最近的一份关于欧盟的研究认为,在合适的政策条件下(没有休耕地,也没有支持价格),欧共体(按9国口径)在1992 —2020年间的小麦生产年增长率将为2.0%,粗粮1.0%〔弗尔默(Folmer)等,1995〕。因此,总的来说,1.1 %的年增长率并不是一个超乎现实的数字。
四、结论
中国很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粮食净进口国。但是,由于政府政策以及生产者、消费者——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其它国家的——都会对所发生的粮食稀缺及价格上升作出反应,最终达到的供求平衡点上的进口量很可能只有布朗所预测的几分之一。只有出现本文作者所说的世界其它国家都在谷物生产增长上发生灾难性的下降,以及出现与布朗所认为的由于短缺而食物消费下降相反的趋势,中国不断增长的进口需求才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在上文对主要国家集团的生产—消费关系的分析中得到证明。和过去相比,将来谷物生产的增长率要降低是毋庸争议的了。这种降低是世界粮食前景中好与坏两个方面发展的结果。好的方面是,世界人口增长率降低以及越来越多的人口已经或将要在消费水平上得到提高,这对需求增长速度的降低都有帮助;坏的方面是,那些几乎连食物需求都无法满足的国家(如撒哈拉周边非洲国家和南亚地区等)的收入和农业生产并没有以与其它国家一样的速度增长,不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刺激它们的食物需求并解决食物营养结构问题。这些国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主要依靠自身农业发展来提高收入和食物供给的国家的情况,必须引起那些关心世界粮食问题的人们的注意。至于布朗关于中国和整个世界粮食市场的过于夸张的断言是否能引起大家对世界粮食问题的关注,这就留给读者去决定了。
(参考文献:略)
(中国农业大学王晓冬译)
注释:
〔1〕布朗所用的粮食(grain)概念是指小麦、粗粮和大米,而中国的概念包括谷物(cereals)(但其中包含的不是大米而是稻谷)、 大豆和薯类,薯类按5:1折算成粮食。因此, 他的数字就与中国生产统计资料中的数字不一样了。这样,1990年中国资料中谷物产量是4.46亿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4)表11—16)。 在这篇文章中采用谷物(cereals)来指布朗所说的粮食(grains)。
〔2〕联合国关于中国人口最新的预测(1994, 中值预测方案)是1990年11.55亿、1995年12.21亿、2030年15.54 亿(注意这个人口数包括台湾在内。1990年为2000万)。在下文中我将15.35 亿这个预测数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数。
〔3〕他的这些数字是这么得到的:把1990年的日本净进口数0.28亿吨乘以10——即1990年中国大陆与日本人口的比率,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依此类推。然而,按照他的“现实检查标准”,应该乘以中国大陆2030年人口与日本1990年人口的比率——因为这个标准意味着中国大陆2030年的净人均进口量必须与日本1990年(或韩国或台湾)的人均净进口量相等(分别是230公斤、230公斤和305公斤)。这样计算的结果,在2030年中国大陆人口15.35亿这个前提下,中国大陆2030 年的净进口量将在3.5—4.7亿吨之间。
〔4〕辛普森(Simpson)及其他资料预测:1990—2025年之间的畜产品产量的增加(肉220%、奶525%、蛋145 %)只需用作饲料的谷物增产170%即可达到。
〔5〕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IFPRI)对中国人均谷物消费量的预测是:2020年上升到360公斤[罗斯格兰特(Rosegrant)等,1995]。日本海外经济合作基金会(OECF)的一项最新研究预测,2010年中国人均谷物消费量是328公斤的脱粒大米、小麦和玉米(OECF,1995)。
〔6〕这些数是这么估计出来的:1990年:产量3.4亿吨,播种面积0.908亿公顷;2030年;产量2.72亿吨,播种面积0.48亿公顷。 这些单产的估计数字中大米是指脱粒大米。如果大米按未脱粒统计,1990年的平均谷物单产将高出18%。
〔7〕我的这个结论是建立在其它一些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的。比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米切尔(Mitcheli)和英格科(Ingco), 1993)]曾预测2010年的单产为5.7吨/公顷;辛普森等曾预测2025年谷物单产是5.2吨/公顷;罗斯格兰特等(1995年与罗斯格兰特,IFPR1 的个人交流)预测2020年平均谷物单产是5.2吨/公顷;OECF(1995)预测2010年小麦、大米和玉米单产是5.0吨/公顷(所有单产数据中的大米是指脱粒大米)。
〔8〕这些估计都是根据《1993 年中国农户调查年鉴》所报道的农村人口人均谷物产量而作出的,而且可以看出1992年的谷物总产量可能会达到5.3亿吨;而《中国统计年鉴》中报道的数字却是4.43 亿吨(根据与芝加哥大学的D.Gale Johnson个人交流资料)。
〔9〕郜若素(Ross Garnaut)和马国南(Ma)(1992)预测1990—2000年之间耕地递减速度为每年500万亩(0.33百万公顷)。
〔10〕OECF的研究预测小麦、大米和玉米的播种面积只有很小的减少,1993—2010年之间减少3%(OECF,1995)。
〔11〕罗斯格兰特等(1995)预测2020年为0.27亿吨,黄等(1995)预测2020年的数字为0.4亿吨,OECF的研究预测 2010年的不足数为0.65吨(OECF,1995)。
〔12〕中国50%的农村人口分布在小麦和玉米的主产省,其中大米(脱粒)在三种谷物总产量中的比例由0%(山西)到43 %(云南)不等。
〔13〕这个数字比看上去要更符合实际,因为前苏联改革的实施使得人均食物消费量由于畜产品生产缩减而下降,饲料用的谷物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总的食物损耗降低了。
〔14〕计算过程是这样的:这些发展中国家1989—1991年谷物生产量是5.4亿吨。它们的进口在将来要增加。 在过于宽泛的假定下(根据布朗的论文),到2030年净进口会达到2.7亿吨(参见下文)。这样, 产量必须增至6.2亿吨,才能与前述的8.9亿吨消费量相匹配。这就意味着1990—2030年间年增长0.35%。
〔15〕这是建立在需求增长“……如我预测的那样”的条件下。事实上,世界消费量在1974—1990年间价格下降的条件下增长了2.3%。
〔16〕这里我是参考D.盖尔·约翰逊的说法。实际上,三年平均的每公顷产量(水稻,未脱粒)美国从1976—1978年的3.8吨上升到 1992—1994年的5.1吨,法国从4.0吨上升到6.5吨,而中国从2.6吨上升到4.5吨。
〔17〕指印度、孟加拉、印度尼西亚、伊朗、巴基斯坦、埃及、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尼日利亚、巴西、墨西哥。这些国家占中国以外的发展中国家人口的61%。
〔18〕上文提到过的世界银行的研究(米切尔和英格科,1993)预测,这个地区2010年的净出口为0.15亿吨。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的研究的数字也与之相同,但指的是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