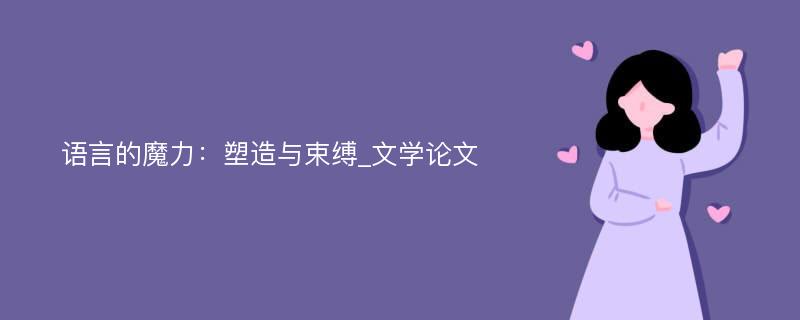
语言的魔力:塑造与囚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魔力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今,一部文学巨著的诞生可能被形容为意味深长的语言事件,一场汹涌的文学革命可能被描述为社会话语内部的语言地震。愈来愈多的人看来,文学是一种特殊组织的话语系统;文学的意义将参照一个社会的语言形势图给予鉴定。这并不是贬抑文学,埋没文学的光辉。相反,这意味着一个崭新的立场和文学的再认识,二十世纪的“语言转向”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后果:语言跃居为诸多人文学科的主角,成了思想展开的发轫之点。人们已经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能够悬空地存留于语言空间之外。事实上,语言是组成一个社会人文环境的基本粒子。作为一种表意和交流的符号系统,语言容纳了人类精神的所有可能,同时也划出了一道不可跨越的精神地平线。处于社会话语的光谱之中,文学话语向来以活跃、变革和富于生气著称;于是,文学话语与诸多话语系统之间的角逐、抗衡、冲突、融汇形成了它参与现实的独特形式。
这样,人们有必要事先引入一个更大的语言背景予以考察。这将使人们看到,文学是在什么场所之中展开,同时又是从什么场所之中突围而出。
一
每一个体成为社会成员的必要条件之一是,纳入这一社会的语言体系。语言体系是凝聚一个社会的基本网络。对于个体而言,语言是一个神秘的符号之网。语言可以潜入最为隐密的社会角落,辗转于人们的口吻之间;同时,语言又可能不尽地延伸,无限扩展,成为个体所不可摇撼的巨大结构。语言并非类似于山川河流的自然物,语言是一种人工制品。但是,人们不可能像对待另一些人工制品——诸如斧头、汽车乃至航天飞机——一样对待语言。语言的神秘性质时常迷惑了人们,即使在当今的理性社会,种种分解语言的手段远未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不仅仅是语言学家在考虑这样的问题:语言是什么?
这个问题的历史已经十分悠久。语言起源的真相埋藏在众说纷纭之后,难以核实。也许,神秘之物总是和不可思议的魔力联系在一起的。对于原始的初民说来,语言如同一个魔具。它更像是一个法力无边的天授之物。那些古老的传说之中,语言的出现时常被当作一个异乎寻常的事件。《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当时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语言和文字包含了惊天动地的不凡威力。许多宗教教义都曾经将语言看作创世的工具。《旧约·创世纪》告诉人们,上帝所使用的语词具有奇妙的神力。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光就出现了;上帝说,水里要有生物,空中要有飞鸟,地上要生出活物来,于是,这个世界随即万物纷呈,生机勃勃。在这里,语词显出了至高的权力——它是实在世界之母。另一些时候,语言甚至出现了僭越上帝的威胁——这就是《圣经》里巴比伦塔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情节意味深长:挪亚的子孙企图建起一座通天塔,他们操持同一种语言,齐心协力,彼此呼应;他们所体现出的力量让上帝感到了不安,于是,耶和华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之无法互相配合。巴比伦塔的故事无宁说是一个象征:这个故事从反面暗示了语言对于人类的左右。
“语言的魔力”不是一个夸张的形容,这无宁说证明了语言以何种独异的形式参与人类现实。所谓“参与”,也就是显明语言怎样介入现实的各个层面,制定社会成员的精神空间,延续特定的意识形态,维护或者破坏既有的价值体系,调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位置,给以人类感觉和经验的模式,提供认识实在的中介,如此等等。例如,语言对于实在的命名亦即是人类记忆实在的提示:语法规则规范了人类意识的基本框架,“神”、“天堂”、“负数”、“形而上学”这些概念致使种种超验的内容获得了栖身的躯壳。“语言的魔力”意味着语言对于人类居高临下的统治,这种统治往往达到这样的程度:人类不再将语言视为意识与实在之间的中介——人类将语言当作实在本身。
卡西尔在《语词的魔力》一文之中曾经发现:诸多神话之中,语词无不处于至高的位置——“太初有词”。在原始人那里,语词和指称物之间通常具有同一性。由于语词的崇拜,“凡被名称所固定的东西,不但是实在的,而且就是实在。”〔1 〕列维·布留尔的《原始思维》列举了众多例子证实,原始人通常将语言与实在视为一体。对于原始人说来,“没有哪种知觉不包含在神秘的复合中,没有哪个现象只是现象,没有哪个符号只是符号;那么,词又怎么能够简单的是词呢?”符号体现出种种神秘的力量,“神秘力量不仅为专有名词所固有,而且也为其他一切名词所固有。”在原始人的心目中,“言语中有魔力的影响,因此,对待言语必须小心谨慎。”〔2〕事实上, 敬畏语言已经在许多社会成为一个秘密传统。人们可以从“敬惜字纸”的风俗之中发现这个传统,字纸上的文字曾经被看作孔子的眼睛;人们还可以从某些作家的想象资源之中发现这个传统——譬如,博尔赫斯在《皇宫的寓言》这篇小说里讲述了一个奇妙的故事:皇帝带领一个诗人游览了梦幻一般的皇宫,诗人对于诸多金碧辉煌的景象无动于衷。他在游览结束的时候吟诵了一篇短短的诗作,皇宫即刻消失了,一切如同被诗的最后一个音节抹掉了一样。当然,诗人终于被皇帝杀害了。可是,诗人说出的那个“包含着整个宇宙的字”却是人类的一个永恒的诱惑。人们的想象深处隐藏着一个秘密的期望:说不定什么时候,语词的魔力可能再造一个栩栩如生的宇宙。
也许,理性社会已经很难察觉到语言的魔力。这种魔力正在和神话一道成为遗迹。如今,人们对于自身的智力有了足够的自信人们自认为可以任意地操纵、驱遣语词了。经历了无数的聚谈、吹嘘、威胁、恐吓、欺骗,经历了种种撕毁盟约、违背合同、出尔反尔,人们已经难以继续慎重地对待语言。语言不再意味着兑现,人们不再顾虑它即刻会转化为实在。语言似乎变得轻贱了。只有那些特殊的话语类型——例如誓言咒语、祈祷、谶言——还提示着语言曾经有过的赫然威仪。誓言意味着一种语言的承诺,宣誓者违背这种承诺将遭受可怕的报应;谶言提前预告了将要来临的事件,所谓“立言于前,有征于后”;祈祷和咒语均表达了言说者的强烈意愿,这种意愿可能通过反复的言说而成为事实。不难看出,这些话语类型仍旧建立在一个古老的基础上:语言可以转化为实在,或者语言就是实在。或许人们还能看到某些人对于姓名的刻意推敲,看到某些字眼谐音所引致的迷信,看到某些数字的禁忌——除此之外,语言的魔力正在全面衰退。
然而,不论是社会管理、文化承传还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往,语言的轻贱都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为了驱散这样的不安,一种维持语言魔力的努力出现了。在我看来,这种努力很可能是造就语言伦理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不难发现,语言伦理学很大程度地围绕着语言与实践的关系——亦即“言”与“行”——展开。人们可以从古代思想家的言辞之中查到大量“言”、“行”关系的论述:
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日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论语·学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
——《论语·里仁》
……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
——《论语·颜渊》
……曰:“言必信,行必果,……”
——《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惮也,言足信也。……”
——《礼记·表记》
“儒有居处其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
——《礼记·儒行》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无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无道,何以为信?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春秋谷梁传·闵公二十二年》
显而易见,在古人那里,一言九鼎成为语言伦理学所推崇的楷模,而轻诺寡信则是难以容忍的恶劣品质。这是担忧语言魔力的衰退而采用的道德弥补措施。尽管语言学的常识已经显明,语言与实在、词与物之间的分裂不可避免,但是,人们还是企图从另一个方面信赖语言——人们不想让话语主体从夸夸其谈背后隐身而去,留下一堆语辞组成的空头支票;换言之,人们仍然想让话语主体在他所描述的实在之中充任预定的角色。至少在语言与话语主体的关系上面,语言必须保持着折算为实在的可靠信誉。在“言”与“行”的关系上面体现出何种道德水平,这是一个社会成员品行鉴定的重要尺度。在这个意义上,人格的完善包含了对于语言魔力的某种认可。这时,语言伦理学甚至介入了一个社会最为显赫的区域:政治。对于参加选举的公众说来,言而无信的人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
确实,语言的魔力早已在政治领域产生了种种不可低估的作用。这是语言参与现实的又一个具体例证。许多时候,语言的魔力体现为政治机构对于社会成员的凝聚、号召、激励、规约,仅仅语言就能够使万众一心,情绪昂扬。卡西尔发现,政治理论之中的神话思维从未彻底消失;某些关键的时刻,神话思维可能轻而易举地淹没理性和逻辑思维。这样的时候,语言的魔力将在神话的气氛之中得到了放大。通常,人们的语言包含了描述功能和情感功能;“可是,在政治神话所提出的语言中,这种平衡完全被打破了。整个强调的重点倒向情感方面,描述性和逻辑性的语词被转化为魔语。新的名词被杜撰出来,旧的名词的意义也大为改观。”〔3〕人们可以察觉,政治家通常善于使用大字眼。 这些大字眼不是一个简单的命名,一个涵义明晰的概念;相反,许多大字眼可能难于定义,内涵与外延含混模糊。但是、当语言的魔力产生作用的时候,含混与模糊恰恰幻化成为一种诱惑人们的神话图景。人们可以在口号和标语之中看到语言魔力的极致。口号和标语常常以“国家”、“阶级”、“战争”、“和平”、以及种种“主义”作为主题词。语言的魔力消弭了概念抽象所产生的隔阂;人们无宁说是用肌肉、神经、骨骼、血液和巨大的激情承受这些大字眼。呼喊口号的时候,理性思辩已被抛弃;种种斤斤计较的分析徒然令人耻笑。语言魔力的蛊惑将抑制乃至取消种种个性。口号能够迅速地制造同仇敌忾的氛围,或者将所有人的兴奋调整到相同的节奏之上。不论每一个人的来历多么不同,一个响亮的口号立即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站立的语言横切面。作为一种话语轴心,一种召唤,一种振奋人心的社会主题概括,一种集合人心的标志,口号典型地展现了语言的魔力在政治领域可能产生多大的奇迹。
这个意义上,语言的魔力必将成为众多方面共同觊觎的对象。角逐展开之后,政治机构通常将控制话语生产权作为一个重要策略。这是语言魔力的因势利导所依据的制高点。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话语的生产也就是实在的生产。因此,无论是巫师嘴里说出的神谕、皇帝的金口玉言还是现代社会权威机构的标准言论和规范口径,权力严密地监督着话语生产。显而易见,这是政治机构对于语言魔力的掌握,也是政治机构对于语言魔力的防范。
二
现在,我必须将视域转移到同一个问题的背面——我有理由指出,汉语文化同时还存在着否弃语言崇拜的强烈倾向。人们意识到语言在主体和客体之间所处的位置;语言的过度膨胀势必阻断主体与客体的依存关系,语言将从中介物上升为主角。对于一些思想家说来,这显然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本末倒置。也许,不同学派的思想家持有不同的动机和立场,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破除语言的魔力,削弱语言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遏制语言崇拜所产生的副作用。
孔子曾经说过:“辞达而已矣。”这句话时常被当作否定语言推敲的一个重要论据。也许,这句话的语气的确表明,孔子对于偏执的语言狂热没有兴趣。虽然孔子也表述过“不学诗,无以言”这样的论点,但是,作为“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倡导,孔子决不愿意语言问题喧宾夺主,从而干扰了教化的基本目标。所以,尽管苏东坡擅自将“辞达”诠释为“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辞达”是“千万人而不一遇”的境界〔4〕,我仍然愿意认为, 这更像是一个作家的借题发挥。事实上,在文学的范围之外,墨子式的“非乐”和韩非子“以文害用”的恐惧得到了更多的呼应。
不难发现,上述观点共同将语言定位为一种工具。这种工具负责主体与主体、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流或者沟通。但是,如果这种工具过分精致以至于夺人耳目,那么,工具就会从交流的手段变为交流的目的。在这里,如何保持主人与工具的主从关系引致一些思想家的高度警觉。老子和庄子的诸多言论均在于提示人们,不该让工具——哪怕是在美学的意义上——僭越和篡权,从而无形地成为交流过程的一个障碍性遮蔽。交流的主体必须尽快穿过语言,毫无阻拦地抵达交流对象。老子的《道德经》谆谆教诲人们:“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辩若讷”;“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庄子对于语言工具有着更为细腻也更为辩证的考虑,人们对于这些名言几乎耳熟能详: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外物》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
——《天道》
轮扁……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者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天道》
汉语文化之中,老子与庄子的言论始终是一种不可抑制的思想势力。众多后继的思想家接过这些言论,使之在不同的层面上绽出了种种智慧之花。老子和庄子对语言的机智观点曾经启迪了佛家和道家。他们洞察到“言语道断”的危险,竭力破除语言对于“道”的干扰乃至干预。为了避免拘执于语言工具而迷失本源,佛家甚至出现了拈花微笑或者当头棒喝这样奇特的布“道”方式。如果说,佛家和道家企图废弃语言而悟道,那么,作家至少知道,语言是他们无法挣脱的镣铐。没有语言符号的文学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并没有使语言崇拜成为汉语文学的首要特征。相反,文学批评史上逐渐形成了“言不尽意”的共识。“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表明了作家面对语言的特殊姿态。作家坚持将主体视为语言之上的一个精神实体,语言只能尾随而不可能穷尽这个精神实体。庄子的“忘荃”、“忘蹄”之说无疑为这样的幻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依据。
不难猜想,“言不尽意”的命题首先来自作家写作所遭遇的普遍阻碍——诸多作家均体会到“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的痛苦。在他们那里,语言仍旧不是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通常,“言”几乎不可能尽善尽美地显现“意”的丰富、独特和微妙。“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这是作家搁笔之后留下的共同浩叹。可以看到,文学批评史上记载了许多类似的表述:
恒患意不称物,言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
——陆机《文赋》
……是以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
——刘勰《文心雕龙》
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展转隔碍,虽写得畅显,已恐不如口舌矣,况能如心之所存乎?
——袁宗道《论文》
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
——叶燮《原诗》
可以看到,这些表述早已在语言之外为主体预订了一个席位。人们没有意识到,主体来自语言的建构,主体即是语言的构造物;撤消了语言,主体将成为一个毫无内容的空洞。人们通常形象地构思,“意”业已事先寄存于灵魂之中,“言”只能是“意”的仆从——“言”的功能就在于追摹、复述或者再现“意”。上述构思将主体视为意义之源,这体现了一种朴素而古老的人本主义。这样的人本主义从未产生怀疑:“意”并不可能由某种先于语言的元素组成,并且在语言符号的辖制之外自由地飞翔。在这个意义上,“言不尽意”无形地产生了抵制语言崇拜的效能。
有趣的是,即使在某些语言崇拜的现象后面,人们仍然能同时发现遏制语言崇拜的努力——我指的是古典诗学之中的“炼字炼句”。古典诗学留下了大量“炼字炼句”的记载。杜甫的“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都成为自述诗人甘苦的名言。不少诗话词话津津乐道于“诗眼”的琢磨和收集“一字师”的佳话。殚精竭虑地推敲字句已经成了古典诗学的一个强大传统。然而,熟知古典诗学的人同时还了解,不少诗人对于“炼字炼句”颇有微词。他们认为,辞句的寻寻觅觅仅仅是一种局部的雕琢,这一类型的诗作小巧玲珑而缺乏宽敞浑厚的风格。诗人的宏大怀抱和出众才智必定不屑于为语言所统治。如果语言崇拜导致痴迷的字斟句酌,那么,人们只能看到一种拘于细部的局促。所以,这样的观点得到了诸多批评家的共同认可:“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5 〕为了协调“炼字炼句”与刻意求工之间的矛盾,这终于导致了古典诗学的一个特殊策略:“极炼如不炼”〔6〕。换一句话说,“炼字炼句”的一个后果就在于, 诗人必须将诗句涂抹得让人看不出锤炼的痕迹为止。这就是苏东坡所谓的“渐老渐熟,乃造平淡”〔7〕。 这种特殊的策略将使诗作在精心制作之后仍然保持一种自然天真的风格。在诸多诗人的心目中,自然天真的美学风格远比“错彩镂金”更为可贵。显然,从“炼字炼句”的推崇到“复归于朴”、“法天贵真”〔8〕,这包含了文学观念的一个迂回认识。 在这样的观念转换之中,人们再度发现了老子和庄子的所提供的思想资源。
谈论汉语文化之中的语言崇拜与破除语言魔力,人们不可能不联想到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这是一场意义深远的辩论。尽管欧阳建曾经写下《言尽意论》宣谕自己的主张,尽管欧阳建通过“名逐物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来反驳“言不尽意”之说,但是,人们无宁说更多地接受了王弼的观点。王弼借助《周易》的阐释设定“言”、“象”、“意”的依次顺序和相互关系。《周易略例·明象》指出: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及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在王弼设定的“言”、“象”、“意”关系图之中,“言”仅仅是阐释“象”的初级工具,“意”是“象”所隐喻的最终目标。虽然这仅仅是王弼对于《周易》的解说,可是,这三者的关系不但指定了语言的位置,而且还规约了语言参与现实的范围。这个关系图之中,语言崇拜已经解除——王弼不过为语言安排了一个叨陪末座的席位。
三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已经得到了语言史、文学史以及哲学史和社会运动吏的共同描述。的确,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转折。白话文运动撼动了社会文化的诸多层面,波及四面八方,如果考虑到语言对于现实的参与和介入,那么,白话文运动包含着一种强大的吁求——强势语言的重新认定表明了社会结构的重大改变;那些行使白话的语言主体已经无法满足于旧有的社会位置,他们正势不可遏地浮出地表。封建社会的终结必将中止陈旧的社会关系结构,既有的文化结构不得不为之改观。这样,白话与文言之争成了一个导火索,这是语言与现实之间深刻的互动关系带来的必然后果。这个意义上,白话文运动远非一个语言学事件。这场运动是一个社会阶层企图走到文化前台的具体象征。当然,这种社会关系的内部震荡不可能赤裸裸地呈现出来;它将经由种种复杂的中介曲折地展示在文化运动之中,并且为这些中介的固有特征所改写。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复杂的局面:那些行使白话的语言主体——那些社会底层人士——并未在白话文运动之中充当显眼的主角,他们仅仅作为一个巨大的背景而存在。事实上,一些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领衔主演。他们以代言人的身份出面发言,激烈辩论;于是,种种社会力量的对比和角逐被很大程度地压缩在文言与白话相互比较的学术衡量之中,诸种社会阶层的相对关系在启蒙主义的形式之下分配就绪,刊物、论文、笔战、演讲、文学作品——这一切无不带有文化运动的烙印。然而,追溯到这一场文化运动的基本社会动力,人们不能不意识到潜伏在社会底层的革命愿望——只不过这种愿望是由一批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最早察觉,并且在他们所兴趣的范围给予大张旗鼓的阐释而已。其实,即使在当时,这批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社会底层的革命愿望所起的作用。陈独秀解释过这样的背景对于知识分子的保护和拥戴:“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要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9〕
文言与白话的争议环绕着文学风起云涌。借用胡适的词汇说,白话是“活的文学”向“死的文学”发出的猛烈攻击。人们可以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文学论争集》和《建设理论集》之中看到,文学是诸多言论指向的核心。尽管如此,几乎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场争议的意义将远远超出文学的范畴。一些人认为白话文“意俗”,“言情涉于淫”,“泄愤而出于毒骂”〔10〕。而且,“且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恺切简明”〔11〕。这不仅是对于一种文学风格乃至一种语言体系的贬抑,这同时也是对行使白话的语言主体作出了基本评价。反之,另一些掊击文言、力倡白话的观点同样显出了深谋远虑的一面。周作人深入地剖析过文言的弊害:“我们反对古文,……实又因为他内中的思想荒谬,于人有害的缘故。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中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12〕而陈独秀发现:“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13〕显而易见,对于文言或者白话两大阵营的主将说来,选择某一种话语体系从来不仅仅是文学问题。
另一方面,即使在文学范畴之内,文学的意义也不是白话倡导者的全部目标。从胡适当时的一批言论之中可以看出,他的兴趣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文学对于汉语所具有的意义。胡适曾经提出一个颇为乐观的设计:将白话文学作为汉语的真正楷模。换一句话说,这意味着让文学掌握话语的生产权。在胡适看来,这样的设计并非悬空拟想,而是当时文化环境里面的可行措施。有人曾经向胡适建议,推行白话文应当先从高等学府做起、胡适并不赞同。他深知教育机构的传统势力盘根错节,一时难以动摇——他宁可选择文学作为突破口:“改革大学这件事不是立刻就可以做到的,也决不是几个人用强硬手段所能规定的。我的意思,以为进行的次序,在于极力提倡白话文学。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14〕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之中,胡适用“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表达这一主题:
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上真正的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
大半个世纪之后,一些人对于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决绝态度表示出相当的怀疑:如此轻率地抛弃文言,这是不是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文化损失?白话文运动之中,汉·语的语义含混和句式多变曾经屡遭贬斥——这甚至导致一批人建议用拼音文字取代汉语。显而易见,这种贬斥的依据尺度是西方语法。时至如今,一些语言学家对于这样的贬斥提出了强烈的异议。他们看来,这种含混和多变恰恰是汉语人文特征的显现;这种人文特征集中了异于西方语言的东方智慧〔15〕。语言的爱好者,诗人也曾经为文言的狼狈境况深感不平。在他们眼里,文言保持着不尽的韵味;拒绝古典文学的白话文学无宁说是自我饥饿和自我贫乏〔16〕。不难想到,这些来自语言学或者诗学的反诘均持之有据。但是,人们没有理由因之遗忘了五四时期的历史语境:至少在当时,语言学和诗学的尺度远远不能遏制隐藏在白话文运动背后的社会动力。成仿吾曾经说过,当时社会所引起的激愤很大程度地导致了白话文学的迅速传播;相对这样的激烈情绪,来自语言学和来自诗学的声音不可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换言之,所有的偏激、失衡和遗憾无一不是当时的历史形势指定的必然。
白话文的历史地位已经由历史事实予以说明。无论如何,人们都无法否认,白话文运动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这场运动是语言参与社会历史改造的一个典型例证。当然,人们已经不再将语言视为神授魔具。不计其数的语法著作拆解了语言的内部结构,种种辞典标出了每一个字与词的涵义,人们可以进入语言内部四处察看,自由地比较和考证,隐含于语言内部的神秘气氛已经打破。人们的心目中,语言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工具。然而,尽管如此,这丝毫没有表明,人们放松了对于语言的利用和控制。人们不相情语言是神赐之物,语言与实在不可等同;可是,人们依然自觉地运用语言魔力所产生的效果,自觉地以语言控制实在,制造实在。这个时候,少数语言学家可能继续关心语言的起源问题,而多数社会机构却注视着话语生产权问题——后者意味着对于语言魔力的具体掌握。无论是三十年代引人注目的“大众文艺”问题、四十年代领袖人物在延安向文学家提出的号召,还是六七十年代“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的论断,八九十年代学术领域大量涌现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汉语之中种种重要的动向均涉及话语生产权。话语生产权的决定范围是,哪一种话语系统将作为话语生产的依据和基础——这实际上也就是决定哪一个社会阶层是话语主体;他们将根据这种话语系统享有何种程度的威望:这种话语系统确认什么样的价值体系;这种话语系统与另一些话语系统的关系如何折射为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如此等等。如果说,“通俗”是三十年代“大众文艺”的重要主题,那么,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无疑强调了相反的一面。从投合大众的喜闻乐见到树立学术话语的特殊权威,这样的转变显然意味着话语生产权力的转移。
话语生产可能隐含了深刻的意义,那么,谁人手执权柄?如前所述,政治权力理所当然地控制了话语生产权——两种权力之间存在着可靠的换算关系。但是,某些时候,话语生产权还可能为另一些权力机构所分割,譬如体现出知识权力的文化机构。在商业社会,经济权力也将染指话语生产权力;这个方面,广告的生产是一个最为合适的例证。目前为止,广告正肆无忌惮地蚕食报刊、杂志、电视屏幕以及种种人们可能接触到的传播媒介。在话语形式的意义上,广告无力与哲学、宗教、史学、文学这些威仪堂堂的传统学科相互抗衡。广告的短小片断更像是可怜地利用人们意识过程所存有的间隙。通常,广告是作为人们阅读或者观看的“边角料”出现的。广告如同一圈花边,一些点缀,它用一些无关紧要的商业消息在电视的节目与节目中间插科打诨,或者在杂志的封三和封底补白。广告无法在大众传播媒介上面充当主角,它只能依赖其他文化品种的夹带与提携。然而,一旦巨额广告费用开始成为广告生产的强大后盾,广告就将与那些传统学科展开一场话语生产权力的争霸战。虽然广告费不能使广告的形象更为深刻,可是,话语权力的掌握导致了广告座次的改变。这时,广告将强制地要求种种传统学科在大众传播媒介上面让位。对于广告说来,再也没有什么精神圣殿不能踏入。电视上的广告可以每隔十五分钟就蛮横地将节目切断一次;刊物上的广告可以把一篇神学论文任意腰斩,而且将剩下的部分随便转到哪一页上去;一份四版的报纸可以拨出一整版归广告独享、这是通常的新闻、特写或者文学作品所无法赢得的待遇。在这里,广告的功能已经不限于购物指南;它还将炫示经济的效力,肯定消费欲望,为商业争取一份美妙的声誉。在广告那里,话语生产权力与货币之间的关系将以数学式的精确显现出来。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人们置身于种种复杂的话语系统之中。政治话语、商业话语乃至学术话语正在从各个方面描述人们的精神蓝图。的确,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语言参与现实的一种主要形式是——语言塑造了人们,同时也囚禁了人们。这难道还不算另一种意义上的语言魔力吗?
四
诸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将目光集中到了语言问题上,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行动。从“新批评”、形式主义到分析哲学、结构主义,语言问题横跨不同的人文学科、成为众望所归的对象。语言与实在、意义的性质、真理概念、言语行为、语词的美学风格、象征与隐喻、语言系统的结构、语言与神话——诸如此类的问题正在各种专业团体之中争论得兴味盎然。然而,尽管具有如此的背景,这样的结论仍然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
“话在说我”的论点无疑包含了结构主义的思想痕迹,人们终于意识到,个人操纵语言仅仅是一种表象;事实上,语言系统的规则章程限定了主体的所有可能。显而易见,这样的发现源于结构主义的深刻启迪。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人们都必须承认,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一系列来自索绪尔的基本设想广泛地进入了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挥斥传统,风靡一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揭示了隐藏于语言符号后面的巨大结构。按照结构主义的观点,一个语词的概念涵义将在这个巨大的结构之中得到确认,横组合、纵组合、差异以及二项对立均在确认的过程参与了种种精密的界定。换一句话说,语言系统的结构已经为所有的语词设定了涵义。这些涵义与语言周围的实在世界无关。“猫”这一字眼的所有意义并不是来自实在世界之中某种四只脚、长尾巴的动物;整个语言系统的复杂结构将为这个字眼指定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这个位置早已配备了应有的确定涵义。这种观点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不少人在索绪尔的激励之下展开了精致的思辩。他们小心翼翼地将语言剥离实在的基座,使之成为独立自主的封闭系统;他们专注地描述了语言系统内部的惯例、运动、交织、紊乱——语言背后庞大的现实和行使语言的主体被毫不犹豫地撇下了。人们很难判断:这是在一种新的语言崇拜之中用语言代替现实,还是巧妙地剥夺了语言参与现实的权利?
如同许多富有启示的学说一样,结构主义同样招致了来自各个方向的诘难。这些诘难之中,巴赫金竭力恢复语言所含有的社会能力。巴赫金首先承认了语言的至关重要;在人文学科之中,人们所能认识的只有由语言组成的文本。但是,巴赫金不愿意像索绪尔那样,仅仅强调语言系统结构的专横统治;巴赫金更乐于发现言语的现实展开所带动的活跃。巴赫金同样考察了语言系统的结构,但是,他更多地从这些结构之中看到了社会因素的干预——例如巴赫金对于话语类型的分析,巴赫金将所有文本和言说单位之间的关系视为对话关系,这无异于在言语的展开之中看到了社会图景的全部复杂性。在巴赫金心目中,语言是通过具体的言语进入现实,现实也是通过具体的言语进入语言,这不啻于是他对语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基本构思〔17〕。
恢复语言所含有的社会能力,这也就是从一个重要方面暗示了种种语言事件可能隐含的分量。在一个最为深刻的意义上,一种新的语言潮汐将是人文环境隐蔽地转换的根本标志。人们同样可以在汉语之中看到,某些意味深长的语言迹象正在出现。
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量的政治术语布满了当代汉语的每一个角落。这些政治术语如同一套严密的路标规范了所有的判断尺度。无论人们谈论何种问题,最终的裁决都将引向严峻的政治准绳。政治术语的强大势力吞没了一切,一个由语言铸成的坚硬槽模顽强地规定了现实的导向。密集的政治术语无疑为人们制造出一个相应的人文环境。有关人的所有解释都将是政治定位。人的精神单一地镶在了政治的维面之上。无论是涉及道德还是涉及生理,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法律制定,一切都将趋归于政治鉴定。当妻子用“官僚主义”形容丈夫粗心的时候,或者,当父母用“修正主义”指责子女享乐倾向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怀疑:除了政治表述,所有的词都已经消失了吗?这一个时期的汉语表明,政治术语的强大攻势成功地从日常话语之中清洗掉种种商业用语、感情用语、性学用语,它们甚至强行打入门户森严的科学用语——人们可以从物理课本或者医学教科书之中读到大段大段支离破碎的政治话语片断。在这里,种种政治术语的使用显然包含着强烈的褒贬。这些政治术语既是命名,又是判断;既包含了赞颂,又包含了指令乃至处罚。总而言之,密集的政治术语同时又在人文环境之中制造出某种紧张气氛。这使日常用语缺少幽默,缺少委婉,咄咄逼人的论战语调代替了温情与智慧。一系列不可冒犯的教条词句在汉语中间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连续体。
不难察觉,这一封闭性的连续体目前正在逐渐瓦解。当代汉语的许多方面似乎进入了更新换代的时期。某些众所周知的语言格式悄悄地过时了,某些口号成为历史风雨之中的遗迹。一些概念、词汇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带上了某种矫揉造作的气味,另一些陈述方式与特殊语气突然具有了令人反感的风格。作为一种替代,一批陌生的话语涌入汉语,新型的语言氛围开始在诸方面酝酿。从人文科学的标准表述到日常用语之中的寒暄、称谓、恭维、玩笑之辞、公共关系用语或者礼仪客套,人们都能察觉到汉语的某种微妙演变。这种演变显然导于新的人文环境。的确,如果从权威传播媒介上看到“老板牌抽烟机”的广告词,人们不可能不意识到价值体系的转移。赢得公认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论证,它还将疏散到日常用语的遣词造句之上,活跃于每一个人的口吻之间。这时常体现为,人们日常使用的词汇表不知不觉地更换了。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曾经用词汇感觉的变异体现旧有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由于憎恨战争,小说的主人公愤然宣称:同村名、道路编号、河流名称、部队番号、日期等具体字眼相互比较,诸如“光荣”、“勇敢”、“荣誉”或者“神圣”这些字眼显得秽亵和下流。在这里,几个概念的沉浮象征了一代人的反抗情绪。对于汉语说来,那张代表了又一个时代的词汇表出现了没有?
日常话语之中,新的语言潮汐通常是以潜滋暗长的形式来临。表面上,陈旧的话语系统一本正经地流通于文牍、社论、报告、官方发言、会议用语、交际辞令以及新闻文体之中。但是,就在种种权威的语言表述背后,一些语言的局部开始变形、锈蚀、剥落、死去;另一些局部产生了有趣的语言萌芽:某一方面前所未有的词汇零星地缀入了人们的会话,某一类型的用语逐渐增添了使用的频率,某种特定的风格或者语气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得列了仿效,如此等等。考察语言内部正统与变异的冲突,人们不能不想到弗洛姆提出的一个概念:“社会无意识”。无论是弗洛姆的师承关系还是这一概念的构词方式,“社会无意识”都明显地带有弗洛伊德“无意识”的胎记。弗洛姆使用“社会无意识”指谓多数社会成员普遍遭受压抑的精神区域。弗洛姆认为,一个社会同样将根据自己的利益压抑某些思想和情绪,使之陷入意识阈限之下的黑暗,成为无名的存在。按照他的分析,语言将和逻辑学以及社会禁忌系统共同组成严密的网络,从而阻止这些思想和情绪浮现到符号层面上来〔18〕。在这个意义上,正统的话语系统同时也就是鉴定某种社会意识可否放行的闸门。然而,弗洛姆同样察觉到了“社会无意识”对于压抑的不屈反抗。这种反抗包括了对于语言闸门的冲击。不难推断,人们所遇到的语言变异即是这种冲击的后果之一——某些“社会无意识”终于通过反抗打入社会意识,并且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形式。
弗洛姆与弗洛伊德的差异在于,“社会无意识”比“无意识”带有更多的社会涵义,同时也呈现出更为宏大的考察视野。弗洛伊德将弑父娶母的欲望作为压抑的主要对象,而“社会无意识”却包含了远为丰富的内容:它可能是主导意识形态所否决的思想学说,也可能是被压迫阶级或阶层的叛逆之声;它可能是某些处于边缘的弱小民族所留下的文化艺术,也可能是超级大国垄断之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本上风格;总之,围绕“社会无意识”的压抑、反抗远远不限于弗洛伊德所关注的文明与个人的关系,这个概念更为适宜于成为各种范围社会革命的描述。在同样的意义上,“社会无意识”的表现愿望也更为强大——它们急迫地渴求进入社会的语言代理。
这就是今日文学应声而出的时刻了。
相对于诸多话语系统,文学话语的、修辞、叙事、母题、类型结构无不更为主动地向“社会无意识”敞开。文学对于感性的爱好,文学对于个性的尊重,文学对于民间和被压迫者的亲近与同情,文学对于自由、反叛、激情的肯定和文学对于超验的浪漫想象——这一切都造成了文学对于“社会无意识”的亲和倾向存这个意义上,人们确立了文学话语的维度。
社会话语的光谱系列之中,文学话语仅仅占据了一个狭小的位置。然而,文学存在于这个系列的首要理由无疑是:坚持文学话语的维度,并且尽可能将这样的维度展示在现实的人文环境之中。
注释:
〔1〕卡西尔:《语词的魔力》,见《语言与神话》第80页, 三联书店,1988版
〔2〕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170页至171页,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3〕卡西尔:《我们的现代政治神话技巧》, 《符号·神话·文化》,第202页,三联书店,1988年版
〔4〕苏东坡:《答谢民师书》
〔5〕见《蔡宽夫诗话》
〔6〕刘熙载:《艺概·词曲概》
〔7〕苏东坡:《竹坡诗话》
〔8〕《老子·二十八章》,《庄子·渔父》
〔9〕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的《导言》
〔10〕汪懋祖:《读新青年》,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46页
〔11〕胡先骕《中国文学改良论》(上),《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04页
〔12〕周作人《思想革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200页
〔13〕转自《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胡适的《导言》
〔14〕参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42页
〔15〕参见申小龙的《中国句型文化》之中九、十两章
〔16〕参见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
〔17〕参见巴赫金的《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 》和《TheProblem of the Text》
〔18〕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第126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