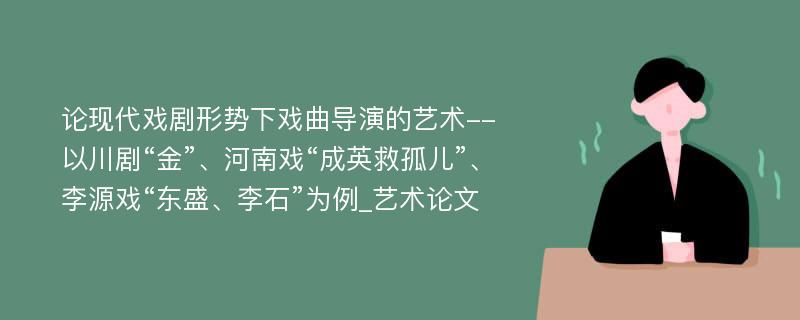
现代剧场境遇中的戏曲导演艺术摭论——以川剧《金子》、豫剧《程婴救孤》和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梨园戏论文,川剧论文,豫剧论文,为例论文,境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戏曲艺术是我国人民群众集体创造并历代传承的一种演艺形式,源自我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高于这一生活,是他们生活理想和审美观念的综合实现。在我国各民族审美心理、民族文化因素以及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文艺思潮的影响下,戏曲艺术表演要素不断丰富,表演技巧不断成熟,表演程式不断完备。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现代生活及其影响的现代人的情趣与戏曲艺术的观念表达和艺术程式逐渐产生了距离,这使得戏曲艺术正淡出当代生活,特别是正淡出年轻人的视野。为了使我们民族艺术瑰宝光彩依旧,戏曲艺术开启了进校园、进课堂之旅。我们作为戏剧艺术工作者,能为传统戏曲艺术回到现代剧场中做些什么,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一.从传统戏楼走进现代剧场
传统戏楼作为戏曲艺术演出的场地,在特殊的观演关系中形成了特定的表演形态乃至表现理念,比较传统的戏楼与现代剧场作为演出场地的表现差异,是我们理解“现代剧场境遇中的戏曲导演艺术”的基点。
1.戏楼的“高台教化”与剧场的“平等对话”
中国传统戏曲的观演关系基本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灌输式、说教式的言说。有趣的是,中国古代戏曲演出场所也多为高高在上的“戏楼”,观众对演员多为仰观而非平视,形成了演员屹立高台、对芸芸众生传经论道的场面。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随着当代都市文化设施的建设,“戏楼”变成了“剧场”,剧场使演员和观众融合在一个闭锁的空间中,缩短了观众与演员之间的物理空间距离,也密切了二者之间心理空间的距离,现代剧场实际上建立了一种“平等对话”的观演关系。
事实上,这种观演关系上的改变,必然对戏曲艺术的思想内容产生影响,使之从“教化”走向“对话”。例如在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中,彭老爷担心爱妻李氏在自己入土后会与别人产生感情,于是在临终前嘱托董生暗中监督李氏,防止李氏有出轨的行为。这种思想和行为本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教化”主张,但该剧的言说却是让董生与李氏彼此产生恋情,“监守自盗”的董生与李氏结为夫妻,体现出人性中对于爱情的向往与追求。这种自由恋爱的思想是对封建教化的一种颠覆,也符合当代社会“平等对话”的主张。又如川剧《金子》,将原剧《原野》仇虎复仇的线,变为突出刻画金子这个人物形象,着重描写她的善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炽热纯真爱情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对懦弱丈夫的怜悯,以及对恶婆婆的憎恨和反抗。这个人物形象体现出了现代女性的性格取向,也与现代观众构成了一种“平等对话”,一种可以默契的思想交流。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现代剧场的“平等对话”,需要戏曲导演摒弃封建礼教的“说教”,更加注重对人性的思考,顺应“戏楼”向“剧场”的演出空间变化,从思想内容上变“高台教化”为“平等对话”。
2.戏楼的“演员本体”与剧场的“综合构成”
传统戏曲的演出方式是“演员中心制”(其实是“主演中心制”)。也就是说,被称为“角儿”的主演除设计自身表演形态以“显摆”自己表现能力外,还要求其他配角(俗称“龙套”)围绕自己的表演而进行。此外“一桌两椅”常常既是舞台道具又是舞台景物,灯光通常就是一般的照明,不讲究特殊的设计。戏曲故事内容的繁复多变,戏曲人物性格的丰富多彩,戏曲冲突境遇的幻化多样,都要靠演员运用从生活中提炼的表演程式来进行表演(或称“暗示”)。这与中国画中“计白当黑”的构图理念,与“移步换形”的透视法则多有相通之处。自20世纪初话剧艺术作为“新演剧”进入中国以来,以洪深为代表的中国话剧的先行者尝试完善专业导演职能并建立正规排演制度,使戏剧演出走向“导演中心制”。“导演中心制”的建立,在于把戏剧艺术的舞台呈现视为一种综合艺术,它需要协调舞台演剧的各个方面,使之成为一种有机的“综合构成”。“导演中心制”的演剧理念不能不影响乃至改变传统戏曲的“演员中心制”。首先,“导演中心制”的建立使演员(包括主演)回归到“人物本体”,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演技来准确地塑造人物性格;同时导演职能的发挥成为演员表演中的一面“镜子”,演员通过这面“镜子”的调适,不仅更贴近人物,而且更顾全大局。其次,“导演中心制”的建立要求舞台美术设计参与戏剧演出,在提示境遇、营造气势、烘托氛围上发挥作用。不光要求演员在舞台上有真实的、扎实的表演功力,而且要求舞美、灯光、音效的有机配合,营造出与所演剧目相关的氛围,使得演员能够在规定情景中更加投入地表演,同时也为当代观众创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观众的情感与舞台人物的命运息息相关。
步入现代剧场的戏曲艺术,要正视由传统戏曲“演员本体”向现代剧场“综合构成”转化,就要在保持传统戏曲艺术特质的情况下,强化“综合构成”的演剧观念。如豫剧《程婴救孤》,导演通过环境的转换将这部戏分为八幕,其中有外景戏也有府内戏。设计者在舞台后区结构了一座桥,这是一座上能站人,下能过人的桥,桥两端台阶是可移动的平台,它不仅规定着情境也渲染着氛围,还能强化演员的内心表现。如在程婴救下孤儿后,为躲避屠岸贾手下的严查而潜逃出宫,导演在处理这一段戏时就利用了舞美设计上的桥洞——程婴在舞台上左钻右蹿、东躲西藏,都是依托着桥洞来做戏,这一设计强化了程婴在逃亡中的艰辛与危险。还如在一些程婴独白的表现中,程婴时常回想起为了替他隐瞒行踪而拔剑自刎的韩厥将军,回想起被屠岸贾重刑虐杀的侍女彩凤和替他赴死的老兄弟公孙杵臼……每当他回忆起这些友人、义人之时,导演就让这些人物出现在高台之上,使观众能更形象地体会到程婴的心象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悲痛和沉重。由此可见,面对当代观众,传统戏曲不能是只依托“演员本体”的表演艺术,它应思考景、光、效、服、道、化的“综合构成”,以此赋予戏曲艺术现代转型的活力。
3.戏楼的“曲线出入”与剧场的“平行调度”
传统戏曲演出的戏楼,演员上下场是由“出将”、“入相”两门出入,又称上场门和下场门。由于上、下场门均在现代剧场天幕的位置,一来使得戏曲不能有更多背景,二来要以“曲线出入”为主。这当然也与“戏楼”作为凸入式舞台要兼顾三面观众的观看相关。现代剧场的舞台呈现为镜框式舞台为主(除了一些特殊的小剧场的中心式舞台)。让观众通过“镜框式”的画面来观察演员的行动,演员的上下场在舞台平行的两侧(尽管我们仍按习俗称之上、下场门),演员的舞台行动主要是“平行调度”。相对而言,“平行调度”比“曲线出入”更贴近日常生活,因而也就更贴近现代观众。
现代剧场的戏曲艺术要在程式化的“曲线出入”和生活化的“平行调度”之间找到平衡点。如川剧《金子》的第三幕,环境是在焦家,焦文星得知自己心爱的金子在外养汉而心情郁闷,一个人在大厅喝闷酒。此时仇虎是为了试探焦大星并且为坚定自己的杀机而来,一无所察的大星还让仇虎陪他喝酒诉怨。金子则在二人间来回斡旋,时而向仇虎夸奖大星,时而提起小时候三人一起玩耍的往事,想打消仇虎加害大星的念头。在这段“三角戏”中,导演利用台上的酒桌和舞台后方焦阎王的画像这两个布景,让三位演员围绕桌子保持一种三角“调度”关系——即金子在后区,大星靠近上场门,仇虎靠近下场门。金子在二人之间的“调度”就像天平的砝码一样来回拨拉,在大星和仇虎的推杯换盏间缓和二人的情绪。我们看到,大星和仇虎的调度都是大开大合,金子则在大星和仇虎之间往来周旋:气氛缓和时,金子的活动空间就会大些,调度也舒缓些;气氛紧张时,金子就被二人夹在中间难以挪步。事实上,这种“调度”所产生的戏剧效果,是“曲线出入”难以达到的。
二.导演艺术需正视戏曲艺术特征
戏曲艺术作为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演艺形态,不仅沉淀着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且会引导着当代的观赏心理。其实,无论从强化民族艺术的个性特征还是从凝聚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来说,我们在关注戏曲艺术的现代接受之时,不是要将其做阉割式的改造,而是要在正视其特征的同时实现创造性转换。
1.“以演员为中心”的演出特征
正如上文提到的,戏曲艺术的演出特征是“演员本体”(也即“以演员为中心”),这是导演艺术在执导戏曲作品时首先要注意的艺术特征。导演要在角色性格和演员技能技巧之间找到结合点。这是因为,戏曲艺术是一种高度程式化的演艺形态,其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往往以技能技巧的形态附着于演员本体,不少优秀的戏曲演员甚至有“一招鲜,吃遍天”的表现才能,因此挖掘演员自身的技能技巧优势,既有助于强化角色性格的塑造,又有助于强化戏曲艺术的本色。
如豫剧《程婴救孤》第四幕中,屠岸贾兵发太平庄,在刺死婴儿和公孙杵臼后打道回府,此时只留下程婴一人在表现丧亲之痛。对这一唱段的处理,饰演程婴的李树建先生充分运用自己的技能技巧,用一组与老生扮相贴切相符的动作“耍髯口”以及一个突如其来的大幅度跐跪过去,抱住亲人的尸骨嚎啕失声,人物的万重伤痛从这极其简约而富有特点的“耍髯口”和“跐跪”的动作中表现出来。这正是导演应挖掘的“演员优势”。再如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导演从寻找角色性格和演员表演风格的结合点着眼,选择了专攻丑角的演员龚万里先生饰董生,利用丑角的表现技巧来显现中国古代书生的痴迷迂腐。董生为信守自己对彭员外的承诺而做尾随跟踪李氏之事,最后自陷相思之苦无法自拔,导演借用丑角的表演优势来助力一种“黑色幽默”,体现出正视戏曲艺术特征的巨大作用。
2.“以歌舞演故事”的叙事特征
王国维先生著《宋元戏曲考》,定义“戏曲”时谓之“以歌舞演故事也”。“以歌舞演故事”作为戏曲艺术的叙事特征,指明了戏曲艺术是“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音乐类戏剧”。戏曲艺术在其历史传承中归纳为“四功五法”,即“唱、做、念、打”和“手、眼、身、法、步”。其本质一是强调体态表现的“一动俱动、配合默契”,二是强调“歌声应节、舞动合韵”。导演戏曲作品不仅要熟悉“生活真实”,还要把握戏曲审美中的“艺术真实”。
如川剧《金子》第一幕中,金子送大星去收账时有一段戏弄大星的唱段,金子唱道:“只晓得油炸花生,脆蹦儿脆蹦儿嚼起香。清炖鸡腿咬起香,晚上的夜宵吃起香,热呵呵的铺盖睡起香,早晨的卟鼾扯起香,胭脂粉闻起香,嫩咚咚的脸儿挨起香,野叉叉的嘴儿啵起香。”这一唱段利用俏皮的唱词和诙谐轻快的伴奏,刻画出了一个山野少妇泼辣开朗的性格,表达出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年轻女子,渴望得到炙热的爱情却面对一个懦弱而又善良的丈夫,那种又气又爱又怨又怜的复杂情感。又如川剧《金子》中焦母摸到了仇虎戴在金子头上的花,她阴沉沉地将花摘下摔在地上,又恶狠狠地要金子将花踩烂。金子对焦母的威逼则是明顺暗抗,从金子“佯装踩花”到“抬脚犹豫”再到“违心踩花”最后“木然拾花”这一连串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导演是刻意拉长了这一段的表演节奏,原本在生活中一瞬间的事情,被导演用舞蹈化的动态刻意拉长,强调“踩花”这一细节对金子的情感刺激,同时也拉长了观众的内心情绪,使观众更加充分地体会到金子在焦家所遭受的虐待,为其日后与仇虎的离家出走作了有力的铺垫。这足以看出“以歌舞演故事”作为戏曲艺术的叙事特征,具有其他戏剧手段无法替代的表现力。
3.“空白处皆是意”的表意特征
包括戏曲艺术在内的中国传统艺术崇尚写意而贬抑写实,戏曲艺术在舞台设计理念上追求“空白处皆是意”的表意特征。所以传统戏曲舞台的设计多在“一桌二椅”上做文章。这使得戏曲艺术不仅要“以歌舞演故事”而且要“以歌舞演情境”。在当下,舞美设计已成为综合性戏剧艺术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戏曲艺术当然莫能例外。舞美设计家胡妙胜认为戏剧艺术的舞美功能主要有三点:一是组织动作的空间,二是再现动作的环境,三是表现动作的情绪和意义。在戏曲艺术中,上述功能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全剧中几乎并没有任何布景道具来辅助表现。舞美设计所发挥的作用仅仅只是将一个“空白”的梨园戏台搭建在剧场舞台上,而所有场景的转换都是通过演员的唱、做等表演体现出来的。该剧的重头戏“登墙夜窥”就是这样表现的:梅香手持一个写有“彭”字的灯笼巡夜,给观众证明周围的环境是彭府;然后李氏上场,催促梅香回去歇息,梅香下场;这时董生从另一侧上场,表示他置身府外,他侧身扶墙状表示他沿彭府围墙而行;这之后他来到墙角下,看到有一棵梧桐树和一把竹椅,也看到府内望月哀叹的李氏。两人虽然同台出现,但两人的互不交流使观众了解两人之间正隔着一堵墙。接下来,董生的表演是将竹椅放到梧桐树下,试试竹椅能否承受自己的体重后,便抬腿踩上,边手扶树干边将头从墙沿轻轻探出,窥探李氏。董生摸黑“登墙夜窥”的一系列动作都是通过无实物表演(即戏曲所言“虚拟”)和唱、做等来实现的,而正是舞台的“空白”,才使演员的表演得到了观众的“意会”。在这个意义上,舞美设计的主要作用通过实在的布景来经营舞台的空间,戏曲艺术更关注布景的布“空”而非布“实”。
三.传统戏曲转型与戏曲导演艺术
所谓传统戏曲转型,最简洁的说法就是戏曲艺术“与时俱进”的问题,也即我们常常谈论的“继承与发展”的问题。为什么要“转型”,就戏曲艺术最迫切的需求是要赢得现代观众群体,要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同时赢得相应的市场效益。但其实,这个“转型”是十分复杂十分繁难十分艰巨的历程。就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戏曲文化建设而言,我们传统戏曲的转型至少要正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向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转型;二是从农耕文明、乡村文明向工业文明、都市文明的转型;三是由相对封闭的地域、域内文明向以“网络生存”为标志全球化进程的转型。在本文的论述中,我们只是在传统戏曲转型的宏观背景下,探讨戏曲导演艺术在“转型期”的作为。
1.戏曲导演要强化案头文本的“动作性”
一些传统戏曲曲目往往只是简单地将案头文本搬上舞台,对于文本的舞台呈现缺少直观的动态设计和较为丰富的调度处理,导致“动作性”苍白和贫乏。强化案头文本的“动作性”,核心在于强化案头文本的演出效果。这种“强化”,要处理好“文本”与“动作”之间的两种关系:一是替用关系,也即有些可用舞台动作表现的东西,不必非将文本的言说照搬,以免显得累赘拖沓;二是辅助关系,即某些文本言说,通过一定的舞台调度处理和肢体动态设计,显得多彩多姿、有声有色。此外,这种“强化”还在于导演以自己的舞台想象去改变和丰富案头文本,既包括宏观层面上戏剧冲突的“动作性”,也包括微观层面上细节刻画的“动作性”。如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第一幕“临终嘱托”中,两个小鬼要带彭员外上路,剧本上对这一段并没有表演上的提示;导演在二度创作中让两位扮演小鬼的演员手持短棍进行表演,这就使演员有可能以富有创意的“动作性”来强化对案头文本的表现。如两个小鬼利用短棍将彭员外的鬼魂拉出,边拉边耍棍强化了以乐演悲的情调;还有彭员外在唱“水车歌”之时,两个小鬼用短棍比拟琵琶和二胡来为其伴奏也别具意味。此外,前面已提及的第三幕“登墙夜窥”一段,演员的无实物表演为唱段中添姿增色,那些爬树翻墙、尾随入房的动作比案头文本的说唱更具表现力。可以说,强化案头文本的“动作性”是戏曲导演的用武之地。
2.戏曲导演要深化人物性格的“体验性”
我们说戏曲艺术是注重“程式化”表演的艺术,是指它在对生活,对生活中的事态、人物加以观察、提炼的基础上,运用夸张,变形的手段,进行着一种“典型化”的创造。但“程式化”容易使个性淹没在共性之中,弱化人物性格的“体验”。越剧艺术在完善剧种形态的过程中,力求实现昆曲对人物性格程式体现和话剧对人物性格深度体验的完美结合。深化人物性格的“体验性”是当代戏曲导演的必修课程。
强调深化人物性格的“体验性”就是要通过体验具体人在具体情境中的具体感受来调整、变化并创新表演程式。如豫剧《程婴救孤》第二幕中,当公孙杵臼决定替死救孤并将护孤成人的重担交给程婴时,说了一段令程婴惊怵的心声:“死,有时要比生容易得多。我一死了之,权当睡过去了;可你要留下来,把孤儿抚养成人,在真相大白之前更要承受世人的唾骂——骂你背信弃义,贪图富贵,势利小人……那滋味不好受哇!贤弟,你要撑得住,忍得住,熬得住啊!”听着这段句句如锤砸在心头的话语,程婴没有走“程式化”表演的套路而是给观众展现一个剧烈颤抖的背影,也正是这剧烈颤抖的背影让观众体验到程婴的一种性格其实;在二人将计划商定之后,相约“泉下相会再叙说别后之情”,这时导演省却了一切调度,让二位挚友在相互凝望的沉默中发出了一声嘶嚎,而后突然冲向前相互跪拜,猛然拥抱。这一嚎、一跪、一抱,十分干净,简练,但却将两个人的内心揭示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切身“体验”的结果。
3.戏曲导演要统合剧场演出的“整体性”
现代剧场艺术是一种综合性的艺术,“整体协调”在“综合艺术”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代戏曲导演要统合剧场演出的“整体性”,是一种全局的、有机的、开放的“整体性”。所谓“全局的整体性”,首先是要对作为“一剧之本”的剧本进行“舞台化”的整体构思,要通过舞台时空的想象重新结构情节流程和情感意象,重新组织戏剧行动和性格冲突,使“案头之本”成为立体化的舞台形象。所谓“有机的整体性”,其基础层面是使戏曲表现手段“唱、做、念、打”有机协调,有交织、有层次、有对比,是对人物性格塑造和戏剧冲突进程的最恰当体现;其较高层面则是使布景、灯光以及LED视屏技术等有机融合,在因情生景、触景生情、境由心造、心到境随中实现“有机的整体性”。而所谓“开放的整体性”,是指导演要用“接受美学”的理念考量创作,要研究观众的心理现实和期待视野。在当下的创作中,我们常说要处理好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关系,其实主要是要处理好艺术的历史构成与大众的现实期待的关系。我们之所以提出戏曲导演还要关注“开放的整体性”,是着眼于戏曲艺术贴近现实并放眼未来的;并且,只有“开放的整体性”才能实现“整体性”的全局统筹和有机构成。
标签:艺术论文; 戏曲论文; 剧场论文; 戏剧论文; 川剧论文; 文化论文; 董生与李氏论文; 豫剧论文; 明星穿搭论文; 娱乐八卦论文; 都市电视剧论文; 中国电视剧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智利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