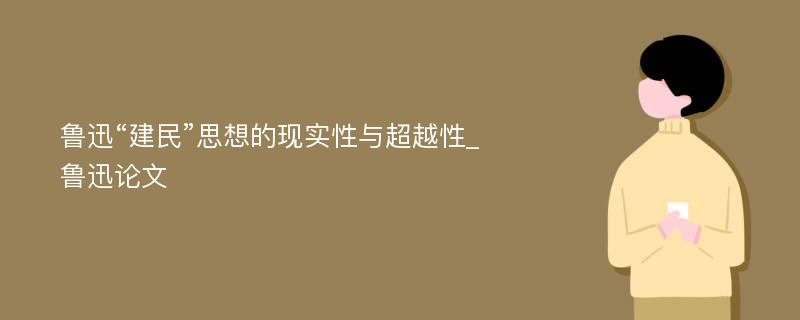
鲁迅“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现实性论文,思想论文,立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把握住“小我”与“大我”、“个性觉”与“群之大觉”的内在同一性,从而以中西文化的撞击为条件,以先觉者的“个性觉”为突破口,唤醒中国人的主体意识、个性意识,摒弃其自身劣根性,确立新型民族性格,促成传统中国人向现代中国人的根本转变,由单个中国人的自立,达到全民族的自立,同时也由此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生存状态产生有益的影响,这是鲁迅在几十年来为改造中国人的不懈奋斗中所形成的“立人”思想,也是他终生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他精神价值的实质所在。
鲁迅的“立人”思想是他置身于中国近现代转型的大潮中,对中国人如何最终摆脱奴役和贫困,迈进“世界人”行列这一严峻现实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是他面对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人类及人类个体的存在意义,这一具有终极性意义问题不断探索与思考的结果,它不仅对中国人的自立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人类和人类个体的自立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鲁迅的“立人”思想既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同时又具有十分明显的超越性。
一
所谓现实性,实际指的是作家在其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生活反映的真实程度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和思想倾向,它与真实性、深刻性、准确性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密切相关。一般说来,凡具有较强现实性的作品,都在真实、深刻、准确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与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的价值判断与思想倾向。对于鲁迅来说,作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无疑是符合这些要求的,而作为他作品核心内容的“立人”思想则无疑也具有着强烈的现实性。
要立人,必须首先要弄清所立之人的生存现状,必须“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注:《华盖集·通讯》。),这样才能引起疗救的注意,才能根治其痼疾、立出“新人”来。鲁迅的立人正是从这里起步的,他“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也就首先在这点上,即在他形象地描绘出了中国人现实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并剖析了中国国民劣根性上得到了体现。
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是鲁迅对几千年来,当然更包括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状态的形象描绘与准确概括。正是由于这种长期的窘态生活,中国人身上积淀下了相当多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不仅妨碍了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而存活,同时也妨碍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正的民族而“自立”。为扫除这一“立人”障碍,鲁迅开始了终其一生的揭示并剖析国民劣根性的事业。从他留日时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起,到辛亥时期的《怀旧》、五四时期的《灯下漫笔》、《阿Q正传》,再到晚年的《运命》、《病后杂谈》, 鲁迅不遗余力地对其进行了揭示与批判,综观他一生的创作,无论是前、后期的杂文,还是小说与散文,改造国民性始终是其基本主题之一。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剖析是全面而深刻的,从由“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目光短浅、卑怯贪婪、趋炎附势的奴性,到永远得意、极易忘却,既不能正视外在世界,又缺乏自我意识,常以自欺之法求得解脱的精神胜利法,到具有“无物之阵”、“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特性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的麻木性和愚昧性,再到只忙于眼前实利的“活身之术”,缺乏热情、不愿冒险、贪图安逸的保守性,世故、圆滑,令对手在不得要领中上当等劣根性,鲁迅一一予以了抨击。把妨碍中国人“自立”、妨碍中华民族“自立”的痼疾,把增大近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难度的障碍展示了出来,打好对其进行疗治的基础。
如何摒弃中国人的劣根性、确立新型的民族性格是鲁迅“立人”思想现实性的另一重要体现。
鲁迅的“立人”是建立在对中国传统文化土壤改换基础上的。早在他“从小康之家坠入困顿”时起,他就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与反省,后经在南京、日本求学期间受到各种近代西方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他的怀疑与反省成为了一种自觉意识和独特品质。在辛亥革命至他晚年期间,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与反省不仅变得越来越深刻,而且也越来越科学。从中他既发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制度等对中国人所具有的残酷奴役性,又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的理性法则等对中国人的创造力和精神自由的严重束缚性。面对传统文化的“吃人”特性,鲁迅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中国几千年来无非是“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即从有文明以来一直排到现在,人们就在这会场中吃人,被吃”,“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注:《坟·灯下漫笔》。)由此鲁迅得出了“原有的文化土壤不铲除,新人万难长成”,“中国的改革,第一著自然是埽荡废物,以造成一个使新生命得能诞生的机运”(注:《译文序跋集·〈出了象牙之塔〉后记》。)的结论,发出了“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注:《坟·灯下漫笔》。)的呐喊。于是他把剔除了诸多不利于“立人”因素与机制(如妨碍人精神自由的理性法则等)的西方文化大胆拿来,在改善人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同时,也开禁了对“人之内”——精神的自由与解放的束缚,对中国的文化土壤作了全面的改换。鲁迅这种带有彻底性的文化改造举措,构成了他促成中国人“自立”的逻辑起点。
在改换文化土壤的同时,鲁迅也开始了他立人的另一个重要步骤——思想文化启蒙。面对着愚昧、麻木、保守和落后的国民,鲁迅表示了极大的忧愤,他说:“中国的呆子、坏呆子,它是医学所能医好的吗?”(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注:《呐喊·自序》。)于是鲁迅操起了从精神上对中国人进行思想文化启蒙这个武器,用以唤醒昏睡的中国人,使其觉醒、觉悟起来,看清自身劣根性,达到彻底根治的目的。在思想文化启蒙中,鲁迅极力把启蒙所需的理性法则与起源于近代理性主义信念破灭之后所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结合起来,同时高扬起了“科学”、“民主”和“主体性”、“个性意识”这两面大旗,在彻底颠覆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去逐一医治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为去掉奴性,鲁迅主张对权势者不是“捧”而是“挖”,要不畏强暴,多力善斗,对手如是凶兽就显凶兽相,如是羊就显羊相;对同是站起来的国民要在人格平等的基础上朋友式地相待。为去掉精神胜利法,鲁迅主张要彻底地打破“大团圆”,要睁开眼睛“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抉心自食,欲知本味”(注:《野草·墓碣文》。),正视人生的缺陷,从自满的“堕落”中走出来。对于愚昧、麻木、保守、中庸等其它劣根性,鲁迅也在其“尊个性,而张精神”的总道术指导下逐个予以了医治。接着,鲁迅又从正面创设了中国人“自立”所需要的现代民族性格:去掉蒙昧、直面人生、树立自信心,增强社会批判精神与社会责任感,确立人的主体性;追求精神的解放与自由,摆脱一切外在内在的支配,确立人的个体性。
鲁迅以现代价值标准为准则,通过揭示并剖析国民劣根性、改换文化土壤、实施思想文化启蒙、医治劣根性和创设新型民族性格等努力,希图使中国人觉醒起来,认识到“人各有己,朕归于我”,由此达到“群之大觉”、“中国亦以立”的目的,为中国社会的“立人”绘制出了一条十分详尽而又现实的畅达之路。
二
在鲁迅的“立人”思想中,鲁迅对中国人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是采用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即在生活体验层面上是感性的,具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在价值层面上则是理性的,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的斜面向上走”的,这样当鲁迅把通过刻骨铭心的独特体验与认知经验投入到他对人的理性关照之中时,他所关注与审视的内容及方式,就一方面保证了他的认知活动能够突破特定的社会历史时空的限制,在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更为久远的时代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也保证了他的认知活动能够不断地向对象本质逼近,由对中国人当下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审视,升华到对人类及人类个体存在意义的寻求与探索上。而就超越性来说,仅在其思想范畴而论,它指的就是文学作品所包蕴的思想内涵能够在历史时空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对其限制产生突破,从而具有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在这一意义上鲁迅的“立人”思想就获得了在这两个层面上的超越性。
鲁迅对“中国人”的关注与审视虽然始终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特定历史时期、并受着特定历史形势和条件的制约与规定的,但由于其又是中西文化撞击与社会转型期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完全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进行,它还必然向外部社会和未来社会敞开。因此,这使得鲁迅的思考不但没有像一些西方思想家那样,只是提出了一套空洞的关于“人”的存在信条,而是使其能够在服务于本民族当下的同时,对处于相同文化转型期拥有不同文化种类民族的“自立”和对完成转型后的中国人的“自立”也具有了指导意义,从而突破了社会历史时空的限制。
在中国近现代转型期间,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愈演愈烈,鲁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如果继续被动地保持现状,那么中国不仅要被排斥在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之外,而且“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被挤出”了。如何使将要“亡国绝种”的中国走出危境?鲁迅认为,应把中国人当下的处境置于整个世界性的冲突中来加以考察和把握,近代中国的出路和希望,在于引入西方先进的文化,在于用西方现代社会的标准来拷问中国人的灵魂,重塑中国民族性格。这样,当鲁迅在这种世界性的广阔背景上为中国人的“自立”找到这条出路时,这条路对西方民族的“自立”也有了意义。(这一点,从人类学和社会学上也可以得到证明)。如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揭示与剖析,就对西方民族照见自身劣根性具有着启示性。又如,鲁迅所创设的现代民族性格就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国民性格。
“立人”是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从早期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唤,到梁启超等辈的“新民说”,再到陈独秀等人的“启蒙论”,各种“立人”主张层出不穷,然而这众多的“立人”学说都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不足,它们要么流于一些抽象的口号,缺乏具体的内容,要么急功近利,因过于实际而无法实施。与之相比,鲁迅的“立人”思想具有他人所无法比拟的可行性、致密性和深邃性。因为他的“立人”是从一种积极参与、改造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态度出发的,是从一种总体性的超越位置上来认识、思考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尤其是现实人生的,是从一种现代社会的要求来确立“立人”标准的。因此,他的“立人”思想就既对中国近现代转型期的“立人”有关,又对转型后的中国现代化的建设有作用了。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奴性、精神胜利法、愚昧性和麻木性等国民劣根性,将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影响着现代化的建设;张扬个性、建立主体性也将仍然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主要课题之一,这些问题一日不能彻底地解决,鲁迅的“立人”思想就一日不会失去价值。
从鲁迅“立人”思想的文化来源看,则是明显地受到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启蒙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和十九世纪后期兴起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当鲁迅把这两种思潮迭印在一起时,他发现启蒙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天赋人权”、“理性法则”等虽然对人的启蒙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它们是属于知识层面的工具理性的范畴,不能在“立人”的层面上深入到对人的终极关怀中去。为补其失,鲁迅吸收了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精华,主张在追求人的社会解放的同时,也应追求人的精神解放,而且尤其是精神的解放,以寻找到人的最终出路。基于这样的思路,鲁迅参照西方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认知模式,积极地探寻了人类和人类个体的存在意义,从而使其“立人”的思想一下子由思想文化层面跃升到了形而上的领域。
“人生究竟是否值得活下去”,也就是人的存在意义到底在哪里?这是鲁迅思考了一辈子的带有倾向性的母题,对这一母题的最终解答,鲁迅是从对死亡的理解和超越中求得的。早在五四前夕,鲁迅就曾说:“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注:《热风·随感录四十九》。)这是他以一个启蒙思想家的姿态提出的带有乐观主义色彩的生死观。以后,随着鲁迅对生之困境感受的加深,对精神自由关注的加重和他世界观的愈臻科学化,他对死亡的理解变得越来越深刻:由对生命现象的单纯思考,扩展到了更深更广的文化哲学层面。面对死亡,他说:“我很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又说:“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注:《野草·墓碣文》。)晚年,当他惊心目睹生命的逝去和死亡的即将来临时,他更是高声赞美起女吊、无常、死火、死尸等一类的东西来。可以看出,对于死亡鲁迅是坦然、微笑的。他何以对死亡如此超脱?他说:“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注:《野草·题辞》。)“……也许有人死伤了罢,然而天下却似乎更显得太平。窗外的白杨的嫩叶,在日光下发乌金光,榆叶梅也比昨日开得更烂漫。”(注:《野草·一觉》。)十分明显,因为鲁迅“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过,因为他在见到死亡时感受到的是“生”的光彩,这里鲁迅不是看穿了死亡,而是超越了死亡,即在生存的困境中,用构造生的意义来对抗死亡,死亡虽是生命的终点,但不是人生的目的,人生应是在死亡之前更加积极地活、踏实地活,这就是鲁迅的死亡观。这不是他冥想的产物,而是他心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对中国历史和国民生存状态、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神圣启蒙使命长期地、不断深入地理性思考的结果。人们对死亡的态度必定紧联着他们对生的看法,鲁迅对死亡的超越就意味着他对人存在意义的获得。鲁迅说:“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注:《坟·写在〈坟〉后面》。)在一年将尽的深夜,他又写到:“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注:《华盖集·题记》。)走好“在此到那的道路”、留下“辗转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即注重生命的“有限”、“中间物”和“当下”,人存在的一层重要意义就在于此。这里鲁迅没有走向个人主义的幻想,也没有落进“存在主义”的旧套,更没有陷入“人道主义”的肤浅,他对个体生存“此在”的把握是深沉而又有意义的。但鲁迅又借过客说:“我还是走的好!”对于过客来说,走便是全部,走便是一切,永不停息地走在无尽无止的路上!因此,人的存在意义还在于对“有限”、“中间物”和“当下”的究诘、怀疑与超越;还在于用“不满”作前进的动力,去不停地反抗绝望,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因为当个体在一片无物之阵中,陷入茫然时,不失其志地反抗绝望将更显生的伟大。由此可知,鲁迅所探寻到的人的存在意义既在于对“有限”、“中间物”和“当下”等“此在”的注重,又在于“向野地踉跄地闯去”地“上路”、“寻找”和“走”之过程本身“彼在”的追求。(注:《野草·过客》。)
郁达夫曾这样评价过鲁迅:“当我们看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于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住了古今与未来。”(注:郁达夫《鲁迅的伟大》。)郁达夫的评论是中肯的,仅从鲁迅“立人”思想在两个层面上所具有的超越性而论,就可以得到十分有力的印证。
一般地说,现实性与超越性之间本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当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范围内构成一对关系时,则就有了一种相互加强、相互提升的作用,即现实性越强的作品,所获得超越性的可能越大,反之,超越性越大的作品,其所具有的现实性可能也就越强。鲁迅“立人”思想的现实性与超越性正是构成了这种关系。鲁迅“立人”思想在对中国人、中华民族如何走出当下的生存窘况,获得社会解放、民族解放的关注中所显示出的强烈现实性,促成了其在时空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的超越。反过来,鲁迅“立人”思想在广阔的背景上和文化哲学层面上,对人类和人类个体存在状态和存在意义的思考与探寻所获得的超越性,又加强了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鲁迅的“立人”思想正是在这两“性”及这两“性”所构成的关系中,获得了超出寻常的意义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