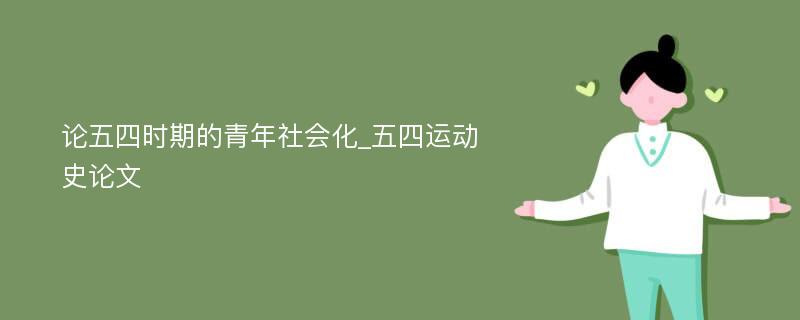
试论“五四”时期的青年社会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时期论文,青年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谓青年社会化,指的是青年通过实践活动,实现从以自然属性为主的人格模式到以社会属性为主的人格模式的转换。质言之,就是实现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换。社会化是青年的本质需求,它必然会渗透到任何有青年群体参与的运动中,并对之发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社会化是青年与生俱来的本质欲求,而本质意义上的青年群众,却是近代的产物,它只能以大工业的出现、近代教育制度的产生为基础。因此,在洋务运动以前,中国还不能产生真正的青年群体,当然也就谈不上青年的社会化。
洋务运动的发展,京师同文馆在1863年成立,晚清教育制度改革的起步,1872年清廷派遣留学生出国,这些都标示着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走向世界。随后,又出现了一批军事与工艺的专门学堂,紧接着又出现了以西学为主的自强学堂,甚至旧式书院也开设了部分西学课程。教育内容和体制的演变,以及其中蕴含的价值观念的递嬗,造就了第一批青年知识分子。进入20世纪后,晚清新政从废科举开始,促成了一场影响至深且巨的改革。20世纪初年第一次留学热开始了,赴国外留学(尤其是赴日本)几乎成了一种风气。在此基础上,青年知识群迅速扩大。随着科举制度的废弃,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场到民间,掀起了一个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据统计,到“五四”前夕的1912年,全国已有新式学堂82272所,学生2933387人。(注: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这样,留学生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的主体,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传统的八股士类。
近代青年群体的递嬗,促使了中国青年社会化欲求的生成与发展。无论是参与“戊戌新政”抑或是投身“辛亥革命”,都与各时代的先进青年(参与戊戌的青年在洋务时期产生,投身辛亥的则主要是青年留学生)的社会化渴望息息相关。到了“五四”前夕,由于数量上的优势以及系统的价值观训练,社会化已成为这一代青年的整体需求。他们深受新思潮、新学理的洗礼,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他们中的绝大数人已不再坐等生理上的自然过渡,已不耐于老一代知识者的薪火相传,而是要以积极的社会参与来促使自身的成熟。社会化,已不再是少数先进青年的先知先觉了。
二
如果说,青年自身的发展是青年社会化渴望产生和发展的内因,那么,社会环境诸因素的作用则是其变化的外在条件,它既规定了青年社会化的运行方式,也刺激了社会化渴望的高涨。
跟西方明显不同的是,中国青年的社会化始终以政治救亡为座标。这既跟中国近代工业的曲折发展,步履蹒跚以至难以充任青年社会化的物质基础有关,也和中国士大夫“兼治天下”、“舍我其谁”的传统心理有关,但更与中国近代日益紧迫的民族危机有直接的联系。近代以降,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步伐不断加快,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清政府不仅没有能力抵抗外来侵略,反而成为侵略者的工具。因此,“救亡”成为涵盖一切的社会命题,它决定了中国青年只有投身到紧张的政治斗争中去,才能顺利完成社会化的使命。充当一个社会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政治人,这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看到,“五四”以前几代青年的社会化都是在政治救亡的洪流中完成的。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其后的军阀混战,民生凋弊,恰恰是帝国主义魔焰高涨和封建势力死而不僵的表现。不仅如此,北洋军阀政府还直接成为青年社会化的阻力。1914年北洋政府公布的《治安警察条例》规定,青年学生“不得加入政治结社”。此外,青年学生还受着失学失业的威胁。据统计,当时中学毕业生能升学者,约为1/2至1/4,而失业的则为1/2至1/3。(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客观现实与青年的主观愿望形成了深刻而巨大的反差,它反过来使“五四”青年更加把自身的社会化同政治救亡结合在一起,更加滋长了政治参与意识和救世热情:“青年为斯世将来之主,学者乃领导标新之人,况生值学道将绝之国,大厦将倾之邦,则吾辈后生责任,不更重大耶。(注:周恩来:《敬业群乐会成立宣言》,《敬业》第4期,1916年4月。)
“五四”前夕,是青年价值观发生深刻革命的时期。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仍遵循着传统的青年价值观,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最先进的中国人都忽略了近代青年与传统自然意义上的青年之本质区别,他们承认青年是未来世界的主体,但他们却否认青年是现实世界的主体之一,即认为青年在现实社会里,仅仅是被动的受教育者。尽管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中,初步形成和发展的近代青年群体之现实作用日渐显露并不断加大,但是,它并未引起社会足够的重视。当时,担当社会精神中枢的,是一些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士大夫(辛亥革命中,留学生参与了领导,但由于人数较少,领导权最终被剥夺)。由于传统的桎梏,这些士大夫们不是成为反对改革的保守主义者,就是成为“皮里阳秋”的“中体西用”论者,甚至连康有为、严复、章太炎这些先进人士,也由于“内心的不自由”,以致虽在正统体系中挣扎苦斗,而最终仍是带着新陈交错,半生不熟的斑痕。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在中国,旧瓶装新酒是不可能的,它反而会成为革命的阻力。这便是陈独秀等“五四”新文化领袖们得出的结论。在陈独秀等人看来,如果没有彻底的文化转换,中国是没有出路的,革命也只不过是“无量英雄无量血,可怜换及假共和”。“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头脑耳目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之中枢。”(注:《新青年》2卷2号。)
由于陈独秀等人还没有看到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仍然只能从知识群体中寻找物质力量。认为要充当新的社会中坚,至少应具备下列条件:从文化积淀看,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绝对不能调和的。陈独秀把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归结为“古代文化”与“近代文明”的差异,认为东洋文明“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而“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注:《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页。)因此,对个体而言,传统文化因素越少越好,而外来文化的积淀愈厚愈佳。再从心理生理素质看,对现实社会愈不满,反抗性愈强,则对旧世界、旧制度的革命就愈彻底,就越有利于辞旧迎新。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等把目光投向了青年:近代青年的传统承载极其有限,又具有相当多的近代知识;同时,青年又是人生情感最为强烈的时期,其反抗性之强、革命性之烈,乃其他年龄群体所望尘莫及的。社会现实的窒息,更加强化了青年的这种激烈性格。这样,“五四”领袖形成了崭新的青年价值观:他们不仅肯定青年在未来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而且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公开承认青年在现实世界中的主体作用。李大钊以诗一般的语言赞扬青年:“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惟知跃进,惟知雄飞,惟知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敏锐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注:《李文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陈独秀得出下列结论:“青年如初春,如朝阳,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予所涕泣陈辞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奋斗耳。”(注:《青年杂志》1卷1号。)
“五四”领袖还以进化论为武器进一步论证青年的作用。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曾这样论述他之所以寄希望于青年的缘由:“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这样,青年期的特质就成为社会盛衰的座标。而李大钊的《青春》一文,更是一篇用进化论论证青年作用的杰作:“俾以青年纯洁之躯,饱尝青年之甘美,沐浴青春之思泽,永续青春之生涯,致我为青春之我,我之家庭为青春之家庭,我之国家为青春之国家,我之民族为青春之民族”,如果让青春占据社会主体地位,“地球即成白首”,亦可以“虽老犹未老也”。
对青年的现实价值作如此肯定,“五四”领袖们必然重视青年的现实作用,必然把发挥青年的现实能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反过来又强化了青年的社会参与意识,它必然导致青年对陈独秀等领导的“五四”的热切向往。
三
挟着社会化欲望的青年之参与“五四”,引发了青年与“五四”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青年是“五四”的青年。“五四”不仅为青年社会化提供了广阔的训练场,而且在各方面规定着青年的行为和主张,从而也决定了青年社会化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程度。但在另一方面,“五四”又是青年的“五四”。因为青年是运动的主体,“五四”就不能不充分重视青年的各种愿望和要求,不能不把保证青年的社会化作为其重要的历史使命。从青年的本质来看,自然性、社会性和实践性是青年的本质属性。在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中,自然属性急剧变化,社会属性日趋成熟,而实践性则不断完善。这些特征,必然会因为青年在运动中的主体作用而折射到运动中,使其跌宕多姿,异彩纷呈。从这一角度而言,“五四”运动必然会凸现出青年性的特征。其具体表现在:
首先,“五四”青年的社会化水平标志着整个运动的发展水平。“五四”的运行过程和青年的社会化过程是互为因果,相互制约的。随着形势的发展,青年和运动都走向成熟。笔者认为,这个过程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15年至1917年。在该阶段,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启蒙,体现在青年的实践上,就是追求人格的平等和解放,冲破束缚和强加在青年身上的封建枷锁。尽管青年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自然属性仍占主导地位,在政治批判和个性解放的双重使命中,后者的成分更为突出。他们的行动仅仅停留在个人的自发奋斗上,还没有形成一定的组织,其个性品质表现得极为汪洋恣肆。这样,它既使整个运动表现出荡涤一切的气概和一往无前的精神,但也因此跌宕无常,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
第二阶段是1917年至1919年,运动的重心转向价值理念的重建。引入新思潮,确定时代真理是社会的一致要求。表现在青年群体上,就是从个体反抗方式转换到自发地相互联系,通过组成团体,追求真理和实践某种理想。他们开始把本身的社会化过程自觉地和社会改良结合在一起,其社会属性大大增强。但与此同时,青年的自然属性仍占很大比重。体现在运动上,就是诸子峰起,具有盲目性和空想性。
第三阶段是1919年至1921年。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历史进入了建党的新时期,“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2页。)在该阶段,青年的社会化步伐明显加快,其思想和行为逐步染上鲜明的理性色彩和自觉成份。他们终于意识到:在黑暗的政治条件下,个体反抗并无出路,群体理想的构建肯定失败,娜拉即使出走,最终也只能回到旧规范的怀抱,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斗争,先去改变黑暗的社会现实,青年自身的真正解放才有可能。“我从此觉悟,要拿工读互助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改造社会要用急进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之改造”。(注: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2页。)先进青年纷纷放弃对所谓人格自由的追求,直接投身于政治斗争,自发的个人斗争转化为自觉的政治行为;青年团体的组织形式也从松散狭小发展到严谨和更具广泛性。于是,社会属性成为青年的最本质属性,青年的社会化完成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其二,青年的参与使“五四”运动以空前激烈的姿态出现,并使其急速地向前行进。
运动选择了青年,而青年则以其鲜明的自然特征使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综观“五四”全过程,青年对传统的排斥,对新事物的勇猛追求,其态度之鲜明,行为之激烈,决不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所能达到的。正是青年的勇猛精进,使“五四”呈现出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壮丽景像。
“五四”青年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实践性。他们不仅通过办报刊、写文章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勇于把自己的行动迅速付诸实践。他们在陈独秀、鲁迅等人的号召下不仅用激烈的言辞痛骂孔子,张扬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些主张变为实践行动。他们突破剪发禁令,要求男女同校,为恋爱自由而抗婚出走乃至自杀。他们组成同气相求的小社团,为国家为民族的前途而奔走呼号、勇于探索。他们并不满足于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作绝望的反抗,而是为着追求理想而上下奔波。“五四”青年的实践性品格正是“五四”运动有别于其他运动的重要标志。
青年的自然属性和实践性,决定了青年必然迅速地实现其行为模式的转换——从家庭出走的个性反抗转换到组织志同道合的社会群体,再一变而为积极参与严肃的政治斗争。它也决定了社会整体的方向性选择如风驰电掣,短短的几年之间便走完了西方经过几个世纪才完成的思想行程——越过实用主义等资产阶级唯心哲学,抛弃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迅即向科学社会主义逼近。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认为,“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其三,青年的参与在另一个方面也导致“五四”运动出现了非理性特征。
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0页。)青年的积极参与,固然使“五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由于青年正值涉世之初,自然属性压倒社会属性,社会经验的磨炼、理性的积淀明显不足;再由于“五四”时期属于文化的真空时期,传统的社会规范体系轰然坍塌,而新的规范体系则尚未形成;更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和寻找中枢力量的迫切需要,“五四”领袖们对青年价值总是大力褒扬。他们认为,青年自然属性的凸现,是整个宇宙生生不绝的标志,是民族活力的象征,对之加以任何的规范和约束,都是错误的:“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残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注:《新青年》4卷6号。)他们对青年价值发挥所体现出来的非理性倾向,不是加以训诫,而是为之欢欣鼓舞。因此,在此背景下,当青年在尽情释放其现实能量时,运动非理性倾向的出现了就难以避免了。概略而言,这种倾向大约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表现为形式主义的倾向。简单地否定一切或肯定一切,是青年期特有的情感特征。无论是对传统的批判,还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吸收上,“五四”青年都出现了这种倾向,他们缺少一种辩证的、理性的态度。如在对待儒教问题上,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儒教无疑应该彻底否定,它和新思想的关系是“耶酥生而犹太灭,孔子生而吾华衰”(李大钊语)。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结构,其中又有合理的内核,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忧外患而终于能保存,儒教功不可没。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去伪存真、理性地扬弃。但是,以青年为主体的“五四”对儒教是全盘否定的。为了表示同孝道的决绝,便宣称“我不再认你作父亲,我们都朋友”。为了体现婚姻自由,于是“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诸如此类的现象屡见不鲜。这在一方面表现了青年片面的深刻性,而在另一方面,也导致深刻的片面性。否定一切并不能达到批孔的目的,它反而成为林琴南等复古派攻击新思潮的口实。
二是表现为各种社会思潮纷涌,难以整合的局面。青年期的特质,使“五四”青年乐于接受新事物,喜欢标新立异,又自以为是,具有广泛的可接受性。而出身和地域的不同,又使“五四”青年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出发来接受新事物,以至“五四”成为各种思潮风起云涌的时期。如以社会主义思潮为例,一时之间,“除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修正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主义以及合作主义。”(注:丁守和:《中国现代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页。)勇于发表独立见解,本是青年的突出优点,但他们又往往具有极强的排他性。“五四”各种思潮之间的大论战,一定程度上便是这种特性的反映。综观这些论战文章,缺少的是理性而中肯的批评,多的是情感激烈的发愤之辞和简单的定性判断,这就使争论本身带有极强的感情色彩。青年的这种强烈情感往往又是很不稳定的。正处于世界观形成时期的“五四”青年,身上常常会同时兼有若干思潮的特征,或者曾经先后信奉过一些彼此对立的思潮。各种思潮处于剧烈的分化和动荡之中,绝大多数思潮的命运也就因此确定——各领风骚三五天。它也影响了青年本身社会化的顺利发展,许多青年在热情退潮之后出现的迷惘,便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