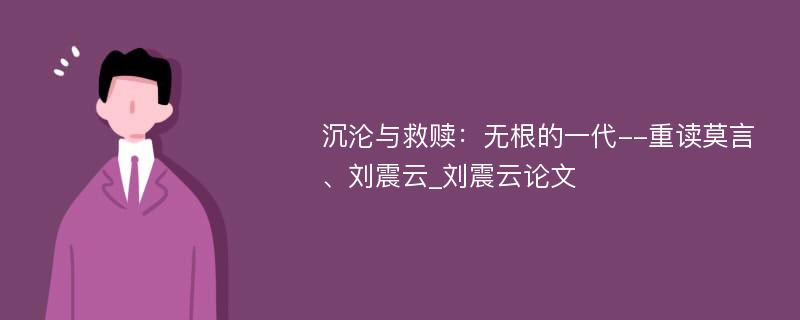
沉沦与救赎:无根的一代——重读莫言、刘震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刘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写下这个题目我也颇觉突兀。
莫言、刘震云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两人在叙述风格、结构规则、语言基调等方面都非常不同。莫言诡秘神异,刘震云质朴素净;莫言以鲜活奇谲的艺术感觉结构着“高密东北乡”的神话世界,刘震云则老老实实地给你讲着“大荒洼”发生过的和发生着的事情;莫言忧郁而痛苦、愤怒而激昂,刘震云平静而冷峻、轻谑而幽默。从各方面讲,两人都颇难默契,评论界很少将两人相提并论是不无道理的。
但仿佛是出于某种直感,我仍写下了这个题目。读莫言、刘震云时,我始终没能摆脱一个感觉,总像有个影子徘徊于房间的四壁,他时不时的就从莫言、刘震云身后站了出来。这影子就是《人生》中命运蹇促的高加林,小说中故乡人奉送给高加林一句俚谣:“哥哥你不成材,卖了良心才回来;”我想,倘若命运留给高加林的夹缝再稍略宽裕一点,他未必就“不成材”,未必就不是莫言、刘震云。重读莫言、刘震云时,烙着“高加林”印迹的一代人从我脑中清晰地浮现了出来。这是生长于贫困与荒凉的一代,这是激烈反抗着祖祖辈辈农民悲剧命运的一代;他们期冀过,抗争过,诅咒过,挣扎过,他们沉默了,沦灭了,堕毁了,消失了。刺激着我的想象的不是莫言、刘震云所叙述的这样一代人的具体生活,而是在他们的叙述中所奔涌的相似的仇恨、愤怒与痛苦的情感;这类精神特征只能出自这样的一代。这一代人大都出生于50、60年代的农村,在困难时期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而恰巧又在动乱结束、经济复苏的70、80年代之交赶上了人生的青年阶段。置身于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交叉地带”,他们强烈渴望摆脱农民屈贱的生活地位及其困顿的生活处境,但既无“平反”之殊遇,又无“返城”之资格,他们不得不和社会发生实力殊绝的直接冲突并注定要承受难以摆脱的人生悲剧;幸运者永是极少数,“不成材”者们唯可得到的是故乡人的谴责,德顺爷爷责备高加林说:“加林啊,我从小亲你,看着你长大的,我掏出心来给你说实话吧!归根结底,你是咱土里长出来的一根苗,你的根应该扎在咱的土里啊!你现在是个豆芽菜!根上一点土都没有了,轻飘飘的,不知你上天呀还是入地呀!”这段话准确地反映这一代人典型的精神特征:无根。在颓败而荒凉的土地上,“高加林”们是一群不屈的苦痛的游魂;我曾经想,倘若这一代中的某些个人偶或幸运摆脱了农村,当他们重新返观故土,尤其是当他们以作家,以灵魂追问者的姿态重新返观故土时,那么,他们会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境中书写、叙述这一代人以及土地的故事呢。
莫言、刘震云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作为“无根的一代”的幸运者和代言人[①],他们既在创作中体现了这一代人具体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验,又和“五七族”、“知青族”一样,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当代文坛上一个独立的创作群体。[②]遗憾的是,莫言、刘震云作为“无根的一代”的深刻意义似乎至今尚未被人注意。以前罗素撰写《西方哲学史》时曾叹息道:“颂扬柏拉图——但不是理解柏拉图——总归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人物的共同命运”,现在看来,平常之如莫言、刘震云,又何曾逃得这种命运?身为“无根的一代”,莫言、刘震云的创作倒底表现出怎样的精神结构和存在形态呢;还是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我把两人创作基本的精神特征归纳为:沉沦与救赎。
1992年,山东人张炜在僻静的登州海角写道:“在漫漫夜色里,谁在长思不绝?谁在悲天悯人?谁在知心认命?”
无根之思:沉沦的土地
重读莫言、刘震云这十四年(1982——1996)来的小说,我惊讶地发现,有一种强烈的情绪,或肆虐奔涌,或潜流旋洄,或直接作为表述对象,或间接作为情感基调,存在于其中。这种情绪就是仇恨。仇恨并非一种新的情感形式,但它在莫言、刘震云小说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作为情感核心,影响着、决定着作品整体的结构形态和存在方式。相比较而言,这种情绪在莫言小说比较直露,尤其是1987年以前的创作,甚至爆发渲泄直如火山的喷吐,这样的作品主要有《枯河》(1985)、《爆炸》(1985)、《筑路》(1986)、《欢乐》(1987)、《红蝗》(1987)、《天堂蒜苔之歌》(1988)[③]在中篇小说《欢乐》中莫言借一农村青年之口表示道:“我不赞美土地,谁赞美土地谁就是我的不共戴天的仇敌;我厌恶绿色,谁歌颂绿色谁就是杀人不留血痕的屠棍。”这种憎恨故土的情绪在刘震云小说中表现得比较平缓、隐蔽,一般是裹藏于冷峻或愤激之中,“我的故乡……没有任何让人心情兴奋的地方”,“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④]表现这种印象的作品主要有《头人》(1989)、《故乡天下黄花》(1991)、《故乡相处流传》(1992)。无论是出于情切义愤的渲泄,还是出于平静蕴藉的叙述,仇恨情绪在内涵及缘起上并无本质的差别,它如潮水般漫过了莫言、刘震云的小说群落,或骤或缓,有力地淹没了那些泛着盐硝的荒野土地,以及土地上世世代代活动着的人群。这种奇怪的情形使我想起一篇先锋小说中的句子:
我沉浸在一种疲惫不堪的仇恨之中,我的经历似乎告诉我唯有仇恨是以一种无限的方式存在着的(孙甘露《我是少年酒坛子》)。
这一代人承受了过分沉重的历史和宿命的现实的人生。我们能够理解生的苦痛及其创伤情境之于这一代人仇恨情绪的关系,但现在更重要的是,我们又该如何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仇恨之于莫言、刘震云创作的关系,换言之,肆虐奔涌的潜流旋洄的仇恨使莫言、刘震云小说以怎样的方式存在着呢。我以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他们此种状态中的小说:无根之思。这是“沉沦”状态中的小说。
在这里面,“根”是从存在的角度指谓普遍意义上人类生存的永恒根基以及个体生命的本源,对于莫言、刘震云这代“地之子”来说,根就是土地,就是他们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土地”与根具有相同的语义空间,它在作品中虽不脱离极具体的经验背景,却主要系指一种价值世界,指涉着生命获取自身意义和存在本质的本原。所谓“无根之思”是指莫言、刘震云的“诗”缺失了必要的根基而沦为“思”;具体些讲,在莫言、刘震云小说中,由于人的背叛,由于仇恨情绪的潜洄奔涌与无限延展,象征的“土地”逐渐沦失了其作为人类生存根基的“意义”,缓缓没入无边的冥暗。“人实际上不过是一棵会移动的树”(张炜《融入野地》),人怎么能够背叛祖先的土地?背叛即意味着罪恶,意味着生命在冥暗中的沉沦。初读莫言、刘震云时,我并不清楚也未曾去想“无根”给他们带来了或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唯一清楚的是,这种小说存在形态在这一代人而言丝毫没有偶然的因素。1993年,莫言这样说起过自己:
十五年前,当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高密东北乡贫瘠的土地上辛勤劳作时,我对那块土地充满了仇恨。它耗干了祖先们的血汗,也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当时我曾幻想: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决不会再回来。所以,当我坐上运兵的卡车,当那些与我一起入伍的小伙子们流着眼泪与送行者告别时,我连头也没回。我有鸟飞出了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儿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⑤]
飞翔之鸟与沉没之土地,成了人与“意义”(生存根基)相互离析的象喻图景。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作为Dasein[⑥]的“人”,作为本源意义的“人”,必然会因为“意义”的析离而失去了“人”的本原,“人”的“家”。这种析离必然使莫言、刘震云沦为无“家”之“人”,陷入无根的焦虑。事实上,这一代人大都与土地若即若离,对土地的感情相当复杂,他们大都是故乡宽阔的土地上游动着的魂灵,郁积着愤懑,飘来荡去,永无居留的所在。重读莫言、刘震云时,这种种图景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两人作品中所展开的“土地的沉沦”过程中。
浸淫着仇恨的土地在莫言小说中失去了自然的春华秋实的循环,而退化为生命悚目惊心的荒野,压抑窒闷,旷冷荒芜,如黑沙滩(《黑沙滩》),如苍白的河滩(《透明的红萝卜》),如枯冷的河道(《枯河》),甚至麇集着世界邪恶的力量,如暗红色的淤泥(《红蝗》);这生命贫乏的荒野又笼罩着一片荒凉苍犷的气氛,《枯河》中“百姓面如荒凉的沙滩”,《白狗秋千架》中“狗眼里的神色遥远荒凉,含有一种模糊的暗示”,《透明的红萝卜》中“女人们脸上都出现一种荒凉的表情,好象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土地”在荒凉中只能走向沉沦,“意义”在贫乏中只能日渐泯灭;莫言通过对乡村沉重苍凉的人生把握住了这种过程。在莫言那些泛着苦涩的白光的土地上并非没有“意义”,相反,“意义”在整体的荒凉背景上显得异常鲜活、突兀,并使其所附属的个体灵魂不安地颤栗着,只是这种“意义”最终无法走脱沦灭的结局;莫言的“沉沦”即在于他反复地不遗余力地突出着乡土生活中“意义”的沦灭过程,为此,他较多地采用了个体灵魂在群体社会中遭受扭曲、变形乃至毁灭的叙述视角。《透明的红萝卜》是莫言最见才华的作品,其中出现了一位光着脊梁、从不说话的男孩儿,他的异乎众人的行为明显负载着世界的“意义”:
黑孩的眼睛本来是专注地看着石头的,但是他听到了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用力地捕捉着,眼睛与耳朵并用,他看到了河上有发亮的气体起伏上升,声音就藏在气体里。只要他看着那神奇的气体,美妙的声音就逃脱不了。
男孩儿悒伤、颤栗、梦幻般的情绪深刻地唤起了曾经有过孤寂的童年农村生活的莫言灵魂里的回响,他在寻找并守护一个鱼群和声音的世界,他帮助着他。这个世界流动旋转于土地之上,饱含着生命的“意义”,男孩儿拒绝语言也拒绝着卑陋荒凉的人世,独自徜徉于美、善和爱的自然世界。但结果竟是这样:
黑孩儿钻进了黄麻地,像一条鱼儿游进了大海。“意义”是保留了,但却是以决绝人间世的方式;在人世现实的土地上,“意义”终是永远地丧失了。类似过程在莫言小说中屡屡出现。倘若我们能够理解莫言对于人的存在的感知方式:“悲剧是世界的基本形式”(《爆炸》),也就自然能够理解“沉沦”一词在他小说中的普遍的意义。土地上生活着的人们,如承受不了人生正常欲望的杨六九(《筑路》),如被绝望与痛苦压垮了的青年农民永乐(《欢乐》),如追踪着灿烂红花而去的小福子(《罪过》),如为自己所击败的复仇者(《复仇记》),或发疯,或死去,或囿于宿命的人生困顿不堪,无不如此陷入“沉沦”的黑色景象。在莫言的叙述中,土地逐渐隐匿了自身的“意义”,存在呈现为不透明状态,人无法栖居于其中;这种叙述与理解悄悄瓦解着莫言自身存在的根基。
这一代人眼见了过多的沉沦,以至于刘震云完全抛开了莫言式的敏细忧郁,他根本不去展示“意义”逐渐泯灭的过程,而直接撕开了世界无意义的本相,根本不去关注个体灵魂的飞扬与坠落,[⑦]而直接透解了土地人群整体沉沦的悲剧。从《新兵连》(1988)、《头人》到《故乡天下黄花》到《故乡相处流传》,刘震云所叙述的人与土地,无一例外都是“无意义世界”,关于这一点已有论者指出,“刘震云的眼光太毒,看得太透”,“他是从比平常的高度更低,并且尽可能低的层面看历史、看现实、看人生的,不料想从更低处看,却看出了更多的破绽和真相。”[⑧]观其最优秀小说《故乡天下黄花》之结尾可见刘震云“看”的功夫:
一年之后,村里死五人,伤一百零三人,赖和尚下台,卫东卫彪上台。……“文化大革命”结束,卫彪、李葫芦下台……一个叫秦正文的人上台。五年之后,群众闹事,死二人,伤五十五人,秦正文下台,赵互助(赵刺猬儿子)上台。
这一“看”就看出了世间万事的本相,所谓“历史”不过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世界有什么意义?人生有什么意义?生与死又有什么意义?世间万事的真相即在于它的无意义。矗立于土地之上主宰着历史的,仅是一种巨大的权力结构;在刘震云的“无意义世界”里,所有具体的人、事、物,所有基本的人性人伦,都以简约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作为权力的附生物而存在,仅因服务于权力的更迭交替而有意义,而这唯一的意义却被作者“看”出了无意义。刘震云的绝大部分小说,包括《单位》(1989)、《官场》(1989)、《一地鸡毛》(1991)、《官人》(1991)一批“准故乡小说”,都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权力叙事”。这一“看”还看出了距离,人与土地在对立性对象性的“思”中相互离析;经验的土地成为思维主体理性观照的对象,被认识,被反思,被批判,而象征的“土地”也相应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较之莫言,刘震云的“土地”更显灰黯、鄙陋,完全沦为非生命非存在的场所。
诗意消失了,鸟高翔着,土地沉没了,人与“意义”完全离析开来;这里面的原因,既有这一代人生存经验的自然支配,又有他们离开故土后所接受的现代理性(认识、反思、批判)提供了强大的逻辑依据。莫言、刘震云的大部分创作,即那些表现乡村中国荒凉人生与病恶人性的作品,都是在这种逻辑的支持下完成的。但是,人的生存不可能完全建立于纯粹理性的基础之上,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有着比理性及其要求更高的东西,这就是情感;情感本身才是人的全部生存赖以建立的基础。莫言、刘震云固然可以诅咒土地批判土地,但他们真的可以长期停留于“无根”和“沉沦”的状态中吗?其实,“无根”毕竟只是一种表象化的描述,但作为社会的文化的存在,人无法拒绝、更改或忘却其为“人”之根,事实上在最深的情感经验里,这一代人仍无以摆脱对于根与“土地”的认同感、依归感,“我总觉得我的故乡有些可怜。我嫌弃它,又有些忘不了它”,[⑨]“对于生你养你、埋葬着你祖先灵骨的那块土地,你可以爱它,也可以恨它,但你无法摆脱它。”[⑩]根系于人类辽远的文化经验(乡土意识),“自人类有乡土意识,有对一个地域、一种人生环境的认同感之后,即开始了这种宿命的悲哀”,“对于‘忘却’的原始性恐惧,对于忘却本原,忘却故土,迷失本性,丧失我之为我的恐惧……是农业社会人们的普遍心理。”[(11)]因了这样两种相对立的精神趋力,联系着生存经验的现代理性和蛰伏于生命意识的原始恐惧感,莫言、刘震云无法逃避两难的尴尬:诅咒着土地却又植根于它,背叛着土地却又不敢承担“忘却”的恐惧。怵怵于土地的荒凉却又同时失掉了存在的家园,人之所遇的困境恐怕再也无过于这样一代了。
当代著名哲学家E·贝克在人身上要把世界诗化(to poetize reality)的原始动机,这种动机是“我们有限生命的最大渴求,我们的一生都在追求着使自己的那种茫然失措和无能为力的情感沉浸到一种真实可靠的力量的自我超越之源中去。”[(12)]背叛了土地,莫言、刘震云还能够找寻到这样一种可以沉浸其中的“真实可能的力量”吗?对这一代人来说,他们必须建立与一种诗化的整体世界的联系,而这联系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世界的敞亮。踯躅于沉沦的荒野,这一代人愈来愈清晰地感受到了一种质问、一种召唤,一种从辽阔、宽厚的大地下面传达出来的声音:“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却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海子《答复》),恓惶的地之子们,怎能面对大地这穿透灵魂的“神秘质问者”?这样的体验不能长久:
我站在太阳 痛苦的芒上
乡间精神:自我的救赎
长久地沉浸在这种灵魂撕裂的生命体验很可能会超出生命所能承受之限;莫言、刘震云还不是那类能够洞彻、追问人之生存困境的作家(这类作家在中国向来极为少见),他们需要自我救赎,化解自身所遇的精神困境,变无根的恓惶为诗意的栖居,变“思”为“诗”。莫言、刘震云从哪里构筑这救赎之路呢?在《人生》中高加林最终“返回”了故乡:
高加林一下子扑倒在德顺爷爷的脚下,两只手紧紧抓着两把黄土,沉痛地呻吟着,喊叫了一声:
“我的亲人哪……”
这一代人的自救注定了要通过土地来完成;具体说来,就是要在沉沦的土地上显现“存在”,要在荒凉的人生中呈明“意义”,凭籍“意义”的充盈使土地还原为可供栖居的家园;这样的救赎之途实际上就是“返回”,从沉沦的荒野“返回”到疗阔、宽厚的大地。
纵观莫言、刘震云的全部创作可以发现,自我救赎的内在冲动在很早就已表现出来,或有意为之,或因潜意识而成,几乎都是自始至终贯穿于他们的创作。两人作品也可以因此分成两个同进并存的大的系列:“沉沦”系列与“救赎”系列;两个系列时有交错,大致说来,后者在数量上要少一些(尤其是刘震云)。两人具体的救赎方式非常接近,莫言虽然常常通过自然“返回”土地,如染成血海的红高粱,但这类自然意象总是附属于人的存在境况的表现,并不能自在自足;真正在莫言、刘震云小说中起着救赎作用的,主要是一种蓄蕴于民间的自足的生存精神,这不是“按住万物突突的脉博”(张炜《融入野地》)的“土地精神”,而是土地上生生不息的人的精神。莫言在《丰乳肥臀》(1995)封面题辞“谨将此书献给母亲与大地”,清楚地反映了他们通过“人”重返土地(“意义”)的救赎冲动。莫言在个体生命中找到了生生不息的精神:
曲调很古老。节拍很缓慢。歌声悲壮苍凉。坦荡荡的原野上缓慢地爬行着爷爷的歌声。空气因歌声而起伏,没散尽的雾也在动……我感到陡然间长大不少,童年时代就像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大风》)。
短篇小说《土塬鼓点后》(1992)是刘震云作品我极为看重的一篇;[(13)]它以散文的方式叙述了一个人的死和一群人的欢乐,在这篇小说中刘震云借助群体生活凸现了同样的生生不息之精神:
这时土塬响起了激烈的鼓点。一开始是一点,后是两点,三点,后来成了密集的鼓点;混乱之后,成了整齐雄壮的威风锣鼓。……我们甘愿沉浸在这音乐中,去生,去死,去随这音乐的吹奏者爬过一道又一道高山,一座又一座的土塬,趟过一道又一道的冰河,看遍一山以一山的漫山遍野的灿烂的花朵。
“沉浸”,是一种生命的沉迷状态,是感性个体溶浸在整体的生活世界之中的状态,莫言、刘震云所陶醉的是一种勃郁、凝重而又流动不止的精神。我把这种民间的自足的精神称为“乡间精神”。它是作家对土地的诗化,也是土地敞显出来的“意义”,它把土地重新变做了“意义”的渊薮。莫言、刘震云正是借助这种精神“返回”故乡从而完成自救的。
这种诗意的乡间精神主要表现于这样一群普通中国农民身上:爷爷(《大风》)、老铁匠(《透明的红萝卜》)、罗汉大爷(《红高粱》)、母亲(《丰乳肥臀》)、金鼓手奎生及其乡党们(《土塬鼓点后》)。余占鳌式激昂高亢狂放奔涌之自由精神,我以为,并不接近乡间精神(后面将论述到)。下面我想集中分析一下乡间精神的内涵与表现。
乡间精神意味着民族生活的某种本质,这本质变形地呈现于《欢乐》的一个句子中间。在生命接近疯狂、崩溃的极端体验中,“本质”以记忆积淀的形式突破日常表象而浮起:
你下沉,欢乐地下沉;周身如刀割,刀割般地欢乐地下沉。
在这里,痛苦与欢乐相济相生,瞬刻爆发的感性欢乐里凝聚着变形的苦难经验。我以为,乡间精神指称的正是一种融合着现实/历史逻辑理知内容与诗意感性生命形式的民族/个体生存精神,一种理性内涵与感性形式完善融合的审美生命境界;它饱含着民族生活的全部诗意,照彻着莫言、刘震云小说的冥暗与荒凉。乡间精神中苦难与欢乐相互浸溶的生命内涵是以静/动互补的外在生活方式表露的,《土塬鼓点后》巧妙地把《欢乐》中的变形本质还原到日常生存状态中来了:
问:这里时常阴天吗?
房东大哥:阴天好哇,阴天可以不下田,在家睡觉。
问:村里热闹吗?
房东大哥:热闹好哇,热闹红火。
“睡觉”守静,“热闹”主动,静动互补阴阳相济,这就是我们民族自足的生活方式。静中有动,在沉抑的苦难人生中迸发出激越的欢乐,动中有静,于生命的冲动、渲泄中又渗进着苦难之体验;静动浑一,苦难、欢乐融合无间,生命意志亦趋于极致。循沿着此一普遍生活方式的一群普通中国农民集中表证着民族生活的此种本质。一方面,他们在对灾难、厄运的长期静态承受中渴求着感性“动”的欢乐,而这欢乐反过来又贯注给“静”以坚韧生命力。艰难生计操劳之间“苍凉悲壮”的歌唱,冗闭、窒抑生活中的“热闹”和“红火”,土塬上急骤热烈的鼓点使人沉醉的唢呐,都是“静”中“动”的涌动、嚣扬;这种涌动以罗汉大爷的行为性格表现最为典型,大静,大动,是罗汉大爷完整的性格逻辑,沉默、温驯、忍气吞声,愤怒、仇恨、爆发,两类绝然相反的性格行为奇特地集中于同一感性个体之上,在他铲杀黑骡、在他惨遭剥皮怒骂不止的瞬刻,感性生命以极端的形式升腾起来,闪耀出我们民族在静态忍耐中所禀有的血烈之性与刚强生命力;包含于日常静态生活中的“动”,是人们用以照彻现时苦难沉入审美生命境界的特定方式。另一方面,感性欢乐的渲泄因有理性或明或暗的制约总只能呈现为瞬刻状态,汹涌嚣动之后即是静默无声。老铁匠唱完凄凉沉郁颤人心弦的戏文,“只是慢慢地站起来”;爷爷一结束歌唱,便马上回复到散文化的状态:“瞎唱呗,谁知道它是什么……”奎生吹完激越、嘹亮的唢呐后,也只是坐下,“默默不语地抽着自己的香烟”;所有“动”中皆有“静”,皆有民族/个体苦难经验的积淀,皆有智达民族对于历史、命运的深刻理知,这使人们日常的感性欢乐都禀有了深厚的理性涵质。这些几乎相近的性格特征都内在地沟通着民族某种精神原型:静中见动,动而归静,于困乏的生活中抗争不止,在激情的渲泄又保持节制,于命运的静态承受中包孕着强烈的生命激情,在激情外化的同时又饱含了历尽沧桑的人生体验。这就是乡间精神所指涉的民族生活的内在“意义”。
当爷爷、老铁匠、奎生这样一群普通中国农民,以与父亲(《枯河》)、杨六九(《筑路》)、老肥、李上进(《新兵连》)、孬舅(《故乡相处流传》)等截然相反的形象,出现于莫言、刘震云的乡土世界中时,一种平实而坚韧的生存精神便充盈了土地,而被对象化的“思”所遮蔽的“意义”也缓缓敞显出来。乡间精神回荡于土地之上,使之变得诗意盎然,它连接着我们民族深久的记忆和流动的现实;在“沉沦的土地”之外,诗意土地又构成了一个自足完整的意义世界。这诗意土地与一般知识者的诗化“乡土”颇有不同。“知识者的‘乡土’通常出于精神制作,它本是不可还原,不可向经验世界求证的”,[(14)]而出于无根一代的自然经验,莫言、刘震云的诗意土地却可以还原至乡村生活的原生真实,与土地有本质的联系,其中包涵着民族生活苦难与欢乐的真实,浸溶着由苦难、欢乐共同生发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一般知识者的诗化往往割裂苦难/欢乐,在苦难/欢乐的对立中偏重于欢乐的表现,并以欢乐掩饰、冲淡苦难;所以,相比较而言,知识者的诗意“乡土”很难以其内在深刻的力量救渡土地之外的沉沦者、漂泊者,一旦知识者发现这“乡土”的虚幻性、无根性,便会再度沦落、漂泊,而莫言、刘震云的诗意土地却充盈着民族伟大坚韧的生存精神,“真实可靠的力量”通过土地源源贯注于沉沦者的精神空间,并把他们从“遗忘”中召回,恢复人之为人的本原;沉沦者重新亲近了土地,土地也重新成了人之存在家园。通过这诗意充盈的土地,莫言、刘震云重新找寻到了生命的根基,与“意义”遭遇。
当然,除乡间精神外,无根一代也还有其他的救赎方式,比如出于知识者思维方式的(无根一代本来就兼有知识者与地之子双重身份),莫言“红高粱系列”即属此类。余占鳌式杀人越货纵横江湖的匪霸生活不但多有精神制作的特点,难以求证于本真的民族生活(比照于《故乡天下黄花》即显而可见),而且割裂苦难/欢乐,抑苦难而扬欢乐,废静而主动,悖于民族积淀的精神原型,其自由抗争精神实际上是生命意志力的狂肆。这类救赎作用只能是暂时的,莫言后来谈起《红高粱家族》时颇觉“悲哀”,认为对于历史和祖先的“添油加醋”不仅虚幻,而且“很阿Q的”,[(15)]语虽自嘲,却也不乏一二真实。真正救助莫言、刘震云“返回”故乡,接近“人”之“家”的,仍是流转于颓败、荒凉土地上的乡间精神;它生生不息,启示着人的根性,莫言、刘震云即在其诗意的照彻中由沉沦的荒野“返回”到了辽阔、宽厚的大地,由非生命的居所“返回”到了存在的家园。
十四年来莫言、刘震云,或怵怵于乡土人生的荒凉,或浸溶于生生不息的精神的宇宙,或恓惶于沉沦之途,或辗转于救赎之旅,形成了其作品奇特精神结构和存在形态;“沉沦”与“救赎”于其中彼此平衡着,映证着,而又纠缠着,冲突着,二者同时并存,相互限制,总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莫言的感受典型地表征着无根一代悖论式的存在境遇:“那个地方(按:指故乡)会永远存在下去,但我的精神却注定了会飘来荡去”,“飘来荡去”系指一种根于一地却又难以系于一地的精神境状,一种徘徊于“沉沦”与“救赎”之间的困惑状态;其实,在沉沦的土地与诗意的土地之间,莫言、刘震云怕只能是彷徨彳亍,不知己之所至矣。
注释:
①莫言1956年生于山东省高密县,1976年入伍离开农村;刘震云1958年生于河南省延津县,1974年入伍,1978年复员,同年考入北京大学离开农村。
②属于这一群体的作家很多,比如路遥、贾平凹、莫言、张炜、刘震云、周大新、阎连科、陈怀国以及海子。
③仇恨、愤怒、痛苦三种情绪在莫言小说中往往纠缠一处,但并非不可分辨。
④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文艺争鸣》1992年第1期。
⑤ ⑩ (15) (16)莫言,《我的故乡与我的小说》,《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2期。此文当作于1990年前后。
⑥Dasein本指一般具体存在,海德格尔把它用来专指“人”的一种现象学存在论的意义,这个意义,简单说来,是指“人”的一种主客、物我、思维和存在不分的原始状态。可以参见叶秀山《思·史·诗》一书。
⑦《塔铺》(1987)倒是例外,因而有些“温情”,作者本人对此是不甚满意的。
⑧张新颖,《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P131。
⑨刘震云,《〈塔铺〉余话》,《中篇小说选刊》,1987年第6期。
(11) (14)赵园,《回归与漂泊(关于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乡土意识)》,《文艺研究》1989年第4期。
(12)转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P32。
(13)刘震云习于以冷峻、甚至带有“黑色幽默”色彩的眼睛“看”世界,似《土塬鼓点后》、《塔铺》一类表现人之正面存在价值的作品是相当少见的。
标签:刘震云论文; 莫言作品论文; 故乡相处流传论文; 故乡天下黄花论文; 透明的红萝卜论文; 文学论文; 欢乐论文; 故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