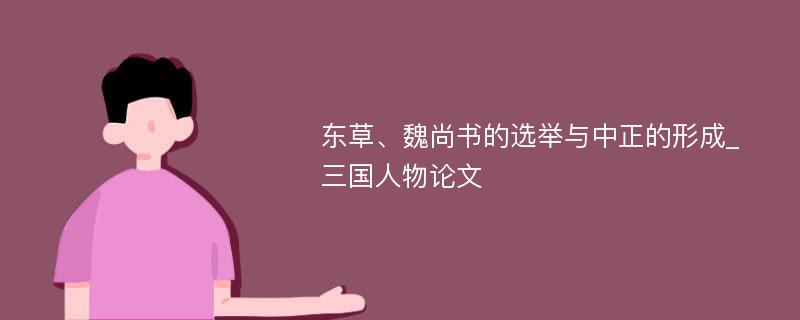
东曹、魏尚书的选举与中正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正论文,尚书论文,东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0)06-0077-06
学术界在对曹操统治时期选举问题的研究中,关注的焦点是曹操选举与延康元年(220)制定实施的九品官人法之间的关联,通常的做法是从九品官人法的制定时间和产生原因等方面,去找寻曹操选举的痕迹。但从曹操政权内已经具有制度化原型的选举方式出发,去看待当时的选举状况,及其对九品官人法的影响,目前还考察较少。本文就此角度,试做论述。
一
建安十八年(213)魏国建立前,曹操府中的选举运作存在着这样一种方式,即丞相东曹掾何夔所言:“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1](《何夔传》)之字面意义上理解,“受教并选”指的是“在朝之臣”要在曹操授意之下与东曹共同选举,“各任其责”则意味着在选举职能上二者各有侧重。
在这里,东曹作为公府中的选曹负责选举,是制度使然,《后汉书·百官志》“太尉”条中就有“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及军吏”[2]。建安时曹操为司空丞相,公府的性质没有发生改变,东曹典选依旧。具体来讲,曹操府东曹的选举主要负责官吏的任用。《三国志·毛玠传》中有“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1],举用是东曹选举时的措辞,这一点在《三国志·邴原传》中东曹掾崔琰对邴原、张范任官时所作出的评语中就表现得更为明显。崔琰语:“征事邴原、议郎张范……举而用之,不仁者远。”[1]其中邴原是由东阁祭酒徙署丞相征事,属府内官吏的升迁。张范则第一次为曹操所用,属未仕人才的任用。此外,《三国志·毛玠传》注引《先贤行状》中有“长吏还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车”[1],《和洽传》和洽对东曹选举的描述中也有“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餐以入官寺”[1],说明地方官吏的任用也由东曹全权负责。可见,东曹掌握了地方官吏、府内官和未仕人才的仕途命运。又由于以东曹掾毛玠为代表的东曹选举切实贯彻了曹操的选举思想,曹操对于东曹选举的意见一般不会加以变动,甚至赞赏有加,《三国志·毛玠传》中就有曹操这样的赞语:“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哉!”[1]这就使得东曹选举的意见成为官吏任免的最终结果。前引《先贤行状》中称:“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1]足见东曹在选举中的作用非同一般。
对于“在朝之臣”来说,“受教”则是其介入选举的关键。曹操的“教”在选举中一般起到了一个指向的作用,如《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列传》中就有“发教选邺令,当得严能如杨沛比”[1],可见,这种指向实则是对选才标准的具体规定。既然曹操在教中已经明确了要选拔怎样的人才,东曹又在任官环节上把关,那么,受教的“在朝之臣”要与东曹形成并选之势,其在选举中所能做的就是推荐与教中规定相符的人才。
曹操统治时期,选举中“由谁来推荐人才”的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一般认为曹操需要大姓、名士推荐他所需要的人才。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大姓、名士作了进一步的限定,提出“大族、名士且又身为中央官者”的概念[3],从作为支持这一概念成立的两个代表人物——荀彧和韩嵩的中央官身份看,建安时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韩嵩则是在刘琮举荆州降操后,被授以汉大鸿胪,可见所谓的中央官指的是汉中央官,这与“在朝之臣”还有一定的差别。我认为,建安时汉中央官能够推荐人才是事实,但随着曹操势力的增强,控制地区的扩大,汉中央官的作用不是得到了加强而是受到了削弱。以荀彧为例,由于荀彧在汉献帝身边,“旦夕谈论”[2](《荀悦传》),日久生情,“在君为君”[1](《刘表传》注引《傅子》),政治见解与曹操的分歧在加大,加之建安九年(204)曹操把自己的权力中枢移于邺,在许都的荀彧自此便在政治中无所作为了,更谈不上举荐人才。而曹操在长时间的军事征伐过程中,各地大族名士陆续被吸收入府,如《三国志·郭嘉传》注引《傅子》记载:“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渐臣使之,以为省事掾属。”[1]唐长孺先生就曾指出:“尽管曹操用人不拘一格,而所用之士仍以大姓、名士为多。”[4](P44)这造成了曹操府成为大姓名士集聚之所。曹操要选用人才,就不必再去借助远在许都的汉中央官。《三国志·王修传》注引《魏略》曹操在给王修的信中写道:“在朝之士,每得一显选,常举君为首,及闻袁军师众贤之议,以为不宜越君”[1]这是“在朝之臣”参与选举的一则实例,显然,以袁军师为代表的“在朝之士”,不是泛指汉中央官,而是曹操府内官。因此,仅以中央官来限定大姓名士有失宽泛,在汉中央官遭到压制的时候,何夔所言“在朝之臣”是大姓、名士,更为重要的他们是曹操府内官。
这样,在汉末名士与大族趋于合一,乡闾清议由名士主持的状况下,作为大姓、名士的“在朝之臣”在推荐人才上的优势不言自明。但在汉末人们避乱离乡流徙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乡闾清议是否会因“考详无地”而失去它的作用呢?应该看到的是乡闾清议要发挥它的作用,是人的问题,而不是乡里地域的问题。像史家经常引用的《后汉书·符融传》,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在京师“卧托养疾……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2]的例子,说明离开乡土的名士,他们的言论仍旧影响到了政府的选举。况且,建安时期曹操为了加强对臣下的控制,实行了“质任”制,内容之一就是将臣下宗族迁居于自己政权中心所在地,如《三国志·李典传》中记载“(李典)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1],就是指此而言。不仅如此,曹操对于地方上的强宗大族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三国志·梁习传》,梁习为并州刺史,“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1]。这就可能形成了各地大族在邺的聚居。在汉末人们避乱迁徙的大背景下,乡闾清议仍旧可以在各地强宗大族聚居于邺的环境中得到延续。只是这时的乡闾清议已不再是大姓、名士把持选举的工具,而成为官方的“廷议”。《三国志·郭嘉传》中陈群和郭嘉同为颍川人,陈群“非(郭)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1],《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中徐宣对于本郡陈矫“婚于本族”[1]的指责,是廷议其阙。这种由乡闾清议到廷议的转化,也就扭转了地方大姓名士把持选举的局面,有利于曹操对选举的控制。从这一点看,曹操应对“在朝之臣”推荐人才加以维护。
唐长孺先生基于曹操统治时期的选举提出了三个统一的问题,即“朝廷选举和名士月旦统一,朝官保举和乡里清议统一,入士徙移和核之乡闾统一”[4](P46),唐先生认为在九品官人法颁布之后,因郡中正的设立才使这一问题得到解决。而上文所言“在朝之臣”所具备的条件——身为曹操府中的官员,与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由现任中央官者兼任,是一致的。再者,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由现任中央官兼任,便于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这与“在朝之臣”作为大姓名士,所把持的乡闾清议已经成为官方的“廷议”,在作用上也是一样的。由此可以推断: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的前身是曹操统治时期的“在朝之臣”,即曹操府内官。
通过以上分析,何夔所言的“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可释义为:“在朝之臣”受教推荐人才,东曹则决定所推荐人才的任官与否。
但在这种选举方式中,由于“教”对人才标准作出了规定,其中也可能限定了任官名额,“在朝之臣”要使自己推荐的人才得以任官,东曹的裁定至关重要。于是,东曹就成了权门请托的对象,《三国志·毛玠传》中就有曹丕“亲自诣玠,属所亲眷”[1]。而东曹掾毛玠却是一个“刚蹇少党”[1](《桓阶传》)之人,在选举中“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1](《毛玠传》注引《先贤行状》),“在朝之臣”在选举中稍有超越法令之处,而想在东曹那里获得通融,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曹丕的请托遭到了拒绝,其理由就是因为所推荐之人“非迁次”,而建安十七年(212)曹操对府内选曹进行调整,却使“在朝之臣”看到了改善选举现状的一线希望。
二
建安十七年的选曹调整,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争议,人们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裁撤东曹保留西曹。理由也很简单,既然只能保留两选曹中的一曹,就按照惯例中两曹地位的高低来取舍,高者留低者去,听起来倒不失公允。但公允背后却隐藏着“(毛)玠请谒不行,时人惮之,咸欲省东曹”[1](《毛玠传》)的真实用心。这里的“时人”就是在选举中负有推荐人才职责的“在朝之臣”。
在与之相左,曹操不同意裁撤东曹。徐公持先生就此问题说,曹操采用了孟子的语言技巧,在《止省东曹令》中只言有关“东”的方位而不言“止省”的理由,这不能从道理上去推求,只能从气力去体味[5](P42),似未察曹操在此问题上的用意。
选曹调整是在曹操用兵关中之后,即《毛玠传》中所说“大军还邺,议所并省”[1]的时候发生的,是“并省”提议中的一个子问题,在用兵关中之后,北方已尽为曹操所有,这时提出“并省”,应与当时的政治发展相适应。在建安十七年年初,曹操再次得到了汉献帝的一份“恩宠”: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1](《武帝纪》)。这对于两年前刚刚向天下表露了心志的曹操来说,既然“人臣之贵已极”[1](《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为何又要接受这份画蛇添足的“恩宠”呢?恰恰也是在这一年,操府军师祭酒董昭提出了关于曹操晋爵国公的倡议,并遍访诸臣,大造声势,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默契:接受“恩宠”是曹操向群臣发出的自己要晋爵国公的讯号,而董昭的倡议则是在曹操授意下上演的指鹿为马的把戏。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所进行的“并省”,就不能看作是一次简单的机构精简,而是在曹操拉开建国帷幕前奏响的序曲,“并省”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为即将建立的曹氏国家政权做一番组织上的准备。
在曹操晋爵国公的问题上,群臣较少持有异议,也就意味着他们领会了曹操“并省”的意图。但在选曹调整上群臣所表现出来的意向——以职责范围仅限于“主府史署用”[2](《百官志》)的西曹来取代对全国选举负责的东曹,这会不会直接造成即将成立的曹氏国家政权中选举机构职权的弱化?对于曹操来说,这一点并不重要,因为要想增加西曹的选举权限,一纸授权令足矣。而在东曹裁撤后,“在朝之臣”在“受教与曹并选”中仍旧会因西曹的存在,遇到与东曹并选时相同的问题——被推荐人才能否顺利地得到任用,如果西曹同样秉公行事,那么,对于“在朝之臣”来说,保留西曹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看来,群臣要求“裁撤东曹保留西曹”还另有隐情。
《三国志·陈群传》中记载了建安初期陈群为司空西曹掾时负责选举的一则事例:“时有荐乐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还教,以为模、逵秽德,终必败,太祖不听。”[1]拿这则事例与“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做一下比较,一个显著的差异在于:前者中作为人才的推荐者不受“教”的约束,表现在乡闾清议上,那就是乡闾清议是独立的,放任的。人才推荐者向曹操推荐他们认为合适的人才,进而转化为曹操的选举意愿,并以“教”的形式直接作用于选曹,即便选曹对此持有异议,一般也不会改变任官的结果;而后者中“在朝之臣”作为受教者,要按照“教”中规定的标准推荐人才,乡闾清议成为政府选举的内容,“在朝之臣”在人才推荐上稍有逾越,就会在东曹那里遭到否定,任官就更无从谈起。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受教对象不同,选举结果就有着明显的差异,对于“在朝之臣”来说,他们又怎能割舍对前者的留恋而钟情于后者呢?而《陈群传》中的选举方式或许一直在沿用,前引《何夔传》“在朝之臣”语中,何夔还提到了“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1],其中“保举”大概指的就是这一选举方式。而在选曹调整之际,群臣突出了对西曹的拥护,不也隐含着用这种选举方式来取代与东曹并选的倾向吗?
曹操对此不会不有所觉察,他在《止省会》中只言“东”的方位,而不言“止省”的理由,就是要以方位这一无法更改的事实来告知群臣,东曹选举符合现实政治发展的需要,保留下来是必然的。在发布《止省令》后,曹操裁撤了西曹,这同样在喻示着东曹的选举方式不容质疑。
但新政权建立在即,“在朝之臣”推荐人才作为选举的基础,还需维护。他们在裁撤东曹上的意向,又不能不使曹操对“受教与曹并选”的方式作一番新的审视。审视后的结果,曹操采取了两项针对东曹的人事任免措施,一是将长期担任东曹掾一职的毛玠调离,委以右军师;二是缩短东曹掾一职的任职周期,从建安十七年“止省”东曹到建安十八年(213)十一月魏尚书台成立之前短短数月的时间里,先后就任东曹掾一职的就有2人,他们是:广陵徐宣、陈郡何夔。从这两项措施中不难看出,曹操有意要在“并选”中造就一个相对宽松的局面,着眼点则放在对“在朝之臣”在选举中权益的维护上。毛玠的调离,是为了消融东曹选举中刻板的一面,“在朝之臣”因“请谒不行”所形成的对东曹的敌视也会因此得到缓和。作为毛玠的继任者,徐宣、何夔皆为名士。徐宣曾为郡纲纪,这一郡中右职多为大姓所垄断,徐宣当是广陵大姓。何夔是车骑将军何熙的后代,何氏系陈郡大姓无疑。作为大姓、名士的东曹掾与“在朝之臣”之间,彼此都会增加一些认同。此外,在就任东曹掾前,二人势必是要经过“在朝之臣”的推荐,这是早期就追随曹操左右,长期执掌选曹的毛玠所不曾有过的体验,也正因为此,徐宣、何夔出任东曹掾,又有了体现“在朝之臣”共同利益,有助于“并选”完善的一层意义。
可是,毕竟时间太短,“并选”中的和谐景象尚未得到展现,魏尚书台就成立了,选举中也就融入了新的内容。
三
《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中记载了魏尚书台的人员组成:“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仆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1],其中五尚书毛玠、崔琰、何夔皆为原东曹掾,常林、徐奕为原东曹属,魏尚书台脱胎于东曹由此可见一斑。曹操以原东曹掾属充当尚书台的主体,注重的也应该是他们已经具有的选举经验。
关于尚书台选举,从理论上讲,五尚书要分曹办事,选举事务由吏部尚书执掌。从现有史料中可确知五尚书中有3人负责选举,他们是:毛玠、崔琰、徐奕。毛玠典选,见于《太平御览》卷214引《傅咸集》所言:“昔毛玠为吏部尚书”[6];崔琰,《三国志·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中称崔琰在尚书台中的职责是“魏氏初载,委任铨衡”[1];徐奕,《三国志·徐奕传》中有“魏国既建,(徐奕)为尚书,复典选举”[1]。洪饴孙大概也是以此为依据,在《三国职官表》中将这3人视为吏部尚书,而3人中究竟谁掌史部,可能有一个时间先后上的差异,但在这里区别吏部人选的意义并不大,因为魏国虽已建立,但曹操并没有称帝,从名义上讲,魏国还是汉的一个藩国,藩国官吏的任免权自西汉景帝以后就已经收归中央,这就使魏吏部要直接行使任免官吏的权力,还有一定的障碍。而魏国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取代丞相府,丞相府仍旧是事实上的中央政府,东曹还是全国性的选举机构,这样,魏国建立后在曹操政权内就出现了两个选举机构的并立,即东曹与魏吏部的并立。结合前文所述,可知东曹在选举中负责官吏任免,而魏吏部职权又不明朗,并且在魏尚书台中,除去上面揭示的毛玠等3人典选的事例外,尚书令也负有选举职责,《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中就有“荀攸后为魏尚书令,亦推贤进士”[1]。此外,尚书仆射也可典选,《三国志·毛玠传》:“魏国初建,为尚书仆射,复典选举。”[1]可见,“典选”并非吏部的专利。那么史料中所呈现出的这种魏尚书台成员的多元典选又作何解释呢?
前引《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在“魏氏初载,委任铨衡”后还有“总齐清仪”一句[1],“总齐清议”显然是对“委授铨衡”做出的诠释,指明了崔琰作为魏尚书的职责所在。这里所说的“清议”不难理解,它就是“在朝之臣”对所推荐人才发表的看法,有学者业已指出东曹掾属转为魏尚书,是“把丞相府选举官吏的一套做法全部照搬到魏尚书台来”[7](P149)。如果将这一思路进一步拓展的话,就会发现丞相府选举官吏的一套做法,尤其是东曹选举中,基于曹操需要形成的“在朝之臣”推荐人才。在魏国建立后,也不会发生改变,但从崔琰的职责看,这时“在朝之臣”的人才推荐已不再由东曹接受,而是魏尚书职责范围内的事了,“总齐清议”就说明了作为魏尚书的崔琰要接受“在朝之臣”的人才推荐意见,“总齐”大概还含有对人才推荐意见进行一番审核的意义。这就为曹操统治时期的选举增加了新的内容:魏尚书接受“在朝之臣”的人才推荐,审核后由东曹加以任官。之所以在选举中会出现这样的新内容,我认为是建安十七年曹操在东曹掾人事任免中体现的对“在朝之臣”选举权益维护的延续。
以建安十八年魏尚书台组成人员的乡里籍贯为统计指标,计有:兖州2人,冀州2人,豫州2人,徐州1人,这是在建安十八年初曹操废除东汉十三州代之以《禹贡》九州,尚书台组成人员的乡里籍贯在九州中的分布。而最初的魏尚书台人选,与此又有所不同。《三国志·杜畿传》中记载:“魏国既建,以畿为尚书。”[1]杜畿是京兆广陵人,京兆在九州中属雍州,但由于河东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曹操虽然已经发出了以杜畿为魏尚书的任命,最终还是决定让他留镇河东。又,《三国志·张既传》中记载的魏国初建之时张既的职官变动与杜畿的经历如出一辙,“魏国既建,为尚书,出为雍州刺史”[1],张既是冯翊高陵人,冯翊在九州中同样属雍州。这两则事例,可以反映出曹操试图以来自不同地域的官吏进入台阁,实现尚书台的广泛代表性。而尚书台成员最终以兖豫冀三州人士所占份额为多,与此意愿并不背离,它是曹操左右权衡的结果,其中可能也有“在朝之臣”推荐人选的因素在里面,否则前文所引《魏氏春秋》中记载的那份名单也不会在魏国建立半年后才迟迟公布,这也充分体现了曹操对“在朝之臣”实际构成状况的认识。在曹操政权中,像文官中著名的颍川谋士群体,武官中的谯沛集团,都来自豫州。另,兖州是曹操起兵之地,冀州则为曹操政权所在地,二州士人多有创业辅佐之功,他们也就成为“在朝之臣”的中坚。
因此,尚书台成员也就是“在朝之臣”的代表,而尚书台成员与“在朝之臣”之间也就可能形成了一种基于乡里地域的对应关系。在选举中,前文已经推断九品官人法中的郡中正源于“在朝之臣”,则“在朝之臣”为郡的代表;尚书台成员为“在朝之臣”的代表,在汉末州已经成为郡之上的行政区的情况下[8],尚书台成员则为州的代表。崔琰“总齐清议”就可以进而表述为:魏尚书崔琰作为冀州的代表,在选举中要接受来自冀州所辖郡的“在朝之臣”的人才推荐。这样一来,在魏国初建之时魏尚书台成员的多元“典选”,就应理解为:具有乡里地域代表性的尚书台成员的共同选举。这样做是对魏国建立前频繁更换东曹掾做法的完善,使分散的乡闾清议得以在尚书台内得到集合,尚书台俨然成为一个人才评议机构,这种共同选举避免了过去因东曹掾个人的好恶而引发的“在朝之臣”的普遍不满,变一人在任官问题上的决断为尚书台成员的共同协商,尚书台成员对相应地域推荐上来的人才做出的审核,想续而已,“在朝之臣”在选举中的权益会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据此,我认为魏国初建时的尚书台成员多元典选最终促成了九品官人法创立时州一级中正,即州都的设立。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是延康元年九品官人法的制定者陈群,时任魏尚书,曾在曹操统治时期担任过司空西曹掾、魏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等职,熟悉上文中所述东曹和尚书台选举的做法,存在着将这一做法在九品官人法中加以制度化的可能。
二是州都的选举职能,如《太平御览》卷265引《傅子》中所言:“魏司空陈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评次人才高下,各为辈目,州置都而总其义。”[6]州都的“总其义”是在郡中正已经做出的人才评价的基础上实现的,这与魏国初建时尚书接受“在朝之臣”的人才推荐,实现的“总齐清议”,在选举职能上是一致的。
三是州都由中央官兼任,而且在九品官人法初创时州都可能就是由尚书台成员兼任州都。关于这一点,就目前所见到的曹魏选举史料中还无法提供直接的证据,但孙吴模仿魏九品官人法所设立的大公平,由尚书台成员兼任却有迹可寻。大公平即曹魏之州都,《太平御览》卷265引《吴志》中说:“大公平,即州都也。”[6]《三国志·潘濬传》注引《襄阳记》中有:“襄阳习温为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后(潘)祕为尚书仆射,代温为公平。”[1]其中潘祕是做了尚书仆射后,才得以代习温为大公平,出现这一顺序大概是由制度造成的。即便是在晋朝,九品官人法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还可以看到州都大中正由尚书台成员兼任的事例。《通典》卷32《职官》十四“总论州佐”条引《晋起居注》:“仆射诸葛恢启称:‘州都大中正为吏部尚书。’”[9]虽然诸葛恢在后面还说到“以为都中正,职局司理,不宜兼也”[9],要实现州都大中正与吏部尚书的分离,但此前州都大中正由吏部尚书兼任则应视为一种惯例。
综上所述,“在朝之臣”作为曹操府内官员受教与东曹并选,使得汉末由地方大姓名士把持的乡闾清议成为政府选举的工具,“在朝之臣”推荐人才,实际上就起到了九品官人法中郡中正的作用。在魏国建立后,魏尚书台成员共同在选举中发挥作用,使“并选”方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促成了九品官人法创立时州都的设立。而无论是“在朝之臣”推荐人才,还是魏尚书台成员的多元典选,从根本上讲,都是为了实现中央对选举的直接控制。陈群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以现实中正在实行的选举制度为蓝本,去制定九品官人法的。
收稿日期:2000-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