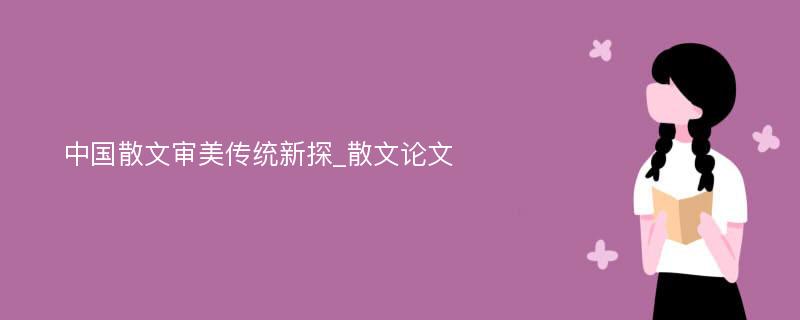
中国散文审美传统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中国论文,散文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散文,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外国散文比较,究竟有哪些中国散文的特质?或我们本民族的审美追求?为了继承这些好的审美传统,细心提取其丰厚的艺术养料,更好地创作与鉴赏散文之美,我们有必要对上面的问题有一个较为明确的认识。
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散文,虽然其审美追求的重点和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的确是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趣味倾向的。这种倾向或传统主要表现在尊用、明道、崇真、主情、重象和尚气六个方面。
一、尊用
散文的尊用观,是指人们对散文社会功用的尊崇与看重的观点,这是中国散文传统审美观之一。历史上曾有“经世致用”、“匡世济时”、“辅时及物”、“有补于世”种种说法,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尊用观上来。
当然,凡文都不应是“为艺术而艺术”,世界上所有门类的作品都是为一定的目的而创作,为人类的自身生存、发展服务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比较而言,中国散文的尊用自从散文的诞生之初就表现出来了,并具有鲜明独特的实用色彩。《汉书·艺文志》称:“古之王者,也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是关于“记言”“记事”的记载,实际上也是指广义上的散文,它是为当时的氏族部落首领或君王所专有,其实用的目的十分明显。所以,郭预衡先生则进一步指出,从中国最早的散文——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来看,“就是从巫卜记事开始的。”“殷人非常迷信鬼神,每做一件事都要占卜。这时的记事文字,主要是记录卜辞”。(注: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有感而发,为记事而作,这些卜辞显然是实用型的极朴拙的远古散文。
中国早期散文的这一尊用特质自然要影响到散文往后的发展,而且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散文记言、记事的社会功用也愈加增强,并形成了一条明晰的审美线索。至汉魏六朝,论述散文尊用的观点便正式提了出来。东汉王充在其《自纪篇》中说,文章“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者,一章无补。”即明确提出了散文要“有补于世”的尊用主张。到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序志》也上承传统,认为“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再往后的各个时代,基本上都是反复强调先秦两汉六朝文家的尊用传统观点,虽然具体口号不尽相同,但尊用的主要精神是一致的。
如果再具体分析一下中国散文尊用的主要内容,则又表现出了以下两点特色:
一是以“善”为散文之大用。我们知道,一切文学作品都要讲究真、善、美的统一,但从东西方的审美传统来看,西方好像偏重在美与真的结合,中国则更为注意美与善的统一,而且又以善为最先。譬如我们仅从造字的角度来分析“美”,就不难发现“美”是从属于“善”的。许慎《说文解字》云:“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在许慎看来,美与善同义,美的含义包含在善之中。事实上,这种美善相兼的思想早在孔子那里就已有明确体现。在《论语·八佾》中有这样几句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据郑玄注,《韶》是颂舜的乐曲,舜以尧的禅让而得天下,并以文德致太平,故孔子称赞《韶》美,骨子里头就是推崇舜之德政。而《武》则是歌颂周武王以武功平天下的乐章,其曲虽美,但内容上不符合孔子主张的仁政,故《武》是美而不善。这就是说,文艺作品既要讲美更要讲善,而且善是放在第一位的。中国散文美学中的尊用传统,实际上也就是这种美善相兼、以善为先思想的反映。
二是强调散文的教化作用。如前所述,中国散文发端于实用,起初是直接用之于占卜或史官的记言记事的,散文的这一实用性质到后来则上升到教化功能,政治教化成了散文的最大实用。甚至有人认为散文应“以立意为本,不以解文为宗。”(注:肖统:《文选序》。)把散文看成是“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注:曹丕:《典论·论文》。)。散文的政治教化作用已成了压倒一切的审美标准,对散文的艺术美则降到了次要的位置,这倒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问题了。
二、明道
“文以明道”,几千年来这几乎是被人们极为推崇的又一传统审美观,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对“文以明道”中的“道”的含义,则是中国古人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概而言之,主要有两种观点:其一是以刘勰为代表的“自然之道”的观点。他认为文章是自然之物,就像龙凤虎豹、云霞草木一样自有其美,并不是什么别的力量“外饰”上去的。所谓明道,也就是要明自然之道(注:参见刘勰:《文心雕龙·原道》。)。其二是以孔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之道”。早在《中庸》一书中,就有“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的话,这里的“道”是指孔子极为推崇的以仁爱治天下的政治理想。“文以明道”,就是要用文章来宣传儒家之道,这也是在中国文坛一直居统治地位的文艺思想。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道”,强调“道”,我们以为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刘勰主张文章写作应是人类自身生活的必然产物,是人类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体现,这无疑是正确的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且给后人以很大启发。不过,刘勰把文章写作与自然界无意识的现象混同,这又陷入了自然主义的泥坑。清代的章学诚纠正了刘勰关于“道”的偏颇。他在《原道》中说:“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在《文史通义·说林》中,他还说:“观于孩提呕哑,有声无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章学诚认为,文章是随着人的变化而自然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必然结果,从而更准确地阐明了文章产生的本原。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散文美学中的“明道”,则是多从明儒家之道的角度来要求的。如何评价这一主张,当然还得从儒家之道本身谈起。我们知道,儒学以“文雅”为风貌,以“仁爱”为灵魂,它在维护社会的稳定,培养良好的仁德精神等方面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儒学将社会阶级关系“血亲化”,将“人伦”关系植入政治统治中,则又给社会留下了许多弊病。所以,这里说的“明道”就要做具体分析了。
同时,过去讲“明道”,还往往将“道”与“文”割裂开来,一味强调“道”的作用,这与片面追求尊用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是一样的。客观地说,“明道”并没有错,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又怎样来“明道”?从散文创作的角度而言,作者应该站在一定时代的前列,在散文中寄寓自己的理想,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思想倾向。一切优秀的散文不仅有“道”,而且都有正确的“道”,先进的“道”。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散文写成是政治教科书,应将健康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巧妙地结合在一起,重“道”亦须重“文”。清人魏禧在《甘健斋轴园稿序》中说:“文以明道,而繁、简、华、质、洪、纤、夷、险、约、肆之故,则必有其所以然。……文不如是,不可以明道。”这里所强调的正是要“文”、“道”兼顾,好的形式可以使内容得以充分的表现,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因而我们就要按散文艺术“必有其所以然”的规律进行写作,否则便不能很好地“明道”。
明道,必须要通过好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重文,其终极目的又是为了明道。在“文”与“道”的关系上,过分强调某一方面都是不对的。历史上只讲“明道”而阻碍散文健康发展的事例已不胜枚举。相反,过于追求艺术形式的美也就会失去散文的社会审美功能,同样不可取。
三、崇真
崇真,是中国散文的另一审美传统,这与中国早期散文源于史官的记言记事有关。因为中国散文从一开始就是属于应用型的,而且当时并没有独立的文学观念,“文学”一词指的是整个学术文化。《论语·先进》述及孔门四科,其中提到:“文学:子游、子夏。”这是说子游、子夏承传了孔子文化典籍方面的成果,并非专指文学创作。直到两汉时期,随着辞赋盛行,文学与学术方始分化。所以,中国先秦的古典散文,都是文史哲不分的,也无所谓文学的虚构,基本上都是历史散文。这些散文,都是直接用之于人类的生存发展的,社会的功用性很强,而尊用首先又必须得崇真。
从先秦的《国语》、《国策》、《左传》等可以看出,这些散文都是当时生活的完全真实的记录。特别是在中国散文发展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的司马迁的《史记》,更是为史学家班固誉为“实录”的典范。(注:参见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史官写历史,要敢于反映真实情况,这是历史写作的一条基本美学原则。比如在《左传·宣公二年》中,即载有晋国史官坚持书赵盾弑君事,并录孔子语:“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这种良史的“实录”精神,往后就一直作为中国散文的一大审美传统继承了下来。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散文从先秦的杂文学体制中逐渐分化出来以后,散文便纳入了文学的范畴,与诗歌、小说、戏剧构成了文学的四大体裁。然而,散文却始终以严格地写真实(并非艺术的真实,而是生活的真实)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汉代王充就以“疾虚妄”、“求实诚”作为《论衡》一书的中心思想,大力提倡“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极笔墨之力,定善恶之实”(注:王充:《论衡·佚文》。),为古代文论中的求实传统奠定了基础。三国时又有曹丕提出“铭诔尚实”(注:曹丕:《典论·论文》。);晋代左思论赋反对“虚而无征”,主张“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注:左思:《三都赋序》。)南朝刘勰则指责“采滥忽真”的流行文风,把“事信而不诞”作为评论散文的重要准则(注:参见《文心雕龙》中的《情采》、《宗经》诸篇。);宋代的欧阳修更是明确指出:“事信言文,乃能见于后世”(注:引自李光连:《散文技巧》第70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如此等等,有关散文写真的论述可谓一脉相承,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
中国散文崇真的审美传统,不仅在理论上有一致的认识,而且在散文写作实践上也是基本上遵循这一美学标准。譬如柳宗元,他在散文《段太尉逸事状》中这样自述写作经过:“尝出入岐、周、邠、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障堡戌”,不仅向有关的知情人做了深入的调查访问,而且又从刺史崔能处“备得太尉逸事,复校无疑”才执笔成篇。又如方苞写《狱中杂记》,其崇真的态度也很鲜明。他先听了洪洞县令杜某的介绍而生感慨,进而调查核实,故他在该文中说:“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像这样的事例,这里也用不着多举。
不论怎么说,崇真作为中国散文的美好传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不过,在现当代也有人对散文的这一崇真传统提出质疑,甚至主张散文也可以像小说那样虚构。我们认为,如果散文也可以虚构的话,那实际上是丢掉了散文这一体裁,散文正是以自己严格的写真而独立于文学之林的。
四、主情
中国散文主情,强调作者独特情志的抒写,这也是为古今的文艺理论家们所一致肯定的。当我们遍观那些优秀的散文,就会鲜明地感受到,它们无不饱含着作者强烈的感情,充满着浓郁的诗意。庄子的《逍遥游》、宋玉的《风赋》、王粲的《登楼赋》、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并序》、江淹的《别赋》、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张岱的《西湖七月半》、龚自珍的《病梅馆记》等等,莫不如此。
中国散文主情导源于诗歌的“言志说”。“言志说”在先秦的典籍里多有记载,最早见于《尚书》,《虞书·舜典》说:“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这里说的“志”,可能与当时颂神祭祀的内容有关,还不一定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作者内心情志。往后,在《周书·旅》中,对“志”的理解就接近于一般的说法了。“不役耳目,百度惟贞,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将“德”与“志”并举,并与“耳目”的物质精神享受联系起来,这里的“志”当指人这一主体的道德情志。再从诗歌的写作实践来看,《诗经》则又开辟了我们民族文学主情的航向,因而“诗言志”自然也就被后人称为中国诗歌美学的“开山纲领。”(注:朱自清:《诗言志辨》,《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以后的诗歌创作, 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航道向前发展的。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在表现风格上尽管富于变化,但抒情言志却是所有诗歌创作的宗旨。其实,散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关于散文的主情观,在晋代陆机的《文赋》中已初露端倪。该文开篇云:“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也就是说,写文章不仅要多观察生活,还要多从古籍中加强情志方面的修养。在陆机看来,写文章是不能离开情志的。这一思想,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就表达得非常清楚了。他在《体性》篇中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而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诗以言志,文以传情,用词不一,含义都是相同的。虽也有人将“志”与“情”对立起来,但大多数人还是持情志统一观。唐代孔颖达说得明白:“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注:孔颖达:《左传正义》。)这样,散文主情的矩矱也便逐渐地深入人心,从而构成散文美的一大特色。
如前所述,中国散文是从记言记事的历史散文开始的。《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未必可靠,但古代的历史散文确有记言记事之分。如《尚书》、《国语》即以记言为主,《春秋》、《左传》又以记事为主。但无论是记言还是记事,所记的内容都是以政治说教和道德训诫为目的的,只是显得比较平实朴拙,与“诗言志”的传统并无二致。到六朝以后兴起的抒情散文和骈文,则彻底地向抒情言志靠拢,以主情为己任,与诗歌一样,完全登上了注重表现主体情志这一符合艺术规律的正途。
中国散文主情性的表现十分明显。那些以直抒胸臆、陈述怀抱为主的散文自不待说,即使是在以记事、咏物或论说为主的散文中也无不以抒情言志为旨归。或寓情于事,或托物言志,或情理交融,在一字一词之中都倾注着作者的思想感情。特别是随着文学表现方法的丰富,唐宋以后的议论散文更是善于将自身融入论题,做到情真意切,理实思晰,既以理服人,又以情感人。例如苏洵的《六国论》,文章旨在论述战国时六国对秦斗争的政治形势,六国灭亡的原因和历史教训。但作者并不是用纯客观的理论推理与分析,而是以情遣辞,情理相兼,全篇贯穿着作者对六国破灭的惋惜与沉痛的反省之情。开篇作者即提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的观点,然后通过两段设问作答的形式进行分析,最后以“呜呼”一词引出作者的感叹,总结全文,照应开头。如此论说,一气贯注,入情入理,显示出了议论散文主情性的特征。
散文的主情性,强调的是作者面对生活,从事创作的时候要充分发挥其主体意识,“以我观物”,使作品具有独具特色的情感美。这一审美传统,与我们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是一致的。中国的文化始终是把对生活、对社会的伦理观照放在第一位。比如被称作卜筮专用的古代经典《周易》,即把制作卜筮的基本符号“八卦”的目的规定为“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注:《周易·系辞下》。)。孔子所提出的“兴观群怨”说更是把诗文的社会功用突出来了,甚至“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也是为了“迩之事义,远之事君”(注:孔子:《论语·阳货》。)。所以,上面谈到的言志、明道、主情等都是从诗文的社会功用出发,要求对于主体意识的高扬。这一点,与西方的文化传统却大异其趣。西方文学的发展是沿着亚里士多德倡导的“艺术模仿自然”的道路前行的。“模仿说”要求作者必须忠实于客观世界的原貌,以真实地模仿自然(再观生活)为审美追求,而作者对生活的审美判断则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所谓“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面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界里面露面一样”(注:福楼拜1875年12月给乔治·桑的信,见《文艺理论译丛》第3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的提法, 正是西方文学,尤其是西方写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真实写照。西方文学的这一审美传统一直在他们的美学思想里占据着支配地位,至少到19世纪都是如此。譬如别林斯基还对这一传统做了发展性的解释,他认为:“艺术是现实的复制。从而,艺术的任务不是修改,不是美化生活,而是显示生活的实际存在的样子。”(注:《别林斯基论文学》第106页, 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可见,他是明确地将对生活的真实摹仿当成了艺术的第一要素。
鉴于以上中西方艺术美学的区别,所以已有不少论者把这一区别概括为“重表现”与“重再现”的差异。中国散文的主情性,即是“重表现”这一美学传统的确切体现。
五、重象
一般而言,重象是指注重用意象来表达思想情感,这是我们祖先最早形成的美学观之一。先秦所谓的“象”,原来都是“道”的物化形式。老子在《道德经》二十一章中写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这里“道”的含义与前面提到的“明道”的“道”不尽一致,老子之所谓“道”,它是哲学中万物的本体,但“道”的观念是高度抽象化的,如何把握它呢?在老子看来,道虽超然,却总以恍惚的物象为存在的形式。所以,“象”从诞生起,就是用来表达抽象的思想观念的。
古人把“象”作为表意的形式,最早出现在《周易·系辞》中:“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象也者,像也。”即是说,古人拟“象”的用意在于形容幽深抽象的自然事理。所以,该书中还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这也是说,圣人的意图是通过形象的方式表达的。关于这几句话,王弼在《周易例略·明象》中做过精彩的解释:“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象生于意而存像焉,则所存者非像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其意者也;忘言者,乃得其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不论怎样来看待王弼的这段话,但有几点是比较明确的:1.“象”是表现人的思想情感的形式——象者存意;2.要能更好地塑造形象,非语言不可——言者明象;3.要能更好地传达人意,又非得借助形象不可——尽意莫若象。这就把创作中的“意”、“象”、“言”三者的关系讲清楚了。它告诉我们,作者有了“意”要表达,就得借助恰当的“象”,寓意于象中,而要把“象”显现出来,最后又得寻求最精确的语言予以表达。在“意”——“象”——“言”这三者之中,“象”是绾合“意”与“言”的枢纽。所以,重象也就作为中国诗文创作的审美特征提了出来。《周易》所使用的“意”、“象”就成了后来重象观的渊源。
把重象观最早引入散文美学的,是晋代陆机的《文赋》,其中有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这里把“物”与“意”对应起来,“物”即包含有物象之意了。再往后,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篇》则又第一次提出“意象”的概念:“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藻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政以怿辞,然后使玄解这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从此,“意象”一词也就代替了先秦“象”的概念,并在往后的文艺美学中被广泛运用。
“象”也好,“意象”也好,其本质内容就是艺术形象。那么,重象也就是重视艺术的形象思维,不能作呆板的理解。譬如说,对那些写物、写景的散文,其寓意于象就比较明显。而对那些记事的散文,又是如何体现“象”的呢?请读苏轼的《记承天寺夜游》。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对文中所涉及到的一些物象,如“月色”、“积水”、“藻荇”、“竹柏”等,我们就不能从这些物象本身去寻找寓意了,而应当从这些物象所构成的整体氛围上去体味作者初受贬谪、闲居黄州时的那种隐隐幽怨之意。
所以说,重象就不仅仅是指重视物象,而在更多的时候则可能是指重视形象思维,应把传统的重象观理解得宽泛一点。不然,对有些全然无“象”的散文就更不好理解了。
散文的重象,它常给人带来的美感是化虚为实,使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成为具象式的存在。所谓“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木写之,”(注:刘熙载:《艺概》。)就是指重象所采用的基本技巧。其次,散文的重象还能给人一种朦胧的美。如前所述,本来就是指“道”的本体的物化,恍惚中有“象”,此“象”,如烟如雾,使人回味无穷。再次,散文的重象还多表现出一种画面的美。因为散文的“象”比较注意内部的组合与联系,它给人的一般不是某个物象的孤立物,而是一种有立体感的多重组合的艺术图画,具有整体的美感。
六、尚气
崇尚散文的气势,这是中国散文美学又一突出的审美传统。清人方东树《昭味詹言》说:“气势之说,如所云‘笔所未到气已吞’。”刘大櫆《论文偶记》也认为:“文章最需气势。”如此等等,都是散文尚气的代表性观点。纵观中国古代文论,“气”这个概念可谓用得最为普遍,譬如上自《周易》开始,往后又有《淮南子·原道训》、《管子》、《孟子》、刘勰《文心雕龙》、曹丕《典论·论文》、王十朋《蔡端明文集序》、刘将孙《谭西村诗文序》、方孝孺《张彦辉文集序》等,直到清代刘大櫆《论文偶记》,姚鼐《答翁学士书》、魏际端《伯子论文》,无不从各个侧面谈到文气。从积极方面说的就有:“生气”、“正气”、“和气”、“英气”、“精气”、“豪气”、“浩气”、“逸气”、“清气”、“奇气”、“异气”、“刚气”、“柔气”等;从消极方面说的又有:“浮气”、“昏气”、“邪气”、“虚气”、“矜气”、“孱气”、“伧气”等;从中性方面说的还有:“静气”、“血气”、“元气”、“体气”、“景气”等。由此可见,尚气观在中国散文美学中的重要地位。
究竟如何理解这个“气”呢?历来的散文美学家们说得颇为玄妙,比较费解,但总的说来可分为两个大类:
一类是指自然之元气,包括人的体气在内的“气”。《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意即万事万物皆由自然元气积聚而成。《淮南子·原道训》有云:“气者,生之元也。”王念孙疏:“元者,本也。言气为生之本”。也是从这个意思上来讲的。既然如此,人也是自然之物,那么元气便包括人的体气了。如《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也说:“气,体之充也。”刘勰《文心雕龙》更是多处谈到“气”,一般也是从人的体气方面说的,“《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又说:“枚乘之《七发》、邹阳之《上书》,毫润于笔,气形于言矣”。
另一类是指文章之气,是文章内容与作者的情感相隔合,并借助语言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抑扬顿挫、高下合度的气势与气韵。明确把“气”与文章写作联系起来的是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但这里的“气”仍还兼有体气的意思在内。明人方孝孺在《张彦辉文集序》中评韩愈的文章说:“退之俊杰善辩说,故其文开阳阖阴,奇绝变化,震动如雷霆,淡泊如韶濩,卓矣为一家言。”苏轼在《文说》一文评价自己的文章也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据此,后人评韩愈、苏轼散文常用“韩潮苏海”加以赞誉,这就是从文气生动、富有气势的角度而言的了。
不论是自然之元气还是文章之生气,实际上两者紧密相关,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在作者身心为元气,把这种元气用语言表达出来也就是文章之生气了。所以说,散文尚气一般也是从这样两个方面来讨论的:一是主张内养身心的浩然之气,二是主张加强词章修养。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他在这里用水与浮物的比喻,即把作者的身心元气与语言表达的关系讲清了。这样,要写好文章就必须养气。比如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就说:“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至。”又说孟子的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是其“善养吾浩然之气”的结果。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更是列专章《养气》进行论述,详细地阐明了养气与文章写作的重要关系:“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埋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认为“吐纳文艺”,必须“元神宜宝,素气资养”,意即要“守气”与“卫气”。
然而,文章毕竟是“气之所形”,因此尚气的另一任务还得要加强作者的文辞修养。刘大櫆《论文偶记》说:“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迹。”这句话又正好说明了加强作者文辞修养对于文气形成的重要性。谈到文辞修养,这方面的论述就比较多了。如“修辞立其诚”、“言有序”(注:《周易》。);“辞尚体要”(注:《尚书》。);“辞欲巧”(注:《礼记》。)等,都说明不能忽视词章的修养。清人张裕钊在《答吴挚甫书》中说:“文以意为主,而辞欲能副其意,气欲能举其辞。臂之车然,意为之御,辞为之载,而气则所以行也。”这就是说,“意”(内容)是一篇文章的根本,“辞”(语言)以副之,而“气”(气势)载其辞。形象地表明文章内容、语言和气势三者之间的关系。
对于上述中国散文的六大审美传统,还仅仅是做了一个粗线条的扫描,而且也不一定就只是这些。在漫长的散文发展史上,这些特点也是互为联系、各有消长的,但它们毕竟构成了中国散文美学的主流。
标签:散文论文; 文学论文; 典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文化论文; 美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心雕龙论文; 国学论文; 尚书论文; 论文偶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