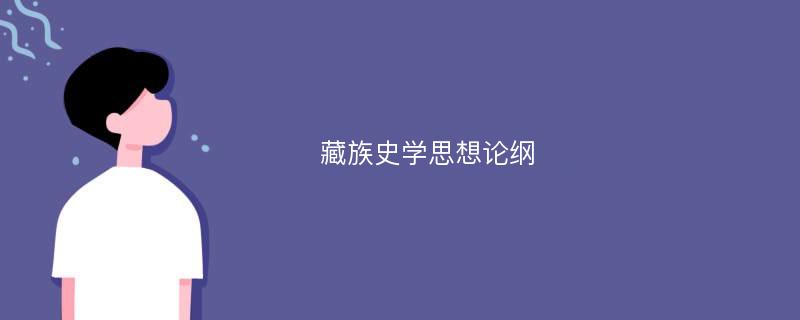
王璞[1]2002年在《藏族史学思想论纲》文中指出藏族历史悠长,史书丰富,但关于藏族传统史学的研究却未受到前人重视。中国史学史不单是汉文传统史学的表述领域,更应有藏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史学的切当位置,本书的写作即旨在改变汉文传统史学的一些惯性理念,而其中的突破点便是史学思想。本书的第一个立论认为,史学思想应包括历史文学、历史编纂学及历史哲学叁个主层次,叁个主层次下又有史书题材等九个分层次,继此我在相关讨论的基础上对史学思想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藏族史学思想的历史分期是本书的第二个论点,构成了正文的基本框架。以藏族史书为载体,从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角度分四个时期对藏族史学思想加以论述和反思是本书的主体。上述四点即是本书的主要新意。与之相应,我希望通过藏族史学思想的探讨能为史学理论的总体建构尽一份绵薄之力,且使有识者能重新审视藏族乃至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诸多价值。这两点又是本书写作的意义所在。
佚名[2]2009年在《书讯》文中认为《藏族史学思想论纲》作者王璞。该书以藏族史学思想生发递嬗的四个时期为经,以藏族史学经典之思想内涵为纬,从历时与共时结合的角度演绎了藏族史学思想的存续流变。作者在序言中写到:如果将历史语言学、历史编纂学、历史哲学叁个主层次及相应的九个分层次,视为史学思想的基本骨架,那么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族群的史学思想无疑是活化这一机体的血肉,基于此解析藏族史学思想,就会发
索朗次仁[3]2017年在《《贤者喜宴》吐蕃史料考析》文中研究指明朗贝吉僧格曾言:“生为人身,若不知自己的祖系,则宛如林中的猕猴,人若不知自己的母系血统,则犹如幻觉中的苍龙”。这说明了藏民族自古以来非常注重本民族的历史。吐蕃时期,藏族甚是重视历史记载,不仅历史文献记录在纸上,而且刻在金石上,其目的是为了引起后辈的重视并传世永久。佛教后弘期,藏族贤者秉承先民之优良传统,编篡了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文章以藏族历史名着《贤者喜宴》吐蕃史料作为研究对象,以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充分利用吐蕃金石铭文、敦煌古藏文文献、以及藏汉古代历史文献;综合运用历史考据学与历史文献学等多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把《贤者喜宴》所载吐蕃时期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之相关史料去伪存真,力求还原其本来面目。文章以六章的篇幅,对《贤者喜宴》吐蕃史料进行考析。第一章,《贤者喜宴》介绍。首先介绍了《贤者喜宴》作者的生平及其着作。其次,对该史籍的纲目及版本进行介绍。另外专门对该史书所载吐蕃史进行概述。第二章,《贤者喜宴》吐蕃史料概述。首先梳理了《贤者喜宴》吐蕃史所引用的史料,并对其进行文献编目。其次,对目录中的历史文献进行论述。第叁章,《贤者喜宴》所载吐蕃赞普世系史料考析。本章共分2节。第一节,《贤者喜宴》所载止贡赞普世系史料考析。首先以历史考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对《贤者喜宴》所载止贡赞普世系史料进行辨伪。通过考证提出,止贡赞普仅有两个儿子即:夏赤(?)、涅赤(?)。其次,《贤者喜宴》等后期历史文献所载止贡赞普之子恰赤(?)的身份进行考析。通过研究发现,“恰赤”并非为止贡赞普之子,乃是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之别名,且史书记载的相关恰赤历史均为聂赤赞普所为。11世纪左右因史家史料运用不当而形成了“恰赤”为止贡赞普之子一说,以讹传讹流传于世。最后,从古代藏族鸟崇拜的文化现象,诠释了聂赤赞普命名为“恰赤”之缘故。第二节,《贤者喜宴》所载赤松德赞世系史料考析。首先对《贤者喜宴》所载赤松德赞之子为牟赤赞普、牟尼赞普、牟帝赞普、赤德松赞之史料进行探源。发现其说法最早可能出现在吉尊扎巴坚赞编着的《王统》一书。其次,依据敦煌古藏文文献和吐蕃碑文,通过考证提出,其实赤松德赞有3个儿子,并非如《贤者喜宴》所言。其排序为牟尼赞普(?)、牟茹赞(?)、赤德松赞。最后提出,《贤者喜宴》等11世纪以后出世之大部分史书中“牟茹赞”之名衍化成“牟帝赞普”(?)之观点。第四章,《贤者喜宴》所载吐蕃名相史料考析。本章共分2节。第一节,《贤者喜宴》所载罗昂达孜史料考析。《贤者喜宴》作者交代罗昂达孜史料均引自阿底峡尊者发掘的伏藏文书—(?)。然而,这部史书与由甘肃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办公室毛兰木嘉措先生依据北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柱间史》(?)写本,与拉卜楞寺藏《柱间史》写本影印件相对照后铅印的《柱间史》,并非为同一版本。其次,对《贤者喜宴》所载罗昂达孜史料进行考证。提出罗昂达孜并非为止贡赞普之臣,而是十二个小邦之一娘若香布小邦之王之观点。第二节,《贤者喜宴》所载大相达扎鲁恭史料考析。以敦煌古藏文文献和雪碑铭文为依据,对达扎鲁恭史料进行辨伪。通过考证发现,达扎鲁恭在吐蕃赞普赤德祖赞、赤松德赞父子执政期间,对赞普忠贞不二,对社稷裨益,心地纯良,尽职尽责,足智多谋,英勇深沉,为吐蕃政教事业有功之臣。然而,11世纪以后出世的《韦协》为主的佛苯历史文献中,达扎鲁恭被塑造为苯教代表人物的形象并非为故弄玄虚,而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第五章,《贤者喜宴》所载吐蕃宗教史料考析。本章共分2节。第一节,《贤者喜宴》所载有关佛法初传吐蕃史料考析。首先对《贤者喜宴》所载有关佛法初传吐蕃史料进行探源。发现该史料引自《柱间史》一书。其次,运用历史考据学与历史文献学研究方法,对这一史料进行考析。通过研究发现,有关佛教最初传入吐蕃的最早记载为英藏敦煌藏文文献IO370.5。该文献记载:“天降之经文一卷”。继而提出,传说中的天降佛经乃外来佛教徒所携带至吐蕃之管见。另外,佛经从天而降之传说,可能出自苯教徒之手;或为了顺利引进佛教,崇佛的赞普及臣相利用苯教徒崇天之性,故弄玄虚也。第二节,《贤者喜宴》所载吐蕃时期佛经目录史料考析。编纂于公元8-9世纪的叁大藏文佛经目录的最早研究者为布敦仁钦珠大师(1290-1364年)。早在公元14世纪,布敦大师对吐蕃时期叁大佛经目录中收录的典籍进行了精细的校对,并根据叁大目录的分类法,编篡了独树一帜的《甘珠尔》、《丹珠尔》目录。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叁大目录中的《钦普目录》和《旁塘目录》先后失佚,只有《兰噶目录》幸存,并收于《丹珠尔》目录中。令人欣慰的是,2003年西藏自治区博物馆,根据新发现的13-14世纪的《旁塘目录》写本,编辑出版了《旁塘目录》一书。该写本的发现澄清了长期以来有关吐蕃时期叁大佛经目录的诸多问题。文章以吐蕃时期编纂的《兰噶目录》和《旁塘目录》为基础资料,结合敦煌古藏文文献、藏文史料以及吐蕃碑铭等文献,对吐蕃时期叁大佛经目录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客观、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一、对长期以来学人通称的《丹噶目录》《(?)》进行了文本研究,提出该书名乃是后期衍化而成的观点。因为现存的吐蕃文献P.T.1085、P.T.1088和《韦协》等史书中编辑该目录的场所-王宫被称作“(?)”,而并非后期史料如《布敦善逝教法史》、《贤者喜宴》史书所称的丹噶(?)。根据藏文书写习惯,“(?)”一词很可能由“(?)”衍变而成,或是“(?)”的误写。但今仍有不少学人以讹传讹,常把《兰噶目录》《(?)》称作《丹噶目录》《(?)》。二、《兰噶目录》是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在位时的龙年(788年)由噶瓦·白孜、昆·鲁益旺布等人肇始编纂,经几代赞普对其进行了增补和完善,最终完成于赞普赤祖德赞·热巴坚晚年。叁、《钦普目录》是公元798年至829年间的某年由噶瓦·白孜、昆·鲁益旺布等人,在《兰噶目录》的基础上肇始编篡,最终完成于赞普赤祖德赞·热巴坚晚年。四、《旁塘目录》是吐蕃赞普赤祖德赞·热巴坚在位时的狗年(830年)由一位噶瓦·百泽晚辈为代表的学者,在以上两部目录的基础上肇始编篡,最终完成于赞普赤祖德赞·热巴坚晚年。总之,吐蕃时期叁大佛经目录编写工作肇始于8世纪下半叶,一直延续到9世纪30年代才完成。叁者并非为毫无相干的叁部独立的着作,而是相互紧密联系的叁部目录。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母体,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和发展的结果。这样的编辑方法甚是符合吐蕃时期佛典翻译中编辑学特点和编辑原则。第六章,《贤者喜宴》所载吐蕃政治史料考析。本章共分2节。第一节,《贤者喜宴》所载吐蕃赞普达日年悉统治小邦之史料考析。《贤者喜宴》载,吐蕃赞普达日年悉陆续征服本巴王(?)、吐谷浑王(?)、昌喀尔王(?)、森波王(?)、羊同王(?)等小邦均被纳入悉补野政权治下。首先对该史料来源进行探究,发现该史料引自《底吾史记》(12世纪)和《第吴宗教源流》(13世纪)。其次,以敦煌古藏文文献、汉藏史料、苯教历史文献等为文献依据,对该史料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吐蕃赞普囊日松赞时期,赞普亲自统兵进攻拉萨河流域统治者森波王,并其被纳入悉补野政权治下。2、公元638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首次进攻吐谷浑,并占领了吐谷浑部分疆土;公元663年,吐蕃赞普芒松芒赞时期再次发动进攻,彻底推翻了吐谷浑政权,是年其被纳入吐蕃政权治下。3、公元64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征服了羊同,并其被纳入吐蕃政权治下。4、吐蕃赞普达日年悉时期,赞普曾亲自统兵进攻本巴王小邦,不料悉补野军队折兵损将,赞普身陷囹圄。据此得知,吐蕃赞普达日年悉未能征服本巴王。5、昌喀尔王乃是吐蕃十二小邦之一斯域热莫空(?)之王。该小邦被吐蕃赞普达日年悉征服一说,未能找到旁证材料,无从考证。从以上数点结论看,《贤者喜宴》所载吐蕃赞普达日年悉统治诸小邦之史料不可尽信也。第二节,《贤者喜宴》所载列朗茹嘎(?)史料考析。《贤者喜宴》载,止贡赞普被罗昂达孜弑杀后,王子们从其父宝库中取出一头神牛犊,其名吉乌朗茹嘎(?),此牛犊善于飞腾。王子骑飞牛逃亡工布地区。首先对该史料来源进行探究,发现该史料引自《雅隆觉沃教法史》一书。然而,从《底吾史记》(12世纪)和《第吴宗教源流》(13世纪)等文献看出,《雅隆觉沃教法史》所载“(?)”一词纯属笔误,其正确写法应该为“(?)”。其次,对该史料进行研究。发现“(?)”并非为一头善飞之牛,而是悉补野王族的传家之宝“王之九坚”(?)之一。“王之九坚”既是吐蕃赞普权利之象征,亦是悉补野王族血统标志;若得到它就等于取得了政权,失掉它就意味着丧失了政权。
孙娟[4]2012年在《米拉日巴各种传记的版本研究》文中指出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是广为僧俗熟知的修行人之一。记载他皈依修行的传记文本繁若星辰。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米拉传记的不同版本,可以较全面系统的把握关于米拉日巴的文献资料;也可以刊误纠谬,为校勘提供基础,避免谬误的流传;还可以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取长补短,丰富其他研究的资料数据。米拉日巴各种传记的版本研究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张未娜[5]2013年在《《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比较研究》文中提出《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作为14世纪藏族传统史学代表作,研究这两部着作对于把握整个14世纪时期藏族史学发展特点以及史学发展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这两本着作的相似点和不同点,试图以一种新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的史学地位和史学意义。
张媛[6]2014年在《试论《柱间史》的史学思想》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柱间史》是伏藏文献中出现较早的一部。相传是吐蕃松赞干布讲述,所以一般也称作《松赞干布遗教》,本文对《柱间史》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简单的梳理,笔者认为即使存在书中涉及到的一些神话传说,及书中的部分内容是由后人杜撰的问题,同样不会影响到本书的完整性及可信度。
杨国桢, 陈支平[7]1991年在《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文中提出今年是本刊创始人傅衣凌教授诞辰八十周年和逝世叁周年,为纪念傅衣凌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卓越贡献,特辟本期为傅衣凌学术纪念专号,邀请傅衣凌教授生前的部分友好和学生撰写论文,以表达我们对傅衣凌教授的崇敬和悼念之情。
泽珍卓玛[8]2014年在《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与中华民族主流政治文化的差异与协调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民族是一个以共同的民族文化为纽带形成的人群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少数民族政治文化是我国统一政治文化中的亚文化或次级文化,这些亚文化又相互构成一种相对于汉族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并有突出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体系。本篇文章从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基本理论为出发点,在研究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概念性理论及其关系的基础上,深层次剖析我国主流政治文化与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差异与协调,明晰少数名族政治亚文化在主流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和主流政治文化对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的影响。以藏民族政治文化为例,分析和归纳藏民族的政治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现状和发展路径,从而实现对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在我们国家当前现状的研究。结合上述研究内容,将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在我国政治文化中的发展和协调机制作为本文的落脚点,改革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保障机制、发展和加强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机制、建立和健全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发展机制,使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更好地适应我国政治文化的发展,完善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
顿拉[9]2018年在《明代藏族史学名着《后藏志》思辨叁则》文中认为《后藏志》成书年代大约为明天启元年(1621年)至崇祯七年(1635年)之间。这部史书的编篡目的,除了赞颂后藏佛教的兴盛,更主要的在于宣扬藏巴汗的统治地位,对其统治前藏制造一种正统性;在编纂题材上,是一部融集教法源流、寺院布局、高僧传记为一体的关于后藏地区的寺院志书,为清代西藏地区编撰寺院志提供了范例。
郭震旦[10]2010年在《“八十年代”史学谱》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八十年代”是一个变革的年代。在这一变革为主旋律的年代,革故鼎新也成为历史学最大声的呼号。中国社会在这一特定时段发生的断裂与重组,其所引起的冲击与震荡,也完全同步体现在史学研究的断裂与重组上来。与共和国的脚步共振,“八十年代”的史学是以一场嫉恶如仇的思想解放运动拉开序幕的。砸碎枷锁,冲破禁锢历史学精神的现代经学牢笼,成为“文革”结束后一个时期、乃至整个“八十年代”的主旋律。劫后余生,历史学家们以一种勇闯地雷阵的决绝向着“文革”史学泛滥成灾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发起最猛烈的进攻,在突破种种明枪暗箭的阻挡之后,终于廓清了长久笼罩在史学上的封建主义、教条主义的迷雾,使早已被“四人帮”的蒙昧主义折磨得奄奄一息、仅剩下意识形态外壳的史学重新获得生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无疑给已经从灾难中复苏的中国史学提供了最强的推动力,史学领域的思想解放遂向纵深挺进。一大批史学家开始对“文革”史学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清算与讨伐,踏上了从学术上重建中国历史科学的征程。从此,中国史学展开一个新的篇章,跨入一个新的纪元。一个个学术坚冰被融化,一个个学术禁区被突破。“回到马克思去”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思潮。这一思潮贯通整个八十年代,在长达十年的时间段中,史学界紧紧扭住流行唯物史观对人类文明史的严重曲解,实现了历史发展动力,历史创造者等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突破,从而拆除了流行唯物史观框架的支柱,使史学彻底摆脱了现代经学的控制。正在史学界“拨乱反正”高歌猛进之时,出乎意料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展开,刚刚从“文革”中复苏过来的史学却不期然陷入了巨大的焦虑和难以把控的失重之中,一场裹挟甚广的“史学危机”开始蔓延史学界。1983至1988年,对“史学危机”的讨论成为史学界最集中、最热烈的话题,也成为整个“八十年代”史学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这是刚刚获得新生的史学的一次“硬着陆”,也是共和国转型期所经历的“阵痛”在历史学界的反映。不过,正是这场危机影响到其后新时期史学的基本走向,一些与建国后前30年史学完全不同的因素开始在这场危机中破土抽芽。获得“重生”的史学正是以这次危机为契机获得了“重构”。这场危机首先肇因于史学与急剧转型的社会之间的错位。面对正在发生转型的社会,史学完全失语,彻底丧失了对现实的阐释力,完全成为一场伟大变革的看客,成为一个“多余的人”。“八十年代”的这场史学危机是全面性的,无论从史学理论、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还是从史学价值、史学功能、史学范式上来说,“八十年代”的史学严重脱离了转型期的社会。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对历史学自身的全面检讨开始了。首先,建国30年来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成为质疑的对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在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后,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形成的知识“范型”已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的发展面前,有些过时了,新时代要求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学习。第二,危机来源于方法论的贫困。第叁,危机表现于研究领域的极度狭窄和集中。由于受到苏联史学模式的影响以及国内意识形态的需要,建国后史学研究的范围主要集中在“五朵金花”。第四,危机在于史学与现实的疏离。危机孕育着生机。正是因为“史学危机”的逼迫,才促使历史学界调整史学的内部结构,开始了艰难的改革之路,并在范型转换、理论建设、方法论构筑、研究领域拓展等方面全面实现新的跨越,从整体上刷新了历史学的面貌,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是呈现“井喷”之势的。1987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史学理论》创刊,其后大批史学概论教材开始出版,如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吴泽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瞿林东、赵吉惠、马雪萍合着的《史学导论》,李振宏着《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等,这些着作的出版,推动着史学理论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八十年代”的史学理论研究一个重大突破主要体现在历史认识论上获得飞跃,彻底改变了过去那种历史认识被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所代替的窘迫。在方法论上,建立历史学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在唯物史观提供的研究方法之外,探索新的方法论途径也成为整个史学界的共识。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联姻的努力,而在引入历史学的自然科学方法中数系统论声势最为浩大。这一时期,外国史学理论也开始大量涌入。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变迁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就来自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引进。外国史学理论为“八十年代”中国史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这也算是改革开放经济领域引进西方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反映。如果说理论建构构成“八十年代”史学重构的一翼的话,那么,在写作实践上回归历史现场则构成另外的一翼。随着80年代之前的史学体系的瓦解,过去完全被排除出历史书写框架的一些历史内容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史的复兴,最能代表20世纪后20年史学研究的新趋势、新潮流,是当代史学的一个标志性领域。中国社会史的兴起对史学体系的转换居功至伟。它至少在以下几点构建了新的范式:一、采取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量吸收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以达至其构建总体史的目标。二、大大拓宽了与国际史学对接的通道。大量西方学者的理论模式被引入到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来。叁、研究领域的大幅度转换,由精英的历史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由政治的历史转向日常社会生活的历史,由一般历史事件转向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会史的兴起,对于中国史学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十年代”的史学留下了巨大遗产。概括来说,有以下几点:一、史学研究的“去意识形态化”。这是“八十年代”留下的最大遗产。在这一时期,史学终于摆脱了现代迷信的禁锢,冲破现代经学的牢笼,解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枷锁,冲破了重重禁区,打破了一系列陈旧史学观念的束缚。二、史学走向多元化,统一的史学形式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史学观念、史学理论,还是史学方法,都体现出多元共生的特征。叁、“八十年代”史学产生了众多的理论贡献。
参考文献:
[1]. 藏族史学思想论纲[D]. 王璞. 云南大学. 2002
[2]. 书讯[J]. 佚名. 中国西藏(中文版). 2009
[3]. 《贤者喜宴》吐蕃史料考析[D]. 索朗次仁. 西藏大学. 2017
[4]. 米拉日巴各种传记的版本研究[J]. 孙娟.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2012
[5]. 《红史》和《雅隆尊者教法史》比较研究[J]. 张未娜.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
[6]. 试论《柱间史》的史学思想[J]. 张媛. 黑龙江史志. 2014
[7]. 傅衣凌晚年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思想的发展[J]. 杨国桢, 陈支平.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1
[8]. 少数民族政治亚文化与中华民族主流政治文化的差异与协调问题研究[D]. 泽珍卓玛. 中国矿业大学. 2014
[9]. 明代藏族史学名着《后藏志》思辨叁则[J]. 顿拉. 西藏研究. 2018
[10]. “八十年代”史学谱[D]. 郭震旦. 山东大学. 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