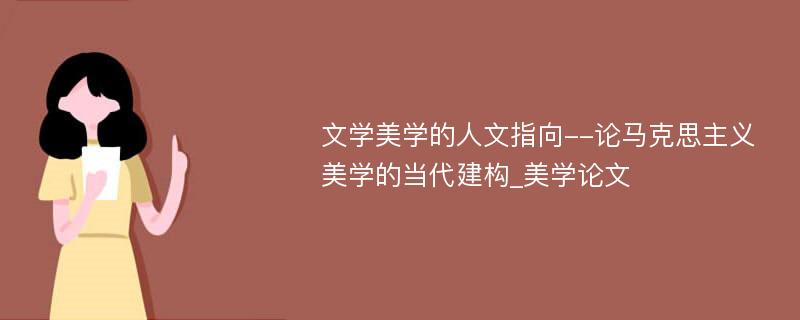
文艺美学的人学方向——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人学论文,文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2)01-0030-05
进入新世纪后,许多学者关心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21世纪文艺美学发展格局中的地位、意义,并思考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现代化问题。可以预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观点在现代文艺学美学研究中出现的频度将会减少,这是正常的,历史的推移总是会使那些曾经对人类认识进程及社会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思想变成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但是,我们却不必担心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理想会过时,因为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精神、美学追求、科学方法都将永远为进步人类汲取和珍视,并将成为未来文艺学新建构宝贵的思想资源。笔者认为,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人学精神、人学理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现代化的关键。
一、思想溯源
我们知道,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不少人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只讲斗争和暴力、面目狰狞的理论。声称维护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的庸俗社会学也以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出发点、基本思想面目全非的解释,迎合了这些指责,仿佛马克思主义理论真的是一种不关心人,与人的尘世生活无关的,只是为了获得政治权力和建立某种抽象正义的思辨体系。在不正常的学术生态中,人们不仅讳言、甚至畏言人道主义。这样,马克思主义不讲人道主义的观点也便以讹传讹,流播于学界。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以人为思维中心,关心人的生活质量、注意人的精神需要与美学生成,因而涵容了人道主义的积极因子。笔者认为,要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人学特征,首先应了解马克思文艺学的思想来源。
在马恩直接承受的西方文化传统中,人文精神始终磅礴其间,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思想体系均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程度包容了人道主义。我们知道,费尔巴哈的理论充任了马克思恩格斯由黑格尔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中介。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不是随便地与无所用心地越过这一中介的,他们是携着人类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积极因子,又吸取了费尔巴哈具有浓重民主色彩的人本主义理论到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的。
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构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另一个前提。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有许多批判,甚至认为它的进步意义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但并没有否定空想社会主义者对受尽苦难的劳动大众所表达的深厚的人道同情,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承认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述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内在联系。他们指出:“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1](P167)他们还据此进行推论认为,既然人是从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经验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识与感觉,那就必须这样来安排周围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1](P167)马克思恩格斯称赞空想社会主义者所作的社会批判,认为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中存在着“天才的思想萌芽”。
我们注意到,否定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的人,总是把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贬得一无是处,粗暴地然而也是徒劳地企图割断马克思恩格斯同这些思想家的某些客观存在的思想联系。我们还时常听到这样的议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接受过人道主义思想的影响的,但随着思想的发展,这一影响便逐渐淡化并最终消失。但笔者认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同样是不符合事实的。在写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恩明确指出,他们已经孕育成熟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已经把人规定为“社会化了的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应被人类唾弃,是因为它剥夺了绝大多数人的“一切现实生活的内容”,使之丧失了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一批判的人道主义意味是毋庸置疑的。他们还认为,在扬弃了私有制之后,“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试问,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肉体与人格的摧残,难道不是基于对人的价值的深刻体认吗?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专门设置了对现实的人际关系的非人性质的描述与分析,特别提到了资本对人的情感的亵渎。这与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讨论人的社会联系与文化形式中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的思想实质是一致的,它们因内含浓郁的人道主义精神而发生深层次的契合与共鸣。
综上,使我们得到这样两点认识: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对失衡社会的人道思考而走向共产主义的,他们逐步认识到消灭剥削与压迫,建立平等、自由、共同富裕的社会只有经过坚决的斗争和共产主义进程。第二,这一思想发展轨迹清晰地昭示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融合过程。马恩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中吸收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内容。而这一融合不仅大大加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力度,而且还大大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感召力、吸引力。
二、美学理想
学术界对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误解从反面给了我们许多启发,在笔者看来,马克思文艺学美学的人学特色与人学理想,正是它能够与时俱进,拥有勃勃生机的表征。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包含了他们对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与审美需要的关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时期,压迫与掠夺是那个时代普遍的事实,与社会黑暗的时代特点相适应,他们的文艺思想中充满了对受压迫者的人道同情。他们希望文艺作品能够给劳动群众以温情的慰抚,使后者能够在困顿中保持住生活的信心,勇敢地直面艰难的人生,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好的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积极进行思想启蒙,呼唤建立一种合理的、能够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提供各种条件与机会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基本功能就是“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2](P83)在笔者看来,这样指向鲜明的美学追求最充分地反映出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人学理想。我们可以对马克思恩格斯在美学问题上的个别观点提出质疑,但只要尚存社会良知、尚未泯灭对人类进步的希冀,你就会毫无保留地认同这样的美学理想,而现代文艺学建构也必不能脱离人民大众的审美需要。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基于对文艺审美本质的认识,重视文学艺术的情感表达功能。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3](P231);“激情、热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2](P126)。在他们看来,这种感情是人与人相通的,它能够向人提供富有力量的心理支持,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克服心灵的孤寂和生活磨难的精神力量。当恩格斯发现“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被破坏得差不多了”[3](P231)的时候,这种审美要求就变得愈发地强烈。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中,爱情无疑属于纯粹人类感情的中心部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肯定了当时诗歌对爱情的描写,并对资本主义金钱关系对爱情这一人类最圣洁的情感的侵蚀痛心疾首。
其三,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人学诉求,还鲜明地反映于这一文艺观所确定的艺术评价体系对人类共同价值的尊重与维护。而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只有融入人类整体利益才是有意义和能够指导人们的实践的。我们注意到,出于对艺术审美特征的理解和对人道主义进步取向的认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创始人机敏地在文艺批评中提出了历史与美学的批评原则,并特别表达了他们对施里加、格律恩之流的“党派的”批评的不屑。一段时间里,笔者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的研究独独在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批评的“非党派”原则时,出现失语的现象呢?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是共产党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以他们毕身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实际看,他们似乎也一定会在文学艺术领域提出一整套党派的、阶级的批评标准。然而他们没有、而且不仅没有,相反还明确地表达了对采用这样的标准不予认同的态度,即宁愿选择历史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方法。笔者认为,这其中颇有耐人寻味之处,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尊重人的审美需要、审美情趣的主旨兴许可以成为解开这一理论之谜的锁钥。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作展开,但美学的历史的批评原则这样3个基本特征却是一眼可见的,即美学的历史的方法是尊重艺术规律的批评方法;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反映了马恩对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审美选择的尊重;美学的历史的批评为文化遗产的继承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三、现实启示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人学特性对当代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启示,因为它关涉到文艺学美学的立足之本。笔者认为,美学是研究人与客观世界的审美关系的人文科学。在这里,人的审美需要与艺术审美的终极目的、艺术审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是研究的主轴,而人的审美态度、审美方式、审美能力是研究的重点,两者构成新美学的经纬。总起来看,笔者认为未来文艺学美学的建构,应当在这样几个方面坚持基本的人学立场。
第一,始终把握好学科的发展方向。美学学科的科学性在于它对人与客观世界审美关系的诠解是否符合人的审美实践,是否能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这是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自然科学绝然不同的特点。自然科学是以实践活动在自然物上所起的反应作为验证自己真理性的依据的,而美学理论要以它所指导的艺术审美活动对人的情感与理性所发生的实际效果作为评判的标准。鲍姆嘉通当初在为美学命名时,选用了“埃斯特惕卡”(aesthetica)这个词源学上意为“感觉学”的名字。这一界定,既有主体的“在场”,又有客体的“存在”,大致昭示了今人普遍认同的美学研究的界域,即美学应当讨论人与对象的审美关系。康德的美学思想继承了他的前人定型化了的观点,他为美学确定的目的便是研究美的东西何以让人喜爱。康德的美学研究将人的审美目的性,美的普遍性——共通性作为重点,充分体现了他的美学思想的世俗性质。前辈们的这些论述给了我们许多启发。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4](P9)相信追求彻底是每一个有事业心的美学理论工作者的心愿,为达此目的,必须研究人,研究人的审美感觉,研究形成人的审美感觉的社会条件和历史发展。
第二,增强美学研究的务实性。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在理论研究的形而上思辨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思维主体隐隐地寓示其中的形而下的实际目的。在近年文艺学美学的研究中,一些人执迷于纯思辨的争论,纠缠于与现实审美无关与文艺发展联系甚少的问题,将文艺学学术的发展进程推向与人民大众与审美实践完全脱离的绝地。马克思说:“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4](P31)当德国思想界为黑格尔派的思辨哲学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马克思将人们的眼光引向欧洲的现实——现实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面前,提出了许多关涉人类进步社会发展的紧迫问题,由此推进了认识,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如果说,哲学社会科学必须贴近人的现实生活的话,那么,以人的情感需要和如何最大限度满足这一需要为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美学就更应将自己的目光紧紧地盯着人,研究现实生活的发展及这种发展的心理投影,研究文学艺术在促进人的发展和精神重建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学应当务实,应当在该学科与人民群众生活的联系中寻找新的生长契机。
第三,强化学术研究的使命意识。在对美学史的纵向梳理中,我们还发现,凡是贴近现实、关注人生的美学理论,多半能够产生较大的影响,并为后继者所吸收、借鉴。在美学史上,我们经常能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在美学研究上投入并不太多的学者,由于他们的理论更多地关注人们的现实审美活动,并对之作出了独到的解说,便能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后继者开拓前进的宝贵的思想材料。在这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车尔尼雪夫斯基兴趣广泛,他长期研究社会、从事文学创作,还亲身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他涉足美学并不深,却因提出了“美在生活”的论断而成为美学史上有影响的一家。还有,德国的席勒是以他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席勒还因写出了一本《审美教育书简》而在美学理论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席勒在美学研究方面投入并不多,但他的一本薄薄的《审美教育书简》却以对人的生命存在的重视和对改良人生的急切的期盼,备受美学理论界的关注,成为了解美学理论史的一部必读书。据此,我们是否应当对新美学理论的建构提出切近现实、切近人生的要求呢?我想这应当是没有问题的。文艺学美学的生命在于更加自觉地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我们不应过分沉迷于思辨的光怪陆离与五彩缤纷,而应重视美学在强化文艺的人学效应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学应当更加世俗化,更加切近人生,应当研究艺术作品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研究艺术作品的审美构成,研究欣赏者的需要与构成。只有这样,新美学才能在人们的文化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收稿日期:2001-12-10
